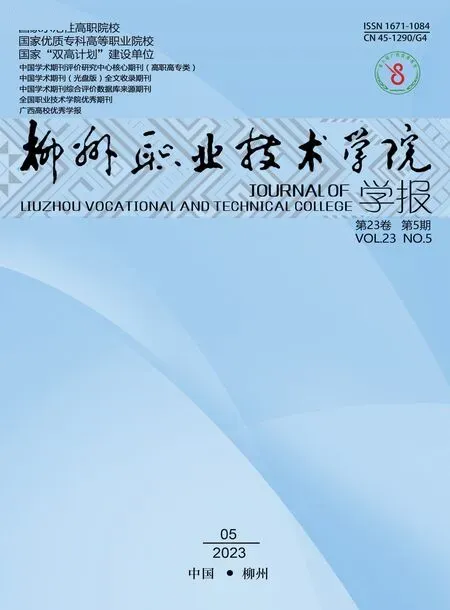张炜《九月寓言》解读:生命本真与历史理性的悲剧性冲突
2023-05-14刘伟
刘 伟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州 350108)
引言
张炜《九月寓言》的发表,对于20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件大事。它令读者日益倦怠麻木的心灵为之一振,因为它触及人类生存的某种本质和永恒的东西。有人认为,在20 世纪末中国文化和人文异常飘浮缺少定准的情境下,张炜试图把文化和生存假象遮蔽下的东西清晰地呈现出来,为读者提供可以想象的生存的稳定感和家园的归属感。不少人拿张炜散文《融入野地》(《九月寓言》代后记)作为一把“解剖刀”来分析《九月寓言》,认为它是在抒写张炜寻家的情急和归家的喜悦。显然,《融入野地》直抒了张炜渴望家园的理想,对于个体生命和灵魂而言,或许登州海角的一间小屋便可容纳了,而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归宿,这是一个远为复杂艰难的问题。张炜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故在小说的结尾处,象征家园的野地在一片火光中被焚毁了。实质上,张炜所维护的“大地”的原生态之美,是一个正在消逝而且无法挽回的稚纯想念。《九月寓言》的主旨在于呈现给读者一个人类生存的走向问题:日暮乡关何处是?所以,与其说张炜的《九月寓言》是对民间本真生存图景的一次诗性挽留,不如说它呈现了人类生存与历史发展冲突的某种必然性命运;与其说是抒发诗人寻家的情急与归家的喜悦,不如说是在叙写一支家园失落的挽歌。一言蔽之,《九月寓言》是呈现时代变革特征的寓言。
一、时空演进中的悲剧意象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象征符号美学的奠基人恩斯特·卡西尔在论“人类的空间与时间世界”中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它的尺度——而这些尺度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每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总是有自己对时空独特的感知方式,正是在这种对时空的充分个性化的感知方式中,凝聚着这个作家对生命、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即读者能通过作家对时空的感知方式和表现方式,从而把握主体的心理体验的深度[2]。因此,对《九月寓言》“时空”形式与意象形态的解读,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九月寓言》里,张炜把“融入野地”的时间选择在“九月”,并且反反复复地把抒情的目标指向“秋天”和“大地”,这是有其深味的:“秋天”(九月)和“大地”是进入《九月寓言》的切口。在《九月寓言》中,“秋”难道仅仅是一个季节吗?九月对于小村人来说,是亲如爹娘的——“难忘的九月啊,让人流泪流汗的九月啊,我的亲如爹娘的九月啊!”,而张炜在《融入野地》里说,之所以把“融入野地”的时间选在“一个五谷丰登的季节——九月”,是因为“被饥困折磨久了”。这二者之间显然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张炜对“秋”的体悟,似乎与西方原型批评家弗莱在古代神话和寓言中关于季节圆周弧线上秋天象征悲剧的结论是相抵触的。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它最充分地展示了大地的奉献,九月把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明确地揭示出来:大地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人与万物的本原。“天”与“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父母”。显然,张炜把“天地”视为《九月寓言》中“鲜廷鲅”们(小村的名字,意思是“停吧”)生命的源泉和落定的归所。然而张炜又说,“秋天是一个喜剧,也是一个悲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它令人联想到日本人在樱花烂漫时节的悲春(悲叹生命的美丽与短暂的感伤)意识,以及中国文人精神中普泛着的悲秋意识。“秋”是生命季节最辉煌的时刻,亦是走向霜雪逼人、衰败死亡的开端。《九月寓言》中“鲜廷鲅”们即在“秋天”与“大地”的时空演进中演绎着生命从丰沛走向衰微,生活从诗意栖居走向家园失落的悲剧性命运。
“大地”这一象征意象,是张炜在《九月寓言》中确立的抒情核心意象,具体为“鲜廷鲅”的家园——村庄与土地的指称,象征着人类命运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艺术的本质是诗,有无核心意象,是一部作品是否诗化的标志之一。诗性与抒情品格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有特征。在过去的许多小说中,乃至当下的不少作品中,作家的智力分析多于体验,反对情感的语言理性力量显得过于强烈,它拒绝人性的温度和诗意的关怀,感动的力量消失了,艺术只剩下分析的力量,那么艺术会渐渐失去抒情性,然而张炜在深情的追忆中坚持了诗性的艺术立场。在《九月寓言》中,张炜炽热渲染抒写大地,咏叹式的抒情将个体丰富的文化底蕴融入广阔的艺术基础——“大地”中。于是大地具有多层意蕴:大地意味着赖以生存的土地,万物由此出现,大地又指涉着精神空间的家园,万物也由此返回,大地作为润泽万物的生息命脉,为万物提供生存的稳定感和家园归属感。《九月寓言》结构的母本〔以肥(小村的幸存者、见证者)的出走返回为结构〕正是一个出走与回返的寻找过程。《九月寓言》在秋天、人、万物与大地之间负载和呈现的人类生存状态,实际上是建立起一个虚幻的预言。《九月寓言》之所以具有那样强烈的情感着迷点和艺术的凝聚力,是因为一切抒情指向了这一巨大的幻象。
二、追思缅怀里的栖居家园
人们对叙事文学的阅读,通常都是从对故事的期待开始的。事件、人物只有通过叙述者的讲述才能被读者感知。没有叙述者这个陈述行为主体,就没有事件或人物这些陈述内容。这并非意味着叙述者只是简单地承担陈述行为,只有呈现事物和人物的功能,只是一种媒介或者工具。实际上,叙述者不仅在陈述事件和命名人物,还在“参与”故事。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叙述者的作用被感知的程度,叙述者的可靠性,都干预、影响着事件和人物[3]。由此可见,叙述者的“叙述视点”在文本中显得尤为重要。
“老年人的叙说,既细腻又动听”——《九月寓言》的题辞已确立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基调:一种追思,一种缅怀。这种追思和缅怀是通过肥和挺芳的叙说体现的,他们于许多年后重返已经被毁而荒废了的小村遗址,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开始对村庄往事的历史追叙,来呈现小村整个的生活图景。张炜在作品中采取了自由的“散点式”结构凝聚时空,作品的七个章节无主次之分和必然的因果关系,时空的模糊性与交叉性贯穿完整的生活世界,并以寓言的方式圆环起源、过程与结尾。“大地”——家园随着叙述的展开趋于到场:敞开、呈现、归闭。对生活的还原结果便是存在的呈现,即把乡村本真的生活状态全面呈现出来。随着乡村本真生活图景的呈现,“大地”的存在被“带出”,“大地”与人的原初关系被“带出”。
(一)“大地”——诗意的栖居地
土地是小村人繁衍生息、耕耘稼穑的乐园。于脚下的土地,小村人享有“独特的、真正的快乐”。瓜干以饱食的物质滋养人的生命,它将这一方土地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一起,处处流淌着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幸福感。于是读者看到了理想化、虚饰化的田野牧歌:年轻人被赖于自然而生长的火红的地瓜所燃烧旺盛的激情而感染,他们游荡于夜幕下的野地里,任情任性而肆意妄为地欢乐闹腾。
张炜痴迷眷恋的“九月”,是这九月的纯化月夜,是月光倾泻的野地上“鲜廷鲅”们吃饱地瓜尽情嬉戏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充盈生命。浓浓的夜色是对白天一切辛劳的抚慰。夜的中心,乃是大地的中心。在夜色的覆盖下,疯长的茅草葛藤,满泊野物吱吱叫唤,山山水水,草响虫唱,无拘无束,生命活力充分流露在这诗意盎然的世界里,尤其是露筋与闪婆的爱情。他们在野地里相爱流浪,幕天席地,以野物野果为食,许多年在野地里奔腾流畅,充满魅力的幸福时光更为野地增添了浪漫色彩。
小村的“鲜廷鲅”们接受着大地精神无言的抚慰,从而充沛恣肆地倾泄人在天空下大地上行走歌哭时那份丰厚的生气和至悦,是一种真正诗意的栖居。
(二)“大地”——安抚灵魂之所
土地不仅以它的丰厚滋养着小村,带给小村无限的欢乐,还以它宽阔的柔怀消解小村更多的苦难,是小村苦难灵魂得以安抚之所。
小村人的生活是充满苦难的。他们的祖先是一群流浪汉,颠沛流离,受尽屈辱和痛苦的折磨,因为实在倦乏于漂泊,不约而同听从了“停吧,停吧”的内心吁求,才在这里驻留下来,生存繁衍后代,故被人称为“鲜廷鲅”——一种剧毒的鱼类。当下,他们还要忍受外村人的歧视、种族延续危机的苦难,还有夜晚小村的野蛮恶俗景象:对妻施暴、虐待儿媳、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田野打斗等。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历史上的苦难,在叙述者的讲述中变成了一种诗意的诉说,沉迷于毫无禁忌的“忆苦”述说中,小村的“鲜廷鲅”们甚至获得了精神上狂欢式的愉悦,在历史感中失却了现实感的记忆。如第二章的金祥寻“宝”一段,更是把漂泊经历幻作趣味与魅力的精神饱餐,金祥也因此成为小村人的普罗米修斯。叙述者为什么如此美好地叙说亲人的苦难?“忆苦”活动为什么反成为小村人盛大的节日?所叙所忆的苦难为什么不再叫人痛定思痛,哀伤欲绝?无尽苦涩的往昔似乎成了酝酿诗情的温床,成了苦难经受者家园精神的纽带,心理空间得到安定和满足。读者终于发现了苦难的转换机制——大地。大地消融了苦难,消融了人类的悲剧。小村人之所以能体认苦难,超越苦难,是因为人间的恶浊之气都被开放无私的天地所吸纳消泯,尽管有磨难、穷苦和疑惧,但大地与夜幕间藏蕴着的无穷的不可言喻的愉悦消弭了这一切,大地成了苦难灵魂的安抚之所。因为有了栖居的家园,有了大地的承载和依托,“鲜廷鲅”们有一种“在家感”,一种“落定感”,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是“尽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的”,所受的伤痛在野地里愈合。
三、冲突抗争中的家园失落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复调小说突破了独白型小说模式,它是多声部的、“全面对话”的小说。“对话主义”已成为巴赫金方法论精髓的代名词[4]。在《九月寓言》中,“地上有一个村庄,地下也有个村庄”,地上地下一明一暗两个村庄的此衰彼兴,实际构成了小说一显一隐的复调结构。
《九月寓言》中的乡村世界是封闭、凝滞的,然而现代文明也在一步一步侵入这一块“世袭领土”。小村人生存的“伊甸园”——那一片纯净甜美的野地在一日日被污染,一日日被毁损。在象征地上村庄的农业文明和代表地下村庄的工业文明的此衰彼兴中,小村一天天被掏空了地基,在一步步走向毁灭。坚定自足的“鲜廷鲅”们虽充满激情与韧性,却终究是无望又无谓地坚守,乡村世界的最后消失恰是工业文明造成的结果。
再看乡村人与工区人的冲突与抗争。在这二者的抗争中,小村人的心理是充满矛盾的。他们在闭守的环境里并不满足仅仅圈囿于小村,于是当工区“入侵”小村后,他们对于工区任何一件事物充满既羡慕又排斥的心态,潜意识里渴求工区的黑面馅饼、胶筒皮靴、澡堂、手帕、琴等新鲜事物,但又本能地去诋毁这些事物,甚至工区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带给他们精神生态的迷惘。诱惑与抵抗同时存在,而结局以小村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是一种精神的毁灭。美丽健壮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赶婴,因受秃顶工程师的亵渎而从此“水灵气被吸光了”,蒙受屈辱的心灵充满着失意惆怅和忧伤,“我变成了一具徒有其形的冰雕……”,赶婴独自喃喃,“看不到边的野地,我去哪儿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黯然神伤的?!三兰子被语言学家遗弃,也遭到小村人的唾弃,被大脚肥肩折磨,落得惨死的结局。三兰子是一个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同时又是香碗与争年爱情悲剧的制造者,由于她的介入,活活拆散了一对不幸的情人,以致香碗“从此没有眼泪了”,争年成了一个呆子。肥目睹了这些爱情悲剧后与挺芳私奔了,从此背离家园,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儿”。少白头龙眼被压进了地底,欢业杀死金友之后逃走,重新踏上流浪之途,溯着祖先的足迹回到了源头,这是人类流浪生命的轮回。
小村在电闪雷鸣、房屋倒塌中灰飞烟灭。现实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都不复存在了,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宿命逃不开永恒的二律背反,贫穷饥馑连同农业文明“遗失的美好”在历史的悖论中崩塌。《九月寓言》的悲剧性结局令人联想到《红楼梦》的结局,雷鸣电闪,房屋倒塌,一个村庄变成一片废墟,与《红楼梦》中的“落得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似有某种谋合,《九月寓言》中一群女孩子的命运与《红楼梦》中一群女孩子的命运也似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张炜说:“女人的命运如何,更能看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性质,它是否是一个尊重人的时代,是否是一个温和宽厚的时代。”[5]或许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表达了一种世纪末的情绪。
张炜的《九月寓言》所呈现的仅仅是乡村命运吗?显然它是带有某种人类性的意义,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张炜只是借助乡村生活的一个个片段来含蓄、委婉地表达工业文明扩张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焦虑。张炜以苦涩、睿智和全面的反讽态度来看待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不见轻蔑感和盲目的偶像崇拜,而是带着真诚的渴望,提炼新的意义,与过时的观念与偏见进行辩论[6]。
四、结语
神话原(Mythoi)是在文学意象世界循环运动中凝成的基本要素,它们是在逻辑上先于体裁的文学叙述程式、叙述结构或叙述模式。弗莱认为文学叙述模式从总体上看是对自然循环运动的模仿,如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潮流涨落等等。弗莱把四种神话原(或叙述模式)与文学的四大类型统一起来,即喜剧是春天的神话原,浪漫传奇是夏天的神话原,悲剧是秋天的神话原,反讽和讽刺是冬天的神话原[3]。从一开始,《九月寓言》的主旨和审美观照即在于上演一出秋天、黄昏、日落、生命衰亡的悲剧。
悲剧是什么?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意识的凸显依靠的是其内在结构的二元对抗,矛盾双方冲突、抗争,一般的结局是居于强势的一方摧毁处于弱势的一方。在中国悲剧模式中,一般有悲剧的肇事者,但因其邪恶得到指证,这也就削弱了悲剧的力量。《九月寓言》的悲剧性高潮竟以一场壮美的焚化告终,令人感动亦令人深思。诗人把城乡、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冲突推到极致,亦把抒情的力量推向高潮,所以这一场悲剧的推动力量是非人化的力量,是凌驾于人之上的。在这场人类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冲突中,人处于弱势,必然要付出毁灭与牺牲的代价,由此可见这种悲剧的冰冷性。《九月寓言》悲剧性结局的诗化处理,哀而不伤,相对于激愤,它给予读者的感受更多的是凝重,是一种情感的节制,这种节制令读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