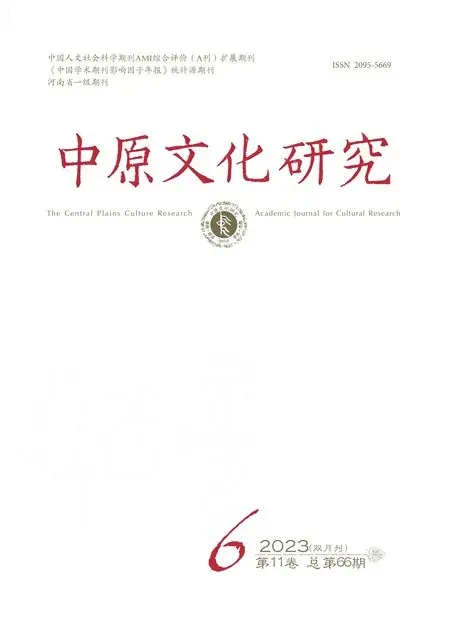“齐气”说及其文学地理批评范式新探
2023-05-12陶礼天
陶礼天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其论述逻辑非常严谨而紧密,从批评“文人相轻”发端,充分论证“文非一体”而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非是“通才”而“鲜能备善”,通过强调作家多为“偏才”而提出重视文学创作个性的理论,从而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949。这就比前人更为明确、突出而且更有理论系统性地提出文体批评方法;又以建安七子及其创作作为案例批评,具体说明作家如何各有其个性、各有其长短,进而由此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文气”说。《典论·论文》中评孔融的“体气”说、评徐幹的“齐气”说等,都可以视为其“文气”说的内容。曹丕通过“文气”说主张作家的气质个性是形成各自独特风格的主体原因,并明确说明作家作品的“文气”,可以分为“清”和“浊”两大类,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说[2]505和“缀虑裁篇,务盈守气”“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风骨”论[2]513-514。曹丕“文以气为主”说,实际是从才性批评的角度,张扬了创作个性的意义,是故接着论述作家个人“立言”的不朽价值,其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既包括“四科八体”的作品,也更强调如徐幹《中论》那样“成一家言”的子书专著。这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包括所有文体的文章,简称谓之“文”。从文学批评立场看,上述的文体批评、才性批评、论建安七子作家作品的经典批评等,无不具有范式意义,对其后特别如《文心雕龙》等杰出文论著作的文学批评范式、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通过研究,对曹丕《典论·论文》“齐气”说作出新的探讨,首先简要交代曹丕《典论·论文》“齐气”说解释争议之问题的由来,并基本认同《文选》李善的注解,认为曹丕提出的“齐气”说,可以直接视为文学地理批评,而且具有范式意义,并对其后如《文心雕龙》等文论论著中有关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其次,结合班固《诗经·齐风》具有“舒缓之体”之说,进一步从文学地理批评角度,论述曹丕《典论·论文》“齐气”说的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讨论刘勰和锺嵘关于徐幹与王粲的比较评论,二是以东汉李巡《尔雅》注所谓“齐其气清舒”和刘熙《释名》所谓徐州“土气舒缓”等解释,指出曹丕“齐气”说作为文学地理批评的渊源与依据;最后,简要分析曹丕“齐气”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学地理批评,具有怎样的范式意义。
一、“齐气”解释争议问题之由来与辨正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徐幹时有齐气”说,李善《文选》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此亦其舒缓之体也。”《文选》五臣注:“翰(李周翰)曰:齐俗文体舒缓,言徐幹文章时有缓气,然亦是粲之俦也。”[1]948此后,关于“齐气”历来从李善注,少有质疑;文字上也不从《三国志》《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作“徐幹时有逸气”。1948 年范宁发表《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一文,以某本《初学记》(今不详何本)“齐气”作“高气”为据,力主《文选》本为误①。其后众说纷纭,或以为文字有误,或以为李善误注,或从李善注并加以补正,还涉及相关诸多问题的讨论,迄今仅发表的单篇论文就有20 多篇,这里不遑细说。
《文心雕龙·风骨》说: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514
可见,《文选》选录的曹丕《典论·论文》作徐幹“时有齐气”,文字不误,《文心雕龙》引文作“齐气”,可谓铁证。《文心雕龙》诸多版本中,唯有元至正本和明弘治本作“济气”,明显乃“齐气”之误②。而李善对“齐气”注解,基本为正解,并无大误。因为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立场看,曹丕的“齐气”说,属于文学地理批评,是对其前的《诗经》《楚辞》的文学地理批评的直接继承,也是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地域文化观和《汉书·地理志》“以诗证史”的方法与观念的继承。只是这方面的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渊源与批评传承,或显或隐,需要深入挖掘才能阐明。
李善拈出曹丕《典论·论文》“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一句中“斯累”一词,认为曹丕意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使“齐气”成为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的批评,应不符合曹丕原意。因为即使曹丕确实如黄侃所言“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3],那么,曹丕之前,班固《汉书·地理志》说《诗经》之《齐风》具有“舒缓之体”的思想艺术特征,亦并非贬义;何况从曹丕存世作品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评:“子桓虑详而力缓”[2]700,徐幹在“力缓”方面与曹丕较为类同,结合其二人传世作品,不难得到实证。是故李善的“斯累”之说和黄侃“以齐气为嫌”之论,当难以成立。因为“文帝《论文》主于遒健”的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故以齐气为嫌”的结论。如《文心雕龙·乐府》说:“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2]101这里的“齐楚之气”,仅为关于乐府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的表达,亦不妨直接视为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亦无褒贬之义。“齐楚之气”即是“齐气”和“楚气”,分别指齐地和楚地的土风。曹丕《典论·论文》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聘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1]948
这里列举建安七子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代表作家,采用的是史传常用的书写格式,就是介绍每一位作家的籍贯、名与字。表面上看,这是史家叙事“惯例”的袭用,也是日常生活中介绍人物的习惯,但实际上却是别有深意。这个“深意”就是因为下文要评论每一位的所长所短,而每位作家的所长所短和创作个性、作品风格的文气“清浊”,又与作家所来自的文化地域(作家的籍贯所属之地)乃至与其流寓之地(文化地域)具有密切关系,虽然曹丕仅指出徐幹“时有齐气”,是与其来自“齐地”有关,对其他作家都没有论及,但已足以成为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之范式。这应是与齐文化和《齐风》具有突出鲜明特点有关,而徐幹又具有这样的特点,曹丕才作如此的论述,这是在前人相关表述的基础上熔铸出“齐气”一词,也可以说提出了文学批评上的“齐气”说。这本身在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不能用难道齐地的作家都具有这种“文体舒缓”的“齐气”特点加以反驳,而认为如果这样认为就逻辑不通;因为曹丕并没有说,齐地的作家都如徐幹具有“齐气”。
这七子的籍贯简要统计说明如下:鲁国孔融文举,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第二十世孙;广陵陈琳孔璋,广陵射阳人,今江苏扬州市宝应县,属江淮之间,其北为淮安市③;山阳王粲仲宣,山阳高平人,在今山东济宁市邹城西南,位于山东西南部,属鲁文化区④;北海徐幹伟长,北海剧人,今属山东潍坊市寒亭区,该区朱里镇汇泉庄东有徐幹墓,属齐文化区⑤;陈留阮瑀元瑜,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位于河淮之间的河南中东部平原地区,西邻新郑,春秋时为郑国别狱所在地;汝南应玚德琏,汝南南顿人,汉代南顿县治在今河南项城市西部的南顿镇,位于颍水与汝水之间的河南中东部,属于汝颍文化地域;东平刘桢公幹,东平国人,今属山东泰安市宁阳县,位于山东中西部,属鲁文化区⑥。
其中,今属山东者4 人:孔融、王粲、刘桢和徐幹,前三者属鲁文化区人,唯徐幹属齐文化区人;今属河南者2 人:阮瑀、应玚;今属江苏扬州市者1 人,陈琳。其中值得特别说明者三人:孔融曾为齐地的北海国相6 年,东汉北海国的都城在今山东寿光市(属潍坊市管的县级市)东南;陈琳大约于汉少帝刘辩时期,在京城长安为何进主簿,后避乱奔冀州袁绍,其后归顺曹操,属于由南入北的文人;王粲14 岁随父居长安,16岁与族兄王凯从长安到荆州避乱,投奔刘表,32岁劝刘表之子刘琮一起归顺曹操,属于建安七子中年少时即由北入南流寓荆州16 年的著名作家。三国曹魏时期,作家以北方人为主,可以做出详细的统计,这就是当时的文学地图,此处暂不详细罗列说明。曹丕《典论·论文》接着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园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1]948-949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对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徐幹时有齐气”的“齐气”一语,作了详细注释,论述很重要,现抄录如下:
齐气——黄叔琳评《文心雕龙·风骨》说:“气是风骨之本。”气在于作家谓之气,形之文者谓之风骨。所以纪昀的评进一步指出:“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文选学》引黄侃说:“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刘文典《三馀札记》:“《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作‘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典案《文心雕龙·风骨篇》作‘时有齐气’,与《文选》合。《艺文类聚》五十三引无非字,余与《王粲传》注引文同。李注翰(李周翰)注并以齐俗文体舒缓释之,亦是望文生义,曲为之解耳。魏文帝《与吴质书》:‘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虽言逸气,然谓刘桢,非徐幹也。”案:李注有根据,并非望文生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公子札来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服虔注:“泱泱,舒缓深远,有太和之意。”这是说齐诗有舒缓的风格。《汉书·朱博传》说:齐部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论衡·率性》:“楚越之人处庄岳(齐街里名)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这都是说舒缓是齐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是齐气为舒缓的铁证。由于齐俗舒缓的生活环境,影响到作家的个性和作品风格。所以说“徐幹时有齐气”。逸气是赞美之辞,齐气乃是不足之称。所以本文于“时有齐气”一句之后,又来一转笔,说“然粲之匹也”。《魏志》注引作逸气,所以下一句转笔作“然非粲匹也”。李善注符合文义。《文心雕龙·风骨》:“故魏文……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以齐气与逸气分别属于徐、刘二人,则本文当依《文选》作齐气为是。[4]
这里对本文认为曹丕的“齐气”说就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并且具有一种范式意义,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分析说明如下:第一,结合刘文典的研究和《文心雕龙·风骨》篇的引文等文献,论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徐幹时有齐气”一句评论的文字,没有错误;第二,《文选》李善注释“徐幹时有齐气”,以“齐俗文体舒缓释之”,“符合文义”,并非如刘文典批评的那样是“望文生义,曲为之解”[5];第三,在李善引《汉书·地理志》举《齐风》说明“此亦其舒缓之体也”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更多文献资料,论证说明:“舒缓是齐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是齐气舒缓的铁证。由于齐俗舒缓的生活环境,影响到作家的个性和作品风格。所以说‘徐幹时有齐气’。”问题由来已经说明,并且谈了本文的思考与论述主旨,说明“徐幹时有齐气”是指其如《齐风》一样的“文体舒缓”,有“缓气”的艺术特征、风格倾向[6],那么下文就接着对《齐风》具有怎样的“舒缓”特点,尝试加以分析。
二、《齐风》“文体舒缓”臆诠
《诗经》中的《齐风》属于当时“北方文学”的东区,共11 篇。《史记·货殖列传》云: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7]
齐国富甲东海,士农工商贾五民皆有,文化风气较为开放,为道家、法家的兴盛之地。吴公子季札在鲁观齐乐云:“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8]1098季札有可能是从齐国霸主的实际政治地位着眼品评的,上文录《中国历代文论选》注“齐气”引《左传》服虔注云:“泱泱,舒缓深远,有太和之意。”所谓“太和”主要就是自然平和之意。
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谓“舒缓之体”,或还有夸诞之气。但必须指明的是,服虔所谓“深远”,有“太和之意”与班固所论并不完全相合。我们诵读流传至今的《诗经》中《齐风》11 篇歌诗,较难体会季札说的“国未可量”和服虔说的“太和之意”。因为读诗与观乐,其感受不可能全然相同,一偏重于声而一偏重于辞义之故,我们即使吟诵时,不顾其诗“义”而专听其吟诵之“声”,那也不过是吟诵的一种语调,每个人的吟诵与体会也自会不同。既然如此,他们说的“舒缓深远”和“舒缓之体”,除了根据季札观乐的评论等文献史料记载外,主要还是根据齐风诗歌的文本作出的判断。
盖风诗是入乐的,是歌词,是与当时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一起来歌唱的。如果说齐风的乐调是泱泱舒缓的,那么在歌词中多少有所反映;如果服虔说的“太和之意”就是指他前面说的“舒缓深远”,那么今天读这流传下来的《齐风》11 首诗,至少是在班固所举的《还》和《著》中还可以有所体会。下文将结合具体作品,稍作分析。
《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三诗,据《毛诗》小传,是讽刺文姜通于齐侯的[9]340-345,既表现了齐国上层统治者的豪奢与放荡,也侧面表现了当地士人“足智,好议论”的风气。这种“宽缓阔达”的“齐气”,主要表现为文辞上善于夸饰,句尾多缀虚词;节奏上较为疏宕(乃至松散),不太注重物色的细致描写。例如《还》《猗嗟》二篇,几乎每句加一个“兮”字,前者写两个猎人的互相赞美,后者赞扬一个少年的美貌与射技。句句缀一虚词“兮”字,令人吟之、听之感觉到其言辞的夸张和文气的疏放。《汉书·地理志》云: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10]
班固举证齐风的《还》《著》两首风诗,作为“舒缓之体”的代表,正是从齐人的“舒缓阔达而足智”推论至齐风的“舒缓之体”的。《毛诗》说:“《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诗三章,章四句: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9]331-332
《毛诗正义》:“还,便捷之貌。峱,山名。笺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猎而相遭也。峱,乃刀反,《说文》云:‘峱山,在齐。’崔《集注》本作‘嶩’。”[9]331孔颖达正义云:
国人以君好田猎,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归说其事。此陈其辞也。我本在田,语子曰:子之便捷还然兮。当尔之时,遭值我于峱山之间兮,于是子即与我并行驱马逐两肩兽兮,子又揖耦我,谓我甚儇利兮。聚说田事,以为戏乐,而荒废政事,故刺之。[9]331
可见齐士大夫们舒缓阔达,喜好“戏乐”而不务实事的风气。班固的意思,似乎还兼顾“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以及“俟我于著乎而”所表达出的民俗风气(生活习气);也就是说,顾及其表现的内容和表现这种内容的形式这两个方面来论说“舒缓之体”。齐风《著》诗云: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9]332-335
著,“门屏之间曰著”。《毛诗》小传认为:“《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郑笺云:“时不亲迎,故陈亲迎之礼以刺之。”[9]332《著》是写一个贵族女子等待新郎迎娶的情景。三章九句,全诗只有“著”“庭”“堂”“素”“青”“黄”六个字不同,且每句句末缀两个虚词“乎而”,来表现她的期盼之情,回环往复,咏叹有余,疏缓有致。总体而言,《还》与《著》之间的区别不大,而这两首诗确实是《齐风》中较为典型的“舒缓之体”。班固所举的这两首中的三句诗,吟唱起来的节奏,感觉该是:“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俟我—于著—乎而”。按照这样的节奏,我们今天吟起来、听起来也觉得是“舒缓”的。因为在古汉语中,“之乎者也”等虚词是起到句读作用的。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解释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正义云:“先儒以为季札所言,观其诗辞而知,故杜显而异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声也。《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长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诗为章,则人之情意,更复发见于乐之音声。出言为诗,各述己情。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神瞽、大贤师旷、季札之徒,其当有以知其趣也。”[8]1096本节所析,或有臆断,然“出言为诗,各述己情。声能写情,情皆可见”。音声与歌诗之间必然存在一定联系,所析仅为说明本文讨论之问题而已。
三、从徐幹与王粲比较中提出的“齐气”说
曹丕的“齐气”说,是在徐幹与王粲创作个性的比较中提出的,探讨曹丕“齐气”说的内涵,应该要特别注意徐幹与王粲的比较研究,注意与六朝人关于此二人的一些评论结合起来加以考辨,如刘勰、锺嵘等相关论述。前文已经引过《典论·论文》所论:“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园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曹丕在此说王粲与徐幹“然于他文,未能称是”,这句话容易使人误解或生出歧义,故先解释一下:这里的“他文”不包括成一家之言的“专著”,如徐幹的子书《中论》;“未能称是”意谓(在曹丕看来)王粲与徐幹的各类文体作品中,以其辞赋创作水平最高,而并不是说这二人的诗歌等其他文体的创作水平都不好、都不如别人。这段评论的开头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王粲很擅长创作辞赋,徐幹亦擅长创作辞赋,虽然徐幹时有“齐气”,与王粲作品所表现的才性气质、风格不同,但仍然可与王粲相匹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徐幹时有齐气”这句话,显然应该理解为不仅是徐幹的辞赋作品,而是他的所有作品都具有“齐气”的特点。“时有齐气”之“时”字,虽然解释为“有时”可通,但结合徐幹的性情与人品,解释为“时常”,更符合逻辑。“时常”具有“齐气”,仍然是包含“有时”没有“齐气”的内涵。这正可以解释《文心雕龙·诠赋》篇所谓“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2]135,刘勰用的是正对,王粲和徐幹的赋都有遒壮有力的一面。所谓“时逢壮采”,这个“时”字表明其反面就是“时无壮采”,也就是“时有齐气”。
刘勰《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以“才性”为主要方法。评王粲,《明诗》篇谓他与曹植能够做到“兼善”,即能备“雅”“润”“清”“丽”诸特点,超过其他诗人[2]67;《杂文》篇谓“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2]255;《论说》篇谓“仲宣之《去伐》”,与嵇康《声无哀乐论》等一样,“师心独见,锋颖精密”[2]317;《神思》篇谓“仲宣举笔似宿构”,虽“似宿构”之作与曹植、祢衡等人的一些作品相若,是快捷而成的短篇,但亦“思之速也”[2]494;《体性》篇谓“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2]506;《才略》篇谓“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2]700;《程器》篇亦谓“仲宣轻脆以躁竞”[2]719。评徐幹,除《诠赋》篇所谓“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和《才略》篇所谓“徐幹以赋论标美”外,《程器》篇谓“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2]719;《哀吊》篇谓“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2]240。另外,锺嵘《诗品》列王粲于上品,评语却说:“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11]37又列徐幹在下品说:“白马与陈思赠答,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叩钟’,亦能闲雅矣。”[11]129虽然“以莛叩钟”之评属于锺嵘的个人意见,并不恰当,但特别指出徐幹五言诗具有“闲雅”的品格,与曹丕的“齐气”之说具有一致性。综述所引刘勰、锺嵘对王粲、徐幹的评论,至少有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王粲、徐幹他们各自不同文体以及同一种文体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特色都有不同;王粲和徐幹都擅长赋和论,刘勰认为王粲的赋作,发篇遒劲,铺叙细密,也善于辨析事理,其“论”体文,善于立意,思想锋利而逻辑严密;对王粲和徐幹诗作的评论,刘勰与锺嵘的意见不同,但大体定位还是较为一致的。刘勰含其赋作一起评王粲为“七子之冠冕”,锺嵘专论诗歌,亦定位王粲为上品,只是锺嵘更崇尚曹植,故置王粲于曹植之后;刘勰认为徐幹也擅长赋和论,所谓“以赋论标美”,但是大概刘勰认为徐幹的诗写得不如王粲的好,锺嵘也仅列徐幹在下品,远不及刘桢,但能够“闲雅”。
二是“躁竞”“躁锐”本指王粲之性格。就才性而言,王粲性情“躁锐”(性急而思锐)而才高,突出表现在其为文快捷、落笔果断,而又能思致绵密,语言亦佳,很少有文辞表达上的瑕疵;而徐幹不仅诗格“闲雅”而且性情亦“闲雅”,人品温和端正、“沉默”深沉而不议论是非,在创作上徐幹善于表现“哀辞”(善于叙悲),在建安文人中,这一点比较突出。
三是才性和作品直接相关。总体上看来,王粲的赋作遒劲有力与他的性情(侧重在“性”而同时说明其“才”亦高)相关者多,而徐幹的赋作虽能“时逢壮采”,但主要与他“博通”的才华有关,其性情如“沉默”、善于体会悲哀之情等,却不适合于创作“壮”“遒”之风格的作品。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北海人徐幹赋作由于其个性原因而有不遒壮(也不够紧密)的一面,这是与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相契的,也是与李善把“齐气”解释为“舒缓之体”相一致的。刘勰《体性》谓“仲宣躁锐”,《程器》谓“仲宣轻脆以躁竞”,刘勰所论本于史书《三国志》及裴注,其性情气质(性格)之“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其性情气质在道德品性方面表现出的与别人“竞”于名利,或可谓不如徐幹之纯粹;第二,是指其性情气质在行为言语上表现出的率直而不深沉。刘勰据此而论文学创作之才性问题。《三国志·魏书·杜袭传》云:“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恰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恰、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恰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12]666《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云: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注谓:“貌寝,谓貌负其实也。通侻者,简易也。”[12]598并叙及“陈留路粹”文下,裴注引鱼豢转引韦仲将(诞)话说:“仲宣伤于肥憨。”[12]604《三国志·魏书·锺会传》裴注引《博物记》云:“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12]796总之,王粲大概矮小而憨胖,且体质不强壮,但性格急躁,任性率为,不如徐幹那样性情“沉默”。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王粲率躁见嫌”[13],此正可与“沉默”的徐幹相匹对。
总之,徐幹性情有齐人之“宽缓”(司马迁的用词),而故有“舒缓之体”的“齐气”,与王粲“躁竞”不同;但其“博通”,虽“时有齐气”,亦“时逢壮采”,擅长“赋”和“论”,可以与王粲相匹敌。
四、曹丕“齐气”说与《尚书》之《禹贡》地理学
《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对曹丕《典论·论文》“齐气”一词有很精到的注释,已如前引,其中主要论及徐幹之“齐气”源于齐地人的舒缓生活习气。但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学界似未关注到曹丕“齐气”说与《禹贡》学“九州之气”说的关系。
实际上,曹丕“齐气”说不仅与班固《汉书·地理志》谓《齐诗》(即《诗经》之《齐风》)有“舒缓之体”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点,《文选》李善注已经予以明确揭示;还可以从东汉李巡《尔雅》注和刘熙《释名》有关解释看其与《禹贡》学“九州之气”说的关系。班固、李巡、刘熙有关论述,都属于《禹贡》之学,其间具有一脉相承的知识与“观念”。理解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皆与《禹贡》学(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学术内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曹丕“齐气”说亦是如此。李巡《尔雅注》已佚,在唐陆德明《尔雅音义》(《经典释文》)之《释地》篇有其关于“九州之气”的注文⑦;其后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亦有引用李巡注文(见庄公十年),较陆德明引文为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等亦有引录,但“齐曰营州”的注文中,缺引李巡之注;清扬州人黄奭有《尔雅李巡注》辑本一卷(见《汉学堂经解》),此不赘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刘熙《释名》(《释名疏证补》)中有补辑:“《公羊疏》引李巡注《尔雅》云:‘齐其气清舒,受性平均,故曰营。营,平也。’今为青州。”[14]51《典论·论文》“齐气”之熔铸成词,盖是脱胎于李巡《尔雅》注所谓“齐其气清舒”等说。
刘熙,字成国,北海人,灵帝时曾任南安太守,建安初避乱至交趾,所撰《释名》,历来被誉为与《尔雅》《说文解字》并列的三大辞书。曹丕是否见到该著虽不可确证,但由此书可以了解曹丕那个历史时期有关“齐气”说相关问题的共同认识,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释名》卷二《释州国》,与《尔雅》“九州”的解释,都是本于《禹贡》之学。先释十三州名,再释十三国名,又释十八郡名,这些“名称”都与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土壤气候、地理方位、天文分野等)或与“事宜”(文化习俗、政教礼制或人情物理等)有关,如云:“青州在东,取物生而青也。州,注也,郡国所注仰也。”又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如此等等。其中与这里要说的问题直接相关者,为释“徐州”“豫州”“荆州”之州名和“鲁”“越”之国名等。其谓“徐州。徐,舒也,土气舒缓也”。又,“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是说这二州都有安舒、宽舒之气。这里就不一一引述。刘熙释徐州得名源于其“土气舒缓”之故等。这些解释与李巡《尔雅注》是一致的,或即参考过李巡的注。可见,称一个地方有“舒缓之气”,并非冷僻之说。班固谓《齐诗》具有“舒缓之体”,曹丕自可据此谓徐幹“时有齐气”。又,其谓:“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必取荆为名者: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之也。”又,“鲁,鲁钝也。国多山水,民性朴鲁也”。又,“越,夷蛮之国,度越礼义,无所拘也”[14]45-53。这是从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格、行为习惯等角度予以解释的,说明一个地方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性格、行为习惯,会被人从某一个特定角度予以概括,这也是在曹丕之前和同时就存在的解释。进而我们也就可以考虑到“齐气”是与“齐地”(齐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风俗等有关,这样解释也就很合理。
一个地方之“气”,其“土气”“风气”等,这些概念内涵比较复杂。一是指地理方面的“自然之气”,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谓“系水土之风气”,应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物质方面的生活条件等综合而成的一种自然特点;二是指生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民人之“气”,大概包括这个地区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习惯习俗乃至个性气质,甚至还包括体形体态、语言声音等综合而成的一种精神面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学者常常说的一个地方的“气”,引申到文学创作风格和文学批评之中,也就要考虑这个地域的作家作品可能所具有的一种文学地域性特征,或者用这种地域之“气”来说明作家作品的某种地域特征。这就是曹丕提出的“齐气”说之思想渊源与知识背景。这种总括地说一个地方之“气”是什么特征,带有“感觉”“印象”的认知特征,既有一定的科学性,又带有人类认知的一种模糊性、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特点,其中不一定完全科学和全面,有时难免从某一个角度去讨论,所以可能会以偏概全,但是从整体上讲,绝不是主观臆断,完全没有道理。
李善注《典论·论文》的“齐气”,引《汉书·地理志》所谓“故《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此亦舒缓之体也”。虽然略去班固“又曰:‘俟我于著乎而’”这一句,但已经明确揭示出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论,就是曹丕《典论·论文》“徐幹时有齐气”之本据,体现出一个注家的学术严肃性,要言不烦,所注基本不误,既指明其出典,又阐释其内涵。今人对李善此注生发出多种诠释,有些解说者似乎未能仔细考察分析李善之所以这样注解的缘由。自唐李善《文选》注释“齐气”为“文体舒缓”之义后,唐宋以至明清的作家、艺术家、文艺批评家,均用“齐气”表示“舒缓”文体、格调或艺术笔法(如书法等)特点,容或存在差异,具体所指的内涵亦有不同,如结构不紧凑、笔力较软等,但“舒缓”之内涵不变,无有严重歧说。
要之,关于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齐气”,唐李善所注基本不误,有本据在焉。反而是今人之反驳,才多为臆断。如何诠释曹丕所说的“齐气”说,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角度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结 语
如上所论,曹丕《典论·论文》“齐气”说,盖为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且对《文心雕龙》中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思想与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难考见的。李巡《尔雅》注“汉南曰荆州”曰:“汉南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15]王粲年少时流寓荆州依刘表16年,其“躁竞”的个性气质,是否受到“其气燥刚,禀性强梁”的荆州之气影响,曹丕把王粲与具有“齐气”的徐幹进行比较评论,是否内含这种文学地理批评的意见,不能“想当然”地臆断。但如果我们撇开曹丕的评论,仅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看问题,可以说,王粲的创作不能不受到荆州当时的文化地域风气的影响,这是题外话。
前文论述说明曹丕“齐气”说,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而且具有范式的意义。通过上文研究,可以看出这是从人地关系与文地关系出发,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与风格成因作出的分析。引申来讲,“齐气”说,关注到地域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的与文学的传统对作家作品的影响问题;从作家的才性批评和文体批评出发看,“齐气”说突出强调体现在作品中的“文气”即创作个性特点,又结合具体作家所擅长的文体及其文体风格进行评论;而且还注意到与其他擅长同一种文体的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又不乏文学鉴赏的主观体验之精神。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学地理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故说曹丕“徐幹时有齐气”这句话,具有丰富的文学地理批评的内涵,足以成为文学批评之一“说”。
注释
①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1948 第1 期。②参见林其锬:《元至正刊本〈文心雕龙〉集校》,出自《〈文心雕龙〉集校合编》,暨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 页;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1060-1061 页。③陈琳籍贯据《孔融陈琳合集校注》,参见杜志勇:《孔融陈琳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1 页。④王粲籍贯据《王粲集校注》,参见张蕾:《王粲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 页。⑤徐幹籍贯据《徐幹集校注》,参见张玉书、邵先锋:《徐幹集校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 页。⑥阮瑀、应玚、刘桢籍贯据《阮瑀应玚刘桢合集校注》,参见林家骊:《阮瑀应玚刘桢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3、403 页。⑦陆德明著、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7-6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