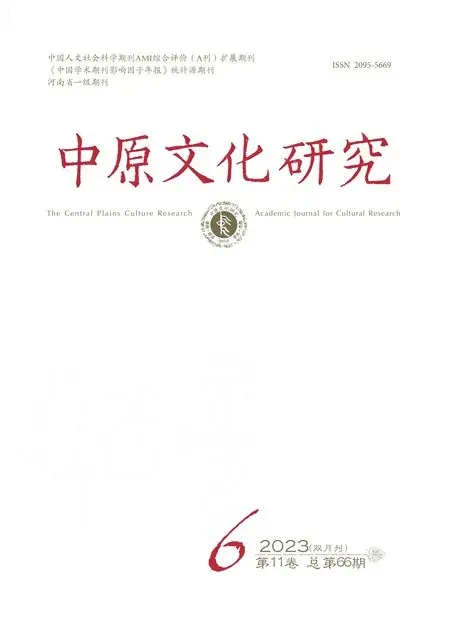南阳夏饷铺鄂侯家族墓地与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的形势*
2023-05-12黄锦前
黄锦前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位于南阳新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500 米处。2012—2014 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发现并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80余座,陪葬坑1 座①。其中一批规格较高的墓葬(M1、M5、M6、M7、M16、M19、M20 等,墓主为鄂侯及其夫人)资料已公布②。据墓葬布局及规模、出土器物形制及铭文,可知该墓地是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夏饷铺墓地的发掘是近年两周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不但丰富和更新了很多旧有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地区的形势和战略格局的重新认识,有重要促进作用。这里拟以夏饷铺墓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就有关问题谈一些初步的意见。
一、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
夏饷铺墓地一期20 座墓葬,从南到北分为四排,其中大型墓两座(M1、M6),中型墓8 座(M2、M3、M4、M5、M7、M16、M19、M20),小型墓10 座。
第一组M5、M6 两座墓并列于墓地东部[1]12-32。M5 出土铜器17 件、玉器18 件、漆木器3 件。铜器分为礼器、工具(5 件)、棺饰(2 件)三类。其中礼器10 件(有鬲2、鼎2、簋2、簠2、盘1、盉1),多为明器。两件鬲(M5∶1、2)[1]15,17和两件簠(M5∶3、4)[1]16,17上有铭文“鄂姜作羞鬲”[1]14“鄂姜作旅簠”[1]17。M6 早期被盗,共出土随葬品542 件,铜器529 件、玉器9 件、石器1 件、漆木器3 件。铜器分为礼器、乐器、兵器、车器、马器、棺饰等。其中礼器6 件,有鼎1、尊1、方彝1、觯1、簋1、簋盖1。乐器6 件,为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的一套钮钟,器身有铭文“鄂侯作”[1]22,23。根据墓葬位置关系、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组合及铭文等,可知M5、M6 为一组夫妻异穴合葬墓,M5 为鄂侯夫人鄂姜墓,M6 为鄂侯墓。二墓的年代发掘者推定为西周晚期晚段,这一年代认定可能偏早,笔者认为应系春秋早期前段。
第二组M19、M20 两墓并列于墓地中部[2]13-23。M19 随葬品共计232 件,铜器223 件、玛瑙珠7 件、绿松石1 件、陶鬲1 件。铜器分为礼器、车器、马器、棺饰。其中礼器10 件,有鼎2、簋4、圆壶2、盘1、匜1[2]封三。1 件圆壶(M19∶10)盖上有铭文“鄂侯作孟姬媵壶”[2]15。M20 被盗,出土随葬品共计75 件,铜器13 件、玉器及玛瑙器62 件。铜器有礼器和棺饰。礼器共10 件,有鼎3、簋4、簠1、盘1、盉1[2]封三,多为明器。簠(M20∶9)器底有铭文“鄂姜作宝簠,永宝用”[2]20,21。M19、M20 亦为一组夫妻异穴合葬墓,M19 为鄂侯墓,M20 为鄂侯夫人墓,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
第三组M7、M16 并列于墓地的中部[3]24-35。M7 被盗,出土随葬品共309 件,铜器303 件、玉器5 件、桃核1 枚。青铜器因被盗,礼器已不存,残存者主要为兵器、车马器、工具、棺饰及其他。M16 随葬品共计141 件,铜器134 件、玉器5 件、漆木器1 件、陶器1 件[3]封二。铜器分为礼器和棺饰两类,其中礼器15 件,有鼎3、鬲4、簋4、圆壶2、盘1、匜1。1 件B 型鼎(M16∶13)腹内有铭文“鄂伯邍作䵼鼎,则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3]32。4 件鬲(M16∶19、20、21、22)沿面有铭文[3]32,匜(M16∶2)内底也有铭文[3]33,均漫漶不清。盘(M16∶1)内底有铭文[3]32,33。M7、M16 也是一组夫妻异穴合葬墓,M7 为鄂侯墓,M16 为鄂侯夫人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中段。
M1 位于墓地的西部[4]36-46,盗扰严重,墓室结构被破坏,部分文物流散。随葬器物仅存48 件,铜器有36 件、玉器11 件、漆木器1 件。青铜礼乐器有鼎7、鬲3、簠2、簋盖2、匜1、盘1、方壶盖2、铃4 等[4]封三。其中5 件A 型鼎(M1∶1、2、4、5、6)腹内壁有铭文“唯正月初吉己丑,鄂侯作夫人行鼎”[4]37,38,3 件鬲(M1∶8、9、10)及2 件簋盖(M1∶13、14)[4]42,40上皆有铭文“唯八月己丑,鄂侯作夫人行鬲”[4]38“唯八月己丑,鄂侯作夫人行簋”[4]39,表明其墓主系鄂侯夫人,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
在夏饷铺墓地发掘之时,南阳市博物馆收缴的4 件铜器中,有墓地西侧邻近M1 位置所出的鄂侯铸叔簠③和上鄀太子平侯匜各一件。匜铭“上鄀大子平侯作盥匜,子子孙孙永宝用”④,结合夏饷铺墓地的布局来看,在M1 附近还应有一座鄂侯墓⑤,该匜应出自鄂侯墓,或系鄀国助鄂侯之丧的赗器。簠铭“唯七月初吉,鄂侯铸叔择匜,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徐少华认为当是鄂侯铸叔的自作用器,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或末年。这位鄂侯应即M1 墓主的夫君,该簠或即出自M1 东侧同组的鄂侯墓⑥。
据已公布的材料,夏饷铺墓地墓葬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和布局。该墓地的鄂侯夫妇墓大致分为四组,由东向西按时间早晚呈“一”字形整齐排列,头向一律朝北。每一组均为两座墓葬,鄂侯墓居东,夫人墓位于西边,间距3 米左右,两组墓葬之间的距离为6 米左右。第一组位于墓地东端,时代最早,M6 为鄂侯墓居东,M5 为夫人墓,位于侯墓西侧;第二组的M19、M20,第三组的M7、M16 亦然。唯位于墓地西端、规模较前三组略大且年代最晚的第四组仅存M1 一座鄂侯夫人墓。
徐少华认为,四组墓葬的墓主应系前后相继的四位鄂侯及其夫人。从夏饷铺墓地布局和出土资料来看,在M1 以东3 米左右的位置应该有一座与其同期同组的鄂侯墓葬(M0),即该墓地中的最后一座鄂侯墓,可能由于早年被盗和后期施工的原因,致使其被损毁无存⑦。其说当是。
二、南阳之鄂的族属与存灭
新的考古发现,不断促使我们对有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近年随州安居羊子山鄂国公室墓地的发掘表明⑧,西周早期鄂国的政治中心应在今随州安居一带,与曾国为邻。或认为西周中叶鄂因受楚的威胁,又南迁至湖北古鄂城⑨。据新的考古发现可知,鄂国在西周晚期确有迁徙,但并非是受楚威胁,而是遭到了周王朝的沉重打击,其所迁之地,也并非今湖北鄂城,而在今河南南阳。
禹鼎铭曰:
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翦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唯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集成》⑩2833、2834)
据鼎铭,西周晚期厉王时⑪,鄂侯驭方叛周,遭王师翦灭,“勿遗寿幼”,即被斩草除根。此后鄂国便不见于文献记载,亦无相关出土文字资料涉及,故一般认为姞姓鄂国自此覆灭⑫。
马承源等指出,鄂为周所伐,禹鼎铭所谓“勿遗寿幼”,其余族则再南迁于邓之向城南,同为西鄂⑬。赵世纲亦云,从禹鼎铭仅说“休获厥君驭方”来看,周王“勿遗寿幼”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鄂国在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其余部即迁于今湖北鄂城、武昌、大冶一带⑭。徐少华则兼采二说,认为可能周天子“无遗寿幼”的征讨令得到贯彻实行,鄂为周师所灭;或者惨遭重创,其后国族衰弱、离散,无力立于诸侯之林[5]25。诸家意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西周晚期鄂未亡;二是鄂之余部或再迁于邓之向城县(县治位于今南阳市南召县东南皇路店镇皇路店村附近,距离夏饷铺村约10 千米)南。但这些皆系推论,并无实据。
夏饷铺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再次出现有关鄂国的记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徐少华认为,夏饷铺M19 所出鄂侯作孟姬壶是鄂侯为异姓女子出嫁所作媵器,夏饷铺新发现之鄂国当是周厉王在伐灭今随州安居一带的鄂国后,将部分鄂国遗民北迁至今南阳一带安置、监管,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恢复后逐渐发展而来的⑮。但鄂侯壶(M19∶10)铭文“鄂侯作孟姬媵壶”并不能证明孟姬为异姓女子,相反却表明南阳之鄂应系姬姓,此鄂(南阳姬姓之鄂)非彼鄂(随州姞姓之鄂),二者时间、空间和族姓皆不相同。结合禹鼎关于厉王时鄂国被翦灭的记载,可知应系姞姓鄂国灭亡后,周王朝在南阳盆地改封姬姓宗亲重建鄂国,夏饷铺鄂国墓地即为其遗存,春秋早期的鄂应在南阳一带⑯,原随州一带的鄂国故地应纳入曾国的疆域范围,姞姓鄂国自厉王以后便不复存在。
总之,南阳夏饷铺新发现的鄂国系周人在今南阳一带重新封立的宗亲,而非原来姞姓鄂国的迁徙延续,禹鼎“翦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即鄂国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毁灭性打击当系实录,而非虚言。
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随葬青铜礼乐器及精美玉器等表明,春秋早期的鄂国,其实力不可小觑。过去有学者认为鄂为楚王熊渠所灭⑰,然据《楚世家》,熊渠是夷、厉时人,故此说不确。但鄂为楚所灭,应无疑问,这与宣王时姬姓鄂国之封是为了牵制楚也相吻合。据目前的资料看,夏饷铺墓地的年代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换言之,鄂灭亡的时间应不早于此。综合来看,鄂国最终为楚所灭的时间,或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
夏饷铺墓地M5 出土鄂姜鬲(M5∶1、2)和鄂姜簠(M5∶3、4)各两件,M20 出土一件鄂姜簠(M20∶9),M5 墓主为鄂侯夫人鄂姜。这个与鄂国联姻的姜姓国,应即当时同处南土与之相邻的申国或吕国。鄂姜或为姜姓申、吕之女嫁适鄂侯为夫人者⑱。
申为姜姓国,周封伯夷之后于申,春秋时灭于楚,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诗·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毛传:“申,姜姓之国。”[6]700《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杜预注:“申国,今南阳宛县。”[7]3724《国语·周语中》富辰对周襄王曰:“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四国皆姜姓。”[8]46
申本系周人同盟,是“姬姜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据铜器铭文,两周之世,申国与周王朝及姬周宗亲如郑国等关系都很密切,世代与周王室通婚。夏饷铺墓地发现的鄂侯夫人鄂姜墓及出土的鄂姜诸器,即系当时申人与周室宗亲鄂国以联姻进一步加强联盟之具体体现。
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 年)曾伐申,申的灭亡大约在公元前687—677 年之间,与息国灭亡的年份(公元前680 年)相仿⑲。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鄂国的灭亡时间,大致也在此时。徐少华认为夏饷铺M1 及其夫君墓(即该墓地中的最后一座鄂侯墓)的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680 左右或稍早⑳,也与这一时间节点相吻合。
三、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与姬姓鄂国的封建
姬姓鄂国为何恰在此时受封于南土,这需要从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的变化谈起。
周初为巩固统治,大规模分封宗室,作为王朝的屏藩。《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8]461“随”即曾,在周初封建屏藩的大背景下,周文王之子南宫被成王册命为曾侯,在今随州一带立国,作为江汉地区的战略防御核心,与在今河南平顶山及上蔡的应国与蔡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构成周王朝在江汉、淮域战略防御体系的核心。西周早期的江汉流域,鄂、曾、楚、邓及鄀等国实力较强,除曾国外,余皆为异姓,封曾于江汉,是为了牵制鄂、楚、邓、鄀等异姓诸侯。相对地近中原的应国而言,曾国是南土的第一道防线和前哨阵地。鄂、曾是周初两个最大的势力集团,分别为姬周异姓和同姓诸侯的代表,楚则相对较弱;成王时鄂、曾、楚共处汉水中游今随州、宜城一带,江汉地区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西周早期江汉地区的政治中心在以今随州枣阳为中心的随枣走廊一带,重心在今随州,曾国是其主导者。至康王时,江汉地区相对稳定。康王以后,楚人反周,昭王伐楚,昭王第一次南征,达到了“唯贯南行”(史墙盘,《集成》10175)即贯通南国交通的战略目的,促进了江汉的开发。昭王第二次伐楚失败,丧师失地,江汉地区战略平衡被打破,楚人迫近,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退缩,防线有所收缩,西周中期曾、鄂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已迁离故地。
昭王南征失败,南土的方伯曾国遭重创后迁徙,实力锐减,一蹶不振,南土的战略平衡被打破。“蔽蔡南门,折(原文写为质)应京社”[9](曾公编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10]5(0曾侯與编钟)皆已成为口号,南土秩序骤变,中原和王朝失去屏障,“金道锡行”(曾伯簠,《集成》4631、4632)的战略意义逐渐削弱。江汉地区,楚人逐渐兴起,与王朝摩擦不断;江淮一带,南淮夷失控,叛服无定,与王朝之间冲突此起彼伏。
穆、恭时期,南淮夷趁机兴乱,乘虚长驱直入,屡屡北上西进,越过成周,深入中原腹地汾涑流域今晋西南一带的晋、倗、霸,直逼宗周。厉王时历史又一次重演,给西周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厉王亲征南淮夷。穆、恭以降,南土及中原屡遭戎祸洗劫,逐渐虚空,秩序遭到系统破坏,屏障作用尽失,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遭到根本的结构性破坏。
《史记·楚世家》说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11]1692,表明在周厉王继位之前,江汉地区的形势已很严峻。楚公逆编钟㉑“钦融内(纳)(飨)赤金九万钧”,“金”即铜,表明此时楚国实力上升,对南土的铜等战略资源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楚世家》云“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11]1692,表明厉王时周王朝在南土尚有一定的控制力,禹鼎记鄂侯驭方率众作乱而被迅速翦灭即为明证。
与楚为邻的鄂,在西周早中期曾强盛一时,为稳定周王朝的南土作出了重要贡献。厉王时鄂侯驭方因叛乱而被翦灭,江汉地区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鄂被灭后,江汉地区能与楚相抗衡者就只有曾,曾是姬周宗亲,是“汉阳诸姬”之长,从此独自承担着抗楚的重任,独木难支。
总之,西周晚期厉宣时期,中原和南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周王朝的决策者考虑及时修复自周初建立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在形势异常严峻的南土地区,率先进行结构性重组。
《诗·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往近王舅,南土是保。”[6]1219-1222周宣王迁其舅申伯于南土(铜器铭文如仲爯父簋㉒、南申伯虔父簋㉓等称“南申”,以区别于之前的申即西申,其地望在今河南南阳一带[5]31-34),“使为侯伯”,“统理南方之国”[6]1221,以图“南土是保”。由《崧高》篇可知,申伯是宣王之舅,王朝重臣。宣王命召伯(召穆公虎)经营南土的谢邑,使申伯徙居。申伯归国时,宣王给予隆重的褒赏,并且亲自饯行。对南方的控制,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政务,申伯的徙封在周朝企图巩固南土的活动中,是一件大事㉔。故《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8]461
与迁申、吕互为表里者,系在今南阳一带重新册封姬姓鄂国,此二举应系双管齐下,同时之事。上述夏饷铺墓地至少埋葬了春秋早期的四代鄂侯及其夫人,可见这里是春秋早期或两周之际的鄂侯家族墓地。该墓地年代较早的鄂侯墓系M6,年代为春秋早期前段。徐少华认为,夏饷铺M7 与M16、M19 与M20、M5 与M6 三组墓的下葬时间分别在公元前710 年、公元前735 年与公元前760 年前后㉕。公元前760 年接近于春秋始年(公元前770 年),可见南阳鄂国的始封时间理应更早,应在周室东迁之前。
史载周幽王贪婪腐败,不问政事,任用奸佞之徒虢石父为卿士,执掌政事,致使朝纲败坏,国祚衰微。幽王时自顾尚且无暇,自然更无雄心壮志重振周邦,封建诸侯的可能性不大。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迁申、吕于南阳盆地来看,姬姓鄂国之封,也应在宣王时期,时间也应与迁申于南土相近。夏饷铺墓地遭到盗掘破坏,据目前所见有关资料,其年代主要为春秋早期。宣王之后系幽王,幽王在位仅十余年,西周覆亡。从时间上看,夏饷铺墓地的起始年代也与姬姓鄂国始封于宣王时基本吻合。
宣王时期,徙封申、吕,重建鄂国于南阳,至少表明两点:一是当时江汉地区的楚人已崛起,周人势力已无法再插手;二是南土在当时周王朝整体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南土不仅是“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同时更是中原地区和周王朝的屏障,起着屏藩护卫的重要作用。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南土皆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周一代,王朝始终将开发南土和江汉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周人自立国之初,便封文王之子南宫于江汉,作为南土的方伯。昭王南征,“广楚荆,唯贯南行”(史墙盘,《集成》10175)。厉王时,面对屡屡进犯甚嚣尘上的南淮夷,又率众亲征,“敦伐其至,翦伐厥都”(钟〔宗周钟〕㉖)。综观周人的这些举措,皆反映了南土在安全和发展方面对王朝的重要战略价值和意义。当初周人为何不惜血本在南土与楚人和南淮夷等土著势力轮番鏖战,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申、吕南迁及重建鄂国的时代背景,同样也要从西周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进行考察。西周早期,周人经略的重心主要在东土与南土,昭王南征虽然失败,但从金文材料来看,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土较少发生战事。由于在南土的扩张势头被遏制,自西周中期穆王开始,周人便试图在宗周以西以北地区有所进取,但成效并不显著,反而陷入了与西北戎狄无休止的战争中,并逐渐丧失了对泾河上游的有效控制。至西周晚期厉宣之世,周人不但要应对西北戎狄的侵扰,还面临着南土夷人的叛乱,经常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宣王时期,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地区和周王朝的屏障,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地区和周王朝。而其中最关键的举措,就是迁申、吕于南土,同时在南阳盆地重新册封姬姓鄂国。
由此也可见,周人在南阳盆地重新册封之鄂应系姬姓宗亲,而非原来江汉故地之姞姓鄂国。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周人大概不会如此儿戏一般,放心地将南土的门户和战略枢纽交给曾大举叛周之异姓鄂人去守卫。果如此,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自掘坟墓。故南阳之鄂不大可能是姞姓鄂国所徙封。
即便如此,周人也已无力回天。西周王朝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同时楚人在南土的崛起,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历史的车轮,已无法逆转。西周中期以来,南土及中原屡遭戎祸,已成为王朝安全的极大隐患。也正是与淮夷的长期频繁战争,大量消耗削弱了周王朝的实力,并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西周灭亡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因为周人经略南土政策的破产,导致中原和王朝失去了屏障。
西周晚期厉王以后,鄂国被翦灭,楚人崛起,曾国衰弱,春秋中期以后,曾国在南方的霸主地位被楚取代,江汉地区由鄂曾楚三足鼎立变成楚人坐大,南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春秋中期以后,楚国急剧崛起,逐渐北上东进,开疆拓土。处于中原和南土之间的应国,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即被楚国北上攻灭。楚人从此势如破竹,南土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河南上蔡一带的蔡国,春秋时期亦屡受楚之侵迫。公元前531 年,楚灭蔡。三年后,蔡平侯复国,迁都新蔡(今河南新蔡县)。公元前493年,又迁都下蔡(今安徽寿县)。公元前447 年,蔡终为楚所灭。
同时曾人日益衰弱,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较量,楚成王以后,“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7]4678,最终沦为楚之附庸。曾侯與编钟“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10]16,加嬭编钟㉗“楚既为,吾逑匹之,密臧我猷,大命毋改”,即周室衰微,楚人兴起,曾国转而归附逑匹楚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退出江汉流域,“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彻底丧失,南土尽入楚人彀中,楚国最终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结 语
据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宣王时期,周人在南阳盆地重建姬姓鄂国,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与申、息二国的灭亡时间大致相当,鄂国约于公元前680 年前后(即夏饷铺M1 夫君鄂侯的下一任鄂侯在位之时)复灭于楚。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骤变,至西周晚期厉宣时期,周人在中原和南土的统治皆面临严峻挑战。宣王时,通过迁申吕、封建宗亲鄂国于南阳盆地,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和王朝的屏障,修复自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但西周王朝衰落和楚人崛起的大势已不可挽回,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南土尽入楚人彀中,“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尽失,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
总之,南阳夏饷铺鄂侯家族墓地的发掘,揭开了两周时期鄂国历史的诸多谜团,丰富和更新了我们对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地区的形势和战略格局的认识,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一些新问题的思考,因而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崔本信、王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 年1 月4 日;崔本信、王伟、曾庆硕:《河南南阳夏响铺周代鄂国贵族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2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 年版,第60-63 页。②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 年第4 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 年第4 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 年第4 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5、M6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 年第3 期。③⑥⑦⑮⑱⑳㉕徐少华:《关于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22 年第2 期。④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12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版(以下简称“《铭三》”),第3 卷,第418 页。⑤⑯有关分析可参看黄锦前:《楚系铜器铭文新研》,吉林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 年8 月,第251-252,251-254 页。⑧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33 页;深圳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第9-63 页。⑨何光岳:《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迁移》,《江汉考古》1986 年第3 期。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 年版。文中及注释均简称《集成》。⑪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 年第3 期;李学勤:《谈西周厉王时器伯父簋》,载《安作璋先生史学研究六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7 年版,第86-89 页。⑫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 年第1 期;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 年第11 期;罗运环:《安居新出鄂侯诸器与楚熊渠所伐之鄂》,辑入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109 页;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1 期。⑬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406,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第281 页,“鄂侯驭方鼎”,注释〔三〕。⑭赵世纲:《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江汉考古》1995 年第1 期。⑰何光岳:《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迁移》,《江汉考古》1986年第3 期。赵世纲亦云鄂为楚所灭,但他将鄂的灭亡时间定在楚惠文王十四年,即公元前475 年,是因对鄬子受钟铭文文字的误释而致,故不可信。参见赵世纲:《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江汉考古》1995 年第1 期,第51 页。⑲㉔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 年第4 期。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8 期;湖北省博物馆:《晋国宝藏——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第98-103 页。㉒《集成》4188、418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 卷,106,文物出版社1997 年版;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0),260,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50 页。㉓《铭三》0474、0475,第1 卷,第557-562 页。㉖《集成》26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 卷,188。㉗加嬭编钟铭文拓片参见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等:《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 年第3 期。笔者的释读与该文有异,原释文的“徕”字应为“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