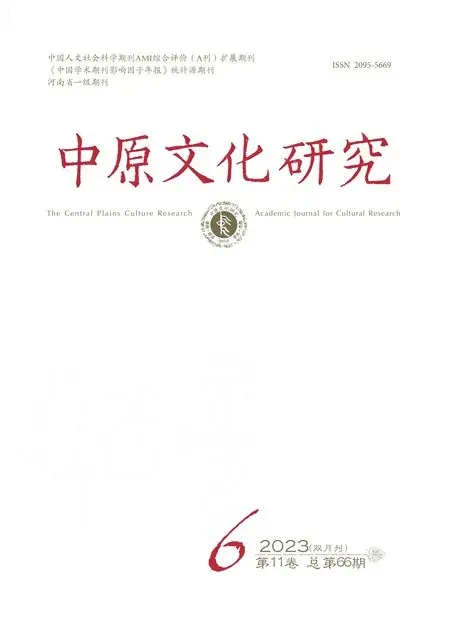“缩”与“不缩”:孟子“养勇”思想的内在理路
2023-05-12周苇风
周苇风
《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是学术界公认的最难理解的一章,冯友兰先生说:“孟子浩然之气章,前人亦多不得其解。”[1]《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的难点很多①,其中以孟子养勇思想的内在理路最为纠缠不清。究其原因,诚如戴震《古训》中所说:“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2]“时之相去”“地之相隔”,简单的事情反而变得复杂起来。要理解古人,消除文字障碍是关键。该章中的“褐宽博”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缩”与“不缩”?这两处文字是理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孟子养勇思想的关钥。
一、“褐宽博”与北宫黝之养勇
北宫黝之养勇,“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此处的“褐宽博”,赵岐注:“独夫被褐者。”[3]2685理解“独夫”与“被褐者”之间的关系是弄清“褐宽博”之义的关键。焦循《孟子正义》云:“褐宽博即是衣褐之匹夫。”[4]206按照焦循的解释,“独夫”与“被褐者”为偏正关系,“独夫被褐者”即衣褐之匹夫。照此理解,“褐”与“宽博”也构成了偏正关系,“褐”被用来修饰限定“宽博”一词。朱熹《孟子集注》:“褐,毛布。宽博,宽大之衣,贱者所服也。”[5]37-38“宽博”是宽大之衣。假如“褐”与“宽博”为偏正关系,“褐宽博”意思即用“褐”制作的宽大之衣。“不受于褐宽博”,意即不受制于穿宽大之衣的人,而这种人的宽大之衣的缝制布料为“褐”。
“褐宽博”也可以被理解为并列关系,“褐宽博”是两类人,“褐”是衣褐之人,“宽博”是穿宽大之衣的人。《诗经·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一句,郑玄注云:“人之贵者无衣,贱者无褐。”[3]389《后汉书·赵典传》“身从衣褐之中”一句,李贤注云:“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6]贫贱者衣褐不难理解,问题是“宽博”是贱者所服吗?穿宽大之衣的人是贱者吗?孔子的衣袖就比较宽大,据《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衣也,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3]1668儒服是儒者穿着的衣冠服带,为了与俗人区别开来,儒者穿着“逢掖之衣”,这是一种袖子很宽大的衣服。除了“逢掖之衣”,儒者还冠章甫之冠,绅而搢笏。《荀子·哀公》:“然则夫章甫、絇屦、绅而搢笏者,此贤乎?”杨倞注:“绅,大带也。搢笏于绅者也。”[7]逢掖之衣,绅而搢笏,儒者所服可谓“宽博”,然儒者是贱者吗?《汉书·隽不疑传》:“(暴)胜之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8]3035-3036隽不疑为当时名人,治《春秋》,为郡文学,名闻州郡。隽不疑“褒衣博带”,着装也可谓“宽博”,然隽不疑是贱者吗?
除了儒者,诸侯国君一般也逢衣博带。据《墨子·公孟》记载,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楚庄王“鲜冠组缨,逢衣博袍,以治其国”[9]703。齐桓公、楚庄王的装束也可谓之“宽博”,齐桓公、楚庄王就更不是什么“贱者”了。因此,晁福林说:“宽博之衣带,并非贱者所服。”明确否定了“宽博”为贱者所服的说法。他对“褐宽博”进一步解释说:“愚疑此处的‘褐宽博’不当释为‘独夫被褐者’,或当为‘臧获’之别称。愚疑这两者的相通,乃是由于古音相近的缘故。‘获’与货音近,‘臧获’,犹后来所语之‘脏货’、‘贱货’。而‘褐’‘博’之音与获、货古音亦近。‘臧获’为战国时期贱役奴徒的一种称谓。”“‘褐宽博’即一个穿褐者,类乎《左传》哀公十三年所提到的‘褐之父’(一个穿褐的老者)。”[10]或成一说,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褐”与“宽博”是两个词,从字面意思上讲,“褐”指布料,“宽博”指的是衣服的样式。《说文》:“褐,编枲袜。一曰粗衣。”段玉裁注云:“取未绩之麻编之为足衣,如今草鞋之类。”[1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枲,麻也……牡麻无实者也。夏至开花,荣而不实,亦曰夏麻。”[12]171枲是不结子实的大麻,其茎皮纤维可织夏布。当时制作衣服的材料除了枲,还有蚕丝。蚕丝织成的布称作“帛”,《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3]2671《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说许行之徒衣褐:“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3]2705“褐”与“帛”是两种不同的布料。《史记·秦始皇本纪》:“夫寒者利裋褐。”“裋,一音竖。谓褐布竖裁,为劳役之衣,短而且狭,故谓之短褐,亦曰竖褐。”[13]283-284裋褐、竖褐、短褐,都是劳动装,便服。“褐”是粗布麻衣,是制作衣服的材料,而“宽博”则指衣服的样式。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君也不都是褒衣博带,《墨子·公孟》说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9]703。沈从文在对比商代墓葬中人物服饰时说:“第三种衣服虽短,身份不一定较低,这一点认识相当重要。”[14]说明先秦时期的上层人物也穿短小衣服,在当时宽袍大袖还没有成为权威的象征。沈从文的看法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印证,自然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儒服制度的形成的确提高了宽衣博带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宽衣博带成为身份的象征。为了提高作战能力,赵武灵王曾进行军事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倡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件事也说明,当时很多贵族已经习惯了宽衣博带。衣着宽博还是短衣归根结底是由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来决定的,宽衣博带显然不便于生产,只有脱离了生产劳动的人才愿意宽衣博带。宽博和短衣是衣服样式,宽博和短衣的布料可用帛,也可以用褐。穷人衣褐,富人衣帛,衣褐与衣帛是贫富的象征。富人如需穿短衣,可以用“帛”来制作。儒者未必都富有,他们的逢掖之衣也可能是由枲织成的毛布缝制而成。
《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赵岐注:“曾子谓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恶于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言义之强也。”[3]2685赵岐将此处的“褐宽博”解释为“被褐宽博一夫”。一夫又称匹夫,《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赵岐注:“言残贼仁义之道者,虽位在王公,将必降为匹夫,故谓之一夫也。”[3]2680王公之外的人被称作一夫、匹夫。匹夫又称独夫,《汉书·刘向传》:“臣闻春秋地动,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这里的“三独夫”是指萧望之、周堪和刘向本人。颜师古注:“独夫,犹言匹夫也。”[8]1931刘向可以自称独夫、匹夫,也称萧望之、周堪为独夫、匹夫,他们都是当时的名人,社会地位不低。由此可见,匹夫有两种:一种是衣褐之匹夫,他们是贱者、贫者;另一种是褒衣博带之匹夫,他们在王者之下,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这里的“褐宽博”就包括衣褐之匹夫和褒衣博带之匹夫。这句话的意思是:北宫黝不怕衣褐的贱者和贫者,也不怕褒衣博带之人。北宫黝甚至不惧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总而言之,北宫黝无所畏惧,不受制于任何人。
二、“缩”与“不缩”:大勇的两种类型
北宫黝之养勇,不肤挠,不目逃,既不惧万乘之君,也不惧褐宽博。同样,“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这句话中,“惴”也应该是怕的意思。但赵岐却这样解释:“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即“不惴”是不使之惊惧。对于赵岐的解释,焦循《孟子正义》说:“褐夫易于惊惧之。不惴,是不惊惧之也。谓不以气临之,使之惴惴也。”[4]209首先,和解释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一样,焦循在此处将褒衣博带之匹夫也排除在外了。其次,如果说“褐夫”是贱者,见识少,易于惊惧,“宽博”则是君子有道艺者的装束,甚至万乘之君也常褒衣博带,他们岂“易于惊惧之”?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其中的“缩”,赵岐注:“义也。”[3]2685朱熹《孟子集注》:“直也。”[5]38按照赵岐与朱熹的意见,“自反而不缩”是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换句话说,就是自觉理亏。理直则气壮,气盛则言宜。理亏了还去惊惧别人,当然称不上“勇”。但理亏了,不去惊惧别人,难道就称得上“勇”了吗?孔子断不至说出这样不合情理的话来,所以王若虚、阎若璩、王引之都不同意赵岐的看法,认为“吾不惴”的“惴”为自己惊惧。但这样一来就更讲不通了,知道自己理亏了,面对“褐宽博”自己一点也不害怕,这算是什么“勇”呢?为了迁就自己的解释,王若虚《孟子辨惑》认为:“不字为衍。不然,则误尔。”[4]209阎若璩《释地三续》也说:“不,岂不也。犹经传中敢为不敢,如为不如之类。”[4]209王引之《经传释辞》则说:“不,语词。不惴,惴也。言虽被褐之夫吾惧之。”[4]209在王若虚、阎若璩、王引之等人看来,知道自己理亏了,面对褐夫应该感到害怕。然而这种无视“不”字存在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
据曾子的说法,孔子将大勇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反而不缩”,一种情况是“自反而缩”。“自反而不缩”的表现是“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的表现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与“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二者所说实为一回事。诸侯国君一般也逢衣博带,“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其中的“褐宽博”也包括万乘之君。和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一样,“虽褐宽博,吾不惴焉”的意思也是不受制于任何人,既不怕万乘之君,也不怕褒衣博带之人,更不用说衣褐的贱者和贫者了。显然,北宫黝之养勇属于第一种情况,“自反而不缩”。孟施舍不畏三军,“能无惧而已矣”,其表现则与“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相符合,故孟施舍之养勇属于第二种情况,“自反而缩”。
“自反而缩”与“自反而不缩”的共同之处是“自反”。“自反”一般被理解为自我反省,赵岐与朱熹的意见便是如此。《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3]2730将“自反”理解为自我反思虽不为错,但并不确切。《孟子·离娄上》第四章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2718将《离娄上》第四章与《离娄下》第二十八章两段文字对照着读,不难发现“自反”的真正意思是“反求诸己”。孟子强调“不动心”。孟子认为,“不动心”不能外求,只能“反求诸己”,也就是“自反”。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大勇,即“自反而不缩”和“自反而缩”,也就做到了“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孟子论养勇是由表述“不动心”而引发的,显然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是被孟子作为“不动心”的例子来使用的。公孙丑问孟子:“不动心,有道乎?”孟子回答说:像北宫黝、孟施舍那样去养勇也就做到“不动心”了。“自反而不缩”是北宫黝之养勇,“自反而缩”是孟施舍之养勇。“自反而不缩”与“自反而缩”都做到了“不动心”,北宫黝与孟施舍都属于孔子所谓的大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北宫黝与孟施舍“未知孰贤”。
但“自反而不缩”与“自反而缩”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勇,它们的区别在于“缩”与“不缩”。什么是“缩”呢?缩从糸,与绳索有关。缩的本义为捆扎,《诗经·大雅·绵》:“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孙炎曰:“绳束筑版谓之缩。”郭璞曰:“缩者,缚束之也。”[3]510散乱的东西经过捆扎,变得整齐有条理,故缩又有整理的意思。《说文·糸部》:“缩,乱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许书之乱字皆治也,理也。此说解及《尔雅》之乱,正谓治理。”[12]286散乱的东西经过捆扎,占用空间缩小,故缩又有收缩、退缩之义。贾谊《吊屈原赋》:“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王利器注:“缩,收敛。引申为深藏不露。”[15]自缩不是消极地退缩,自缩是为了自珍,而自珍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焦循《孟子正义》说:“养勇即是养气。”[4]207《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轼)。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16]248怒蛙即鼓足气的蛙。在勾践看来,怒蛙体内的气就是战士打仗需要的勇气。孟子在《公孙丑上》第二章说自己善养浩然之气,而且浩然之气要“配义与道”,“无是,馁也”[3]2685。《孟子·告子上》第四章主要记述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争,孟子主张“义内”,告子则认为“义外”[3]2748。在《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孟子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3]2685。既然“义内”,而且要与浩然之气相配,则浩然之气也必须在“内”。然而气并不必然在“内”,《孟子·告子上》第八章提到一种“平旦之气”,是积存了一夜的“夜气”,但“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3]275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存气的功夫,气很容易就跑掉了。浩然之气如果不配义与道,也会跑掉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气馁”。孟子称孟施舍“守气”,“守气”就是存气,对“气”加以控制。“守气”谓之“缩”,不能“守气”谓之“不缩”。孟施舍不畏三军,“视不胜犹胜”,凭借的正是“自反而缩”的“守气”功夫。
《孟子·公孙丑上》说:“气者,体之充也。”[3]2685“守气”首先要体内有气,像怒蛙一样,勇士首先要让体内勇气充盈起来。《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1767使体内的勇气充盈起来比较容易,但要使其长时间保存在体内比较困难。战斗中,士兵们可以一鼓作气,一往无前,视死如归。但时间一长,遇到挫折,便“再而衰,三而竭”了。“自反而不缩”不需要存气和守气,单凭一鼓作气,不等“再而衰,三而竭”,也不给“再而衰,三而竭”机会,就完成了英勇壮举。“自反而不缩”是北宫黝之养勇,北宫黝只需要做到“自反”,做到“不动心”,使体内勇气充盈起来就可以了。北宫黝这种类型的勇士,他们的惊天伟业是靠激情与冲动做出来的。我们常说慷慨赴死易,北宫黝就属于慷慨赴死的勇士。对孟施舍来说,慷慨赴死当然也不在话下。而且由于他的勇气不会外泄,他还可以从容赴死,“虽千万人,吾往矣”。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从难易程度上讲,孟施舍之养勇的难度显然远超北宫黝,因此孟子认为孟施舍比北宫黝“守约”。
《韩诗外传》卷八:“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抟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17]303-304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他说:“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像抟轮的螳螂,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螳臂当车,自不量力,这在先秦时期被视作勇敢的行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杀齐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3]1984。刘向《新序·义勇》:“齐崔杼弑庄公也,有陈不占者,闻君难,将赴之。比去,餐则失匕,上车失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闻战斗之声,恐骇而死。人曰: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18]北宫黝和孟施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勇士,孟施舍的勇气与齐太史、陈不占类似。
三、“守气”“守志”与孟子的养勇立场
子夏即卜商,孔门十哲之一。《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3]2498子夏传文学,后世学者治五经,往往称得之于子夏。相传《毛诗序》即为子夏所传,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犹未尽,毛更足成之。”[3]269据说《公羊传》《穀梁传》也为子夏所传,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3]2190晋范宁《春秋穀梁传序》唐杨士勋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3]2358《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又问:“礼后乎?”子夏能够举一反三,孔子很高兴,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3]2466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13]2203在后人的印象中,子夏首先是一个学者。
然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却记载:“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19]当时人们有种观念,认为气郁而疾,志意不通,需要勇武之人陪侍。遇到这种情况,孔子就让勇武的子路和子夏陪侍。由此可见,子夏不仅善文学,勇武也比肩子路。孔子死后,弟子们互不服气,相互攻讦,曾子、子夏、有若、子游、子张是儒家早期内部纷争的主角。《孟子·滕文公上》:“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3]2706和其他派别相比,子夏这一派主张“君子有斗”。《墨子·耕柱》:“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9]657子夏一派主张“君子有斗”渊源有自,《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3]1284-1285子夏从孔子那里接受了“君子有斗”的思想,并使之成为子夏一派的鲜明特色。
《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子夏与公孙悁言勇一事,子夏历数了自己做过的三件勇猛之事:第一件事是随卫灵公西见赵简子,赵简子披发杖矛,不朝服而见卫灵公。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子夏挺身而出,厉声对赵简子说:“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最后迫使赵简子“反朝服”而见卫灵公。第二件事是从卫灵公东至阿与齐国国君相会,齐君重鞇而坐,卫灵公单鞇而坐。子夏认为诸侯相见,“不宜相临以庶”,于是“揄其一鞇而去之”。第三件事是随卫灵公打猎时,卫灵公遭到两只野兽的攻击,子夏“拔矛下格而还之”[17]224-226。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楚返卫,孔门“弟子多仕于卫”[13]1933。《韩诗外传》卷六说子夏曾任卫国行人一职,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韩诗外传》卷六也佐证了《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的说法,即在孔子感到气郁而疾、志意不通的时候,子夏的确有资格和勇武的子路一起陪侍孔子。或者正因为有过陪侍孔子的经历,《韩诗外传》卷六中子夏才有信心毛遂自荐,要代替公孙悁陪侍卫灵公。子夏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在别人都胆怯的时候,子夏敢于拔矛与野兽搏斗,并最终将它们赶跑了。子夏是一个不肤挠、不目逃的勇士。他与北宫黝一样极为看重个人的声誉,“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面对公孙悁的公开挑衅,子夏毫不退缩,针锋相对,所谓“恶声至,必反之”,充分表现出子夏一派的好斗作风。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子夏在赵简子、齐君面前也毫无惧色,甚至不惜“以颈血溅君之服”。子夏在万乘之君面前的表现,可以说比北宫黝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子夏与北宫黝的行为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北宫黝与子夏属于同一类型的勇士。
《孝经·开宗明义》:“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2545曾子恪守师命,在《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中说:“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又说:“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曾子还说:“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20]《礼记·曲礼》也说:“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又说:“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3]1233-1234曾子至死都很爱惜自己的身体,《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3]2486曾子笃孝,爱惜身体,自然不会像子夏那样轻易许人以死。
孟子服膺曾子,在《离娄下》第二十三章中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3]2729孟子反对无谓的牺牲,不赞成争勇斗狠,将其称为小勇、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第三章中,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告诉他:“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3]2675北宫黝“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恶声至,必反之”,这与齐宣王的“抚剑疾视”何其相似乃尔!按照孔子的说法,北宫黝与孟施舍之养勇都属于大勇。孟子在承认北宫黝与孟施舍之勇“未知孰贤”的同时,却又认为孟施舍比北宫黝“守约”。虽然孟子对孔子的大勇标准没有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对“好勇”有自己的看法。
曾子重“养志”,《孟子·离娄上》第十九章说:“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3]2722一般人们认为,曾子笃孝,奉养父母,顺其意志,谓之“养志”。此章首句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3]2722此章重点论述了事亲与守身之间的关系。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2491曾子在《论语·泰伯》中也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3]2486-2487事亲要养亲之志,守身当然是固持己志。孟子在《公孙丑上》第二章中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又说:“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3]2685固持己志谓之“志一”,孟子理想的大勇是“志一”,是“志一动气”,是“持其志,无暴其气”。孟施舍的“守气”,充其量只做到了“气一”,“气一则动志”,还不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勇。曾子能够固持其志,可见曾子已经做到了“志一”。“志一则动气”,说明曾子不但可以“守气”,而且能“持其志,无暴其气”,做到了对“气”的有效管控。孟施舍“自反而缩”,确保了勇气不外泄,从“守气”这一点上说,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然而用“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的标准来衡量,“守气”当然不如“守志”,故孟子又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对于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赵岐说:“孟子以为曾子长于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虽众,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以黝譬子夏。”[3]2685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与孝之大小有什么关系呢?赵岐只记得子夏善文学,却忽略了子夏还是一个廷折诸侯、格斗猛兽的勇士。朱熹的说法更加含糊,他说:“黝,务敌人;舍,专守己。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5]38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如何就与北宫黝、孟施舍“各有所似”了呢?在孟子那个时候,子夏与曾子思想上的分歧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北宫黝与孟施舍养勇方式上的不同也不难区别,只是到了后世才变得复杂起来。
结 语
“养勇”是《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的重要内容,但一些关键字词的歧义与隐晦却模糊了孟子“养勇”思想的内在理路。首先,“褐宽博”不是贱者,而是指所有人。“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与“虽褐宽博,吾不惴焉”的意思一样,都是不受制于任何人,既不怕万乘之君,也不怕褒衣博带之人,更不用说衣褐的贱者和贫者了。其次,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与“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二者所说实际上是一回事。孟施舍不畏三军,“能无惧而已矣”,其表现则与“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相同。最后,“缩”与“不缩”是孔孟重要思想,“守气”谓之“缩”,不能“守气”谓之“不缩”。孔子将“大勇”分为“自反而缩”与“自反而不缩”两种情况,孟子则进一步认为“自反而缩”比“自反而不缩”更加难能可贵。孔子死后,儒家内部纷争,孟子服膺曾子,他通过“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态度。
注释
①杨泽波将此章难点归纳为十个问题:一、什么是不动心?二、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养勇”有哪些不同特点?三、如何理解“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四、如何理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五、什么叫“志至焉,气次焉”?六、什么叫“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七、如何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断句?八、如何理解“塞于天地之间”?九、如何理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十、什么叫“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杨泽波:《孟子气论难点辨疑》,《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