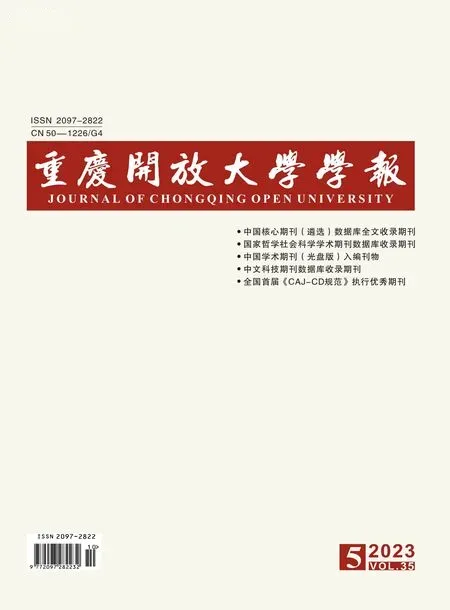冯至诗论的三重面向
2023-05-11梁芹
梁 芹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鲁迅在谈论木刻艺术时对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了阐释,他在《〈木刻纪程〉小引》一文中认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1]自1840 年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在现代西方的冲击影响下,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不少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语境中,因而“外国的良规”与“中国的遗产”成为五四及以后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两大源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就呈现出新的面向,即更加注重政治性与人民性。因此,冯至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五四的激情、现代的隐匿与革命的批判,其诗歌理论也就呈现出三重面向,因而冯至诗论的成就与缺憾也就在这三重空间中被建构与重识。
一、面向传统:自然的浪漫与现实的融合
冯至对传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不同于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片面否定,他认为传统并非等同于“颓毁的宫殿”。在《传统与“颓毁的宫殿”》一文中冯至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旧大陆上最古旧的民族里的一个,有过光荣的富有创造性的过去,我们负担着一部悠久的历史,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接触到历史的遗迹,很难遇到一块新地供我们前无古人地去耕耘”[2]25。所以人们“回忆”的文章也就特别多,冯至担心大家回顾过去就只看到“颓毁的宫殿”,因而也就看不到传统的真正面目。所以在动荡的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廓清了不少附着在文学史上乌烟瘴气的部分,而显露出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2]27。这一时期,冯至的诗歌创作也将最真实的传统精神挖掘出来,即古典的浪漫主义。
在冯至早期的创作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的因素。概因冯至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绝大部分文本都是用以宣泄情感、表达个人体验的,因而鲁迅将其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但若细读冯至的诗歌文本,便能发现他在文本中对于古典因素的运用。冯至虽然没有接受过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系统训练,但他在进入中学以前就接触到不少古典文学作品。而他对“古典主义”的论述在不同的地方也有所区别,在进行具体的诗歌批评时,他的“古典”概念则指向的是超越时代和种族的经典作品。他在《我与中国古典文学——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一文中谈到古典作品时用曹禺做了例子,“听说曹禺在中学时就读易卜生原著,所以他很早就能写出《雷雨》那样的作品”[3]237。他也用“古典”来说明自身创作的源泉,“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了不少养料,也借鉴了西方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法”[3]236。在讨论有关诗学的理论时,他所指的古典主义是带有自然的情调、理性节制情感、和谐统一、注重伦理的倾向。
在冯至看来,古典浪漫主义的一大特征是自然。在《新诗蠡测》一文中他就强调诗的自然,文章谈道:“在古代,屈原、沙浮、宾达那些伟大的抒情诗人的诗里,哪一处不洋溢着自然界的风、雨、光、云以及草木的枯荣。近代不是没有自然诗,但一经比较,便会看得出和古代的是有怎样大的区分,一个化身于自然中,好像就是自然的本身,一个却是与自然有无限的距离。”[3]267-268但是,现代生活似乎让人们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各种光怪陆离的新事物已经掠走我们的注意力,在现代生活中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压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的原始自然情感。同时,冯至在文中还对时代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阐释,“诗,脱不开他的时代”,而处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又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冯至进行了回答,“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承袭了欧洲18世纪的启蒙精神,以为要创造新文艺,必须把文学从死的形式,干枯的理智,因袭的社会里解救出来[3]269。”显然,五四的新诗创作已经完成这一目标,但被解救出来的新诗形式如何能进一步突破与发展,就需要回归到自然、爱情、宗教中创造新的形式与培养深切的情感。由这种自然的古典浪漫主义的诗学观反观冯至的诗歌创作,他的《蛇》算是代表作。“我的寂寞是一条蛇”,这是冯至最脍炙人口的诗句之一。具体而言,这句诗表露出了冯至早期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以净化后的情感为意象;二是自然情感与智性思考的充分融合,这两种创作倾向体现出的正是冯至高超的抒情水准。
古典浪漫主义的另一特征是浪漫与现实的融合。在中国古代诗歌世界中,既有李白浪荡不羁的自由与浪漫,也有杜甫沉郁顿挫的苦闷与无奈,但在冯至看来,那些浪漫中也有对现实的关切。在《漫谈如何向古典诗歌学习》一文中,他就谈道:“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密切结合。中国最成功、最受人民爱戴的诗人都是积极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生活的,他们为现实歌唱、说出人民在封建社会中的痛苦,同时他们也有丰富的想象,用以鼓动人民的情感的昂扬。”[3]409冯至提倡从古典诗歌中汲取经验的诗学主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很多诗论都带有古典的影子。五四时期的诗学流派可以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主要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他们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强调对现实人生的表现,如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就强调要“写实的描画”,肯定“完全写实”的诗歌。而浪漫主义则以创造社为代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诗学最突出的特点为“一是明确提出了‘情绪论’和‘自我表现论’;二是强调灵感和想象在诗中的作用;三是在形式上强调个性的无拘无束的表现”[4]。从两个学派的主张来看,“写实”“灵感”“想象”的诗学观点则与《诗经》中的写实倾向、严羽的“妙悟”、李白的“想象”等古典诗歌主张有着极大相似性。
冯至主张的古典浪漫主义诗学观带有自然与写实两大特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古典浪漫主义在动荡的时局影响下呈现出悲剧性与理性。在战乱的大时代中,冯至的创作最初的落脚点是担当传递悲剧命运的“绿衣人”。在他所偏爱的以恋爱为主题的诗歌中,尽管写的是常见的“爱而不得”的悲剧,但他所选取的意象,无论是“流泪的明珠”,还是“破碎的小船”,也总是能让读者联想到当时四分五裂的国土和灰暗的社会图景。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被天生带有强烈悲剧意蕴的浪漫主义所吸引的,包括风格幽婉的冯至在内的诗人们面对无奈的现实便难以不感到幻灭和痛苦。这些痛苦引发的激愤十分强烈,当他们将这些情感诉诸笔端时,常常未将其净化便直截了当地一泄而出。情感与理智在文学创作中缺一不可,情感固然需要理智加以制约,但理性也需要情感的烘托。冯至在《读<茅于美词集>》一文中曾说:“过去人们评论诗词,常常谈到情景交融,我却更喜欢情与理交融的作品。”[3]147而冯至早期作品中呈现的幽婉沉郁风格既是他体验情感、净化情感的表现,也是他用理智制约情感、追求情理交融的结果。
总而言之,冯至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是他看到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文学价值,另一方面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尽管五四时期不少诗人意识到要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养料,但在实践过程中其眼光更多的还是聚焦现代西方文化。五四时期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时代,在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与现代西方社会的靠近则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所以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渴求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心理。反映在诗歌领域上,便呈现出西化的诗论观,如泛神论对郭沫若诗歌创作思想的影响。泛神论是郭沫若五四时期诗论的哲学基础,所谓泛神论,就是否认上帝以及各种人造的神袛,认为一切自然实体和自然都是神,因而我就是神。但郭沫若并未深入理解泛神论的思想,尽管他借鉴泰戈尔、惠特曼的诗歌具有泛神论的外部特征,可并未参透泛神论形而上的思想内核。郭沫若借鉴现代西方文化的得与失,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盲目追从。之后,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因素更加浓厚,民族的东西越来越少。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冯至后来就意识到中国新诗的发展不能一味地索取西方文化,也需要根植于本土的文化土壤,才能建设属于中国的文化。
二、面向西方:形式的自由与时代的哀歌
中国新诗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西方诗歌的影响。前面提到鲁迅认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既要“择取中国的遗产”,也要“融合新机”“采取外国的良规”,对其加以发挥才能使得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加丰满。因此,鲁迅主张翻译外国诗歌,但是也反对将外国的诗歌形式一味生搬硬套过来。冯至同样也看到中国新诗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在《中国新诗与外国影响》一文中他阐释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影响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5 世纪到8 世纪,由于佛教的输入,中国大量翻译佛教经典,印度的思想和传说对中国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对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他又重点梳理了从“五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特点:“一是从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部分重要西方诗人和流派对中国新诗都发生了影响,留下了痕迹,这些影响与痕迹是跟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化相关联的。二是有的诗人与西方诗人的情感有共鸣之处,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三是通过外国诗的借鉴,中国新诗在本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了不少新的意象,新的隐喻,新的句式,新的诗体。四是中国新诗人能直接读外国诗的只是一部分,有成就的诗人中通过译诗,或通过理论的介绍,间接接受到外国诗歌的也不在少数”[3]182。因此,中国新诗在经历前面三十年的成长积淀后也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不少现代诗人与西方诗歌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冯至也不例外。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也接触到很多西方作品并翻译了一些西方诗歌,比如歌德、海涅、尼采、里尔克、荷尔德林等诗人的作品,后人将其编为《冯至译作选》。冯至的翻译与创作是同时进行的,在西方诗歌的影响下,他也创作了具有西方色彩的诗歌,后来编成诗集出版,《十四行集》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冯至在早期并不主张创作格律诗,在他看来五四时期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人为了推动新诗的发展,提倡格律诗,但这一举动无疑为刚从旧诗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新诗套上新的枷锁,所以他更主张诗歌语调的自然与适当的形式。但到抗战时期,随着对外国诗歌的接触,特别是里尔克的诗歌,让他对十四行诗的创作形式与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曾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这类诗体是因为翻译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冯至是学德语的,但是他的一个友人范希衡是学法语的,一次范希衡给冯至背诵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并将其翻译出来,冯至根据他的讲解将这首诗记录了下来,成为一首译诗收到诗集《北游及其他》中。后来冯至也接触到一系列的十四行诗,他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一文中谈道,“十四行诗与一般的抒情诗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3]93。但是,真正促使他创作十四行诗的两大因素,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峻的社会形势以及自我思想的成熟;二是受到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启发。在冯至看来,里尔克借奥尔弗斯的形象表达了他的生死观,这让他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但里尔克对十四行诗的“特殊实验”才让他真正有勇气创作十四行诗。十四行诗在早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严格的格律限制与固定的形式,到里尔克这里便不再遵守这一规则,在里尔克看来十四行诗是最自由的,其诗的形式是最能变革的,可以随时变化和处理。冯至在里尔克“特殊实验”的启示下,才大胆地创作能“呼吸”的、自由的十四行诗。
从冯至的诗学主张中不难看出,他看到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现代诗人对西方诗歌的吸收也应转化为适应中国时代语境的新诗。从他自身的创作来看,在《十四行集》中他试图通过对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拷问,来唤醒每个人对真实存在的自觉、勇猛以及良知的感知,这受到了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里尔克等人的影响。但诗集中,冯至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十四行集》中冯至对“物”的感知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与里尔克认为物有所不同。①里尔克认为,物不仅拥有完满自足性,而且可以独立存在,因此,物得以象征人类的存在。在里尔克的笔下,物往往不被人所占有,相反物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通过这种方式,诗人得以在物的世界中将自我抽离,回归存在的本质,并且物本身带有内在的张力,在创作时应该把握物质客体的张力。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崇尚自然无为,大到宇宙、小到个体生命乃至尘埃,老子均予以赞美、称颂。老子的理想世界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贞”[5]。道家所特有的灵动、生机与和谐是里尔克所不具备的,但是却出现在了冯至的《十四行集》所构筑的生命体系之中。从“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他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我们准备着》)到“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有加利树》),这些诗中全然没有里尔克诗歌中的紧张感,而是舒缓与自然的诗风。总体来看,《十四行集》在形式上受到西方诗歌的启发,但在内容上表现的却是中国的时代精神与诗人个体心境的新诗,即中国化的十四行诗。
冯至的《十四行集》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他在《诗的呼唤》一文中提出了“新的形式是新诗发展的自身要求”[3]102这一观点。其实,新诗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摆脱旧诗的束缚,可随着新诗的不断发展,形式上的创新成为很多诗人创作的瓶颈。因此,新诗自身也在呼唤一种新的形式,西方诗歌便缓解了中国新诗涅槃的“阵痛”。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尽管中国现代新诗向西方自由地汲取养料以丰富自我的形式与内容,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但当知识分子兴奋地面向西方想象未来时,民族的危机会将他们拉回现实。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时代的哀歌扩展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内在张力,冯至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谈道,这一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光荣与屈辱、崇高与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耻……等等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眼前,使人感到兴奋又沮丧”[3]94。诗人们在时代的沉浮中,抒发个体的飘零与孤寂。因此,虽然西方诗歌为中国现代新诗打开了无数的创作窗口,使中国新诗与世界接轨,但是,中国现代诗人会选择适应自我、贴合时代的西方技巧融入到中国诗歌语境中,创造新诗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起点。
三、面向革命:民间的格律与“诗的还原”
郭沫若曾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进行过讨论,他认为,“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先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对立的”[6]。从20 世纪4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冯至的诗论主张也逐渐围绕革命①主题,而冯至的文学转向伴随着当时中国新诗史上最为重大的文化转向而来,即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明确提出了有关文艺的态度、立场和服务对象等问题。文学创作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诗歌要反映生活、歌颂生活。冯至积极地响应了这一号召。抗日战争期间,冯至创作不少政治抒情诗,比如《我们的西郊》和《我的感谢》等诗歌,“使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有了光彩/像是面对着东方升起的太阳”(《我们的西郊》);“你比太阳的光照还要普遍/因为太阳还有照不到的地方/它每天还在西方下沉”(《我的感谢》)。
这一时期,冯至对革命语境下的诗歌创作并没有以专文进行详尽讨论,但从他晚年的诗论中能寻到他对这一时期新诗发展的建议。在《扩大视野启发思路——读<中外民间诗律>》一文中,冯至认为,“这一时期民歌创作大都采取七言四句的形式,千篇一律,给人的印象好像民歌就是这个样子……可实际上民歌体裁多种多样,变化无穷。每句的字数可多可少,有的还插入长短不同的嵌字或衬字”。同时,他还对“民歌是诗的根源”这一观念的狭隘理解进行了批判,“以当前的新诗而论,若以狭隘的因袭观念看民歌,则民歌所能输送个新诗的,确实很有限”[3]159-160。因此,冯至认为,要平衡民歌与新诗之间的关系,才能促使两者之间相互借鉴与融合。正如冯至所批判的那样,中国新诗对民间诗歌吸收得太少,导致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虽然在20 世纪40 年代,一些人曾经主张诗人将民歌、民谣、快板、说唱等民间艺术融入到新诗创作中,使得“西化”的新诗迅速本土化。但新诗对民间艺术的汲取更多是为响应当时的文艺政策,诗人并没有潜心研究民间艺术与新诗的融合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歌谣体诗歌的千篇一律。总之,从冯至的诗歌创作到他的诗论观,在政治语境浓厚的年代,尽管他创作了一些符合时代语境下的诗歌作品,但也对这一时期产生的诗歌乱象进行了批判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在20 世纪40 年代,冯至的诗论除了反思革命时期大主题下的诗歌创作问题,也关注到诗歌创作中的文学素养问题。1944年,他发表的《诗与事实》一文批判了一些诗人为了作诗不顾事实。在冯至看来,诗是“事实”的,后世会将其作为最真实的史料,但如果这些“事实”是被一些冷漠的作者改编过,“人间便充满了不真实的文字”[2]49。这篇诗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诗人本身的文学素养与职业道德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性。1946 年,他在《论新诗的内容与形式》一文中则以“真实”为理论基点,分别讨论了新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收获。在冯至看来,“真实”是衡量诗的价值的标准,中国古代诗歌的成功是由一批“真实”的诗人造就的。虽然新诗还处在成长期,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冯至认为,“一部分现代诗人还是把握住了真实”。之后,冯至具体阐释了中国古代诗歌与现代新诗在内容上的区别,说明了中国新诗的三种境界,即“对于宇宙与人生的感应,自然的爱与积极的精神”[7]。最后,针对诗歌的形式问题,冯至认为“从旧形式的解放,再追求新的形式,这是新诗所表现的生命的欲望”。但新诗在形式上的创新也遇到了困境,冯至以李金发为例,指出了20 世纪20 年代诗人对西方诗歌技巧借鉴的得失,尽管这类诗歌在形式上让人耳目一新,但“过于艺术反而失去诗的生命”。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和反思之作。此后,冯至发表的《诗的还原》一文是他在1948 年南开大学新诗社上的演讲稿。文章主要讨论了诗的本质问题,冯至从“真实与空虚”“游戏与玩弄”“工作与聪明”“讽刺与油滑”“自由与散漫”五个范畴论诗,除了“自由与散漫”讨论的是新诗的艺术形式外,另外四个都是对诗歌创作态度的考察,他希望诗人都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完成诗歌。由此,冯至批评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左翼诗人的古板与夸张,他们往往将自己圈禁在小屋子里进行创作,缺乏真实的战斗经验而盲目地鼓吹光明与胜利,因而做出来的诗歌便是空虚的。
从冯至的三篇诗论来看,他将“真实”贯彻到诗人以及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严肃的创作态度以及自由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他对中国新诗近三十年的发展作出总结,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也对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风格、重要诗人及作品进行了点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冯至的诗论成就较之其诗歌作品缺少创新性。关于诗的“真实”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提及,如鲁迅揭示新诗的诗情所具有的特征第一个便是“真实性”,鲁迅认为“只有抒写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8]。而冯至对诗歌“真实性”的讨论并未超越鲁迅的观点,缺乏理论的深度与讨论对象的广度,这也是冯至诗论的不足之处。
四、余论
冯至的诗论作品并不多,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不可多得的创作时间逾70 年的诗人,他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国传统审美以及时代变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观,其诗论也就呈现出传统、现代与革命的三重面向。在这三重空间中,冯至自觉担任起中西诗学的建构者,也成为革命时期诗歌创作问题的批评者。他以一个文人的严谨态度意识到时代变化下的诗歌创作不能只汲取西方文化,也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使得在他的诗学观中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姿态。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冯至以“真实”为核心的诗学观以及价值观推动其走向另一个高度,他的文学态度对二十一世纪的新诗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