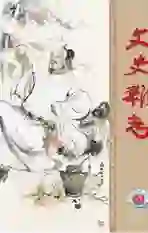古蜀文化研求浅论
2023-05-06李诚
李诚
摘 要:从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包括神话传说上分析,蜀、巴并非所谓共同文化,学界不可笼统以“巴蜀文化”呼之。从《山海经》的扶桑树与考古出土的三星堆青铜树相互发明而推出新认识的论证过程看,可以说,学术思想与研求材料两者乃相辅相成。
关键词:巴蜀文化;《山海经》;神鸟扶桑;新认识
没有对古蜀文化、古巴文化及其与巴蜀域外关系比较全面、客观、透彻的研究,任何有关华夏文化构成的讨论都将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随着近来三星堆考古再度的重大发现,尽管现在和未来这一方向的研究都难免有许多课题内外的纷扰纠结,却仍然值得研求者跋涉前行,予以艰苦的探索。故本文欲从学术思想与研求所使用材料两个角度,略陈对古蜀文化研求之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蜀文化”与“巴蜀文化”
或许读者已经注意到,本文以“古蜀文化”为题与时下言必称“巴蜀文化”略有不同。
当然,我并非在一般意义上非议“巴蜀文化”。“文化”乃一定时段、一定地域、一定族群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共有表现。它既是流动的(不断演变),也是历时的(可多层次切分),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但无论如何流动变化,上述四个“一定”与“共有”却乃基本前提。准此而论,笼统地提“巴蜀文化”,显然并不合宜。历史文献中, “蜀”固然见于甲骨,但纸质文献中却罕见。《左传》宣公十八年有“蜀之役”,但杜注却云:“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故于甲骨、《尚书·牧誓》中所谓“蜀”,顾颉刚先生亦以为类同《左传》中“蜀”。此说甚是。与之不同,“巴”则屡见于《左传》。故概观之,春秋及其以前,蜀、巴与诸侯关系完全不同,且蜀、巴之间亦罕有交流。这便无所谓“巴蜀文化”了。
“巴蜀”作为词组连称,始见于《战国策》。至于汉,则往往多见,尤以《史》《汉》二书为甚。但此“巴蜀”,不过秦汉以来涉及地理、行政區划之习谈。又特别值得注意者,西汉以还,中央朝廷注意于蜀而非巴,故往往言虽连带及于“巴”,而其实乃蜀。如班固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汉书·地理志》)又:“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同书《食货志》)是皆实说“蜀”而统称“巴蜀”也。又或所言本“巴”,却又往往连“蜀”而称之,如班氏所称“巴寡妇清”,太史公则称“巴蜀寡妇”。北宋建川峡四路,加之后来所谓“湖广填四川”之类区域外人口流入,以“四川”而统言“巴蜀”成习,更强化了以“巴蜀”连称或以“蜀”而概括“巴”作为地理、行政区划的意识,如明曹学佺于四川任上撰《蜀中广记》,名义上虽仅言蜀,实即兼述巴地。
又巴、蜀族群来历、民风、习俗乃大有不同,自古而然。揆之载籍,扬雄《蜀王本纪》谓蜀的来历云:“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全汉文》卷五十三)而范晔《后汉书》谓巴的来历则云:“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是皆神话传说中可觅蜀、巴之来历。仅此已不难见,从社会经济、文化形态而言,蜀、巴实有极大不同。蜀、巴各自所遗神话传说如此,已清楚显示出蜀、巴并非所谓共同文化。故缪钺先生说:“蜀在川西,巴在川东,经济文化,各有不同,并非一族,极为明晰” (《〈巴蜀文化初论〉商榷》),诚为的论。
“巴蜀文化”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不过近数十年来之事。其先后经历了郭沫若“西蜀文化”、徐中舒“古代四川文化”、顾颉刚“巴蜀”与“古蜀国的文化”,直至卫聚贤“巴蜀文化”,方成为论及今日重庆、四川等地域文化经常、当然使用的术语。然而综上所述,可知言必称“巴蜀文化”者,实多受秦汉以还之地理或区域表述习惯影响而未暇细思的结果。而这一问题的明晰,正是任何涉及巴、蜀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巴蜀文化”以坊间习称言,固无可无不可;若以学术研究言,则不能不考虑一定时段、一定地域、一定族群及其特定之文化特征与交流之历时过程,应有严格限定。窃以为,似可参考林向先生《“巴蜀文化”辨证》说,以古蜀文化、古巴文化、狭义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各自为题展开研究或更合乎文化历史的客观面貌。就古蜀文化研究而言,以由三星堆考古为代表的蜀地考古为背景,展开古蜀与中原,与巴之间联系的研究,与南丝绸路关系的研究,或将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这一研究对象,自然不能笼统以“巴蜀文化研究”称之。
二、纸质文献与考古材料
人文科学研究以求“真”为第一要义、为终极归宿;虽然这所谓“真”,始终是相对而言的。而欲得“新”,材料亦即证据的使用,毋容置疑乃关键环节。陈寅恪先生曾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固已说明新材料的紧要性。不过,以新材料研求新问题,所得固然“新”;以新材料结合旧材料以探索已经陷入绝境的旧问题,窃以为亦可谓之“新”。
如《山海经》,学人向来视为奇书,公认为中国神话之渊薮。以太史公之博学,亦谓“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山海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所记之域为何方?作者为何方人氏?与何种文化密切相关?历来多有讨论。上世纪,顾颉刚、吕子方、蒙文通诸先生即以为此书颇与古蜀相关联。惜生不逢时,讨论不了了之。如今,以三星堆出土的考古材料,可否与纸质文献相互发明,以证顾、吕、蒙诸先生所论之旧问题呢?诚然应当!兹举一例以明之。《山海经》记载有关太阳神话诸条,以诸材料参合观之,其大意为帝俊与其妻羲和生有十子,亦即十太阳。母亲羲和在甘渊为其子沐浴,沐浴毕,即让其停留于扶桑树上,一子停留于上枝,九子停留于下枝。当一只“乌”背负一子从扶桑枝头升起,太阳即出来了。这无疑是人类关于太阳及日出最美丽动人的神话!诚然,这一神话在其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变化:羲和由日母变为日御(《离骚》),再变为历官(《尚书》);乌则由背负太阳而居太阳之中,甚而成为太阳之代称。但《山海经》所讲述无疑更在上述变化之前。今考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青铜树,树枝分为三层,每层三枝,每枝上皆站立一鸟,全树共有九鸟。惟树顶上一枝已经残缺,但不妨大胆确认,树巅之上,定有一鸟。虽无法臆测此鸟与其他九鸟状貌是否有所区别,但却几乎可以肯定,它正是那只在《山海经》记载中背负太阳即将升起的“乌”,亦即为后世诸多文献中艳称的“金乌”。如此看来,此青铜树亦正《山海经》中“扶桑”树;此青铜雕塑所立体展现者,正乃《山海经》中太阳神话。不过颇为遗憾者,这座堪称世界瑰宝的青铜雕塑在一直以来的展览中,却与所谓汉代摇钱树置于一室,这就难免给参观者造成错觉,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系。其实这件瑰宝不仅不应与汉代摇钱树相提并论,更重要者,亦不宜如目前简单称之为“青铜神树”,而应呼之为“金乌扶桑”。“乌”乃古代文献中吉祥之禽,故这“金乌”,在历代文献尤其文学作品中又多称为“神乌”,是此瑰宝亦可得称“神乌扶桑”。与此相关,成都金沙遗址所出那件精致无以复加的“太阳神乌”金箔,也一定与“金(神)乌扶桑”一样,乃《山海经》太阳神话更为抽象的反映(似乎透露出古蜀人对四季的认知)。其所以只能称其为“太阳神乌”或“太阳金乌”,而不宜如目前简单称之为“太阳神鸟”,那是因为,“鸟”“乌”一字之差却决定了这件金箔与《山海经》的关系。且“太陽神(金)乌”正可与“金(神)乌扶桑”相互发明。这两件考古文物与《山海经》之紧密联系可谓意义重大:“金(神)乌扶桑”“太阳神(金)乌”立即获得了传世纸质文献所构成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撑。还不仅此,古蜀考古成果业已昭示,早在四千年前,传说中之夏肇始前后,古蜀之域就已出现非止一座城市;如此,则前贤已经论证过的《山海经》的地域、作者、文化归属便都有了地下考古文物确凿而不容置疑的铁证。《山海经》一书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亦将获得学术界全新的认识和重估。
回顾以上讨论,可以说,学术思想与研求材料两者乃相辅相成:在一定学术思想的自觉与指引下,往往能够显示出材料新的意义;而新旧不同性质材料的交叉、集合使用,又往往能够催生出新的学术思考。而更重要的是,以这样的思考为背景,过去所有尘封已久的语言、故实、民俗、神话传说,甚至前贤对古蜀文化研求的成就,或会重新苏醒过来,接受新的时代、新的学人的拥抱,并给予新的学人新的思想以有力的哺育和支撑。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