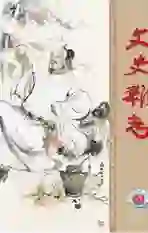从文物角度探秘“蜀身毒道”
2023-05-06王锦生
王锦生
摘 要:“蜀身毒道”是南方丝路的一部分,属于最早的中西交通线。在这条通道上发现的琉璃珠(蜻蜓眼)以及现存文物(如新津观音寺塑像及壁画)和史料证明,“蜀身毒道”不仅仅拥有中外商贸功能,而且还具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功用。
关键词:琉璃珠;异物;竺法兰;观音寺
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历史非常悠久,早于从中国西北、经西域去欧亚大陆的那条通路。
南方丝绸之路又分为多条道路,其中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它是最早的中西交通路线。
一、“蜀身毒道”发现的“蜻蜓眼”
“身毒”读作“冤读”,应是“天竺”(印度)的音译(《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从名称上看,“蜀身毒道”表明它是联接蜀地与古印度的通道。
“身毒”这个名称以及身毒国与蜀地的方位距离和早已存在的商贸情况最早是由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打听到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沿着这条路线发现过许多文物,它们以实物的形式见证着“蜀身毒道”这条路线曾经的情况。
图一是汉代石棺侧壁上的浮雕图像。画面表现的是一座庄园(或村寨)内妇人与外来商贩的交易情况。(按:此图上的庄园门阙、阙上的凤鸟、阙内妇人手中所举竹筹等其他内容因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无直接关系,故略去不表。)
该画面最为突出的是图左那位深目高鼻尖下巴、形象服饰与中国人样子完全不同、手持满挂絮状物品的售货撑杆并带着一个小孩的货郎。那个小孩的形象服饰与货郎完全一样,他们像是来自异域的一对父子。
从形象服饰看,这对父子应该是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人种。商贩撑杆上悬挂售卖的似是珠串或琉璃的那一类饰品。
前几天学生问我:“南方丝绸之路中国主要出口哪些商品”,我脱口说出“蒟酱、蜀布、邛竹杖”。其实,既称“丝绸之路”,丝绸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商品(在中国,丝绸的存在大大早于棉布),“而且近年在埃及的木乃伊还发现了丝绸”(赵殿增:《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专家们认为那些丝绸极可能是来自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国。而“蜀布、邛竹杖”则是汉代蜀地独有的最具四川地方特色的物品,是《史记》等典籍所记载过的经南方丝绸之路行销至异域的商品,也是汉代及汉代以前南丝路特别是蜀身毒道这条通道存在的证明。
而古代通过蜀身毒道到底有哪些异域商品进入中国,则历来语焉不详。
通过新津崖墓出土的这幅汉代画像至少可证明两点:一是除蜀地商人沿蜀身毒道前往域外,亦有异域商贾不远万里来到蜀地。如果认真考查,还能确认这些商贾到底是什么人种、来自哪个国家。另外就是通过此幅汉代画像可以看到沿蜀身毒道进入中国的商品的种类(从图上看至少有各种材质的珠串或琉璃制品)。它证明产自异域的各种材质珠串必然是战国(甚至更早至三星堆文明时期)及两汉时销入蜀地的主要商品之一。
四川地区的人们从来就有以各种珠串打扮装饰自己的风俗。从各地考古发现的大量珠子看,用珠串来夸富、敬神和打扮装饰自己的这种习俗从上古时期就一直存在并在以后的各個时期流行并流传下来,而且这种风俗至今还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盛行。
在四川地区各代遗址中多有各种材质的珠子出土,从石珠、骨珠以及玉、玛瑙、玉髓、水晶到琥珀、蜜蜡、珍珠、琉璃珠(图二)等皆有。这些珠子在唐代杜甫的诗歌中也能证实。杜甫将成都古墓葬中被水冲出的珠子称为“瑟瑟”。(按:杜甫诗《石笋行》所言“石笋”是战国时期古蜀墓葬地面的墓表。)四川出土的各种汉代珠子中有的材质(如绿色、黑色玉石珠等)明显不是国内所出。这些材质奇特的珠子也许就是随古蜀商人和许多与新津汉代石棺画像上那位异域商贾一样的商贩经由南丝路进入并沿其流布至国内各地的。
以各地考古都发现过的被称为“蜻蜓眼”的琉璃珠为例。据专家考证那种“蜻蜓眼”琉璃珠的原产地应该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被称为“两河文明”的伊拉克一带以及古埃及地区。专家们一直在为国内出土的那些战国至汉甚至更早的琉璃珠到底是本土制作还是自两河流域传入而争论不休。虽然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将出土的这类琉璃珠直言为“自两河流域传入”,但因没有明确证据而不能服众。而新津出土的这件汉代石棺画像则有力地支持了琉璃珠“外来说”观点。这些琉璃珠更是南丝路特别是“蜀身毒道”曾存在过的有力证明。
据查,两河流域地区的商贸本来就非常发达。那里的商人们善于贸易,其贸易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贸易方式之一”。那里“是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中心”。“考古发现史称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苏美尔人与阿卡德时代,有来自安那托利亚的黑曜石、来自阿富汗东北部的青金石、来自迪尔蒙(今天的巴林)的珠串和一些刻有印度河文明的文字的印章,说明当时在波斯湾沿岸有着很广的贸易网。”特别是“苏美尔的石匠和首饰匠会加工雪花石膏(方解石)、象牙、金、银、玛瑙石和青金石”,它们说明两河流域的商贾确实拥有制作珠子的各种质地材料和制作成商品的珠串。
二、琉璃珠是中外商贸的产物
仍然回到琉璃珠这个话题。
国内展示汉代琉璃珠最为有名的是云南省博物馆。该馆藏有云南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一批琉璃珠,其中还有形体纹饰与后来为藏族人珍视并被赋予浓厚宗教色彩的“天珠”相似的珠子。
除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那批琉璃珠外,云南其他地方也有琉璃珠发现,曲靖、大理、呈贡、楚雄、昭通等地都有过出土。所以过去有人认为这种琉璃珠是产自云南并将其纳入“古滇文化”。而如果联系到“南方丝绸之路”、联系到蜀身毒道、再联想到云南虽出土那么多琉璃珠但至今未能发现制作琉璃的遗址,而且联想到沿蜀身毒道经过云南域外之东南亚、南亚、西亚沿途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等物品,本人以为这些琉璃珠子制作于云南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证明它们是来自域外的可能性则极大。(按:云南省博物馆引以为骄傲的滇王墓出土的由很多珠子编成的“珠襦”,过去曾有人认为是受汉代中国葬制金缕玉衣的影响,而埃及考古则发现“有着复杂的穿缀方式的披肩式珠串,是每个法老及王后都佩戴的装饰品”。这种“披肩式装饰品”与滇王墓出土的珠襦比较接近。虽然《汉书·霍光传》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的记载,但描述的是生者的穿着。“每个法老及王后都佩戴”的以及“滇王墓”的珠襦的共性均是于墓葬中出土。)何况“滇王墓”位于蜀身毒道的重要节点上,说明滇王以珠襦入墓这种现象受两河或古埃及文明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珠子进入中国是与蜀身毒道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
除云南上述地区外,《三国志》记载(位于云南与缅甸接壤的)永昌郡“出异物”,这些“异物”甚至有详细清单:“犀角、象牙、帛叠(木棉布)、水晶、瑠璃、轲虫、蚌珠”(任乃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而在清单中“瑠璃(琉璃)”赫然在列。
“出异物”的上述这些地区恰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而且汉武帝所派出寻找蜀身毒道的多批使者都是找到了那里,却因被滇王留挽而没有继续寻找下去,导致当时官方寻找蜀身毒道的努力功亏一篑。这也旁证了滇王墓中这些包括琉璃珠在内的奇特珠子和南丝路蜀身毒道的关系。那些来自异域的“异物”应该都是经南丝路而带来的。
前举成都新津区的那幅汉代石棺画像因有人物形象存在,更是有力地支持了琉璃珠“海外传入”这个观点;并且因为是图画,这个证据便更直观而一目了然。
成都地区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应该有许多琉璃珠出土。事实证明不但在成都附近的汉代及汉以前的遗存中屡有琉璃珠出土,巴蜀其他地区的考古报告也屡有关于琉璃珠的记载;典型的、被引用较多的资料是1954年,在四川巴县冬笋坝遗址(今属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船棺葬中曾发现蚀花琉璃珠两颗。其球面有白色眼形纹(注意“眼形纹”已经与藏地“天珠”并无二致)。1978年,在重庆南岸区马鞍山西汉墓中又出土蚀花琉璃珠两颗,等等。
据考古资料,琉璃珠(蜻蜓眼)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汉代墓葬中出土很多但单座墓葬里出土的又很少,普通汉代墓葬里仅有一粒。能入墓随葬说明琉璃珠是墓主生前喜欢珍视之物;随葬数量少,说明琉璃珠这种异域商品十分珍贵。报载,2020年7月,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也在战国墓葬中出土有“蜻蜓眼”一粒。彭山区与出土石棺画像的成都市新津区紧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浪漫地认为,彭山区出土的这粒蜻蜓眼琉璃珠“就是”石棺画像上那对异域父子售卖给当地村妇的那一批蜻蜓眼中的一粒……
除琉璃珠外,对在古蜀遗存发现的早期作为钱币的贝壳,有学者認为是出自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
有学者还认为,彭山汉代崖墓里雕刻在墓门口的看家犬,其原型应是出自马尔代夫的“马尔代斯犬”。
将这些文物联系起来,一条沟通中外商业贸易的绵长通道便清晰起来了。
三、“蜀身毒道”还具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功用
相关文物及史料证明,“蜀身毒道”并不仅仅是一条商贸通道。
被尊为“中国佛教鼻祖”、被东汉明帝迎请而来居于洛阳白马寺中的印度高僧竺法兰是圆寂于洛阳白马寺,但他曾经在成都大邑县雾中山寺庙住过。(大邑雾中山上的寺庙与竺法兰之关系已有多人撰有考证文章。)
大邑雾中山是蜀身毒道(南丝绸之路)上的一座佛教胜地。而山中的寺庙开化寺恰是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仅晚于京城洛阳白马寺6年。这似也证明竺法兰是经蜀身毒道来到中国的。他是在大邑雾中山驻锡修整后才北上到的洛阳。
文献记载竺法兰本是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结伴前来中国的,因迦叶摩腾被弟子挽留,“法兰乃间行而至”,两人最后才在洛阳白马寺会合。竺法兰既是“间行”,显然就不是走的后来一般人常走的经由中国西北的那条大路,而应该就是经蜀身毒道历尽艰险才来到成都。
对从古印度到蜀地可供“间行”的通道,有不少典籍记录,如《大唐西域记》卷十就记载说,印度诸国之伽摩缕波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大唐西域记》等文献的记载亦足以旁证竺法兰“间行”之路线与历经艰险的情况。
从印度经由蜀身毒道来到中国的僧人应该历代皆有,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成都新津区观音寺罗汉塑像中有完全是印度僧人形象的。
新津观音寺罗汉殿过去开放时,好多游客看到这尊罗汉造像时都会联想到印度电影,一些老年人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哼唱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在观音寺众多罗汉的塑像中,其他罗汉都是正常的中国人甚至是典型四川人形象,惟图三的这尊是印度人形象。
新津观音寺塑像及壁画是明代成化四年(1468年)塑成的,足见当时亦有印度僧人在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此尊罗汉旁边的那位罗汉就是完全的四川人形象,可以推测,明代画工在塑像时比照的“模特”就是当时四川本地寺庙里的和尚,而那些和尚中有一位是来自古印度的僧人。
除了由古印度来中国传播佛教的僧人外,后来也有许多中国僧人是沿南方丝绸之路至古印度的。唐代僧人义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州牂柯道出,向摩珂菩萨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任乃强先生注:“现今地属东印度”)。
不但在唐代如此,后来各个时期也有中国僧人沿蜀身毒道进出弘法,直至近现代。其中最有名的是谢无量先生族弟、原籍四川乐至的万慧法师(1889—1959)。万慧法师于成都大慈寺削发为僧后云游四方,经云南出国至缅甸,又赴印度钻研佛法,后定居于仰光,为缅甸社会各界尊崇,在华人圈中有着极高地位。
一般人概念里,中国前往古印度等地的僧人只是“取经”“学法”。其实文化交流是双方的事。那些前往印度的僧人必然也是将中国文化带到了印度。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的众多在印度求法的僧人中有一位道希法师。《高僧传》说他在印度“周游诸国,遂达莫诃菩提,翘仰圣踪经于数载。既住那烂陀,亦在俱尸国。蒙庵摩罗跛国王甚相敬待。在那烂陀寺频学大乘。住输婆伴娜(在涅槃处寺名也)专功律藏。复习声明颇尽纲目”。
《高僧传》还说,道希法师“有文情善草隶”,曾“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并在那烂陀矣”,也就是说道希法师曾在印度留下了记载中国经籍文化的石碑、留下过“中国石经”。
此外,据唐代《大唐西域记》《慈恩传》《开元录》等多个典籍记载,印度戒日王曾对玄奘说到流行于大唐的《秦王破阵乐》。连大唐的音乐都被印度人熟悉了,可见当时文化交流的盛况。而这些都说明丝绸之路除巨大的商贸功能外,还有重大的文化交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