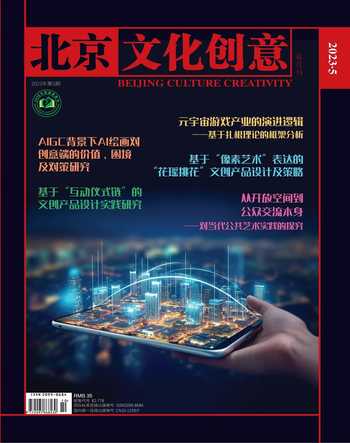传统文化跨文化传播背景下“鲁班工坊”走出去路径探究
2023-04-29曾淑媛汪星星
曾淑媛 汪星星
摘要:“鲁班工坊”是我国职业教育跨文化传播发展的样板,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由著名工匠鲁班生发出的符号化联想也为现代职业教育赋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能量,使得鲁班代表的工匠精神伴随着“鲁班工坊”的“走出去”在不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落地生花。本文主要探究“鲁班工坊”的文化符号建构,并借由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这六种传播类型对“鲁班工坊”的海外传播实践进行解读,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鲁班工坊 文化符号 传播类型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及其相关应用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
学界普遍认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在其1959年发表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正式提出的,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历史却可以被追溯到人类社会初期。①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学者将跨文化传播从更为宏观的人类学知识谱系中剥离出来,通过从语言学、教育学、传播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拓宽学术领域、深化学科范畴,使之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跨学科理论体系。②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之下的。因此,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西方学界主流侧重于关注它是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影响人类交流活动的,并强调因东、西方的主、客体身份所带来的“差异”和“冲突”而形成了二元对立局面。③
而后,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研究被引入我国学界,并再次经由多学科视角的汇入形成了交叉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拓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学者们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研究出发点,针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热情高涨。但是,“跨文化传播”作为舶来的学术理论概念,在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因其长久此以往的“二元对立”学术惯性,不可避免地让学者们落入西方研究框架的窠臼。同时,国内的多数研究仍处在用既有西方理论对本土案例进行阐释的阶段,还未触及对理论核心的更新和再发展。除此以外,在阐释的过程中仍集中在以物质文化为重点的文化内容推介上,而以物质文化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被受众接受并不一定代表着其文化理念被认同。④在研究内容上,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关注跨文化传播学理层面,并主要集中于将推动文化“走出去”作为研究目的进行讨论。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国家软实力、媒体传播力、文化辐射力几方面出发,属应用型研究,对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以及“对外文化传播”几种研究取向则界限模糊。因此,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通过对本土实践、理论的深度探究,探索关于“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和“中国理论的世界阐释”有一定研究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传播理论应用:“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主导的跨文化传播
有别于“冷战”之后形成的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在平等与合作的新型理念指导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学者苏婧与刘迪一认为,与主流西方二元对立、凸显主客体的思想内核不同的是,“一带一路”作为国家之间的顶层倡议,倡议的是恢复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关系的内在特性,即在保留各自文化核心特征的基础上,主张多元共存而非同化同质。在此语境之下萌生的跨文化传播相关讨论和实践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和传播,典型案例之一是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已有多年发展经验、并在海外合作国家收获良好口碑的孔子学院。而被称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的“鲁班工坊”,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样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
二、跨文化传播的平台:“鲁班工坊”现状概述
“鲁班工坊”是以“大国工匠”精神为依托,由天津市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它搭建起我国职业教育与世界国际教育接轨的桥梁,旨在培养一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和平、德技双修的具有国际合作精神、适应合作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①“鲁班工坊”的名称取自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发明家和工程师鲁班,他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工匠师祖。鲁班本人所代表的工匠精神和创新智慧,加上其所处时代应运而生的“兼爱”“非攻”的班墨文化,使得“鲁班工坊”这一职业教育品牌的命名既能体现传授技术技能的功能性作用,又能展现植根于厚重历史文化背景的深远内涵。②
如果说“孔子学院”是现代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开拓者,那么“鲁班工坊”则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打开了“新窗”。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教育充分发挥了其夯实基础的先导作用。“鲁班工坊”不仅鼓励各国分享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成果,搭建互利共赢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③,还作为中国在境外创建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合作载体,在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和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备里程碑式意义,丰富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和具体实践。④
自2016年首个鲁班工坊投入使用以来,该模式行之有效,至2022年,我国已在亚、非、欧三大洲19个国家建成20个鲁班工坊,全球化布局已然开启,⑤并为世界职教贡献了“中国方案”。“鲁班工坊”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旨在以境外办学和国际合作办学为主要方式,为沿线国家和国内外相关产业输出我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培养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⑥“鲁班工坊”既面向市场、利用市场手段,又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抓手,使得此模式兼具四重功能,分别是:培养优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功能,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实体化的社会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并与欧亚经济对接合作的经济功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成熟的中国特色教学模式的文化功能。⑦四种功能彼此相融、相互促进,使得“鲁班工坊”的跨文化传播迸发出新的发展可能性。
三、跨文化传播的内容:“鲁班工坊”的文化符号建构
“鲁班工坊”作为一种“走出去”的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始终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出现,其名称由“鲁班”和“工坊”连缀而成,二者作为独立的符号有着专属的传统文化意涵,当合二为一时又使得以“鲁班工坊”为名的职教品牌焕发新的生机。与此同时,它的文化内涵也随着越来越多所“鲁班工坊”在海外的建成而不断演绎,不仅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打开了新思路,也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传播路径。
(一)“鲁班工坊”作为文化符号
“符号”在人类文化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文化符号更是承担着展现文化软实力、传递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功能,并辅助国家主体形塑国家形象、建构文化身份、增强文化自信。从20世纪初,现代符号学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语言学的视角下提出所有符号都包含“能指”和“所指”两部分②,到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从文化的本质入手,提出人与动物的不同是能否利用符号和以符号为手段,阐释已有事物,③到20世纪60年代,以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推动了“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建构,④到20世纪下半叶,罗兰·巴特在索绪尔语言学角度的符号学的启发之下,拓宽了结构主义的研究疆域,认为“人只是结构中的一个符号”,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赋予事物意义,才能达到“结构”的目的,并以敏锐的时代目光剖析了各种文化现象,可谓是意义分析的利器。⑤至此,文化结构主义的形成标志着文化符号学的成熟。⑥总体而言,将符号理论引入文化研究领域,为学者们观察世界和研究历史提供了崭新的思考角度,基于此,本部分也将分析“鲁班工坊”的符号意义。
有关于鲁班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播历史,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内,鲁班都不再单一地代表具体历史人物形象,而是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承载了深刻意涵。鲁班又名公输盘、公输般,尊称公输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著名工匠。据现存的文字记载和口述文艺,有关鲁班的历史可划分为以下阶段:在先秦和汉初,鲁班事迹的记载多基于历史事实。而汉魏至唐代,鲁班形象及事迹则逐渐传说化。⑦在现有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与“鲁班”传说相关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匠精神”与鲁班形象的共通性上,并以鲁班这一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工匠精神”的历史演绎和文化内涵。⑧
“鲁班”作为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传说中多被描述为木匠行业祖师爷和神圣的技艺传授者,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在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文化符号“鲁班”才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形塑文化身份、增进民族团结、加强文化自信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建构文化认同体系。⑨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思想深入人心,类同祖先作为一种符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整合起一个区域的文化认同,作为手工业祖师爷的鲁班也以拟亲缘的方式串联起手工业从业者的情感联系,用文化符号“鲁班”唤醒“根基性情感”,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提供重要动力。⑩爱尔兰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符号则是想象共同体的媒介,因此,民族共同体实质上是符号共同体。?故而,“鲁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背后的“工匠精神”的文化内涵和“大国匠心”的文化认同连结起来,形成了稳固的“文化认同—文化行为—文化符号”的映射关系。
“鲁班工坊”通过文化符号“鲁班”来建构具有标识性的文化身份,深层融合现代教育和传统文化,以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形式传递我国主流价值观,有助于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跨文化传播。从名称上看,“鲁班工坊”由“鲁班”和“工坊”连缀而成。前者是代表着技术技能领域的高超技艺、精益求精和创新精进的匠人精神的文化符号,后者则强调工作环境的小而精和工作流程上的雅且细。除此之外,“鲁班工坊”的品牌标志也是重要的视觉符号。其标识设计主要由圆形和方形组成,寓意“天圆地方”。“鲁班工坊”的汉隶四字以金镶玉的理念呈现,并成为该标识的视觉中心,以此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的输出对于“鲁班工坊”的重要性。①其背景融合了祥云、书本、阶梯和滴水檐四种传统纹样,在彰显教育理念的同时寓意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不忘初心,面向未来。②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鲁班工坊”的名称上,还反映在视觉设计上。因此,“鲁班工坊”不仅在推进国家文化符号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实践了跨文化传播,还以其多元的文化吸引力拓宽了国际文化传播途径。
(二)“鲁班工坊”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平台
“鲁班工坊”作为一种以技艺相传为表现形式的文化传播,本质上是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和融合。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主体在本族文化背景下进行编码,通过媒介将本民族文化传达给受众,受众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进行解码,传受双方的文化差异制约着解码的有效性。③对于“鲁班工坊”而言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得益于相对接近的地理位置、经由历史发展而带来的文化上的接近性,不仅使解码成功的可能性增大,也使得传播的阻碍减小,有助于“鲁班工坊”这一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的作用。
综上所述,“鲁班工坊”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具有一体两面的特质。“鲁班工坊”不仅从名称上通过文化符号“鲁班”来建构具有标识性的文化身份,更以职业教育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平台传递我国主流价值观。伴随着更多所鲁班工坊在境外院校扎根,其符号的内涵必将经历不断演绎的过程,其文化意涵也将随着传播路径的多元化而逐渐丰富。
四、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鲁班工坊”蕴含的六种传播类型
“鲁班工坊”在实践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利用了人类传播的六种传播类型,即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鲁班工坊”目前已通过这六种传播类型建立起了踏实稳固的传播渠道,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丰富的借鉴意义。因此,本部分将结合“鲁班工坊”在海外实践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拆解其使用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并对应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内向传播奠定传播基础
内向传播(又称为自我传播、人内传播)是传播活动的基本类型,它是人在意识世界中不断调动新输入的外部信息与人脑中积淀的内部信息,进行一系列的符号化操作,诸如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最终形成决策,以便指导自己后续言行的内在过程。在此基础上,人类开展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活动。④
“鲁班工坊”通过直接的面对面课堂教学和文化推广活动,将中国文化与工匠精神的形态和理念传递给受众。以英国“鲁班工坊”开展的国际化中餐烹饪专业人才培养为例,纵然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中餐热”也在世界遍地生花,但外国受众普遍对中餐烹饪的原料、调味、用具等存在认识盲点,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鲁班工坊”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首先,他们创立了中餐烹饪艺术培训模块,通过系统性的讲解和演示,教师将中餐的原料、调味、用具等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引导他们亲自动手操作。其次,他们运营面向公众开放的产教融合“鲁班餐厅”,通过实践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餐烹饪的实际操作和菜品创新。同时,在“鲁班餐厅”的装潢设计中,融入了鲁班锁、鲁班伞等具有文化内涵的设计元素,让受众们沉浸式地体验鲁班工艺,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⑤受众接触这些信息后,经由味觉、视觉、触觉等过程进行信息处理,并针对信息内容向鲁班工坊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在沟通的过程中,受众的认知不断调整与适应,而后实现认知和谐,传授双方从而实现意义共享,在中国文化元素理解上达成一致,受众也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和“鲁班工坊”从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到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活动的完整内向传播过程。
(二)人际传播助推二次传播
文化是一套符号和认知的系统,鲁班工坊将文化符号所承载中华文化加以推广,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认识、了解以及认同中国文化和工匠精神,使中外双方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建立意义的共享,其主要途径便是人际传播。目前,鲁班工坊主要通过直接的课堂教学、文化推广活动等人际传播形式推广中国文化和工匠精神,受众经由内向传播成功认知鲁班工坊及其所代表的工匠精神,进而自发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再次完成了人际传播活动,鲁班工坊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得以扩大。在此过程中,相关参与人员的跨文化认知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人际传播的效果,这就需要跨文化人际传播的参与者不仅具备坚实的汉语言文化知识,而且需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不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在他者文化中顺利完成传播过程。故与其他几种传播类型相比,人际传播的效果更为直接,是鲁班工坊实践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群体传播促进文化认同
群体传播是一种具备传播主体多元和非制度化、非中心化特点的传播形态,群体成员的参与、互动及分享不但可以促进意义在空间上的弥散,而且可以促进情感在时间上的延续。①国际学生作为双文化个体有更复杂的文化知觉和文化知识结构,因而更容易受第二种文化环境的影响。在群体传播中,国际学生个体通过主动管理和调整认知来积极寻求身份认同,并在群体中获得的积极情感从而满足其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最终接受新文化语境下的自我身份 。②
在线下教学课堂群体中,课堂文化很大程度影响着课堂成员的心理和行为。因此,良好的课堂传播生态环境对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鲁班工坊定期组织中国教师和技术人员,为当地教师开展技能培训,同时也会邀请对方来中国进行实地交流,这种线下互动教学是“鲁班工坊”在进行群体传播时的具体实践。教师可以通过研究国际学生的课堂传播运行过程和接收信息的意识、态度及行为,探讨有效的班内传播策略。在此过程中,以班级或学校为单位开展国际学生跨文化教育对达成群内共识起到重要作用。
(四)组织传播推广品牌活动
组织传播是指一个组织使用其特有的组织媒体工具和传播措施来进行的传播,其目的是形成组织氛围,凝聚组织力量,展示组织影响,促进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和组织外部的良性互动。③组织传播把传播作为描述和解释组织的一个途径,组织、受众和媒介三大要素构成组织传播,其中媒介是组织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受众是组织传播中特定的受众群体,组织是维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传者主体,也是组织传播活动的核心所在。④就组织传播的主体而言,“鲁班工坊”将政府视为其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依托政府间的战略合作为“鲁班工坊”的有效性背书。同时采用非政府组织形式,借助职业院校间国际合作以及企业间需求间校企合作,搭建起世界范围内职业院校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也与世界共享了中国职业院校技能的标准和形成模式。⑤简言之,我国以“鲁班工坊”为传播媒介建设了全球性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平台,并在平台内部凝聚国际各方力量,积极开发国际议题,从而向国际共享中国职业教育智慧。
(五)大众传播拓宽传播路径
大众传播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是文化的引领者,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⑥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并由专业化群体依托这些机构和技术,运用如报刊、广播、电影等技术手段向广泛受众传播内容所使用的工具⑦。在鲁班工坊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常常借助电视节目、报纸、广播等媒介将鲁班工坊的相关信息以新闻的形式传达给受众,受众会综合新闻报道情况,构建自己心目中的鲁班形象及工匠精神。因此,大众媒体如何报道鲁班工坊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鲁班工坊形象的认知和建构。在融媒体时代,鲁班工坊与时俱进,于2023年2月,正式启动“鲁班工坊”网络传播项目,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丰富大众视听体验,聚合多方面受众为中华文化打造立体化、多维化的传播空间,让更多跨文化故事得以广泛传播。
(六)国际传播助力民心相通
国际传播指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实施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由外向内的传播是指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由内向外的传播则是指把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向国际社会传达。①
在宏观层面上,鲁班工坊从具体情境出发,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心的国际传播中,结合受众自身的政策、利益等因素,通过建设体验馆、参与举办世界职业教育大会等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促进民心相通,充分利用能让全体受众共享并具有较强传播感染力的因素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微观层面上,无论是外派至境外“鲁班工坊”的中国教师还是深耕本地职业教育的当地教师,都秉持着“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的原则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启迪。为了提高沟通效率和增进中外友谊,几乎所有外方教师都注册了微信,双方教师因地制宜改进培训内容,②以期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才,为中外务实合作提供新的典范。
五、结语
“鲁班工坊”依托于我国自古闻名的鲁班工匠精神,积极实践了六种传播类型,现已成为中国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③从名称上看,“鲁班工坊”不仅通过“鲁班”的符号化联想来建构具有标识性的文化身份,更以“工坊”这一彰显职业教育色彩的媒介传递我国主流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家“鲁班工坊”在境外院校扎根,它所代表的符号也经历了不断演绎的过程,其文化意涵也将伴随着传播路径的多元化而逐渐丰富。“鲁班工坊”在践行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中也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传播的六种类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跨文化传播的效用,为其他跨文化传播组织,尤其是教育主体,提供了发展思路。
Abstract: “Luban Workshop” is a Chinese educational brand that can provide a new context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mpowered by the craftsman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well-known craftsman “Luban”, “Luban Workwhop” and its artisan spirit have been initiated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symbol construction of “Luban Workshop” and interprets i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through six types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group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work to support for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uban Workshop,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