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静止到运动
2023-04-29刘阳tasi赵洋逸管陶然
刘阳 tasi 赵洋逸 管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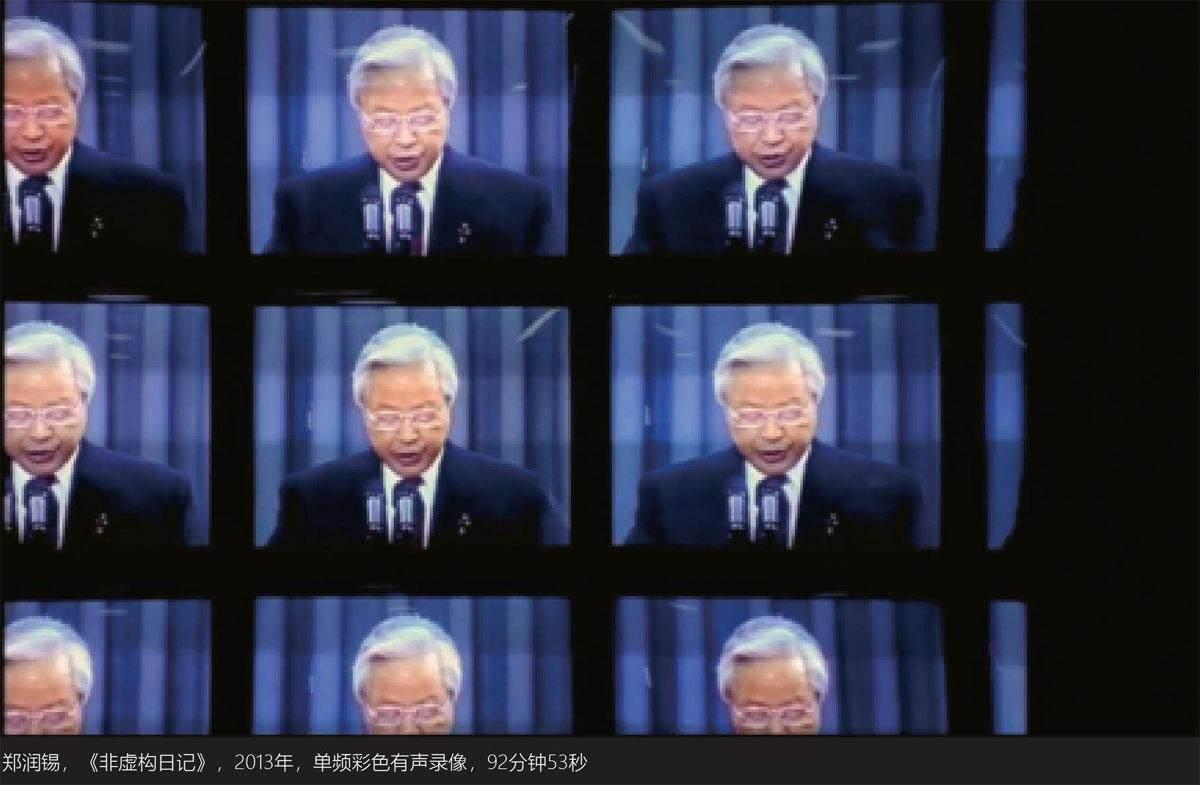
Video art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其便成为了艺术家们的重要艺术媒介。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变化性的艺术形式,Video art与科技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与现实交相互动时,光有皮肤已不足够。科技已然成为身体存在的新的保护膜。”(白南准)并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Video art和摄影一样,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因为Video art的包容性和变化性,这也打破了由绘画、摄影和雕塑等媒介所构建的“艺术形态”,成为当下艺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23年6月22日,由蔡冠深基金会与法国驻华大使馆联合推出的“蛇纹绿岩”展览在北京白云馆开展,它是一个关于第二届“蔡冠深基金会当代艺术奖”获奖艺术家的集中展示——通过曹明浩和陈建军、阿德里安·米西卡(Adrien Missika)的艺术实践,来展示/讨论人类与世界/自然之间的“新”关系——“此次展览的题目借用了曹明浩和陈建军作品中所提及的‘蛇纹绿岩。……蛇纹绿岩把我们对于那些自然灾难频发地区(如山脉和海沟)的成因,从‘断裂引导进一种‘缝合的思维里去。作为一个美好的隐喻,蛇纹绿岩给我们提示了一种与他者和未知的相处之道。我们应该不断地去努力靠近复杂的现实,主动想象一种不走向各自为战的文化断裂与生物阻隔,把天然的差异与激烈的碰撞看成一种积极的缝合行为。这也是展览中艺术家的创作给我们最好的提示。”(文字选自策展人卢迎华在展览“蛇纹绿岩”开幕式中的讲话)
在2023年8月26日,“意义”展览在北京中间美术馆开展——“展的起意与我们的近况有关。回望过去漫长的三年多时间,旅行几乎中断。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也依旧努力与世界各地的创作者及艺术机构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个在美好的全球化时期生长出来的艺术网络经历了由于物理空间和思想智识上的阻隔所带来的种种考验,仍然保持着友谊的信念,在无法见面的情况下将其他地方的艺术讯息传递给我们。透过这样一些联系,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全球年轻创作者的一些近况,其中以录像艺术为主要的创作媒介。在身体无法抵达彼岸的情况下,来自全球各地的影像创作为我们保留一个透视世界的窗口。”(文字选自“意义”展览的前言)
近些年,“影像艺术”“录像艺术”“视频艺术”等词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并成为我们观看和讨论的热点。但是,相较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摄影艺术”,它们似乎显现出了不一样的内容与形式——其既有许多与摄影相似的部分,也有更多与摄影迥异的部分。这就让很多以摄影知识/经验为基础的人们在具体观看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困惑——我们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解读,甚至不能理解它们出现在艺术机构中的缘由……那么,藉由这些疑惑出发,我们一起来重新观看和梳理“影像艺术”“录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历史、内容以及它们与摄影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我个人认为:“影像艺术”是基础,也是最近于Videoar t的译词,而“录像艺术”“视频艺术”则是“影像艺术”的具体形式——虽然在艺术史中,“录像艺术”才是最早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出现要远早于“影像艺术”。作为一个舶来品,“Video ar t”这个名词在具体传播的过程中,以及不同的展览/讨论语境里被我们人为地转译成了不同的中文名词——“录像艺术”“影像艺术”“视频艺术”“多媒体艺术”等等,以此来适应人们的不同需求,虽然它们的基础同为“Video ar t”。而且,在转译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就像摄影领域里,在将日本的“私写真”转译为中国的“私摄影”时,无形之中,其原本的含义就被我们改变了。作为一种文化的梳理过程,借用当下的艺术史体系/脉络自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因为“录像艺术”作为众多转译词汇中出现最早,也是“Video ar t”里最为重要的一个存在——尤其是在“艺术”的语境下。那么,一切讨论的开始也便从具体的“录像艺术”的发展逻辑作为起点。
录像艺术(Video ar t),是一种依靠录像技术作为视听媒介的艺术形式,其因最初的模拟录像带而得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的消费级录像技术(如录像机)开始在广播公司以外的领域被使用,而模拟录像带是当时最常用的记录技术,许多艺术家开始探索将录像——动态影像——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于是,录像艺术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变化起来。录像艺术有多种形式:记录传播;在美术馆或博物馆观看的装置艺术;在线流媒体作品、以录像带或DVD形式发行的作品;以及结合一台或多台电视机、视频显示器和投影设备,显示现场或录制的图像和声音的表演等等。
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争的远去,世界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科学技术重新向民用市场转移——以原子能、航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在美国率先兴起;经济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速基本稳定在5%左右,其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0%,众多美国人无需过多工作便能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准;文化中心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而且,它们在美国被迅速地吸收和转化后,开始发生新的转向——“在纽约,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克雷斯·奥尔登伯格(ClaesOldenberg)和吉姆·戴恩(Jim Dine)的偶發艺术,罗伯特·劳申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混合媒体作品(配有床、小鸡标本和电线),卡罗里·施内曼(Caroles Schneemann)的身体装置,以及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霓虹灯画板,不过是当时展出的多元化艺术品中的数件而已。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曾宣称,艺术(他指的是绘画和雕塑)的意义蕴藏在作品之内;现在,他的座右铭受到了冲击,因为时下的观念是,观念和语境才是艺术实践的核心。”(文字选自《20世纪后期的录像艺术》,作者迈克尔·拉什)于是,世界艺术开始进入到“后现代主义”阶段,其核心为反对精英艺术,将个人主义的主观表达转向为注重客观世界,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注重使用大众传媒和消费形象,使艺术走向平民化……其中,电视或者说电视系统是文化转向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作为凝结了科技与经济的集合体,它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恢复了固定电视节目,而到了1960年,美国90%的家庭会拥有至少1台的电视机,并且,其每日的平均播放时间也超过了5小时……在这些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电视悄然地改变或者说重塑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政治理念……博特·马尔库斯(Herber t Marcuse)就曾指出:大众媒体和社会控制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创造了一种索然无味的一致性,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被称作“单维度的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对于主流社会和价值观没有任何判断,更不会提出反对和批判的意见。
20世纪60年代,战争再次成为了重要的问题。而且,随着“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诸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激进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兴起,美国也从“平稳期”重新进入到了“振荡期”——“与此同时,政治呼吁、毒品的泛滥和摇滚音乐的流行也为这股青年反叛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主流社会和反文化英雄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这些反文化的年轻人渴望一种更加开放和平等的社会。这些新崛起的、政治化的一代开始采用一种批评性的姿态和截然不同的制作方式来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以此发展一种新型的和更加包容的社会结构、替代性的机制和更加民主的文化制作类型。”(文字选择《砸碎显象管:有关录像艺术的简史》,作者凯特·霍斯菲尔德,译者马永峰)那么,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动荡的社会环境等多元背景下,艺术作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具体反应,其内容开始变得更加多元,更迭的节奏也开始变得更加快速——在短暂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主旨迥异的艺术流派如浪涛一般汹涌而来,“抽象表现艺术”“波普艺术”“环境艺术”“地景艺术”“极简主义艺术”“概念艺术”“激浪派”“贫穷艺术”等等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迅速地蔓延开来。
贡布里希曾说: “ 没有艺术这种东西, 只有艺术家。”那么,“录像艺术”的内容和定义也是由艺术家的具体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在多元与变化的背景下,索尼于1965年推出了便携式摄像录像机——Sony Por tapak(有的资料显示为1967年,但如果是1967年,这就与白南准的最早录像艺术实践相矛盾),这成为“录像艺术”诞生的直接原因——赫敏·弗里德(Hermine Freed)曾这样评价Portapak——“Por tapak似乎是专为艺术家而发明的。就在纯粹的形式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在制造物品在政治上变得令人尴尬,而什么都不制造却令人啼笑皆非的时候;就在许多艺术家都在做行为作品却无处表演——或者觉得有必要记录他们的表演——的时候;就在提出伯克利式的老问题——‘如果你在沙漠中建造一座雕塑,没有人能看到它,那它存在吗?——开始显得愚蠢的时候;就在电视比墙体能够向更多人传达出更多清晰信息的时候;就在我们明白为了定义空间,必须要有空间感的时候;就在其他学科的许多既定理念受到质疑、新模式被提出的时候;Portapak出现了。”
据传,1965年,白南准在麦迪逊大道用1000美元购买了当时刚刚上市的索尼Por tapak,而后就用它拍摄了一段教皇保罗六世车队巡游纽约时的情景,并于当晚在格林威治村布里克街的一家咖啡馆里进行了放映——从现实的意义讲,白南准的这一行为是将原本由国家/公司控制的拍摄与传播的权利释放到了个体身上。由此,艺术史工作者们便将1965年10月4日称作“录像艺术”的诞生日。但是后来,人们在整理白南准的作品时,却意外发现作品ButtonHappening 的存在,它应该是白南准现存最早的录像艺术作品——这也可能是他的第一盘录像带,它记录了白南准的一个简单的表演动作——扣上和解开夹克的扣子,完全遗传了激浪派的艺术理念。
从作品Button Happening 中可以看出,“录像艺术”与“激浪派”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比较确切地说,“录像艺术”的最初起源与“激浪派”有着紧密的关联。1959年,当白南准在联邦德国广播电视台工作时,他开始接触到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的艺术理念——“我带着一种讽刺的心态去看约翰·凯奇的音乐会,我想看看美国人将如何处理东方的文化遗产,在音乐会过半后,我慢慢有了兴趣。在这场音乐会后,我彻底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文字选自《录像艺术史》,作者克里斯·米-安德鲁斯,译者曹凯中、刘亭、张净雨)后来——1963年3月,白南准在联邦德国伍珀塔尔的帕纳斯画廊(Galeri Parnass)举办了自己的首个个展 ——“对音乐的说明——电子电视”(Exposition of Music——Electronic Television),通过对电视机的线路进行调整,他将电视从既有的“社会系统”中脱离了出来,并进入到了艺术的语境中——从某种意义讲,这跟杜尚( Marcel Duchamp)的《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随着电影、电视、广播视频和投影等技术的发展,摄像机和电子混音器等电子产品开始进入了艺术家们的视野,并成为他们进行艺术实验的工具——新的科技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1963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开始拍摄自己的实验电影作品——《睡眠》(Sleep ),他用固定机位以长达5小时20分钟时长的超级长镜头拍摄了约翰·乔诺(John Giorno)的睡姿,以此来模糊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后来——1970年初,沃霍尔也购买了索尼Portapak,开始将录像正式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媒介。
盖瑞·苏姆( Gerry Schum)则是德国录像艺术的早期实验者,但他的录像艺术实践与白南准和沃霍尔有所不同——或者说,他是将白南准与沃霍尔的艺术实践方式进行了融合。他将电视系统视为艺术体验的直接媒介,在1968年夏天,苏姆创作了录像作品《消费艺术的艺术消费》(Konsumkunst-Kunstkonsum ),同年10月,他在科隆德国联邦广播电视台上播映了这个作品——以公共播映的方式呈现了这个作品,这也传递了德国艺术家海因茨·马克(Heinz Mack)对于电视的某些设想:“我打算做一個不在博物馆举行的展览。这个展览不在画廊里,只在电视上出现一次。我在本次展览中展示的所有物品将只通过电视机向公众宣传,然后这些作品就会被我销毁。”后来,苏姆还成立了“电视画廊”,这是一个在电视上展出视频艺术作品的画廊 。
从白南准、沃霍尔和苏姆等人的具体艺术实践出发,我个人认为“录像艺术”的形成并非是单一线索的,“激浪派”“电视系统”“电影”等艺术形式与文化系统共同影响或者说孕育了“录像艺术”的出现。而且,作为一种由多元文化形式/系统形成的艺术形式,“录像艺术”天生就具有极强的包容与多元的属性——“正如本杰明的观察所示,这个‘科技复制性的世纪,不仅改变了创作方式——因此电影,以及其他所有由电影而生的事物(电视、录像带),就成为本世纪的中心艺术——而且也改变了世人观看现实并体验创作物的方式。”(文字选自《极端的年代:1914~1991》,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而作为最早的录像艺术实践者/实验者——白南准、沃尔夫·弗斯特、沃霍尔和盖瑞·苏姆等人,为录像艺术的出现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他们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将录像从电视和电影系统的集权中解放了出来。但因为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大部分的录像艺术实践依然停留在比较基础的层面——罗伯特·平卡斯-维塍(Robert Pincus-Witten)曾做出过这样的评论:“创造‘第一技术艺术工具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在未来的神话中‘迷失自我,同时拒绝承认其制作的‘劣质艺术品。‘图像处理技术的缺陷正是因为其与现代主义绘画主义过时、陈旧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利萨如图形的象征,电子艺术流行的旋转振荡,被综合成一种最熟悉的表现主义并置:深层图像或结构上的分离性与不连贯性。”
20世纪70年代,新的录像设备/技术和剪辑设备/技术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它们的出现让艺术家拥有了更多的进行视觉实验的可能性——例如:键控、混频、色彩调整、图层以及从多台摄像机上输入画面等。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艺术家而言,这些技术仍然难以被接触到,而且,一些艺术家也不满足于这些在市场上流通的设备,他们想要创造出更多、更“自我”的影像艺术作品,于是,几种不同的倾向就这么产生了:一些艺术家开始学习电子工程方面的知识或者和电子工程师们合作,电子工程师开始介入到“录像艺术”的领域中。他们开始自己设计、制造后期处理设备,例如,“Paik-Abe”合成器、“通用伪装者”视频调制仪、直接视频合成器、“Rutt/Etra”视频合成器、“Videokalos”图像处理器、U-matic VO-2850磁带格式编辑器……这些新设备的出现让“录像艺术”从基础的记录功能里解放了出来。
1969年10月, 一个由艺术家、作家和激进的媒体梦想者组成的团体在纽约成立—— 雷舞公司(Raindance Corporation),在麦克卢汉(Herber t MarshallMcLuhan)的《理解媒介》和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传播理论”的影响下,雷舞公司制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激进软件》的期刊,里面介绍了视频的各种替代方法。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信息秩序的概念——“权力已经转移到那些控制媒体的人身上,权力不再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来衡量,而是通过信息使用权和它的传播方式。只要最有力的工具(并非武器)仍然掌握在拥有它们的那些人手里,没有任何另外的文化远景值得我们期待。除非我们重新设计并贯彻交替性的信息结构,这种结构能够超越并重新配置现存的体系,其它的交替系统和生活方式将只是现存过程的产品而已。”后来——1975年,艾拉·施耐德(Ira Schneider)和克洛特(Beryl Korot)又编写了一本叫《录像艺术:选集》(Video Ar t:An Anthology )的图书——这也是雷舞公司的最后一本出版物,他们走访了73位以录像为媒介的艺术家,并在具体的背景下研究了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弗兰克·吉勒特(FrankGillette)、约翰·汉哈特(John Hanhardt)等人的文章。雷舞公司的出现对“录像艺术”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雷舞公司对于视频使用的兴趣大于画廊艺术,但雷舞的很多重要核心人物,包括吉勒特、施耐德和克洛特都支持一种观点,即新兴通俗视频媒介会挑战广播电视在美国的地位,并为超越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系统的新通信方法奠定基础”。
1970年,纽约州立艺术委员会(NYSCA)开始将“录像艺术”作为资助的艺术类别,为个人、媒体艺术中心等提供资金支持。其中,他们的第一批资助范围就包括了各种类别的录像作品——录像装置、行为录像、用视频合成器制作的录像作品以及在街头拍摄的记录片……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基金会的資金赞助都对“录像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让“录像艺术”正式成为一种被“承认”的艺术形式,也让众多以录像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们可以更加安心地从事录像艺术作品的创作。此外,纽约州立艺术委员会(NYSCA)也资助支持了媒体中心,这就为其它的艺术委员会树立了榜样——不久之后,许多新的媒体中心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为“录像艺术”的宣传和创作提供更加合理的生存环境。
1971年,盖瑞·苏姆在杜塞尔多夫建立了一个“电视画廊”,以此来展出和销售“录像艺术”作品。当纽约州立艺术委员会让“录像艺术”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艺术形式后,在各个州立艺术委员会、各种私人基金会以及国立艺术基金的资助下,许多由艺术家创办的艺术空间在美国的各地建立起来,而且,因为它们大都是非盈利性的艺术空间,所以它们所展览的内容一般都是最新的、非商业的艺术形式——“录像艺术”便自然地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由此,“众多录像艺术作品的放映活动在各种场地中轮番上演,从博物馆、画廊、替代空间、媒体艺术中心到以社区为基础的活动中心,这为录像艺术的展览和推广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机会”。不久,很多大学和学院也开始将录像和行为艺术作为课程来教授——学术界开始接受“录像艺术”,这就巩固了它在学术中的地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将录像作为自己的创作媒介,越来越多的“录像艺术”作品和“录像艺术”展览,以及越来越多的与“录像艺术”相关联的理论的出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的《控制论》、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通讯的数学理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体》、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等,“录像艺术”体系开始正式形成——“1965年至1975年间,世人对录像艺术做出了定义”。与最早期的录像艺术实践者们——白南准、沃尔夫·弗斯特、沃霍尔等——不同,后来的录像艺术实践者们——蒂芬·帕特里奇(Louis Partridge)、大卫·霍尔(David Hall)、达拉·伯恩鲍姆(Dara Birnbaum)等——在尝试建立自己的艺术语境,“试图将艺术从制度与思想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并在‘录像艺术的范围内宣示主权”。在新的科学技术和理论的推动下,这些“后来”的“录像艺术”实践者们开始“从早期专注手视频的‘现代性(在此期间许多录像艺术家参与调查视频的内在属性,比如视频记录过程的本质及其线性、字段、帧的组成部分,相机及其功能和操作,电视‘盒子及其观看条件),转向关注更广泛的问题:关于媒体的性质、表现形式以及社会政治含义。这一转变在本部分所涉及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从史蒂芬·帕特里奇的《监视器》、沃塞区·布鲁萨斯基(WojciechBruszewski)的《视频接触》、大卫·霍尔的《这是一个视频显示器》、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的《邸园中央》表现出来的对‘唯物主义的隐忧,一些作品明显解决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争论和问题,比如,塞拉和斯库尔曼的《电视传递人》、伯恩鲍姆的《技术或是转型:神奇女侠》、迪伟兄弟(Duvet Brother)的《忧郁的星期一》(Blue Monday ),以及丹尼尔·里夫斯的《强迫发生》(Obsessive Becoming ),这些作品似乎占据了一个特殊领域:视频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模式。同时显示了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新潜质——它既是主观视点,也挑战了广播电视的既定模式。一些作品,如琼·乔纳斯的《垂直滚动》、罗伯特,卡恩的《时间正好》(Juste leTemps )、伍迪·瓦苏尔卡的《记忆的艺术》、凯瑟琳·埃尔威斯的《和孩子在一起》(With Child )和比尔·维奥拉的《池中倒影》(The Reflecting Pool ),都是抒情和感性的,这些艺术家通过对技术形式的诗意探索、创新实践和对叙事传统的解构,吸收了‘唯物主义时期的遗产,并分享了对某些表达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观照。”(文字选自《录像艺术史》,作者克里斯·米-安德鲁斯,译者曹凯中、刘亭、张净雨)也由此,“录像艺术”开始真正地展现出自身的魔幻魅力——而彼得·唐鲍尔(Peter Donebauer)便曾如此写道:“录像作为媒介,即时视觉与听觉体验能随着时间延长并记录,这种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而未有人定义视频。随着电子技术在规模与加工技术方面的突破,录像技术扩大了它的可能性。如今,我们的外部环境在很多方面是有限的,而人类意识与电子的可能性之间的互动似乎是无限的。”
1985年,索尼又推出了全新的便携式录像机——Video8,因为其尺寸小、成本低、画面解析度高等特点,一推出就迅速地得到了人们的追捧;后来——1995年7月24日,索尼公司还发布了全球的第一款数码摄像产品——DCRVX1000,它采用mini DV带作为存储介质,由此,影像开始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和储存。1977年,在Radio Shack TRS-80,Commodore PET和Apple II取得成功后,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制造商都开始推出自己的家用电脑系列——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大量的新型计算机——BBC Micro、Sinclair ZX Spectrum、Atari 800XL和Commodore 64——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到了1982年,大约有621000台家用电脑出现在美国的各个家庭中。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很多计算机制造商开发出了新的编辑机器——1985年,宽泰(Quantel)公司发行了“Harry”剪辑软件;1987年,艾维科技公司(Avid Technology)推出了Avid / 1 Media Composer 剪辑软件……这让录像的后期制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非线性的编辑软件开始代替传统的模拟线性编辑系统,最新的数字软件也让艺术家可以在相对低成本的电脑上完成整个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在价格昂贵的后期制作系统中浪费金钱和时间。“非线性编辑技术的出现可以被称为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艺术家们对图像的编辑和组织方式,同时也对视频编辑的可操作性和录像艺术作品的类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录像的领域中,新一代低成本的数字设备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出现——例如,家用录像系统(VHS)、费尔莱特复合视频接口(CVI)图像处理器、beta制大尺寸磁带录像系统、3/4英寸磁带格式(U-matic)、时基校正器、帧存储器、视频混合台、图像键控器……在这些新技术的影响和帮助下,艺术家们的录像艺术实践变得更加活跃和高效,这远比上个时代的“Rutt/Etra”视频合成器、“Videokalos”图像处理器等的能力强大得多——科技与“录像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1990年底,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网页浏览器和第一个网页服务器,这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也促使了互联网的出现;1993年,蒂姆·伯纳斯-李又宣布:“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这项技术。”对于“录像艺术”而言,互联网的出现又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艺术家们不再执着于影像的自我生产,而是在网络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影像素材。后来——1993年左右,一些艺术机构和画廊主开始将摄影与版画中的版本概念引入到“录像艺术”作品中,这就解决了“录像艺术”作品的销售问题。从此,“录像艺术”作品开始像绘画、雕塑等艺术品那样被拍卖、收藏和流通。但是,版本的限制以及作品的出售却违背了“录像艺术”的最初意义——“早期录像艺术实践者将录像媒介的非永久性和瞬间性视为一种优势。那些希望回避艺术市场商业性所带来的影响的艺术家,被录像媒介这种临时的、转瞬即逝的特质所吸引。”(文字选自《录像艺术史》,作者克里斯·米-安德鲁斯,译者曹凯中、刘亭、张净雨)此外,由于一些艺术家不能像那些以单频道录像为创作方式的艺术家一样,可以在更加传统的放映场所里展现作品,并需要在限制版本的条件下出售自己的“录像艺术”作品,那么,这就要求这些艺术家的“录像艺术”作品需要具有明显的差别性——只有不一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而且,在画廊展出的“录像艺术”作品往往具有严格的美学策略,它们会使用循环播放、慢镜头、大特写、声音效果等特技,以及带有冥想性质和隐喻特征的画面效果,语言也会具有明显的试验色彩和藝术氛围——例如比尔·维奥拉的作品,无形之中,它们——这些一切的规则——成为了一种方法、一种束缚。
对于“录像艺术”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转折性的阶段,新的录像器材、新的电脑和剪辑软件、互联网以及影像的数字化……这些都让“录像艺术”蜕化到新的阶段——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他们越来越多地去尝试探索“录像艺术”的潜力,以期实现对影像的绝对操控性,但是,这种操控性并非只关乎技术,它们开启了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视觉体验,探索了感知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克里斯·米-安德鲁斯,Chris Meigh-Andrews)的个人经历完全可以作为图像处理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例子。从1978年开始,我就从事模拟图像处理工作,并将其输出为U-matic磁带格式(3/4英寸)。借助Videokalos图像处理器,我开始尝试对彩色视频图像进行“实时”控制。与其他设备相比,Videokalos 接口信息处理器(IMP)提供了一种“同步锁相”,借助它我就可以将单一的视频磁带源与单色或彩色视频摄像机进行同步、混合、调整(亮度和色度)复合颜色控制(分别控制红绿蓝三色通道)的图像擦除方式(包括垂直、水平、圆形、椭圆四种方式)。这一时期,我主要使用一种黑白资源(名为Por tapak)制作了以下单屏作品,包括《水平与垂直》(Horizontal& Ver tical,1978)和《分心的司机》(The DistractedDriver,1980)。1980年至1981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名为Three-Quarter Inch Productions),当时只有一个素尼2860型的U-matic 编辑工作台。1982年,我用便携式U-matic 记录器(索尼VO4800型)和一台使用videokalos 接口信息处理器的彩色摄像机(JVC KY1900型)制作出包括《房间的风景》(The Room with aView,1982)和《时间旅行/一个真实的故事》(Time-Travelling/A True Stor y,1983)在内的作品。随着1985-1986年CEL数字框架存储器和双子星(Gemini)双生时基校准器的引入,我的特效储备得到了极大加强,在此之后我便可以将多个录像带来源进行混合,制作出视频帧抓取效果(一种类似慢动作的图像排序效果),或是图像“翻转”效果(制作视频序列的镜像效果)。这一时期的新单屏录像作品,包括1985—1987年作品《河流》(The Stream)的最终版本以及《虚构的风景》(AnImaginary Landscape,1986),都充分利用了屏幕分割、图像翻转、影像撷取以及数字像素化技术,通过多个视频源的混合制作完成。图像的新效果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视觉复杂性,也给我带来很大启发,特别是与电子图像本质相关的问题,以及图像与视觉感知和思维的潜在关系问题。
在新作品中我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参观者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问题直接导致我在1988年之后放弃了对单屏视频格式的使用。20世纪90年代我制作了一系列参与型多屏装置和雕塑视频作品。作品包括《水的烟花》《流线型》(Streamline,1991-—1992)《交义电流》(Cross-Currents,1993)《永恒运动》(Perpetual Motion,1994)《旋涡》(Vor tex,1995)《心灵之眼》(Mind's Eye,1997)及《飞蛾之光》(Mothlight,1998),数字成像技术在以上作品中发挥了更大作用。90年代中期,我的作品在后期制作阶段完全实现数字化,而模拟录像带只局限于在展览阶段使用。例如,在作品《永恒运动》中,我使用的是苹果电脑(Mac Quadra840AV),作品图像通过Macromedia公司的“Director”软件进行输出录制。《旋涡》则使用了Quantel公司的“Paintbox”软件,由数字慢动作视频和3D文本混合而成。《心灵之眼》在计算机上将功能磁共振大脑扫描图像转换为Betacam格式(一种广播视频格式)。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全球化进入到新的阶段。从宏观的角度看: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一些重要变化,发展中的亚洲经济迅速增长,使全球经济的力量均势发生改变,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变化将对日益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世界人口每年增加7000多万,到了2050年,全球经济必须有能力让90多亿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其中85%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面临巨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是以自然环境退化为代价来维持的——覆盖地球的近一半森林已消失,地下水源正迅速枯竭,生物多样性已大量减少……全球各种经济进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越来越密切,农业和工业生产日益通过国际公司主导的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全球危机表明金融市场如何相互关联,显示系统的一个部分出问题如何迅速给系统的其他部分带来冲击波;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刺激新型文化形成的同时,原生的地方性文化也面临新的挑战,文化趋同现象越来越明显……而从个人的角度讲:全球化对当下的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具体的深刻影响——工作学习、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交往通信……我们开始用全新的视角来观看和思考世界以及自我的状态与意义——“个人全球化”这个新名词开始出现,这些新的、具体的改变自然影响到了每一个“录像艺术”实践者身上,而且,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影像制造工具和编辑软件的陆续出现,也让“录像艺术”产生了更新的变化——毕竟,从“录像艺术”发展脉络看,科技的发展是其前进的直接动力。“录像艺术”的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其与电影——尤其是实验电影——之间的隔阂开始变得模糊,在王拓的“录像艺术”作品“东北四部曲”系列中,便能明显地看到这一变化。此外,当具有摄像功能的智能手机变得普及后,录像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日常行为,越来越多的影像开始在网络中传播,这等于延续了白南准等人的艺术理念,让录像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地解放,这在陶辉的“录像艺术”作品《跳动的原子》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而且,随着SketchUp、3DS MAX、Maya等建模软件的发明,“录像艺术”的实践变得更加“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藉由自己想象来凭空地制造出“錄像艺术”作品,而不再需要“现实素材”的限制,尤其是在AI技术逐渐成熟的背景下,这种创造会变得越来越容易;随着“网络时代”的真正到来,“录像艺术”凭借自身的数字特性,其能够凭借网络来实现迅速、自由的传播和观看——甚至因为VR等设备的发明,“录像艺术”可以构建出全新的观看体验与表述方式。
作为一种新的、没有历史规则束缚的艺术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录像艺术”一直都在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处于一种时刻变化的状态中,所以,它的内容和边界也就变得多元和包容,能够自由地借鉴与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特点,是一种真正符合“当代艺术”理念的艺术媒介。
在观看和梳理完“录像艺术”的脉络之后,我们便对其有了基本的认知。在文章之初,我们便知晓:“Videoar t”在传播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其被人为地转译成了不同的名词——“录像艺术”“影像艺术”“视频艺术”“多媒体艺术”……而且,我们也知道“录像艺术”所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影像艺术”,那么,我为何要将“影像艺术”作为其他“名称”的基础?这就需要跳跃到另一个重要的设问——何为“影像艺术”?而在正式讨论这个设问之前,我们也要挪用我们在分析摄影艺术时所使用的逻辑——要先给“影像艺术”设定一个具体的讨论语境——我将其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语境。其中,在狭义的语境中,“影像艺术”是我们以物理的方式(例如照相机、录像机之类的工具)将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记录和保存于存储媒介(胶片、存储卡等)中,以此形成了特殊的“物质”,它是一种静态“图像”的包含与延伸,或者说,是一个“静态图像”和由“静态图像”衍生的“动态图像”的集合——这里用“图像”的缘由是想与“影像”做区别,就像迈布里奇(Eadweard James Muybridge)将“静态图像”连接成“动态图像”后的那个瞬间;而在广义的语境里,“影像艺术”则是一种包容的状态——是对于前面的狭义语境内容的扩延,它是人类对于视觉感知的一种再现,包含了photograph(照片)、video(录像)等等依照“影像狭义语境”的逻辑所衍生出的所有“内容”。从逻辑上讲,这里的“狭义”与“广义”的形成基础是由影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态所决定的。由此,我们便会发现:由影像是构建“Video ar t”的基础。那么,顺理成章,“影像艺术”便是其他“名词”——“录像艺术”“视频艺术”等——的基础,它们是在转译的过程中,所凭借名词自身而引发的各自演变和发展——我个人觉得,“影像艺术”是一个大的、含混的概念,而“录像艺术”“视频艺术”等等则是大概念下的具体形态。
而早在190多年前——1826年的夏天,为了能够记录下我们眼前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Nièpce)在乐加斯乡间的别墅工作室里进行了长达八小时的曝光实验,拍摄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照片——《乐加斯窗外的景色》(View from the Window at Le Gras ),摄影术由此诞生,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摹写也开始进入到“机械时代”,最初的影像——或者说静态影像——也在此诞生。后来——1878年,为了验证动物在奔跑时,四条腿是否会同时离地,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利用并排设置的12台相机拍摄了摄影史上的著名作品——《疾跑中的萨利·加德纳》(Sallie Gardner at a Gallop ),人们将这12张照片进行连接,因为“视觉暂留”,它们就形成了连续运动的影像——摄影开始向电影迈出了第一步。1888年10月14日,路易斯·普林斯(Louis Aimé Augustin Le Prince)在奥克伍德农庄拍摄了一段2秒钟的影像作品,这部名为《郎德海花园场景》的短片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真正的“动态影像”开始出现。1895年12月28日,当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卡普幸路14號的地下室里公开放映他们的电影短片——《工厂的大门》后,电影开始正式进入大众的视野,电影的时代来临了——也从这里,“动态影像”开始与“静态影像”产生了疏离。
“录像艺术”的源头是电视/电视系统,而电视与电影却有着相似的工作逻辑——它们都是一种影像的“释放”过程,都是将人们制作——绘画、拍摄等——的图像/影像投映到现实/虚拟世界之中。那么,从电影到电视,我们似乎也可以观看到摄影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共同面对电视系统的强大影响力时,不同的艺术家做出了不同的艺术反应——白南准、沃霍尔和苏姆等人将录像作为了自己的艺术反击,而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Prince)、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雪莉·莱文(Sherrie Levine)等人则将摄影作为自己对于电视系统的艺术回应。从广义的语境看,它们——摄影与录像——都是“影像艺术”的具体部分,而且,它们也都是对电视系统的一种反抗与反思——正如白南准所说:“我们一生都在被电视袭击,现在我们可以反击了。”
QA对话“意义”影像艺术展策展人
在2023年8月26日,“意义”影像艺术展在北京的中间美术馆开展,作为一个由15件影像艺术作品构建的展览,通过对它的具体观看,我们在反思自己当下生存处境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动态影像”与“静态影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也为此,我们对“意义”影像艺术展览的策展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FOTO:首先,举办这个展览的最初原因/目的是什么?此外,名称是“意义”,为什么?是对展览本身的一种“定义”,还是对展览内容的一种“回应”?
管陶然:“意义”展有两个充分必要条件。充斥不确定性的三年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未来的困惑直接导向对当下的无力,出现了诸如“躺平主义”“全职儿女”等概念,始终挥散不去的“内心秩序如何恢复”的疑问和探索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全球化时期形成的艺术网络在物理空间和思想智识受阻时仍保持活跃,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全球各地的艺术创作,得以看到几乎所有近五年来在东亚、东南亚、南美崭露头角的录像创作者。他们立足于自己关切的土壤,揭开个体或群体因各种问题受创所结的痂,为了愈合,更为了铭记。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于现在的我们尤为重要。
意义,是一种价值,它曾被作为人活着的根据和世界存在的理由。在互联网工作时,几乎每天都会自问或被问“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是否有区别于他人存在于此的意义与价值”,陷入自证的漩涡。如果找不到肯定的答案,自己便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意义是一个怪物,寻觅时却藏而不露,追逐时像天边的地平线,是对批评的永远的诱惑。(《意义的诱惑》,时代文艺出版社)“意义”是一个充斥于日常交流中、象征含义远大于本身含义的词语。与其说这个题目是对展览本身的“定义”,或者是对内容的“回应”,我可能更倾向于表达为是想通过15件作品实现对“意义”的解构,重新唤起批评与批判,唤醒被物欲压制的人文精神。中间美术馆一直坚持从全球视野中的当代艺术现场汲取出色的创作案例,呈现艺术本该有的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FOTO:整个展览一共有15组作品,并分为了三个部分,作为策展人,那能否讲解一下展览的逻辑和设计?例如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三个部分的分类?等等。
管陶然:展览从整体希望可以呈现一种消弭边界的视觉感受,所以用柔软可变的纸墙取代实体墙。观众进入展厅后,便被包容进这个世界里。首先接触到的作品都是艺术家从自身出发,可能是困扰自己的疾病、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偏颇之处,这些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个体可能遇到的问题,艺术家对这些问题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能。步入第二部分,个体与社会发生碰撞,作品指涉的对象趋于严肃沉重,从大屠杀到隐虎游戏,个体在洪流之下如浮萍、如砂砾。为了更好地配合这部分的主题,展厅几乎隔绝了所有自然光,观众被作品时有时无的光线引导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升至三层,重获天光,作为展览的终章,这部分通过4件作品呈现了过去到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一直处于混乱与平静、失序与恢复的交替中,处于其中的个体可能像《非虚构日记》中一样陷入疯狂,也可能像《从海阳到黎明》中一样流离失所,这些发生过的事情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逃避不会让痕迹消失,直面才能找到立足的意义。
FOTO:从媒介上讲,这是一个以录像/视频为主要媒介的展览,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媒介,录像/视频作品具有传播性(其可以在任意的荧屏上播放)与时间性(观看时具有固定的时长)等特点,那在展览设计的过程中,你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如何的考虑?
管陶然:呈现是作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所有作品都可以在任意荧屏上播放。为了让作品有最佳的呈现效果,我们会在展览思路确定后与艺术家沟通展陈方案,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美术馆的特点进行创新和调整。即使观众在其他空间看到过某些作品,也可以在我们统一的表达下,进入“意义”的世界中。
为了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展体验,在选择作品时会尽量减少时间过长的作品,此次仅有两部作品超过1小时,大部分在10-20分钟,还有4部作品在5分钟左右。在展陈设计时,会将不同时长的作品进行搭配,并将时间较长的作品放在后半程,减少观展压力。在展览设计时,会通过不同的主视觉色彩、作品高低位置、观众观看方式(站立、卧躺、坐凳、蹲踞)、作品易理解程度等错落搭配,释放和抓取观众注意力,缓解观展疲劳。
FOTO:能具体讲讲展览第三部分的构架么?我觉得它与前面两个部分具有很大的不同,从作品《手牵手》《永远的朋友》到《非虚构日记》,从《从大海到黎明》到《反转》。
管陶然:在展览设计时,虽然所有作品讨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每一层都有各自的侧重,观感上也会有所差异。观众已通过前两部分形成对展览的理解,有个体面临的重重阻碍,也有集体对个体的影响。作为整个展览的终章,第三部分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供可能,一种如何缝补世界裂缝的可能。这四部作品所指涉的对象并不陌生,《〈手牵手〉和〈永远的朋友〉》中的奥运元素、《非虚构日记》中对90年代暴力事件的新闻报道、《从大海到黎明》中难民的挣扎与幸运,以及《反转》中殖民历史挥散不去的影响。面对诸如新自由主义浪潮、全球化发展、工业变革等社会的剧烈转变,逃离、沦陷、麻木都是可能的选择。最后留给观众的,是一个自身如何选择的开放性命题。
FOTO:参展的14位/组艺术家大都比较年轻,而且是近些年才刚刚出现的艺术创作者——“参展艺术家多生于八十年代,也有一些七十、九十年代生人……”“看遍了几乎所有在近五年内崭露头角的东亚、东南亚、南美录像创作者……”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管陶然:很多成熟录像艺术家的作品已经有广泛的展示,大家对他们也已比较了解。此次展览希望可以呈现不同代际的录像艺术家的作品,通过他们的方式重新解读长久存在的问题。
这里也特别感谢哈恩内夫肯基金会对录像艺术以及此次展览的支持。正因为有他们持之以恒的支持,优秀的录像艺术家才能不断地被发现;也正因为有他们全力的协助,我们才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作品并且展示出来。
FOTO:在“网络时代”和AI逐渐成熟的当下,你如何看待录像/视频这个媒介?
管陶然:可能我不太会用“成熟”来形容网络和AI的发展,虽然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web3.0阶段,但技术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真正的技术性革命进展还远未到来。从神经网络到OpenAI,都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目前可以在某些领域的部分模块起到辅助作用。保持问题意识是艺术家创作的基石,所以包括技术在内的发展、变化都会成为艺术家思考的对象,也会为创作提供支持和辅助。在图像可以被肆意合成的时代,录像这种媒介仍有一定的独特性。优秀的录像艺术作品往往需要耗费巨大心力。技术的革新与迭代,在为录像创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FOTO:能简单讲述一下作品《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这组作品么?
管陶然: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是此次展览中唯一有两部作品展出的艺术家,他在加札马达大学学习媒体传播研究,并在萨纳塔达摩大学获文化研究硕士学位。他的研究实践涵盖历史、民族志和博物馆学,以各种媒介创作,模糊想象与记忆之间界限的叙事,对权力的殖民性和看不见的东西提出了疑问。《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这件作品正是通过赋予“被消失”的文献以生命,揭示了荷兰殖民者如何利用爪哇的斗虎仪式控制百姓。16分钟的视频没有一丝血腥的场景,但透过录音机传来的亲历者的回忆,令人不寒而栗。而他模糊真实与伪造文献的方式,又时刻提醒着观者保持质疑和批判。
FOTO:在具体观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属性,这让普通的观看者在观看作品时会自然地形成一种隔阂,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管陶然:这种可能存在的“地域文化”属性,恰恰是我想要营造出来的。在选择作品时,便希望可以尽可能多地展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不同的生存生活状态。有了隔阂,便有了打破的欲望,也就有了理解的可能。在我看来,这是美术馆或者展览的重要角色之一,即打破地域的阻隔,呈现多元的视角和思考方式。但其实,之所以说“可能”存在的地域文化属性,那是因为虽然艺术家所处地不同,但讨论的问题是与我们共通的,并不存在“隔阂”。这些作品中所揭示的各种遭遇,个体的、集体的、当下的、历史的、肉体的、情感的困顿,以及人在面对这些限度的时刻所展现的恐惧、无助、绝望与希望,是人的本真最为真切的证词。看到作品的同时,观众也能照见自己。
当然,我们也會通过作品解读、艺术家分享、公共教育活动,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展览,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和作品的内核。
FOTO:在展览本身之外,中间美术馆是否会组织其他的相关活动来与展览形成补充?
管陶然:此次展览容纳了多种议题,我们将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挖掘展览:邀请部分参展艺术家来中国,直接与大家分享创作背后的思考;从作品指涉的主题出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讨论;面向不同受众,组织线上、线下Opencall和工作坊,让观众都能参与进来。
FOTO:最后,你希望这个展览产生何种的效果或者意义?
管陶然:回到展览的缘起,我没有寄希望于通过一个展览解答什么是意义。但期望可以通过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的15件作品,提供关乎人性和意义的一课,挣脱娱乐消费的陷阱,重新拾起把握世界、辨别真相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