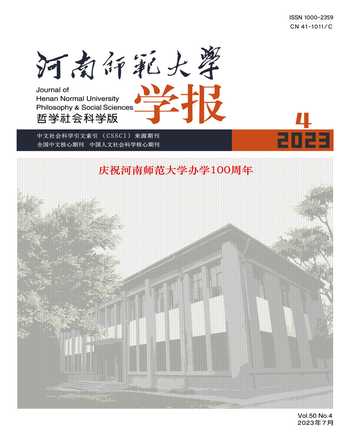尧舜共同体的早期国家特征论析
2023-04-29李玲玲
摘 要:尧舜共同体在国民结构上出现了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具备了按地域划分国民的国家特质;在国家权力上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发展,并初步具备了王权特征;在国家结构上呈现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初期特征。这三点与夏商国家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是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体现,唯其仍有一定原始性,所以可称为早期国家的初始阶段。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尧舜共同体时期社会发展的反映有一致之处也有差异,其差异体现了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的三个特点:早期国家初始阶段,具备国家要素的城邑(或中心聚落)为少数,大多数古城和聚落的发展仍比较原始,规模小,社会形态单一,仍以血缘组织为统治基础;进入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城邑(或中心聚落)大多规模较小,影响有限;从全国范围看,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处于多中心状态,直到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才得以凸显。
关键词:尧舜共同体;早期国家;夏商国家
作者简介:李玲玲(1979—),女,河南济源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79);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2XWH020)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4-0085-08 收稿日期:2021-12-14
目前,学界对夏商已进入国家阶段几无异议,但对夏代之前尧舜时代的社会性质则有所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为部落联盟尧舜时代仍处于氏族社会,为部落联盟之说,常见于古代史和先秦史教材或著作,如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9—141页;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14页。;二为酋邦或酋邦联盟酋邦的发展阶段在社会等级与社会分层方面高于部落联盟,但其核心仍是血缘组织。该理论由张光直先生传入我国后,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赞同,代表学者有谢维扬、沈长云等。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9—275页;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9页。;三为早期国家。三种观点中,前二者认为夏代之前社会发展未进入国家阶段,到夏王朝才形成真正的国家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于夏代,龙山时代尚未形成国家的学者主要有安志敏、李先登、李伯谦、晁福林、谢维扬、刘莉、沈长云等。参见王震中:《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夏代之前国家要素已经出现,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认为古代最早的国家形成于龙山时代或之前的学者,侧重于考古材料中显示的夏代之前社会发展中国家因素的产生,代表学者有唐兰、田昌五、石兴邦、黎家芳、高广仁、邵望平、苏秉琦、严文明、李学勤、王震中、许顺湛、高炜、张忠培、任式楠、钱耀鹏、王巍、何驽等。参见王震中:《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差异的产生主要来自对国家产生标志认识的不同。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上述问题有了更广泛的研究空间,且有向第三种观点汇集的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尧舜共同体与夏商国家的比较入手,揭示尧舜共同体的早期国家特征及其所处的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特点。
一、尧舜共同体具有与夏商王朝相同的国家特征
尧舜共同体是否进入国家阶段,以往的研究主要以国家产生的标志来衡量。长期以来,学界多遵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项重要标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学者对此标准提出异议,认为古代中国一直到商周时期,血缘关系在社会政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即“国家必然建立于地缘组织之上”这一标准,不适合中国古代国家的实际王震中:《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晁天义:《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家产生的标准仍难达成共识。基于此,我们可另寻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既然夏商进入国家阶段已成共识,我们便可从夏商王朝的国家核心特征出发,将其与尧舜共同体进行对比,由已知推及未知,或可对夏代之前尧舜时代的社会性质有更清晰的认知。
1.从国民构成看,夏商国家分别以夏族、商族为主体,容纳广泛区域内的众多同姓和异姓部族共同构成,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这种特征在尧舜共同体中已初现端倪。
尧舜共同体以尧舜血缘部族为核心,包含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诸多部族,民众构成和社会管理上已突破原始社会单纯的血缘关系统治模式,初步形成了以血缘为主的血缘和地缘的结合。
尧、舜均有自己的血缘部族,由具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家族、宗族、氏族共同构成,有不同的活动区域和控制范围。尧部族的活动地主要在古冀州之地。《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淮南子·坠形训》高诱注:“冀,尧都冀州。”具体地望为晋南地区。郑玄《毛诗唐谱》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河即今山西南部的临汾一带。舜部族的活动地有山东、晋南等不同说法,都城则主要有“蒲坂”“平阳”之说。
尧舜共同体内除了核心的尧舜部族外,还包含多个来自不同地域、无血缘亲缘关系的部族。《尚书·尧典》载,尧舜共同体内中有四岳、鲧、禹、皋陶、伯益、契、弃等重要成员,囊括了当时中原和东方地区的多个重要部族。其中,禹、契、弃与尧舜同属中原地区的重要部族,皋陶、伯益则为东方夷族的首领。这种民众构成层次在《尚书·尧典》中有明确体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其中,九族为尧自己的血缘部族此九族自古有同姓、异姓两种说法,从下文对应的“百姓”“万邦”来看,“九族”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更具合理性。,侧重于直系家族;百姓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异姓部族。九族、百姓属于尧部族的层面,以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氏族为基础,属于血缘组织范畴。而“万邦”则是共同体层面的地缘组织,包括加入共同体内的其他区域的多个部族,属于地缘组织范畴。这些记载说明尧舜共同体时期,已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地域融合,民众构成和社会管理出现了血缘和地缘的两相结合。
2.从国家权力看,夏商时期社会公共权力比较发达,有较系统的国家管理机构、职官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王权集中,最高权力实现了家族世袭。这种社会公共权力早在尧舜共同体时代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只是不如夏商国家成熟和完善,同时尧舜共同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了夏商王权的特性。
尧舜共同体的社会公共权力得到了一定发展,存在社会管理机构和职官体系,但具有初始特征,仅体现出一种大范围的职能分类,更突出个体能力,尚未形成后世那样完备细化的职官体系。《尚书·尧典》载舜担任共同体首领后,设官分职,任禹作“司空”平治水土;弃为“后稷”,主管农业,播时百谷;契作“司徒”,敬敷五教;皋陶作“士”(法官),主管刑罚;垂作“百工”,主管各项手工业制作;益为“虞”官,掌管山林川泽;伯夷为“秩宗”,主管典礼祭祀;夔为乐官,制礼作乐;龙为“纳言”,负责传达王命。舜有此二十二贤人,以致天下大治,百业俱兴。由于文献的成书时代远晚于尧舜时期,因此可能附加有当时人对尧舜时代的理解和认知,甚至不排除以后世职官名称加以比附的情况。但抛开职官名称的准确与否不谈,尧舜共同体已设立不同种类的职官,分别处理各种政务应是可以确定的。职官和社会管理机构作为社会公共权力发展的体现,是伴随社会分层和阶级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其细化和完善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即是国家官制不断完善的反映。尧舜共同体内的职官设置和管理机构正处于初期阶段。
与职官和管理机构相伴生的是社会管理制度。尧舜共同体社会管理的某些方面已初步实现制度化,保证了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增进了管理的有效性和社会的稳定性。舜时,天子巡守四方已经制度化,《尚书·尧典》载,舜继位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这里不仅体现出当时天子巡守已形成制度,而且有相关祭祀制度和朝觐制度与其密切配合,共同构成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这些制度在尧舜时代初步形成,夏商时期不断完善,在加强最高权力中心与众多邦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先秦巡守制度的研究参见李凯:《五帝时期的巡狩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巡狩史实》,《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晋侯苏编钟所见的西周巡狩行为》,《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此外,官员的荐举制和考核制在文献中也有体现。尧为选共同体最高首领的继任者曾向放齐、四岳咨询;为选拔治理洪水的官员向驩兜和四岳征求人选;舜继任后,选拔官员同样“询于四岳”。《尧典》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表明当时已有官员考核制度。刑法也已初步建立,《尧典》载舜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任皋陶作“士”官,掌管刑狱,“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由文献记载看,尧舜时代社会治理的宗旨是慎用刑法,以教化为主,说明其时刑法还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刚脱胎于社会习俗和习惯法,缺乏细节,也不完善,但不可否定其已具备一定的强制性,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保障。
此外,尧舜共同体最高首领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和集权性,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夏商王权的特性。《尚书·尧典》载,尧在选共同体继任者时,放齐提出让尧子丹朱继位,被尧否定,尧认为丹朱“嚚讼,可乎”,即其言语悖谬,又好争辩,不可担当重任。驩兜推荐共工处理政务时,尧认为共工“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意即太过傲慢,表里不一,不可重用。说明当时官员任命虽然可以举荐,但最终的决定权则在最高首领个人。此外,最高首领还拥有对共同体内其他部族及部族首领的奖惩权,有着“协和万邦”的崇高地位和权威。《尚书·尧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中共工与鲧,为尧舜共同体的内部成员,他们或因不敬上天,或因治水无功,即被定罪,处以流刑。至于三苗等敌对势力,则联合共同体成员的军事力量,以武力将其驱赶至边远地带,从而树立尧舜共同体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力的集中性和强制性是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或酋邦阶段的酋长无法比拟的,具备了夏商国家王权的初步特征,是社会公共权力发展的重要体现。
与夏商国家相比,尧舜共同体社会公共权力的发展,显然还不够完善和系统,存在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意味着当时已经出现了超越氏族组织范围,为不同阶层、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遵守的强制性权力,这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也是最能体现尧舜共同体早期国家特征的内容。
3.从国家结构看,夏商国家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在这种国家结构下,夏后氏和商族自己的王邦为宗主国,众多附属方国和诸侯为属邦,尊王邦为共主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37、472页。。宗主国的君主夏后和商王既是自己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整个贵族国家体系中各方国诸侯认同的中央政权的政治领袖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这种国家结构的雏形早在尧舜共同体时已经形成。
尧舜共同体包含两个层面,从共同体的组成成员看,是多个独立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血缘部族,这些血缘部族均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在政治经济上有较强的独立性,其首领在共同体内担任不同的职官;从共同体层面看,则以尧舜部族为核心,容纳广泛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权力辐射范围远超过单个的血缘部族,尧舜作为共同体的最高首領对其他部族具有一定的支配权。这与夏商时期以夏商王国为宗主国,控制着诸多附属方国诸侯,共同构成夏商国家的状况基本是一致的。
尧舜血缘部族与尧舜共同体的控制范围是有差异的,体现的是一国统领万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前文已提及尧、舜部族的活动范围主要涉及今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但从共同体层面看,权力辐射范围远大于尧舜部族的控制范围,不仅包括尧舜部族的活动地,而且扩大至共同体内其他部族的活动区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向南可能扩展到安徽。即《尚书·尧典》所载舜继位后巡守四方的界限,东至岱宗,南至南岳,西至西岳,北至北岳。岱宗即山东东岳泰山;南岳,《史记》认为在今湖南衡阳的衡山,清人孙星衍认为“唐、虞五岳即是霍山”,位于今安徽潜山市或霍丘县,而非湖南衡阳。西岳为今陕西华山;北岳,《尔雅·释山》云“河北,恒山”“恒山为北岳”。尧舜在这样的大范围内,划分政区,确定疆界,分区而治,强化管理,即《尚书·尧典》所载“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尧舜既为本部族的首领,同时也是共同体的最高首领,其他部族首领在共同体内担任不同的官职。这与氏族社会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统治基础有着根本区别,与夏商国家则有着一致性。
由上观之,文献中的尧舜共同体与夏商国家在国民组成、国家权力、国家结构等国家的核心特征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尧舜共同体进入国家阶段应是比较明确的,即夏代之前已经出现了国家,只是因其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可称为早期国家的初始阶段。
二、龙山晚期所见尧舜时代的社会变化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文献中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有更密切的对应关系,时间范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具体到尧舜共同体,文献记载尧舜纪年总共也就150年左右杜勇:《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学理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处于五帝时代晚期,与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更贴合。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的庙底沟文化二期及龙山时代之前的仰韶文化相比,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文献记载的尧舜共同体时期的社会发展多有相合之处。
1.龙山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古城数量激增,与文献中尧舜共同体时期万邦林立的记载相吻合。
尧舜时期存在诸多邦国。《尚书·尧典》载尧对内能“以亲九族”,对外则“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到周初还有一千八百国。这在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龙山文化前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不少规模大小不一、分布相对集中的古城址,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并不突出。此时,北方地区河套左近的“阿善文化”和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出现了大量小型石城,有石筑城垣,但遗址内涵上并未显现出明显的贫富差异和等级,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环壕聚落和垣壕聚落众多,遗址多达上千处,并且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形成了大型的中心聚落聚集群,可能形成了以石家河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郭伟民:《试论中心聚落历史进程的连续与断裂:以城头山、石家河遗址为例》,《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91-119页。。长江下游则出现了良渚古国,与周边聚落共同构成了多层级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群。与上述两大区域相比,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区和东方海岱地区,城邑发展则相对落后,城址数量并不多,未有明显的大型中心聚落或城邑。整体来看,龙山文化早期,虽然出现了众多古城遗址,并形成了个别大的中心聚落,但除良渚古国达到了较高发展阶段,遗址内出现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墓葬区,存在明显等级分化和阶层分化,可能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外,其他区域的古城遗址大多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并不明显。
到龙山文化晚期,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古城数量激增,成为同时期古城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与尧舜共同体权力辐射范围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万邦林立,包含多个不同部族的记载是一致的。此时晋南临汾地区出现了超级中心城邑陶寺遗址,太行山东南麓的黄河两岸至淮河支流颍河上游一带也发现了10余处城址。但除陶寺遗址外,中原地区的其他城址虽有夯土城垣,但多规模不大,延续时间不长,并未发现其他规模超大,具有较大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整合迹象。此时,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海岱地区,古城遗址也呈现激增状态。这些古城多有双重或多重围垣、环壕,建筑方式为平地起建,有不断增扩的迹象,使用时间较长。有的古城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心聚落的作用得到强化,与周边聚落遗址共同构成了都、邑、聚的多层聚落结构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112、127页。。
黄淮流域之外,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出现了古城址群。整体看,该区域古城址为夯土城垣,作用重在防洪,虽然聚落形态出现了两极分化,但总体上仍是一个比较松散而简单的社会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龙山时代早期城址较集中的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此时出现了变化:陕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持续发展,出现了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大型中心聚落群;龙山早期时最繁盛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处于衰落状态,遗址数量减少;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国中断消失。这种全国范围内古城址的变化及不同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消长,对应文献记载,可能与尧舜共同体由中原和东方族群构成,势力强盛,长期征伐打击南方三苗族群有所关联。
2.龙山时代出现了超大型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城邑,与文献记载中尧舜共同体有都城存在相对应。
进入龙山时代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古城,并汇聚形成了区域性聚落中心,出现了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几个超大城邑。这些中心城邑不仅规模大,出土器物级别高,文化影响范围广,而且遗址内涵体现着鲜明的社会等级和分层,社会复杂化程度高度发展,聚落等级均出现了“都、邑、聚”的多级形态,具有明显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后世都邑性质,社会发展应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在这几个中心城邑中,学者多认为陶寺古城应为尧都或尧舜共同体的都城所在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发展》,《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杜勇:《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王震中:《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朱乃诚:《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都城是最能体现尧舜共同体社會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物化形态,从都城的各种遗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社会分层与等级、社会分工、社会公共权力的发展程度等有关社会性质的诸多内容。
陶寺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城址规模小,周边统辖的聚落群范围也比较小,虽然墓葬中表现出明显的贫富分化和身份等级差异,但血缘关系仍相当强烈。整体看,陶寺遗址早期时社会形态相对简单,应是尧部族的发展状态。到中期时,陶寺遗址发生了重大改变。“聚落总面积急剧扩大到了约400万平方米,而且主体部分环绕有大型防御设施,城内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宏观聚落格局显示陶寺所整合的地域范围很可能覆盖了临汾盆地的大部,并且拥有比早期层级更多、结构更复杂的聚落控制系统;聚落内有集中分布的‘宫殿建筑区,南部高处‘小城内则有以结构复杂的大墓IIM22为核心的较独立的‘王族墓区,其旁边还有一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IIFJT1),而石器等手工业生产和分配也显露出了集中控制与管理的迹象。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陶寺中期聚落较早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具有很多与二里头相似之处,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戴向明:《陶寺、石峁与二里头:中原及北方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年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6—60页。。这种变化,与尧在此时担任共同体最高首领,其所在部族发展成为尧舜共同体的主体,陶寺由尧部族的统治中心上升为整个尧舜共同体的都城密切相关。陶寺晚期的年代下限当进入二里头一期,此时的陶寺似乎因外在的暴力冲击而出现许多衰败迹象。可能体现的是共同体宗主国地位的更替杜勇:《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即禹继任共同体首领之位后,共同体的依托国很可能变更为禹所在的部族,政治中心也会随之变迁。陶寺作为尧部族的政治中心继续存在,由尧子丹朱统治,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禹继任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但实力必然会随之衰退,周边实力强大的其他族群入侵,最终导致城毁宫移。
至于时代稍早的良渚古国、与陶寺同时期的石峁古城,遗址性质与陶寺大体类似,拥有多层级的聚落形态,有跨区域、影响和辐射范围,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显著,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具有鲜明的中心都邑性质,与陶寺古城一样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这在目前已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
3.龙山时代晚期,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在大的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与文献记载中尧舜共同体以中原和东夷族群为主,势力强大,协和万邦的记载相一致。
龙山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在大的文化面貌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而且形成了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大型政治中心。这与文献中尧舜共同体主要以中原族群和东方族群为主,包含众多小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范围广泛是可以吻合的。龙山时代的得名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初,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文化面貌上的一致性,曾被广泛地称为龙山文化。其后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这些文化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其来源去向则根本不同,均是独立发展的文化类型,所以山东龙山文化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中原地区又细分为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等不同类型。虽然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考古学文化族属不同、各有特点,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不仅有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与融合,甚至有人群的迁徙流动,如此才导致了文化面貌上的广泛一致性。这反映的可能正是黄河中下游区域大范围联盟或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同时也为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李玲玲:《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中州学刊》,2018年第10期。。黄河流域中下游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广泛一致性,是长江流域、北方辽河流域所不具备的特殊现象。龙山时代早期兴盛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虽然也曾在局部地区产生了跨区域的较广泛的影响,可能也形成了某种政治或文化共同体,但范围和影响力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且最终因各种原因相继衰落中断,未能延续。虽然它们可能也迈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但终究没有实现国家形态由起源到成熟的完整演变历程。
可以说,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尧舜共同体的形成,为国家在这一区域的发展演进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这种大规模联盟及政治共同体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公共权力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各族群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大的征战或工程建设时,更能有效强化最高首领的权力,增加族群认同感,促进国家的发展与成熟。
三、从文献与考古的差异看早期国家阶段性特征
前文将考古材料中龙山时代晚期的社会发展与文献中的尧舜共同体时代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诸多相合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献中所包含的真实历史因素。但二者相较,也有不少差异,这种差异正体现出我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
1.文献中尧舜共同体时期万邦林立状态与考古资料中显示的仅有少数中心城邑进入国家阶段之间存在差异,反映出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尧舜共同体时期万邦林立,这些“万邦”均为相对独立的部族或政治体,有自己的活动区域与都城,社会发展程度应该不乏与尧舜共同体类似的情况,但考古发现却仅有极少数的中心聚落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进入国家阶段。這一方面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文在论述尧舜时代万邦林立的状态时曾提到,龙山时代晚期古城数量激增,尤其是黄淮流域,但在众多古城中,控制范围广泛,具有多层级聚落形态,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等级和社会分层显著,明显具有都邑性质而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中心城邑却极少。目前所见仅有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和时代稍早于二者的良渚古城。其他多数以小型古城和聚落为核心的政治实体,虽然有环城壕或城墙,但大多遗址形态简单,多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或聚落形态单一,社会管理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仍处于氏族、部落或较高级的酋邦阶段;或社会分工和等级不够明显,难以体现社会公共权力的发展。即“尧舜禹时期的‘万邦中,既有初始国家(早期国家),亦有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应当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王震中:《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只有那些拥有多层级的社会结构,实现了跨区域控制,民众构成包含血缘和地缘两个层面,具有联合体性质较大的政治体,如尧舜共同体,才是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正是探讨我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关键,目前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2.文献中尧舜共同体影响范围广泛与考古材料中尧舜共同体偏居晋南影响有限的差异,体现了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小国状态,即控制范围较小,影响有限。
上文已提及,文献记载中尧舜共同体的权力辐射范围以黄河中下游、黄淮流域为主,涉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这与尧舜共同体成员以中原和东方部族为主密切相关。但从考古学文化的显示来看,这个范围对应的是整个龙山时代广义龙山文化的涉及范围。具体到尧舜共同体所在的陶寺文化,其范围却是有限的,远达不到文献记载的广泛性。
陶寺遗址偏居晋南临汾盆地,陶寺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也位于临汾盆地汾河下游一带,北至太岳山南麓,东至太行山西侧,南至中条山北麓,西达吕梁山东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这一范围可以理解为尧舜共同体的直接控制区,以尧部族的控制范围为基础。其间接影响区则有所扩大,涉及陕西、河南、河北地区。考古资料显示,陶寺文化与其西面陕西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南面的三里桥类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北面的太古白燕三期文化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交流融合的程度较深,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文化面貌上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76页。。这种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反映的可能正是尧舜共同体的政治影响范围,但由于这种交流融合是相互的,因此无法判定不同文化间的统属关系,这与夏商是有区别的。夏商时期,二里头夏文化和以二里岗、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明显呈现出一种输出性特征,有鲜明的主导性和核心性特质,这在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尧舜共同体文化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与文献记载中尧舜共同体的强大也是有差异的。
由陶寺文化的影响范围看,尧舜共同体呈现的是一种小国状态,与夏商国家无法相提并论,反映的正是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特征。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形态。学者将国家的发展概括为“古国——方国——帝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0—167页。,“古国——王国——帝国”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邦国——王国——帝国”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9—66页。,等等。这些说法虽不一致,但都体现了国家动态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3.文献中尧舜共同体天下一统的局面与考古材料显示的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不同的超大型都邑中心存在差异,体现出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多中心并存状态。其时,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并未凸显。
文献记载,尧舜共同体时社会公共权力已有较大发展,共同体首领一统天下,周边诸侯臣服,共同体及最高首领的天下共主地位非常明显,已经具备了后世夏商王朝国家高度集中的王权特征。但考古材料中的显示却并非如此。考古材料表明,这种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夏商时期才开始出现。夏代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殷墟文化对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明显占据主导和核心地位,周边区域无任何地方文化可与之匹敌。而尧舜共同体所处的龙山时代却远未达到这样的水平,虽然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文化面貌呈现出大范围的一致性,但各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其独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万邦性质更突出,陶寺文化的共主地位无从体现。
将视野扩大至更广泛的区域,更是如此,当时全国范围内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状态,而非天下一统的区域核心主导。龙山时代晚期,除了晋南地区的陶寺古城发展成为超大型中心城邑外,紧临陶寺古城的还有其北方的石峁古城。二者时代几乎同时,地理位置南北接邻,长期并存。社会发展也与陶寺类似,已进入国家阶段。这与文献记载中尧舜共同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有较大差异的。此外,长江流域还有时代稍早的良渚古城,与周边的众多聚落也共同构成了一个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良渚古城、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作为区域性中心城邑,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独立甚至并峙,而非统属,天下一统的局面远未达到。对此,学者有不同认识,或认为龙山时代甚至更早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已经开始凸显,此后不断得到强化,延续发展到三代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严文明、张学海、赵辉、韩建业、戴向明等,参见韩建业:《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的中心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日,第4版;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或认为中原地区核心地位的凸显到二里头代表的夏文化晚期才开始出现曹兵武:《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之前甚至夏代前期都处于多中心状态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高江涛:《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原核心论未必符合现实,即便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其文化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李新伟:《从广义视角审视“最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1日。。但由前文分析可知,至少尧舜共同体时期社会发展仍处于多中心状态,并未形成明显的核心区域或引领区域。
由上可见,考古与文献对尧舜时代的反映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既与文献本身的滞后性、主观性有关,也与考古发掘的偶然性和阐释的主观性有关。文献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从时间上看,史前社会的相关文献记载在西周以后才逐渐出现并增多,记载的依据是流传于各地的长期口耳相传所保留下来的原始記忆,距离尧舜时代已千年以上,必然会与最初的历史真相有所差异。其次,从空间上看,西周以后的文献记载,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原族群为主线和核心,反映的是中原族群的发展演变历程,所以其他区域如北方、南方地区的族群或国家,必然不会过多涉及,即便有也是以中原王朝的附属国或战败国面目出现,目的在于凸显中原王朝天下一统的地位。另外,早期国家出现以后,只有中原地区得以延续发展,完成了王国、帝国的演变,周边地区的国家发展进程或中断或衰落,这也是后世文献中有关周边族群发展演变记载相对缺失的重要原因。最后,从主观意识表达上看,文献的记载与流传有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文献记载会被附加更多的主观意识,或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感情倾向,或出于传授的限制,与真实的历史必会有所出入。关于传世文献的局限性,江林昌先生做过系统阐述,他认为由于客观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不能反映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而这种局限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叙述的内容上,以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对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有许多删减甚至消除;二是在叙述的态度上,突出美化中原文化,而贬低排斥周边文化”江林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兼谈传世先秦秦汉文献的某些观念偏见》,《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所以仅凭传世文献的记载来探讨尧舜时代的性质和社会发展,既不全面也不客观。
文献不足征,考古材料也有局限。系统的考古发掘虽然有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初步预判及前期的勘测和规划,但重大遗址的发现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目前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历史的全貌,这也是学界公认的“说有易说无难”,没有发现不代表没有。以文字为例,至今未发现系统的夏代文字,但因为商代甲骨文已是成熟的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字,早期文字必然存在,只是一直未能发现而已。关于夏代存在与否的认定也是如此,文献有明确的夏代史实记载,只因考古未发现夏代文字,诸遗迹未能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就否认夏代的存在,也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要求。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外,考古遗址现象的主观阐释也会造成历史真相的偏差。现象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现象背后反映的内容,以及对现象的阐释却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考古学家倾向对现象的客观描述,但这种描述本身即带有阐释者的主观意识和选择性,同样的遗址现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解释,未必准确客观,何况脱离历史背景的现象描述,其意义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关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的相關研究,不仅要结合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不可畸轻畸重,而且要有意识地避免各学科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如此,才能尽量客观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综上所述,以恩格斯国家产生的标准为基础,对比夏商国家的特征可知,尧舜共同体已具备了国家的核心要素和特征,社会发展进入国家阶段,社会性质与夏商国家一致,但具有一定原始性,可称其为早期国家的初始阶段。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的尧舜共同体时代有一致之处,同时也存在差异。其一致之处体现了文献记载中蕴含的真实历史因素,其差异则体现出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进入国家阶段的城邑(或中心聚落)极少,大多数仍处于较原始的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血缘部族状态;进入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城邑(或中心聚落)多为小国状态,范围有限,影响较小,与后世夏商国家相比有较大差异;早期国家初始阶段为多中心并存,无明显的核心区和引领区,与夏商国家以夏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明显有别。
Abstract:
In terms of national structure, the Community of Yao and Shun appeared the combination of blood and geography, and possess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viding people according to region;In terms of state power, the social public power developed and initially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yal power;In the state structure, it showed the ini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ite state structure. These three point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and were important embodiments of the Community of Yao and Shun entering the state stage. However, the Community of Yao and Shun still had a certain primordial nature, so it could be called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arly stat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reflecting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Yao and Shun community, and the differences reflect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arly countri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arly state, there were few cities (or central settlements) with national elements, and most of the ancient cities and settlements were still relatively primitive in development, small in scale and single in social form, still ruling on the basis of blood organization; Cities (or central settlements) that entered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arly state were many in size and had limited influence;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te was in a polycentric state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became prominent in its core and dominant position.
Key words:Yao and Shun community;Early States;Xia and Shang Dynasties [责任编校 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