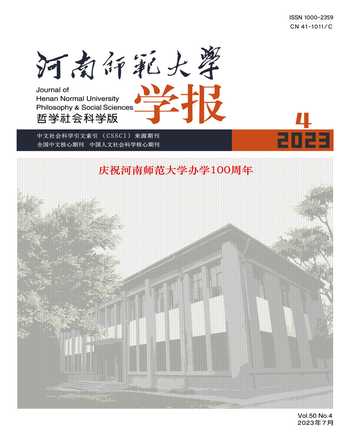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学理逻辑、旨意与价值
2023-04-29陈伟
摘 要: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学理逻辑在于科学文化哲学“明理”内涵的规约及故事化叙事的“大众化要求”与“共情”能力;旨意在于构建一种以“崇善”价值为核心的具有普适性的新中国科学精神,以此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价值在于借助精神的内涵和情感在激变的文化现实和国际关系中寻求文化建构的力量,通过促进文化认同,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文化实践不仅是科学普及与传播,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性深化或2.0版。
关键词:科学文化传播;故事化叙事;科学文化哲学;崇善
作者简介:陈伟(1970-),男,江苏兴化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科学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科学文化翻译与传播、翻译学、语言学等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YY100)
中图分类号:G3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4-0072-06 收稿日期:2022-09-15
亨廷顿指出,21世纪现代化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所有文化都在朝着现代化迈进 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李俊清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立足这一现实,科学文化传播的内容与机制需重新定位,以便释放科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品格的社会建构力量,由此揭示科学文化传播在当代人类文明中的进程与价值。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宏大语境中,中国科学文化潜在性地指向故事化叙事的传播策略,即深耕中国科技素材与优秀文化资源,采用全球思维下的叙事方式进行故事化塑造,在不违背真实性底色的基础上着力书写一个艺术隐喻形式的文本精神世界,从而以一种人文交流样态演绎中国科技与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涵 陈伟:《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学理接口、运作路径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最终实现“解释性效应”。那么,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具有怎样的学理逻辑,又承接怎样的旨意与价值呢?
一、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学理逻辑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叙事转向”的时代,叙事被当作“至尊话语”(Queen of Discourses)。费希尔指出,世上一切事,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还是内心体验,都以某种叙事形式展现而存在,并通过叙事形式传播某种观念 Fisher,W.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Value and Ac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7,p193.。叙事作品在其充要条件上包括一个讲述者和一则故事。从“场”理论角度说,故事本质上是在真实素材基础上,通过创作者的“在场”而对素材进行“发掘”与“重塑”,实现创作者与作品在情感、观念和生活上的融合。纵观人类文明史,“故事”是最基本的人类文化活动。尽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叙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规则,但这种叙事文学“始终是最受欢迎、最具影响的文学类别” Scholes, R., Phelan, J, & Kellogg, R.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6.,对文化的传播与分布举足轻重。
(一)科学文化哲学的内涵规约:“明理”
故事以叙事方式讲述一个有寓意的事件,创作要素之一是有立意,即记述和传播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道理或价值观,引导社会性格形成。讲故事就是话语的叙事模式,而话语则帮助“形成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观念和理解事物”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0页。。可见,故事要有“深度”,核心价值在于“明理”,即通过具体叙事活动揭示文化意义,解析文化思想,阐释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思想性成为“评价中国故事内容好坏最重要的指标” 陈先红,李颖异:《基于综合评价法的中国好故事指数研究》,《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中国故事应该“指向并构成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维度,从而与专门处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理念问题的文化联系起来” 王一川等:《中国故事的文化软实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在科学哲学的逻辑认识论、技术中心论抑或科学史研究的“内在主义”向度下,科学普及或传播的重心是科学知识,而远离“价值维度”。随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分裂与冲突中走向沟通与融合,从斯诺、萨顿到拉宾格尔、柯林斯,两者被努力整合为建设性对话图式:科学是一种像人文学科一样的文化,应该受到社会学的考察。由此,科学哲学在新世纪被推动发展,从关注科学对“物”的存在性反思的“知识论”范式,演变为视科学为一种具有丰富社会价值观内涵的文化(活动)、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深刻融合在一起的科学文化哲学。这一演变或转向立足生活世界指向人的存在意义和实践价值,科学文化被视为价值观的源泉之一。
科学文化哲学揭示出人类围绕自然的价值诉求,其内涵为故事化叙事提供了“明理”的逻辑条件。真正的科学人文主义并非仅局限于斯宾塞变革社会理论式的科学理性观念,而是以人类的现实关怀为本,自觉继承并高举文艺复兴以来尊重人性、讴歌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自由与平等的人文主义传统。事实上,随着科学社会化和国家化进程与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开启,科学文化景观逐步清晰,以一种二元组合结构回归作为一种具有道体内涵和人格化特征的文化事业,价值理性突显,强调在科学作为全球价值与全球文化中探討和阐释科学对人类与个体解放的意义问题,形塑人类文化价值建设与世界文明发展图景。
从动态反馈系统角度说,“科学传播内容不能独立研究,必须与传播机制的探讨结合起来” 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5期。。在此意义上,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是一种“巧妙叙事”,解决了传统科学传播“把内容与手段分开处理”的问题,叙事者借助适度“灌输”修辞方式,以比接受者更有优势的话语地位,忠实呈现叙事内容,准确挖掘科学文化故事背后的思想性和现代文明理念,并艺术性呈现出来,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巨大影响“不仅得益于其价值观念的创新,还得益于其话语表达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程志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文化传播策略及当代意义》,《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5期。。
(二)故事化叙事的“大众化要求”
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一书中把故事称为“文学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我们生活中基本而不可替代的需求之一,体现了一种“大众化要求”。怀特认为,以读者熟悉的“生活形式”方式讲故事,他们就能够“把它与自己隐含在文化实践中的理解模式相连接”,“与自己‘熟悉的事件相联系” White, H.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p195.,由此加以认知与诠释。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根本上预设的是交流修辞,重视叙事对象的主体性及其观念和接受表现,强调通过叙事者和叙事对象的交流与讨论达成共识。
从“大众化要求”出发,只要逻辑上自洽自立,平民化、具象化的故事化叙事,一方面在宏观叙事层面展现科学实践推动历史进程这一大道理或大图景,另一方面则在微观视角放下科学范畴的精英化身段,作为一种与大众日常生活相融相交的“代表性文化”走进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让他们“简单化”地感受并理解科技的技术魅力与价值理性。具体地,故事化叙事不但着眼于内容的“可普遍化”,注重科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在历史考据的真实科学实践基础上以普适性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立意,构建具有共通情感、促进行为认同的故事叙事,也着眼于机制的“可接受性”,注重公众对叙事方式的能动“接受”表现,重视从情节、人物刻画等方面提高故事饱满度。
在全球化、多极化的世界趋势下,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大众化要求”也指向世界情怀,强调立足全球讲故事。这无疑能迎合我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发展战略,即“高度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表达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传递全人类的共同诉求、昭示中华民族的世界担当” 吴汉全:《话语体系初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08页。。在思想性层面,基于全球共有文化价值观讲述中国故事,能预设互鉴互通的品质,推动在许多理解水平上的互动和对话;在话语风格层面,故事化叙事则脱离政治宣教的枯燥风格,能消解东西方话语体系在话语习惯、叙事结构、情理逻辑等方面的差异,提高文本的本土适应力,用客观事实与曲折情节获得国际认同。
当然,21世纪以来媒介环境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也强化了科学文化基于“大众化要求”的故事化叙事的逻辑。社交媒体的全球交互性消融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普通民众成为个体故事的国际讲述者,个体故事与情感被公共化、国际化,也激发了受众对共同情感和体验的分享动力。
(三)故事化叙事的“共情”能力
国际叙事中情感共鸣是灵魂。“叙事的功能并非‘表现,而是建构场景” Barthes, R.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Heath, S.Noonday,1977,p123.。故事聚焦于描述一个情理交融的事件场景,重视情节生动性和复杂性与语言艺术性,强调以情(情绪或情感)动人,借此与受众互动,让他们在故事的情感体验中找寻社会一致性与情绪共通性,从而共享价值观念,增进文化认同。这是对人际传播的回归,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无法通过智力去影响别人,情感却能做到。因此,在国际传播中“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
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承接了这一能力,作为一个在新时代秉持文化建构理念、让大众接收和接受且发挥叙事者能动性的活动,不仅发掘、描绘中华文化资源中基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体现我们今天和整个时代的精神图景,也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让故事走入人心、走向世界,从而重构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形象是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 王一川等:《中国故事的文化软实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页。可见,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思想性诉求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诉求,意在还原科学知识的情感面,形塑一种更加宽阔、融会贯通的价值体系和审美特征,实现与读者的“情感性”连接。
媒介环境发生的革命性变迁在此也强化了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逻辑。平台型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个体化与共享性方式最适合讲故事,便利个体在自身经历的事实或体验中融入人类共通的情绪和情感,从而激发共情,凝聚共识,最终提高个体故事的“声量”。这也放大了受众接受惯习中的故事性和情感性因素的需求。
二、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旨意
(一)科学文化传播事业中缺位的“崇善”价值
学术共同体普遍认为,文化之于“人”的本质在科学文化中体现为“求真”“崇善”“臻美”或“追求真理、追求至善”的价值诉求,并据此理解和诠释。然而,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创包蕴崇尚理性、尊重经验、师法自然等科学精神的人文主义传统,近代科学文化及其理论阐释系统都把“核心理念”定位在“求真”精神或追求超越功利的真理的技术理性维度,例如任鸿隽在《科学救国之梦》中认定“崇实”“贵确”“察微”“慎断”与“存疑”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特征。
科学文化的价值诉求如果仅局限在通过科学研究更为精确地认识世界、发现自然规律,无疑会极大消解科學文化的现代文明价值,尤其是弱化在科学与人文融合视角探讨人类价值与文明问题的力度。人文精神应该“体现在科学家、专家学者本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面” 葛剑雄:《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人文”》,《文史哲》,2021年第3期。。传统科学哲学经过历史主义的范式革命和反科学主义的社会批判,逐渐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关注科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基础,奉行以解放人性、宣扬人性为目的的建构主义进路,确立了人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质言之,完整意义上的人文实质上就是人性,“只有从人性的角度理解科学文化精神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要义和深刻内涵” 毕吉利,刘旭东:《科学文化建构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规定》,《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年第6期。。可见,“崇善”才是人性的基础和人之发展的向度,真正指向科学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关怀。
从当下社会现实角度说,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与自然灾害、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叠加,另一方面市场化、工业文明的非人性化冲击加重,人文精神和精神自主性越来越缺乏,涉及良知、人性、伦理、道德等基本价值观和超然审美越来越稀薄,社会戾气与反智主义由此越来越横行。这些都迫切呼唤科学文化的崇善价值对人性的完善,既不要让世俗利益遮蔽了人性,从而文明利用科技,避免科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更要真正理解、重视并维护人的自由和解放、法治和契约精神等现代文明要素的当下意义,积极以共情、同理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理解精神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强调人性是风纪的源泉。人类的本体之善在科学作为人的理性实践活动中臻于完善,这才是科学取向的文化基石。可见,科学文化描绘的意义图景必须深刻嵌入人类生活世界并成为其中一部分被重新定义,由此,科学文化传播需以独特机理指认自身具有时代性与现代性的品格——基于“人性”或“崇善”价值的故事化叙事才是以文艺手段实现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融合的经典实践,指向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文化空间。
(二)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旨意: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
当今时代,思想文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才能真正产生凝聚力。这是新时代正确解读国家和民族发展、国际关系想象的关键。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称性破缺:近代,遭遇了嚴重外源性文化危机;当下商业社会与全球化时代,文化消费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使得自身文化陷入异化困境。在这双重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与过去时代相适应的陈旧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缺失足以支撑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民族意识与价值精神。而且,现代化加固了现存文化,多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永远存在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李俊清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先进性文化具有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品格,能消解加剧的文化冲突,驱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是自然辩证法自身理性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要求。
历史上,科学文化融入欧洲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重塑了人文文化制度,并据此实现社会治理。为此,“将西方的科学型文化与中国的伦理型文化相结合,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在科技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国人的健康、健全、积极、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董春雨,陈旭:《从复杂性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若干理论原则》,《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这揭示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本质在于通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融合,面向世界先进性文化促进传统文化观念的创新和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科学化。这一定位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的差异协同,张扬了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理性力量对文化建设与社会建构的意义,旨在通过对自然实在论的批判与接受实现科学本体的社会化诠释和人性回归。
可见,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旨意在于立足中国科技成就,坚守中华优秀文化立场,依据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寻找并张扬故事性,以独特创作理念与有效叙事手段把真实素材艺术变形为自成一体的故事,构建以“崇善”价值为核心的具有普适性的新中国科学精神,然后通过传播不断完善、践行这种普适性,从而以科学人文主义情怀的行动范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的现代社会建构与治理。鉴于科学文化是历史化产物,一方面文化本地性使科学活动从起源上获得了本地性,另一方面科技因为自身浸淫了社会制度、文化观念、道德信仰等,其社会转移也会产生文化摩擦或冲突,这种新中国科学精神的普适性实际上体现为现代文明诉求。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思想贡献在于“主张文明的价值首先在于有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聂敏里:《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5月17日。对中国科学文化而言,由此需要立足民主政治的全球化态势,“探讨科学当前如何适应开放创新主流价值观的问题”,提炼优质价值观要素,让它们“进入到当前社会主流的科学精神价值体系骨架中” 汤书昆:《关于我国科普时代与科学文化时代的思考》,《科普研究》,2017年第6期。,塑造自身本土科学思想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相融合的独特品性,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精神桥梁。这应是科学文化“崇善”价值的时代表达。在此意义上,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不仅是科学普及与传播,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性深化或2.0版。
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不仅是科学传播方式的一场转变,更是基于文化完满性的文化自信的深层表现。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表现,文化自信是自然辩证法哲学属性的规约,“源于对情势所做的理性、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董春雨,陈旭:《从复杂性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若干理论原则》,《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借助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开启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运动,表明了文化主体在面对世界与文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积极主动实现自身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确信能够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最终深刻影响社会历史发展。
三、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价值
由于深刻融入人文属性,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获得了特定价值直接性,由此深层次塑造能使公众清晰感知的“传播视野”。从国家战略层面说,这一文化实践以新中国科学精神为思想内涵,通过故事化叙事搭建特定的科学文化时空,向世界范围内的公众传播,借助精神的内涵和情感在激变的文化现实和国际关系中寻求文化建构的力量。具体来说,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通过促进文化认同,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
(一)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自觉首先是文化层面的自觉,因此,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不断加剧的流动性导致部分个体越来越脱离社会成为相离散的原子式个人,他们的自身文化在被动接受的异质文化与价值观影响下逐渐消逝;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本土行为者知晓其文化的所有方面,而且每一个行为者都对(文化)符号有着不同解释” Keesing, R. Theories of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74,(3).。传统科普重于传播科学知识,疏于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的体用逻辑,揭示并培育渗透中华文化精神的内生性科学文化体系,公民失却了在自己精神世界里再现中国科学精神而获得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机会。
科学精神通过特定文化选择,在漫长时空流转中形成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记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文化故事使科学精神融入民族精神,科学文化由此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认同的独特内容。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背景,其作为基石的新中国科学精神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这正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共同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质言之,在对内传播向度,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能加深国人对自身优秀文化的自觉认知,引发他们基于社会主义和现代文明优越性的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鸣,由此构建一个触发文化身份认同的无形精神或文化社区。
科学家形象是科学精神的具象化。袁隆平是新中国科学精神的典范表现:既体现我国科学工作者务实求真、敢于创新、团结协作等科学理性精神,更体现他们推崇善行/意、尊重生命、坚守人性、遵从良知等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情操。这些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昭示与结晶,能激发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由此释放巨大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增强对中华文明主体性塑造的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
(二)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自觉意味着全球化时代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眼光与空间意识,在知识社会领域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使命。事实上,文化价值冲突与观念博弈已成为全球化、多元化時代的重大历史难题。为此,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新理念,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与世界的主动思考与关怀,一方面彰显了我们在坚持主流价值观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则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类基本精神普遍性的价值追求。“只有科学与人文携手并肩,我们才有希望在发掘人类思想的共同性上获得成功。” Rabi, I.I. Science:The Center of Culture. World Publishing,1970,pp37-38.虽然科学文化往往保存了其缘起环境下具有鲜明地方性特征的审美和道德内涵,尤其具有理念多样性,但与其他文化实践相比,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上具有独特优势。
首先,新中国科学精神有着世界普适性。文化本质上是不同民族人民创造的现实世界的内在模式,并据此审视、理解他者文化。这样,文化故事在另一民族或国家中的重构与认同,在维持正常话语调适的前提下,文化内涵的价值同一性就成了不同文化在保持各自异质性状态下实现互渗与“共情认同”的关键。以“崇善”价值为核心的新中国科学精神立足于以自然辩证法为核心的现代科学理性精神,融合了中华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与先进品性的现代文明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前途和命运、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终极关怀。可见,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暗合了价值同一性,更利于作为人类基本价值观中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自然”路径而服务全球文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
其次,科学成果有着人类共享性。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让全人类获得更好体验感和幸福感,这才是科学的终极价值。根据科学社会学研究,文化认同已经被科学和技术实践深刻地改变了。菌草技术是我国发明的一项前沿技术,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渗透的以中国科学家的真诚、守信与全人类情怀等为内容的新中国科学精神超越文化对抗,展现出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消除人类困境的优秀品格,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再次,人类对科学文化故事有着趋同的审美与价值旨趣。这一点在前面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大众化要求”部分已做了论证。“科学”这一主题决定了“文学是人学”命题总是扩展到对人类整体命运关注与表达的层面,注重从“类”的范围刻画人物形象,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与其他题材的严肃叙事相比,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更能激起我们共通的情感、审美与价值旨趣,并通过动态层累加强化对中华文化与现代文明追求的认知,形成同构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软实力视角的思考
萨顿认为,“科学给我们人类提供的最大价值是它的精神力量”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页。。作为一种文化发展战略,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软实力经典概念,“狭隘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可能产生软实力”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6页。。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表征的是以科学理性文化为主导、现代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文精神交汇的一种新型文化体系,它以具有普适性的新中国科学精神为基石,体现了中华民族思考和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本民族与他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先进品格,张扬人类共通的价值和情感,因而能激发基于现代文明的人性共鸣,作为民心相通的天然手段而产生文化软实力,由此提升中国形象。
另一方面,国家文化精神和气质主要体现在国民个体或集体表现中,国民素质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要素资源。一个国家如果国民素质不高,经济再发达也不能赢得尊重,也就无法产生软实力。素质在哲学层面是人性的基本方面。在国民素质中,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是核心要素,它“所包含的理性思维和民主精神等内容是人的现代性的具体表现” 张红霞:《序言》,万东升:《中国文化视野下的科学教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比科学知识更重要。但是,科学精神失落、科学素养缺乏已成为当下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些人缺失现代公民精神,一边在享受文明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边却实施与文明世界对抗的行为。科学文化传播与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路径。然而,科学素养向来被排除在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外,迄今“科学文化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思维仍然没有在学生和教师的心中生根发芽” 张红霞:《序言》,万东升:《中国文化视野下的科学教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在此意义上,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以其明确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超越传统科学知识传播与教育而获得基于全人素质教育的历史价值:帮助公民获得现代思想意识和文明观念,不断提升文明程度、道德水准、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结语
“如何将人文精神渗透到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中,促进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融汇,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课题。” 彭纪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走向21世紀的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3期。对我国而言,利用科学文化进行社会重建则是面对新时代与新国际形势承担的历史使命。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在其学理逻辑推动下成为走进科学文化、走进科学精神、走进现代文明而实现新时代新思想建构的文化教育与传播路径。如何立足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充分利用这一文化实践建构基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鼓励真理追求的对外话语与叙事体系,真正意义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交相辉映,同时推动我国完成从文化自信到跨文化自觉、从文化自觉到传播自觉的国际传播能力转变,值得深入探讨。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tory-telling narration of scientific culture, as for theoretical logic, lies firstly in the philosophical emphasis on value of scientific culture, secondly in the popular requirement and empathy ability of story-telling narration. Its purport is to construct a universal new scientific spirit of China with “good” at its cor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value is by seeking the power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hanging cultural rea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enhance internally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elp to build externall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This cultural practice is thus set to be a historic deepening or Version 2.0 not only of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culture, but also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Key words:scientific culture communication;story-telling narration;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culture;seek goodness [责任编校 刘 科,彭筱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