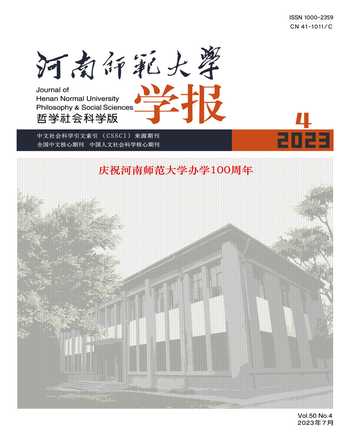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2023-04-29房慧颖
房慧颖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治理理念;生态法益;刑行衔接;刑民共治
作者简介:房慧颖(1990-),女,山东德州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预防性刑法、经济刑法、刑法解释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EFX003)
中图分类号:D922-6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4-0063-09 收稿日期:2022-06-29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用最严格的制度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用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是刑法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大潮中的重要使命。从污染环境罪条文的修正历程来看,刑法治理污染环境罪的理念发生了从事后惩治到事前预防的根本转变。事前预防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实现对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刑罚处罚,遏制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不断高涨,但也面临着司法认定和适用效果方面的一系列纷争和难题。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对于污染环境刑事治理机制中犯罪圈的划定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治理环境污染不能仅凭刑法的一己之力,民法、行政法作为法治系统中的要素,与刑法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陈庆安:《〈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回应性特征与系统性反思》,《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8期。。
一、现实图景: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的理念演进
根据1997年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只有当非法排污行为累积而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且能够证明污染行为和污染事故之间的实在因果联系,污染行为才具有刑事可罚性,这是典型的事后惩罚主义的体现。经过2011年和2020年的两次重要修正,刑法规制环境污染行为的时间提前至环境介质被严重污染而非必须等到严重后果形成之时,即通过事前预防环境危险行为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优先保护,说明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房慧颖:《污染环境罪预防型规制模式的省察与革新》,《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因此,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理念的分水岭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
从1997年到2011年,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治理模式采用的是事后惩罚主义的理念,采用事后追责方式进行法益保护,而环境本身并非刑法的保护对象。具体表现有二:其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这一法益定位立基于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刑罚的启动皆因公民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被环境污染行为所损害,而生态环境的安全只能被看作公民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的附属品。其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构造为结果犯模式。如果只是生态环境本身遭到侵害,但并未损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则刑罚无法启动。这一时期刑法以事后惩罚主义治理模式惩治污染环境犯罪,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与刑法理论背景。这一时期我国坚持“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是常态。同时,这一时期坚持事后、消极、被动的结果本位的古典主义刑法观。在古典主义刑法观的指导下,只有在法益遭受实际侵害时,国家刑罚权才得以发动。古典主义刑法观有其自身合理性,在保障公民自由、防止国家刑罚权恣意发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征,而在结果本位的古典主义刑法观指引的立法模式下,出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等原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条文基本处在虚置状态刘德法,高亚瑞:《论环境刑法视域下的生态修复性司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面对日益加重的环境污染现状,刑法却有心无力,司法机关对环境污染治理处于难作为的尴尬境地,由此宣告了结果本位的古典主义刑法观指引下的事后惩罚主义刑事治理模式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失灵。
2011年和2020年的两次刑法修正,标志着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彻底转向事前预防主义的治理模式。具体表现有二:其一,生态法益具有了刑法上的独立价值,不再是刑法保护公民生命、健康与财产法益的副产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安全本身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其二,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转变为抽象危险犯模式。从结果犯向抽象危险犯的转变,意味着犯罪门槛的降低,契合了风险社会中刑事治理早期化的趋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仅需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则是“情节严重”而非“后果特别严重”。这一修订清楚无误地传达了刑事立法通过法益保护前置化来遏制污染环境行为的意图。立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刑法理论发展背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发生了从事后惩治到事前预防的根本性转变。晚近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环境保护上升为国家基本国策,生态安全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组成部分的战略高度,“绿色原则”被写入民法典。与此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促使各国刑法观逐渐从事后、消极、被动的结果本位的古典主义刑法观转向事前、积极、主动的行为本位的预防主义刑法观。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和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恐怖主义犯罪、环境犯罪、食品药品犯罪以及网络犯罪等一系列犯罪的修订与相关新罪的增设,标志着预防主义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转变为事前预防主義,实现了生态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隐性废除了在事后惩罚主义治理模式下难以证明却必须证明的污染行为与公民生命、健康与财产法益遭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缓解了环境侵害累积性与环境治理恢复长期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刑法顺应社会发展模式作出了正确的调整,在污染环境治理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二、理论省思: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机制的系统构造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338条所作的修订,使得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罪过形式等问题的长时间争议。对上述问题的厘清,不仅关乎污染环境罪的认定,而且对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一)法益定位:污染环境罪侵犯的法益为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
修正后的刑法第338条所保护的法益为生态法益或者环境法益,在学界已几无争议。但是如何理解污染环境罪所侵犯的生态法益,学者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关于污染环境罪所侵犯的生态法益,理论上存在秩序本位的生态法益说、生态本位的生态法益说和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之争。秩序本位的生态法益说认为,生态法益的本质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秩序,也即污染环境罪的设立是为了用刑罚惩罚的手段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秩序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5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第1389页。。生态本位的生态法益说认为,生态环境法益,也即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本身就具有刑法独立保护的价值,而非依附于公民的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存在伊东研祐:《环境刑法研究序说》,成文堂,2003年,第42页。。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认为,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与人类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关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对于污染环境罪所侵犯的法益定位,本文采取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
笔者认为,秩序本位的法益说和生态本位的法益说存在明显缺陷。秩序本位的法益说过于强调社会的规范秩序,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秩序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一部分,其规范保护目的并非空洞的行政管理条文与规章,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公民的人身與财产利益。秩序本位的生态法益说对这一点的忽视,导致其陷入形式主义立场,偏离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形式主义缺陷会进一步导致法益内容的空洞化,从而使得法益保护管理秩序这一手段无法实现社会保障与个体权利保护的实质目标Vgl. Hohamann, Das Rechtsgut der Umweltdelikte: Grenzen des strafrechtlichenUmweltschutzes, Verlag Peter Lang 1991, S. 188 ff.。生态本位的生态法益说忽视了法益应服务于具体的人类利益这一基本出发点,虽能够实现对生态法益的有效保护,但却可能过度地牺牲公民自由与权利。法律是人类为人类制定的规则,而非为非理性的生物制定的规则高鸿钧,赵晓力:《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页。。所谓生态本位的生态法益,因为过于强调生态系统的独立性,始终未能厘清自然意义的环境媒介之于人类社会运作的关联意义,这种将人和环境截然分开的逻辑思维,忽视了人和环境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为割裂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使得法益保护走向物本主义极端。
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并非单纯证立国家刑罚权的扩张,而是立基于对公民个人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同时又承认生态环境超越公民个人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实存地位,具有合理性。刑法保护生态法益的目的是通过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而维持人类的存续与发展。事实上,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将回避生态环境危险以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作为宗旨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从生态环境这一整体视角看来,人类是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维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维护好人类的根本利益。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例,生态环境对于人的生命健康维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依赖生态环境而得以存活。环境污染可能会直接损害人类的肌体健康,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命。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认识到,保护环境最终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但是这里所说的人类的利益是一种预期利益,在现实中只能转移为和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1页。。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说与我国法律规定相契合。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而此处的国家规定包括环保法律法规。环保法律法规所关注的生态环境,并非自然意义上的环境媒介,而是关注生态环境所内含的社会性意义古承宗:《刑法的象征化与规制理性》,台湾元照出版社,2017年,第206-207页。,而社会性意义上的生态法益,即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生态环境的安全是公民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得以保全的根基,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生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良性或恶性影响。从形式而言,生态法益是能够实现对公民个人法益(即公民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系统性、长远性、前置性保护的集体法益,代表的是国家提供的保证公民个人生存、发展的制度性、体系性生态环境条件房慧颖:《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价值定位与规范化构造:以刑民关系为切入点》,《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这种制度性、体系性生态环境条件是抽象的,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法益的简单累加,所以不能以作为集体法益的生态法益能否还原为公民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来作为其正当性根据吴登堡:《德国刑法学的现状》,蔡墩铭译,台北商务书局,1977年,第59页。。从实质而言,生态法益自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实现对公民个人法益的保护,生态法益是对个人法益的前置性防护。
(二)行为构造: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
刑法设置污染环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根本上决定了污染环境罪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和污染环境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根据,这是认定污染环境罪的基础。在明确污染环境罪条文的保护法益为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之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通过污染环境罪条文的犯罪构成设置探讨本罪的行为构造,即污染环境罪条文的犯罪构成设置所体现的法益保护程度。换言之,污染环境罪处罚的是对侵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的实害、具体危险抑或抽象危险?这是对认定本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对污染环境罪行为构造的探讨建基于污染环境罪条文的保护法益。污染环境罪条文的保护法益为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生态法益是集体法益,具有不同于个人法益的特征。尽管犯罪的行为构造设置应以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为优先,但是从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本身的特质出发,将污染环境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具有必要性。其一,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作为集合法益,具有一般集合法益的特性,即精神化和抽象性特征,而非具体实存,表达为抽象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对其侵害(实害或者具体危险)往往难以通过经验化的判断来说明,更无法准确说明集合法益之侵害(实害或者具体危险)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李川:《二元集合法益与累积犯形态研究:法定犯与自然犯混同情形下对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污染环境行为所产生的对生态法益的侵害属性,通常只能进行抽象意义的推定或拟制,基于这一原因,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设置为抽象危险犯更为妥切。其二,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生态法益受侵害的过程、程度以及与污染环境行为的因果联系很难得到准确说明,引入有一定偶然性。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生态法益被侵害的结果或具体危险未必会即时造成明显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其侵害结果或具体危险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通常会有一段时间间隔,甚至需要经过代际更迭才得以体现。同时,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法益的侵害通常表征为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往往具有共害特征,即生态环境系统破坏的原因在很多情形下源于多个主体同质污染行为的渐次累积。生态环境系统破坏具有不可逆性,为了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刑法就不能等污染环境行为造成明显的法益侵害结果或者具体危险,而需提前到法益侵害风险产生的初始阶段予以规制,以实现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预防。
抽象危险犯的设立代表着国家刑罚权的扩张与公民自由的限缩。为了防止刑法不当限制公民自由,需要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侵犯个体法益的抽象危险判断,形成对污染環境罪抽象危险犯认定的限制过滤。具体而言,对污染环境罪抽象危险犯认定的限制过滤机能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对污染环境行为侵犯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法益的判断,这是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观的必然要求。应当承认,当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法益的侵害已是一种抽象的、拟制的危险,则其对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法益的侵害就更不可能是具体危害结果或者具体危险。同时也应看到,如果某种污染环境行为只是对侵犯生态法益具有抽象危险,但是缺乏形成侵犯公民人身与财产法益的抽象危险的逻辑进路与具体经验,则不宜被认定为侵犯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的污染环境罪Vgl. Hohmann, Von den KonsequenzeneinerpersonalenRechtsgutsbestimmungimUmweltstrafrecht,in:GA 1992,S.79.。在人本主义的生态法益观视野下,生态环境因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具有被刑法独立保护的价值,与人身和财产要素完全割裂的生态法益缺乏被保护的正当性与意义房慧颖:《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与认定的教义学展开》,《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38条所言之 “严重污染环境”,意味着当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水体、大气、土地等造成实际损害(如水体污染物超标、大气雾霾、土地污染等可感知的实害结果)时,才构成污染环境罪。因此,污染环境罪应是实害犯姜俊山:《论污染环境罪之立法完善》,《法学杂志》,2014年第3期。。这一结论的得出事实上混淆了生态法益与生态要素。生态要素是指水体、大气、土地等具体的可感知的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具有局部性和具体性;而生态法益是指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具有系统性和抽象性。一方面,对生态要素的破坏不能直接等同于对生态法益的侵害。对水体、大气、土壤等生态要素的破坏,可能会因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在一段时间之后消失,此时,不能认为对生态要素的侵害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只有当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要素的破坏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进而影响到作为整体的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时,才能认为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了生态法益。另一方面,对生态法益造成侵害不一定意味着对生态要素也造成侵害。污染环境行为造成对生态法益的抽象危险,但并未实际破坏生态要素,此时也应认为行为符合“严重污染环境”要件。例如,严重排污行为被及时发现,尚未造成对水体的实际污染,此时尚未对生态要素造成实际破坏,但是行为已经对生态法益造成了抽象危险,已经达到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刑法第338条所言的“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指对具体生态要素的可感知破坏,而是指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抽象危险,即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具有拟制或推定的抽象危险。因此,从污染环境罪条文保护的集体法益即生态法益的抽象性出发,将本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更为妥切。
(三)罪过形式: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为故意
认为污染环境罪可以由过失构成的学者提出,尽管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有意为之,但是对于以上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是持否定态度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第858页。,而判断行为人构成犯罪故意抑或犯罪过失,应以行为人对结果的心态为标准,并非以行为为依据,因此污染环境罪可以由过失构成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3页。。上述说法与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观相违背。当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生态环境面临抽象危险时,即是对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的侵犯,而生态环境面临的抽象危险现实化之后所表现出的具体的严重危害后果,则并非污染环境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所描述的危害后果。事实上,实施污染环境这一行为本就内含着对生态环境的抽象危险。对于污染环境罪这一抽象危险犯而言,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侵害属性,通常只能进行抽象意义的推定或拟制。保护生态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一种未来的、预期的利益,反之,污染环境行为对人类利益的损害也是一种未来的、预期的损害。当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时,即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一种未来的、预期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可以被抽象或者被拟制为“严重污染环境”这一危害后果。换言之,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污染环境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且仍然有意为之,即可认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污染环境”后果至少存在间接故意而非过失。
值得说明的是,将本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并不会造成不当地缩小本罪处罚范围的后果。有学者提出,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后将其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旨在扩大处罚范围,严惩污染环境的行为;如果污染环境罪不处罚过失犯,则是不当缩小了处罚范围,与修法初衷相违背苏永生:《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研究:兼论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及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例外》,《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陈洪兵:《模糊罪过说之提倡: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上述论说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对污染环境罪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构造有所误解。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成立,需以法定危害后果的出现作为重要构成要件。而污染环境罪的设立,将原来刑法处置污染环境行为的节点大大提前,因此仅因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就认为不当缩小了处罚范围的观点过于武断。此外,鉴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是抽象危险犯,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即已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危险,而行为人明知污染环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可以认定为行为人是故意犯罪。相比较而言,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明显大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罚范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后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之对比即是有力证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失导致污染物泄漏的情况下,根据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条文,可能成立本罪;但是如果将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来认定,反而不可能构成本罪,这便是将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罪认定从而缩小处罚范围的典型例证陈洪兵:《模糊罪过说之提倡: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上述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将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罪来认定,则因过失而导致污染物泄漏的情况确实不可能成立污染环境罪,但不能就此认为将污染环境罪的责任形式认定为故意便缩小了刑事处罚范围。因过失而导致污染物泄漏可具体划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因过失而导致污染物泄漏,但是并未就此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该过失行为因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所要求的结果要件而不能成立本罪。此时,行为人的行为既不成立作为过失犯罪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成立作为故意犯罪的污染环境罪,将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从而缩小了刑罚处罚范围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房慧颖:《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规制困局与破解之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其二,因过失而导致污染物泄漏,并因此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行为人的行为虽不能成立作为故意犯罪的污染环境罪,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未危害公共安全,在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此时,将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也不存在缩小刑罚处罚范围的问题。当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未危害公共安全,也未造成人身伤亡,仅造成财产损失,且不符合其他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对行为人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而是通过民事、行政、经济法规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此时,因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预防必要性也较小,对其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并无不妥,不存在不当缩小刑罚处罚范围的问题。
三、法治系统:污染环境罪刑事治理机制的范式建构
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效能,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一)刑行衔接:污染环境罪中“违反国家规定”之解读
《刑法》第338条中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这意味着污染环境罪是法定犯,具有行政从属性。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主要体现在行政标准对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影响。其一,污染环境罪成立需要参照行政标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行为规制首先依赖于行政法律法规,这是由现代法治系统中不同法律机制的作用与特性所决定的。在认定行为人成立污染环境罪之前,首先要对其行为进行行政违法性判断,换言之,在生态环境领域,刑事违法性成立的前提是行政违法性的成立。污染环境犯罪是违法性程度更高的行政违法且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换言之,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是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双重违法性的行为时延安:《刑法规范的结构、属性及其在解释论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其二,对生态法益受侵害程度的识别与度量,需要参照行政标准。污染环境罪侵犯的法益为生态法益,对行为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判断过程,也即衡量生态法益是否受到损害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害的过程,需要参照更为专业、细致的行政规定和标准焦艳鹏:《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与此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被污染程度的评估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要在行政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标准的指导下进行。
行政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环境罪的成立具有过滤与限缩作用。不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即使在实质上具有严重危害,因不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构成本罪,否则便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以陕西凤翔血铅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发生于2009年陕西省凤翔县。一家名为东岭冶炼公司的铅锌冶炼企业,年产铅锌达20万吨。企业所在地附近的两个村庄有731名儿童参与血铅抽检,其中615名儿童血铅招标,167名儿童达到中度、重度鉛中毒。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东岭冶炼公司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是造成这些儿童血铅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但是东岭冶炼公司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企业周边的土壤铅含量也并未超出国家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此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为:东岭冶炼公司全面停产,与此事件相关的凤翔县11名领导被予以党纪处分。张晓媛:《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刑法的立场转换:以环境损害的二元特征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为例,冶炼公司排放含铅有害物质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周边村庄儿童身体健康的严重损害,但是由于其排放行为符合当时的国家标准,不符合“违反国家规定”的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不能构成污染环境罪,只能采取刑罚处罚之外的其他方式对该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活动的需求来说,必须是一种相对化的利用模式。这里所谓的相对化是指不应追求保护生态环境的绝对性,而是基于永续经营的观点,也即在生态环境自净能力的极限范围内、在特定的利用条件下允许一定程度的污染。生态环境是一个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系统,且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利用生态环境的这种能力进行生存和发展。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几乎能够完全被环境自动净化,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为人类的排污行为设置标准来控制人类向生态环境系统中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但是工业时代来临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向生态环境系统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呈爆发式增长,环境的纳污能力已濒临极限。人类排放的有害物质一旦超越生态环境纳污能力的极限,人类社会便终将面临灭亡的可怕后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有二:一是由法律禁止向生态环境系统中的排污行为,这样等于放弃物质文明为人类社会带来的舒适和便捷,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二是由法律制定一定标准,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只要人类无法做到对物质文明的彻底拒绝,就必须在一定限度内忍受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而忍受程度要结合当地人口密度、污染物特质、受影响的环境介质性质,进行专业判断、统一协调,由行政法律法规确定明确的标准,以将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稳定发展的范围内石亚淙:《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的分类解读:以法定犯与自然犯的混同规定为核心》,《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排污许可制度就此产生。行政法律法规对排污数量、种类、地点等进行规制李兴锋:《排污许可法律制度重构研究: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视角》,《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未超过行政法律法规所规定标准的排污行为不具有行政违法性。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具有二重违法性,即既有行政违法性,又有刑事违法性。且刑事违法性的违法程度明显高于行政违法性。所以,如果一个行为尚未达到具有行政违法性的标准,则这一行为显然不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
构成污染环境罪,则行为人的行为必然违反了国家规定,反之则不成立。行政不法行为与刑事不法行为之间并非简单的“量”的关系。换言之,刑法与行政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存在“质”的区别,不是所有的严重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都应受到刑事法律制裁。同时,污染环境罪条文中明文规定了“违反国家规定”的构成要件,对条文用语进行分析可知,对严重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时,要将行政法律法规之规定作为重要依据。但是应当看到,对刑法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要以刑法目的作为标准,而不能照抄照搬行政法律法规之规定张明楷:《行政违反加重犯初探》,《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行政法的目的是追求管理秩序的稳定与效率。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只有达到足够严重的法益侵害程度、值得刑罚处罚时,才演变为刑事不法行为。因此,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在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并不一定都符合“违反国家规定”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只有当污染环境行为达到对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的严重侵害程度时,该行为所具有的行政不法性才上升为刑事不法性,成为值得刑法科处刑罚的行为,否则便混淆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认定基础。换言之,对行政义务的违反所直接连接的法律后果是行政制裁,无法作为刑事不法即法益侵害实质内涵的论证基础。刑法与行政法是同一法治系统内的分工不同、作用各异的组成要素,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具体而言,行政违法行为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具有法益侵害之危险的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第二种是仅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定但并不具有法益侵害之危险的行为。对第一种情况而言,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区别在于“量”,当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危险的程度达到刑事法律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时,行政违法行为同时也成为刑事违法行为。对第二种情况而言,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的区别在于“质”,基于行政法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同,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的基础,即使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因其并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该行政不法行为也无法上升为刑事不法行为。如果行为本身只是违反了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中有关管理秩序的规定,不包含侵害法益的危险,则此处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不能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条文中的“违反国家规定”所言之“国家规定”。
(二)刑民共治:污染环境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机制之健全
《民法典》第9条所规定的“绿色原则”《民法典》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民法学界将该原则称为“绿色原则”。,不仅会在民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影响,而且在刑民一体化思维的影响下,其贯彻实施需要刑法治理手段的保障,反之也能够促进环境污染刑事治理体制的完善,进而实现污染环境罪的刑民共治。所谓污染环境罪的刑民共治,在污染环境行为的法律后果方面,表现为从民法的无过错责任到刑法的过错责任之间层次分明的衔接;在污染环境行为的诉讼机制方面,表现为污染环境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推进与运行。
根据《民法典》1229条之规定,污染环境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他人损害即需承担责任,不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七章专门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229条的规定是对上述立场的延续。。这在《民法典》第1230条的规定中可以得到印证《民法典》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民法典》第1230条之规定正是第1229条无过错归责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同时,《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第1235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从刑民一体化思维出发,刑法领域的污染环境罪治理和民法领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可以衔接起来,从而形成多维度与多层次的归责设置黄云波:《论一体化刑事法学的问题与出路》,《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刑法领域的污染环境罪治理和民法领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二者之间的衔接,不是指刑法和民法在归责原则上的等同。事实上,在刑法领域,贯彻无过错责任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不具有合理性。刑事治理机制与民事治理机制中归責原则的衔接,是指从民法的无过错责任到刑法的过错责任之间的位阶清晰、层次分明的衔接关系。
尽管污染环境罪条文经过历次修正,已经从结果犯演变为抽象危险犯,处罚节点提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对污染环境行为的预防作用,但是应当看到,刑法事后法的特性决定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仍侧重于对实施污染环境行为人的事后处罚。对行为人的事后处罚只能起到对污染环境行为的一般预防功效,但就已经被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而言,对行为人的事后处罚已于事无补。对污染环境罪条文的历次修改体现出刑罚前置化、法定刑加重的趋势,反映了立法者希望通过刑罚处罚方式来达到矫正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功效,但却忽略了污染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处境及已经遭到污染与破坏的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犯罪有其特殊性,除以传统刑罚处罚方式来处罚犯罪人,以达到吓阻和镇压功效之外,也应当考量被害人对被破坏环境恢复的殷切希望。而民法的功能正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领域,民法的主要作用是弥补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及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而刑法的主要功效在于惩罚与矫正犯罪人,二者的作用形成互补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235条《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和相关司法解释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的规定,检察院就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同时,可以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机制以环境犯罪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为补充,填补了刑罚处罚无法恢复被污染环境的漏洞,能够及时保护生态环境,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如前所述,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行为人虽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法益并不会自动修复,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惩罚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系统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了完善治理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司法保障和救济手段,在追究相关行为人刑事责任时,也应一并追究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所涉及的民事侵权责任刘子阳,张守坤:《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在行动》,《检察日报》,2020年8月20日。。追究行为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民事责任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合理地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在传统犯罪中,受害人通常对危害行为的内容、损害程度、发生过程具有明确认识,对危害结果的内容也具有直观感受。但是,污染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累积性、隐蔽性,侵害范围广,受害人众多,且较难确定污染环境犯罪的发生原因、侵害事实与损害的内容、程度等。这就导致污染环境犯罪的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求偿时存在巨大困难。此外,鉴于污染环境犯罪的上述特征,单纯使用刑罚的报应与矫治模式难以达到对抗犯罪的效果,需要兼纳民事赔偿与修复等手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之功效。尽管《民法典》第1235条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处理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当中,如何鉴定生态环境受损害的程度并进而确定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费用,仍存在很大困难。根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之规定,生态环境损害不仅包括对生物和环境要素的直接损害,也包括生态环境系统整体功能的退化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对前者损害的鉴定相对容易,可以通过观察或者测量得出结论;但是对后者损害的鉴定则较为困难,因为生态环境系统功能退化通常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损害,难以通过观察或者测量得出结论吕忠梅,窦海阳:《以“生态恢复论”重构环境侵权救济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因此,完善污染环境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机制的关键问题便是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准确鉴定。
根据《民法典》第1235条之规定,对于环境犯罪提起公益诉讼,既可以独立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者无疑更为妥当,更有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原因在于,在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原告的调查权优先,导致相关证据获取困难。而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中涉及的刑事证据可以用来证明附带的民事诉讼中的民事侵权行为事实,这就可以显著减少证明民事侵权行为事实所需要的证据核实与调查工作刘加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通过综合运用刑事法律对污染环境行为的制裁与民事法律对被污染环境的事后修复作用,可以增强环境保护法治系统对行为人的震慑作用,且能够充分提高诉讼效率,遏制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有效实现对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治理,有力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
在刑民一体化视野下,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机制不能仅停留在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上,而应同时借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救济与优化保护。
Abstract:“Criminal Law Amendment (8) ”and“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have amended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reflecting tha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 to prevention in advance. The legal interest orientation, behavior structure and culpability for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are not purely theoretical issues, but also affect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the ecological legal interest of human standard, the form of the crime is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and the subjective fault is intentional. The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needs criminal law mechanism, and other legal mechanisms are part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in which the related elements have both functional distinction and value connection. Administrative law emphasizes the risk defense or risk control in advance, while the function of civil law is to fill the damage afterwards. To construct the crimi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we ne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mechanism and administrative law, civil law and other department law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law and order,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department laws, so as to form a leg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with clear hierarchy, orderly severity, moderate severity and remarkable effect.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governance concept;ecological legal interests;connection between punishment and execution; co-governance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責任编校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