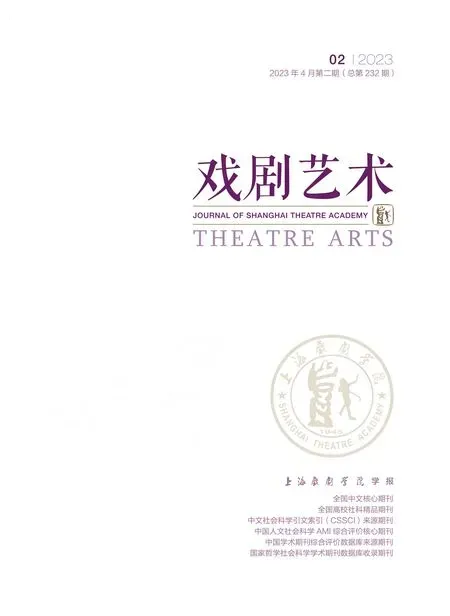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中音乐的戏剧功能
2023-04-26郑剑南
郑剑南
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讲述了美国开国元勋及首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跌宕起伏的一生,曾一举斩获托尼奖11项大奖。此剧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其作曲者兼词作者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1)《在高地》(In The Heights, 2007)是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作词作曲林-曼努尔·米兰达创作于《汉密尔顿》之前的外百老汇成功之作。《在高地》首演后,米兰达曾向时任纽约杂志戏剧评论的杰瑞米·麦克卡特强调,“我们多次忽视了嘻哈音乐对于剧场的重要性……用嘻哈音乐讲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嘻哈音乐无关,只是将它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并非内容”。See Lin-Manuel Miranda and Jeremy McCarter, Hamilton the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New York City: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 133.2009年5月12日白宫的演出便是米兰达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次的白宫演出,米兰达只演唱了一首开场曲。历经七年的苦心创作,《汉密尔顿》于2015年8月6日在百老汇首演。创造性地运用美国少数民族嘻哈风格音乐(2)嘻哈音乐也译“说唱音乐”,具有随着伴奏、带着韵律吟诵(即饶舌说唱)的音乐风格,最早要追溯到1970年代的美国。它流行于贫民区的青年中,其中大多是纽约的黑人。所用的伴奏多产生于音乐取样手段,亦被称作“嘻哈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最早的嘻哈音乐由主流社会边缘的青少年组织为地下音乐形式,后被一些唱片公司发现并包装推广,形成了一种主流音乐文化。该文化包含了饶舌、控盘、霹雳舞、涂鸦等几种街头艺术。参见编辑委员会中方委员钱伟长、周有光等,美方委员吉布尼(Frank B. Gibney)、索乐文(Richard H. Soloman)等: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十五版),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90页。贯穿全剧,开拓了音乐剧中较强叙事性、节奏感及感染力的词曲糅合创作模式,在音乐的戏剧功能上有很大的突破。本文将从“音乐动机贯穿故事不同发展阶段”“‘说唱’中的叙事性及不同节奏韵律推动情节发展”“合唱烘托戏剧氛围”“戏剧性歌曲建立戏剧高潮或低谷”这几个部分对《汉密尔顿》一剧进行分析。
一、 音乐动机贯穿故事不同发展阶段
1. 音乐动机明确故事情节发展脉络
《汉密尔顿》全剧共51首乐曲(包括返场音乐),是一部歌曲贯穿式的音乐剧形式(Song-through Musical)。(3)Lin-Manuel Miranda and Jeremy McCarter, Hamilton the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New York City: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 10.曾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先生在书中提出:“戏剧结构,可分为头、身、尾三个部分,也可以分成起(开端)、承(发展)、转(高潮)和合(结束)四个阶段。”(4)顾仲彝: 《编剧理论与技巧》,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0页。通唱音乐剧《汉密尔顿》具有叙事音乐剧的特性。叙事音乐剧(Book Musical)的核心是剧本(Book),它采用的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单线条叙事方式,优势在于可以简化真实世界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与复杂性,隐藏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在有限的戏剧时间内交代出一个有始有终、相对完整的叙事情节。(5)罗薇: 《斯蒂芬·桑坦概念音乐剧的戏剧特征》,《戏剧》,2013年第3期。
作为一部通唱音乐剧,《汉密尔顿》与史诗型音乐剧《悲惨世界》同样采取一唱到底的结构方式,全剧没有一句对白,上下两幕共由49首曲目(6)全剧共51首乐曲,其中49首含有歌词。组成,无论是人物独白、对话,还是历史文献原文,都通过歌曲形式呈现出来。而作为一部有接近24 000个单词的历史题材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信息量远大于《理查二世》(RichardII)等莎士比亚历史剧。(7)李晓昀、李晓红: 《嘻哈、移民与多元文化——音乐剧〈汉密尔顿〉的“革命性”与“美国梦”解读》,《戏剧艺术》,2020年第2期。
全剧中音乐动机(Music Motif)(8)“音乐动机”是音乐结构中的最小单位,通常表现为一串特性化的音列组合或标志性的节奏片段,并由此构建整部音乐作品或部分音乐主题的基本音乐元素,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之门”音乐动机。参见罗薇: 《斯蒂芬·桑坦概念音乐剧的戏剧特征》。曾四次出现,并被巧妙地运用于故事的不同阶段(见表1):

表1
纵观全剧,第1首开场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至第8首《得力助手》(RightHandMan)【起】以八分音符三连音结合八分音符及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为动机贯穿全剧,将全剧划分为四部分。开场曲由独自站在追光下的带着悔恨的伯尔及劳伦斯、杰佛森、麦迪森、伊丽莎白(伊莱莎)及姐姐安洁莉卡、佩吉、华盛顿、穆里根、拉法耶、玛莉亚及汉密尔顿本人相继出现,运用大量说唱(Rap)及个别带有旋律的演唱讲述自己的境遇,以倒叙且平铺直叙的方式总结汉密尔顿与相关人物的生平及其生命终结的原因,下文从较具代表性的伯尔、汉密尔顿及劳伦斯的说唱词句分析其叙事特点。歌词部分译文如下:
伯尔:一个野种、孤儿,妓女和苏格兰人的儿子是如何在加勒比海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降生的?生于贫困潦倒、卑鄙肮脏之所,长大后却成为一个英雄和学者?……我就是那个该死的开枪打了他的傻瓜。(9)本文中歌词翻译均出自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19级大三上学期表演汇报剧目《汉密尔顿》,翻译: 张影伦。
劳伦斯:十美元上的国父没有父亲,却走得比别人更远。通过更加努力的工作,变得更聪明,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人。14岁之前,就被委以重任,负责贸易文书……我为他而死。
汉密尔顿:我还有无数的事情没做,但是你们等着瞧吧,你们等着瞧!
(合唱)亚历克斯(Alex,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的母亲却撒手人寰……看啊,他正站在船头,前往新的土地。在纽约你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伊莱莎:他十岁时父亲就彻底离家出走,留下他们债台高筑,两年后,亚历克斯和母亲卧床不起,半死不活,坐以待毙,散发着阵阵恶臭……我深爱过他。
从伯尔、劳伦斯及伊莱莎的说唱(Rap)唱词中不仅可以获取汉密尔顿家庭背景、个人奋斗的经历及所作贡献的具体信息,而且在歌曲结尾段,恰到好处地用一句话“我深爱过他”总结伊莱莎自己与汉密尔顿的人物关系;在众人合唱中提到,人人口中的“在纽约崭露头角”(10)英文原句“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其中“new man”指家族中第一位进入管理决策层的人物。,恰蕴含着“美国梦”的意味。而汉密尔顿唱段中多次出现“等待”(Wait)一词,又与伯尔在剧中第13首《伺机等待》(WaitforIt)交相呼应。
另外三首运用相同音乐动机做引子的唱段,皆由伯尔独唱开场,伯尔的唱词中高度凝炼了整部剧中诸如野心、冲动、爱恨等错综复杂的人性。其中,第9首《冬之舞会》(Winter’sBall)【承】的音乐动机巧妙运用较开场曲动机高半音、以同节奏型的移调方式,整体音高有了提升,在更为明亮音色的变化中糅合了更为激动人心的舞会场面。在这次极为重要的舞会中,汉密尔顿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伊莱莎。而此时伯尔的唱段与开场曲唱词功能不同,口吻中带着不解与蔑视,译文如下:
一个野种,一个妓女的孤儿,是怎么就不断前进崭露头角的?
它起到推动剧情发展及故事层次上的递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开场曲中所有角色均以第一人称出现。谭君强教授指出:“人物叙述者与非人物叙事者的区分和故事内叙述者与故事外叙述者的区分有所关联。人物叙述者从其名称可以看出,既作为叙述者,同样又是人物。叙述者处于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层次,并且是这个故事层次中的一个人物。”(11)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1页。此经典叙事手法的运用,赋予本剧中重要人物伯尔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双重身份。言简意赅却承载较大信息量、厘清各人物间关系的同时,清晰地概括故事发展脉络及主人公的结局。在2009年白宫演出中,米兰达仅凭此曲即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剧的赏识及观众的肯定。
第18首《枪与舰》(GunsAndShips)【转】处的音乐动机与开场曲调性、动机以极强力度呈现,进而衔接伯尔独白式说唱。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伯尔形容汉密尔顿身世的名词不再是“孤儿”(Orphan),而是“贱民”(Ragtag)。从中性词到贬义词这一词性的改变,表现出伯尔心态上极度的不平衡与嫉妒之情,标志着他由友变敌的角色转变。“移民”(Immigrant)一词的反复强调,也从侧面显示出当时美国社会对身份地位的看重。另外,作者还借伯尔之口讲述汉密尔顿在短短的时间内给美国政局带来的巨大变化。伯尔说唱道:
一个你所认识和喜爱的移民,他无畏地加入我们,他带给英国人无尽的烦恼,让我们热烈欢迎美国人最爱的法国盟友。
第37首《亚当政府》(TheAdamsAdministration)【合】,此处音乐动机及调性与第1首开场曲首尾呼应,连接绵密的八分音符与切分音乐队伴奏音型,彰显紧凑戏剧节奏。此时伯尔歌词中,取代谩骂之辞的则是在列举汉密尔顿的丰功伟绩、称其为“海岸警卫队及纽约邮局创始人”(Creator of the Coast Guard, Founder of the New York Post)之后,却引发如何诋毁汉密尔顿的名声(destroy his reputation)的念头。由此表现出伯尔由妒生恨,人格逐渐扭曲的特点,也为故事人物性格塑造的多面性与丰满性提供有力的证据。
总而言之,音乐剧就是以文学、音乐、戏剧和舞蹈为载体,为观众讲故事。戏剧文本和音乐文本是音乐剧的灵魂所在,音乐不仅参与叙事,且在表现剧情的同时传递重要信息,在连续叙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12)温馨: 《跨媒介叙事: 当代百老汇音乐剧的叙事策略——以音乐剧〈圣诞颂歌〉为例》,《戏剧艺术》,2021年第2期。嘻哈音乐中说唱的叙事性功能特点在此剧中得到充分体现。
2. 灵活的曲式紧密连接音乐与戏剧关系
著名歌剧、音乐剧专家居其宏教授提出:“在音乐剧唱段中,分节歌形式,单段体、单二部曲式、单三部曲式等小型曲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最普遍常用的曲式结构。这样的例子在欧美音乐剧经典剧目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13)居其宏: 《如歌抒咏 直指人心——音乐剧音乐创作散论》,《黄钟》,2001年第4期。
米兰达在《汉密尔顿》中则不落俗套地将全剧最温柔的一曲献给《亲爱的西尔多莎》(DearTheodosia)(西尔多莎是伯尔的女儿)。在米兰达与麦克卡特合著的书中提到,此曲在创作时他与妻子领养了一只流浪狗,并在不久之后又有了他们的结晶。米兰达的父爱溢于言表,全部倾注于此曲的字里行间。(14)Lin-Manuel Miranda and Jeremy McCarter: Hamilton the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New York City: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 128.此曲分为四小段的单段体曲式,结合摇篮曲风格,加上固定伴奏音型,音乐的韵律感似持续摇晃的摇篮,将处于不同空间的伯尔与汉密尔顿先后的独唱旋律衬托得更为温暖纯真。本曲最后以二重唱的方式结尾,放下身段,抛去权力与野心,仅余浓浓的父爱,展现了两位政治人物刚中带柔、立体多面的性格。另外,此曲还为汉密尔顿因儿子菲利普决斗后中枪而亡所产生的极度悲痛情绪做了反衬。(见表2)
本剧最后一首歌《谁生,谁死,谁将你的故事传颂?》(WhoLives,WhoDies,WhoTellsYourStory?)是剧中较少出现说唱段落的歌曲。作曲家以肃穆、古典的旋律及和声写作手法结束全剧。此曲运用短小的“前奏+A+B+C+D+E+F+结束段”的多段式点题,以歌词“他们会讲述你的故事吗?”将各段落串联。全曲由伊莱莎采用第一人称演唱,叙述汉密尔顿死后,她与姐姐安洁莉卡如何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汉密尔顿,将他的精神及功绩代代相传。
伊莱莎的部分歌词译文如下:
我让我自己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不再浪费时间以泪洗面。我又活了50年,我采访了每一个和你并肩战斗过的士兵;我试图弄懂你那成千上万页的文字,你写得真快,好似你已时日无多;安洁莉卡是我的依靠,我们讲述你的故事……我为华盛顿纪念碑筹款……我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我能告诉你,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吗?我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我帮助抚养了几百个孩子,我看着他们长大,在他们的眼里我看见了你。
伊莱莎没有将自己沉浸在失去儿子与丈夫的悲痛之中。她振作精神,与姐姐一起将汉密尔顿的精神发扬光大,并将所有的爱献给了她所建立的孤儿院的孩子们。她呼吁废除奴隶制,为华盛顿纪念碑募捐,整理汉密尔顿的遗作,这从侧面展现了当时女性的觉醒,她们不仅开始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且努力为创造更有价值的生活与更美好的世界而做出自己的贡献。《汉密尔顿》一剧提倡的为家庭、为祖国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在本曲中再次得到更为深刻的体现。
二、 “说唱”中的唱词特点与韵律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西方系统且严格的记谱法,将节奏严谨准确地呈于乐谱之上。音乐剧记谱中,速度、节奏、力度与歌词紧密连接,将缜密的演唱表演信息精准地传达于演员(或音乐剧学习者)。《汉密尔顿》以嘻哈音乐为体,深度挖掘嘻哈音乐中适于音乐剧的特性,将多功能合唱中节奏音韵相结合的韵律感、氛围感,以及朗朗上口、生动且具有叙事功能的语言特性恰到好处地嫁接其中。
在音乐传统中,“‘唱’是对‘说’的否定——一方面,它否定了‘说’相对贫乏的言情表意能力,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诗序》)”。(15)王逸群: 《嘻哈音乐的世界感: 音乐形式中的反讽意蕴》,《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1期。此观点与《汉密尔顿》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汉密尔顿》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说”与“唱”天衣无缝地融于一部作品中。作曲家米兰达在个人采访中曾说,《汉密尔顿》歌词的细节运用受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及音乐剧泰斗桑德海姆《拜访森林》等作品的结构及语音的启发。(16)Suzy Evans, How “Hamilton” Found Its Groove, https: //www.americantheatre.org/2015/07/27/how-hamilton-found-its-groove/.在多首气势恢宏的唱段中,作曲家米兰达将唱与说中的情绪能量层层叠加,将人声与电音进行有益结合,震撼的音响效果烘托了恢宏场面的气势。王逸群教授曾这样描述嘻哈音乐:“在快速流动的说唱中,词语越密集,人声所积累的动能就越大,而押韵往往也就越多。每个乐句中,每次押韵都是对声音动能的一次缓冲,而随着音乐整体的推进,多个乐句中云集相应的韵词构成了阻隔这种动势的更为强力的屏障。尤其是乐句尾部的韵词,它们往往被歌手有意识地突显出来,小规模地释放一部分能量,又与下一个乐句中呼啸而来的韵词联手完成新一轮的封锁。”(17)王逸群: 《嘻哈音乐的世界感: 音乐形式中的反讽意蕴》。
3) 4种工况中,只有工况3时立杆有一处Von Mises应力值稍微超过6061-T6的屈服强度,属于极个别点,可认为立杆满足施工设计要求。施工平台其余各部件4种工况下Von Mises应力值均小于6061-T6的屈服强度,满足施工设计要求。
在《汉密尔顿》里,既有纯押韵,也有不完全押韵的片段,这就是嘻哈音乐的特点。在嘻哈音乐中,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押韵方式。(18)王逸群: 《嘻哈音乐的世界感: 音乐形式中的反讽意蕴》。以第三首《我的机遇》(MyShot)为例,句尾音的押韵在切分节奏及小连线的推动下,将本在弱音及弱拍中的句尾词尾音“ly /liː/” 延长并强调,如“无休止地”(endlessly)、“必须地”(essentially)、“不屈不挠地”(relentlessly),描写英国殖民者不依不饶、无情地征税,致使殖民地民不聊生,民怨持续攀升,殖民地的人民强烈地渴望从英国独立出来。又如,“狂欢”(pree)、“非自由”(ain’t free)、“一个世纪”(a century)三个同样以元音“/iː/”为韵脚(第三个韵脚为刻意延长并强调),反映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正挥霍无度、臆想殖民时代永恒之时,殖民地的人民却在为自己在那个世纪结束殖民统治而奋起反击。
首尾押韵的排比句句型烘托了气势,提升了情节发展的节奏速度及紧张度。以第24首《从不停歇》(Non-Stop)中的唱段片段为例,“你究竟在等什么?”(“What are you waiting for?”)“是什么拖住了你?”(“What do you stall for?”)“这一切是为了什么?”(“What was it all for?”)以“什么”(What)为起始押韵词,且句型相同,以“for”为句尾押韵,且“for”一词较其他词时值更长,充分展现嘻哈音乐中节奏、重拍拍点的灵活性,也将疑问句中汉密尔顿坚定的信念、迫切渴望改变的心境展露无遗。
美国音乐评论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曾在《饶舌: 百老汇的新爵士?》一文中提出:“‘唱’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最自然地表达‘说’。‘说’不仅感觉更为自然,而且更贴近人们每天生活所用的语言。”(19)John Mcwhorter, Rap: Broadway’s New Jazz? https: //www.americantheatre.org/2016/03/18/rap-broadways-new-jazz/.故而,《汉密尔顿》的成功与音乐形式及表达的正确选择息息相关。嘻哈音乐语言中的富于节奏感、多层次、擅叙事特点,在此剧中得到充分发挥,这对于人们正视嘻哈音乐,重视代表不同民族特性的音乐风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合唱烘托戏剧气氛
《汉密尔顿》中具有强烈氛围感的合唱片段蕴含着不同的声音色彩与能量,这些合唱片段运用大量音响,对比、烘托、营造激烈的或庄严肃穆的气氛,并与剧中的说唱片段交相呼应,展现米兰达音乐剧作曲技巧的同时,也将音乐与戏剧紧密相连,达到戏中有乐、乐中有戏之境界。
合唱中不仅有角色,也有态度——或肯定,或否定,或主观,或客观。本剧采用不定式聚焦与集体式聚焦(20)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87页。两种写作手法,融入合唱角色及声部的变化,将音乐与叙事结合。《汉密尔顿》中,持不同理念的民众以合唱为媒介,加上各抒己见的集体式聚焦,将合唱与叙事巧妙地结合,更具戏剧张力。
在第30首《决策现场》(TheRoomWhereItHappens)中, 合唱如蛊惑人心的恶魔,从合唱进入(GROUP ENTER(21)此乃排练乐谱中的唱段标记。)段落开始的二声部,至本曲第2段段落中的四声部,再至曲谱中第65小节处与伯尔同时进行唱词相同的合唱段落,从声部递增的布局中逐渐增强音量,犹如煽动伯尔心中愤愤不平的小火苗,逐渐跳荡张扬起来。其中,四次连续快速的唱词“伯尔,你想要什么?”(“What do you want, Burr?”)一步步逼迫、鼓动着伯尔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与此同时,音乐速度以“稍慢—一点一点渐快—回到原来速度”的起伏,与音乐节奏中掌控伯尔心理变化的“犹豫不决—激烈内心挣扎—下定决心”之戏剧节奏相辅相成。
在合唱中,演员还能化身为投票的民众。以第46首《1800年的大选》(TheElectionof1800)为例,声部分为女声男声轮唱、重唱唱段,展示当时美国民众对选举的举棋不定:“杰佛森还是伯尔?我知道选谁都不咋地。”随后这些民众选择倾听汉密尔顿的建议:“亲爱的汉密尔顿先生,杰佛森还是伯尔?”汉密尔顿经过深思熟虑后回答:“我投杰佛森一票。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杰佛森的政见。我们好像经历过,差不多75次敌对。但是归根结底,杰佛森有自己的信仰。伯尔完全没有。”民众仔细地倾听着汉密尔顿的建议,且不时给予附和。此处合唱队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从侧面表明当时选民听从且信任汉密尔顿,将选票投给了杰佛森,导致伯尔最终的惨败。这次选举成为伯尔选择与汉密尔顿决斗并残忍枪杀他的导火索。
合唱对语言层次的清晰化起到了辅助的作用。第49首《海纳百川的世界》(TheWorldWasWideEnough)中,合唱唱词中出现了有固定韵律感的序列性语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清晰地列举了不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决斗注意事项。这开拓了合唱部分的功能,将合唱以“说明书”式的解析方法植入独唱中,打破固有独唱节奏的同时,加入短小精悍的和声,在丰富音乐之时也增添了枯燥乏味的序列性语言的趣味性。
合唱语气烘托了气氛,合唱中能妙用拟声词。在《枪与舰》(GunsandShips)中,合唱演员唱出弹药的爆炸声,与电子音效结合,齐唱“砰!”(“Boom!”),体现战争中人类血肉之躯的渺小和牺牲精神的伟大,以“声”配合编舞动作及舞美效果,达到视觉及听觉上的多重刺激。在歌曲《无法自拔》(Helpless)中,拟声词“砰”则代表了伊莱莎心动的声音。“砰”(“Boom”)的一词多用,奇妙地展现在不同音乐语境中,同样的语言可表达完全相反的意味。
合唱中的语气词有助于亮明民众的不同政治理念、丰富唱段的语言风格。在第24首《从不停歇》(Non-Stop)中,多次出现女声声部演唱的带装饰的“嘿”(Hey),点缀于紧张气氛之中,将连续八分音符的韵律打破。“嘿!将会过时”(“Going out of style, Hey!”)以肯定句式与男声声部的疑问句“为什么你总在奋笔疾书好似时日无多?”(“Why do you write like going out of style?”)齐唱,好似一问一答,强调汉密尔顿陷入了焦虑——他快马加鞭地写作,唯恐自己的思想马上就过时。本曲合唱声部的两次向上滑音、两拍拖长的“嗷——”(Awwww!),以一个语气词点明此时美国民众的鲜明态度,他们开始厌恶、反对汉密尔顿,更倾向于站在伯尔一边。
合唱营造了凝重的气氛。在本剧最后两首歌曲中,作曲家大量运用西方古典和声四部、六部写作手法,以极简的长元音“啊——”(Aaaah)营造以下一系列气氛: 汉密尔顿死后,它反映了伊莱莎及民众的悲痛之情,也衬托了伯尔枪口瞄准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的枪口对准天空后,伯尔无比悔恨的内心活动。最后一首中,由合唱队重复演唱华盛顿说过的那句话:“谁生,谁死,谁将你的故事传颂?”(“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伊莱莎与世人都将这句话牢记于心,在汉密尔顿死后,仍坚定信念,继承他的奋斗精神。
总之,丰富的音乐材料充实了戏剧,明确了音乐的抽象语言对戏剧表现的重要性。一部好的音乐剧将形而上的音乐及中心思想具象化,擦出音乐与戏剧新的火花。
四、 戏剧性歌曲建构戏剧高潮或低谷
傅显舟曾指出:“用戏剧性歌曲建立戏剧高潮,是音乐戏剧作曲家惯常采用的方法。戏剧性歌曲音乐语言与结构的复杂性就是戏剧内容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戏剧性歌曲可以根据戏剧高潮形成的过程来调整自己的音乐语言和结构。”(22)傅显舟: 《音乐剧歌曲研究——三部国产音乐剧歌曲分析引发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博士论文,第119页。
例如《我的机遇》(MyShot),它是一首“多功能”的戏剧性歌曲,主要以汉密尔顿的“不会错失良机”及“奋起”为主旨,是汉密尔顿的角色主题歌。本曲分为“引子—A—过渡段1—B—过渡段2—A1”三段式。所谓“多功能”,即本曲叙事上的复合功能。(见表3)

表3
这首歌曲在彰显汉密尔顿雄心壮志的基础上,依次介绍劳伦斯、拉法耶、穆里根的出场及性格特征,还引出毕业于普林斯顿的高才生伯尔对时局的看法。随着伴奏织体的逐渐密集(低音声部与高音声部节奏交错进行),唱段中弱起的切分及三连音节奏叠加,歌词中连续八次的“我不会错失良机”,将歌曲推向第一个小高潮;中间过渡段运用八度大跳演唱“哇”(Whoa),采用较为舒缓的节奏,转换戏剧气氛,继而进入B段(奋起),“奋起”(Rise up)规律地出现在每小节的第一拍重拍,对其着重强调,同样运用紧密重复叠加出现的写作手法,将本曲推向第二个小高潮;突然的音量变弱,速度放慢,预示着第二个过渡段的进入;速度逐渐加快,音量逐渐变强,合唱声部音色逐渐厚重,以“奋起”“不会错失良机”及“过渡段1”三种音乐元素重叠交错出现的方式,推向本曲最有力的戏剧高潮。
伊莱莎定情之歌《无法自拔》(Helpless)中,曲式为加小引子的四段式。以略带趣味性的演唱声部弱拍、伴奏声部正拍的节奏型交错做引子,男生女生错开一小节的群像出场富有动感与节奏韵律感,形象地代表了舞会中先后而至的男士与女士队伍,整体音乐风格清新轻快,体现了伊莱莎初识汉密尔顿时的青涩,以及两人一见钟情后的幸福之感。(见表4)

表4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曲的叙事中,B段以第一周、第二周为清晰的时间线讲述一见倾心后故事的发展,从写信沟通、加深两人情感到征得岳父同意后求婚。结尾段巧妙地运用《结婚进行曲》主题,以音乐引入剧中婚礼场面,女声合唱“在纽约,你会成为有地位的人”,预示着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改变。一首时间叙事节奏紧凑的《无法自拔》(Helpless),不仅表现了汉密尔顿与伊莱莎从相识、相知直至步入婚姻殿堂的过程,也将汉密尔顿与斯盖勒家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赋予这首情歌多重的意义,这是描写男女主人公情感线上的一次戏剧高潮。
悲剧性歌曲《肃静的城市》(It’sQuietUptown)是全剧的低谷,刻画汉密尔顿夫妇丧子后无比悲痛的内心世界。全曲以“引子+A+B+C+D+A1+结束段”多段式曲式展开,B段旋律多次出现在D段与结束段中,从第三人称视角描述汉密尔顿夫妇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在此唱段中,伊莱莎极少出现,从戏剧情节上更为反衬出她难以名状的悲痛。本曲伴奏织体运用单音重复十六分音符下行的旋律加八分音符分解和弦两种写作手法,十六分音符如眼泪般滑落,八分音符缓慢且安静,描绘了主人公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行走的画面;四小节的引子通过寥寥数音便勾勒出悲伤的画面,乃本曲的点睛之笔。(见表5)
最后,傅显舟还提出:“我们区分普通歌曲和音乐戏剧歌曲创作的规律的不同在于后者必须接受戏剧内容的制约。”(23)傅显舟: 《音乐剧歌曲研究——三部国产音乐剧歌曲分析引发的思考》,第121页。音乐剧音乐中的戏剧性无处不在,多样的曲式结构体现了音乐剧音乐服务于戏剧的特性,有着明确的戏剧指向性。

表5
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一大成功体现在它的音乐、节奏与人物、戏剧都有着理性与感性上的紧密联系。音乐剧中,音乐服务于戏,戏中有乐,乐中有戏,这是音乐剧音乐创作的宗旨。其多样的歌曲曲式,以嘻哈音乐为体,发挥其叙事特点,利用共同音乐动机将乐曲分成【启】【承】【转】【合】四段,利用独唱、重唱、合唱多种演唱形式将故事串联成戏剧性歌曲,巧妙运用排比、押韵、拟声词等语言写作技巧,综合地体现了艺术性、严谨性及开拓性。《汉密尔顿》中音乐戏剧功能的运用,对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与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