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偷而不能读也
2023-04-23曾颖
曾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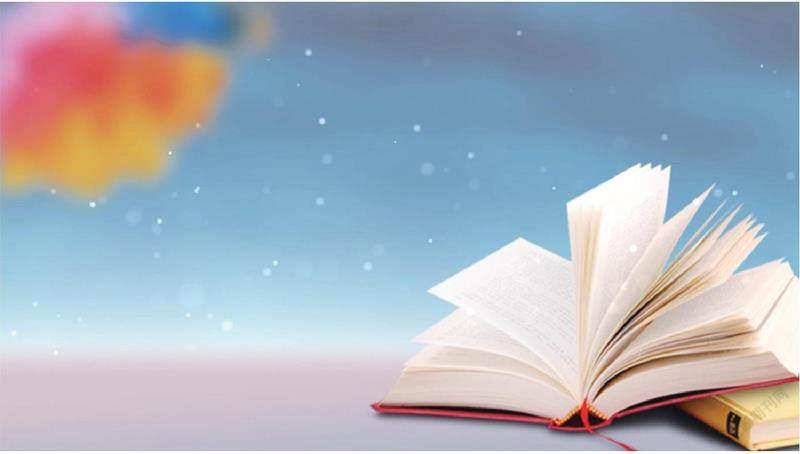
在我短暂而漫长的青春岁月里,出现得最多的一个主题词,便是“偷书”。按照前辈孔乙己先生的说法,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故而我也择雅而從之,仿他的说法,窃一回。
我不知道孔乙己的书,究竟有多少变成铜钱换了黄酒,多少用来打发寂寥漫长的日夜;但我知道,我所努力想要窃的书,没一本是打算拿去换麻糖和花生吃,而是为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的需求去窃。如果单纯是为了要换糖,我完全可以像小伙伴那样,向我家背后的铁工厂废料场下手,只需要从墙下的水沟洞里钻进去,捡两块称手的铁扔出墙,几块麻糖和花生便到手了,无须像书那样,费尽周折,而且,收废品的根本不喜欢。
那时,街面上没有网吧和游戏厅,青少年最喜欢去的就是连环画店。这些小店,通常以一分或两分不等的价格,把厚薄不均的小人书租借给孩子们看。我最初的阅读兴趣,就是在那光线并不十分充足,几块砖垫一块木板做成的长凳上养成的。满满一屋孩子密密地挤坐在一间小屋,屏神静气看书的场景,至今仍是我心中最美最温暖的画面。
但是,比起记忆的温暖,现实却是冰冷而骨感的。虽然一分两分钱的租金,现在看起来不贵,但在当年却是很具体的。那时候,米不过一毛三分多一斤,肉凭票七毛多一斤,一分钱也就是一杯爆米花,两分钱就是小半瓶醋,谁家的经济条件,敢放敞了让孩子们由着阅读兴趣去花钱读书啊?况且,一本新连环画也不过一两毛钱,这直接让人产生租不如买的不平衡感,像现在买房人的心态一样。
14岁的我,疯狂的阅读愿望与有限的图书供应量之间出现巨大的反差,这使得我不得不想出各种各样的歪点子去筹集看书的资本,而为了炫耀自己看过的书多,进而产生拥有更多书的愿望,由此开始了我的窃书生涯。
我第一个下手的目标,是邻居朱爷爷。朱爷爷是一家单位的会计,常年并不住在家中,以至于他的那座小院,有一种荒弃的感觉,檐下挂着蛛网,墙上长着杂草,自不必说,那间终年无人的小院,是周围家鼠野狗小猫和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的乐园。小时候在那里扮鬼捉迷藏,只对墙上挂着的铁剑感兴趣,稍大懂些事了,便对那黑屋子里的大书柜感起兴趣来——那里面有好东西。
朱爷爷的书,大多数是很久以前置办下的老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拍案惊奇》之类,还有《山海经》《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聊斋志异》。我凭着十几岁少年的阅读兴趣,窃过“西游”“三国”和“水浒”。我的另一位伙伴,窃得一本《芥子园画谱》,由此开始学画,最终成为一位知名的山水画家。我所窃的书,原本看后也是想放回去的,但一想着放回去还不知会进了哪家小伙伴的灶门,于是一狠心,就昧了下来。此事一直到多年后朱爷爷去世房子也拆迁改建为楼房,也没人问起。我虽然一直心存愧意,但想想那些书最终没有一直在蛛网尘灰中变为鼠虫的美食,而成为一个青春期少年的精神食粮,不禁有些释然,甚至还有一种拯救了它们的小小愉悦感。
我下手的第二家,是离家不远的建筑公司工会图书室。与朱爷爷家里的书一样,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丝毫“偷”的负罪感,倒是觉得那些被铁栅栏封锁着的书,如同被投入牢狱的老友,正等待着我的搭救一样。
为了接近那早已无人搭理的图书室,我也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首先,和门卫的儿子以及他家的狗搞好关系;接下来,做好堂弟的思想工作,因为他的身体够瘦小,可以从图书室的护窗爬进去,我可以在窗外接手,即便被抓住,别人也不会拿七八岁的他怎样。
经过周密筹划,在一个月黑风高适合偷书的夜晚,我和堂弟出动了。我们学电影里的侦察兵,都穿了黑衣,还很二地往脸上抹了锅底灰。我们从建筑公司后院的地沟里钻进去,迎面就撞到守门的大狗阿黄,看在平常给他丢馒头和挠痒痒的份上,它原谅了我们的古怪行为,摇摇尾巴自个儿玩去了。
我们从山一样的木头垛子缝隙里穿过去,很快接近了目标,堂弟不负众望,三两下爬上图书室的护窗,然后就往外递书,我凭手感,凡是塑料封皮包着的精装书,都不好看,扔在一边,匆匆忙忙抱了一堆手感尚好的,用衣服包了,凯旋。
这天夜里成功越狱的有《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战争与和平(上)》,还有《敌后武攻队》《吕梁英雄传》等,以苏联书为主,也有一些读不懂的法规和理论书,这些对于我来说,已是非常棒的收获了,那几本苏联小说让我在其后整整一个暑假里,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中。
建筑公司一直没有发现图书室有什么异样,这使我和堂弟又轻车熟路地干了几票,直至有一天,废品公司的一辆大货车开来,把图书室的书都运往了纸厂,我和堂弟才开始为自己人小力气小无法偷走更多的书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像阿里巴巴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发现的宝库被洗劫一空一样。而最令人愤怒的,是抢走这些宝物的人并不认为宝物是宝物,而拿去铺了路。
建筑公司宝库的沦陷,让我不得不把窃书的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上——父亲的书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在大衣柜下面的底柜里建起了一个小小图书柜,他时不时会把一些崭新的图书和杂志放在里面。那些新书,有很多是我做梦也想得到的,比之于我先前窃来的那些泛黄甚至发霉的旧书,它们简直就像衣着鲜亮的天使。它们中,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唐·吉诃德》《欧·亨利小说集》,杂志则有《奥秘》《少年文艺》和《读者文摘》,都是我非常想看的。
但是,父亲每次买了新书,自顾自看完,就把书小心而平整地放进衣柜下面的书箱里,然后锁上,让那些泛着书墨芬芳的尤物,与我一箱之隔,令我抓狂不已。
为了摸清父亲书箱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我可谓费尽了心思,找他借指甲剪,侦察钥匙并没在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然后,就是床上、枕边、米坛、蜂窝煤后,甚至连泡菜坛子也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我也曾想正面向父亲借,但父亲一脸吝啬和不情愿,仿佛是担心我损坏他的书,又仿佛是那其中有些书,是我现在不适合看的。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下决心一定要把它们得到。
一连很多晚上,我都静等着父亲看书,睡觉。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他放书,并把钥匙小心地放到挂蚊帐的竹筒里。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新书了,那高兴劲,至今想起还兴奋不已。
多年后,我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语文老师,一次在饭桌上聊往事,说起了童年这些趣事,我以此事来取笑父亲的吝啬,父亲听了不仅不生气,而且很开心地笑了,说:“傻孩子,如果我不那样坚壁清野神秘兮兮,你会那么快那么认真地读完那么多优秀的外国经典?那些书,都是专门为你买的,而且,我藏钥匙的时候,早就知道你那小脑袋瓜在门上的窗户上盼望了好多天了,我就是为了吊吊你的胃口,让你好好珍惜那些书。不是你小子聪明,而是你爸爸太有心。”
選自《阅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