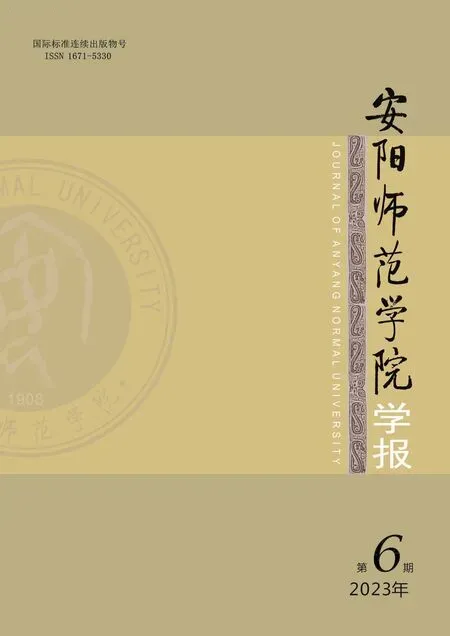叶适对神秘易学和易学迷信的批判
2023-04-22路永照
路永照
(温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 温州 325035)
叶适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的南宋大儒。永嘉学派的学者多有治易者,而对易学有系统论述的则首推叶适。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专以四卷论易,该书其他卷次也有涉及易说者,《水心别集·进卷》中另有《易》一文表达了他对易学的整体认识。叶适的易学思想独具个性,特别是他对传统易学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怀疑部分成说的可靠性,拒绝神秘易学,抨击易学迷信,对于推进易学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适反思整个易学发展的历史,认为易本身是古人对生活经验所得进行高度概括的结果。然而,其一旦成为经学典籍,则生机不在,且象数、卜筮之学假其为说,于是神秘气氛和鬼神迷信借以流行,遂成为无用乃至有害之学。叶适在《水心别集》中写道:“书之未备也,易存乎道,见道者足以为易。书之既备也,易存乎书,天下即其书而求之,书备而易始穷矣。测之以象数,别之以筮占,离析其卦爻而杂之以事物之故,辨智几殚而不得其毫芒,于是阴阳、律例、曲学小数,时日下俚之说,与夫素隐行怪、窥测异端、恢诡不伦之士,埋伏于山林草野之间者,又皆自讬于易。故后世以易为幽远难通之书,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穷诘,而无以为用于天下。”[1](P685-696)在此认识基础上,叶适对《周易》产生的历史、易学中的基本理念和易学的应用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对《周易》三古来源之说的批判
对于易学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一说法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为《系辞》等《易传》作品所接受,最终完全成型于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该文载:“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2](P1353)这段文字引述《系辞》,肯定了伏羲画卦、文王发展易经以至孔子作传的易学演进线索。这一说法把易学看成是不断发展的学说,有随着时代被加工的过程,且观取说否定了所谓“河出图、洛出书”的神授观点。但该说并非学术考察的结果,而是崇古风气蔓延的产物。“三圣”“三古”之说使得易学本身被赋予神圣性,有无上权威,同时也无法完全摆脱神学气氛。
首先,从学术态度上,叶适以理性认知的精神反对易学生成的神秘主义解说,认为伏羲画卦、文王作易的说法“神于野而诞于朴,非学者所宜述”[3](P39)。对于易之产生,他认为《易传》本身的说法就自相矛盾,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传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远或近,不能自必其时也,皆以意言之而已。”[3](P49)即所谓周易为古圣所做之说难以统一,只是好事者根据己意信口而言。战国时期,儒家崇尧舜,墨家崇大禹,道家崇黄帝,为易者遂拉伏羲氏为先,实质上都是崇古之风作祟的结果。学者对其他学派的崇古之说,往往能理性看待,而对周易伏羲之说则欣然接受,这需要引人思考。这里面既有汉易家不加分别,使之成为经学内容的影响,也有研易者意识深处对圣学权威臣服的因素。
其次,叶适考察《周礼》所记,并研究易卦成立的基本道理,认为先有伏羲八卦,而后文王演易成六十四卦之说并不可靠。叶适据《周礼·春官》有太卜掌三易之说指出:“按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3](P739)既然并非先有八卦,而后又演绎发展为六十四卦,那怎么理解八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呢?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开篇即提出:“其为三,阳也,天也,此易之始画,(自注:本一而三者,非三则无以为八也。)其有阴,则地也。理未有不对立者也,阳之一雷二水三山,阴之一风二火三泽,此卦也;其为六也,阳则乾、震、坎、艮,阴则坤、兑、离、巽,此义也。以卦则三足矣,以义必六,而交错往来所以行于事物也。学者观其一不观其二,此易道所以难明也。”[3](P1)也就是说,古人发现了事物以对立性而存在的基本规律,以之延伸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就有了以卦表自然界大物象的做法,阳性的乾、震、坎、艮代表天、雷、水、山,阴性的坤、兑、离、巽代表地、泽、风、火。如此,本来八卦就够了,但八卦的功能在于取象,而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作用,则需要八卦互相叠加为六十四卦方可。即有八卦,自然需六十四卦,若把六十四卦视为别于八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观其一不观其二”。
最后,叶适认为,易是来自先民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是对生存规律的深入把握,而并非是有一个先天玄上的易道在决定着一切事物的存在样态,“天地固准易,而易非准天地也”[3](P42)“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1](P695)。基于永嘉之学对物本身价值的肯定,叶适认为易道不能脱离物的实际而产生,它是从现实之物概括出来的,通过观物归类,提取物的性质即为所谓的“义”。基本易象得以成立,物本身也就隐退了,这就是“取物以配义,义立而物隐”[3](P42)。从易卦创生而言,八卦就是八种事物,两两相对,相互作用,人们对其存在和联系的规律的提取就成为义理,“圣人”的作用是肯定规律、讲清规律。叶适撰《易》一文说:“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则取配之,后有圣人焉,推而明之。”[1](P696)在叶适看来,“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3](P46),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的产生本身并不神秘,也不存在玄上的易道,卦画、易理皆来自对实际生存条件的观察和抽象。
从源头上分析《易经》之产生,剥离其与伏羲、文王的关系,杜绝了易学滑向神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厘正《易传》与孔子的关系,杜绝易学成为圣学。作为儒家学者,这一点不容易做到,这不仅在南宋,整个儒学史上的学者很少有人会质疑孔子作“十翼”的。北宋时,欧阳修举《易传》多有自相矛盾之处,说明《易传》非一人之作,但缺乏细致论述。叶适明确指出,《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文曲为解说“皆非易之正也”[3](P1),特别是《说卦》等以乾坤为父母、其余六卦为男女等说法都属于结合卜筮验辞而生的虚合之文,而“非孔氏之书所道也”[3](P40)。
叶适认为孔子虽“述而不作”,但确实独于易有所著述,而孔子作易则限于《彖传》《象传》。不过,传本《周易》以及《彖》《象》与《系辞》等逞于辞、夸于神的作品合编,造成了易道与孔学的不彰。《习学记言序目》说:“自有易以来,说者不胜其多,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孔子之学,无所作也,而于易独有成书,盖其忧患之者至矣。不幸而与《大传》以下并行,学者于孔氏无所得,惟《大传》以下之为信。虽非昔之所谓淫诬怪幻者,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3](P39)
叶适之所以主张《彖》《象》乃孔子本人所作,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二传不尚虚辞,讲求君子之道,即彰显人文精神,文简而切,与《论语》中孔子谈话的风格相类。叶适说:“《彖》《象》辞意劲厉,截然着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颜、曾而下,迄于子思、孟子,所名义理,万端千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学者诚有志于道,以是为经,而他书特纬之焉可也。”[3](P35)也就是说,即使子思、孟子之文,也有泛而无当之辞,但《彖》《象》意思明确直截,切入宗旨,当属孔子所为。除了言辞特色,叶适推论《彖》《象》为孔子所为的另一个证据是二传不以象数为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论《毛诗》时说:“古卜筮家皆用其所自为繇,国各有占,人自立说,而象数之学胜,道益以茫昧难明,孔子将以义理黜之,故别为《彖》《象》,专本中正,不用象数,所以合文王周公之本心,盖一家之学而天下从之,固非删定诗书之比也。”[3](P80)当然,归《彖》《象》于孔子只是叶适从二传言辞特点进行的推论,并无学术史料证据的支持。二传是否确为孔子所作,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重点在于叶适由此否定了神圣化“十翼”的观点,是杜绝借《易传》之言行术数之事的努力。
《序卦》往往是治易学者对于天道规律进行曲折解说的凭据,也是理学家铺陈天理、道学的资源,“对《序卦传》的重视可以说是程氏易学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亦是程氏易学由易学转出理学的关键。”[4]而在叶适看来,《序卦》为害尤大,其“按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3](P50)。因此,他认为程颐、张载虽竭力排斥老佛之学,却“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以《易大传》误之,而又自于《易》误解也”[3](P751)。理学家往往着力研究卦序的“微言大义”,比如上经以乾、坤开篇,下经以咸、恒为始,便说上经立天地男女之大理,下经倡夫唱妇随之家风。叶适认为这种观点十分幼稚,经分上下,无非是“简帙繁重,分之然也”[3](P19)。
叶适对《周易》产生的源头进行了考察,其目的正是清理神学、圣学弥漫的易学,昌明人本身把握客观规律的必要性。朱伯昆对此评论道,叶适“对《易传》的研究,就文献的考证说,比欧阳修前进一步,对近人研究《易传》的形成,同样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功利学派研究经史文献的收获之一”[5](P561)。
二、对太极、数术、河洛之说的批判
太极衍化、五行配属、河图洛书等说力图对自然演进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及事物之间互联互通的属性进行符号式反映,对于人总体上把握世界当然有意义。但在追溯事物源头时突出一个悬置的太极理念,会消解对事物具体价值探索的动力,而流行取象配数之说,反而会给占卜迷信大开方便之门。
叶适反对完全抽象意义上对形而上之道的讨论,坚持“物之所在,道则在焉”[3](P702)。自周敦颐为《太极图说》以来,把追求形而上之理归向太极之学成为宋代理学家的重要选择,与叶适同时代的朱熹即是如此。叶适认为倡导太极之说于道学无益,只会“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3](P47)。另生一个玄上的概念,究竟对于儒学有何价值,这是可以讨论的,而叶适专从易理本身拒斥太极之说。《习学记言序目》载:“‘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3](P47)在叶适看来,八卦即象八物,六十四卦即表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基本推动力来自乾阳之运行,是不需要横生出一个“太极”来的,孔子所作之《彖》亦无“太极”之说。叶适易学本身持乾阳独运的观点,对于“太极”作为生成事物的根源自然不予接受,斥之为“文浅而义陋”。
太极学说在宋代道学家用于伦理生活法则反求形上天道的依据,具体事物之理是统一之大理之分化。然而,事物由统一性到具体性的中间环节始终是一理论难题,即一个无分的存在是如何被赋予具体性质的。《系辞》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6](P245)叶适认为,《彖传》的释卦都是从卦本身的取象性质以及卦之间刚柔、顺逆、往来关系而论得失的,没有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等说。更进一步,叶适站在儒家立场上看所谓“无思无为”等说近乎道家、佛家之论,谓“今之言易如此,则何以责夫异端者乎”?[3](P46)
叶适反对拉天理、天道讲人的社会生活的准则,认为人之作为都是自身行动的结果。如他对无妄卦的分析就是以乾阳独运为角度展开的,认为乾为上卦时,下卦为坤、离、艮、兑、巽等,都不是吉卦,但下卦为震的无妄则不同,这是因为震为刚居内而消阴,“妄”即为阴,“无妄”即为刚居内而消阴。叶适说:“圣人欲以教天下之不为妄,则必自其刚之居内者始。近世之学,谓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则有妄,夫卦之画,孰非天者,偶震与乾合,而遂谓动以天为无妄,则他卦之妄者多矣,岂足以教人哉!且人动,则固人而已矣,又孰从而天之?不见其天而强名焉,是将自掩而为妄不可止也。”[3](P16)人的作为因果皆对应于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在天命观余絮所及之天道观影响下的学术思潮中,叶适能如此发论,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置易学神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五行、八卦、干支等表物象的符号系统进行配数,这也是哲学观念能转化为占筮工具的中间环节。叶适不认为数本为易之所有,一方面,从《彖》《象》看,“孔子系易,辞不及数”[3](P580);另一方面,易卦以义而立、因象成理,如有数,数也是从属于象或义。叶适批评扬雄的《太玄》说:“《易》之始,有义而已,义立而后数从之,今之所谓数者,非易之初也。雄见其已成,而谓为易者必先数而后义,故研精殚虑于历而后玄始成,不知数既立则义岂复有哉!”[3](P655-656)即扬雄颠倒了数与义的关系,而这种颠倒正是把易学庸俗化的表现。
叶适考察易学发展历程,认为以数解易出自刘向、刘歆父子。在《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二》中,叶适批判刘歆之治学时说:“宓牺画卦造字,虽古有其说,然考详于书,圣人之道,非待画卦而后明者也;经过之用,尧舜禹汤之所以勤劳其心力者,非因卦之次序而后立也。近自文王,易道始著,孔子尽心焉,凡三易怪异之说,象数浅末之义,黜而正之,而后始得为成书。而刘歆乃谓‘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又谓‘古者三年通一艺’,其浮妄不经如此,学者欲援是以至道,难矣哉!”[3](P316)在这里,叶适的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伏羲画卦之说,只是一种崇古传说,古代的政治并不是在易卦指导之下的,而是“勤劳心力”的结果,至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弃除了象数怪异之说而为传成书,易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但至汉代神学思想流行,易为数之说又成了天人相通的表达,成了人道伦理的理论根据,确实可惜。
河图、洛书之说出自《系辞上》,是易神授之说的代表,这一说法本身与《系辞下》的观法取象而生易之说相矛盾,自然荒诞不经。但汉代以来河洛之说被学者所重视,配属数字之说逐渐流行,宋代仍有不少学者乐于追捧,遂有陈抟传图、朱熹取之刊于所著《周易本义》篇首。细思之,河图、洛书之图应是崇古者先据河洛之说将五行、八卦等配以数字,又有好事者继之将数字图示化标识出来而成。叶适说:“使河出图而为易果在伏羲之世,则雒出书而为洪范乃在禹之时,前后悬远,何昔经而今始经纬乎?易不知有书,书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义象,九畴兼政之细者以类行,当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诸八物,安在其相表里也?”[3](P313)河图、洛书不是八卦产生的源头,反而是易学流行以后,山林之士借易而为,拉河洛之说为学,除了使基本道理更说不清,更致易于低俗,毫无意义。
叶适对于与易学相关的几个基本观念,包括太极、数理、河洛等,既从易学史考察,又从易理本身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努力导儒学进入理性与常识范畴,拒绝脱离实际的空泛之理成为思想包袱;二是力争使易学回归人文与物象本原,清理沦为术数占筮说理工具的相关概念。虽然叶适之说仍以儒学立场为论,卫孔教排佛老,但其治学精神仍有后人可资借鉴之处。
三、对卜筮迷信之说的批判
易卦之产生本与占筮行为相关,而易学之形成则与儒家学者对古易进行阐释有关。可以说,易作为一种学说为后世继承,正是儒家学者发掘其中人文精神的结果,而不是象其他占筮技法一样淹没于历史尘埃中。在这一点上,人文的与迷信的构成易本身的两种内在张力。易道昌明时,正应该是其理性思想要素得以彰显之时,卜筮迷信借易为说,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肃清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历史思想根源,也有为学者不能准确清理文化遗产的原因。
叶适认为,孔子解易,独于义理阐发,而不及占筮之类。《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载:“凡卦之辞,爻之繇,筮史所测,推数极象,比物连类,不差毫发。独孔子以为不然,故孔氏之系易,以为必如是而测之,由其中正而不以祸福利害乱其性者,此君子之所以为易也。学者既不能知,反援孔子之易同归于筮,以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后成书。嗟夫!学者之自聋瞽,无足怪者,而吾辈其转相聋瞽于人而未有已也。”[3](P88-89)也就是说,孔子为易本是排斥卜筮之言而明确人之作为的价值,但后学者反而将孔子易学亦归于占筮迷信,兹后又把它作为基本易学观念予以接受,遂使易道愈发不明。
占筮家以《系辞》“大衍之数”起卦最为“正宗”,这是因为相比摇铜钱、看时辰等方法,这种起卦之法是对天道衍化序列的模仿。根据《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6](P242)。在叶适看来,如此为卦也是不足为论之“浅事”,他说:“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数晓然而名义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挂非归非再扐能通也。然则自乾而智未济,皆已具矣,已具则必有起数,故筮人为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当某卦,某爻当变,变当之某卦’而已,此易之浅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后,今传之言若是,是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为易,无惑乎易道之不章也。又谓象三材四时,一闰再闰,愈浅末矣。”[3](P45)也就是说,所谓“大衍筮法”不是易之本具,而是易成之后,占筮者以之为材料编造出来的。卦三画成宫卦,六画成六十四卦,本是象义自然而为,并不是一画一画伸发出来的,以占卦过程仿卦之生成也只是占筮之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五行配数是术数家复杂其说的一个基本依靠,后世六爻排盘、干支八字无不是以五行纳甲等为说,其根据之源头也在《系辞》。对此,叶适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阴阳奇耦可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按《洪范》以凡举五行,鲧之所以汩陈者,谓其以土捍水尔。五行无所不在,其曰天生而地成之,是又传之所无有,而学者以异说佐之也。且使其果信,则于易之道曷损益乎!”[3](P46)在叶适看来,天、地配数只是用来说明阴阳奇偶的道理,而加以五行生克,其实即使在《易传》中也是没有的。
叶适认为,五行是古人对于生活条件,特别是五味养民的概括性认识,将其与人的德威与吉凶配合是汉代儒门学者为祸之论,“今汉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位”,因此“汉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沦坠矣”[3](P314)。
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治理条件下,各家思想互动整合,元气论兴起,思想家对天人关系既有深刻思考,又有受宗教神学气氛蔓延影响,把人与环境的统一性诉诸神学化表达,星象观念由此而生。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叶适对班固的相关学说提出了严厉批评:“按经星之传,远自尧舜,而位置州分侯国始详于周衰。然则唐虞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春秋记星异,左氏颇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至秦汉一变,诸侯权轻,专地久,星官祖述故书旧事。今班氏所志,有其变而无其应者众矣,况后世乎!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所当阙也。顾乃学之以为博,言之以为奇,以疏而意密,则学者之所慎也。”[3](P312)叶适认为,在术数范围内的所谓“天文”“地理”等都是人为对自然事物的划分,它们对人的祸福影响也只是个人想象而已,本就是不可靠的。
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一贯以明确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为己任。他在《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二》中曾言:“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3](P312)天有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对人行为的影响,这是需要敬畏的,但敬畏不是“求”,敬畏是理性看待,承认自然的力量,“求”就是精神信仰,矮化个体创造力,所以“求天”“责天”废弃的是“人道”。概言之,人的命运,还是人道为主。
叶适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易学主乾阳之说,即是对进取、创新精神的肯定。其所言“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3](P42)“‘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虽差,犹可也;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3](P47-48),叶适这些观点虽有所偏而招致不少争议和批评,然其初衷必是对人本身价值的肯定而为之的。同样,对于“物”的现实性的观照也是其思想特色,如其言“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1](P699)“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1](P614)。对于人、对于物的现实性的关注,使得叶氏之学既拒绝空泛的形而上学,又反对术数迷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
叶适易学思想独具特色,而这种特色正是来自对经学藩篱的突破。朱伯昆说:“叶适关于《周易》的论述,在易学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他依《周礼·春官》,怀疑伏羲画卦说,否认文王重卦和作卦爻辞说,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传统易学是一种突破,对近人研究《周易》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5](P576)叶适的易说是在神秘易学和易学迷信尚普遍弥漫的古代社会产生的,是一种思想反叛,对于理性开展易学研究有重要启发,对于今天科学开展古代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无神论教育也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