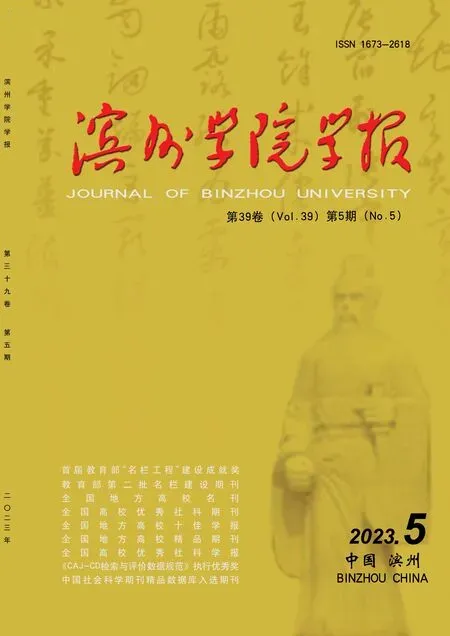时变与理论:全面抗战前后的《孙子兵法》研究
2023-04-19付耶非
付耶非
(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北京 100091)
自晚清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开启以来,随着军事体制近代化进程的加深,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传统兵学也面临着向现代军事学理论的转型。在这其中,作为中国传统兵学代表的《孙子兵法》也开始在现代军事学理论的视野下重新得到审视和研究。[1-6]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急遽紧张,一批经受过现代军事学理论洗礼的知识人,开始在时局的刺激下,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传统兵学理论加以研究(1)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大量有实战经验以及理论功底的军人,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加入,使得这一时期孙子研究蓬勃发展”。参见邵青:《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并做出了从古典兵学资源中汲取与建构中国现代军事学理论的尝试。及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人更是结合抗战实践,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对《孙子兵法》中的“久战不利”的思想进行阐发,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他们的思考对于当下重新认识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亦不无启示之处。
一、中国传统兵学的再审视
晚清以降,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在西潮的强力冲击和涤荡下,曾经历过一个“消极生存”的阶段。温晋城《孙子浅说补解》一书中指出:“从事整理经史的工作多,从事整理子集的工作少,所以坊间关于子部书籍的著作仍感贫乏,这又不能不说是周秦诸子的不幸了,周秦诸子当中,恐怕又要以孙子最为不幸。”(按:据相关资料显示,该书初版时间为1939年,由位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出版,该书封面书名由当时主持校务的代教育长陈果夫题签。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62页。)随着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引入,诸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论》等著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翻译引进,成为时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资源。[1]173-175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中国现代知识军人承续这一视角对中国传统兵学进行了新的审视和定义。这批浸淫于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知识军人对于西方的先进作战方法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更希望从中国传统兵学中得到启示,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现代军事学理论。1934年,《军事杂志》在改组启示中,就明确提出这一宏愿。“中国为世界文化最早的国家,学术之伟大,在数千年前,即已光大世界,即就军事学术而言,亦复如是!”[7]
在此过程中,如何对中国传统兵学进行定位,成为摆在民国知识军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有论者就指出,“我国军事,自古以来已占有历史光辉”,接着举例说道:“若夫蚩尤氏之构成烟雾法,与现在由发烟剂而构成之烟幕法,想像(象)其理固无不同”。[8]依其意而言,中国古代军事有着辉煌的历史,西方先进的战争技术在中国已有与其原理相似之例,这一比附透露出自晚清以来普遍流行的“西学源自中学”论的痕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无荒谬之处,但回归其立论语境,却反映出民国知识军人渴望建构与西方比肩的中国现代军事学理论的迫切心情。
中国传统兵学便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军事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总体而言,民国知识军人对中国传统兵学采取的是一种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关注要点在于古代兵学对现代军事实践的作用,而较少从版本考订、文字疏解等学术本体的角度加以考量。1929年,周筠溪即从此角度提出要对中国传统兵书进行“新评价”。他指出,“许多人都以为古代兵书是不合现代的”,认为古代兵书成为“明日黄花”的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古代的兵器和战术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对此,作者并未予以否认,明确表示“古代的刀剑弓矢,已非今日的炸弹水雷可比,因之古代的战术自然不能适用于今日”。而后,他笔锋一转,写道:“固然古代的兵书有一部分不适用,然古代的兵书大概都没有论到兵器的用法、射击、战术及操典等,都是泛论为将、治兵、虚实、奇正、行军及类今日攻击、防御、筑营等方法”。[9]
概而言之,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古代的武器战术确实不合于时,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兵书都不涉及武器、战术、操典等具体的技术层面问题,兵书着重论述之处在于具有跨越时空性的经典战争指导原则和思想,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兵书之于现代军事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事实上,李零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中国传统兵书中有“兵法”和“军法”之分,前者着重体现战争指导原则即作者所言的“作为战争艺术”的兵法,其代表如《孙子兵法》;后者则带有具体的军事实践操作色彩,代表如《司马法》。参见李零:《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作者建立了将西方现代军事技术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的“器”与“道”的高下之别。作者的这一论述思路仍隐隐透露出“中体西用”的思想痕迹,有其时代局限性。[1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路对于我们在当下的条件下,重新认识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无启示。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战争中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在更高层次却有其相通性。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兵书中,《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他(指孙子—引者注)的理论,实在不关于时代,而可以说是千古不灭的道理”。同时,他还指出,“古代兵书还有现代军事研究不到的地方”。紧接着,他更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要“如胡适先生所说的整理国故”,以“冷静的头脑、沉定的精神、条分缕析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并提出了六个审视古代兵学的原则,即“宜向理论处着眼毋固执于字句”,“不合时代的地方一律略去”,“应求根本原理”,“不宜昌尽信”,“应审度它合理与否以作实行的标准”,“死书活用”,“用科学的方法把它整理起来”。[9]其目的就是在于最大化发挥中国传统兵学的对于现代军事的作用,使传统兵学的智慧不会碍于时代的阻滞而丧失价值。
这一思路成为时人审视《孙子兵法》的普遍路径。1936年,叶慕然在其所著《孙子兵法新诠》一书的“篇前序语”中也说道,“要在过去战争底经验所得来的原理原则上去寻求启发,才可以得到我们军事行动上的伟大底助力”,接着他指出,“我国军事的专书很少,而能够保持其超越时代底价值的只有《孙子》十三篇”。在他看来,“《孙子兵法》的好处不在它里面的原理原则是有先见之明,而在它能以尽人力谋胜算作它主论的中心”,“它能够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完全是因为这样”。事实上。作者十分清楚,由于时代的不同、兵器的精进,《孙子兵法》的方法“也有许多不能适用于现实的”。[11]在认清《孙子兵法》在战法等战争技术层面的时代局限后,作者更加注重从“原则原理”上去阐发《孙子兵法》的超越性价值,而重视《孙子兵法》超越时代的战争原理原则是作者对《孙子兵法》予以重新诠释的基本立足点。
可以看出,民国知识军人参照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谱系,重新定义中国传统兵学的位置,着重阐述传统兵学中所蕴含的亘古不变的具有超越性的战争指导原则,进而发掘出传统兵学的价值。而在这一过程中,《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战争艺术”的代表性兵书,对此书研究的复兴,实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
二、时代背景与《孙子兵法》研究
民国知识军人在中国传统兵书中着重发掘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战争指导原则,而作为中国传统兵书典范的《孙子兵法》受到了高度重视。《孙子兵法》寄托着民国知识军人从中国古代兵学中提炼总结出中国本土现代军事学理论的希望。1929年,有论者就此做出了尝试,撰文“以现代战争之事实证明真理(指《孙子兵法》—引者注)是否适当,有无谬误之处”。作者立论的基础在于承认中国古代兵法中所蕴含的哲学并无时代限制,而是有其超越性。对此,作者还援引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资源加以说明,他引述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表明“操典和战略学”有所不同,后者“无所羁束,真理及实际之外,不知有威权,亦不知有信条”。而《孙子兵法》就是讨论战略问题的“军事哲学”,因此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经典性。为此他还特意区分了“战略与战术”的概念,指出“战略与战术,其思想决然不同,基本战术,包含在操典内,所以示行军地形及战斗诸方法也”。而《孙子兵法》则不同,“孙子学说,只言用兵之思想,而不具其条件,故孙子纯为战略学,用兵的原理,所谓理的哲学也”。[12]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复兴实际上有其内在的学理逻辑。这也反映出在引介和吸收西方军事理论的基础上,民国知识军人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的军事学理论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和思考。
需要加以关注的是,民国知识军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集中思考建立中国军事学理论有其论说的现实指向性。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在日本步步紧逼侵略的救亡环境下,催生了民国知识军人对《孙子兵法》研究的关注。一位留学日本的青年军官在文章中写道,“孙武之兵书十三篇”,“此均为外人所心佩服,或偷录研求以为己有也,惜我国人不加深究”。[13]言论中透出对国人怠于《孙子兵法》研究的惋惜与急迫感。事实上,作者所说的“外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确有所指。日本学者近代以来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十分重视[1]216-226,[13],尤其是日本学者大谷光瑞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在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下,加强对战争指导原则的《孙子兵法》的研究无疑是民国知识军人重点关注之所在。
就此而言,此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不仅是构建中国军事学的理论探索,更具有救亡图存的现实意涵。关靖更是针对《孙子兵法》受到日本重视,而在中国却鲜有问津的情况提出诘问,“因何吾国最高军事学府暨一半军事学校不注意者,及此而日本对于孙子十三篇反秘密研究耶?”[14]针对大谷光瑞的研究,他还指出,大谷的研究虽然为《孙子兵法》提供了译注,但却未能对中国以往积累深厚的《孙子兵法》研究成果加以吸收,故而对其评价并不甚高。
“大谷光瑞君所注《孙子》,只举魏注寥寥数语而已,若大谷先生,可谓大胆敢为已极,予对于崇高战理,固无研究,而魏武以次十家注,并赵注蒋注等,指不胜屈,靖虽不敏,未敢苟同。”[12]
关靖的评价在当时的环境下多少带有一些争胜的意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光瑞的《孙子新注》也并非是从纯学术角度对《孙子兵法》的解读,而是以“所谓的‘新注’的形式来宣扬自己的‘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和对华观”,目的在为日本侵华行径张本。[15]由此可见,关靖从“学术”角度的批评与大谷所注《孙子兵法》的意图之间存在“错位”,以后见之明而言,关靖的批评实为切中大谷《孙子新注》一书的肯綮。然而背后却反映出中日两国知识界围绕《孙子兵法》这一微观知识场域的激烈斗争。
在当时的环境下,类似的声音并非罕闻。叶慕然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说道:“我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只有全国一致以抵抗敌人的侵略才可以从死里求生路”。[1]篇前序言他指出:“在这个侵略者鼓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底狂潮骇浪中,全国一致皆为战时的准备以外,还要随时寻求普及军事智识的方法”,但是现实境况是“在国民军事智识极端贫乏的中国,而说普及军事智识,这确是千头万绪”。随后他又明确表示,“要在过去战争底经验所得来的原理原则上去寻求启发”,而《孙子兵法》则是“有口皆碑”的学习范本。[1]篇前序言接着,他笔锋一转,指出“侵略者”——日本对于《孙子兵法》研究和普及的重视:
日本人士已经将它(《孙子兵法——引者注》)来研究了数百年……所以他们自从维新到了现在,对外的关系无论政治的、或军事的,以一本《孙子》十三篇可包括而有余。故此他们以泰西各国的军事学说来探索它的原理,出有专书以外,最近还由政府的文化机关计划出版全集,几为国民必读的专书。[1]篇前序言
他以痛惜的笔调写道,相比之下,因诸种原因,中国对这本“固有的宝籍”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没有切实可用的论著。因此,他明确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普及国民军事智识和减省一般武装同志研究《孙子兵法》的脑力”,“以现代的军事学说和国际的关系用来从新的诠说”,提供一本可供全国军民研究和学习的切实有用的《孙子兵法》著作。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亦有引为同调论者表示,“《孙子》一书,虽著作于远在二千年以前,而所持原理,实深合乎现代战争崭新之法则,不仅德军因此而获胜,反观我们敌人日寇,亦何莫不欲效仿抄袭?我们固有的宝贝,不知珍贵,外人得其精髓,反因获伟大之成果,事之可耻,孰有逾于此?”[16]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其背后的关怀还是在于现实的刺激。
可以说,构建中国军事学的理论思考和面对日本侵略的现实关怀始终交织在民国知识军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规模侵华,为配合全国抗日的大形势,一大批《孙子兵法》研究的著作应运而生[1]183-184,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呈现出复兴的蓬勃局面。(3)有论者以文献计量研究方法考察抗战前后《孙子兵法》研究的情况,指出,“抗战时期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播成果斐然。”参见邵青:《对抗战前后孙子兵法研究的计量学考量》,《孙子研究》2016年第1期。《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典范,对于它的研究不仅仅是构建中国本土特性的军事学理论创新问题,在对其研究的背后更有救亡图存的深层意涵。韩一青在其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浅释》卷首题岳飞的《满江红》词,在序言中更是开宗明义说出注释从《孙子兵法》的用意,“我华这次被日本侵略……人人都充任斗士,可是军事知识也当人人具备,才可和敌人疆场相见,因取《孙子》十三篇加以浅释”。[1]184可见,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复兴与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反映出时代变局对中国现代军事学理论的催生作用。
三、《孙子兵法》研究在战时价值的凸显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孙子兵法》研究的蓬勃发展无疑与抗日救亡的时代旋律相和韵,涌现出的大批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论著,其现实指向就是要唤起全国军民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坚持抗战的信心。正如前引叶慕然所述,这一时期《孙子兵法》著述的目的就是在于向国民普及军事常识,并为军队提供可资借鉴、通俗易懂的《孙子兵法》读物。在这一鹄的指引下,战时的《孙子兵法》研究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实用性色彩,更加偏重其在实践层面上的价值。“民国的《孙子兵法》研究……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积极反映和满足时代的要求,体现了《孙子兵法》经世致用的价值。”而抗战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经世致用色彩无疑更为浓重。[1]188可以说,正是抗战救亡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孙子兵法》研究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紧密结合现实环境、注重联系战争实践,是抗战前后《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播的突出特点。这一点在抗战前后各种见诸报纸杂志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939年,楼桐孙就曾撰《从孙子兵法断定倭寇必败》一文,明确表示:“中倭战局,于我是延长愈久,愈为有利,反之,于倭寇方面,却是延长愈久,愈为有害”。在此基础上,他以鼓舞人心的笔调写道:“这是我们全国同胞对于战局前途所应深切认识不可稍有误会的”。[17]而作者此番判断的依据就是《孙子兵法》中的“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利国者,未之见也”,“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作战篇》)等论述,说明长期用兵的弊端,并以此指出日本必败,以激励国人抗战的信心。最后,作者对此又重加强调,坚持抗战“在倭是‘贵胜不贵久。’在我是‘贵久不贵胜。’”并表示“胜负之数,时间自然会替我们作一个公正的证人,而皆一一合于我兵祖孙子所论的原理”。[17]作者通过阐述《孙子兵法》中长久用兵一方之不利,并结合抗战相持阶段的实际情况,得出日本必败的结论。此举固然重在鼓舞国人士气的,亦透露出《孙子兵法》这一经典兵学著作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所焕发出的生命力。
事实上,上述观点成为抗战时期讨论《孙子兵法》文章中的普遍论调。邓冶欧也根据《孙子兵法》中相关长久用兵之弊的论述,指出“抗战已经到二十六个月了。敌人的‘不战屈兵’‘速战速决’和‘速和速结’的战略,是已成为过去的名词了”,随后表示“我们既已踏入抗战第二阶段,当然工作更艰苦,更要加十百倍的努力奋斗。”[18]以此鼓舞国人坚持抗战。1942年,钱基博也借由《孙子兵法》论证日本必败,除《孙子兵法》中被普遍征引的长久用兵不利的观点外(4)典型观点为《孙子兵法》中《作战篇》相关论述:“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在文中还引用了克劳塞维茨之语与孙子的论断相互证,“克氏著书论兵法,每谓:‘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参见钱基博:《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大中国(重庆)》1942年第1卷第2期,第15页。,钱基博在文中还特别强调运用现代战争史例来对《孙子兵法》的原理加以阐述。他引述德人克老山维兹(今译为克劳塞维茨——笔者注)之语:“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在克氏的基础上,他指出:“战史之尤繁钜以媲于现代史者,盖莫如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采用“古书新证”的方式“发前人所未发者”。[19]他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德为首的两大同盟胜负的情况,分析道“亦即旷日持久,而德不得志”,指出英胜德负的根本在于,拥有众多资源的英国对以速取胜的德国采取了持久封锁。他借欧战史例论证《孙子兵法》中久战不利的观点,其落脚点还是在于对抗战局势的关注,随后他写道:“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交杀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19]这一断言,显然是感于抗战时局而发,用其所言即“以‘待’而制胜”的方式坚定国人抗战决心。
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为鼓舞士气,坚定国人的抗战决心,报纸杂志上关于《孙子兵法》的文章中皆大量征引《作战篇》中关于久战不利的相关论述,以此强调持久抗战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指出:“‘持久战’实为抗战全程的官方主流称谓。”[20]不难想象,在重庆国民政府当局的强调下,“持久战”话语通过各种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共识。在这一思路下,不惟凭借《孙子兵法》对国内战局加以分析,甚而有论者作《从孙子兵法论断纳粹必败》一文,表示:“希特勒指挥下之纳粹大军与东方倭寇,侵华五年,不能自拔泥足者同其命运,屈力殚货已兆端倪,不戢自焚,何待耆卜,是又与孙子‘兵之情主速’之原则,转相悖谬。”[21]随后论者还专门写道,“此文作一年以前,此一年来,纳粹遭苏联之坚强抵抗,其势已成弩末,最近苏联有史城之捷(指斯大林格勒战役——引者注),纳粹军队,望风瓦解,崩溃之期,定在不远”。文章结尾作者写道:“此文倖而言中,益见孙子兵法,论断精微,故敢付梓,就正国人。”[21]论者通过强调自己一年前的预判与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相吻合,表明《孙子兵法》这一古老的兵学著作中所蕴含的战略智慧具有的超越时空的价值。进而言之,作者虽针对纳粹的局势做判断,实际上其关注的重点仍落在国内,其根本用意是从国际形势上鼓励国人的抗战信心。(5)全面抗战时期,国内与国际的战局相互关联,某种程度上而言,国内战局就是国际战场的一部分。相关研究参见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蒋永强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从《孙子兵法》中撷取理论资源以应对现实,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取径。每当现实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口,历史往往成为人们应对现实的重要理论资源。被誉为中国传统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在抗战前后价值的凸显,即可作如是观。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国统区人士以《孙子兵法》的相关论断来支持持久抗战的观点。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也发出了声音。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对于坚定全国抗战信心具有重大意义。而“《孙子兵法》是对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影响很大的一本书”,“《论持久战》是对《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运用和发展”。[22]此外,毛泽东还专门安排郭化若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研究。据郭化若回忆:
毛主席把宣传古兵法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我作些系统的研究,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以便向国民党军官进行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这是当时宣传古兵法的直接目的,也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古为今用”的一种特殊需要。[23]162-163
中国共产党人借助《孙子兵法》对国民党进行宣传,侧面也反映出《孙子兵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6)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参见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第162页。而郭化若本人也在研究《孙子兵法》的过程中,结合古代战例对其中的持久战思想加以阐述,这体现在《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此文虽然不是直接就《孙子兵法》本身内容展开研究,但却贯穿着《孙子兵法》中攻方久战不利,而守方持久抵抗扭转局势取胜的思想。(7)郭化若本人曾对写作这篇文章的意图进行过解释,“我认为齐国能转败为胜,除了采取火牛阵和突然袭击的战法外,最根本的是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参见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第165页。这一文章的旨归亦未脱离于全面抗战的现实,他借齐国坚持抵抗转败为胜的史例意在说明,“在我国现时的抗日战争中,日寇只能逞凶于一时。人民中有无限的力量潜存着,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配合军队作战,就能最终打败敌人,取得抗战胜利。”[23]165
全面抗战时期,《孙子兵法》成为当时人们论证持久抗战、坚定抗战信心的重要标的,更是在全面抗战中结合战争实践,从而孕育和更新中国军事理论的重要资源。具体而言,《孙子兵法》在全面抗战中价值凸显具有双重意涵。在精神层面上,《孙子兵法》作为两千年前的兵学著作,根据其原则仍能观察和分析当下的战局,这样的经典为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论断,鼓舞抗战信心;在具体的军事理论上,时人根据抗战的形势,灵活运用《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这一原则本是基于强势进攻的视角而发出的警醒,时人则通过反向思考,结合中国所处的弱势防守地位,反向思考着重阐发“久战不利”的思想,从而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其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杰出的代表。[24]桑兵指出,《论持久战》的问世“使得战略层面的持久战思想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世界军事史上据有重要地位,受到普遍的重视”。概而言之,全面抗战的战争实践为《孙子兵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也映衬出其独特的时代价值。
四、余论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孙子兵法》研究的复兴既有其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同样有催生其蓬勃发展的外在时代背景。自晚清以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在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冲击下开始转型。当时的军事学界承接晚清余绪,以西方军事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兵学。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晚清的发展和积淀,民国时期的军事学界,并非如晚清人士刚接触西方军事理论时那样对中国传统兵学加以否定,而是在吸收西方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孙子兵法》等传统兵书的价值。他们借助于西方军事理论的框架,着重挖掘《孙子兵法》中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性原则,开始了发掘传统兵学资源的学术富矿,以构筑中国本土的现代军事学理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这些都催生了此一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复兴。
在全面抗战的时代环境下,《孙子兵法》的价值更进一步得到凸显。不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持久战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8)桑兵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乃至举国上下都知道中日之间敌强我弱,对日抗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有可能由弱转强,争取最后胜利。”参见桑兵:《抗日战争持久战要多久:社会各界的呼吁与期盼》,《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人们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汲取资源,在敌强我弱的现实境况下,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将《孙子兵法》中“兵闻拙速”的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着重阐发其对立面“久则钝兵挫锐”,从而论证持久抗战必胜。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通过这些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时代变局之下,《孙子兵法》这一中国传统兵学名著对中国现代军事学理论的孕育催生作用。
正如论者所言:“一切军事学的基础均在于军事史”[25],结合时代条件,通过借鉴、总结与反思既往军事理论资源,返本开新,无疑是军事理论建设的有效途径,古今概莫如此。细绎过往的讨论,尤其是如何看待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关系,对于我们在当下的条件下,重新认识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无启示,对于构建中国军事理论话语体系同样具有历史维度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