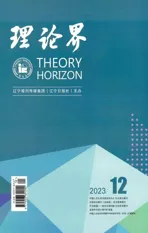“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2023-04-17谈天
谈 天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紧密关系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客观呈现问题。《中庸》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孟子》中亦有“有诸内必形诸外”之语,出土文献《五行》篇更是围绕着“形”展开一系列论述。而在《荀子》中,“形”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出现次数为57次,依字面含义划分为4类:
(1)人的形体、躯体。例如《荣辱》篇:“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1〕此处“形体”即人的自然身体。《正论》篇:“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2〕此处“形”亦是作身体来理解。
(2)人的特定行为(尤其指道德修养)客观呈现的含义。例如《劝学》篇:“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3〕此处“形”指的是“学”的过程中客观呈现的一种状态。《不苟》篇:“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4〕亦指的是道德修养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3)事物、事情的展现、表露。例如《解蔽》篇:“万物莫形而不见。”〔5〕此处“形”指的是世间万物的呈现。《儒效》篇:“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6〕指的是道德风气的流行。
(4)形势。例如《强国》篇:“其固塞险,形埶便”。〔7〕《正论》篇:“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8〕以上两条均作形势来理解。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形”本义为模型、象形之义。《说文解字》曰“形,象也。”段玉裁注为“象当作像,谓像似可见者也……《左传》‘形民之力’假为型模字也。”〔9〕由此可见,在《荀子》文本中,在使用“形”这一概念时,往往取其譬喻义,来赋予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我们认为,《荀子》“形”概念的第二类含义有着独特的理论含义,有进一步讨论的理论空间:人的特定行为(尤其指道德修养)的客观呈现,既关系内在的修身处,也关联评判行为的客观准则问题;而人的道德修养的客观呈现,必然涉及一系列重要因素,如人心、礼则等。学者指出荀子在道德修养的问题上,相对于思孟学派,具有明显的礼则化的特征,〔10〕而人的行为实践,亦有赖于“心”的主宰,故“形”要由“心”来实现。〔11〕可见,由“心”主导的“形”之呈现,和道德修养具有的形式化、礼则化之间,尚存有较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形”究竟在“心”和礼则之间扮演了怎样的理论角色,仍然有待言说。
一、“形”与“心”
在战国中晚期,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人的内在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不仅会在其心灵、思想上有所体现,同时也会呈现在外部的容貌、气质上。譬如《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2〕这里所讲的是君子身体所展现的特殊的样貌,而这种样貌正与仁、义、礼、智四端之扩充紧密关联,换言之,孟子所谓之“生色”,即是“精神化身体”〔13〕的呈现。又如《管子·内业》所言“心全于中,形全于外”,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心”与“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节中,我们通过梳理《荀子》中“形”与“心”的关系,尝试解答人何以能“形”的问题。
总的来说,对《荀子》中“心”与道德修养关系的探讨,使我们注意到“形”的实现,即道德修养的客观呈现,具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在了解“形”与“心”的关系时,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劝学》篇的一句话: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4〕
杨倞注:“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入乎耳,箸乎心,谓闻则志而不忘也。”〔15〕梁启雄曰:“箸,借为‘贮’。《说文》:‘贮,积也’”。〔16〕李涤生曰:“‘箸’,同‘著’,存也,积也……‘形乎动静’,谓日常行动合乎道德标准。”〔17〕荀子这句话中的观点是,君子的成德之学,以耳朵听闻,牢记于心,经过不断积累,作用在四肢躯体上,使进退举止皆有所“形”。〔18〕由上不难得知,“形”是成德之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君子通过客观经验的认知,于“心”中有所积累,进而作用在身体上,使得客观呈现的“形”成为可能。不过《劝学》中的这句话,仅展现“形”在成德之学中的大致角色,也只粗略为我们点出“形”与“心”之间存在的联系。若要进一步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荀子》文本作进一步分析。
《解蔽》篇中,荀子论述了“心”与身躯之“形”的关系: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19〕
一方面,荀子认为“心”对于人的自然身体具有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在荀子看来,“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指的是人的身体可能因为外在的因素而有所变化,而“心”却不会因为外部的因素转变意向。所谓“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皆是对心的自我调控能力的描述,也就是说,即使“心”改变了意向,也并非外部因素直接作用在“心”上,而是“心”的“自取”“自夺”的结果,是“心”的思虑与决断的作用,即“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显然,“心”的自主的意志品格在“成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解蔽》篇中,荀子亦强调,“心”必须在“知道”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行为,否则就会出现蔽塞而导致危害。“心”必须经历“知道”“可道”“守道”的过程,从而使道德修养由内向外呈现:
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20〕
此处“治之要”之“治”,乃“治乱”之义,陈大齐先生解释道:“道是思想言行的究竟标准……必认识了道,而后才能以道为可,才能守道而不违背。若不认识道,势且把不属于道的误认以为可,而把真正的道误认以为不可了,故‘知道’是‘可道’的先决条件。”〔21〕由此不难推断,荀子所说“治之要在于知道”,是说实现“治”,必然先要使“心知道”,“心”既能“知道”,便能了解到“道”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根本准则。有此认知的积累,就能够“可道”,即以自我意志进行决断,进而能够“守道以禁非道”,以“心”之所知、所可付诸行动,从而作用在实践上。《解蔽》曰:
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身尽其故则美。〔22〕
“以赞稽之”,或作“壹于道以赞稽之”,〔23〕意为专一于道,以参于物,而可知万物且不蔽。“身尽其故”之“故”,杨倞注为“故,事也。尽不二之事则身美矣。”〔24〕李涤生注曰:“‘故’,事物之理。身尽其道,物尽其理,则完成人格之美矣”。〔25〕“心”能够认知万事万物的道理,故而于己“身”之修养、践行,亦有明确的认识。因此,“身”之“故”,即是“身”之本然的道理,李说是也。“身尽其故则美”,意味着在认识到事物的道理后,能够充分地践行。“美”,《劝学》曰“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指人格之美。此种人格之美的展现,便是认识到事物道理后,充分践行的结果。
结合我们对“心”之治、养所做的分析,不难推知“心”与“形”的理论关系:
第一,“心”对于人的自然身体有着主宰作用。虽然身躯之“形”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受到影响,但“心”却不会受外物所牵制。只有经过“心”的认识与认可,意志才会进行改变。
第二,人的自然身体可能因外在的因素而有所差别,但是无害于道德的修养。在个体修养的过程中,“心”的“治”“养”才是最为关键的。《非相》篇曰:“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在成德之学的过程中,经验性的知识通过“心”的积累、思虑,影响外在的行为,使得道德修养的客观呈现,即“形”,成为可能。
第四,“心”之治需要经历“知道”“可道”“守道”的过程,“知道”是“可道”与“守道”的前提。通过“虚壹而静”的修养,能够对事物有客观、准确的认识,了解万事万物所因循的准则、道理。
第五,“心知道”能够认识到事物所具有的道理,掌握事物因循的准则。因此,君子可以恰当地参与万事万物的活动,充分践行所认识的道理。身尽其道,物尽其理,荀子名之曰“美”。虽然荀子并没有就“身尽其故则美”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不难推知,经历了审慎、专一的治心、养心的工夫,“心”权衡、思索事物所因循的准则,进而使人能有所践行,这样由内而外的过程,也正是道德修养外在呈现的过程。
二、“形”与“诚”
学者指出,在荀子那里一个人行善是因为他认可行善,人行为的“可”与“不可”的能力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可能。自我教化的过程,始于对礼的实践,起初人们并不习惯,但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人们为了自身的原因,乐于礼的实践,欣赏经典文本。而且人们必须被训练成乐于礼,欣赏经典文本。〔26〕如果说人们被“训练”成乐于礼,那么“训练”的方式是怎样的?经过“训练”,人们所呈现的样貌又是怎样的呢?《不苟》篇曰: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27〕
《不苟》篇的这段文字,不论在思想内涵上,还是在文本问题上,都留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譬如牟宗三先生指出:“此为荀子书中最特别之一段。‘诚心守仁则形……谓之天德。’此与《中庸》‘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唯能化’义同。”〔28〕又如廖名春教授指出:“《不苟》篇中,荀子却吸收了大量《中庸》的思想,例如对‘诚’的论述,对‘慎独’的论述。”〔29〕由上述观点可知,对于《不苟》篇这段文字,学者常认为受到《中庸》的影响,化用了《中庸》中的句式,或直接认为与《中庸》中部分思想相同。但我们认为,对这段文字进行分析时,不能照搬《中庸》中的观点,《不苟》篇作为《荀子》中的一篇,存在着思想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解读此段文字,仍然要从《荀子》文本内部入手,寻找《荀子》文本自身阐释的可能。
在对《解蔽》篇“心”的认知方式进行分析时,我们论述了“心”经历“知道”“可道”“守道”的过程,并阐释了通过“虚壹而静”这三种修养工夫能够对事物有客观、准确的认识。但问题在于“心”的意志品格决定了“心”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全然自主,那么“心”从“知”到“可”,由认知的积累转向意志的决断,必然需要持养的方法,就留有可解释的空间。
回到《不苟》篇,我们就会发现,荀子提出了以“诚”养心的方法。“诚”,在前人的理解中,或作为坚定笃行的品质,或作为真实之义,或作为自我完成来理解,所以至少就“心”的修养来说,“诚”指向的是心灵之真诚。一方面,“心”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特性,使养“心”的工夫必然涉及“心”本身的认可,不强迫、欺骗“心”;另一方面,“诚”并不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品格,而是养心的方法,“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在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中,仍然是依从“仁”“义”展开。
对“诚”的了解,使“诚”与“形”的理论关系变得明晰:
第一,“诚心守仁则形”,是在“诚”的持养下,“心”有所认识、认可并愿意付诸行动,故而能“形”,能于外有所呈现。“变化代兴,谓之天德”,下文解释道:“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即是以“诚”养“心”,在认识到万事万物因循的准则、规律后,正确地统摄万物,故荀子称之以“常”。
第二,“形”是“心”认识、思虑、认可与决断后的结果,“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一个善于为道的人会明白,不诚心守仁行义,就不能用心专一,若不能用心专一,便不能“形”。“形”不同于“作心”“见色”“出言”等外在的状态、容貌,在荀子看来,“形”是由内而外,诚心守仁行义的结果,而不是刻意地展现、表露道德化的容貌。
三、“形”与礼则
陈大齐先生在《荀子学说》中依《劝学》“礼正其经纬蹊径也”,推论荀子之道即是礼义,礼即是蹊径,道亦是蹊径。〔30〕其说虽可商榷,但不能否认的是,荀子之道落实于人类社会,其表现形式就是礼义。如果由上言不合于道则乱,那么推至礼义,则不合礼义亦乱。荀子之礼义,具有客观与普遍的意义,《王制》曰: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31〕
以一行万者,与其说是道的功用,毋宁说是礼义的施行。在荀子的描述中,礼义的客观性与普遍性表现得尽致淋漓,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均在礼义的规定下各行其是而有不易之分位。
在前文中,我们已认识到,“心”可以“知道”,能够通过修养,认识到万事万物因循的准则,落实在人类社会,这种根本的准则就是礼义法度。那么,涉及“形”,即个体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也与礼义法度紧密相关。回到《劝学》篇:“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我们可以发现,君子成德之学,通过知识的学习,于心中有所积累,展现在身体上,一静一动皆有所“形”。此处“形”即是内在修养的呈现,而此种呈现,在举手投足间“一可以为法则”,具有了准则的意义。所以,“形乎动静”不可停留在普通的仪态上,一方面缺乏客观性的保证,另一方面,君子的举止言谈若不进于礼则,便缺乏了普遍性。因此,荀子对道德修养所呈现的容貌、仪态,保持着警惕:如果道德修养的呈现,即“形”,没有标准进行衡量,那么我们无法判定其人修养的境地如何,也无法知晓“形”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由是,荀子对注重容貌、衣冠、仪态的子张氏、子夏氏之儒给予批评,《非十二子》曰: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32〕
头戴美冠,言辞浅薄,刻意模仿舜、禹的行动,是子张氏的“贱儒”;衣冠整齐,容貌庄严,终日不言不语,是子夏氏的“贱儒”。二者共同的特点是对外在样貌、衣冠、仪态的重视,通过容貌、行为的模仿而呈现近于圣人的形象。荀子的批评正是由此而发:雕饰出外在仪表上的盛况,以显示其德行之盛,实际的内在修养,却不得而知,所以《不苟》篇才会强调“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形”不同于作心、见色、出言。一方面,如第二节所述,“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形”得以实现的背后,是诚心守仁行义、专一笃志的内在修养工夫。只有经过“诚”“独”的持养,内在修养的提升,“形”才能得以实现,而作心、见色、出言,则并未有如此内在修养的积累;另一方面,对于礼义的学习,使君子于举手投足间合乎礼则,“形”实际上具有了客观化、礼则化的意义,而作心、见色、出言,仅出于一己之私意,故荀子认为“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
结语
在荀子那里,人必须重视“心”之持养,注重“心”的知虑、决断作用,使“心”能够持久地接纳并践行道德,故能有所“形”,但无论是“心”之知虑、决断,还是修养的呈现,均要以道为准绳,使“形”之实现有一客观准则能够衡量,并使身体之行动展现普遍性、客观性。
君子能“形乎动静”,始于知识的积累,通过“心”的持养,对于万事万物根本规律能有一准确认识。在荀子看来,对于事物的接触、认识、思虑、辨识,使得经验得以积累,对“形”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荀子重视“心”之持养,强调决断与意志在“形”的过程的作用。一方面,《解蔽》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心”对于“道”有了真切的认识,有理智的思考与判断,因此,构成正确行为的前提,对自身的行为能有所决断,有所命令。另一方面,养“心”莫善于“诚”,“诚”是养“心”的方法,于内展现为真诚的心灵状态,不强迫、欺骗“心”,帮助“心”真切地认识、认可与决断,帮助人在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中保持专注、真诚,使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践行道德。
但内在修养的呈现,或者道德行为的实践,必须有客观准则来衡量。《正名》曰:“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依荀子,“心”本身并不可作为一衡量的标准,必要使其合于道,《正名》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因此,荀子论说“心”之持养与“形”之可能,在根本上是要以道为准则。落实在修养的呈现上,即“形”的实现问题,荀子认为,仅仅依靠知识的积累与意志的决断,是不足以实现“形”,或者说“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之“形”,是不可靠的,根本上要以客观的准则来衡量。所以,在荀子看来,“形”之可能,不仅出于经验之积累与心意之肯认,更要有客观准则作为衡量,由此准则义,不仅使君子之“形”得到信赖,更可使君子之“形”具有教化的意义。我们便可推知,荀子论“形”之基本理论目的,是要确立客观准则,即礼义法度,在道德修养中的理论地位,个体的修养不仅要因循礼义法度,亦应当于外在呈现上符合礼义法度,使之客观化、礼则化。所以在《荀子》中,无论个体的内在修养,还是外在呈现,均与礼义法度紧密关联,个体气质之变化并不是荀子论“形”的主旨,此“形”能否普遍化、礼则化,才是荀子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