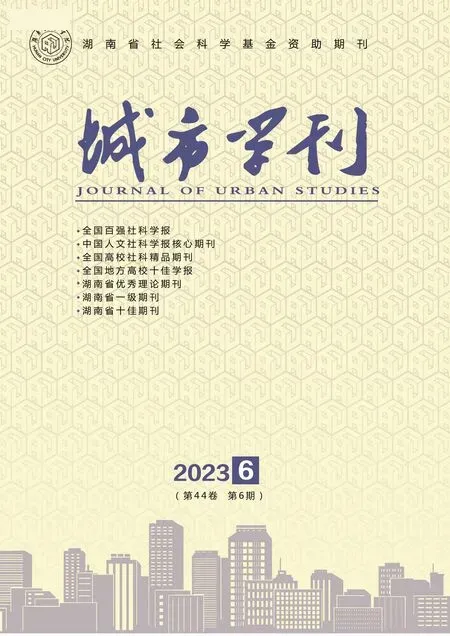作者电影的许氏风格与《第一炉香》的形象偏离
2023-04-17傅守祥谢苗苗
傅守祥,谢苗苗
(1.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2.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于1943年4 月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创刊号上开始连载,标志着张爱玲正式走向文坛。2020 年8 月,以当代作家王安忆改编的蓝本为基础,导演许鞍华完成了电影《第一炉香》的拍摄,并于2021年11 月公映。前期主创团队的强大阵容和张爱玲作品本身的热度,吊足了观众胃口。但这部受到观众格外期待的影片却票房不佳,目前豆瓣评分仅仅5.0,远低于李安《色·戒》的8.6 分。
这部电影真如评分所代表的那般低劣吗?或者说如此低的评分,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许鞍华本人的创作初衷和影片本身来看,她接受张爱玲的文本,然后以跨媒介的方式向大众输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这一解读过程是否为观众接受以及接受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作者的创造、导演的考量、观者的思虑等各有各的主体性,三者不见得也很难会在同一个层面,许鞍华影片《第一炉香》的认可度低,可能是因为观者多半忠于张爱玲笔下具有多元指涉意味的文本,而她则执着于自我内心解读的那个超脱俗世、真纯过度的“爱而不得”故事,正如她自述“我就想拍一部爱情片,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从来没好好地爱过,你要让我爱一次”。[1]让我们对比细读小说和电影,体会人物堕落因由和故事画风的微妙转变,品味许鞍华导演在其光影叙述中的人性纠缠与沧桑呈现。
一、从玲珑到天真的女主角葛薇龙
许多观众批评葛薇龙的饰演者并不具有原作的特征,甚至相悖。这一外貌体态上的指责略显表层,但在此之下潜藏的是受众对女主人公内在神韵的精妙把控。从小说到电影,媒介形式的转化使得大量文本空白得以填满且实体化,葛薇龙这一关键性的形象也在跨媒介的叙述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她是张爱玲笔下许许多多工于算计、清醒冷静且有着“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之美誉的上海女人中的一个,那么在许鞍华改编后的电影中,她已然成为偏向当下青少年口味的“傻白甜”,这一改动向着当代青春片靠拢。很显然,停留在浅层次的天真女性形象,早已无法俘获电影院线的主体观众。然而,一方面作为视觉性媒介的电影难以传达主人公复杂细腻的心理变化;另一方面为追求较纯粹的爱情神话,影片不得不采取简化乃至纯化葛薇龙原有的盘算形象,进而弱化内心书写的粗暴手段。经由此途径,原作中的台词和场景再现几乎面面俱到,但外化心理感受的缺失几乎造成了这一女性形象的质变。
张爱玲充分发挥小说这一叙事媒介的特征,既有客观叙事中戏剧冲突的故事性,又有主观叙述上的雅俗共赏、譬喻经典和评析精当等先锋尝试。许鞍华和王安忆的改编则经由电影试图表达和还原小说场景,然而一方面她们强调拍摄过程和台词的翻译、移植、保真,另一方面她们又很难做到对原作的“高保真”,于是“不完全的”保真,让改编之作陷入不伦不类的失落。因为电影难以还原张爱玲对人物心理的精妙评述与譬喻,是客观的具体影像使然,而从人性深度上降低女性形象,则是源自导演对电影的主观定位。许鞍华极力消弭掉葛薇龙嫁人的一番思量,把只会花钱玩女人的乔琪塑造成饱受身世之苦、缺乏母爱的男子,张扬在二者之间的是女主角无可救药而卑微不已的爱,于是高尚和“不知所起”的爱情旗帜被高扬了起来。这是导演本人想要 “好好爱一场”之表现,也是迎合大众情感需要的一种手段。“电影只要定位为大众媒体,就难以真正接受张爱玲这种以审视物欲为基础的女性形象;只要为了满足大众消费,女性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但又是刻板的弱者形象。”[2]然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真的难以面对人性批判和欲望审视吗?李安的《色·戒》无疑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否定性的回应。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内心活动的人物往往外表沉静而不动声色,这是张爱玲的高妙,如何将复杂者的心理感受外化为合乎逻辑的行为细节却也是导演改编时用简化和套路化方法无法解决的难题。
小说中葛薇龙的机敏和落落大方从踏入梁府大门的那一刻就开始表露,她有林黛玉般的聪慧多思、自尊好强。虽然她和黛玉寄人篱下的心思相仿,但其身处的地方显然有别于贾府。前者不过是殖民地治下畸形颓废的摩登景象,后者却是不失礼仪秩序的簪缨一族。在踏入姑妈家的大门时,她已经清楚自己的求学目的要和过程的流言分离开来,成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因此她赔着笑任由丫鬟的鞋子砸过,却不发一言;梁太太的言语虽刻薄到使之落泪,她也在镇定中既为父亲曾经的过激言语道歉,又几番周旋说出自己的拜访因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爱情书写,并不单是对‘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的时代注脚,而是以自足的姿态遭遇更高强度的世故算计并予以顽抗,从而在时代背景下突显苍凉况味。”[3]然而她的清醒理智和自我劝诫,远远敌不过人性的弱点——对于美丽服饰所象征的奢靡生活之渴望、对于情欲袭来时的难以抵抗。即便她对自己此番羊入虎穴的经历认识透彻,却也欲罢不能地走上自欺欺人的道路。
电影中葛薇龙(马思纯饰)的形象在根本上有别于原作,她以几近天真愚笨的姿态羊入虎口而不自知。小说中葛薇龙的那股子聪灵气和知书达理的落落大方全然不见,取而代之以惊惧惶恐的神情和木讷健硕的肢体语言。开场时还未见到梁太,她已经被两个丫鬟取笑奚落至极。丫鬟们趾高气扬地问她找谁,她怯生生又毫无底气地回应“我找姑妈”展露出其憨态可掬、不善交际的一面。在她们质疑薇龙“左一个姑妈,右一个姑妈,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姑妈”的声讨中,她却低头回应“是不是,等姑妈来了就知道了”。三句话不离姑妈的台词,加上略带怨气的口吻,再次强化她语言上的贫乏和小家子气的底色,也让镜头前的观众忍不住喷笑。几个语言回合下来,女主人公愚笨痴傻、天真懵懂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原作中玲珑精巧的上海女人就这样在相似的描摹场景中变了模样。
影片中梁太太与葛薇龙的对话,前者语含讥讽、话中有话,后者低眉顺眼、欲言又止,女主人公丰富的内心活动及对周遭环境的打量思考完全没能表现。她向梁太(俞飞鸿 饰)求助时展露的低三下四和畏首畏尾是一种粗线条的场景勾勒,一个穷学生对象征金钱的梁宅之恭敬,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原作中虽处困境,却不失娇生惯养小姐风范的叙述。她的独白自省要么被移花接木到其他相关人物上,要么化作无动于衷的释然。初入梁府,她对自己的身份处境无知无觉而满心欢喜地接受梁太的物质“关怀”,于是女仆睇睇(张佳宁饰)在一门之隔的外面嘲讽她像是“长三堂子的讨人”;园会上,她颇有好感的卢兆麟(尹昉饰)被姑妈三两下就吸引过去了,她却只能被动地伫立在一群修女身边、目光涣散地寻找、心不在焉地应付,姑妈的一个眼神便将之唤去应对乔琪(彭于晏 饰)……导演所说的保留原作内容、仅作嫁接式修改的结论在此有所体现,一个迥异于原作、天真懵懂的葛薇龙已经完全成形。
张爱玲本人不曾建筑过女性的任何尊严,给予女性群体任何救赎的希望,甚至缺乏女性主义者提倡的憧憬光明和对抗黑暗的力量,她笔下的葛薇龙深深陶醉于“屈抑”男性的快活和耽湎自弃的快感,进而“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后堕落到黑暗的深渊。[4]与作家的话语相对,许鞍华指导下的葛薇龙则为爱牺牲、为爱堕落,她渴望由爱情救赎乔琪,进而救赎自我,这已俨然是导演刻意为之的当代爱情神话,用于救赎不言自明的大众群体。一如戴锦华对该部电影所评论的那样“你们两个和张爱玲之间隔着的不是道德感,而是某一种爱。可能你们心里有一种不能放弃的爱,而在张爱玲那里,我不能说她没有爱,但是她没有你们这样的爱。”[5]拥有这样爱的许氏,本渴望通过女主人公释放久久压抑的情欲来平复大众在浮躁社会影响下日渐萎缩的内心,却收获了“青春疼痛片”“媚俗”等一众指责。
二、从物欲到情欲的堕落因由
欲望是一种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辩证法,它常常意味着现实的匮乏。如果说完备的物质和身心可以造就欲望的诗意呈现,那么反之,也就易于陷入不畅甚至进入异变、扭曲的轨道,从而与传统认知上的自然和人性相背离。文学史上的欲望书写不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可歌可泣的情欲张扬,更有《包法利夫人》这样为消费主义冲昏了头脑而饱受物欲控制的女性人物。作为人之本性的情欲和物欲又常常加诸女人,使她要在满足肉体生存和满足精神愉悦之间做出取舍,这对生命来说本身就是极大的残忍。于是张爱玲和许鞍华在表述相同的故事时,给出了程度不同的理解和包容。
葛薇龙身处摩登时尚的香港殖民地,这里汇聚起更多享乐的感官主义和物质主义。在此背景下,作为初步具有现代性觉醒意识的女性,她对物质的渴望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从不遮掩自身的物质欲望,物欲之于女性在此获得了理解性的肯定,甚至成为女性获取主体和自我的一种手段。“消费文化的出现,促成了女性新的主体形式的塑造,女人秘密的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被商品的公共再现及这些再现所承诺的满足感所影响。”[6]恋物的女人充满欲望、自恋不安,却永远积极主动地为自我谋求出路。但电影中的葛薇龙显然隐没了物欲升腾的自我,化为爱情角逐金钱的高尚卑微,她直接的恋物情结在影片的表述下转了个大大的弯——她为着心爱的人恋物,于是她由恋物的主体转化为男性视野下的他者客体。原文本建构下的自私女人,摇身一变成了为爱而奉献堕落的苦情天使,也因此仅仅考虑精神层面的圆满和释放,无视现实生活的艰辛而做出的纯爱选择,多少都会被质疑出于商业目的而成为类似青春疼痛片的媚俗艺术。“因为徒有爱情的人生不仅是对真实生活的远离,还是对生活的一种简化或悬浮化书写,从根本上说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背离。”[7]
如许子东所评论的那样,“葛薇龙的故事是‘详前略后’的,堕落前的每个环节步骤每次犹疑选择都有详述细描。”[8]壁橱中金翠辉煌的衣服,实在是小说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它揭示了女主人公无意识的渴望,是梁太太精心设计的一个华丽圈套,一场关于美丽的引诱、温情的腐蚀。在此梁太太以身体悦人谋取金钱的生存法则,和女学生用思想悦人的新女性求取生活的方式,展开了一种隐秘而盛大的较量,结果是葛薇龙在清醒地认识到华丽背后的肮脏交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后,又于试试看的恍惚里缓缓下落。衣服的描写,既倾注了张爱玲个人“衣服狂”的情感体验,也预示着葛薇龙缴纳知识和理性投降的第一步,贪恋锦绣云衣是她自觉自主的选择。
在电影中,导演本人似乎有意略过这一段,关于衣橱的特写镜头短暂且缺乏引人入胜的魔力。姑妈具体而切中要害的诱惑,在此仅表达为女主人公衣橱前的短暂停驻,一双眼睛迅速地瞟过去,而那故事里各色质地、适用于各种场合下长长短短的衣衫,为许多颜色黯淡的碎花裙、格子裙代替,唯一的一件“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般的”裙子得到了重视,主人公的目光为之停留。这一裙装在后来的几个场景中渲染出现、着重表达,然而呈现出来的感觉却像宽大肥胖的睡衣一样不合体。许氏刻意弱化对“物”的表现,从而为情欲的张扬留下了巨大的剖白空间。这成为张爱玲与许鞍华在文本上的巨大分歧所在。
如果说原作中葛薇龙的坠落由物欲主导、情欲为辅,那么电影中则完全颠倒二者的次序,情欲成为她由女学生沦至交际花的首要原因。梁太太和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为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可以放弃年轻的爱和喜欢,而后者则是两个都要——要一个爱人的所有权,也要成全对方想要的生活。关于情欲场景的展现,在影片中刻画较多,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对“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的诠释。这一极富当代感的情话,传达出要享乐而拒绝负责的意味。它挑战了长久以来女主人公的生存信条,碰撞的结果是她屈服于对方看清一切、游戏人间的态度。乔琪给葛薇龙的快乐,除却身体的直接快感,更多是紧绷心灵和精神的片刻舒缓。
从这一角度出发,回看不同场景下主人公的“笑”也就有了全新的解读意味。初见彼此的男女主人公,微笑着面对面交谈,展露出二人审慎节制、富有教养的维度。但大笑的场合次数,却构成了乔琪吸引葛薇龙的致命武器。“滑稽的事物能够引发愉快的情感,因为放松和大笑都与灵魂的自然状态相关。”[9]为着能再见到对方一面,她亲自跑去传话,女人的那一点小心思谁都看得穿。当假装鲁莽的乔琪闯入薇龙和吉婕(梁洛施饰)笑吟吟的安闲茶话,他说着英语扮丑服务员、手持香槟却怎么也打不开、香槟酒倒入花盆来打趣家中年老的女仆,原本矜持庄重的谈话在哄堂大笑中结束。一个习惯了不苟言笑的正经生活,另一个却永远嘻嘻哈哈、笑对一切。喜欢开玩笑的他,必然对周遭人的性格和气质有深入的了解,幽默背后藏着更整全的人性、更文雅有度的智慧。乔琪引导周围人发笑,这一笑对其他人不打紧,却魔性地撕下了女主人公戴着的面具,还油彩浓重的脸谱以本来面目。
“乔琪是对的,乔琪永远是对的”折射出葛薇龙的匍匐和仰望姿态,她终于放弃理性思考,投到他的价值观下苟且谋生。而其情欲中不仅包含对乔琪高于常人心智能力的仰望和欣赏,更有着母性的温柔怜惜。婚后她接到金主司徒协(范伟 饰)的上海邀约,便一口答应。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的三个人,站在不同立场的言说“各显本色”:梁太太屈服于钱,她为来电者说话;乔琪自以为占理,他为自己的丈夫身份摆明立场;葛薇龙先为她的爱情,再为生活向金钱低头,她夹在二者之间可怜又可笑。在只有他们两个的卧室,他吵着闹着要求同行,她勉强笑着安慰说给他带好吃的……这一场对话,在笑声和拌嘴中掩饰女主人公辛酸流淌的泪,也在默默妥协中流露出母性和童真。
三、始终与渐进的苍凉况味
张爱玲的《第一炉香》,苍凉是贯彻文本始终的底色;然而在许鞍华的电影中,这份感觉不仅被稀释,而且成为渐进性叙事中后知后觉的存在。其实两种面对人生的态度,没有好坏之分,不过是前者看得太透彻,而略显悲观;后者怀有对人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惜曲笔将苍凉视为最后的顿悟。“任何虚构的人和事, 应符合小说文本规定的生活逻辑与性格逻辑的可能性。”[10]从这一标准出发来看,导演对人物的把控的确并非无可指摘。
因个人曲折坎坷的身世和颠沛流离的人生体验,加之中国古典文学以悲为美的熏陶,张爱玲对人世的认知是悲观的,进而影响她的创作:“我是喜欢创作,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1]小说《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次踏入梁府,便感受到了坐落在群山之间梁宅的鬼气森森:屋檐下吐着红色芯子的“绿蛇”,燃烧的烟卷烫着灼灼其华的红花瓣直至枯萎发黄。在此过程中,梁宅和姑妈所象征的是具有摧残一切美好事物能力的毁灭者,人和物以触目惊心的绚丽糜烂,如睇睇一样学会独自营生,却面临被梁太太撵走,随便找个人嫁了的凄惨结局。对于姑妈居所的准确把握,使葛薇龙清醒地将自己置身事外才获取继续读书的资助,她预言了自己若是中邪也怨不得旁人的结局。个体与环境的疏离经由一切开始之前的内心活动得以表现,她在整个故事中的行为都带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于梁太太的一切抱有更多的敌意而非接纳认可。两种媒介叙述的差异性,在此体现得更加明晰:小说文字表达的巧妙之处,电影却难以给予准确的视觉化。原作中葛薇龙和周边的疏离从内心深处生发,影片则在人物和背景的清晰与模糊中做文章,视觉上传达的隔膜显然是含糊甚至难以辨认的。当她站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接受裁缝量取身体的尺寸时,当她参加园会讪讪地同乔琪打交道时,当她在蜜月期吹着海风如愿地同丈夫调情……每当镜头特写瞄准女主人公,全部带有指向性意味的、超出葛薇龙原有范畴的事物都被呈现为一个隐约的背景轮廓。太过于隐晦的表达,让观者难以把握导演心绪。
影片中的苍凉被铺垫成葛薇龙一步一个脚印走着姑妈老路,待她结婚后才浑然发觉的梦魇时分。甚至可以说,许鞍华将苍凉替换为小说最初提及的“鬼气森森”,接着在后半段将这种诡异的感觉细致地表达出来。先是姑妈为了物质嫁给年逾古稀的老头,她受尽旧式大家庭的种种屈辱且等待对方死亡的过程,几乎耗尽了生命中饱含活力的青春。这种回忆的出现几乎不分时间和场合,在她一人梦中惊醒的寂寂午夜、空旷华丽又灯火通明的梁宅,在葛薇龙乃至其他人结婚拍集体照时喧闹欢乐的天空下……镜头于过去和当下之间来回切换,预示着过往种种纠缠梁太太的生活,当下的热闹也无法填补当年的死寂,使之不得安宁。其次是葛薇龙在成为交际花,出入各种声色享乐场合时,看见年轻的梁太太那步履和笑容打扮,一如当下的自己。这种年轻与年老,过去和当下的时间交错、人物承替关系,表达出荒凉的现实和无边的诡异。
最能凸显这一“苍凉的鬼气”的情景当属整部电影的爱情变奏。“爱情不可能构成叙事,它只是一番感受,几段思绪,诸般情境,寄托在一片痴愚之中”。[12]对于葛薇龙来说,尽管她的感情早已千疮百孔,但那的确是她追求的爱情,是她为自己构建的精神堡垒。结婚时,凝固在照片上的新郎新娘之笑容略显紧张;蜜月期,目睹乔琪与印度女郎在水中互相爱抚的场景,蓝绿色的天空和海是她惶恐无助、却又无处可躲的灰暗人生;晃荡的船上,体面的人群说笑也无法掩盖破败不堪的内里。过度地将一己生存之道,建诸对另一人的喜欢和爱上,使得看似沉重和高尚的选择又迅速地滑入轻飘而虚无的崖底。导演本意是赋予女主人公一个牺牲的淑女形象和一段挚爱的人生经历,但却导致了另一个极端的形成——过度的完美造就极致的虚假。
四、电影的“形状”与“沉浸感”的追求
电影“作者论”发端于20 世纪40 年代,法国电影评论家阿斯楚克提出:“摄影机应像文学家的笔一样,去自由自在地描写事物,必须具有作者自己的个性,即要确认电影作者的地位。”[13]作者电影有两个较为明显的标识:一是对抗性,导演不受既定模式和类型的禁锢, 大胆创新。二是导演的核心地位,电影要彰显导演个性, 其风格特征明显且具有连续性, 电影蕴含着导演个人的思想内涵。
从电影《倾城之恋》(1984)、《半生缘》(1997)到《第一炉香》(2021),许鞍华对于张爱玲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电影《第一炉香》的改编,如果单从作品本身来讲,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譬如每一帧都足够精美的镜头呈现,给人以极大的赏心悦目之感;化繁为简、移花接木的手法,让原本精致而极富时代气息的内容变得时尚而贴合当下。但是对于一篇有着深远影响力和广大受众的经典文本,它的改编电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精髓,把握的主题和思想是否准确,也是衡量其水平高低不得不考虑的标准。“爱而不得”的赞歌甚至挽歌并非不能写,只是张爱玲的笔下从来没有“为爱情而爱情”的故事:书香之家走出来的上海女学生葛薇龙,聪慧敏睿,对自我的沉沦有着清醒的认知。
作为香港电影圈乃至华语影坛举足轻重的导演,许鞍华是香港七九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导演。因个人特殊的中日混血身份及从小生长在港澳两地的经历,许鞍华电影擅长以“生活流”和完全冷静、客观的视听语言传达“人的流离不安”母题以及在苦难中挣扎求存之时面临的乡情、亲情和传统伦常观念的纠葛,其电影作品常常透露出一种顺承直觉的信仰和局外人的冷漠。因之,影片中葛薇龙对于爱情信仰般的追求也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许鞍华曾经表示反对概念先行,反对电影的“教训”功能,强调电影的形式即内容,同时她很认同电影未来对于“沉浸感”的追求。许鞍华期望的电影的“形状”应该是,“我希望人家在我的电影里头,在一些画面、人等等的配合中感受到一些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某一条线,或者是单一两个人的关系。”[14]于是,我们发现相较于张爱玲文本中葛薇龙单向度的人物链条关系,许氏影片中各色人物之间联系紧密而呈网状交织。有趣的是前者人物关系虽然简单,却暗含复杂的心绪;后者各类人物错综复杂,却只表达一种纯化的感情。
许鞍华影片塑造的傻白甜形象几乎完全偏离原作,但是又服务于她自己的主题:好好地去爱。只能说原文本经由电影这一媒介被印刻了许氏导演的人文关怀风格,她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极富个人化解读意味的《第一炉香》,已经不是张爱玲小说原本的样子。因此,关于这部电影,常常听到的一句评价是,这是许鞍华/王安忆的《第一炉香》,不是张爱玲的。在张爱玲的世界里,葛薇龙对乔琪的爱,不过是她贪慕虚荣、堕入繁华用来“自己哄自己”的借口,在许鞍华导演的这一版《第一炉香》里倒是无比认真地陷入一场“爱而不得”的沉沦。尽管不曾拥有所谓的真纯爱情,许鞍华也依然为大众建构了自己信仰上的爱情,期冀经由情欲理解些许看似荒唐的抉择,进而给千万如自己般的普通人一个生存的“白日梦”。如果说原文本基调于清醒中透出接纳忧伤的冷漠,“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5]那么经由人物形象的改变,影片营造出前期美丽梦幻而后期破碎清冷的氛围,这当然合乎许多人对爱情的理解和生活逻辑,也印刻了一直以来“许氏风格”的人文关怀,但当今的观者却无法接受对经典文本做出的这一巨大改变,导致目前的评分不高。关于诸多负面评价,也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正如著名学者戴锦华所言,“许鞍华的电影不光是半部香港电影史,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记忆,包括许多历史片段的影像画廊。许导影片很有意思但是不强势,每个观众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进入她的电影,继而进入自己的生命,也进入20 世纪中国的历史。”[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