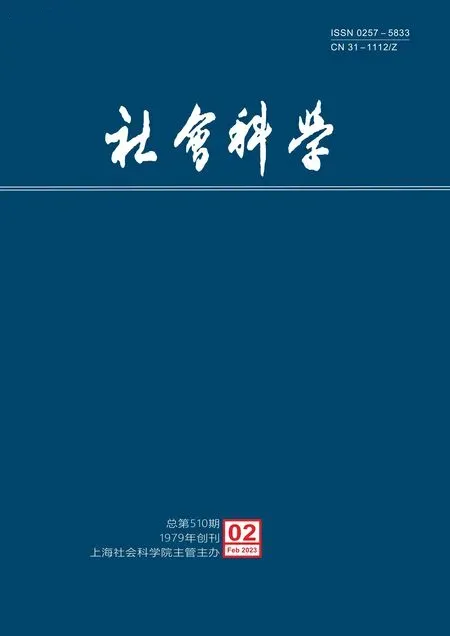“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2023-04-16王坤鹏
王坤鹏
上古中国地广人稀,相关文献记载更多显示了族邦整合或相服属的一面,对早期国家的疆域范围并无太多明确的反映,由此引发了学界有关早期中国国家疆域连贯性的讨论。学者或认为早期中国关于国土只有“点”的观念,尚未形成“面”的观念;①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2 期。或认为战国以前的国家并非疆域式的,只是都鄙式邑群;②林沄:《商史三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 年,第4—6 页。国外学者在研究商王国时亦认为其疆域就像一种瑞士奶酪,遍布着“非商”的孔洞,而非像豆腐那样密实。③David N. Keightley,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No.5, 1980, p.26.上述说法固然能找到一些史料证据,但论证却失之简单,既未纳入大量与之相斥的证据,又无法深刻揭示早期国家疆域形态复杂的面相。早期国家疆域的不连贯性只是一种历史残留,对其片面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深入认识早期中国国家形态的一种阻碍。本文试在前贤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传世与出土资料,对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这一课题再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早期中国疆域形态的相关探讨与辨析
夏商周三代王国的形成是中心邦服属次级邦的结果,此即《尚书·尧典》中所概括的“协和万邦”。①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250 页。所谓“协和”,实指在不同族邦之间通过某些规则建立起一种统一的政治秩序。由此种方式形成的三代王国,从逻辑上讲,其内部不同族邦之间在地理空间上不必是相连的,其间可能存在着尚未纳入王国政治秩序的区域。此即是早期疆域的不连贯性。围绕该点,学界曾进行过一些讨论,涉及三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形态等重大课题。
有学者否定三代时期广域国家的存在,甚至认为其时之人尚未形成有关广大疆域的观念,而主张三代国家只是不同等级的邑的聚合体。例如,王玉哲先生曾认为,商、周王国当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并以之为中心,远近散布着属于王国的诸侯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还散布着不属于王国的许多方国,商、周时人对于国土只有分散于各地的一些“点”的观念,还没有整个领土相连成“面”的观念。只有到了春秋以后,尤其是战国中期,诸侯方国领土扩展到互相接壤的程度,各国的疆域才逐渐由“点”发展为“面”。②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2 期。林沄先生亦有类似观点。林先生所设想的早期国家为“都鄙群模式”,认为早期国家起源于一些由不同等级的邑所组成的都鄙式邑群,邑群之间又形成联盟,直到西周时期,在结成联盟关系的复合都鄙群及简单都鄙群之间,还存在着大片未开垦的荒野。商朝和西周王朝实际上都是由传统形成的交通道路联系起来的结盟方国的网络,而疆域式国家是东周时期才开始形成的。在这种由多个都鄙群组成的联盟中,为首的方国首脑被称为“王”,他只是“国联”的主席,是多国联军的总司令。③参见林沄:《商史三题》,第44—46 页。美国学者吉德炜在研究商王国疆域形态时提出了一种更形象的说法,他认为整个商王国,除了其中心,不会有一个界限明确的领土,就像一种原产于瑞士的格鲁耶尔奶酪,其上遍布着“非商”的孔洞,而并非像豆腐那样是密实的一整块。商王国政体是以个人权力和亲属关系而不是地域来设计的,商王国只是一系列与中心有特殊关系的辖区的聚合体。④David N. Keightley,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No.5, 1980, p.26.
可以看出,上述论点主要是以早期中国疆域形态的不连贯性作为立论基础。如果单独看某些材料,早期国家疆域中的确存在着一时不受王国控制的区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导,的确很容易得出早期国家只是不同势力联盟的产物。学者提出上述这类看法,通常或显或隐地基于以下两种理由:其一是从逻辑上进行推理。这种思路一般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社会上所存在的就是一个个大体均等的邑,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邑开始分化而形成邑群,每个邑群的中心大邑成为“都”,其他次级的邑则成为中心都邑的“鄙”,都鄙群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合或联盟,中国最早的国家应该就是从这样的多层次的聚落群中为首的方国演化而来,反过来又影响到参盟的都鄙群也向国家性质的社会政治组织发展。其二是对考古学文化的面状分布持怀疑态度。田野考古发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遗址点,点与点之间仍是空白的,不能确定是否布满了同一种文化,即使在一片区域内分布着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也不能反映其属于同一个国家。⑤以上两点均可参见林沄先生的论述。林沄:《商史三题》,第36—45 页。
前者的推论看似合理,实际上并不可取。从时间上来看,自新石器时代前期邑聚产生至史书记载的夏王朝时期,中间历八千余年,邑群组织出现于何时、又在何时结成联盟等均无实证。即使从逻辑上来推理,若说在此八千余年间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只是邑的分化与联盟,甚至连广大疆域的观念都未产生,则明显是不可信的。至于后者,黄铭崇已据商代后期的相关考古发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检讨:其一,殷墟与华北平原同时期存在的其他聚落相比从尺度上看是不对等的,例如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济南大辛庄面积只是殷墟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其二,殷墟是华北平原同时期遗址中,唯一有大规模青铜礼器作坊的地点,华北平原大多数聚落出土的晚商青铜器,风格相当一致,可能都是在殷墟制作;其三,殷墟以外有许多族氏分封的地点,这些分封的族氏虽然距殷墟少则80 公里,最远者超过400 公里,但是他们都遵守与殷墟相同的秩序——商王朝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从考古资料来看,到目前为止,华北平原尚未出现过一个“非商”的都邑能够堪称商王朝的同侪政体。①参见黄铭崇:《晚商政体形态的研究——空间模型的考察》,《新史学》2011 年第3 期。
总的来讲,上述关于早期中国疆域形态的看法虽然注意到了其时疆域具有不连贯的现象,反映了王权衰落之时所产生的某些疆域割裂的情况,但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是以历史残留来代替历史全貌。对于早期中国不同政治组织间的关系,如果仅仅以联合或联盟来概括,既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大大削减了早期国家疆域形成过程的丰富内涵。另外,也不能仅以王权衰落时期(例如春秋时期)所存在的疆域割裂、次级邦各自为政的情况来佐证王权强盛之时亦是如此。讨论早期国家疆域这一问题,还应回到实际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入考虑历史发展趋势以及早期疆域形态的丰富性、多层次性等特点。实际上,若综合更多资料以及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奶酪”状的疆域并非常态,早期国家疆域的密实程度或统一程度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加强,夏商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广域国家。
二、早期中国“广域”国家形成的证据
如果说二里头文化遗存或其主体部分属于夏王国的话,则夏时期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其后商、周只是进一步拓展并充实了王国疆域。早期国家疆域形态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愈往后其疆域变得越密实,中间的空隙地带愈少,而且密实化疆域形态的产生不会太晚。在殷商黄类卜辞中,已记载有“土”的概念:
己巳王卜贞: [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②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 年,第36975 号。下引该书皆简称《合集》。
过去学者或认为卜辞中的东、南、西、北四“土”是指距商都不远的区域,③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337 页。此认识可能有误。上引卜辞中的“商”,既然说到“受年”(即获得丰收),应是农业区,自然非指商都本身,而是指以商都为核心、拥有周围农业区的商邦。那么与商邦相对应的四“土”就不是商都附近之地,而是指商邦之外受商王廷控制的四方区域,大致相当于文献所记的“外服”之区。西周时期仍延续了四“土”的概念,《左传》昭公九年云:“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④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66 页。此四“土”均远离周的核心区。另《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周宣王册封申伯:“我图尔居,莫如南土”,⑤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 之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22 页。据朱凤瀚先生的研究,“南土”是周王国在南方的领土,大致在淮水以北,包括申伯所驻守的南阳盆地。朱先生亦指出,周人以方向加“土”的命名方式与殷墟卜辞所见商人所称的四“土”相近。⑥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 年第4 期。商王占卜四“土”能否获得好的收成,显见四“土”与商王有密切关系,应属商王国的疆域。“土”指一定范围的土地,译成今词,实即领土。四“土”之上虽或存在着某些由商王派驻行使治理权的贵族及其族邦,但卜辞所言为“土”,而非“邑”,反映了商王并非只关注具体的邑,其所关注的还包括成片的领土。
西周时期已形成广域国家的证据更为丰富。周克商并征服了东方广大地域,其征伐所及的大部分土地也就成了周王国的疆域,是以周王可以将东方的民众和土地赐予贵族。例如以下两篇铭文:
唯三月,王令荣眔内史曰:“匄井(邢)侯服,赐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井侯簋,《集成》4241)
如果说上述赏赐土地和民众之事仍只能间接反映周王国占据着广大疆域的话,那么西周时期在东方地区广泛册封及徙侯之事则是更为直接的证据。西周早期的宜侯夨簋记载了周王国“迁侯于宜”之事: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入土(社)南向。王令虞侯夨曰:“迁侯于宜。”……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赐在宜王人□又七里,赐奠七伯,厥卢□又五十夫,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集成》4320)
宜侯夨簋铭文中的王是周康王。铭文记载康王省览武王、成王时期伐商的相关地图以及周东国区域的地图,之后即命令虞侯夨迁侯于宜地,并赏赐给他土地、人口等。从铭文可以看出,周王廷保存着东方广大地域的地图,周王通过观览地图,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或调派诸侯以治理地方。
《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周宣王册封申伯:“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②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 之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21—1222 页。周王将申伯册封到南土的谢邑以作为周王国在南方的屏障。诗言“我图尔居,莫如南土”,与宜侯夨簋铭文中周王观览地图后将虞侯“迁侯于宜”是同类事情,可能也是在观览南国地图后做出的决定。周王可以根据统治的需要将贵族封派到地方并根据需要将其迁转至他处,恰能反映周王所领有的是广大的疆域,而非仅是若干据点或交通网络。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沈尹戌的言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③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67 页。其中所说的“古者”至迟是西周时期,其时“天子—诸侯—四夷”的政治等级及相应的疆域层次已经形成,所谓“天子守在四夷”,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广域的疆域形态。如果周邦与其他族邦之间仅是联盟关系,周人的“天下”“受命”“明德”“保民”等观念便无从谈起,似乎就成了周人某种自大狂妄的想象,而史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三、早期中国的疆域观念与边界意识
虽然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具有一定模糊性或者经常发生变动,但并非全然无规则可循,也不能由此认为当时就没有边界意识。有学者曾提出,商王为农业收成进行占卜的区域可能就是与商王国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地区。④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234 页。统治者是否能从中收取贡赋,应是判断其地是否属国家疆域的一个重要标准。另外,与殷商国家疆域有关的,还有文献所记的“内服”与“外服”。《尚书·酒诰》记载周初周王之言:“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9 页。“服”义为职事,“内服”与“外服”都是商王国设官以治理的范围,只是据实际情况将疆域划分为内、外两层,施行不同的治理方案而已。商王廷既然在其地设置职官,其治理对象及范围大体应是清楚的。当然,王国内层或外层的疆域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动,但不能说没有边界。
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 孳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 孳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集成》260)
铭文记载周厉王省视南方疆土,认为南夷、东夷这些族邦占据了周王国的土地,是以对他们施以征伐。西周晚期周王国与南淮夷之间的战争具有复杂的原因,经历了长期的过程,铭文所说的征伐理由不一定完全就是事实。不过铭文却显示了周王国的疆域观念,至少是周王等贵族阶层对何处属于周的疆土有着清晰的认知,故铭文直言“我土”。类似的观念亦见于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文:
铭文中的兮甲,因征伐玁狁及管理成周地区的征贡事务而受到周王的奖赏,故有此器的铸造。铭文自“淮夷旧我帛亩人”至“则亦刑”的部分,介绍了周人处理淮夷相关事务的一些政策,从语气来看,可能出自周王的命书。①西周贵族制作铜器时,常将周王的命书或其他诸如土地交易等文书节略或截取部分内容制成铭文。参见李峰:《西周的读写 文化及其社会背景》,《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11—128 页。铭文讲到淮夷“进人”即为周王国提供人力资源,“贾”意为商业交易,淮夷的“进人”大概亦属商业交易的一种。从铭文可以看出,周王国对周人贵族与淮夷的接触或交易有着严格的规定,交易行为要在“市”“次”等特定场所进行,不允许擅自进入对方领域私下交易。此种规定显示了周王国对己方及淮夷各自的地域有着较清晰的界定。
至于早期国家的边界具有一定模糊性,有多方面的原因,诸如地广人稀、不同族群社会与政治发展水平不均衡等,但这并不等于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考虑疆域边界的问题。实际上,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对其统治的边界还是比较清楚的。《说苑·辨物》记载了一则小故事,与早期国家疆域有一定关联: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盈车,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问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一乎?”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②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457—458 页。
《说苑》由西汉学者刘向搜集、整理流传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多种资料编纂而成。③刘向《说苑序奏》称:“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 别次序……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孙诒让曰:‘新事’当作‘新书’)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 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参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说苑序奏”第1 页。与上述史事相似的记载还见于《尚书大传》④参见《太平御览》卷785“四夷部”六所引。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785,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3475 页。《韩诗外传》⑤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80 页。等文献,反映了这一故事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古文《尚书》有《归禾》《嘉禾》两篇,《书序》云:“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6 页。上引这类故事大概就是缘《尚书》两篇记载再创作而成,其中所录的周公言论或即本于古文《尚书》。引文周公之言,所谓“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不能施加政令的地区即不能算作国家统治的对象,说明早期的政治统治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模糊、没有规则可依,对某地能否施加政令是统治者判断该地是否为其疆域的前提。
夏商周三代国家与秦汉国家的差别主要在统治的方式与强度上,广土众民的疆域模式既是前后相继的,也是前后一贯的,其间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断裂。故两个时期在处理疆域及族群问题时的政治逻辑是相似的,与上述引文类似的情况在汉代也曾发生过。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率部款塞。关于如何安排匈奴单于,汉朝君臣经过一番商议后,最终按大臣萧望之的意见处理:
Analysis of ecological wisdom of Quanzhou traditional houses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①班固:《汉书》卷78《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3282 页。
从这段史料来看,西汉王朝并未将衰落的南匈奴视为其治下的臣属,而是以“不臣之礼”待之,主要考虑的也是汉王朝未能对匈奴之地施加有效的治理。《白虎通· 王者不臣》引《尚书大传》云:“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②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318 页。所谓“正朔不加”即上引《说苑》“政令不施”。尚未建立有效的统治,就不能将之作为臣属来对待,此当为上古乃至秦汉处理疆域问题的一项通例。
四、早期中国的“疆”“略”之别
承认夏商周三代国家已具有广大疆域,并不是否定其时疆域具有模糊性及多变性等特征。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相较于不连贯性,早期国家所具有的“疆”“略”之别这一特征当更具代表性,对后世疆域形态及边疆治理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疆”字本义指土田间的划界。《说文》云:“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疆,畺或从彊、土。”③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3 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291 页。商代甲骨文有“ ”字,④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744 号。会田与田相界划之意,或作“ ”(《合集》27879),从田,上下两横划指示田界。西周大盂鼎铭作“ ”(《集成》2837),添加“弓”形为声符,字转为形声。春秋时期秦公簋铭文中作“ ”(《集成》4315),又增加“土”旁为义符。⑤关于古文字“疆”的说解参见季旭昇:《说文新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954—955 页。关于甲骨文中的“ ” 字,相关工具书多列为未识字,本书采纳季先生的意见。另《殷虚书契后编》下2·17 残存一字“ ”,从“弓”从“畕”,或 认为即“疆”之原字。惟卜辞残缺,义不可晓。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3 版),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 年, 第1474—1475 页。从字形看,疆的本义指田间的分界或整理、划分土田的分界。《诗经·小雅·信南山》云:“疆埸翼翼,黍稷彧彧”,⑥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3 之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11 页。疆所指的就是田界。《诗经·大雅·緜》云:“迺疆迺理,迺宣迺亩”,⑦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6 之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98 页。疆理即划分与整理土田的界划。在此基础上,“疆”衍申出边界及疆土等义项。《尔雅·释诂下》云:“疆,垂也”,⑧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02 页。《礼记·曲礼下》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7 页。疆均指国家的边界。
殷商甲骨文中涉及“疆”的辞例不多。《英国所藏甲骨集》第744 号作:“…… ……于畕。”⑩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第744 号。有学者认为“畕”字“似为地名”。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2135 页。上引《合集》27879 刻辞有残缺,行款亦较散乱,学界读法不一,我们赞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的意见,将“翌日”句单列为一条,⑫姚孝遂主编,肖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823 页。如此,则整片卜辞可读为: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疆”亦有两种内涵。其一为土田的界划,例如五祀卫鼎铭云:“厥逆疆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政父田,厥西疆眔厉田。”(《集成》2832)其二为疆土、疆域,例如大盂鼎铭云:“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越我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集成》2837),又例如周厉王胡钟铭:“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集成》260)。这两种内涵之所以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能够征收赋税的土田之区便是早期国家实施统治的区域,即为疆域。周代所说辟疆仍具有最初的内涵,即开辟可以征收贡赋的土地。《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高本汉认为:“‘辟’的意义一定是‘开闢’,不过是‘开闢田地’的意思。”④高本汉著,董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983 页。诗篇谓召伯虎在江汉水滨接受王命,开辟四方并在开辟的土田上征收贡赋。所谓“疆土”主要指已整治、可耕作的农业区。
综上所述,“疆”由田界之义引申出疆土、疆界等内涵。“疆”在上古时期与农业经济有密切关联,商、周王国所统治的疆域一般即是开展农业生产并征收贡赋的区域。也可以说,“疆”是早期国家设置治理机构、实施稳定统治的区域。
早期国家在“疆”之外复有“略”。“略”的内涵与“疆”有所不同,其在早期文献中常用来表示国家等势力攻伐或影响所及的区域。可举以下数例:
(1)《左传》隐公五年云:“公将如棠观鱼者……公曰:‘吾将略地焉。’”杜预注云:“略,总摄巡行之名。”孔颖达疏云:“言欲案行边竟(境),是孙(逊)辞也。若国境之内不应讥公远游,且言远地,明是他竟(境)也……盖宋、鲁之界上也。”⑤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49 页。据注疏,“略地”指鲁君巡行沿边地区尚不属于鲁的土地。这种“略地”,并非将其地变为国家的疆域,目的应只是巡查边疆并向域外扩展本国的影响力。
(2)《左传》僖公九年云:“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⑥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08 页。所谓“不务德而勤远略”即指齐桓公不修国内事务而好向外征伐以扩大齐国霸权的影响。“远略”就是指下文的伐山戎、伐楚、召集盟会,“东略”即向东方攻伐其他族邦。可见所“略”之区实在本国疆域之外。
(3)《左传》僖公十六年云:“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⑦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25 页。所谓“东略”,即齐国会集诸夏联盟打击东方的淮夷小邦。其所“东略”的淮夷之区显非齐国的疆域,充其量只是齐国影响所及的地区。
(4)《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郑厉公平定周王子颓之乱:“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杜预注称:“略,界也。郑武公傅平王,平王赐之自虎牢以东,后失其地,故惠王今复与之。”孔颖达疏云:“言武公之略,则是武公旧竟(境)。”⑧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50 页。注疏将“略”释为郑的疆域是有问题的,所谓虎牢以东为“武公旧竟(境)”、郑“后失其地”并没有根据。“武公之略”实是西周末年周人向东方转移过程中,郑武公匡正东方诸侯时所建立的势力范围而已。清华简《系年》云:“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⑨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第138 页。郑武公匡正东方诸侯,实是作为宗周的代表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其所略之地当属周王室而非郑的疆域。①参见王坤鹏:《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兼说〈左传〉“艳而富”》,《殷都学刊》2015 年第3 期。正是因此,后来周惠王才得以将这些土地赏赐给郑厉公,并不存在郑“后失其地”的情况。
(5)《左传》宣公十五年云:“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②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098 页。狄指赤狄潞氏,此前灭掉了黎侯国。晋于鲁宣公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复立黎侯。所谓“略狄土”,实谓晋以强力将狄地纳入自己霸权范围内。晋国所“略”的狄地并非晋国实施有效治理的疆土,最多只是晋的新附区。也正是因此,晋在黎地复立了黎侯。
(6)《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云:“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杜预注:“略,行也。行吴界,将侵也。”③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74 页。“略”指楚国进入吴国疆域宣示霸权,兼之抢掠人、财、物等。文献直言所“略”对象为“吴疆”,显然非楚疆域,至多是楚王宣示霸权的势力范围。
从以上史例可以看出,早期文献中“略”的对象并非指本国设立统治机构的区域,所“略”之区只是该国的附属区,而非其原有疆域。春秋时期的霸主与商周之王有一定相似性,在王国外围亦存在类似的附属区。《左传》昭公七年记述周代制度:“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④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47 页。天子与诸侯在西周政治体制中地位不同、职能有异,“经略”与“正封”一虚一实,正可反映早期国家“疆”“略”有别这一特征。“经略”倾向于强调周天子负有向四方特别是异族所处之地进行开拓的责任,并非实指周王国所能施治的疆域,其内涵类似《诗经·小雅·北山》“经营四方”及《大雅·棫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而“正封”之“正”意为治理,⑤《礼记· 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正”为使动用法,意为使之正,即治理之意。杨伯峻已指出此点,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1115 页。“封”意为封疆,“正封”指设置封疆并加以治理。周天子委派诸侯治理某一区域,设立统治机构,则其地确凿属周王国的疆域。“经略”针对的是“略”,是影响所及之区或附属区,其地尽可以广泛;而“正封”针对的是“疆”,则要有确切的范围。
相较不连贯性,“疆”“略”之别实为夏商周三代国家疆域形态一个更重要的特征。“疆”之内一般是商、周王国设置治理机构、征收贡赋、实施稳定统治的地区。而“略”则是王国势力有所攻伐或施加一定控制的地区。由于没有常设机构从事有效的政治管理,“略”尚不算是王国的疆域,不过却是王国势力所及的范围,也是其疆域盈缩区。一旦中心王国势力强大,往往会加强对这些区域的控制,存在将其变为疆域的可能性。但也应注意到,一旦中心王国势力虚弱,外围方国族群势力兴起,以前的“疆”也有退回为“略”的可能。上古国家的改朝换代实际上亦只是“疆”“略”的重置而已。当原处于“略”之内的方国强大起来,取代了中心王国,原来被视作边缘的“略”成为新国家的疆域,“疆”“略”的范围便会重新划分。
结 语
有学者认为夏、商、周三代国家只是不同规模的邑的聚合体,否定三代时期广域国家的存在,进而认为早期中国疆域的主要特征是其不连贯性。学者之所以会形成这类看法,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将早期国家发展过程简化为“邑—都鄙—都鄙群”的发展线条,另一方面则是将此过程投射到夏商时期。实际上,自新石器时代前期邑的广泛形成至夏王朝建立,其间已历八千余年,并无证据表明上述发展过程延至夏商时期仍在进行。相反,有大量证据反映夏商时期已形成广域国家。
夏王国的建立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只是进一步拓展并充实了此疆域。据卜辞所记,四“土”与商邦相对,显然是指四方较广大的地域。商王占卜四“土”的农业收成,反映了商王并非只关注具体的都邑,其所关注的还包括成片的领土。西周时期的疆域情况更为明确,周王可以将东方的土地和民众赏赐给贵族,亦能根据统治需要将侯伯册封或移封至东方、南方较为遥远的地区。为便于疆土的治理,周王似已掌握了东方、南方等广大地域的地图。
虽然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存在一定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更不能认为当时不存在疆界意识。商代有“内服”“外服”,“服”义为职事,显示其地均是商王廷设置官长加以统治的地区,即商王国的疆域。西周铜器铭文中有“我土”观念,周人与淮夷的交易场所有专门的规定,这些不仅反映出周人具有疆域意识,也说明周王等贵族阶层对何处是周人领域、何处非其领域有着清晰的 认知。
夏商周三代国家与秦汉国家在疆域形态与疆域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其区别主要在统治的方式与强度上。两者广土众民的疆域模式是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其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断裂。故三代国家与秦汉国家在处理疆域及族群问题时的政治逻辑也多有相似之处。
相较不连贯性,早期国家疆域更突出的特征是“疆”“略”有别。“疆”由田界之义引申出疆土、疆界等义,在上古时期与农业经济有密切关系。“疆”内一般是商、周王国设置机构、征收贡赋、实施稳定统治的地区。而“略”则是中心王国不时攻伐或施加一定影响的地区。“略”尚不算是王国疆域,不过却是王国势力所及之区,也是其疆域盈缩区。一旦中心王国势力衰落,原处于“略”之内的族邦势力兴起,就可能建立新的王国,重新区划“疆”“略”,故上古时期国家的改朝换代从某种角度看亦只是“疆”“略”的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