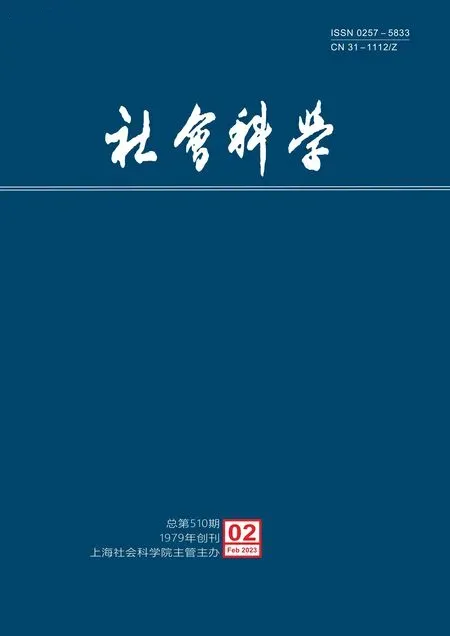天道与经世*
——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2023-04-16陈畅
陈 畅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思想争鸣时代,“天崩地解”的政教危机以及西学传入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都极大地激发了时代的思想活力。对于包括天道、上帝、魂魄等观念在内的“天人之际”思想(本文称为“天学”)的重新讨论,就是其中的热点。明清之际的“天学”讨论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就后者而言,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以天主教绝对超越性和创世者概念为标准,突出中国六经传统固有的上帝或天之信仰成分,以达到“使原作顺从”天主教概念的目的。这个传教策略引发了中国士人的激烈反驳,催生了钟始声(蕅益智旭禅师)《辟邪集》、杨光先《辟邪论》等理论辨析著作。①郎宓榭:《利玛窦和杨光先》,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办公室合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1 年,第234—250 页。清初大儒黄宗羲(号梨洲,1610—1695)晚年最后一部著作《破邪论》与上述著作名字相近,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又有极大不同。黄宗羲自述此书主题是“天人之际”思想,他在此书中对上帝、魂魄观念以及民间迷信诸“邪说”展开严厉的批判和清理,以破邪显正的方式阐述了其对“天学”思想的崭新理解。事实上,黄氏此书更多的是针对中晚明以来深受阳明学宗教化思潮影响的各种世俗观念的批判,天主教观念只有其附带提及的极少部分。
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对黄宗羲《破邪论》文本有诸多误解,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刻意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其实,黄氏文本主要是对其师刘宗周(号蕺山,1578—1645)为代表的晚明心学之继承和独特发挥,代表了明清之际儒家“天学”的新视野。本文将围绕《破邪论》几个核心观念展开分析: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本文的研究将表明,黄宗羲的昊天上帝观念强调气之理的自为主宰意义;而魂魄与精神观念,则强调精神的客观化进路。两者结合在一起,展现了黄宗羲全新的天道观念;既坚持了儒家传统的立场,又体现出阳明学派心学在明清之际大变革时代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昊天上帝:气之理的自为主宰意蕴
众所周知,“天学”思想侧重关注个体存在与天道、天命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议题。明清之际思想家特别是黄宗羲对于“天学”的重新讨论有其特殊的思想史语境,需要细致的梳理。由于该时期“天学”讨论有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天主教思想两个独立的思想源头,虽然后来两者有合流的趋势,但是在黄宗羲思想中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指出,黄宗羲《破邪论》涉及对天主教思想的吸收,如在论证上帝存在及以灵魂不灭论述魂魄等方面即是。①刘耘华、陈受颐、许苏民等学者持此说。参见刘耘华:《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94 页。陈受颐、许苏民之说,参见许苏民:《黄宗羲与儒耶哲学对话》,《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4 期。这类研究的特质是突出黄宗羲“上帝”观念中的“主宰”含义,将其与天主教教义中作为创世者的上帝主宰万物的含义等同起来。黄宗羲一生致力于学术经世,他对当时经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科学和宗教思想亦有深入探讨。学界研究表明,黄宗羲与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游,并广泛涉猎经由传教士传入的西学著作。②徐海松:《黄宗羲与西学》,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夏瑰琦:《黄宗羲与西学关系 之探讨》,吴光等主编:《黄梨洲三百年祭》,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但这并不意味着《破邪论》是在吸收天主教思想的语境中完成的著述。黄宗羲一生的思想事业,以破解中晚明阳明学过度伦理化与宗教化所导致的丧失经世致用功能之弊端,恢复儒学治平天下的本来面貌为职志。③参见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陈畅:《方学渐心学的 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 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并且从《破邪论》文本来看,黄宗羲主要是针对当时儒学和世俗流行的神道设教思想展开专门批判,这与他的学术职志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把黄宗羲《破邪论》理解成吸收天主教上帝观念而撰写的文本,那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想象。
黄宗羲的“天学”论述只有被放回到中晚明阳明学发展脉络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阳明学的过度伦理化趋势源自阳明四句教的思想结构;④参见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陈畅:《方学渐心学的 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 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而阳明学过度宗教化趋势则是源于阳明后学对“心即理”原则之现实有效性的反思,由此发展出依赖外在超越力量来完善道德人格的思想路径。吴震先生的研究指出,泰州学派罗汝芳“上帝日监在兹”观念的提出,实际上代表了中晚明时期阳明学者对良知自力的怀疑,并由此导致敬畏上天的“敬天”思潮之发端。其世俗影响是演变为“化儒学为宗教”“融宗教于伦理”的劝善运动,各种“功过格”“感应篇”“阴骘文”等道德实践手册盛行于明清之际,当时占据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既有早期中国传统的上帝观念、儒家的伦理说教,也有佛家的轮回果报、道教的阴府冥司等观念。⑤吴震:《罗汝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03—429 页;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4—6 页。刘宗周的代表作《人谱》就是针对袁了凡《功过格》“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惑人为甚”⑥刘宗周:《人谱》,《刘宗周全集》第2 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 年,第1 页。之弊端而撰写的拨乱反正之作。黄宗羲《破邪论》在思想立场和理论命意上与其师作品是一致的。因此,《破邪论》“天学”论述的问题意识就是:如果说阳明学的过度宗教化(伦理化)是黄宗羲所要解决的学术弊端,那么如何依靠本心良知取代“上帝日监在兹”的宗教意识,进而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目标。
厘清了黄宗羲“天学”论述的思想史背景和问题意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是围绕《破邪论》文本展开细致研究,进而回到文本产生的思想史现场。在黄宗羲思想中,上帝与天是同义语,而用法稍有区别。这是继承自刘宗周的理气论思想。理气论是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明清之际最富有创造性的哲学理论。黄宗羲曾自述其《明儒学案》之撰述“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10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78 页。事实上,黄氏其他哲学著作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把黄宗羲的论述置于其师门学术语境中,方能全面彰显其思想内涵。黄宗羲《破邪论》论“上帝”称:
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②黄宗羲:《破邪论· 上帝》,《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4 页。
《破邪论》是黄宗羲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可能是由于精力不足的原因,此书许多地方的论述文字过于简略。对比黄宗羲其他著述,上引文更加完整的表述是:
天地间只有一气,其升降往来即理也。人得之以为心,亦气也。气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荣枯,寒暑之运行,地理之刚柔,象纬之顺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气之自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间气之有过不及,亦是理之当然,无过不及,便不成气矣。③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崇仁学案三· 恭简魏庄渠先生校》评语,《黄宗羲全集》第7 册,第42 页。
“天一而已”是指“天地间只有一气”。有学者把黄宗羲“天一而已”解读为天主教的“一”天说,认为其带有较明显的天主教上帝观念的情感意志色彩。④刘耘华:《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第194 页。这种解释实为误读。实际上黄宗羲此处提法源自刘宗周,这在其晚年与中年阶段都是一以贯之的。刘宗周称:“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谓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谓之意。”⑤刘宗周:《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522 页。“意”是刘宗周哲学的核心概念,本文暂不论及。在中国思想史上,东汉郑玄与曹魏王肃分别提出上帝有六位的“六天说”与上帝只有一位的“一天说”;至隋唐时期“一天说”获胜,其名称也固定为“昊天上帝”。⑥李申:《God 与上帝——中西宗教比较研究》,《科学与无神论》2017 年第2 期。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天一”说,是指日常语言中对“天”有各种称呼,但其实质是统一的;就其主宰含义而言,这个统一的“天”又被称为“帝”或“昊天上帝”。刘宗周、黄宗羲所说的“主宰”,是指气之运行秩序和条理。升降往来是指阴阳阖辟、事物变化之秩序条理。每一事物都围绕其自身的秩序条理而变化,如气候按照春夏秋冬之次序往复,纵使其间会存在着一些偏离秩序的过与不及现象,如夏季突发降雪、冬季偶尔酷热之类,也属于正常现象;但秩序条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样态,如牛、马、桃、李有各自的样子,它规定着事物的存在。因为秩序条理是每一事物自身所蕴含,故而称其为“自为主宰”。秩序的主宰义,称为“理”,又称为“太极”。太极并非超越于气的存在,而是气之秩序条理,亦即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气。称之为太极,是因为在发生学和源起的意义上讲,“盈天地间皆气”,太极和理不在气之外,本无所谓太极和理,刘宗周将这一层意义称为“性无性,道无道,理无理”;⑦刘宗周:《会录》,《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608 页。但就存在的根本意义而言,作为气之理想状态的太极与理,规定和主宰着气的存在。因此“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本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⑧刘宗周:《圣学宗要》,《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268 页。这种对于太极和理的规定,既能保证理则的主宰性,又能随顺万物(气)而不失其真;其目标是彰显生生不息、活泼泼的形上真实存在。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将这一特质描述为“主宰亦非有一处停顿,即在此流行之中”,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黄宗羲全集》第8 册,第891 页。刘宗周解释称:
天有五帝,而分之为八节、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没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处。⑩刘宗周:《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522 页。
此处“天有五帝”的提法并非《破邪论·上帝》中所批评的《周礼》、纬书和郑玄之“五帝”,而是源自《孔子家语·五帝》记载老聃之言:“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八节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十二辰即十二地支,春秋时代开始以十二支纪月,“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就代表万物从生发、繁茂、成熟、衰败,再到重新萌芽的过程。“帝出乎震”一句出自《周易·说卦传》,意指万物在天帝(北斗星)指向震位(东方)时开始生发,指向巽位(东南方)时长势洁齐,指向离位(南方)时成形,指向坤位(地)时长成以蓄养劳作,指向兑位(西方)时成熟喜悦,指向乾位(西北方)时阴盛阳虚短兵相接,指向坎位(北方)时归藏,指向艮位(东北方)时终结和重新萌芽;上述过程在节气上分别对应八节。刘宗周以万物生长化育的客观规律来描述主宰(帝)的内涵,由此论述主宰不是别有一物,而是在万物生长过程中呈现。此即“即主宰即流行”体用观。在这一意义上,主宰概念强调的是存在的真实内涵,反对将天理抽离活泼泼之现实生活。刘宗周、黄宗羲将后者称为“臧三耳”之举,这是明确批判朱子学者的“性即理”学说。在他们看来,朱子学者“理生气”之类的命题把“理”“性”都对象化了,在气(情、心)之外另寻“太极”(理),而对象化的结果则是把性情、心性割裂开来,使“太极”脱离流动的、活泼泼的现实基础(情)而成为“逃空堕幻之见”。①刘宗周:《学言中》,《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492 页。黄宗羲:《孟子师说》卷3“道性善”章,《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 78 页。当事物急剧变化、社会历史发生大的变动时,这种“逃空堕幻”的性理难免与现实发生乖离,流而为僵化拘执的观念。此即朱子学“惨刻而不情”②刘宗周:《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刘宗周全集》第3 册上,第23 页。流弊的理论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在《破邪论·上帝》中称:
今夫儒者之言天,以为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诗》言“天降丧乱”,盖冥冥之中,实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时将颠倒错乱,人民禽兽草木,亦浑淆而不可擘矣。古者设为郊祀之礼,岂真徒为故事而来格来享,听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实不虚者存乎其间,恶得以理之一字虚言之也。③黄宗羲:《破邪论· 上帝》,《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5 页。
“今夫儒者之言天”是指朱子学者;“冥冥之中,实有以主之者”就是上文所述每一事物自为主宰。清初从官方到民间皆盛行朱子学,排拒阳明学,这一学风对阳明学者造成不小的思想压力。例如,在此种压力之下,刘宗周之子刘汋甚至试图修改刘宗周文集,将其往朱子学方向靠拢,从而引发刘门弟子的群起批评。④详参李纪祥:《清初浙东刘门的分化与刘学的解释权之争》(李纪祥:《道学与儒林》,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年)、孙中曾: 《证人会、白马别会及刘宗周思想之发展》(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8 年)、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在刘宗周、黄宗羲看来,朱子学者的性即理思想决定了其“以理言天”之举无异于在真实存在之外悬空求一物,以之为存在之主宰,这就走向了“逃空堕幻”之虚构。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强调主宰的真实不虚含义,目标在于说明仁、义、礼、智、信不是抽象的名目,而是充盈着真实的情感作为内容。故而黄宗羲说“恶得以理之一字虚言之”;刘宗周也说:“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谓之性本无性焉,亦可。虽然,吾固将以存性也。”⑤刘宗周:《原性》,《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330 页。这种“性本无性”的存性观,从本体的层面确认了“气”的自我延展与自我更新,赋予每一个体性事物以内在创造力与自由,其理论旨趣是一团生气、生生活泼的宇宙。
事实上,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理气论是阳明学派心学内部催生出来的气学思路;笔者的前期研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独立于理学和心学的气学之诞生,而是代表着阳明心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理论意义是力图解决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⑥参见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从本节的讨论来看,黄宗羲理气论在根本上与阳明心学的哲学立场是一致的:强调活泼泼的、真实不虚的力量,反对在人心之上另设一个超越的理体。这是黄宗羲坚持阳明良知学自由体悟的基本立场之表现——任何外在的教条、人格神观念都是良知发用的障碍,应加以破除。换言之,黄宗羲的“昊天上帝”观念并非在提倡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越主宰,而是回到阳明心学的立场。
二、魂魄与精神:精神长留天地的客观化进路
前引文中“古者设为郊祀之礼”,是在祭祀与教化的实践层面谈论天道之主宰性。正是在祭祀与教化的层面,黄宗羲简略批评了“天主”。实际上,黄宗羲对“邪说”的批判是分别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是哲学形上学层面,另一个是祭祀与教化的实践层面。他并没有像钟始声、杨光先那样,在形上学的层面与天主教观念展开辨析,而是在祭祀与教化的层面安顿和批判之。黄宗羲认为,天主教所论之天主实际上不过是作为中介者的“人鬼”:
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记其事,实则以人鬼当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此等邪说,虽止于君子,然其所由来者,未尝非儒者开其端也。①黄宗羲:《破邪论· 上帝》,《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5 页。
《破邪论》中提及天主教的地方只有上引寥寥两句话。黄宗羲强调祭祀场合“真实不虚者存乎其间”,除了是心学立场的表达,也是坚持儒家传统的观点:祭祀是教化之本,侧重性情的陶冶。人在祭祀过程中恭敬虔诚、纯化情感,自然能感格神灵。感格神灵有其规则:“天地间无一物不有鬼神,然其功用之及人,非同类则不能以相通。”②黄宗羲:《孟子师说》卷7“民为贵”章,《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60 页。在祭祀礼仪中,人与鬼神不是同类,两者的相通需要中介。中介者就是死去的人士,包括祖先和历史上死后被神化的人物,这就是人鬼。例如,句龙死后被奉为社神,弃死后被奉为稷神,祭祀既是纪念其功勋,也是借其与天地相通。黄宗羲认为,天主教的上帝观念除了类似于朱子学者悬空求一物以言主宰,更在于混淆了两个层面,即把作为中介的人鬼错置于形上学层面。对他来说,这些错误观念之所以能得到传播,根源在于“吾儒”的理论缺失:自家有错误理论在广泛传播,外来的相似学说自然得以传入流行。因此,当务之急是批判“今夫儒者”,天主教尚无此紧迫性。
黄宗羲对祭祀原理的理解,是建立在其元气论基础之上的。刘宗周、黄宗羲对鬼神做出彻底理性化的解释,他们认为,鬼神和太极、独体、几希一样都是对“天命之谓性”的描述:以其情状而言是鬼神,以其理而言是太极,以其恍兮惚兮而言是几、希,以其位而言是独。“情状”是情形、状况之意,出自《易传·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北宋大儒程颐认为,“《易》说鬼神,便是造化也”。刘宗周、黄宗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鬼神之情状”是指一阴一阳流行过程中的似有灵觉与意志的赏善罚恶:符合秩序为福、为善,有过不及为祸、为恶。这是以事物秩序为标准的福祸观,赏善罚恶、好善恶恶是事物真实存在的内在要求,是万有不齐中的一点真主宰,其中的主宰者是每一事物自为主宰。③详见程颢、程颐:《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288 页;刘宗周:《学言上》,《刘 宗周全集》第2 册,第449—450 页;黄宗羲:《孟子师说》卷3“道性善章”,《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77 页。这种理解源自东林学派集大成者孙慎行,黄宗羲认为,这是孙慎行“有功于孟子”的创见之一。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9《东林学案二》,《黄宗羲全集》第8 册,第813—814 页。关于孙慎行思想对于黄宗羲之师刘宗 周的影响,详见陈畅:《孙慎行慎独学的义理结构》,《中国哲学史》2009 年第2 期。究其实质,黄宗羲所理解的祭祀,重点不在于与外在超越力量的某种“沟通”形式,而是侧重激发“自为主宰”的万物秩序所拥有的神妙转化力量。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论可概括为两个面向:转化自我与转化世界。在黄宗羲所坚持的心学立场,这个转化力量来自良知心体,而不是外在的超越上帝。黄宗羲论述的特别之处,表现在将其引向一种客观化的历史文化之学。此即见于《破邪论》对魂魄、精神观念的独特建构。
总体而言,黄宗羲在魂魄与精神议题上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学的基本论述,并做出了独特的阐发。以气论魂魄是先秦思想的通行观念。例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子产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孔颖达疏曰:“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这是用魂魄来说明人的生命现象。魂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心灵,是基于人的形体而产生又可以离开人的形体的存在。古人用魂魄来区分两种生命现象:魂属于高级的心智能力,是气之神、精神,涉及人类的认知、情感、思维、道德和感受神圣的能力;魄则属于与身体相关的感官经验和运动能力。从根本上来说,魂魄属于阴阳之气的运动在人身上的表现作用。如朱子所说:“精气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离乎人而言。”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1544 页。黄宗羲对魂魄与精神的论述没有超出上述意义范围,他在《破邪论·魂魄》开篇即批评医家以人体五脏系统(五行)与神、意、魂、魄、精(志)相配的观点,强调人身上只有魂与魄二者:魄是依赖身体感官的精气作为,依形而立;神与意与志,是魂之所为,无形可见。“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②黄宗羲:《破邪论· 魂魄》,《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6 页。在人死去之后,魂魄的消散有快有慢,“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黄宗羲认为,普通人去世之后,其魂魄终究要消散;而圣贤则不同,其精神长留天地,死而不亡。这种强调圣贤精神长留天地的观点,似乎与天主教“灵魂不灭”学说相近,许多研究者据此认为黄氏此处受到天主教学说的影响。在天主教教义中,天主赋予每一个体的灵魂永存不灭的精神实体,区别于作为有限存在的肉身。利玛窦《天主实义》由此批评中国传统的魂魄观念:“人有魂、魄,两者全而生焉;死则其魄化散归土,而魂常在不灭。吾入中国尝闻有以魂为可灭,而等之禽兽者;其余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魂不灭,而大殊于禽兽者也。”③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天主实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26 页。利玛窦虽然也使用了中国的魂魄术语,但其背后的思想根据是天主教的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的观念;这与中国古代魂魄观念是基于元气运行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大异其趣,故而有上述思想冲突。事实上,黄宗羲的“圣贤精神长留”的观点是在中国古典元气论的土壤中产生的,与天主教学说无关。
黄宗羲的论证要点在于:“志士仁人,其过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犹能以仁风笃烈,拨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诬也。死而不亡,岂不信乎?”④黄宗羲:《破邪论· 魂魄》,《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7 页。这是强调圣贤的人格和思想对于社会历史而言具有永久的教化影响力。世俗庸人则是另一番生命形态:没有高尚的思想人格,精神处于依草附木的懵懂状态,其魂气自然很容易随着形体的消失而散去。进一步说,圣贤精神长留天地的原因在于它是天道秩序的体现,非一家一世之学:“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⑤黄宗羲:《破邪论· 从祀》,《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93 页。体现天道秩序的精神生命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指标,因此可以说是“死而不亡”。由此可见,黄宗羲的观点其实是表述道的功用,阐述精神道德的现实影响力;与天主教的灵魂不灭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论述一方面是延续了魂(精神)观念中涉及道德和感受神圣的能力的内涵,如《庄子·知北游》所说“精神生于道”;另一方面则与他独特的道德精神客观化思路有关。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⑥黄宗羲:《蕲熊封诗序》,《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62 页。命题,黄宗羲在论述道德与事功之关系过程中对此命题有精彩的分析。
黄宗羲定义“仁义”与“事功”之关系为“古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他批评“后世儒者”将“仁义”与“事功”分离,使得“仁义”沦为空谈,在面临政教危急时刻“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⑦黄宗羲:《国勋倪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498 页;《孟子师说》卷1“孟子见梁惠王”章,《黄宗羲全集》第 1 册,第49 页。黄宗羲的理气论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形上学解决方案。作为阳明学派内部发展出来的气学思想体系,其理论实质是在作为绝对主体的良知心体概念之外,另外树立一种展现泛存在论意义上的“气”概念;由此令良知学摆脱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局限,拥有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丰富内涵。⑧参见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如前所述,黄宗羲在理气论上主张理是气之条理,不是脱离现实(气)的虚幻玄想。这一主张蕴含了气的理想状态是以秩序条理的方式展现自身,这属于客观化的表现方式。换言之,作为天理的仁义道德若不是空疏的玄想,必以富有创造性的现实事功见用,仁义与事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能够合仁义与事功于一身的人格典范就是豪杰。这一提法源自刘宗周的“真至精神”之说:
先生曰:“不要错看了豪杰,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谓诚也。唯诚,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虚假,便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何从生出事业来?”①刘宗周:《会录》,《刘宗周全集》第2 册,第601 页。
“信之当时,传之后世”即“长留天地”,其基石是圣贤豪杰的“真至精神”,而真至精神的内容是天道之诚。体现了天道秩序的精神,自然能够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政治领域以及其他所有领域经纬天地、建功立业。至于具体领域的区别,则在于各人情志各异,所遇不同。如章学诚所论:“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524 页。黄宗羲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具有“真至精神”的豪杰,而非仅仅“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③朱熹:《答陈同甫四》,《朱子全书》第2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581 页。的道学先生。这是黄宗羲对于明清鼎革的思想反思,他自觉接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反对只知背诵语录、空口谈论义理而无真才实干的腐儒。相对于醇儒形象,豪杰形象的最大特点是将“精神”因“所寓”而客观化。黄宗羲认为,历史上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一生之精神所寓也”。④黄宗羲:《蕲熊封诗序》,《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62 页。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皆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传之久远;并且在历史开展过程中具有客观化的知识意蕴。显然,这是黄宗羲基于其师门学术建构的理气论形上学思想及其功效,并非受到天主教灵魂不灭学说的影响。
三、经史与性命:黄宗羲“天学”的新视野
经由上文对《破邪论》气之理与主宰、魂魄与精神概念的分析,可总结出黄宗羲“天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即建立在理气论的基础上。若脱离黄宗羲理气论的语境,则不仅其“天学”论述精义全无,也很容易导致各种曲解。概言之,黄宗羲的理气论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气之理”自为主宰意蕴,肯认每一个体的自由体悟与探索,不能妄立一个外在标准(任何外在的教条、人格神观念)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精神的客观化进路强调本体的转化力量不能停留于观念的内省,而必须展现于客观化的现实事功。换言之,这种理论拒斥了向外寻求至高无上的超越力量来推动、帮助个体道德完善的思路,同时也强调心学的精神转化不能局限在观念的自我满足,而必须落实在人类历史文化的实际开展中。所谓历史文化,在儒学语境中就是经史。这是黄宗羲针对阳明学过度宗教化(伦理化)弊端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其理论视野中,历史文化的开展本身既包含儒学经世致用的形态,也包括了超越性⑤本文对于超越性概念的使用,采取张汝伦先生的定义,即“将它原有的希腊哲学的存在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的上帝等特殊内 容抽去不顾,而只采用其超越有限事物的无限义和绝对义、世界的最终根据义和价值本源义,以及决定者而非被决定者义”。 详见张汝伦:《论“内在超越”》,《哲学研究》2018 年第3 期。的独特展现方式。这是黄宗羲“天学”思想的新视野。
有趣的是,港台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认为,黄宗羲的理气一体思想落于自然主义之实然平铺,有将理降格为气之“谓词”的倾向,进而失去了理的超越地位。⑥详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上册第333—345 页;中册第102—114、173—177 页。实际上,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气之理”的理并不会失去超越性,黄宗羲突出其主宰含义就是强调它不会沦落为气的谓词。质言之,作为气之理想状态的太极与理,其超越性来自气之感通通达。这一意义结构在根源上来自朱子天理观。朱子对天理的定义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⑦朱熹:《大学或问上》,《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8 页。这种定义既包括当下事物之变化的个别性之理,也包括超越个别性限定的根源之理、结构之理,天下万事万物因此而被纳入相互通达、彼此相与的贯通状态。上述两个含义分别代表个体性与公共性。而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对于天理概念的改造,在个体性与公共性结构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意义表述途径:每一事物之条理秩序既是个别性之理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事物之间本真联系的重建。换言之,“气之理”破除了事物彼此不相与、不相知、不相通的存在状态,由此亦具备超越有限事物的无限义和绝对义。其效应可借用朱子的一句话加以描述:“天地之化,生生不穷,特以气机阖辟,有通有塞。故当其通也,天地变化草木蕃。”①朱熹:《中庸或问上》,《四书或问》,第72 页。气机之感通通达具有神妙的创造性意义,这说明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天理观的超越性与创造性意蕴,正由气的通达状态奠基;作为“气之理”的个体性之理本身就具有超越意义。这是一种建立在个体性基础之上的超越性思想机制。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工夫开展过程中以何种方式达到“贯通通达”?黄宗羲《明儒学案》对此展开了别致的思考。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撰著,本质上是对于“真至精神”客观化的知识路径之展示。黄宗羲撰著《明儒学案》的思想动力,来自其“精神长留天地”的观念。明亡之后的康熙九年(1670),作为明遗民的黄宗羲为亡友撰墓志铭,其中有一段文字为:
明年,过哭旦中,其兄臣四出其绝笔,有“明月岗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之句,余改“不见”为“共见”。夫可没者形也,不可灭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则堕鬼趣矣。②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326 页。
如研究者所论,上引诗句中的“明月”指明朝,“青”借代清朝:“形寄松下”是指个体在清廷治下的有形世界中的生活;“神留明月”是指个体对明代圣学之精神的承继。③包赉:《吕留良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76 页。孙中曾:《后刘宗周到后南雷时期之知识社群:以刘宗周证人 会复举为考察》,陈来、高海波主编:《刘宗周与明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2020 年,第406 页。“不可灭者神也”既是指明朝遗民的精神世界,更指向有明一代学术所透露的精神与道统。所有有形质的物体都会毁坏无存,有明一代学术所代表的“真至精神”长留天地。需要注意的是,黄宗羲所说的“可没者形也,不可灭者神也”之神,是在与圣贤之道相关的意义上讲的;常人之魂魄精神不在“不可灭者”的范围。如黄宗羲《家母求文节略》中引用的“汝父忠义之气,自应不昧”,④黄宗羲:《家母求文节略》,《黄宗羲全集》第11 册,第25 页。是与道相关的“不可灭者”;《读葬书问对》引用范缜《神灭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作论据,⑤黄宗羲:《读葬书问对》,《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660 页。是在常人魂魄的意义上讲。这些不同层次的用法并没有矛盾。如前所述,黄宗羲所理解的“真至精神”并非仅仅停留于观念内省层面的精神实体,而是直接展现为人类生活与历史文化领域经纬天地、建功立业之事功。这个内涵被黄宗羲概括为后世著名的命题:“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⑥黄宗羲:《明儒学案· 自序》,《黄宗羲全集》第7 册,第3 页。本体不是脱离每一个体事物的虚假抽象物;变化不测的万殊事物,其个体性的实现就是本体(超越性)的展现,此之谓万殊一本、殊途同归。这是黄宗羲理气论“气之理”自为主宰意蕴的表现,而不设置外在标准局限每一思想家的自由体悟与探索,就构成《明儒学案》思想结构的重要特质。学界研究亦认可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撰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将如牛毛茧丝般细致微妙且各具特色的心性之学思想按知识类型组织起来:《明儒学案》“以平面类比的方式组织知识”,能客观地彰显各家学术特质,“具有独立和开放意义”。⑦朱鸿林:《为学方案——学案著作的性质与意义》,《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68—373 页。其将学术精神以客观化的方式呈现的思想机制,在黄宗羲《明儒学案序》中有表述:
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焉,因圣人之耳目也……此犹中衢之罇,后人但持瓦瓯樿杓,随意取之,无有不满腹者矣。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7 册,第4 页。
明代思想家群体一生的工夫探索,展现了本体(精神)的万殊面向。这些自由的工夫探索和体悟所得各不同,“深浅各得,醇疵互见”正体现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事实上,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两篇序言和《发凡》中反复强调,他表彰的是明儒“其人一生精神”,他在撰著过程中竭尽心力“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黄宗羲通过分源别派的方式,使得明代诸儒者学术思想宗旨历然,令精彩纷呈的“精神”以客观知识的方式展现。重要的是,资质和兴趣爱好均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明儒学案》之后,“随意取之,无有不满腹者矣”,都能有所收获。黄宗羲对此非常自信,而事实证明亦如此。换言之,《明儒学案》将以往表现为玄虚、抽象的形上本体之学按知识类型组织起来,同样拥有神妙的精神转化能力。由此观之,钱穆先生曾判定黄宗羲晚年撰写《明儒学案序》时论学宗旨大变,此前则“仍徘徊于本体渺茫之说”;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29、30、75 页。此论显然有待商榷。从本文的分析来看,钱穆所看重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命题正是黄宗羲一生坚持的理气论顺理成章的结论,两者之间并无悖反之处;从黄宗羲在此之前完成的《明儒学案》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其精神客观化进路反而具有打破“本体渺茫之说”的功效。这涉及如何评价黄宗羲学术特质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思想家沿用心性形上学的概念表述思想,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思想就必然是“本体渺茫”之学。讨论的重点应放在对其形上学概念内涵的界定和使用方式上。黄宗羲《孟子师说》一书完成于康熙八年(1669),时年60 岁。此书对于本体与工夫有一段论述,其内涵与《明儒学案序》“心无本体”的著名命题基本无异:
性是空虚无可想象,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可以认取。将此可以认取者推致其极,则空虚之中,脉络分明,见性而不见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③黄宗羲:《孟子师说》卷7“尽其心者”章,《黄宗羲全集》第1 册,第148 页。
笔者的前期研究指出,这段话是黄宗羲理气论的重要表述:作为“气之条理”的形上本体由石火电光般的隐微形态,在工夫实践过程中,亦即事上磨炼的历史人事中逐渐展现其性状,最后以最完备的条理形态显现。一方面,形上本体“空虚无可想象”,它必须在工夫实践的过程中构建和开展自身;另一方面,形上本体在工夫实践过程中“推致其极”,具有开展为历史与人事内容的知识规范性。由此,历史文化与人事之学,亦即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黄宗羲心性之学开展的一部分。笔者称之为“寓性命之学于经史”的学术形态。④参见陈畅:《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现代哲学》2019 年第5 期; 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由此可知,钱穆先生基于《明儒学案序》“心无本体”命题判断黄宗羲晚年思想有大转变,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按黄宗羲的自述以及《孟子师说》的著述时间点来看,黄宗羲思想发展即便存在所谓的大转变,也是发生在其抗清失败“僵饿深山”发奋苦读刘宗周著作的“近二十年”,⑤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 册,第4 页。而不是在其晚年。
黄宗羲“寓性命之学于经史”的学术形态,在《明儒学案》一书对“真至精神”的客观化表述方面就有典型的展现。此书把宋明时代学者对于心性之学的形上探讨,转化为形上“精神”在工夫实践的时间性中逐层开展的“过程”与“历史”。因此,对心性之学的研习,就被转化为对心性之学的历史开展形态的“知识”把握。在黄宗羲独特的“寓性命之学于经史”思想中,形上本体不是内在具足的,而是有待于时间性的开展,在历史与人事活动中完成自己。因此,性命之学的超越性不是在观念内省过程中展现,也不是在人格化的神圣者当中展现;而是在历史文化中展现,亦即在经史之中展现。其中起作用的思想机制不是向内反求先天具足圆满的本体,而是向外结合社会历史与人事(经史)作出客观化的扩展。经史之为“物”在此就拥有本体论的地位,而不是被定位为心体的附属物。如全祖望指出:“(黄宗羲)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授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学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219—220 页。在经术所以经世观念的指引下,黄宗羲将性命之学与经史之学融会贯通,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结 论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独立的思想源头,黄宗羲“天学”思想批判是专门针对其中一个源头,亦即阳明学过度宗教化而发端的敬天思潮而提出的。当前学界研究有误区,其根源就在于将黄宗羲《破邪论》误置于天主教语境中定位。这也表明,对《破邪论》这种辨析驳异性质著作的研究,不能离开具体的思想史语境。具体说来,我们无法脱离黄宗羲的理气论讨论其“天学”思想。一旦抛开黄宗羲的理气论,只从字面上空头讨论其对昊天上帝、魂魄、精神的观念,实际上也就离开了黄宗羲思想的源头,无法理解其“天学”思想的新视野。
如果说天主教的上帝(天主)观念代表着现代人熟悉的超越性哲学概念之原型;那么在黄宗羲《破邪论》“天学”思想批判的背后,事实上体现了中西方哲学文化关于形上学、超越性概念的不同思路。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在于,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历史文化(经史)不是一个独立实体,其本质上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在与真实世界打交道过程中展现精神(良知)之创造性和客观化条理的记录。在历史文化或经史之中的超越性,仍然是人类精神(良知)的超越性本身;但又避免了良知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弊端,以“经术经世”的方式把握真实世界并恢复儒学经世致用功能,这是明清思想转型的心学路径。黄宗羲《破邪论》代表了明清之际“天学”的一种独特嬗变,并且这一思想形态在清代亦有其后续影响。章学诚评价其所代表的浙东学术特点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3—524 页。从上引全祖望的文字来看,黄宗羲之学明显是经史并重,章学诚的用词有其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因此,笔者将黄宗羲之学命名为“寓性命之学于经史”的思想形态。黄宗羲的宋明理学总结工作、社会政治构想、经史撰述,都是其“寓性命之学于经史”思想的表现。这是心学在明清思想转型的历史情境中的自我更新,心学不再以独立形态的性命之学表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