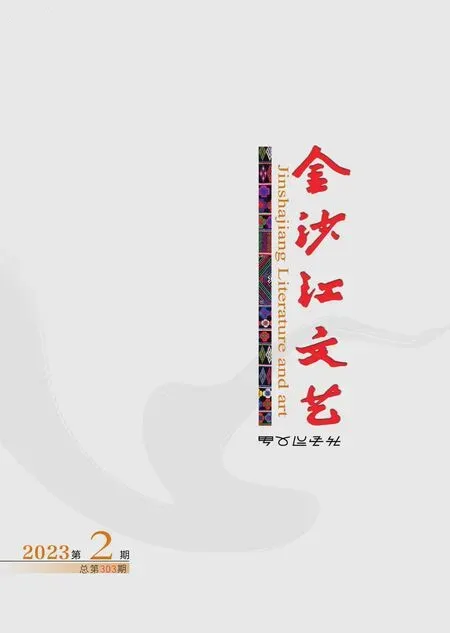曲中人
2023-04-15离离甘肃
◎离离(甘肃)
我约了顾青青一起喝咖啡,我们依旧选了靠窗的位子。
还是单位附近的那个书店,好多次我都去那里写稿子,简简单单要一杯咖啡,临窗坐下来,有时候稿子写不下去时,就习惯性地看看窗外,那里正好有一幢旧了的楼房,它的一角对着我。我喜欢那些暗红的砖块,砖和砖紧紧挨着,是温暖的方式,暗红的颜色早已渗透进彼此了,是温暖的颜色。有一天,我有个中篇写不下去了,就去书店里坐着数那些砖块,数到一万八千零三十八块,我的眼前突然一晃,我的目光着落处已经散乱了,看似一样的砖块,一样的暗红色,我找不到原来的那块了。我的生活也是,开始变得散乱无章,因为就在前一天,我结束了我的前一段生活。
下午的光斜照在桌子的一个角上,就那一块明亮又突兀出来,和别的地方有了明显的不同。我轻轻用手抚摸那点明亮的地方,木质光滑,木纹清晰,就像爱。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爱就像光一样,爱你的人都会带着光来,温暖你,照耀你,所以,爱会使人明亮,使女人变得光艳又漂亮。而有的爱也是模糊不清的,有交错感的,就像把楔子钉入木头,那种交合,有种疼痛,但不会再分开。
顾青青新做的锁骨烫让她看起来有一身的女人味,她看着头发凌乱的我,说:“看你现在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多了。你也养只狗吧,就养个小泰迪。她说:“我们小区院里有好多养狗的,金毛,哈士奇,吉娃娃,博美,蝴蝶啥的都有,我家对门就有个很漂亮的小泰迪,那个长发披肩的女人一天出来遛三次狗。小泰迪一出门就蹦蹦跳跳的,很让人喜欢,但是一看狗的主人,总是冷冰冰的,所以我每次就和只小泰迪打个招呼,之后它就蹦蹦跳跳走了。哈,真是有点讽刺。” 说话间,她用手抓了一下她的头发,说:“你看,我都有白发了,我从来都没仔细照过镜子,还是那天王鹏在我头上发现的。我让他帮我拔掉,他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会越多。后来我就自己对着镜子拔,把能看到的都拔光了,我对白发很恐惧,感觉自己完全被岁月打败了。”顾青青有点难过的样子。我笑她太自恋了,对她说:“到我们这个年纪,有几根白发很正常,你看看我,我撩起自己的头发让她看,不也有稀稀拉拉的白发吗? 我都不当一回事,管它们干嘛呢。我倒是希望自己一夜醒来白了头,那种银光白,真的很优雅很漂亮。”
顾青青喝了一口咖啡,说:“我还是担忧,老天肯定会折磨我,给我的不是全白而是灰灰的那种,满头的沧桑感,你说哪个男人还会看我?”她突然又深深地看着我问:“李可,你爱陈岩吗?” “爱啊,不爱干吗要在一起?” 我回了她一句。“可是我不爱王鹏。我只是需要,需要依靠,还有性。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男人,不会再爱,王鹏也需要一个女人。都是成年人,谁还认真呢!”
快到中秋节了,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蛋糕店的门前排了长长的队,在等着买月饼。陈岩把他单位发的蛋糕卡给了我,让我自己去取。我说不用,我会自己买。突然间就有点失落,自己被敷衍的感觉不好受。傍晚的时候,陈岩自己取了月饼送过来,让我到小区门口取。我说算了,不要。我已经买了好多。后来他一直在等,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说出来,我们一起去吃饭,赏月。那天的月亮其实并不明亮,在小区院子里我就抬头看了,朦朦胧胧的,也不够圆。一个人看到的月亮和两个人看到的月亮没啥区别,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不同的只是心境。陈岩的车上播放着一首歌,我听着,没说话,我知道陈岩是故意找的,他想说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少年。我们之间,他没变,我也没变,那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之间,毕业后多少年未见,如今又在这个城市不期而遇,我们甚至都以为,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牵扯着我们。比如那天在“花之林”,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也正好回了头,我们几乎同时叫出了彼此的名字。
“真是奇怪啊,怎么那天就能遇到你呢。”
“哪天?”
“就那天,在花之林。”
他的手伸过来,紧紧握了我的。他喜欢在开车时一只手握着我的手。这样,也是我喜欢的。
最近我也单曲循环这首歌,仿佛是为了所有重逢的人写的。
他继续哼着歌,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曾经的那个少年,那时候还没长出胡子来。如今,眼角已落了沧桑。
“今天我们还去花之林,我前面已经订好了位子。”
我们在地下车库兜来兜去转了几圈,最后在一个角落里,他找好了地方停车。然后紧紧地拥抱我。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答应我。是老天注定要我们在一起,答应我。今天我们好好喝两杯,我把所有的事都推了,今天只有我们,没有什么再能打搅我们了。”
陈岩说,“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政治老师吗,有点卷发的那个,后来得病死了。” 我说,“记得啊,有一次期中考试前,他说要出题,还管我借我的政治笔记。”
“听说他挺色的,跟你借笔记,他可能有别的心思吧,难道有歪想法?”
“谁知道呢? 但那次我感觉怪怪的,还让我给他按摩肩膀,我留下笔记就出来了,后来他叫我去取,我一直没去,他就给我带到教室里。那时候他有个女朋友,听说在县里哪个小学当老师,每次来找他时,他就带到隔壁老师的宿舍里一起做饭吃,后来他女朋友就和隔壁的老师在一起了。”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那俩老师争吵时,我正好在那堵墙的后面背英语课文,就听见了。”
那天我们在去当年的学校的路上,说起了很多旧事。陈岩有时候会拉起我的手,在手背上轻轻地吻几下,这让我感动又温暖。我说好好开车啊。
当年中学时坐过的教学楼已经被拆了,所以感觉学校里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陈岩说,当年我还为了你打过架,你可能不知道吧。
“真打过吗? 和谁?”
“王朝阳。”
“怎么会和他打架?”
“他说他喜欢你。”
“那也正常啊,用得着打人一顿吗?”
“用得着,虽然你那时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心里有一点苦味涌上来。那时候,我本来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所以对别的男生真没正眼瞧过。
他又拉起我的左手,轻轻地吻了几下。
陈岩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属于哪一种,遗憾,还是失而复得。他说大学时有一个师兄,周末带他去录像厅。他说:“我第一次看到女人裸体的样子,就想到你。想着你是不是也是那个样子。” 我狠狠瞪他一眼。
“真的,你不知道,我手心里都是汗,紧张得不行,呼吸困难。后来我一个人跑出来,朝着河堤跑,喊你的名字。那时候真想把你紧紧抱在怀里,狠狠地亲。”
“那为什么不找我。”
“找了,又忍了,感觉自己还是配不上你。后来有一点自信的时候,又找了你,可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
“撒谎!”
“真的。”
吃完饭他送我到楼下,他说,“我想上去坐坐。” 他此时这么说就显得很暧昧,但在这样月色朦胧的夜晚,需要这样的暧昧。我似乎犹豫了几秒钟,又轻轻点头,我看见他眼里弥漫的东西,在中秋的夜晚很迷人,也很撩人。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轻轻把我揽进怀里,我们都喝了酒,周围弥漫的是酒气和欲望混合的气味。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更多的是欲望,彼此的需要,彼此不断地摸索,从之前的陌生和期待,到后来的熟悉和渴求。
那段时间我晚上一直都做梦,总是梦见以前的学校,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学生时代的共同话题总是说多了。记得有一次我们都在原来的教室里,有个男生跑进来说,中午在马家磨枪毙死刑犯,你们去不去看。我一听就被吓到了,双手攥紧了,静静地坐着,陈岩过来问:“你去不去看,吓晕了我背你回来。” 有几个同学开始起哄,喊着 “背一个,背一个!” 我白了他一眼,说:“滚一边去。” 后来他们男生大多都去看了,下午回来后都在教室里议论那事。我还是不敢听。我一直都胆小,一想到血腥的场面就发抖。我甚至都不敢想象那种场面。陈岩过来说:“我给你讲啊,那个,那个场面真是太吓人了,啧啧,吓得我今晚都睡不着觉了。”
前段时间,单位的一个同事是退伍军人,一起打球时他说自己以前是武警,另一个同事就问,枪毙过人吗? 他说,做过副手。我问啥是副手,他说,就是犯人一枪打不死的情况下,就该他上去补一枪。我全身又开始发紧,我又问,那你补过吗。他说没有。想起中学时那次陈岩他们去看枪毙人的事,晚上我问陈岩:“那次你们去马家磨看枪毙犯人,究竟看到啥了。” 他说:“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我说:“突然就想问了。”“什么都没看到呀,离得那么远,只听见枪响的声音。” 我说:“那你当时为啥骗我。” 他说:“说实话你也不信啊。我给你说我喜欢你,你总说鬼才信。”
“那时候都还是孩子,孩子说的话谁会当真。”
“那现在我说的话呢? 现在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是认真的。”
“现在我们挺好啊!”
顾青青打来电话,声音很急切。让我赶紧过去一趟。我问怎么了,她说,“你先过来再说,有钱吗,有的话借我一点,刚还完房贷车贷,后面再还你。” 等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客厅里转圈,之前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圈了。我说:“你能不能停停?别转了,我都被你转晕了。”
“王鹏会不会丢工作?”
“应该不会,聚众赌博会被拘留罚款,视情况而定。”
“他之前总是说几个朋友一起玩玩,不玩大的,就是打发个时间。谁知道这次被其中一个的老婆给举报了。真是,自己的男人还去举报,真是吃错药了。”
“但是这样也好啊,起码以后就会断了这方面的念想。” 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了,她一会儿骂一会儿哭,其实也不算哭,只是轻轻抽泣,双肩跟着轻轻地动。我抱了抱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跟着她骂王鹏吧,似乎不妥,万一被王鹏知道了,以后见到了还挺尴尬的。我陪了她一晚上,给她微信转了一万,第二天就去上班了。第三天,她给我退回来五千,说罚了三千,她去交了,两千就给王鹏爸妈送去,老人说没钱买药了,剩下的给我,欠下的下月还。人被拘留几天,暂时得瞒着所有人。她说让我帮她接送一下孩子,她得去看看王鹏的父母。我有时候也替顾青青感到累,女人像她那样活着真累,一个人支撑了那么多,不过也挺佩服她的。她总说她需要一个男人的肩膀靠靠,可我总感觉她是给男人肩膀依靠,给他们全家依靠,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依靠。今天不是王鹏的这个亲戚来看病,明天就是那个亲戚来找工作。我真不知道她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和耐心。她说,“你不懂,这就是爱,我现在是真心爱上王鹏了,我愿意为他和他的家人亲戚做这些。之前只想着搭伙过日子,没想到真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这难道就是爱吗? 我一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可以是一个人,可以好到不分彼此的那种,可以在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可以吃一个碗里的饭,甚至相互喂着吃,用一个杯子喝水,可以说掏心窝子的话,可有时候就是两个人,是独立的,总要有独自的时间和空间,甚至情感。两个人的家庭亲戚,最好不要太多牵扯进来,不是不够人情世故,是太拥挤了,两个人的感情里盛不下。
两年前,我和顾青青是在一个户外群里认识的,也一起骑车出去过几次,她体力很好,对别人都很照顾,我们都叫她顾姐。王鹏那时候也一口一个 “顾姐” 地叫着,其实他比顾青青还大两岁,等大家都熟悉了,我才发现他们总是避开别人,要么拼命往前面骑,要么故意落在最后面,再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那次我们一帮人骑车出去,在下山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其中一个女的连人带车摔到一个沟里了,等我们都到山下的平缓处休息聚集的时候,发现少了她,然后几个人又返回去找,后来就在山下的沟里找到了。当时赶着送医院,还不知道有多严重,后来说是颈椎断了,肋骨也断了几根刺进了内脏。我当时差不多半闭着眼睛,我的胆小让我很羞愧。救护车走远了,我腿抖得还是骑不了车。顾青青给其他人说,你们先走,我们挡个车回,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无话不谈的那种。感觉人和人之间真的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有的人一辈子也走不近彼此,有的人突然就走进你的心里去了。顾青青说我们俩属于后者。
过了几天,顾青青打来电话说:“人没了。” 我说:“谁?” 她说:“骑车掉沟里的那位。”
我突然就僵在那里。好端端的一个人,去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回来咋就没了。顾青青说:“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和喜欢的人相爱,或者和不合适的人分开。再不能浪费生命了,生命太逗人了,你看看,人说没就没了。” 我说:“我再不骑车了,有心理阴影了,我决定退出。” 她笑了:“看把你给吓的。命数也是天注定的,床头还摔死人呢。你能躲到哪里去?”
“还有一件事让我很难过。” 顾青青说:“你还记得我对门的小泰迪吗?”
我说:“记得啊,见了你总是蹦蹦跳跳的。”
“它被车轧死了。它在蹦蹦跳跳过马路的时候,被过来的一辆车碾过去。那么小,之后也是那么一点点,似乎没有骨头,软软地躺在那里,只有一摊血,染红了它白色的毛,白云一样的毛,再也白不了了。我真是难过,我那天正好出门,在小区对面碰到他们。长发披肩的女人坐在那里一直哭啊一直哭。我好久都挪不开脚步,后来又返回去,和那个女人一起去公园把小泰迪埋了。” 顾青青在电话里又一次泣不成声。我也哭了,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哭什么,她说的小泰迪我也没见过,但我早就熟悉它蹦蹦跳跳的样子。她说的长发披肩的女人我也没见过,但她的冷漠我也知道。还有顾青青,她说我们再不能失去什么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我说:“我们一直都在失去,阻止不了的。阻止不了相遇,就阻止不了失去和离别。你看过 《万箭穿心》 那部电影吗? 这辈子,横穿于我们生活的道路太多了,它们在各个方向错综交错,所以,有些悲剧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今天躲过了,明天,或者后天也会发生点什么。”
我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突然想给她讲李猫的故事。尽管我一直都没给人提过,就因为失去了,才不忍,才足够伤心。
我说:“我养过一只猫,养了整整十年,我叫她李猫,随我的姓,因为她是只米猫,我们老家管母猫不叫母的,叫米的。因为她是米的,所以被原来的主人遗弃了,我在路边的树丛里捡到她时,她应该还没满月,因为她啥都不会吃,只会舔一点牛奶,后来慢慢会吃一点火腿肠,我就给她一箱一箱地批发火腿肠,她最爱吃的还是泡面拍档的那种。那时候我写东西时,她就趴在我的腿上,有时候睡着了,会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妈妈说那是猫在念经。我妈还说,猫难养,而且随便不能弃,不管多远,都会自己找回来,而且猫会告状。我说,一只猫能去哪里告状。她说告阴状啊。我笑她这么迷信。我给李猫脖子上挂了个小铃铛,所以她走到哪里我都能知道。我每天都叫着她,李猫,李猫过来吃饭,李猫我们去睡觉。她就像个小孩一样,我把胳膊伸出去,她就躺下来了,有时候爪子毛茸茸的,轻轻地挠我逗我。后来有一天,她在屋里跑来跑去,开始嘶叫,声音仿佛在喉咙里,发不出来,有时候感觉又在她的腹腔里。妈妈说,米猫就是麻烦,她开始发情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那个小县城还没有宠物店,我去找兽医,他说把猫放出去,让她自然受孕就好了,我说我怕她再生小猫,他就给我一支母猪止排的药剂,让给李猫注射,说再没别的办法。我拿着那支药剂回家,找了邻居帮忙给李猫注射了。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感觉自己是个足够阴险狡诈的人,也狠毒,我剥夺了李猫恋爱和生儿育女的权利。我抱着瑟瑟发抖的她哭了。那样的事我每年都在做,一年大概两次,直到后来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很反感她歇斯底里的叫声,尤其在半夜里,她的叫声让人心里发慌。直到有一天,我怀孕七十多天的孩子流产了。我妈说,作孽呀! 赶紧把猫扔了,扔得远远的,要不她还能自己找回来。我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多月时又停育了。我妈一开始哭,后来对着李猫大声喊,把门打开,让它赶紧滚出去,可是李猫躲在我的怀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我舍不得。我一直拿李猫当孩子养着,就那样一直过了十年,直到我来这个城市之前,那时候李猫已经老了,她每到春天还是会叫,但力气已不如从前,持续的时间也短。我感觉她已经爱不起来了。就像生活中的我,对爱也是力不从心。我决定把她送到老家去。我拿了一个纸箱,她很开心就跳了进去,我马上用胶带封了口,只在一侧剪开了一个小洞通空气,等她明白了之后,她就拼命地抓纸箱的内壁,我怕她抓破,又加了一个纸箱在外面,像筑牢一道铜墙铁壁,我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刽子手,但整个过程我都在哭。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我的灵魂一直都有双面性,一个我想留着她,另一个我想抛弃她。两个我一直在斗争中,不停地折磨着我……”
顾青青哭着说:“你别再说了。”
“后来过了三四天,我接到老家来的电话,说李猫不见了。最开始一两天她还爬上院墙看看外面陌生的世界,但之后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没有。我疯了似的坐车赶回老家,我以为我的声音还能唤回她。只要能找到,从此,我会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我在老家院子外面的前后左右都找遍了,一直叫着李猫,李猫回来。我叫着叫着,感觉是在叫自己,叫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叫着自己的灵魂,叫着自己的心,我把我的一个灵魂和心都弄丢了。我找不到她。我再也找不回她了。”
“她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顾青青突然不哭了,问我。
我说:“不知道。现在我真怕她再找回来,爪子都磨掉一截……我宁愿她死了。”
“为什么?”
“死了就再没有分离的悲伤了。”
我和陈岩不咸不淡地处着,我们之间,有时候就像老夫老妻一样,因为太熟悉,而少了一些激情,就因为太熟悉,也多了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有不断的回忆,也有新的进展。他带我去正式见了他的父母。其实他们也都认识我,也很喜欢我。他们知道我的过去,所以我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我和陈岩都是有过去的人,都属于别人口中有故事的那种人。所以他现在总说,要是当初你信我,不那么骄傲,我们不至于兜兜转转这么辛苦才再到一起。我说,那都是命,我现在相信命运。如果我们当初真在一起了,说不定现在早已经分开了,或许还会成为话都不说的仇人。
那天,我第一次主动问:“你还会想念你的前妻吗?” 他说:“我不知道,应该不会,但会想起。” 我靠过去抱紧了陈岩,终于,我主动抱着他,让他有点意外,也有掩藏不住的惊喜。我的脸微微发烫,有红晕漫过来。他也迎了上来,他的唇马上覆盖了我的,他的身体也覆盖了我的。
凌晨一点了,我从他的臂弯里逃出来,突然想给脚趾甲上涂指甲油。两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我就开始喜欢抱着双膝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夜,等天微微发亮,我才能睡去。后来,我把氟西汀、舍曲林那些都扔到垃圾桶里,我想靠自己挺过来,那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脚趾甲涂指甲油,有时候是某一个下午,我拉上窗帘,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涂,有时候是黄昏,鹅黄的光照着屋子里的静物,我感觉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不爱走动,感觉自己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块玻璃,一盆绿植,或者一件衣服,反正不是我自己,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海上漂着,在风里被撕扯着,在雨里被水淋着,又被黑暗包围。有时候是半夜里,我把双脚伸出来,仔细看,抚摸每一个指甲,那些我身体上坚硬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被软化了,我就开始涂指甲油,涂完左脚涂右脚,然后等着晾干。我只喜欢涂车厘子的颜色,我对那种感觉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喜欢。那种喜欢里,我看到自己被隐藏的风情和孤单,但涂了指甲油的脚从来没有外露过,我只喜欢自己看自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身体的这一部分,身体的那一部分,或者,挂满水珠的全部的自己。就像那天看到陈岩画的那幅写意画,我说出水芙蓉啊,水珠晶莹剔透,他说就像你,刚出浴的你,全身挂满晶莹的水珠。
但我以后不想再涂了,我把那十个刚刚涂好且已经晾干的趾甲上的指甲油用湿巾拼命地擦,直到擦得什么都看不到了,仿佛不想留下任何印迹。
大概两点多,我摇醒陈岩,对他说:“我不想结婚了。”
他仿佛被突然惊醒:“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我不想结婚,我害怕那种婚姻里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
“我们不一样,和彼此之前的不一样。你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他轻轻拍着我的背,每一次我难过或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轻轻地拍我的背。
我突然抱着陈岩,开始哭。我是被婚姻折磨怕了的,不敢轻易再迈出那一步了,不管对方是谁。既然相爱,为什么非要结婚在一起,
“明天咱们再好好说这事,现在啥也别想了,先睡觉。”
但是第二天一早,陈岩家里出事了。他爸爸心脏病突发,他妈妈因为失眠,那天晚上正好吃了安眠药睡得很沉,所以,他爸爸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120送到医院还是没能抢救过来。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妈妈一个人在楼道里哭。那样子,让我看到相依为命的两个人,说分离就分离,甚至来不及说点什么。我突然很愧疚,那天半夜里为什么要对陈岩说那样的话。
陈岩陪着他妈妈,我先回到单位处理手头比较紧急的稿子,发完邮件后又赶去陈岩家。两个人的家,如果一个人突然不在了,那个家就空了。陈岩给我开了门,我看到客厅里再没有人,陈岩说,“我妈妈刚刚睡下,他朝着卧室的门看了一眼。”
突然感觉,那个家真的空了。他爸爸在的时候,每次我们周末回去,他都会在阳台上侍弄花,或者给我们煮茶喝,高兴了还会做两个菜,可这一切现在都没有了。陈岩说:“我妈的天塌了,我得帮她撑起来,她现在只有我了。” 我说:“对不起,昨晚还跟你说那样的话。我一直都在,我们不分开,一起好好的,照顾妈妈。”
那段时间,我和陈岩,我们似乎都身心俱疲,在一起也说不了几句话。他爸爸的突然离世,使得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有模式都变了。白天,陈岩每天得回一趟他妈妈家,买日常生活用品,做饭,晚上也回去陪他妈妈,有时候等他妈妈睡下了,他才偷偷跑回来,然后倒头就睡。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有时候,一个人的突然死亡,真的会带来更多的连带死亡。陈岩爸爸的去世,直接导致了那个家的聚变,他妈妈似乎也被掏空了,就剩那样一个身体在动,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陈岩也是,我感觉我和他的爸爸妈妈像天平一样,就分别在他的两边,现在,他妈妈一个人轻飘飘地、高高地翘了起来,他怎么也掌握不好那个平衡。
那天,主编说有个去外地的培训,要半个月,问我去不去。正准备回家赶稿子的我想都没想,说:“不去。”路过花之林的时候,突然想和陈岩去那里吃个饭,我们好久都没有好好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于是上去选了一个位子,然后给陈岩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的,我以为打错了,她说她叫王悦。我突然就僵在那里。
王悦是陈岩的前妻。她说不久前才知道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她回来已经有大半个月了。
“你是李可吧,陈岩早就给我说过你俩的事。”
可陈岩并没有告诉我,他前妻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而他,最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回来过。
我一个人从花之林出来,站在马路边上,不知道该去往哪里。紧接着,陈岩的电话打过来了。
“刚才我在厨房,王悦说你打电话了。”
我说:“没事,就是想问你一声你在干嘛。”
我突然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原来我的这一边还隐藏着一个人,现在她终于出现在明处了。我和陈岩是在花之林相遇之后开始的,我突然想在这里结束,真是挺有戏剧性的。然后我给主编打电话,告诉他,我去参加那个培训。
我突然想起来,好久都没和顾青青联系了,想问问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很想和她一起坐坐,即使一句话都不说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