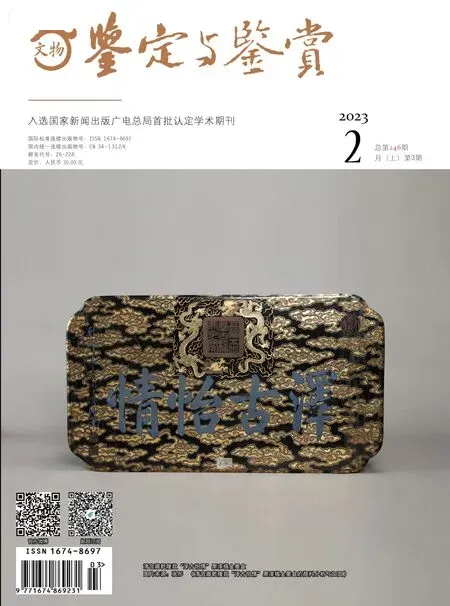试论口述史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运用
—以十三师新星市地窝子遗址为例
2023-04-15高萌
高萌
(漯河市博物馆,河南 漯河 462000)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的快速发展,新疆成为国内旅游的首选地,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窝子遗址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当前,十三师新星市红星二场的地窝子遗址正以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推进①,但本文认为遗址公园的保护力度远不及遗址博物馆。未来,地窝子遗址博物馆一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将面临各类文字与图片资料缺失的状况,利用口述史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并在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展览中起到关键作用。
1 地窝子的背景及新疆境内部分地窝子遗址的现状
地窝子建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全体指战员接到进疆剿匪与生产建设任务后,在面对戈壁滩夏热冬冷、干燥少雨、风沙大、生产力低下、物资不足以及生产周期紧张的情况下就地取材所建造的②。地窝子的建筑形式与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难说那一时期是否有考古学人士参与地窝子建筑的规划与修建。当前,全疆境内地窝子遗址存量少、规模小,这与该地区风沙大、植被覆盖率低以及人们搬出地窝子之后没有再回来的意愿相关。虽然地窝子废弃时间不过60年左右,但由于废弃之后无人看管,在经历长时间的风沙侵蚀后逐渐坍塌,只在地表留下一个个浅浅的窝痕。
目前,经多方走访与调研,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境内见到三处地窝子遗址,分别是:①十三师新星市红星二场军垦地窝子遗址群,它是兵团范围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整连建制遗址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50多亩(每亩约为666.67平方米),约有150多个遗存③,文中要构建的地窝子遗址博物馆也是针对该遗址进行的,下文不再赘述。②十三师新星市红星二场“高烟囱”遗址群,据专家考证,这应是一处烧碱的烟囱,遗址群包括干打垒(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墙体、芒硝垒制墙体、地窝子遗址群、废弃的坎儿井等。而地窝子应为当时的工作窝棚,为了便于识别当地人称其为“高烟囱”。整体占地面积约100亩,其中地窝子遗址占地50多亩,当前该遗址还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范畴,其内分布着30多个大小不一、毫无秩序的地窝子遗址。其中,少量遗址能看清建筑结构及内部构造,据遗址的布局与使用痕迹等情况,判断这是一处时代较晚的民用地窝子遗址。③八师石河子市军垦第一连红色旅游景区内还有少量地窝子遗存,但整体毁坏较为严重,在地表只留下似隐似显的痕迹。
2 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
地窝子遗址建筑作为20世纪50年代初军垦战士的生活场所,见证了第一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和屯垦戍边的历史。为弘扬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新星市红星二场与对口援疆的河南省文物局于2014年委托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设计研究中心对红星二场的部分地窝子进行修缮④。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沙的侵蚀与人为破坏,之前所修缮过的部分地窝子遗址先后出现了屋顶坍塌、局部被风沙掩埋的现象。2022年,为喜迎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延续胡杨精神、传承兵团精神为目的,十三师新星市再次委托相关专业部门对地窝子遗址进行修缮维护。
真正的地窝子长什么样?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深入了解地窝子的建筑构造、工艺及用料等,通过翻阅文字记载,以及实地考察石河子市军垦博物馆、石河子军垦第一连以及十三师红星二场的地窝子复原建筑,发现前两者并无较大区别,而后者与前两家单位复原的建筑形式存在较大区别。初期,认为这与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受来源地建筑习俗影响较大有关。随着深入走访兵团老人,发现上述三家地窝子复原建筑都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地窝子遗址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若不及时弄清上述问题,地窝子遗址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其内部构造、建筑支撑材料以及野麻草屋顶也将跟随地窝子遗址的消失成为谜团。
未来,建设地窝子遗址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建成后不仅有效解决了地窝子建筑造型及内部结构等问题,而且可以避免风沙侵蚀与人为破坏造成不可逆现象,同时还具备相对专业的研究人员与设备对其进行保护与维护,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文物部门,并与其进行沟通、修缮;另一方面,地窝子遗址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共文化实践场所,不仅可以吸引国内外更多的观众来此接受心灵的洗礼,学习兵团精神,体会兵团人敢于吃苦、无私奉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可以揭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神秘面纱的一角,使其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探索。
3 口述史在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展览中的运用及意义
新时代博物馆理念从关注物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转变为逐渐关注人与物之间的结合,这是一次质的变化。当然,有问题出现就会有对策解决。例如,刚进入博物馆视野的口述史就是处理博物馆人与物相结合的最好方式。口述史一般是指用笔录、音频、视频等形式,记录采访者与访谈者之间就某个话题开展的一系列对话内容,是人对物或者事件的描述以及看法和思考等。地窝子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利用口述史,不仅践行人与物紧密相结合的理念,而且能改善遗址博物馆内的缺憾,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3.1 丰富展览内容
地窝子遗址虽不是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物,但可以是蕴含着深刻历史内涵的见证物。地窝子遗址博物馆是众多遗址类博物馆中的一员,长期以来,遗址类博物馆的展览一直围绕遗址及遗址出土物进行展示,内容单一,吸引力差。由于地窝子遗址属于近现代的产物,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很多物品被人们以“珍藏品”的形式保留下来,所以它与传统意义的遗址博物馆不全相同。
在地窝子遗址博物馆落成后,可以向文博机构以文物借展方式获得相关物品展示的权利。多数机构长期聚焦于古代文物,对于近现代文物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导致在征集文物时并不注重历史背景资料的搜集。但当这些藏品进入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后,就急需解决物与人相结合背后的众多问题。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利用前期大量采访得到的口述史,既可以将展品与该物品使用者对应起来,又能弥补展品在前期征集、购买、接受捐赠、借展时对其历史背景等信息搜集不全的状况,继而丰富展览的内容。当口述史与地窝子遗址博物馆的实物相互印证,或是与史料、田野调查相吻合,无疑会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材料,不仅可能成为博物馆未来收藏的藏品,而且能为展览增添新的展示内容⑤。
同样,让生活在十三师新星市的民众参与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史的建构,是当下充实展览内容的重要手段之一。邀请曾经生活在地窝子的军垦老战士及后代饱含深情地讲出自己及身边故事,并鼓励他们捐赠相关物件将是地窝子遗址博物馆未来开展工作的一个方向。通过口述史不仅收集了兵团老人的经历与故事,也改变了大众对博物馆的刻板印象,拉近博物馆与民众的距离,而且能有效促进博物馆藏品多元化,为博物馆展览内容开辟了新领域。
未来,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应把口述史资料征集与实物征集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由于地窝子这段历史涉及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很多职能各不相同的部门为了补充和完善历史文献资料,已经展开了相关的口述史访谈工作。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应抓住时机,与其他机构互通有无,将这段历史以拼图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丰富展览内容。
3.2 展览形式多样化
展览中的任何一件物品,在展出前有着各自特定的生成情境,以及复杂的内涵与价值,这些先决条件使展览在叙事上很难呈现出逻辑合理且完整的一个故事。而口述史以其表现形式的灵活性、叙事的纪实性、采访对象的特殊性等特点弥补了这一不足⑥,它能以文本资料形式直接出现在展柜、展板以及互动体验设备中,或以音频、视频等形式为场景复原、展品解读等提供素材,从而间接出现在展览当中。例如:通话机是互动性设备,可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展厅的互动屏幕中预先存入多位军垦老战士及后代的口述史访谈对话,大众通过屏幕选择通话的对象,接通后观众拿起屏幕旁设置的通话机进行聆听或提问,由人工智能自动截取口述史访谈内容进行回答。相信听他们说,更具说服力、感染力。照相机作为拍照工具,在展览中不仅应发挥其实用性功能,更要增加展览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观众操纵展厅内预先植入的多张照片的相机,可拍摄一张地窝子建造或者地窝子生活场景的老照片,照片拍摄成功后在其空白处自动生成一段关于老照片介绍的口述史文字。相比之下,这些比较单调突兀的通话机、照相机放在展柜中更能引起观众的关注。口述史的运用不仅对地窝子遗址博物馆的基本展陈进行了阐释,使展览变得耐人寻味,更为重要的是使展览的形式趋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利用它直观、生动、逼真的特点,给参观者带去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视听体验。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应主动探索,利用VR、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展示,在虚拟影像中将几条叙事线索交叉并置⑦。如参观者在虚拟现实中通过选取不同的讲解员,历史的见证者—相对年轻的兵团后代,或历史的参与者—一位身着军装、躬着腰、手里拄着根拐杖、迈着蹒跚步伐的老爷爷或老奶奶,邀请参观者到他们家做客,几位虚拟讲解员利用口述史为观众讲述具有神秘色彩的地窝子故事,通过他们的指引,观众可看到与众不同的地窝子及展品。见证者角度:虚拟现实影像通过口述孩童时趣事的方式反映地窝子的样貌。傍晚,参观者跟随几家的孩子跑出地窝子,奔向远方玩耍,直到天彻底黑下来,他们才急匆匆回家。由于夜晚视线弱以及地窝子为半地穴式建筑,他们有时找不到自己的家,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会突然听到一声大叫,这准是误踏他人家的房顶。参与者角度:在虚拟影像中会出现几处选址,讲解员对其一一分析,最终确定选址方位。口述史以最贴近大众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的面貌出现,不仅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而且起到丰富展览形式、增强吸引力、加深展览印象的作用⑧。
3.3 场景复原客观化
由于地窝子历时较短,作为普通的居住、办公与娱乐场所,官方的各类文字、图片资料中没有太多记载,而口述史的出现犹如雪中送炭。关于地窝子样貌的复原,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军垦老战士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地窝子的兵团后代对当代多处地窝子复原造型是不认可的,如地窝子的屋顶、天窗、门等,诸多细节与事实不符。但小部分复原专家们认为问题不大。
当前,关于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与军垦第一连所复原的地窝子坡面屋顶,存在很大争议。为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在建馆前,针对社会的声音,既不能搁置争议,也不能以专家身份单方面地垄断话语,而是通过引入不同的声音,将地窝子复原延伸为一次探讨⑨。那些曾经居住或出生在地窝子的人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人群。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在前期撰写展陈大纲和制作设计方案前,应针对军垦老战士及后代广泛开展“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地窝子建筑及内部构造时发生的各类事件”口述史访谈以及收集、整理工作,由于受访谈人员的身份与教育程度不同,他们表述时会掺杂个人的情感与想法,但我们相信通过个人感受的差异性来反映大时代的状况显得更为客观生动。
在制作复原场景时,就地窝子建筑的某些细节性问题,可利用口述史,但应格外注意辨别口述史的真实性。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口述者身上的历史密码获得了解析,诸如他们之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所以对某些细节,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尝试做出几种模型以便参与访谈的兵团老人确认。通过多位亲历者的描述与辨识,让待复原的地窝子建筑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这种让普通民众或者亲历者通过口述史途径参与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方式,不仅凸显了口述史的重要性,又能确保地窝子场景复原的客观性。
3.4 拓展展览叙事角度
历史见证物多数是过去遗存的碎片,其中蕴含的各类信息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地窝子遗址也不例外,它作为历史的见证物是抽象的、无逻辑的,只有通过人才能赋予其生命,因此地窝子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展示的主要内容,又是其存在的意义。
长期以来,地窝子遗址一直被视为进疆初期的生活场所,并未得到重视。直到近些年,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地窝子遗址亦是如此,从地窝子废弃到第一次修缮前的记录以及历次规划与修缮方案,这些资料如同地窝子的身世档案一般。由于地窝子遗址博物馆的建成时间晚于修缮时间,所以对于修缮和规划过程中遇到了哪类问题,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不甚了解,若要从正式的文件当中得到答案,也是不现实的。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可以对当时参与修缮的工作人员进行口述史访谈,并收集他们手头现存的资料以及当时的工作笔记、草图等。这既为未来再次开展遗址修缮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地窝子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新思路—地窝子遗址的修缮成果展。
类似于上述的展览思路还有很多,由于口述史中涉及的人和事,多数是过去人们了解较少的,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⑩,所以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应对多位亲历者口述史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根据不同的内容,策划不同的展览,如地窝子婚房布置与使用的规定、地窝子住房分配制度等,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也有助于人们通过口述史了解历史的真相。
4 结语
地窝子作为战士们进疆和生产建设初期的居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0世纪60年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兵团人搬入地上建筑,地窝子逐渐废弃被人们淡忘。吃水不忘挖井人,正是先辈们的付出才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不仅应当珍惜当下幸福生活,更应当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地窝子遗址博物馆落成后将以它的独特性,收藏与保存、研究与展示同军垦战士相关的藏品,但也是因为遗址类博物馆的单一性,大众无法深入了解其蕴含的内容。针对这类问题,本文利用口述史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存、恢复城市记忆和更新与延续大众的历史记忆的特点[11],来丰富地窝子遗址博物馆展览的内容与形式、展览思路。
(本文为2022年援疆工作部分成果。)
注释
①马梦.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访十三师新星市党委书记、十三师政委马学良[EB/OL].(2022-03-31)[2022-08-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801498114804301&wfr=spider&for=pc.
②③④张勇,牛力.新疆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军垦旧址勘测及修缮设计简报[J].文物建筑,2016(00):212-219.
⑤⑥⑩k肖冠雄.口述历史:博物馆资源再创造[J].上海陈云研究,2013(00):311-316.
⑦陈慧娟.从世界博物馆现状看未来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J].金田,2013(6):314.
⑧刘燕,邓普迎.口述历史与革命纪念馆研究[J].中国纪念馆研究,2013(2):148-155.
⑨侯春燕.口述历史博物馆化:博物馆学发展的新趋势[J].中国博物馆,2008(3):38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