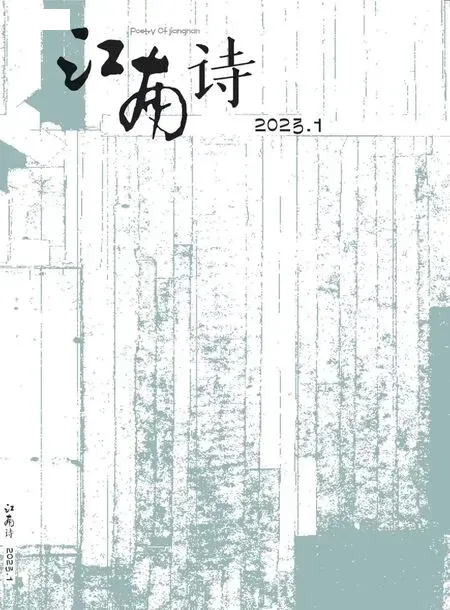诗歌,自己豢养多年的另一根阑尾
2023-04-15张文斌
◎张文斌
一、山村与诗
我热爱大自然,但是我首先热爱故乡的那个山村,这种感觉与生俱来,远在我会写诗之前。我的孩提时代,总是懵里懵懂的。父亲是不拘言笑的山村中学校长,也是语文老师,母亲是小学数学老师。他们总是望子成龙,从小逼我读天书一般的《古文观止》和《诗经》,学拉二胡、京胡和吹笛子,我总是很抗拒。我的兴趣在山谷,在丘陵,在旷野。除了到雅梅小学上课,其余时间都是在门前洋田野和家对面那片山林中度过。在粗糙的松树上攀爬磨破裤子,在高高的枫杨上掏鸟窝,在齐头高的茶林里捉迷藏,在泥泞的黄泥山道上滚铁环,在弯弯曲曲的山溪里抓石蟹,在半山腰的梯田上一层层往下跳,我过的是典型的浙南山区放养式童年,充满着原野气息和快乐。我从何时开始写诗,还真的记不真切,大致在读小学之前,在父亲威逼之下,写过一些十分幼稚的儿童诗。现在回忆起来,也就只记得其中一首的最后几句:“什么花儿冬季开,洁白雪花冬季开;什么花儿四季开,大寨红花四季开。”
黄坦,大山里的古镇,位于飞云江上游,明清时期,境域属青田县八外都。而离黄坦北面27公里处,就是明朝开国元勋、大明军师刘伯温的出生地南田镇,时属青田县柔远乡九都。它们于1948年同时划归文成县,县名取自刘伯温的谥号。所以我是从小听着有关刘伯温传说成长的。我在大山里念的乡村学校,然后一直在省城和外省读书,那些都是苦行僧般的生活,而如今能够让我回味快乐细节的只有水云峰脚下十分简陋的黄坦中学和前溪畔十分瘦小的雅梅小学。时常回忆学校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辈子拥有医学学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以及经济学博士学位,只有诗歌创作是自学的。没料到多年后写诗成为一种习惯,已似乎成为自己身上的另一根阑尾。不少人把阑尾看作是退化无用之物,但研究表明,阑尾本身有丰富的淋巴组织,它能分泌免疫物质,更能增强人体抵抗力。写诗,对我来说,就像《庄子·人间世》里说的“无用之用”。我觉得自己被黄坦古镇那里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所触动,一直不能忘怀。时隔多年后,我依旧有再现古镇风土的创作欲望,因为无穷的瞬息和记忆早已刻在我的脑回上。古镇属中山丘陵盆地,是蜿蜒浩荡飞云江的源头。常年覆盖着松林的丘陵山冈上,不时有挑担负重的村民走过。水云峰半山腰上常年云雾缭绕,山脚下就有白墙黛瓦的农舍。山脚不远处,过了石桥,村东头就是我的老宅,三间瓦房,我在这里生活了17年。有一年冬天,我放暑假回家,下午五点到县城时下大雪,到镇的汽车停开。我走山路,翻过整座水云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行走,回到老宅时已晚上九点。当母亲看到我一身雪花,脑门上热气腾腾,她当时就落泪了。如今慈母离世已三年多,我再也未敢回到这里,老宅在风雨中飘摇。因公务关系,我的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和国内所有的省份,无论我走多远,我的原点依然在水云峰和水云峰下的那片泥土。不管我身居于何处,心都居于形而上学的“老宅”中。离开黄坦30年后,我在《南歌子》里写到水云峰“它放慢了我的记忆,我的繁华和荒凉皆于此地升起”。陆陆续续写了近百首具有浓重黄坦味和乡愁的诗歌,结集成为《南歌子》出版了,扉页上写道:“谨以此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黄坦这片故土。”
多年以来,孜孜以求地学习和领悟各种诗歌技巧,想让自己的诗歌技艺日臻完美。在实践中,更多的只是机械搬运词句,生硬地表达人世间的某人、某事、某时和某地。后来才发现诗歌的一些重要元素,譬如简约、私密和戏剧性。诗是语言的超常结构,诗歌的语言是少而精的,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韦勒克·沃伦说过:“诗是一种强加给日常语言的‘有组织的破坏’。”正是由于这一破坏,给诗的语言增加了语言的陌生感和独特性。如果说诗歌是通神的艺术,那么私密就是通神的暗道。私密是洞察现实与你意识所见的联系密码,密码一定会有你故乡的基因。写有关故乡的诗时,我私底下会不自觉地用到一些黄坦土话和地名,那是刻在骨子里的DNA。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曾宣称的“一切诗歌的表现方式最终都是戏剧性的”。戏剧性则是诗歌属性的核心地位,背弃戏剧性绝不是聪明之举,那样会使诗歌艺术成为一种太直白的东西。我苦苦追寻多年而无法企及的境界,水云峰山谷中的那条山泉却把这一切都做到了。山泉总是那么简洁洗练,单纯明快,辞少意多。沿溪收集了松尘上的露珠、鹅卵石的秘密和翠鸟的私语,踩着只有水云峰意会的节拍。哪怕到了断崖前,也在断然超越自我,纵身一跳,据有与光阴相抗衡的力量,这是山溪达到的最高戏剧性效果,这就是大自然的诗,可以打垮现实中所有的诗人。
二、专业与诗
华夏大地历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自《诗经》以降,产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人们唯独把诗仙和诗圣这两顶代表诗歌最高荣誉的王冠戴在李白和杜甫头上,尽管他们两人没有文凭和专业,也阻挡不住后人对他们诗歌成就的首肯。英国大诗人威廉·布莱克终生未上过学,著有《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名篇。约翰·济慈15岁辍学后当了医生学徒,其作品《夜莺》如今可说是被奉为英格兰代表诗作。
从大山里出来,学医八年,先后学过放射专业,解剖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拍片子时,要像摄影家那样把控精准的曝光量,人体在射线下只剩一副骨架,没有气息和表情;制作人体解剖标本时,要像雕塑家那样反复斟酌,通过皮肤、浅筋膜、脂肪层、深筋膜、肌组织和神经血管,力图表现出层次感、空间感和秩序美;医生是个技术活,对开颅破肚习以为常,有着手术台上的“刀光剑影”和急救室里的惊心动魄。我想医学与诗人有相通性,需要悟性和洞察力。事实上,那时我写诗的题材与医学无关,试图描绘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和世界。也不懂得把细节从千姿百态的人世间当中萃取或离析出来,而是直接抓取。喜欢纯粹主义,根本不知道抽象创作是一种法宝。
后来到武汉在职攻读西方经济学博士,导师宋德勇比我还年轻,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苦读了三年,研究建模、边际效益、流动陷阱、函数、斜率、双重效用、投资消费等。在东湖边,冰冷的模型,悲伤的流动性陷阱、苍白的边际效益和繁复的数据,竟然让我焦头烂额,十分疲惫。写诗是自己与自己搏弈,就像在东湖边喝“白云边”,喝高时,快乐升水了 ,滞后期的痛苦紧随而来。也许面对诗,人是纯粹的。面对模型,人是功利的。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认为:“在这个聒噪喧嚣,充斥着各种思想的世界,诗歌的终极目的应该是重建沉默。”而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从人性出发,追求所有人的福祉。我做不到像20世纪美国大诗人埃兹拉·庞德那样有本事,他不仅发表有见地的经济学论文,而且还在诗歌创作中广泛应用。那三年,我用左脑写经济论著,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经济专著《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用右脑写诗,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诗影集《诗影江南》。
三、职业与诗歌
写诗对我来说是自己豢养多年的另一根阑尾,无关名声与期望,甚至有时候还是一种致命的痛。而职业,则是在人世间稻粱谋的一种妥协。周朝专门设立了采集诗歌的官员,称之为采诗官。由于他们的努力,时隔数千年,我们还能读到美轮美奂的《诗经》。到了汉武帝时,有乐府的工作者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演奏之用。唐宋元明清时期,均设有教坊,负责培养演唱诗歌的乐工,并纳入国家公职人员系统。
而我自然是没有这样的福分,近40年的职业生涯,除了短暂地当过教师和医生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政机关里度过。在中枢机关里,会写领导重要讲话的高手那是真正的高手,容易受领导器重和提拔。而写诗歌往往被看作“不务正业”,常常被同僚挖苦。在他们的思维定式里,似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省府路8号工作的八年时间里,白天用逻辑性思维写公文和领导讲话稿,晚上用发散性思维写诗文,就像两个人在体内不断拉扯和打斗。所有的诗稿都锁在抽屉里,没有去发表,更没有与其他诗人交流。事隔多年后,当我将出版的诗集送给曾经的同僚时,他们大吃一惊:“你竟然会写诗啊?”
在甬城工作的那些年,公务繁忙,诗越写越短,我很喜欢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汉斯·霍夫曼曾说的:“简化的能力,意味着剔除不必要的东西,从而让真正需要的事物吐露心声。”
比如我写海上那对白鹭时,只写了短短几句:“两片陷入爱情的雪,它们爱上了飞翔,始终没有融化。”
后来奉调到雪窦山下那座美丽的小县城工作时,压力很大,挤压了写诗的时间。每天六点半起床,十二点睡觉,脑袋里填满各种经济指标、政府债务和民生实事。三年多的时间,几乎中断了诗歌写作,却收获了高血压、声带息肉、荨麻疹和失眠症。
人生兜兜转转,从大山水云峰脚下出发,到了省城宝石山下读书并工作,再到旅居四明山下,后调往雪窦山下的美丽县城就业,三年前又回到了宝石山下时,已是过了知天命之年,我用不同的职业豢养身体内的另一根阑尾,却一直未被割除。
习诗几十年,尽管也出版发表了诸多的诗集和作品,写诗不是我的职业,是源自内心的召唤。如帕斯所说:“每个诗人都是传统之河上的一个波纹,语言的一个瞬间。”也可以理解为,我只不过是黄坦水云峰脚下,山溪里的一道波纹而已。一声山鸟的鸣叫,终将归于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