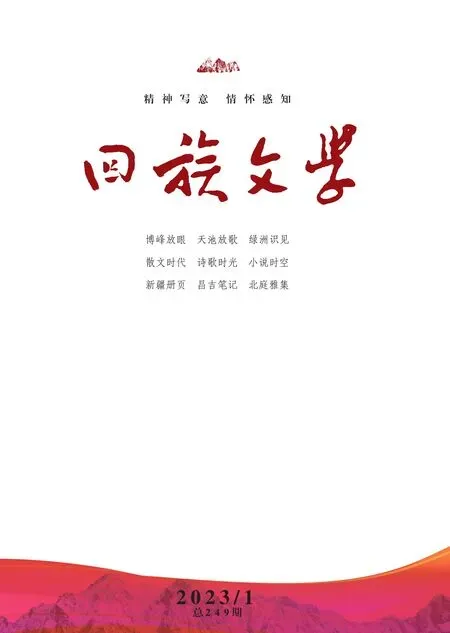生活解剖录(组篇)
2023-04-15曾龙
曾 龙
丁 克
我从小便决定不生养儿女。
父母的婚姻给我留下了极深的阴影。撕打、争吵,司空见惯的血、伤口和弥漫的硝烟,让我的生活充斥着颤瑟与不安。儿女,这对生命个体有限性的补充,抗争死神的利器,抑或未来的豪赌,成了我拒绝复制的悲剧。
孩子可爱、无邪,在恋人的交媾中点亮了存在的图腾。这团同时兼备了残疾与完美的圣火,让无数人为之燃烧终生。
我曾有个叫林的女友,每日幽囚斗室,醉心阅读与写作,在忘我的生活中乐此不疲。林深受梭罗的影响,喜欢《瓦尔登湖》与大自然,除却精神与存在的求索,傲视一切的物欲与名利,甚至淡漠亲情与母性。她定定地告诉我不想结婚与生育,只想在写作中获得永生。不久,林独自行往终南山,消隐于世。
我无法理解林的行为,也未读过《瓦尔登湖》,更不懂深奥的存在主义,只觉得她的想法甚为荒谬。文字,多么廉价的象形符号。每人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大量生产着信息垃圾,她却希冀从这些垃圾中拼凑出永恒;人类文明都不配奢望的果实,她却狂傲地想僭越上帝的灵位。
那时我正整日醉心名利,奔赴于各种社交场,希冀在推杯换盏间猎取人脉。幼年的经历使我渴望在光环中伪饰内心的自卑,哪怕那样的光环只是一层镀金的项圈。尝到甜头的我,像一只即将大放异彩的蝴蝶,在热捧与虚荣的暗茧中积蓄势能。
林劝我沉下心来阅读与写作,少去追逐那些名利场上的过眼云烟,我却对她的话不屑一顾,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林,这个枕边的依偎者,温柔而体贴的伴侣,却越来越变得像一个潜伏在我身边的猎人,企图在我破茧的那一刻扣动扳机。后来,我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同样以丁克作为归途的我们,最终走向了人生陌路。
不久,林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像空气一样从我的生活里淡去,却越来越变得像一块顽癣,让我瘙痒难忍。
世界变成一个子宫,不死的婴儿,在羊水中任性畅饮。
是否,拒绝死亡,拒绝牧师的祷告与安抚,拒绝天堂的降临,拒绝地狱的火,拒绝因果轮回与报应不爽,拒绝沙漠里生长绿洲,就会让生命获得永恒的延续。
其实林不懂得繁衍也是延续存在的方式,甚至更为简单易行。基因见缝插针传播后代,古希腊人希冀借由肉体的延续获得灵魂的永存。当林有一天成为人妻,生育了一堆儿女,她同样也可以拿起教鞭,在严厉的面孔下向他们灌输存在主义、梭罗……直到孕育出一批淡泊名利、淡漠情感的存在主义者。就像那些将孩子锻造成考试机器的家长,希冀通过一次金榜题名,让自己随着鸡犬升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冒险,反而顽固、彻底,矢志不渝地为信仰殉道。她恐惧儿女会成为一张潜藏于暗夜的蛛网,伺机将她困束,使她无法挣脱,直至被吸干成一具空无的躯壳。她要清晰而确定地存在,像主人掌握着宠物的生杀予夺。
我没有林追求自我的勇气,生存的铁蹄将我践踏成了卑躬屈膝的奴仆,在无痛的模仿中惯于复制他人的人生。逃避存在、思索、死亡的清缴与追问,在美丽的虚无之上建造意义的天国。林,这个离经叛道的另类,这个不容世俗,也不被世俗所容忍的亵渎者,她是如此急切而傲慢地拆穿国王身上那件羞耻的新衣,最后再潇洒而永远地逃离。
林是否也饱尝过孤独与虚无的苦痛,是否知道生离死别、旦夕祸福,都掌控于神的恩典与护佑。或许,神也是一位丁克,他的神性只是无须繁衍而抵达了永恒。
仪 式
仪式是对死亡的抗争、表演或自欺。
我惧怕青春的慢性衰亡,以至于每年都会在生日和跨年举办各种仪式,期许在时间的脊背留下齿痕。
大学的某次跨年夜,我正在宿舍绞尽脑汁筹划新一年的跨年仪式。临近午夜时,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念——为逝去的一年举办一场葬礼。有了念想后,我立马打开手机的音乐软件搜索丧歌,随着悲怆而高亢的旋律响起,我开始面对着墙壁默哀,脑海中飞速闪现过去一年的际遇。
就在我沉浸于回忆时,一声破口大骂忽然从我身后传来。我惊愕地睁开双眼,回过头,只见宿友盘腿而坐,瞪着一双讶异而愤怒的眼睛。我这才恍然,刚刚一心想着跨年仪式,忘了睡梦中的宿友。被丧歌吵醒的宿友,龇牙咧嘴地咆哮起来,“要不是我脾气好,早就把你暴揍一顿了。”
不断以尴尬收场的仪式,并未让我有所醒悟。不久,我与好友阿基去大西北七座城市巡演,回到学校后,又开始琢磨着用什么方式来告别即将结束的大学时光。最后,我们决定在学校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毕业演唱会,阿基演出,我演讲。
举办毕业演唱会需要场地,在街边或学校操场实在太low,我们便将目光瞄向了学校唯一的报告厅。
老师生硬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越过老师去找系主任。系主任是个和蔼的中年男人,他听过我们的想法后没有直接拒绝,推说要先向学院领导申请,让我先回去把活动方案拟出来交给他审定。回去后,我兴致勃勃地花了两天时间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活动方案,满怀期待地上交,结果半个月后得到的答复却是“领导不批”。我并不死心,仍然日日去办公室纠缠,最终成功打动系主任,他以系里的名义为我们申请到了场地。
申请到场地,余下的任务便是招募观众。我们打印了数幅海报贴满了学校各个教学楼,每到晚饭点就去宿舍楼下、食堂外等人流密集处演出。后来,见反响平平,我们便拿着演出设备每日跑去六道口和中关村附近街演,就这样宣传了半月,观众群里的人数终于破百。
一个月后演出开幕,来的观众不多,仅前排寥寥坐着数十人。开场节目是霹雳舞,表演者为学校田径队一队员。因节目未经彩排,我并不知表演者的真实水平,只是见有人主动报名支持活动,便都批准了。结果,那名队员上台后在劲爆的音乐中四肢僵硬、扭扭捏捏,活像耍猴,让人大跌眼镜。第二个节目为阿基的演出,阿基抱着吉他在台上刚要开口,不料报告厅的音响忽然发不出声音,我们连忙把平日街演的音响插上才应了急。阿基的演出一如既往地精彩,浑厚的嗓音里激荡着青春的不羁,不过在演唱一首原创歌曲的高音部分时却意外地破了音,引得台下哄笑连连。演出最后是我的毕业演讲,为显隆重,从未穿过正装的我向朋友借了一套大码西装,结果登台后宛若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处处流露着别扭。最终,演唱会就在这样接二连三的意外中狼狈收场。
大学毕业后,我与阿基各奔东西,但我对仪式的追求却丝毫不减,每次生日会给自己写一封信,每年跨年都会去拉萨,在凄冷的布达拉宫前对坐一夜……我就在对仪式狂热的追求中挥舞着对抗时间的利剑。
当有一天我行将就木,是否命运会将我所有的仪式串成一圈献给死神的花环。
朋友圈
我喜欢发朋友圈。
我一天最多发过二十条朋友圈。
大学我没上过几天学,学校为放养制,每日不用签到,也不用为学分与论文疲于奔命。考试全为开卷,为防学生在书上找错答案,老师还会提前将开卷的答案公之于黑板。
班主任为一大腹便便的老头,两颊间挂着一颗熟樱桃般的酒糟鼻,他每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等上课铃响后,去宿舍被窝里掏还在睡梦中的学生。
宽松的氛围使我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自由探索,其中最为醉心旅行和各种活动。大学我近乎跑遍了全国,常有了神往就会立即起程。到景点后,我会立马掏出手机,打开朋友圈开始拍摄录制,再配上一段装模作样的话语。一趟下来,数十条动态陆续以刷屏之势霸榜朋友圈。
有一段时间,我无钱再去旅行,为了不让朋友圈停更,于是制订了每日爬一座山的计划。连续一个月,我都坚持早起,坐公交去打卡北京的各座名山。虽疲惫不堪,但只要见有人在朋友圈互动点赞,便又斗志满满。
除了旅行,大学参加的活动更不计其数。其中有如发呆大赛、死亡咖啡、逛鬼市等博人眼球者,也有各种高端的讲座与音乐会。后来,参加的活动多了,我对活动开始挑剔了起来,只挑取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活动打卡,如邀请了某某诺贝尔奖获得者、某某著名作家或学者。去到现场后,拍照定位转头即走,然后在朋友圈编辑一段心潮澎湃的话语,宛若备受洗礼。若因其他事情冲突,无法亲临现场,我会把链接发给好友,以各种理由怂恿他去参加,等收到活动现场照,我再移花接木地假装去了一番。
用博取眼球指摘我大学里的行为实在有失偏颇,事实上,我这晒朋友圈还有一套自创的理论,叫作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活。操持着这样的理论,我开始像只不知疲倦的飞鸟,往返于北京各地,以此让每一天都度过得新奇而有趣。学校有一姓王的好友为我拥趸,我们趣味相投,时常结伴打卡,在实践中不断充实着我们的精神胜利法。
除了在朋友圈晒旅行和活动照,平日里我还喜欢写些无病呻吟的诗歌。每日笔耕不倦,灵感泉涌时,一日会写上几大首。我自诩为八岁写诗,天赋异禀,同时难耐孤芳自赏,每日会像晒活动照一样,在朋友圈穿插着晒我写的诗。甚至还更进一步,将发在QQ空间的诗转到各个群,借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为此,我开始疯狂地在QQ上加群,每当群主通过后便立即转自己的作品。如果作品后面回应着陌生群友的鲜花与夸赞,甚至有接连的好友申请,我就会为自己的才华得到他人激赏而扬扬得意。
若无人回应,我也并不气馁,仍会每天按时按点地转发作品,笃定坚持不懈终会打动群友。每日心绪就随着作品的阅读和点赞数波动起伏。这样的转发我整整坚持了两年。
朋友圈成了我个人的导演和狂欢,我沉迷其中,每日的生活和情绪受其左右。直到毕业后,我开始疲于为生存奔命,朋友圈才日渐减少,偶尔发一条也是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几年后的一日,我因翻找之前的照片,偶然滑到了大学所发的朋友圈,不由触目惊心。眼前的自己是何等轻浮与陌生,在荒诞的行径中不停耗损着青春,而过去那些让我自鸣得意的诗歌,其实读来满目疮痍,语言肤浅,结构紊乱,像号叫般充斥着无病呻吟。在客套的阿谀和甘美的毒药中,我不停地为自己加冕。
而今,我已近一年没发朋友圈,也不再写诗与旅行,甚至淡漠了一切社交,在迥异的生活中稀释着过去。朋友圈,我曾经坚贞不渝的信仰,成了我如今不敢触碰的谎言。
兴许,有一天我会彻底将朋友圈关闭。
网 瘾
我初中时染上了极重的网瘾,常会趁午休偷跑去网吧玩一个小时,晚上又继续翻墙通宵。
在网吧通宵叫包夜,一晚十元。学校为防学生晚上偷跑出去,将宿舍一二楼的窗户都加装了铁栏。想去通宵,必须用一包烟买通查寝的高年级学生,否则只能等查完寝后去爬水管。
曾有胆大者,犯了网瘾,直接从三楼的阳台一跃而下,竟毫发无损,不过无人敢去模仿,一般都会从三楼偷爬水管。水管光滑,需先侧身抱紧,然后慢慢腾挪,等找好着力点,再从窗台一跃,便可直接滑下去。不过爬水管同样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从三楼摔下去,轻者破皮见血,重者骨折。我有恐高症,从未爬过水管。
我一周生活费仅五十元,除去车费和饭钱,余下的就全部贡献给了网吧。随着网瘾愈烈,网费的占比开始节节攀升,我只能不断挤压伙食费。一次,我连着去网吧通宵了两夜,提前花光了生活费,余下三天我粒米未进,每日头昏脑涨,最后得一位同学救济才撑了过来。
不久,通宵上网的事败露,班主任将我唤至办公室,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爷爷骑着摩托车从二十多里外的老家火速赶至学校,一进办公室便满脸赔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好烟双手奉上。班主任接过烟,眉头渐渐舒展,语气也缓和下来。不过,他却坚持要取消我的住宿资格。生性老实的爷爷听后望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自此,开始每日起早贪黑接送。
一日放学,天空电闪雷鸣,乌云密布,我钻进爷爷的雨衣,像狼狈的逃兵顶着骤至的枪林弹雨。快近家时,摩托因泥路淤积寸步难行,爷爷让我先步行回家,他再慢慢将摩托推回。我到家,食过晚饭,仍不见爷爷回来。磅礴的大雨在眼前倾盆而下,如狂乱的鼓点。
不久,一个浑身上下血迹斑斑,一瘸一拐地推着摩托车的身影缓缓出现在眼前。在大雨里,爷爷深一脚浅一脚,踉跄着好不容易挨到家。我这才知道他因摩托车轮打滑翻入了沟底,险些丧命,许久,才忍着伤痛,将摩托从沟渠拖出。
爷爷的瘀青像一根针,在我的体内迅速蔓延、游走。每当我网瘾难忍,那根看不见的针就会以一种剧烈的刺痛终结我对虚拟世界的痴迷。
今年夏末,我偶然路过初中常去的网吧。门窗内陈设未变,唯机型换新。不过比起我上学时的人头簇拥明显清寂,玻璃门上贴有一张网吧转让的纸条,像在兜售着一座廉价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