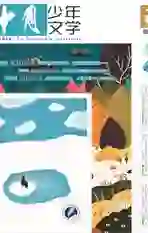柴火般暖的人
2023-04-12夕子
多少次,
我在梦里,
如一架飞机,飞呀飞呀,
越过重重光阴,
停落于
在外婆身边度过的童年时光里,
在那儿慢慢加满油,
再飞回来。
灶膛里,两根木头交叉摆放,外婆从土箕里抓了一把干松针扔进去。松针助燃,刺啦作响,木头引燃了,柴房亮堂了。像水面一样晃晃荡荡的火光,让外婆的面庞犹如透过层层涟漪看到的水中倒影一样,也是飘飘悠悠的。
外婆时而起身时而坐下,瘦小的身影忽明忽暗。铁锅热气腾腾,靠墙一侧伸出来的一截细竹筒里,蒸馏而出的米烧酒汩汩流出,刚好落入底下的粗陶酒坛里。温一小壶自家酿制的米烧酒,是这儿待客的礼俗。
柴火旁暖洋洋的空气里,混合着松针和米酒浓郁的香味。我坐一条小矮凳,双手托腮支在膝盖上,守在外婆身后,如一只温顺的猫咪。确切地说,是一只等待美食的馋猫。不久,外婆用铁钳从灶膛里夹出一个个煨鸡蛋、鸭蛋、红薯、板栗或芋头,像掘开了一座宝库。她一边倒换着手捧着滚烫滚烫的鸡蛋,一边嘴里呼呼地吹蛋壳上的黑灰。淡淡的焦香诱人,我迫不及待地剥开蛋壳,咬上一口:真美味!煨过的鸡蛋比水煮鸡蛋要更紧实、更细腻。
外婆在后院养了一群鸡,鸡蛋天天有;外婆每天围着灶台打转转,煨鸡蛋也就天天有。我就是在外婆一个一个煨鸡蛋的喂养中长大的。
长大后,不管我的世界有多大,离外婆有多远,外婆始终都是如冬日柴火般暖人身心的存在。那暖烘烘的柴火的光亮,也一直在照耀我前方的路途。
一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她和这儿所有的女人一样勤劳,在田地里日晒雨淋,在家洗衣做饭,眼里心里装的尽是活儿,从早到晚少有停下脚的片刻。但是,外婆有天生的白净皮肤,怎么也晒不黑,出门总是穿戴整洁,头发梳洗得一丝不乱;若去做客,外婆会在手腕上套一个玉镯子,手指上戴一个雕花银戒指。而且,外婆说话总是轻言慢语、客客气气的。不像有些人在家也会扯着嗓门说话,常年跟人吵架似的,隔着一条巷子都能听到。
母亲说,年轻时候的外婆在镇子里可是出了名的标致可人,巴掌大的瓜子脸上却有着轮廓分明的五官,眉目疏秀,两根乌黑透亮的辫子,皮肤又好得出奇,无论是自个儿去池塘边的丝瓜架上摘几根丝瓜,或是拉着小姐妹去村东头看台花鼓戏,还是跟着太婆去土地庙烧个香,都有人等在道旁或一路追着看她的模样。后面的故事当然也是母亲说的,外婆和外公的父母家都做点儿小生意,因往来合作密切,两家父母商量着就成了亲家。
外婆家中没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只能靠想象。要是能穿过时间的隧道,一睹外婆少女时代的芳华该有多好。虽有遗憾,但在成年后的我看来,外婆是不曾上了年纪的,她的身上始终留存了某些少女的气息:无论生活有多么粗粝,仍有对美的顽固持守;仍然有天真活泼的心,和小孩子总能玩到一处;说话从不尖酸刻薄,总有一种因照顾他人感受而表现出来的含蓄、善意或羞涩……想到这些,儿时的画面便一幕幕地涌到我的眼前。
一个夏天的下午,从隔壁镇子吃完酒席回来的邻居在院门口议论:做寿人家的儿女为表孝心,请了电影放映员晚上过来。不知有多久没看过电影了,我喜得心花怒放,咚咚跑回屋内。
屋内只有小姨,正在试穿她的松糕鞋。“我可舍不得让这双新鞋第一次就走远路。”小姨一口回绝。我盯着松糕鞋厚厚的鞋底,突发灵感:“不是可以找对象吗?”这话是从隔壁小伙伴冬梅那儿听来的,据说她爸妈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认识的。“像我这样的,还用得着去找吗?”小姨总以为自己如花似玉、美若天仙。我朝她吐了吐舌头,耸着鼻子没好气地答:“哼!小心嫁不出去要做老姑娘。”那时候“臭美”一词还没时兴起来。
外婆呢?外婆不在家,说是去菜地里摘瓜果了。在哪处菜地呢?我出门到处找,溪畔的扁豆地,桥洞下的冬瓜地,古井边的辣椒地……每一块我曾跟着外婆去过的菜地都跑遍了,可就是不见外婆的踪影。气喘吁吁中,汗珠子吧嗒往下滚,泪花子也扑扑往下掉。
“玲子,大热天的,跑什么呀?”没错,是外婆的喊声。我循声望去,外婆站在高坡上,正戴着草帽立起锄头定定地看着我。听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后,“看来我得早早收工啦!”外婆只轻巧地答了这么一句,就又埋头给秋豆角搭架子了。我开心得在原地转起圈圈来。我就知道外婆会答应!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外婆。现在想来,那种被宠爱的感觉多么好,那里边有一种坚信,就是坚信那个人总会尽心尽意地成全你,哪怕你有一点点任性,一点点刁蛮,也坚信那个人乐意和你待在一起,不嫌你麻烦,也不嫌你闹腾。
外婆果真早早收了工,提前和我吃过晚饭。“小孩子娇皮嫩肉的,最容易被蚊虫叮上了。”外婆一边说一边给我换上了一身绵绸的长衣长裤。虽是旧衣裳,但有娴静的小碎花,不蔓不枝,透着太阳晒过的芬芳。外婆拿起粉色头绳还要给我扎羊角辫,我有点儿不耐烦:“不要扎了!晚上墨黑墨黑的,谁会看我的头发呀。要是去晚了,电影可就开场了!”我恨不得即刻抵达,守着放映员搭建银幕才安心。
中途,遇到去看电影的几支队伍,有好多小孩子都跑来和我搭话,一边玩耍一边赶路。我那会儿已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一身清爽的孩子。比起那些浑身脏兮兮的小孩,我心里头是有自豪的。而重要的是,稍稍讲究一些,让自己赶赴的心情好像也更郑重、更美丽了。
到了那儿后,做寿人家的地坪上,几个大人拿着铁锹还在挖坑,正准备用两根长木搭建放电影的白色幕布呢,就像外婆在来的路上预料到的那样。人头攒动,有搬了竹椅或板凳来的,有趴在稻草垛上的,也有爬到树杈间的,还有坐平房顶上看的。背着泡沫箱子卖绿豆冰棒的师傅尚未到,大伙儿还没到口渴的时候。
放的是什么电影,我已全然不记得。但我记得,有一场电影快到剧终时,情节感人,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往旁边一瞅,外婆正拿着花手帕拭泪呢。不知何时,外婆悄悄递过来一根绿豆冰棒。那时的钱值钱,绿豆冰棒得五分钱一根,但外婆可不会让我少掉这份快乐。闻着绿豆的清香,吮着沁凉的甜水,看幕布上场景变幻,甭提有多惬意了。
电影散场,回家就是走夜路了。快活的萤火虫在瓜棚底下舞蹈,可爱的青蛙们在荷塘里呱呱对唱,心满意足的我,在乡间小径上走得飞快。小径两旁没有路灯,夜黑得像锅底。外婆打着手电筒走在后边,时不时叮嘱我要慢点儿跑,要小心左右的沟沟渠渠。
到了家,已是深夜。尽管来回走了二十里地,躺上凉席后,我仍是兴奋得睡不着觉,要吧啦吧啦聊电影,谁谁谁太坏,谁谁谁不该死,结尾要是怎样才如何如何好。蚊虫嘤嘤嗡嗡地绕来绕去,外婆的蒲扇在我的身上摇来摆去不停歇。直聊到再无话可说才沉沉睡去。梦里,有电影中各式角色的喜怒哀乐,有冰棒里熬过的绿豆的清香,还有甜酒冲蛋令人微醺的甜香。
二
甜酒煮沸,倒入蛋液,外婆用木勺一拌,米白中便荡漾起片片金黄,醇香扑鼻。一觉醒来,睡眼惺忪中,喝上一碗外婆调制的甜酒冲蛋,通体舒畅。
碗一放下,院子里就传来小伙伴们的喊叫声,像是迎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踢毽子的,跳皮筋的,抓子儿的,拍三角纸板的,还有玩东南西北的,院子俨然是一个小型幼儿园。那是一个没有平板和网络的时代,我们在古老的游戏里,在真切的人群间,在四季流转的大自然中,找寻最简单的快乐。
与其说左邻右舍的孩子爱来找我玩,不如说他们爱来外婆家的院子玩。外婆家的院子宽敞、整洁又漂亮。她每天早起洒扫院落,料理植物。农具整齐地靠墙摆放,小花坛也都在角角落落里,种着高高的开红花和黄花的美人蕉,矮个子的是鲜红的鸡冠花,也有玫红的夜来香和爬墙的月季。院子中央就留出了一大片平整的空地,我们疯起来也不用担心磕磕碰碰。小孩子追追赶赶的时候,可都是不看路的。
而院子的女主人—外婆,不嫌热闹,对待小孩子和和气气,用本土话形容是“耐得烦”。跳房子用的“田螺项链”,是外婆穿成的。在一个个田螺空壳上扎上孔,将线穿过孔,就穿成了一条踢起来会清脆作响的“田螺项链”。丢沙包用的沙包,是外婆用零碎布头裹入沙子缝制的。我们折叠的纸飞机怎么也飞不起来,外婆会手把手地教。打仗用的刀剑棍棒之类,打在身上是不疼的,是外婆带我们用挂历纸糊出来的。
农闲时节,外婆将衣叉杆当成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扛在肩上,挺起肚子绕着院子踱步,会加入我们一行人马演《西游记》呢。客串到中途,外婆忍不住笑得捂肚子,很欢畅的样子。我们都人小鬼大,猴精猴精的,能很快辨别出哪些大人是真心想和我们玩的,是享受其间乐趣的,而不是三心二意或是做做样子而已。外婆无疑是属于真心爱和我们玩的。
有个叫“解手绢”的四人游戏,就是在同一方伙伴的手腕上将手绢系到最繁复、最结实,然后跑去和另一方调换,看谁最先解开对方系的手绢。解得慢的一方就输了,要求表演节目。外婆输了也不敷衍,每次都唱花鼓戏。“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啰/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行哪/走啰嗬/行啰嗬/走啰嗬/行啰嗬/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哎哎哎……”外婆的双手有时上下挥舞,有时左右摆动,像各执了一把彩扇似的飘逸。这样节奏欢快的曲调,带着鼓动性,我们根本稳不住,听一会儿就跟着外婆扭动起来,动作有夸张的也有怪异的,一顿群魔乱舞。
“风箱拉得响/火炉烧得旺/我把风箱拉,我把锅来补/拉呀拉补呀补/拉呀拉补呀补……”外婆有说有唱,夹杂着撩门帘、端茶、擦汗、推拉等动作,一人分饰几角。后来我才知外婆的这两个拿手曲目,一个叫《刘海砍樵》,一个叫《补锅》。虽然不懂唱词的意思,但旋律都喜庆又诙谐,我们都爱听,听得多了也都会哼唱了。
除了唱花鼓戏有模有样,外婆做起法官来也是有板有眼。我们不仅爱表现,还都争强好胜,为争出个你输我赢,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外婆上前,一把拉开两头正顶得不可开交的小牛:“谁先动手的?动手在先的,先道个歉,再讲别的。”这头的小牛气呼呼地指着对方的鼻子:“是他先动手的!”那头的小牛急得眼圈红红:“你耍赖!明明是你先动手的。你不仅动手,还骂人了!”这时,外婆就得找“目击证人”了。但围上来的各路“目击证人”,七嘴八舌中往往又带着各自的私心,跟谁关系好就会偏袒谁,甚至想借此一报私仇。那时候的我们,世界小得很,心眼儿只有米粒大小,都是睚眦必报不好惹的主儿。事情还真是棘手呢。好在外婆总有办法,能让双方达成和解并心服口服。
一到饭时,各人的家长就站地坪里响起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小伙伴们乐不思蜀,有些磨磨蹭蹭还要玩上一会儿。外婆一边择菜,一边帮家长催人:“伢子们,呷了饭过来,才有劲耍。各回各家喽!”
三
有些小伙伴玩心重,把家长的话当作耳旁风。家长唤了几次仍不见人影的,就有直接来外婆家寻人的,有些家长手里还拿些贴己的东西互通有无。
“上回我一个表兄家新房子上梁的时候撒糖果,我在地上捡了满满两衣兜,吃完酒席还打发了一袋子糍粑。两样我都拿了点儿过来,给玲子当零嘴啦。”五彩的糖果和白花花的糍粑分装在红袋子里递了过来。盛情难却,外婆道着谢接了过去。我眉开眼笑地跑过去挑糖果,剥开糖纸最艳丽的那一颗扔嘴里:“我等下不要米饭,要吃糍粑。外婆给我烙糍粑,要不要得?”
“有个好吃鬼,糍粑还能留到过夜啊?让你吃完就不用惦记了,免得你一天到晚叽叽歪歪缠磨人。”外婆瞪了一下我,故作嗔怒,进屋烙糍粑了。糍粑搁在火钳上,待糍粑烤到两面焦黄,外婆插入一块黄片糖,就可以入嘴了;黄片糖快速融化,待黄褐色的糖汁就要从糍粑上淌下来时,我的嘴迎了上去。糍粑软软糯糯,我用嘴将里边的丝扯得细又长。
来院里寻人的,也有拿了菜过来的。“上午摘了一担葫芦南瓜回来,两个小的给你。大的切开得吃上几天,连吃几顿就腻。觉得好吃,让玲子上家来搬。你种河岸的南瓜苗不是被水给淹了嘛。”葫芦南瓜是一种葫芦形状的黄皮南瓜,果肉紧实,又甜又面。外婆笑吟吟地接过瓜:“费心了!都记挂我家南瓜今年没收成。结果比起往年,今年还要多吃了一些南瓜哩。”
我也隔三岔五被外婆差使,给东边婶婶送几个外婆自制的松花皮蛋,给西家大娘送两个刚挖出来沾着泥的白薯。我倒喜欢这类跑腿的事,看到人家欢欢喜喜的,我心里也说不出的高兴。有时人家收了东西,进屋就拿了小零食出来,泡泡糖、酸梅粉或辣椒糖。我跑起来更带劲了。
有傍晚来院子里寻人的,小孩子若还不肯走,大人就和外婆多扯上几句家常再等上一会儿。傍晚时分,人们都收了工,不用赶点了。聊来聊去就不免聊到眼前的孩子。
“你看,我家冬梅个儿比玲子矮一截了,她吃饭太刁。牙齿是越长越稀,眼睛眯眯的就一条缝,光占爹娘的缺点。以后还不知有没有人家肯要呢。”冬梅的奶奶倚着门框对外婆说。冬梅的弟弟和另外几个孩子在玩地道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怎么也不肯回家。冬梅在旁边守着。
以前听冬梅讲过,打从她出生起,奶奶就不欢喜她是个女娃,虽是头胎,满月酒也不肯做。奶奶平常宰了鸡鸭只端去给弟弟吃,没有冬梅的份儿。冬梅到哪儿都带着弟弟,像个小小的母亲。若弟弟身上有磕着碰着的地方,奶奶骂起她来口无遮拦。
“可不能这么讲小孩子!他们都还没长开的,一年一个样。女大还有十八变呢。再说了,你家冬梅眉毛生得威武,头发多细多黑啊,逢人就喊,一口的笑,任谁都想生个这样的宽心宝。”外婆放下手中的活儿,向冬梅看去。
“可不能这么讲小孩子”几乎就是外婆的口头禅。若有大人评论孩子长相的好丑,外婆还说过:“长相又不是小孩子自己选的。人都生出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眼光脚健最要紧。”“眼光脚健”是本土话,大概是眼神明亮、四肢健壮的意思。这也是逢年过节外婆在堂屋祭祀先祖时,口中反复念叨的一个词,她只祈求先祖们多显灵,护佑全家老小都眼光脚健。
外婆这么看别人家的孩子,也这么看自家的孩子。外婆就从未说过丁点儿玲子眼睛生得小、鼻子长得塌之类的话;在外婆的眼中,玲子哪儿都长得恰恰好。后来,我上了学,看到同桌因为长相而暗暗自卑,我就用外婆的话安慰她。与同桌不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长相这件事根本不在意,我就傻乎乎地认定:我家外婆从小就夸我长得好看,那就是真的好看啦;别人夸我好看,很可能是恭维,但外婆是我最亲的人,她说的一定是真话。
四
“做爆米花的师傅来了!”有小伙伴在院门口报信。我们一听,不约而同地拔腿就往外跑。
我钻进人群,正见一个老师傅接过邻居的一小袋白米,倒入一个铁筒。铁筒有个圆滚滚的肚子,外层被烟熏得乌黑,我们叫它“黑炮弹”。老师傅将一侧的盖子用力拧紧后,往炉子里添上一把木炭,再把黑炮弹搁炉子上。他的手抓住方向盘似的圆柄摇啊摇,炉火呼呼地烧呀烧,黑炮弹飞速地转啊转……待到他一把拎起笨重的黑炮弹,要和躺地上随时待命的布袋子对接时,有男孩大呼一声:“黑炮弹要爆炸了!”我捂住耳朵第一个扒开人群跑了出来。
只听身后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还有男孩们的尖叫声。好吓人!待白色烟雾散尽,米香味飘出,我又凑了上去。挤进去后,我发现外婆就站在对面,正拎着一大袋子苞谷粒也在排队呢。
外婆晓得我容易眼红,每次只要老师傅过来,她都会拿一袋大米或苞米过来。回去路上,我一股脑儿扎进手上捧的爆米花,一口一口,差点把几粒爆米花吸进鼻子,按外婆的说法,就是饿得跟从牢里刚放出来似的。“哎呀呀,今天怎么爆了这么多的米花呀?”我将黑砂掌又伸向了外婆手中的袋子。外婆有点儿神神秘秘地说:“今天晚上呀,家里要来好多人,只怕不够吃。”
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大事吗?难道是小姨的对象找好了?可那也只多了一个人;不对,还得有一个媒婆,但总共也只加了两个呀。难道是父母亲要把我接回去?那我可是要倒地上打滚撒泼的。我心神不宁地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谜底在下午就揭晓了。原来是外公买了一台电视机回了家。这可是村里的第一台!我奔走相告,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这事。
这台黑白电视机是上海牌的。小小的、带天线的灰盒子,却能播放节目,还可以咔嚓咔嚓调频道,可真稀奇啊。果然,屋子里站满了人,窗户上也趴着人。电视屏幕上闪现的雪花点,不时插播的广告,偶尔发出滋滋的嘈杂声,都没有减少我们对下一个节目的耐心和期待。我们一边吃着脆香的爆米花,一边盯着电视屏幕,兴奋不已。
这可是件宝贝,外婆第二天就给电视缝了一件连体衣,是一个碎花布罩,锁着荷叶边,与电视机的身段严丝合缝。天色向晚,外婆把电视机搬到院子,搁在饭桌上。院子里可以多挤一些人。来了年纪大的人,外婆忙着回屋给他们找凳子端茶水。有些小伙伴看到很晚还意犹未尽,家长只好过来将人一把扛回去,若出了院门,还能听到哭闹声,外婆就跟出来,站院门口喊:“电视已经关了,玲子也得睡了,明天再来啊!”小伙伴听了这话,心安了些,从大人的肩上跳下来,依依不舍地走回去了。
不到一年,村里其他人家也陆陆续续有了电视机,晚上来家的人渐渐稀少。但外婆家里又来了一个稀罕的新玩意儿,那就是电话机。因外公做生意,常常需要与江浙的商家往来,那边安了电话机的商家就几次三番地让外公也装一台,这样联系起来方便。这下,外婆家又热闹了。
那是一个米白色的座机,右侧是数字按键,左侧搁放话筒。在我眼里,电话机可比电视机要先进。连着电话机的白线,为什么能将声音传输到别人家呢?是空气在帮着传播吗?这端的一串数字嘟嘟嘟地按下后,是怎样让那端丁零零响起来的?
虽然没有专门打给我的电话,但有了电话机后,我也忙起来了。外婆拿起话筒,总是爽快地回道:“要得,要得,我现在就去你家喊人。”不然就是:“就按你说的这个时间吧。我让你娘夜里早点儿过来等电话。”想着人家打过来话费贵,外婆匆匆就挂掉了电话。这下我就得做飞毛腿了。有时一溜烟冲到人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闭,又急乎乎跑回来跟外婆汇报。外婆咕哝着:今天没有集要赶的呀,是不是在谁家打牌,难道去了田里干活?外婆就自己出门寻人去了。
记得有次半夜两三点,电话铃猛地响起,尖厉地划破了我的梦乡。只听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急促,外婆挂断后,叫上外公,两人拿着手电筒就跑出去叫人了。一段时日过后,有个伯伯特地拎了一只鸡过来答谢,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伯伯的姐姐突发疾病在县人民医院抢救,幸好通知及时,伯伯得以赶去见到姐姐的最后一面,没有留遗憾。这个伯伯住在茶山脚下,是村边缘的位置,外婆和外公走了许久的夜路才到。
五
窗外,地上铺着厚厚的雪,覆盖了白天打过雪仗后脏乱的黑脚印,白茫茫地显得那么清洁。白雪映照下的院子,像是沐浴在纯净的月光里。
屋内,灶膛里的柴火眼看要灭了,外婆用长铁钳向里掏了掏,往外挪出一堆柴灰,火苗又小精灵一般蹿了出来。摇曳的火苗,照见了外婆皱纹密布的额头,也照亮了小姨桃花般的面容。
“一辈子很长很久的哪,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要聪明懂理的。”外婆的话悠悠地传来。
“身高外貌就不管了?这也是要看一辈子的。家境不能太差吧,不然跟着一辈子受苦受累。”小姨的声音由高而低,像是在反驳。说完,小姨的上身趴了下去,支在膝盖上的双手揉搓着,看着火苗若有所思。
“外表嘛,过得去就行,不用太讲究。这日子过的是知冷知热,是有商有量。”外婆转头朝向小姨,“只要待你好,勤劳肯干,苦也是甜。再苦还能比我们那会儿的日子苦吗?”外婆的语调缓慢悠长,像是要把人拉去更久远的岁月。
两人一来一去在柴火边说了很多话。寒冷的冬夜里,那些围着灶火说出的一字一句,仿佛也被烤热,温温乎乎地在空气里飘散开来,让屋内更暖了。我知道,她们在谈一件对每个女孩子而言都很重大的事情,也就是外婆说的“终身大事”。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没有调皮捣蛋,也没有百无聊赖。好像只要回到外婆烧的柴火旁,我都变得乖顺。这柴火暖着人的身心,有一种令人放松和安定的力量。外婆在柴火旁说的一席话,也模模糊糊地留在了我心里。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后来我唤作“姨父”的人就开始常常来家中做客。人不高,但温和亲切,每次都会领我玩一会儿,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就是房前屋后地帮忙,做煤球、挑井水、搬重物,不怎么落座。外婆又坚持不肯让他做,每次两人都推来抢去弄半天,跟打架似的,我在旁边看着总觉得好笑。有次,他拿了一个茂密的、长长的竹扫把过来,说是留意到外婆家的竹扫把有点儿光秃、有点儿短,他自己劈了些竹枝动手做了个新的,用来给外婆扫院子用,这样不累腰。那一段日子,外婆逢人便讲这事。后来外婆一开头,我就模仿她的语气把一来二去讲完,把大家都给逗笑了。
待到院门口的那棵大桂花树都开满细细碎碎的花朵,隔很远都能闻到香味的时候,外婆开始给小姨张罗嫁妆了。外婆请来了两个木匠,堂屋的地上铺满从木头上推出来的长长的刨花;又来了两个棉花匠,雪白的棉絮伴随着有节奏的弹棉声在空中飞舞;还请来两个有儿有女有福分的婶娘缝了一天的喜被,上上下下飞舞的一针一线里,都是祝福。
出嫁那天的小姨,一身红衣,唇是红的,高高盘起的发髻上插着的花也是红的,是那么的明艳动人。大门和窗格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堂屋的八仙桌上,摆满供品,红烛高照;院门口,鞭炮声声,人声鼎沸。外婆却一个人躲在里屋的床头直抹眼泪。
我跑过去,蹲下身,将头歪放在外婆的膝盖:“外婆,还有我呢。我以后不嫁人,一直一直陪着你,哪儿也不去。”
外婆破涕为笑,狠狠地揪了下我的冲天辫:“那可不行!外婆是太高兴才这样的……小姨今天美不美?”我点点头:“小姨本来就长得美,今天更美!”
“我家玲子以后也要找个顶好的人家,像小姨这样漂漂亮亮地出嫁。玲子只要常回来看看就行的啊。”外婆的眼圈又红了。
言犹在耳,我却已身在一个离外婆很远的城市,定居在了异乡,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偶尔回家看望她。曾经陪我来回走二十里地去看电影的外婆,如今两脚蹒跚,拐杖离不了身。外婆家的老宅子早已拆除,大舅新建了一个洋气的三层楼房。那台黑白电视机被高清超薄大彩电取代,固定电话机没了,那个承载着无数欢声笑语的院子没了,那间可以烧柴火煨鸡蛋的柴房也没了。放电影的、卖绿豆冰棍和做爆米花的师傅也都不知去了哪儿。
虽如此,每当我累了、倦了、哭了,只要浮想起灶膛里刺啦燃烧的柴火,还有火光中外婆和煦的脸庞,我便觉有无限温热从心底生出,自信和勇气又重新回来了。我是曾被一个亲近的人那样结结实实地爱护过、那样彻彻底底地被接纳过的人啊。无论走在哪片天空下,我都应该信心满怀、蓬蓬勃勃地生长。
多少次,我在梦里,如一架飞机,飞呀飞呀,越过重重光阴,停落于在外婆身边度过的童年时光里,在那儿慢慢加满油,再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