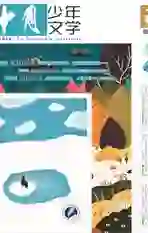阳台上的池塘
2023-04-12吴越
初衷
大概是去年开春的时候,家里刚冬眠醒来的龟崽生了场眼病,整个眼球都蒙上了一层白膜,得了白内障一般,几经求医问药,折腾了大半个月,才终于好了起来,指点的高人说,问题出在自来水里的添加剂,对眼睛有刺激,今后不能直接换自来水了。
不得已,我找来了个塑料箱,放在阳台上照得到大半天阳光的地方,替龟崽们“晒”水。起初我就这点儿愿望,但没想到这却是一场喜出望外的开始。
箱子不大,大概半米见方,也就是从衣橱里临时征用的,胜在有一定的透明度,虽不能说比得上专门养鱼的玻璃缸,但晒水肯定绰绰有余了。阳光打在里面仿佛凝固着的果冻一样,就像看小池塘的感觉。
像小池塘?我为自己的这个念想感到好笑,我知道那些附着在箱壁上的气泡,其实是析出的氯气,那原本是给自来水消毒用的,和池塘里的气泡完全不同,这可是让最皮实的龟崽都能生病的自来水,哪还能和生机勃勃的池塘相提并论呢?我便没接着往下想,把箱子丢在阳台上就不管了。
几天之后,当我准备取水给龟崽换水,走到阳台上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那个阳光通透的角落,小小的塑料箱早已大变样,水碧得如一汪深潭,阳光下,像一块澄澈分明的翡翠,越看越叫人欢喜,几乎要漫溢出来。我赶忙走上前去,蹲下来想看个究竟,水绿得很均匀,且没有杂质,却又不像染料那样,呈现的感觉完全不同,这绿水自然而轻盈,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会泛起波光;而在箱壁上,则长出了细密的、毛茸茸的水藻来,它们如今还很细小,就像初生在婴儿头顶的胎毛,随着窗外的和风微微颤动。
一瞬间,我仿佛真的闻到了池塘的味道,索性决定:如果它真能“长”成一方小池塘,那就顺其自然吧!
看不见的客人
我小的时候,家附近有一处烂尾楼,刚把地基挖好开发商就跑路了,留下很深的一个土坑,黄梅天里,洼地很快集满了雨水,土坑变成水坑。
工地外的栅栏很高,决计无人能进,所以谁也没想到,那个水坑里居然长出了生灵来,半夜里面传出蛤蟆叫,还时不时有鱼儿跃出水,水草和芦苇就更是不知道何时就占领了那里,沿着水坑蔓延一周长得茂盛无比。
我曾有过很多猜想,或许是路过的水鸟蹼间粘着鱼卵,或许是风吹来的落叶里夹杂着种子,或许还有更神奇的方式,生命总是令人意想不到,处处充满了惊喜。
我的水箱如今也开始了这种过程,特别是在我放进去一段“沉木”之后。所谓“沉木”,就是一些年久的枯木,通过经年累月微生物的改造,质地发生了变化,泡在水里会沉底,能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是我从养鱼的高人那里取来的“真经”,其实无非就是取得了适合生化作用的益生菌。
但我没想到的是,那段小小的沉木上除了那些细菌,还“偷渡”了不少客人。
第一个被我发现的是水蚤。某日我照例蹲在水箱前观察—几天下来,守着这一泓意外的水景已成了我最大的乐趣所在,彼时水藻已初具规模,那些附在箱壁上的愈加欣欣向荣,变得更粗也更密集,将向阳的两面箱壁铺满,另外两面上虽不及这般热闹,但也呈现出蔓延的态势,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把箱子的内表面占满,它们已经不像婴儿的头发了,更像一种绿色的绒毯,附着在潮湿的石缝里的那种青苔。
另外一些则向沉木上延伸,顺着褐色的纹理冒出好几朵鲜艳的绿色来,好似返青的老树。沉木上的水藻和箱壁上的似乎还不大一样,它们更集中,仿佛拧开的礼花筒般一簇一簇地往外冒,丝带要更长也更细,就像少女的发丝那般——因为查不到名字,我便擅自替它们做了主,箱壁上的起名叫绒藻,沉木上的则叫丝藻。
就着和煦的阳光,我发现绒藻上散布着一些黑色的小颗粒,虽然只有针尖大小,但就像地毯上起了毛球,直叫人犯强迫症。我找来滴管,准备给清理干净,不想管尖刚一到绒藻附近,那些小黑点却一扭一扭地动起来了!
我找来放大镜仔细瞧,发现它们有鼻子有腿——正是生物书上的剑水蚤,因为体形小得不易察觉,极可能是我从河里捞沉木时,藏在缝隙里便带了进来,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然而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几天之后,我在水箱的另一处又发现了一窝“黑点”,它们比前面发现的个体更大,身体也没那么黑,像小颗的沙砾,起初我以为也是一种水蚤,没有在意,不想它们的个头越来越大,背上还隆起一个尖尖的小角,我这才发现,它们竟是螺蛳!原来不只水蚤这种小生物,连螺蛳这样的“大物”也会趁着自己幼小的时候搞“偷渡”。
后来螺蛳越来越多,大有泛滥之势,我不得不清除它们中的大部分,拿去喂龟崽们。一开始我还有些心疼,毕竟这也算是我“一手带大”的,好在,螺蛳的繁殖能力超强,要不了多久就又能长出密密麻麻一大片来,让我的“负罪感”减轻了不少。往后的日子里,时不时就能看见箱壁、沉木上挂着一种透明的、像鼻涕一样的黏液,其中有一些比针尖都小的密密麻麻的小黑点,那就是螺蛳的卵袋,不出几日,小螺蛳就会从里面爬出来,背着自己尖尖的壳,开始满箱子闯荡。
往后的日子,箱子里时不时就会蹿出一点儿惊喜,比如来路不明长得像蚬子的迷你河蚌;喜欢一边划水一边捉水蚤吃的水螅,样子袖珍的水母(据说水母原本也有水螅的形态);几朵忽然出现的浮萍以及慢慢舒展开的水芙蓉……一个下雨天,沉木冒出水面的部分冒出两朵小蘑菇来,撑开灰白灰白的伞盖,像童话里顶着硕大钢盔的呆头哨兵,真是可爱极了。
当然也有惊吓,有一次我看见水底有一种红色的肉虫在探着脑袋摆动,一打听,才知道那是摇蚊的幼虫。摇蚊虽不叮人,但我可不想往后的日子耳边天天是嗡嗡声,何况摇蚊比普通蚊子体形要大上数倍,单是晃在眼前也瘆得慌,赶紧从河里请来几只黑壳小虾,不一会儿就把那些虫子啃干净了。
还不到两个月,这还没正式进入夏天,我那一方小小的水箱已经向着池塘的模样快步奔去了。恍然间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是那个让我儿时困扰又着迷的水坑正在我眼前重现,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时分,那些个作业怎么都写不完,却总能抓住空隙跑出去疯玩的夏天。
夏日的烦恼
日子一晃进入了夏天,因为北半球的夏天太阳角度比冬天要来得高,所以能够伸入阳台里的太阳“尾巴”便短了些,水箱所在的位置也从能晒大半天变成了只能晒小半天,不过虽然到日照的时间变短了,但照度肯定更充足,这一点很直观地就在水藻上体现出来。
绒藻还好,毕竟只能贴着箱壁生长,把四面占满也便无处可去,最多不过更厚实一点儿,变成一块针脚更密的挂毯罢了,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丝藻就不一样了,它似乎并不拘泥于一处,也不限于在初生地沉木周围,它变得越发繁盛修长,招摇的丝带就像无数触手,伸向水箱里并不广阔的天地里,一发不可收拾。立夏没几日,翠绿的“少女发丝”彻底爆发成“三千烦恼丝”,把整个水箱都挤得满满当当,可怜的黑壳小虾在里面吃力地进进出出,像极了挤早高峰的上班族。
没办法,我只得人工清除那些恼人的丝藻。与我想的不同,丝藻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柔柔弱弱,这些丝的韧性极好,只需汇成面条那般粗细的一束,我便没办法徒手将它们扯断,这又增加了不小工作量,逼得我最后竟然用上了剪子。挥汗如雨了大半个下午,才把它们清理得七七八八,事到如今,一开始想的顺其自然,实则已经言不由衷。
然而如此辛苦换来的劳动成果保持不了多久,不出一周,水箱里便再次盘虬卧龙、“藻满为患”。无奈的我只能再次出手拯救我襁褓中的池塘,其间还失手掐死了一只黑壳虾,误伤的大小螺蛳不计其数,我望着清理出来成绞的细丝,挽上两个毛线团子尚且绰绰有余,当初“少女的发丝”那种浪漫的想法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无尽的苦恼,这是一场惨烈的硬仗,我与丝藻两败俱伤。
那天以后我痛定思痛,决定像治摇蚊幼虫那样请来帮手,可按丝藻那样的韧性,连嗜藻的黑壳虾都啃咬不动,上哪儿去找更厉害的家伙呢?
家门前的小河里全是宝,我带着网兜逐个瞧:青鳉只在水面附近活动,同水藻没有来往;虾虎是吃肉的,丝藻治不治得住说不好,虾和螺铁定保不住;草鱼是素食主义者,体形却不合适,我这小庙里难请大神……思来想去,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一想到今后还得继续同丝藻战斗,心里就一阵懊丧。我泄气地把手里的丝藻扔进河里,没想到马上聚过来几条小鱼,不由分说就对着那团丝藻撕扯起来,仿佛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面条。我仔细一看乐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它呢?
鳑鲏,在家乡,俗名叫菜板鱼,是一种又宽又扁的小鱼,长相酷似鲷鱼烧,体形却像铜锣烧。虽然体色鲜艳,身上的鳞片泛着彩光,但却极难伺候,传说菜板鱼离不得水,只要从水里捞上来,眼睛立马一红,就活不长了。鳑鲏我本是不愿养的,从前也没打过它的主意,可事到如今,也只能试试看了。
我小心翼翼地抄起网,飞快地捞起两条来,又装上大半桶河水把它们放进去。其实鳑鲏并非离不得水,只是对水质的变化极为敏感,如果那条小河被污染了,那么率先遭殃的肯定是鳑鲏,堪称小河里的金丝雀。
我把它们带回了水箱,连带换上了半桶河水,又紧张地观察了几个小时,确定它们没有不适,这才蹑手蹑脚地悄悄地离去。我的心里仍然忐忑,两条鳑鲏虽然活着,但也没有去啃水箱里剩下的水藻,不知道是不是当着我的面很腼腆,还是搬运的过程中造成了不易察觉的“内伤”?那一夜我就在这样的不安中度过了,第二天一睁眼,我便迫不及待地跳下床,跑到水箱跟前。当我看到水箱的那一刻,不觉眼前一亮:两条鳑鲏生龙活虎地翩翩摆动,而水箱里剩下的丝藻全都不见了踪迹。
往后的日子,我慢慢发现,鳑鲏实乃不挑食的“大胃王”,不管多少水藻,无论什么种类,交给它们保管错不了,鉴于它们的食量,我怕饿着了这两位“功臣”,还从河里捞过不少不知名的水藻喂给它们,它们也不叫我失望,全都满口吞下,不问出处。
菜板鱼,果然心大体宽。
这一份经验物尽其用,后来我龟缸里的水藻爆发的时候,也是请来的鳑鲏帮忙,无论多么棘手的水藻,只要它们出马,不出几天保管还一片清爽,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自从鳑鲏来了以后,丝藻就像“隋炀帝遇上李世民”,被杀得丢盔卸甲,曾经统御水箱的“暴政”一去不复返,再也猖狂不起来了。而我发现,最大的赢家竟然是绒藻,它们同箱壁贴合得很紧,拼尽全力在那光滑的塑料上扎下根来。鳑鲏虽然也啃绒藻,但却啃不到根,所以四面箱壁上的绒藻虽然薄了些,但势力范围却一点儿没有缩水,并大有朝着沉木和箱底蔓延的趋势。
丝藻张扬,绒藻坚韧,本是同族,仅是这点脾性不同,面对“顺境”与“逆境”的结局便截然不同。
小小一方天地,竟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虾兵蟹将
时间一晃就快入秋了,其间水箱的演义继续上演着, 经历了一个夏天的相处,里面的各种生灵也找到了各自的生存之道:水蚤吃浮游,水螅吃水蚤,黑壳虾吃它们仨;鳑鲏继续追击着生生不息的丝藻,顺便把螺壳上附着的水藻也啃个精光,还螺蛳们一个帅气的光头。
平心而论除了与丝藻斗争的那一次,水箱的一切都算顺利,也算是无心插柳了,箱底已经沉淀了一层薄薄的尘埃,就好像真正的池塘水底那般。旗开得胜,令我备受鼓舞。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河边走走,一来给鳑鲏捞点水藻,二来秋天晚饭后的河风真是顶顶惬意。不止我一人觉得如此,小河边钓鱼的人们也变得络绎起来。沿着堤岸走去,常是十步站一人,好不热闹。跟他们熟络以后,我便时常能讨着一些“宝贝”—溪蟹。
溪蟹不像它的亲戚大闸蟹,它个头又小又瘦,吃起来索然无味,所以除了给小孩子养着玩,这些家伙在大人眼里并没有什么价值。钓鱼的人尤其不待见溪蟹,说蟹钳会剪断鱼线,所以抓到以后经常都会就地正法,直接摔死。我便向他们讨过来,明面上说带回家养着,实际上我带着它们在河堤上遛一圈,便找个旁人看不见的地方暗戳戳地放回河里去。
这招屡试不爽,只有一次,我照例要把讨来的螃蟹放生,正拿起最后一只,忽然注意到它圆润的肚皮上正往外“掉渣”,我定睛一看,可不得了,这哪是“渣”啊,是从腹腔里爬出来一只一只的小螃蟹!我一激灵,赶紧用桶在下面接住,不知是不是受了惊吓,母蟹挣扎起来,那些小螃蟹便从它的腹腔里像挤豆子一样往外冒,冒了得有两分钟还停不下来,我眼见不是办法,赶紧把母蟹放走了,任由它带着剩下的子嗣回归自然,在来年继续祸害钓鱼人的鱼线。
低头一看,那些前面落下的豆丁小蟹已经密密麻麻地占满了桶底,正横七竖八地胡乱爬来爬去,我心里一热,赶紧拎着桶子快步朝家里走去。
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见溪蟹生产。第一次时我还在上小学,是小伙伴抓到送给我的,因为是在家里,所以看得很真切,我还记得母蟹张开它圆圆的腹腔,就像电影里面的飞碟打开舱门,只有黄豆大小的小蟹们彼此挤在一起,像一簇一簇的向日葵花蕾,我取出一只放在指尖,细胳膊细腿,眼睛也不突出,只有两个浅浅的黑点,与其说像螃蟹,倒不如说像小蜘蛛。那时年幼的我雄心勃勃要把它们养大,结果不得要领很快就全军覆没了,这个遗憾便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这次我一定要把它们养大,我对自己说。虽然仍有一点儿慌张,但如今我可是有法宝——一方原汁原味的“小池塘”。回到家里,我大致数了数,一共有二十多只豆丁蟹,我用小棍半推半赶将它们悉数引导进箱子里,刚一入水,它们便像许愿的硬币一般飘飘摇摇地沉入水底,随即立马跑到沉木下面躲了起来,我怕躲避的空间不够,它们会因为太过拥挤干架,还特意找了几块多孔的石头放了进去。
小螃蟹入水箱的前几天,相安无事。螃蟹是夜行生物,白天大多躲在石缝里面不见踪迹,连着好几天都没有见着它们,我心里有些不安,难道历史又一次重演了?忐忑的我用小捞网在箱底的泥沙里翻找,终于在沉木后面背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它”浑身煞白,果然不动了。我难过地把它捞起来,准备移到花盆里安葬,不想当我凑近一看,不禁笑出声来。
那不是小螃蟹,而是小螃蟹蜕下的壳。这证明它们不但活下来了,并且活得很滋润,开始慢慢长大了。
那天夜里,我定好闹钟,半夜两点起来打着手电往箱子里张望,果然发现了小螃蟹的踪迹——它们纷纷从石头、沉木底下探出来,一个个挺直了身体,哨兵一般神气活现地站在水底,二十多只,一点儿没少,我真是大喜过望,赶忙凑近来更仔细地瞧着。只见它们用身体最靠前的一对大钳不断夹着水底泥沙中的碎末塞进嘴里,虽然看不清食物具体是什么,但它们的两片口器不断地翕动着,应该吃得很香。螃蟹是杂食动物,荤素都吃,箱底那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水藻残枝、虾螺尸体等有机碎屑正好派上了用场,也进一步净化了水质,我的小池塘又向着真正的池塘更近了一步。
一个月后,小螃蟹又经历了两三次蜕壳,个头长了不少,差不多有小指头大小了,胆子更大了,阳光好的时候,我能看见它们探出水面晒太阳。这里绒藻又立了一功,经过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发展,前赴后继的绒藻们彻底改造了箱壁,牢牢地附着在上面,把箱壁变得凹凸不平,这恰好方便了小螃蟹,它们日渐修长的八条长腿顺着绒藻爬行的时候如履平地,有些一边爬一边还用钳子扯下一片绒藻往嘴里塞,又贪玩又贪吃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随着小螃蟹的长大,我开始担心水底的食物是否够吃,于是弄来风干的鸡胸脯肉撕碎了喂给它们。一开始小螃蟹们显然没接受还能“天降美食”的设定,眼见投下来的碎鸡肉还以为是“深水炸弹”,每次都慌里慌张地躲进石缝,倒是黑壳虾比较神经大条,不一会儿就寻香而来,三五成群趴在肉末上大快朵颐,不过等到几天之后螃蟹们反应过来,黑壳虾们便吃不上这些美食了,螃蟹总会第一时间冲出来,挥舞着大钳将虾全部赶走。
只有鳑鲏自始至终没有动心,每天仍然专注地嗦藻,一副佛系的样子。
国庆之后,秋意渐渐浓了,经历几场巴山夜雨,气温便降了下来。我知道动物们一般都会囤积秋脂,好对抗寒冷和匮乏的严冬,我生怕小螃蟹们还不够肥壮,于是自作聪明,从熬冬瓜文蛤汤的材料里抽出几只蛤肉,给投进了水箱里。当时我便隐约有点儿感觉,这次投喂的量比从前任何一次都多得多,但之前成功的经验让我自信起来,并且想着相比鸡肉,蛤肉似乎也更适合水生环境,肯定没问题,于是便心安理得地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隐隐闻到一股腥臭,还以为是地漏出了问题,可等我洗漱完毕如往常走上阳台之时,这股味道却愈演愈烈,我望了一眼水箱,这才发觉大事不好,只一个晚上的工夫,原本翠绿了一整个夏天的水箱,如今已经变得浑浊不堪,水体灰白,水面上浮着细密的白色泡沫。可怜的螃蟹纷纷爬上箱壁避难,就连从不出水的黑壳虾们也爬上水芙蓉,身体微微颤抖,好像呼吸困难一般,最惨的是没办法离开水的鳑鲏,一条侧翻在水面上,眼睛蒙着一层白灰,已经死去了,另外一条也岌岌可危。
我头皮一阵发麻,赶忙捞出了开始腐败的蛤肉,徒手舀出了整整大半箱泛着腥臭的脏水,换上新鲜的干净水。因为我的错误,水箱失去了一条鳑鲏、五只螃蟹、八只黑壳虾,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包好,埋进了花坛里面。无限的懊悔涌上心头,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着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半米见方的小水箱在我的心目中有了重要位置,一鱼一虾一蟹、一朵浮萍甚至水藻都成了我不可代替的朋友,同它们在一起的这一年,我看见了生命从无到有的奇景,看见了不同物种的竞争、制衡与兴衰,也见证了新生命诞生的生生不息,这是生命的法则,值得我学习、尊重和敬畏。
一时间,我也说不上,成长着的是它们,还是我自己。
由于补救及时,水箱虽然伤了元气,但好歹还是挺了过来,赶在冬天来临之前,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气温越来越低,虾与蟹早已将自己深埋在石缝当中,白天黑夜都不再露头。看着剩下的那条鳑鲏在水箱里孤零零地游动,我打定主意,开春要给它再找一个伴儿,最好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希望它们也能像螃蟹、螺蛳和黑壳虾一样,在阳台上这方小小的池塘里演绎生生不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