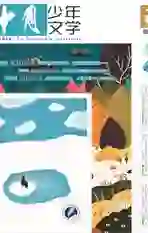当然是夏天到了
2023-04-12费晓莉
一
忽然一天,我家对面山坡上那两片云回到天上去了。
这是夏天到了吗?
当然是夏天到了。
那是两棵高大的茶果树,开花的时候,像两朵云走累了,从天上掉下来,正趴在半坡里歇脚。那两朵云迟迟回不到天上去,当它俩突然不见的时候,夏天就到了。
花木开始扶疏,风月开始琳琅。
南墙拐角处出现了一张大大的银色补丁。那两面墙之间有一条缝隙,那里住着一只穿着土褐色衣裳的蜘蛛,一到夏天,它就迈着毛茸茸的大腿从墙缝里爬出来,日复一日地帮助我家修补墙缝,只是它的针线活不够精准,打的补丁虽然又圆又大,但不够长,始终没有把墙缝补好。
“长高”来了。多亏了树,好多树,没有这些树,这鸟是一趟都不肯来的。
我妈说,“长高”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圆脸大姑娘。它叫一声,夏天就不得不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我们叫它“长高”是因为它一来,就拣一棵庄稼地边缘林子里的大树,站在最高处,不停地喊 “长—高— ”,“长—高—” ,耐心地劝说庄稼长大。长用二声,高用一声。
它一叫,人们的力气一下子变大,口气也一下子变大,牵着牛,背上背篼,天天往田地里走。
放羊的吴爸爸喜欢唱歌。
他早上这样唱:“长高虫儿上来了,白杨的树梢上喊了。”
下午这样唱:“日头儿跌了者实跌了,长高虫石崖上过了。”
他总是提到的“长高虫”,就是“长高”。明明是鸟,人们一定要叫它虫,不知道“长高”心里有多生气。还好,我们一直叫它“长高”。
“长高”叫一声“长—高——”,山谷原样学一遍。“长高”生气地重新找棵树喊,但四周的山谷还是会学一遍,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学。“长高”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生气。
“长高”不喜欢扎堆,不像麻雀。它清高,孤傲,独来独往,像个孤僻的少年,完成任务就走。
庄稼在“长高”的劝说下长高后,换另一种鸟来催庄稼长熟。换来的鸟是个快嘴巴,不停地喊,“快熟快黄”“快熟快黄”,很不耐烦的样子,好像庄稼要是不快些变黄变熟它就要生气了一样。一定是青稞和大麦成熟太迟,它很不高兴。
一到深秋,“快熟快黄”也不见了。很快,“宝宝吃”就来了。
“宝宝吃”穿着灰色的外衣,个头有麻雀的两个大。
“宝宝吃”一来,先站在坡上喊一阵“宝宝吃,宝宝吃,青稞大麦我不吃”,之后,便一头扎进青稞地和大麦地里,吃饱后,又喊着“青稞大麦我不吃”飞走了。
它们一来一伙,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像快速飘过了一大片有声音有力气的云。
“长高”和“快熟快黄”喊大催熟的庄稼,就这样让“宝宝吃”成群地偷吃。宋奶奶经常指着它们的脊背骂几句,但它们假装没听见。
二
厨房灶台上的那一窝蚂蚁也现身了,缓慢行走在靠墙的一端。它们总是排着队走路,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像从墙缝里抽出了一根毛茸茸的细线。
我没有仔细地调查和深入地研究过,要是做一个稍微深入一点儿的研究的话,就能发现它们的秘密:要么立春,要么惊蛰,最迟就在春分那天,它们就悄悄爬了出来,而不是等到夏天才出来。
它们又细又小,只有一颗黄米粒那么大,大概是世上最小的蚂蚁,我看不出究竟谁是大蚂蚁,谁是小蚂蚁。
它们也是走得最慢的蚂蚁,好像在这个世上,它们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办妥,再没有什么要紧事值得它们走快一些。
它们和我一样深爱着我家的厨房。
它们一定也像我一样深爱着我妈做的饭,每年都准时出现在我家,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
多少年了,我没有给它们端过一次我妈做的饭,它们光是年复一年地闻着我家饭的味道,竟然也一年年地活着,并且活得安安稳稳。
山野里的居民也开始频频光顾我家。
括括(就是蝈蝈)有时到我家光秃秃的屋顶上高歌一曲,更多的时候趴在菜园子里某个菜棵的头顶上放声歌唱。它们有的红肚皮,有的绿肚皮,都是很胖的大括括。
括括在准备唱歌前,先“啧”一声,过一小会儿,再“啧”一声,好像是先试一试声嗓,看能不能唱起来,然后才是一首长长的曲子。没有唱词,不知道它在夸赞什么,但可以肯定,它在夸一个不错的物件。我听到第一声“啧”就开始悄悄找寻它的位置,但它经常再无下文,让我空等一场。
为了捉一只括括,我在菜园子边的猪圈墙边蹲半天,等它唱在兴头上时悄悄站起来,但它每次都能准确地感知到我的存在,总是在我起身的刹那赶紧把嘴巴紧紧闭上,让我不能确定它的确切位置。这让我十分生气,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括括除了蹦子跳得高些,歌唱得好听些,耳朵灵些外,再没有其他本事。把它捉住,它只会边搓手边在我的手心吐褐色的口水。
括括大概认为自己的口水有毒,吐一口就能让我乖乖地把它放掉。事实上,它的口水只是又黏又稠,不好洗,并没有一点儿毒。
蚂蚱除了不会唱那么好听的歌,括括的本事它都会。
我有一次跟我妈说,由于我追得紧,一只蚂蚱从我家的屋顶上一个蹦子直接跳到屋后山坡一棵正在开花的山丹花边,但我妈不信。
一只蚂蚱,有多能,还跳那么远?
我妈不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我家屋顶到山坡,还隔着一个鸡圈,一大墩刺梅花,一条土路。
那么远的路,蚂蚱一个蹦子就跳上去了?
我非常无奈,但这是真的。幸亏父亲见得多,知道得也多。
那怎么不能?夏天晌午的蚂蚱,能跳十几米远,要是从山坡上往下跳,一个蹦子就跳到半坡里了。他说。
虽然我不知道十几米具体是多远,但可以肯定,很远。照这样的跳法,蚂蚱从我家屋顶跳到山坡上,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父亲说捉蚂蚱要早上捉。早上,露水把蚂蚱的身体打湿了,蚂蚱跳不远,好捉。一到中午,太阳一晒,蚂蚱晒干手脚,身体变轻巧,一个蹦子就把人撂远了,不好捉。
表姐在山上唱歌:“毛毛的个雨儿里抓蚂蚱,我看你飞哩嘛跳哩?抓住你的尕手手问实话,我看你哭哩嘛笑哩?”
我在吃饭的时候把这首歌学出来,全家人惊呆了,都停下嘴巴和筷子看我。父亲立刻瞪我一眼,说,好的不学,一天净学这些个五五六六的东西。然后,又瞪一眼我妈。
我知道,他后面和饭一块儿咽到肚子里的话是说给我妈的:当妈妈的不管教丫头,还要等着我这个当大大的管教吗?也可能是一句老话:儿子不教父之过,丫头不教母之过。
父亲就会这一句古话,不知道是谁教的,每到我犯一些“五五六六”的错误时,父亲就会把这句话拿出来交给我妈。
父亲说的“五五六六的东西”具体是啥不清楚,反正都不是啥好的。用烧烫的筷子把刘海烫卷“像个麻柳精一样”;在脸上抹一层厚厚的粉“像驴粪蛋子上下了霜一样”;给嘴唇涂抹厚厚一层五毛钱一管的口红“像吃了生肉一样”等等,都是“五五六六的东西”。
我再没敢唱过。
我妈说听都不要听那些需要在山里唱的歌。但不听可不行,因为整个夏天,山里随时会钻出这样的歌,更不要说我几乎天天在山上。因为一到夏天,吃的,看的,玩的,都在山上。
不管在哪座山上,我只害怕两种虫子,一种是没有脚的,比如蛇和长得像蛇的软虫。第二种是脚太多的,比如“蛇阿舅”,蚰蜒,还有蝎子等。
软虫种类多,红的绿的花的都有,都很胖。
变成蝴蝶前的虫子都是软虫。
这种长不过一寸的胖虫子会以它的形状在一瞬间把我吓住,我的心和舌头会在一瞬间打结,一股麻愣愣的感觉一瞬间就会从我的脚后跟跑到头顶。
我比它们大出了不知道多少倍,应该一千倍都不止。按理说,我应该把它们吓坏甚至吓死才对,但事实是,它们只是趴着不动,不用一招一式就能把我吓坏,让我落荒而逃。
我觉得这些身材细长的家伙肯定和蛇有着某种关系,它们再长几天就都会变成蛇。
三
你一条蛇,跑到我家干啥?你快些到坡上去。
是隔壁宋奶奶的声音。
原来有一条蛇跑到宋奶奶家了,宋奶奶用一根长木棍把蛇挑出来,扔到屋后的坡上,然后她站在坡跟前给蛇讲应该怎样做一条蛇。
我闻声跑过去的时候,蛇已经不见了。
一个麻蛇,不大,这么粗。宋奶奶说着伸了一下自己的大拇指。
咦,宋奶奶,你不是说家里来蛇是好事吗?
但宋奶奶没听见,只把脊背送给我。
宋奶奶吃斋念佛,她说蛇是灵物,不能打,更不能往死里打。她还说蛇来家里就有好事,蛇还会找好人家做邻居。但看起来,宋奶奶也不想和蛇做邻居。
三婶说,蛇看见洞就钻。你们拿个瓶子,把瓶口对着蛇头,蛇就会乖乖进瓶子。
于是,我们握着一个长脖子的空酒瓶子和木棍朝着蛇住的坡上走,去抓蛇。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是蛇不愿意自己进到瓶子里,我们就用木棍把它赶进去。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六个人,加起来难道还没有一条蛇厉害?
走到半坡的时候,从一墩矮狼麻后猛乍乍飞出一只浅棕色的大鸟,怪叫着,飞过我们的头顶。
是不是有蛇?走在最前面的六六停下来,扭过头问我们。
是蛇把那只大鸟吓走的吧?我们相互看着,都噎在了半坡。就在这时,拉花说她饿了,六六说他渴了。我们只好快速原路返回。
虽然没见着什么像样的蛇,但这一趟也不是一点儿收获都没有。我们用木棍挑着几张蛇皮下了山。
蛇把穿旧的衣裳扔在矮矮的刺墩上,透明,修长,还保留着一条蛇的样子,像是刚刚脱下来放在那儿的。
我走几步,朝后看一眼,老觉得蛇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还好,没有蛇撵下来。
我们把蛇皮拿到村医的药铺里,换了一些薄荷片和一沓夸赞。
薄荷片和去痛片一样大,一样白,装在一样深棕色的大玻璃瓶子里,但味道简直天上地下。薄荷片是我们的糖,不,那种麻酥酥的味道,糖都比不上。汪奶奶用鸡蛋换去痛片,我们用蛇皮换薄荷片。
不久以后,听说河滩里养蜂的那两个外地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竟然捉蛇吃,这让我们吃了很大的一惊。
最初发现这个事情的是挑水的赵婶婶。
她说她看见那个瘦男人蹲在河边拾掇一条蛇,差不多有这么粗的一条麻蛇。说着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个大圈给我们看。
虽然她没有看见那两个人具体是怎么吃的,但她肯定他们就是准备要吃了。
不吃,剖开蛇的肚子干啥?蛇肚子里又没有金元宝。
这样的事情,宋奶奶一般都是要管一管的。
宋奶奶经常说,牛羊是自己养大的,想吃就宰了吃,但山野里的物件不能动,那是老天爷养大的。
果然,听完我们的述说,她非常生气。
这些“拉猴儿”!她说。
当然,“拉猴儿”也不是骂人的话。
凡是打南边来,说着一嘴我们听不懂的话的人,我们一律叫他们“拉猴儿”。
据说以前经常有一些从南边来的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拉着几只猴子,在场院里敲起锣打起鼓,让猴子表演爬竿、钻火圈、骑车等给我们看。从此,“拉猴儿”这个叫法就产生了。
那时候,会做新式家具的木匠,会画棺材的画匠,会做马甲的裁缝,都是打南边来的走家串户的匠人,我们统统叫他们“拉猴儿”。
我妈说“拉猴儿”就是能些,画在棺材上的龙和凤凰简直要飞出来。我们村里可没有那么能的人。
宋奶奶把穿着黑色条绒鞋的小脚在河边安顿稳当,然后背起手站下来,像个大人物。我们一伙“碎籽籽”也严肃地站在宋奶奶的身边,像一伙跟班。
咳——咳—— 宋奶奶照例咳嗽了两声。
河对面,男“拉猴儿”正蹲在一个蜂箱边,把不大的屁股对着宋奶奶和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快要下山的太阳在他灰色的套头衫上染了一层暖暖的黄。
蛇是你拉大的吗?宋奶奶大声问。
男“拉猴儿”一惊,站了起来,他向周边看了一眼,确定再没有别人后,才确定宋奶奶问的就是他。
遇到这样的事,宋奶奶多半会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把好多人问住了。
镇上的几个干部来河里网鱼,她问,这河里的鱼是你们拉大的吗?干部们相互看半天,谁也给不上一个回答,站半天,只好把鱼全部还给河。
我们去山里捉来鸟,她碰见了就问我们,鸟儿是你们喂大的吗?当然不是,谁没事干会去喂鸟。我们只好假装没听见。这个问题谁也不想回答,除了假装没听见,再没有别的办法。
果然,男“拉猴儿”一言不发地进了帐篷。然后,女“拉猴儿”的脸从帐篷里面朝外伸了一下,又赶紧收进去,再无动静,只有一股蓝色的烟在帐篷的头顶慢悠悠飘着。
宋奶奶只好对着一顶不敢还嘴的帐篷和一股绕着走的炊烟骂了半天。
有零星的蜜蜂飞过来,黄灿灿的,在我们的眼前跳一阵舞,又飞走。好像它们的主人惹祸了,它们专门来给我们跳舞,替主人给我们消气,求我们原谅的。
这山里跑的和水里游的都是老天爷养大的,你没有拉扯过一天,没有喂过一把青稞,凭啥吃?你问问老天爷,他答不答应?
最后的这个问题应该彻底把那两个“拉猴儿”问住了,因为老天爷从不露面,更不要说回答他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跟着宋奶奶气势汹汹地回了家。
哼,敢吃我们村里的蛇!我们不要说吃蛇,连蛇的坏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我们村的人谁都知道,碰见蛇要说好话,蛇到家里来更要说着好话送出去。
虽然我们碰见蛇,蛇就会用它修长的身材把我们全部吓住,我们只好扭头没命地跑开,把说好话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我没有跟蛇说过一句好话。
放羊的赵爷爷说,山里最大的蛇能把你们这些“碎籽籽”囫囵囵咽下去,你们只能在大蛇的肚子里一天天坐着等死。还好,那么大的蛇,我们村的人谁也没有见过,这让我稍微踏实了些。
四
大林子里传出好多忽高忽低、时远时近的笛声的时候,夏天全部都来了。
汪奶奶家最小的儿子总是在黄昏的时候,吹着笛子走在一对灰驴子的身后,沿着桦树湾那条斜路走出来。他的手指在那根简单多孔的棕红色竹笛上此起彼伏,左挪右移,制造出的那些声音,好听极了。
笛声是我能听到的唯一的丝竹声。
我在大路上走,路边的林子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以为吹笛子的人就要出现了,可看半天,从林子里悠然钻出一头大黑牛,喘着粗气,头大肩宽,毛发油亮。村里全是黑牛,毛发婆娑。南方那种屁股浑圆、脖子里总摞着几层肉、浑身毛发短密像套了紧身衣的黄牛,一头都没有。我在美术课本上看见那种粗脖子的短角牛,好奇极了,趴着看了半天。
袁枚说的那种骑着黄牛走在山路上,一路走一路高歌,看见蝉,突然闭口立的牧童,我也一次都没有见过。我见过的牧童都骑着黑牛唱着歌。
口哨声也密集起来。
最爱吹口哨,吹得最好的是多吉和才让两兄弟。
他们家在岭上。他俩总是吹着口哨行走在上山回家的路上。这让我觉得上山的时候只要吹口哨,就一点儿都不累。
我家在山脚下,我没有吹口哨的机会。一次我站在大门口试着吹了一下,还没有吹出一点儿像样的东西来,就让父亲骂了一顿。
“一个丫头家,还打哨子。”他这样骂我。
事实上,我三个哥哥也不能吹口哨。
没事多想想庄稼,吹来吹去,把一些福气都吹走了。他这样跟哥哥们说。
因此,我们兄妹几个谁都不会吹口哨,到山里只能巴巴地看别人鼓着双唇吹,吹得山高水长。
五
除了笛声,林子里也传出了更多的鸟叫声。
有几种鸟,每次只叫出一个字。
一种鸟叫声干脆,叫一声“嘚”,半天,再送出一声“嘚”,短促,干脆,像是再三地想了又想后,才答应了谁的一个请求。它躲在树叶深处,我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个灰黑色的背影。
有一种鸟,乏乏地叫出一声“丢”,过一阵,再吐一个“丢”出来。让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什么好东西丢了,才这样念念不忘地一直述说。
有一种鸟叫声又凶又狠,只有一个“咂”字。我在林子里走,它在树顶上“咂——”一声,吓我一大跳。这种鸟身子麻雀大,但尾巴长,喜欢不停地飞。它飞到这棵树上叫一声“咂——”,忽悠悠还没站稳,又换到另一棵树上,又叫一声“咂——”,又换。不知道这么凶地喊着要“砸”什么。
“呜啊”的叫声非常沙哑,像是刚刚哭了一场,把嗓子哭哑了还在呜啊呜啊地叫,听上去非常伤感,让我也心生难过。我以为头一年它的嗓子哑了,第二年会变好一些。但它年年那样。
有的鸟一声不吭,只闷腾腾地飞,像个哑巴。好像它的日子过得毫无头绪,没有一点儿说话的心情。
有一种鸟叫羊屎蛋。它当然比羊屎蛋大很多,有大拇指那么大。它衣裳很黑,个头很小,圆嘟嘟一个。实在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叫它羊屎蛋了。它个头小,但嗓门可不小,还叫得热火朝天,一直“唧——唧唧——唧”地叫个不停。好像它不用吃饭,这样不停地叫着日子就过了。
“青石头”住在大山的石头缝里,跟青石头颜色一样。站在青石头上,要是它不突然朝天翘一下它的长尾巴,谁也不会知道那里有一只青色的鸟。
“青石头”能在水面上钻一个窟窿飞进去,在水里飞半截,又钻一个窟窿飞出来,衣裳上还是干干的,一滴水都不淌。有时候,为了给我们展示轻功,它像个侠客一样踩着水面逆水跑一阵,再轻轻巧巧地落在河岸上。向我们炫耀一番姿势后,它“嘻——”一声,一头扎进远处的林子。
到林子看一看,我才知道,到村里去的鸟只是鸟中的一小撮,按照数学老师的说法,大概百分之一都没有。就是不知道它们全部的名字。
六
盛夏,山丹花开了。
山丹花只有红色,一朵要开很久才会谢掉。
兽医站的曹爷爷说山丹花要靠花朵的数量来表示自己的岁数。一岁开一朵,两岁开两朵……十岁开十朵。要是活上一百岁,它就得开出一百朵花。
那么大岁数的山丹花,我一次都没见过。我不知道它能吃。几大坡山丹花,都让我白白糟蹋了,除了揪下来染了个红脸蛋,再没有派上什么大用场。
山丹花鼓着肚子把花瓣翻卷着开出来,吐出几根长长的花蕊,上面的花粉足以把一只蜜蜂的腿绊住。
我把花朵揪下来,把花蕊放到脸蛋上染几下,把两个脸蛋染红。我抬着两个红彤彤的脸蛋回家。
像个唱大戏的。我妈说。
不要说大戏了,小戏我都不会唱一句,但染的红脸蛋影响深远。
那个红,红得深远,透彻,长久,直到长大,长到现在,再没有褪过。看样子,直到我长老,也不会再褪了。
七
除了一窝蚂蚁,我家还有一个癞嘟呱,住在菜园子里。
盛夏,癞嘟呱总是缓慢地行走在靠近土崖的那一边。它不肯轻易现身,现身的时候也是躲躲藏藏。我妈说它是癞宝儿,给家里守福气的,不能伤它,更不能赶它走。
它太难看了,我不敢抓它。
洛桑见啥抓啥,又胖又黑的毛软虫、油油腻腻的大泥虫、疙疙瘩瘩的癞嘟呱等等。对他来说,丑算个什么东西,但对我来说,丑是个不得了的东西。
不管是癞嘟呱,还是癞蛤蟆,这三个字放到一起看起来就是一副难看的样子。因此,我不抓癞嘟呱,但喜欢看它的动静。它缓慢地走,我蹲下来耐心细致地看,直到看得它走不动,趴在大头菜底下不动弹。
泥虫就是蚯蚓。我们不叫蚯蚓,就叫泥虫。它一辈子生活在泥里,叫泥虫是一件多么正确的事。
下了一场大阵雨,雨止住后,一伙大人扛着铁锨在门外喊父亲,父亲也扛着铁锨出了大门。
我们攒在村口。师大大对我们说,走,娃娃们,赶紧走,大路上一伙癞嘟呱在耍拳。说着他朝我们挥挥胳膊,走了。
癞嘟呱在耍拳?这个我们得去看看。
那时候我们刚看完《少林寺》不久,少林拳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印象。但除了学会一句“贪吃贪睡,不可教也”,并时不时地拿出来用一下外,我们还连一招一式都没有学会,难道癞嘟呱已经学会少林拳了吗?
大水果然把大路冲出了一个大坑,汪了一坑水。我们围着坑看了半天,一个癞嘟呱都没有,更不要说出来打两拳。
师大大他们边用铁锨补路,边看着我们哈哈大笑。
八
坐在大门前晾晒的青草上,我妈在给我布置一些活:到山里不要光想着玩,拔来些荆芥、薄荷和小柴胡,再挖一些野蒜来。但周围大白杨上蝉的声音又急又吵,把她的声音打败了,我只好认真地听蝉说话。
蝉说啥话了?我父亲问。
蝉的话我当然听不懂。
连个蝉的话都听不懂。蝉在说“记住记住记住”。父亲神秘地说。
我又仔细地听了一阵,果然,蝉在说“记住记住记住”。不知道它要记住什么重要事情,也不知道它究竟记住了没有。反正一到夏天,蝉都要这样辛辛苦苦地抱着树枝,粗声大气地反复提醒自己“记住”。
九
我家的猫像个高傲的公主,总是深沉地走在大墙上,当它的脚步突然变快一些的时候,夏天就要走了。
那两棵茶果树上密密麻麻的茶果还绿着,要等到秋天的霜杀一杀,茶果才会熟,到那时候,远远看去,像是谁在半坡里晒了两张金黄色的被面子。
杏子熟了。
只有宋爸爸家养着一棵甜杏仁的杏树。
但宋爸爸家的杏子我吃不到。不要说杏子了,他家菜园子里的蚂蚱我也不敢打主意,都是他家的。他家上面站着的云也是他家的,我不敢多看一眼。
我只能吃苦杏仁。
吃苦杏仁会中毒。兽医站的曹爷爷这样说。
但我们总是记不住,每年总有一两个人会因为吃了苦杏仁而呕吐不止。手扶拖拉机总是喘着粗气,把馋嘴惹事的人赶紧送去医院。
我吃多了苦杏仁的那个夏天,先喝了师奶奶端来的满满一大碗酸菜水。那是一碗世上最酸的酸菜水,一到夏天,我就会想起那个碗,一想起来,我的嘴里就会在一瞬间渗出满满一嘴酸水,让我吞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