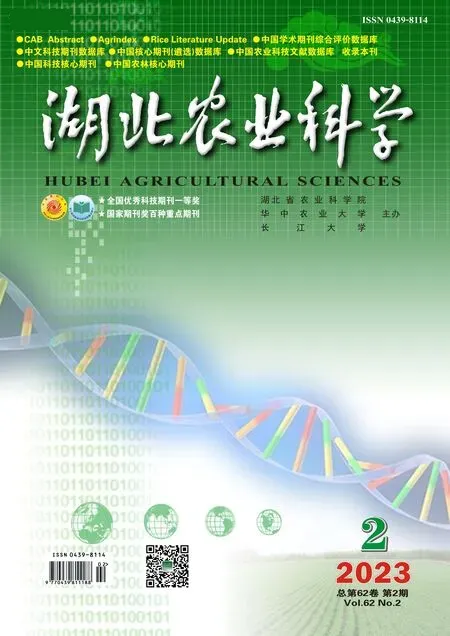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潜在风险和实践策略
2023-04-11何经纬孙子月
何经纬,孙子月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经过长期努力,2020 年中国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消灭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但是,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中国贫困问题就此消失,而代表着中国反贫事业迈向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起点[1]。相对贫困,是指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满足,但是与社会一般成员相比,经济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还存在绝对贫困的风险,特别是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不足,从而制约了其获得较高收入的一种贫困状态[2]。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于经济社会中,影响着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质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也指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在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无论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都是整个扶贫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绝对贫困治理阶段,中国以人均最低纯收入标准线或使用“两不愁三保障”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界定标准具有绝对性。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是贫困治理的深化,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相比,具有相对性、长期性、动态性等特征[3]。所以,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也应该要有所转变,否则将阻碍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但当前中国对于相对贫困人口识别仍主要以绝对贫困阶段收入标准为依据,对于相对贫困识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明显不足,迫切需要一个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标准。鉴于此,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制定新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探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及提高其瞄准度的实践策略。
1 学界对相对贫困识别标准的观点
贫困识别是贫困治理的起点,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和扶贫效率。长期以来,学界针对绝对贫困人口识别提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建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部分学者开始将贫困识别问题转向相对贫困领域。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有3 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应坚持单维收入标准。大多数学者认为不管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在社会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应该把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惟一或重要指标,但在具体的标准制定上还存在一定争议。孙久文等[4]提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选用不同比例的居民平均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线,并设置合理的浮动空间。还有一部分学者依据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最适宜的相对贫困最低收入线。如王小林等[5]认为按照国际相对贫困标准经验和中国反贫困的内容边界及政策效能来看,将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的25%作为相对贫困线比较合适;沈扬扬等[6]则建议相对贫困标准在城乡之间分开设置,并将居民收入中位值的40%设定为相对贫困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多维标准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一些学者认为相对贫困建立在生存性贫困满足的基础上,不能仅关注收入水平这一个维度,必须建构多维化的相对贫困认定标准及政策体系。檀学文[7]在其论述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兜底型、数值型、比例型、多维型及共享繁荣指标”为一体的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标准体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韦凤琴等[8]认为相对贫困除了关注到收入维度外,还应该关注生态和社会两个维度,并主张用AF 方法进行测量。唐任伍等[9]主张,为了提升贫困治理的效率,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建议将“关系贫困”“文化贫困”“精神贫困”等发展性贫困纳入贫困识别体系之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建议从教育、就业等其他维度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10]。
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们既不主张单维收入识别标准,也不建议运用多维识别标准,而是主张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制定更高的绝对贫困标准。如汪三贵等[11]认为,2020 年后中国贫困治理应参考国外贫困治理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科学合理地确定社会公认的基本需求水准并转换成与之相对应的价值量,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
总体来看,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问题。在这3 种观点中,第一种单维收入标准操作最简便。但正像第二种观点所说,单以收入指标识别贫困人口目的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不能反映相对贫困的全部内涵。所以,应该坚持多维测度标准。当前坚持多维测度标准的学者们虽然关注到相对贫困不仅要扶“贫”,还要扶“困”,但在制定指标时却割裂了收入之“贫”与发展之“困”的关系,导致多维指标过于混乱,现实中无法操作。第三种观点根据人的基本需求来制定更高的贫困标准也并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另外,不管哪一种识别标准,学者并未就其在测度过程中会遇到何种阻碍识别精准度的困境进一步讨论,也并未提出相应的实践策略。
2 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及潜在风险
本研究基于相对贫困的含义和学者已有观点认为,相对贫困不仅要测量收入之“贫”,还要测量发展之“困”。但如果不厘清收入之“贫”与发展之“困”二者的关系,将会导致贫困识别指标间缺乏系统性、难以比对[12]。所以,在把握收入测量与发展权利测量的关联性基础上,构建了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多维测度标准(图1),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在具体测度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实践策略。

图1 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多维测度标准
2.1 相对贫困人口多维测度标准
2.1.1 收入标准测量家庭之“贫” 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不可否认的是物质层面的贫困都占据其中首要位置。测量经济层面的贫困最简单、高效的方法就是测量收入水平。国际上通用做法是制定最低贫困线,即把收入低于贫困线下的人口界定为贫困人口。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中国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而在相对贫困时期,为了体现贫困的“相对性”,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优化贫困线标准,主张采用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中位值法来确定贫困线的标准[13]。
2.2.2 发展权利测量家庭之“困” 相对贫困除了收入上的“贫”,也包含发展权利上的“困”,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不仅要测量农户收入,还要对农户的发展权利进行测量。当前,影响个体发展权利并最终将导致收入贫困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和公共政策的享受情况。选择这3 个指标进行测量原因在于:第一,受教育情况关系到农户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影响个体收入;第二,劳动力就业情况也会直接影响个体收入;第三,公共政策的享受程度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权利实现,影响家庭收入和支出。
综合以上两点,并结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相对贫困的识别测度标准首先要对家庭收入情况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受教育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和公共政策享受情况进行评定,最终确定贫困户资格。
2.2 相对贫困多维测度标准的潜在风险
2.2.1 收入难以直接测量 由于农户收入具有非货币化、不稳定等特征,用统一的核算标准来计算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存在一定的难度。正如斯科特所言,这种简单化、清晰化的做法比较高效快捷,并且可以有效规避管理风险[14]。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收入不再仅依靠农业生产,也包括务工等其他途径,很难找到所有收入来源。即使收入来源已知,务农和气候有极大关系,务工天数和工资也较难预估,很难准确计算其中收入。除此之外,测量农户收入需要农户主动配合,但很多农户在“财不露白”的心理下或为了获得贫困户名额而选择低报自己的收入。
2.2.2 收入及发展权利地区差异大 绝对贫困阶段主要是解决生存性贫困问题,所以采用统一的绝对低收入线来进行识别。但是,相对贫困人口是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确立贫困资格。所以,参照群体的选择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还比较明显,城乡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相差较大。即使同样是在农村,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如果相对贫困识别标准不考虑地区差异,一律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则会增加瞄准误差。因此,在相对贫困多维测度的实施过程中,应该统筹城乡关系,制定差异化的标准。
2.2.3 “福利养懒汉”现象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认为,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国家应承担责任去改变贫困户的贫困境遇。但是,过于强调国家责任而忽略农户主体性,将与社会上多数人认可的伦理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容易导致福利的“污名化”[15]。
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不存在生存性的绝对贫困,所有贫困都是在比较中得来,具有相对性。这种比较如果不遵守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则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相对贫困多维标准的测度中,如果只单纯强调国家责任,不考虑贫困户的主体性,则会导致那些因赌博、好吃懒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等原因贫困的家庭都可享受扶贫资源。这种“福利养懒汉”现象与农村社会社区伦理相悖,会导致很多边缘户、非贫困户产生相对剥夺感,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2.2.4 “精英捕获”现象 “精英捕获”是指在资源下乡过程中,村干部等乡村精英利用身份、地位和关系垄断或截取资源的现象[16]。村干部属于乡村社会内部成员,对农户情况更为熟悉,在贫困识别时自由裁量权更多,影响更大。村干部要遵循国家行政体系中理想的科层制,但其权力来自村民,行事逻辑和权力生态深刻地嵌入在基层社会秩序中。农村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人们的日常行动总掺杂着人情和利益关系。因此,村干部在其施政过程中容易被人情和面子所裹挟。在相对贫困识别具体测度中,村干部可能会出现3 种倾向。
第一种是“帮亲”倾向,即村干部在对相对贫困户识别中存在“优亲厚友”现象。这些亲属是村干部选举过程中最大的支持者,如果村干部拒绝,就意味着他将失去所有的选票。第二种是“帮能”倾向,即对有利于自己仕途的“乡村精英”给予更多的偏袒。村干部会给予低保、贫困户等名额以获得“精英集团”在工作上的支持。另外,这些“乡村精英”比起贫困户发展意愿更高、能力更强、空间更大,更容易完成脱贫指标。第三种是“不出事”倾向。在基层社会,不管工作结果好坏,“不出事”是很多干部施政的首要原则[17]。黑恶势力和上访户作为农村治理中的“麻烦”人物,是“出事”的主要因素。村干部为了让这些“麻烦”人物服从自己的管理,只能给予其恩惠。
3 农村相对贫困识别多维测度标准的实践策略
3.1 可视化原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用统一核算标准对农户收入直接进行测量,存在很多难点。但是,收入贫困作为相对贫困多维测度标准中的首要方面,又必须进行测量比较。借鉴绝对贫困治理经验,认为可以采取一些可视化的指标来代替细致的统计测算。
第一种可视化指标可选择“购买物”来进行参照对比。消费情况直接反映家庭收入,这些购买物应选择可视化较强,操作简单,不用过多计算,通过走访便可一目了然的指标,所有农户都可进行参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消费能力过高、购买力较强的农户不允许被纳为“相对贫困人口”。譬如,高装修、高档次住房、买豪华车或大型农具、参加高档社交活动、水电和通讯费严重超标、子女就读高档学校等消费能力显然高于一般家庭的农户。反之,消费能力过低、购买力较低的农户应优先纳为“相对贫困户”。譬如,家庭中缺少必备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的农户应该被优先纳入。
第二种可视化指标可选择职业来评定收入情况。较低收入的职业人群优先纳入相对贫困人口中。职业是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不同职业对应不同的收入,可视化较强。通过对家庭所有成员的职业类型进行登记,再进行比较,会降低直接测量收入的误差。
第三种可视化指标可选择劳动力指标,通过观察家庭中劳动力多寡和强弱来进行家庭收入评定。劳动力数量越多、能力越强,家庭就能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一般来说,同村农户生存环境基本相同,一部分农户相对贫困往往是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或劳动力能力不足导致。在相对贫困识别多维标准测度过程中,应优先纳入家庭中缺少青壮劳动力或残疾等家庭。
3.2 差异化原则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发展不均衡问题。虽然经济社会整体向前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城乡之间、东西部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8]。相对贫困是以收入贫困为主、发展权利缺乏等全部包含在内的一种贫困类型。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均衡性,在相对贫困识别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必须体现其差异性。
首先,在收入测量层面,应该设定不同的贫困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2 189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 834 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21 元,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差1.56 倍。这充分表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上出现明显的高低差异化现象。为了适应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相对贫困人口的界定必须制定不同的最低收入贫困线。
其次,伴随着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也会产生差异。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教育和公共福利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尤其“寒门再难出贵子”问题逐渐凸显。在进行就业情况、受教育情况、公共政策的享受情况等测量时,如果不加以区分,则会导致多维识别标准信度和效度难以保证,难以瞄准真正的贫困人群。
3.3 组织化原则
为了避免相对贫困识别过程中,村干部等精英凭借自己在村中的身份和地位截取扶贫资源或出现“寻租”“优亲厚友”现象,要强化科层化组织建设,避免人情关系。
借鉴绝对扶贫中做法,在相对贫困识别中可规定村干部家庭或两代亲属中有村干部的家庭不准成为贫困户,以此来防止村干部优亲倾向;针对贫困识别过程中的“精英捕获”现象,建议可规定“私营业主或雇佣他人做生意、养殖或种植大户、工程拆迁户”等不准成为贫困户;而对于一些“弱者不弱”“老赖”现象,建议规定“群众反映强烈、长期上访、黑恶势力的家庭”不准成为贫困户。通过将上述3 类人群排除在贫困户资格之外,降低了科层治理在进入农村社会后的瞄准偏差。当然,如果这3 类人群中存在特殊情况,也可以申请进行审核评议。
3.4 合理化原则
国家责任下的扶贫工作主要以扶“穷”为主,但不管是在收入测量还是在发展权利的测度过程中不关注贫困户的主体性,便容易导致以下3 方面问题。一是让部分好吃懒做导致的贫困户形成“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丧失改变自身处境的内生动力;二是让其他非贫困户感到潜在的公平剥夺感,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三是导致福利政策的“污名化”。把贫困资源给予好吃懒做的居民,让其他人对福利政策产生质疑,出现福利政策的“污名化”。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在相对贫困识别标准测度过程中,应该设定一些行为规范化指标。这些行为规范性指标可从2 类指标进行评定:一是是否存在违背乡村伦理的行为。譬如,因为好逸恶劳、赌博造成的贫困家庭,子女有能力但没有赡养的老人、举家搬迁从不参与村中集体事务的家庭;二是是否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譬如,为了获得贫困户的资格而选择分户或折户、隐瞒或私自转移财产等问题的家庭等。通过这一系列行为规范性指标将一些丧失主体性贫困户排除在外,保证了扶贫资源的公正性,也彰显了扶贫政策的价值导向性。
4 小结与讨论
2020 年后,中国进入了相对贫困的治理阶段,迫切需要新的扶贫理论和实践研究。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不仅要体现经济之“贫”,还要体现发展之“困”,且不能割裂二者存在的关联性。因此,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应该有异于绝对贫困识别的单维收入标准,而应该将收入指标作为主要方面,还要包含就业情况、受教育情况及公共政策享受情况等多维发展权利指标。但是,在其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譬如,收入难以直接进行测量,存在较多误差、收入及发展权利地区差异较大、容易出现“福利养懒汉”“精英捕获”等现象,这成为阻碍相对贫困多维识别标准精准度的因素。为了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建议使用可视化、差异化、组织化、合理化等具体的实践策略,以此提高相对贫困识别多维测度标准的瞄准度。
本研究主要是对农村相对贫困识别标准进行讨论,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总体上优于农村,形成机理也有所不同[19]。纵观1949—2020 年绝对贫困治理各阶段的经验,也都是从整体农村开始,最后才发展到城乡扶贫政策的统一。所以,对于相对贫困治理不能操之过急,要先从农村开始,在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达到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再适时实现城乡相对治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