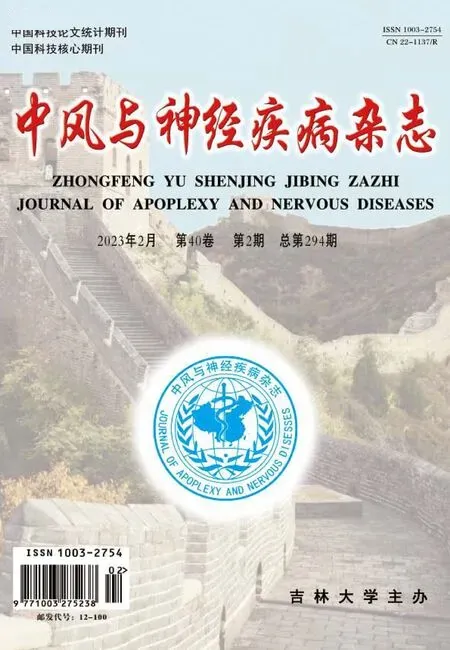VR技术在构建AD患者视空间障碍的数字化诊断标志物体系中的价值
2023-04-10何晓玲胡冉婷许若琳综述徐武华审校
何晓玲, 吴 臻, 胡冉婷, 许若琳综述, 徐武华审校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构成全球重大社会和经济威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之一,早期识别、诊断和干预是其预防的关键。传统的以临床经验和生物学标志物为依据的AD诊断体系存在储备的局限。随着虚拟现实技术(VR)等可穿戴设备的不断发展,AD“数字化生物标志物”诊断体系正在形成。本文将重点阐述VR技术在早期识别、预警、诊断AD时的研究进展,并展望其在未来AD防治中的应用前景。
1 日愈严峻的AD防控形势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和各类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普及,全球痴呆人口正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2021年WHO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现有痴呆患者约5 500万,未来10年还将增加40%,预计2050年将达到1.39亿。中国是痴呆症的重灾区,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认知障碍人群已高达5000万,其中6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6%[1~3],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致痴呆最主要的病因,对痴呆的贡献值超过50%[4],但在国内,长期存在的“三低一高” (识别率低、就诊率低和干预率低和误诊率高)现象以及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均加剧了本已举步维艰的AD防控形势。鉴于现有的防治手段均难以实现AD临床和病理的逆转,长期和大量的诊治和护理成本对家庭、社会和医疗机构均构成一种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大量的证据表明,早期干预有助于减缓AD的进展,早期识别处在痴呆前期的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主观认知减退(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甚至更早期的有病理无临床症状阶段(见图1中的B1~BX阶段)并及时进行预防性的干预可显著减少痴呆的转化率[5~7]。为此,当前学术界的最大共识是不断前移AD的识别和干预窗口。
2 现有AD诊断模式的弊端和新型“数字化诊断标志物”的兴起
基于病理学观察,长期以来Aβ蛋白沉积(A)、高度磷酸化的tau蛋白(T)和大量神经元细胞的变性和丢失(N)一直被视为AD最主要的脑内病理特征,也是构建不同时期AD诊断体系的核心标志物。从2007年的NINCDS-ADRDA诊断标准到2018年的ATN诊断体系[8],大部分实验室检测均是围绕这3个病理现象所产生的标志物而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AD临床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9]。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断优化的诊断体系越来越依赖有创性的腰椎穿刺[10],昂贵的(分子)神经影像学检查(如高分辨率的MRI[11]、特殊分子标记的PET-CT[12]等),且依然需要长时间的定期随访,从而难以成为社区大规模筛查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生物学诊断标志物(biological diagnostic markers,BDMs)与AD患者的认知障碍以及痴呆相关的精神行为异常(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BPSD)症状的外在表现缺乏明确的或点对点性的关联,也难以作为AD居家和社区早期识别的有效工具。事实上,轻症AD、MCI、SCD患者(可能还包括图1中的B1~BX阶段的患者)最早和最主要的外部表现多为日常生活、行为举止、视空间、言语、精神心理等方面的细微改变,通常只有患者本人及其最亲的家属或照料者才能感知,几乎无法通过任何问卷式的评估量表和/或基于BDMs的传统诊断体系识别。而随着近年来可穿戴设备、5G网络、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早期行为学(而非纯病理学)的细微异常正在催生一种基于可穿戴设备的数字化诊断标志物(digital diagnostic markers,DDMs)的AD早期识别全新体系。

图1 实线框表示该临床病理阶段的识别与干预手段已写入相关疾病诊治指南;虚线框则表示基于DDMs结合BDMs早期识别AD和超早期认知康复介入体系的构想;斜线上的8个AD脑病理示意图(从上至下)分别表示脑内病理从无到有、从轻到重
3 VR技术与正在兴起的DDMs体系
严格意义上说,VR技术并非一种新型技术。最早可追溯到1838年英国科学家Charles Wheatstone利用人类的视觉成像原理发明的立体镜。但早期的VR技术只有立体现实功能,无法做到姿态跟踪,而现代VR技术雏形是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Ivan Sutherland在1968年发明的巨型VR眼镜。上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游戏的兴起,VR技术引来了第一次发展热潮,而真正意义的现代VR技术则起源于2012年问世的一款为电子游戏设计的头戴式显示器(Oculus Rift)[13]。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和5G网络与数据时代的来临,VR技术正在实现全方位调动体验者视、听、触、嗅、味觉等各种感官,从而为认知医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众所周知,现代VR技术的基本特征是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构想(imagination),而虚拟技术的核心是建模与仿真,从而允许用户沉浸于虚拟的环境,产生新的想象和仿真的体验。目前,在用和在研的VR系统主要根据沉浸程度和系统组成分为以下3种: (1)非沉浸式的桌面VR系统,主要是以计算机显示器或其它台式显示器屏幕为虚拟环境的显示装置,用户通过键盘、鼠标、触屏或操纵杆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制作成本低,容易普及,但虚拟系统视野小,沉浸感差。(2) 半沉浸式的大屏幕VR系统是桌面式的升级,只不过显示屏为弧形宽屏幕、360°环形屏幕甚至全封闭的半球形屏幕,可将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相对更好地隔开,但所需设备复杂且昂贵,通常只用于某些特殊场合。 当今在认知功能VR评估研究中最为理想,使用最便捷的是。(3)全沉浸式的头盔式VR系统,由于它可将虚拟景物直接显示在头盔显示器(VR眼镜)上,完全隔离了体验者的现实环境,在高度实时性的基础上,辅以听觉、嗅觉、触觉、位置觉等其他感官信号刺激,大大增强了对虚拟环境几近真实的体验感[14]。而正是这种逼真的身心联结体验使得许多原本只能通过病史询问和纸质版问卷(如MMSE、画钟试验等)才能粗略探查的认知域功能(如视空间能力、执行力等),现可在虚拟真实的环境中得到数字化的精准测评,一旦结合任务导向性的认知康复训练,就有望实现“查-打”一体化的全新AD防治体系。
4 VR技术在识别AD患者视空间障碍中的研究进展
AD患者最大的临床特征是全面的认知功能减退与极少的躯体功能障碍形成鲜明对比(见图1),AD脑内病理所呈现出的慢性、迁延性、进展性特点决定了AD早期外在临床表现的隐匿性和轻症化,其中又以视空间记忆障碍最为突出[15]。 目前已知,视空间功能至少包括视空间感知能力、视空间结构能力和视空间记忆能力3个概念不同但环环相扣的功能分区模块,任何一个环节受损都可能导致视空间记忆障碍[16]。 早期的临床调查证实,几乎所有的AD患者及38%的认知正常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觉空间迷失[17],近一半的患者存在有视空间障碍方面的抱怨[18],以及在描述物体形状、颜色、对比度、运动感、阅读、空间取向和视觉搜索等高级功能的困扰[15,19~21],并在感知空间的连贯性和体验空间的丰富度上存在不足[22]。必须指出的是,早期的视空间障碍研究手段均采用问卷、量表、画图等传统神经心理学定性或半定量检测工具,存在着主观、重复、枯燥、容易受环境和人为因素干扰等诸多缺陷,尤其不适合轻症AD、MCI患者,甚至更早期的AD高危人群的识别。如何利用不断完善的VR技术构建一个能更早期识别AD的DDMs体系,以定量、实时、便捷反映与AD脑内tau病理密切相关的视空间记忆障碍是未来AD防治研究的新方向。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取得更多有关两者之间定量对应关系的循证医学证据;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社区和医院大数据的预测模型;最后还需在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并借助相关的干预手段(如基于VR技术的视空间康复训练)验证该模型对AD防治的有效性。
众所周知,AD两大病理现象(细胞外的Aβ沉积和神经元细胞内的神经纤维缠结)最先累及的脑区为记忆相关的内嗅皮质,然后才波及海马等其他脑区[23],长期以来,记忆力减退被视为AD最早和最主要的外部表现,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有相当多的患者在记忆力减退之前就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视空间障碍[24~27],且在疾病进程中的下降速度最快[28]。我们认为,这一错觉的产生一方面与这两个认知域在内容构成上以及神经传导解剖学通路上就存在着较大的重叠;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神经心理学评估工具不够精准有关,而能生动、具体显示视空间能力的基本要素(如距离、速度、位置关系、物体的形状等)的VR技术正好弥补这些缺陷。
无论是在动物还是在人类的认知地图中,路径整合都是一种至关生存的重要空间导航能力之一,且存在着连续型和布局型两种路径整合策略。前一种策略主要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更新(spatial updating)来实现,确保个体有效避开障碍物;后一种策略则是通过以环境为中心的空间更新来实现,确保个体不迷失方向[29]。Schöberl等[30]对照研究了21名遗忘型MCI患者(其中10例为ATN诊断体系中的A-,11例为A+)和15名健康人的现实环境空间导航能力,结果发现与健康人和A-患者相比,A+患者在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环境为中心的导航表现更差(P<0.001),其灵敏度和特异性(AUC=0.89)高于传统神经心理测试(MMSE:AUC=0.63)。Coutrot等[31]分别测试了49名年轻志愿者在真实街道环境和VR游戏环境中执行寻路任务时的表现,结果发现两者具有良好的匹配度。在一项开创性的VR导航测试结果与BDMs对照研究中,Howett D等[32]测试了45例MCI患者(其中A+T+12例;A-T-14例)和41名健康人的虚拟导航能力,结果发现:与后者相比,前者在找回起始位置时存在明显困难,绝对距离误差约为(57.33±17.87) cm(P<0.01),且A+T+患者MR测量到的后扣带回、海马、内嗅皮质体积更小(P<0.05)、绝对距离误差更大(P<0.001)。必须指出的是,这是首个人类路径整合受损与后内侧内嗅皮质体积减少密切关联的客观证据,不仅夯实了VR技术在检测视空间能力中的价值,也为基于VR技术所构建的DDMs体系应用于社区筛查MCI以及AD患者提供了依据。
而在一项多中心研究中,测试者通过操纵杆操纵虚拟人物在不同的VR环境进行各种日常生活活动,并首次引入VR分数[(导航能力+空间方向+记忆召回+正确视觉记忆-不正确的视觉记忆)/2]作为一种视空间能力综合指标检测受试者的视觉感知、视觉构造和视觉记忆功能,结果发现正常人(U=4.532)、MCI患者(U=3.500)和痴呆患者(U=0.944)的VR分数呈进行性下降趋势[33]。但这项横断面研究并未纳入SCD人群,也未考虑年龄相关的生理性变化(见图1A~E,特别是B1-BX阶段),因此我们认为,在明确VR分数对AD早期识别和诊断价值之前,首先应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年龄相关的VR分数变化曲线(常模),其次还需要更多前瞻性的基于高危人群的随访研究证据。
必须承认,绝大多数AD诊断学研究仍主要围绕基于脑内病理的BDMs而开展,而具有认知医学研究价值的现代VR技术起步时间较晚,且视空间障碍显然较一般的病理现象更为复杂。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实了VR技术在早期识别AD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其构建的DDMs体系仍较为稚嫩,远不能取代甚至平齐BDMs在AD的诊断价值,更未写入任何国内外AD诊治指南。认知领域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最大的难度在于实验的干扰因素和实验结果的解读方式更多。如前所述,VR技术已经开始展现了可能较BDMs更早期、更便捷、更生动、更适合开展认知障碍精准康复的临床价值,但作为一种电子化设备,它依然存在着目前难以克服的障碍,如老年体验者的接受度低、测试过程中的恐惧感、晕车样的头晕、眼花、恶心、共济失调等不适反应等[34]。
5 前景展望
近年来,VR技术及其相关设备正在快速升级换代和商业化普及,伴随着其他信息技术(如5G网络、大数据平台等)的同步快速发展,其在AD防治中的应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但它的优势与劣势同样明显。就劣势而言,部分是技术层面的问题[34];部分是文化心理层面的问题[35],但均不是无法克服的问题。我们认为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研究:(1)进一步验证基于VR技术的DDMs体系与基于脑内病理BDMs之间的匹配度和互补性;(2)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构建基于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DDMs常模;(3)鉴于AD型认知障碍的全方位性以及VR技术的局限性,评估与筛查时还应同时结合其他可穿戴设备(如眼动、步态、足底压力、关节运动传感器、头套式脑电信号传感器等)所采集到的DDMs;(4)鉴于AD患者及其高危人群多为老年人,认知评估与康复均具有极强的个体化色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检测和康复治疗时的不适感,VR设备还可更轻巧和小型化,并在设计虚拟场景时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视觉和心理适应能力以及个体文化与心理因素。综上所述,VR技术已显示出在构建AD患者视空间障碍的DDMs体系中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仍亟需大量的研究证据和技术上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