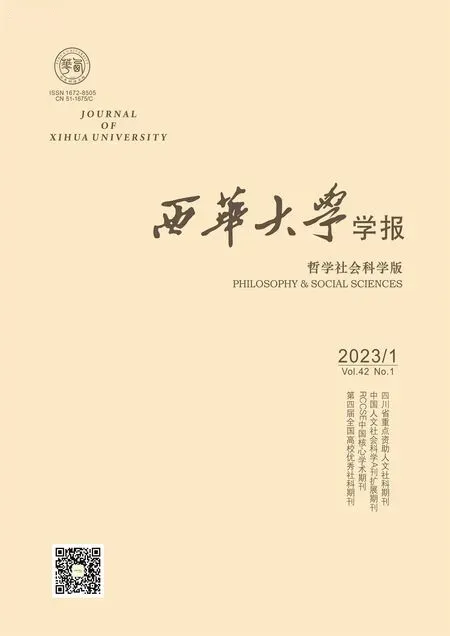程瑶田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兼谈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
2023-04-07王寅
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笔者曾于2007 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1](下文简称《初探》)一书,指出外语界的同仁在学习国外语言理论的同时,也应重视我国先辈们有关语言方面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华夏有着高度发达和灿烂辉煌的文明,古今学者对于语言的研究成果丰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语言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遗憾的是国内大多外语学界的同仁未能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笔者还认为,比较语言学,或曰对比语言学,不仅要专注中西语言表达和现象层面的对比,还要加强理论层面的对比,详析各自的成就与得失,以能形成互补之格局,而不再是一味地进口,盲目崇拜舶来品,学术上的崇洋媚外要不得,很要不得!外国的“学术月亮”常常不如中国的圆,这就是钱冠连所说的“当西方的灯不亮时,何不亮起东方之灯”[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地球村的互通有无和融合交流,才会出现学术研究“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繁荣景象。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学界在语言理论层面的对比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建立了对比语音学、对比词汇学、对比语法学等。笔者认为,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展开对比,但遗憾的是语义层面的对比研究尚为空白,这就是当初笔者写作《初探》的初衷。注意,仅是个“初探”而已,未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汉语界的训诂学与外语界的语义学一直存在各自为政的状况:汉语界少有通晓西方语义理论的学者,外语界也极少有人学习训诂学,将中西语义理论进行对比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两界长期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尴尬局面。《初探》意在对此不足有所弥补,但离解决这一缺憾的目标差之甚远。完全可以预见,加强中西语义理论的对比研究,将是21 世纪对比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笔者所言:“当我们站在今天人类认知的发展高度来回顾往昔、观察历史,完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运用对比的方法将有关的同类观点、相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如果要考虑到时间因素的话,那就是西方思想的很多精彩观点在我们老祖宗的文本中早有表述,正是这些闪亮的思想火花构成了中国国学的精华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语言学研究团队发现美国学者Lakoff 和 Johnson[3][4]所创建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也存在诸多不足,为弥补其不足,团队成员提出了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5][6]。
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通过考察,guŏ luŏ音可写出332 个不同的词语,所体现的正是“体(语音感知)”和“认(心智加工)”原则,也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完全吻合,这为当下所论证的像似性观点提供了中国古代学者的佐证。近来,我们认真学习了他的这本著作,感触颇深,心得甚丰。
一、程瑶田在学界的评价
程瑶田在汉语界被关注的程度较低,处于吠影吠声之状①,在外语界更是鲜有人提及,一直是久付阙如,但他头上的光环却很多,在诸多著述中常称他为:清代最卓越大家之一、第一流学者、经学大师、乾嘉精英、著名徽州学者、皖派之学的大儒。他与乾嘉学派最重要的学者皆有交往,堪与顾炎武、闫若璩、江永、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等比肩而立。
王念孙在《果裸转语记》后的记跋中给予程瑶田高度评价:“先生立物之醇,为学之勤,持论之精,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7]王国维曾评价道:“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棲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天道剥复,钟美本朝,顾阎浚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学之奥启于金坛,名物之赜理于通艺。”[8]“程氏”指程瑶田,他见长于“名物学”研究,“通艺”指程氏的《通艺录》,达42 卷之多,为名物学之精华。
在陈冠明校点本《程瑶田全集》的前言中曾引用我国著名经学史研究者周予同的话:“乾嘉学派吴派、皖派,唯独不及程氏。”[7]接着他又引用了我国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的话:“历述汉代郑玄弟子到清代承传郑学之人,清代有二十人,有江永、金榜、戴震、段玉裁、淩廷堪、胡培翬等,同样唯独不及程氏。而程氏《通艺录》于三礼、于郑玄之贡献,无疑要超过上述诸人。”[7]他还指出:“林昌彝、章炳麟、梁启超等独具慧眼,对程氏作出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将其纳入乾嘉学者精英乃至清代经学精英之中。”“程氏学说,深为同时代学者推崇,甚至可以说,在学者心目中,程氏所考,已经达到同类著作最高水准。”[7]
从以上评价可见程瑶田所享有的学术地位之高,这也是安徽省大力支持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整理出版《程瑶田全集》(共四卷)的缘由。笔者认为,这当引起学界(包括汉语界和外语界)的高度重视。
二、程瑶田《果裸转语记》学术价值之当代解读
在程瑶田的所有作品中,《果裸转语记》最为学界所熟悉,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因此自笔者拙书《〈果裸转语记〉现代汉语译本及其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9]出版后,很多学者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并非是对拙书的赞誉,而在于程瑶田的功德。本书名曰“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在该书第一版前言中有所述及,且在第三章中从“声训法与音义学”和“像似性十辨”这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现笔者再作小结,以飨读者。
(一)开拓精神值得继承:学科门类的突破
程瑶田开拓了一个新学术领域“名物学(又叫名物训诂、名物研究、名物文化)”。正如上文所录王国维的赞叹语“名物之赜理于通艺”,充分肯定了他所著的《通艺录》(42 卷)及其他著述的学术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将“名物”解释为事物及其名称。那么据此“名物学”就可描写为:一门解读古代语言中名物词的学科,主要研究以名指物,得名缘由、异名别称等现象,考证事物之名称和实体间(即名实)的关系,探索名物渊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该学科②通常隶属训诂学,关涉语源学。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会涉及成千上万的事物,任何作品都离不开用词语来指称事物,可谓俯拾即是(钱慧真 2008[10],张桂丽2015[11],青木正儿 2005[12])。正如王强(2004)所言:“有文明兴起,就有名物产生。名物本身毫无遮蔽地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显现一个民族各个历史阶段时代灵魂的事物。”[13]
人类生活在“名物世界”里。由于自古至今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人群的迁移和融合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史,言语也一直处于不断流变和互通的过程之中,方言也多有各自的表达习惯和交流方式,今古异称,方土殊名,传写之讹,转注之变,假借之乱,名物指称的考证就显得异常复杂,历来令学者们深感棘手③。但程瑶田能综合形与声的联系,观察其中变与不变的关系,探赜索隐,睹其会通,穷其变化,确证名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充分显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当受到语言学界(包括汉语界和外语界)同仁的高度关注。
“与时俱进”是我国当下社会的时代精神,“继承创新”是各条战线的主要旋律,这也正是当代科研人员所应牢记的奋斗目标。我们应当继承程瑶田这种开拓精神,勇于创立新学科。程氏在《果裸转语记》文首有一句话:“双声叠韵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7]该句的主语“双声叠韵”可换成其他若干词语,一言以蔽之,任何学科的许多现有论述不可为准则典要,大有可被解构和突破的余地,当遵从“唯变所适”的规律行事。我们要永远走在追求学术前沿的路途之中。
(二)勇于拓宽学术视野:学科内层次的扩展
我国古代的名家学者常被冠名为“杂家”,因其往往是多科学问兼而通之,可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还可能兼为科学家等。程瑶田也不例外,他集多科目于一身,学术视野十分开阔,堪称“跨学科、超学科”文理兼通的博学型人才。正如陈冠明[7]所说,程瑶田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既是汉学家、朴学家,又是宋学家、理学家。他对义理、训诂等兼而治之,且在诸多领域皆卓有成就。
大多学者是以《果裸转语记》而认识程瑶田的,其实除此之外,他的《通艺录》(42 卷)所涉内容更为宽泛,具有上文所述“杂家”的一切特征,更该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他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建树,其思想是整个清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程瑶田的理学研究在总体上虽说属于唯心主义,但也不时放出唯物主义的光芒。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的学术视野之宽泛。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他也勇于拓宽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如下3 个方面。
1.从字层面到词层面
扬雄在2 000 多年前所提出的“转语”(郭璞称之为“语转”,戴桐、方以智称之为“一声之转”),主要考察的是“字”的层面,而程瑶田将其拓展到“词”的层面,使得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从“字源学”进入到“词源学”领域,这两者可统称为“语源学”。西方19 世纪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此相同。这也与上文所说的程瑶田所具有的“开拓精神、体认原则”完全吻合。
程瑶田较为系统地探索了古人“称名辨物”之意,标志着汉语训诂学和词源学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同时也是连绵词(又叫“嗹语、连语”)研究的科学化开端。他在《果裸转语记》中首开先河,尝试从民俗学、语源学的角度来探索古人命名事物的体认理据,使得国人进一步认识了“因声而知义,知义而得声”④的训诂原则,率先从同源词角度来汇释在音义上同出一源的双音词,且以“果裸”为线索,将与之音义相近的332 个连绵词进行丝联绳引,疏通证发。程瑶田认为,不但在单音节字中有转语现象,在双音节词中也大有此类现象,且加以广泛调查、认真收集、系统论证。该文虽仅限于“果裸”,但对于同源词族的训诂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从声母层面到声母兼韵母
方以智称“转语”为“一声之转”,后为清代学者所接受,且将其上升为“声近义通”的训诂原则,这是就“声”部(即辅音)而言的。程瑶田将其拓展至“韵”部(即元音),提出了“韵叠理论”和“韵同义通”的原则,这就是他在文首开门见山所亮出的全书论点“双声叠韵之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洪印绶在《解字小记题识》中对这句话注释为“双声不可以声拘,叠韵不可以韵限,唯变所适而已”。
这就将语音的两大分类(声母、韵母,辅音、元音)与字、词两层面的转语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转语”中“语”的内涵更为丰富,“音形义”诸要素的研究更为深入,训诂学的视野随之更加开阔,语言的系统性也更加得以彰显,他的开拓精神和睿智多谋由此可见一斑。
3.从书面语到鄙谚里语
昔日训诂学家,如扬雄、郭璞、戴桐、方以智、戴震、王念孙等先贤诸家,主要以字书、词书、韵书等书面语言为考察对象,而程瑶田还兼顾到方言谣俗。正如他在《果裸转语记》篇末所言“来今往古,四方上下,大夫学士,老妪稚子,典册高文,鄙谚里语。胡不佽焉,兹为遗矩”[7]最后八个字的意思为:何不将它们编录在一起,作为一个准则。
王念孙在《果裸转语记》后的记跋中也指出:“由经典以及谣俗,如出一轨。而先生独能观其会通,穷其变化,使学者读之而知绝代异语、别国方言,无非一声之转,则触类旁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7]一个“独能”,说出了程氏独具慧眼的才能;一个“会通”,道出了他融会贯通的治学风格。
这种“拓宽视野”的研究思路,对于21 世纪的学者来说也很有指导意义。科研人员都有各自的专业,如何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拓宽视野,对于能否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语言学界,之前的语言学研究多局限于词层面,是乔姆斯基,将其拓展到句层面;韩礼德,又将其拓展到语篇层面;王天翼[13]始而关注拷贝句的邻近句群,从而又开发出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层面;近来,杜布瓦和曾国才在体认对话句法学的理论框架中开始研究邻近语对的对话层面,他们的创新方法与程瑶田的研究思路完全相符。
(三)实证考据的体认方法:实证主义之中国先驱
汉语历来有倡导语料考证的传统,这种方法历史久远,也为汉学界所擅长。而程瑶田则将这一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为学界所称颂。他深入民间,调查方言,且以其证古,兼顾方俗,广求同例,博考文献,观其会通;他还敢于挑战前贤⑤,拨乱反正,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冠明[7]指出,扬雄、郭璞、戴桐、方以智、戴震、王念孙等先贤诸家主要从事理论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多不带有实践性;而程瑶田率先将转语理论付诸于实践,用理论来解决实践问题。朱星[14]评论说,程瑶田此文实为清代转语音变论词源学最早一篇应用于实践的论文。这都充分说明程氏为“实据考证”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
正如上文所引王念孙对程瑶田的高度评价,说他持论之精罕有其匹,之所以能持论精确,正在于他擅长实证考据,如他在《释虫小记》中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更正了前人之误。《诗经》曾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后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说文》还认为此乃果蠃无生育能力所致;毛传、郑笺也都认为“果蠃养螟蛉之子”。而程瑶田发现,果蠃以螟蛉之子为己子之食,而不是在养育螟蛉之子,这说明果蠃是有生育能力的,从而更正了古代名人之言,只有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才能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这正是对“体认”二字的最好诠释。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源自人们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感知体验才能发现“音”和“义”之间的理据性关系。
另外,他所撰写的《九谷考》也须常到田间询问农民才能写得精准,正如陈冠明所言:“几乎事事、处处,亲临考证,皆凭‘目验’。”⑥“程瑶田考据名物,尤重实证,反复取证,不厌其烦,要在于证成其说而已矣。”[7]这确实大有唯物主义科学家的风范,也是清人治经的重要特征。
只有经过穷搜曲证,多方对比,深入民间,才能求得真知灼见。程氏这种批评前贤之论述、废弃古人之陈言的精神,也与上文所述的“开拓精神”完全吻合,他以其卓见高识,耳证目验,通过实证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之所在。正如姚淦铭所言:“经书不当经书看,而当史料读;圣贤不当圣贤看,而当凡人看。”[8]这也是他能成为清朝一代鸿儒名家的原因。
“考据学”中的“考据”,又叫“考证、考核”,是古典学术研究中一种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指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史料和史实的本源、流变、时地、真伪、是非、异同等进行探源、疏通、索隐、纠谬、考辨等的对比研究。若将该方法提升为一种方法论或学问时,就称其为“考据学”或“考证学”。该学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可包括古典文献学的所有领域和治学方法,后者指古典文献学或朴学的一个分支[15]。程瑶田与其他乾嘉学者一样,重视实证,善于考据,他的《果裸转语记》便是最好的例证。
考据学意在考证文献资料的正确性,存真去伪,其主旨在于一个“考”字,在广泛和深入考证史料后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可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史料或为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们都极尽考据之能事,为该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程瑶田也不遗余力,考证名物之制,写了许多以“考”为题的作品,诸如“九谷考”“禹贡三江考”,还有很多“记、说、录、述、议”等,在整理、考辨、校勘的过程中,无一不以“实证”为方法,既考名物,也证制度[7]。
程瑶田长于小学,也精通考古学,故而常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小学训诂”,这必然要持“据实为证,实事求是”的立场。他曾作《考工创物小记》(共8 卷),对车制、兵器、理器、乐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如他曾听说一位姓宋的朋友谈及一把古铜剑,就索来亲自审验鉴宝,发现这把剑与《考工记》⑦所述不同,据此断定它为秦汉之后的物品;又据其形制,经反复考证认定此为《汉书·匈奴传(下)》所说的玉具剑,这就将鉴宝活动与名物训诂和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此类例子甚多,恕不一一列举。他的这一实证考据的研究方法对考古学无疑也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难怪商承祚直接将他称为近代考古学之“开创者”[16],郭沫若直接称其为“先驱、开山鼻祖”[17]。
程瑶田还在生物学、农业学领域卓有造诣。他在《九谷考》(共4 卷)、《释草小记》(共2 卷)、《释虫小记》(1 卷)中既参照文献,调查经传注疏,进行字词训诂方面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目验”,反复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还亲身实践,进行田间地头的试验,从而得出了很多科学结论。因此,他首开近代生物学研究、农业考古学之先河,郭沫若就此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为这两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瑶田还著有《数度小记》,“数”意为“计数”,“度”意为“测量”,这显然与上文述及的生物学和农业学一样,隶属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属于经验科学,这其中必定要涉及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
西方自孔德于1836 年正式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之后,倡导文科和理科都可统一在这个研究框架之中,当今语言学界提出的“数据库”“语料调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法,与程瑶田所倡导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文科研究切忌放空炮,政论文必须要有论点和论据,缺一不可。程瑶田在《果裸转语记》的第一段中就开门见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当今普通语言学中的许多观点与其完全相通);其后便是论据部分,从古籍和方言中收集了332 个“果裸语族”派生词以佐证自己在文首提出的论点;最后两小节为结语,堪为演绎法文章之佳作。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内容丰富,论点正确,论据充实,不愧为今人所高度称颂的优秀传世作品,称程瑶田为“中国实证主义之先驱”,当之无愧!
(四)转语理据与像似性:批判索绪尔任意说
转语起于“形同(义同)则音同”的原则,在体验事物形状、用途等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基础上,古人就“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的‘取’,体认语言学所论述的‘认知加工’与其相似)”相同或相近的读音来命名。程瑶田基于“果裸(guŏ luŏ)”音分析了332 个同族派生词,以此来证明了这一论点,这与Lakoff 和Johnson[3]所论述的“隐喻认知理论”和“像似性”大有相通之处。当产生某一语音常用来表示某一意义的象征关系之后,古人就会用“转语”的方法来派生相关字词,这也与汉语造字六法中的“假借”认知方式密切相关。同时这也充分说明,字词的语音形式与所表意义之间的结合并非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这也印证了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观点:“像似性”才是语言的本质之一,从而批判了索绪尔的“任意第一说”[18]。倘若他能在百年前读到程瑶田这本著作,就不会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任意第一说”了。
笔者在《〈果裸转语记〉现代汉语译本及其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的前言中已述及这一点,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何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前后修改了二十几遍,仍会有误)来将程氏该文译成现代汉语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中我们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研究国外语言学的同仁不必仅将眼光盯在国外学者及其论著上,不可忘却宝贵的本土文化,也应继承程瑶田的“开拓精神”,不断“拓宽视野”,认真学习我国学者(包括古人和今人)的经典论著,既要进行中西语言表达层面上诸多现象的对比分析,也要开展中西语言学家及其理论方面的对比研究(参见文首所述)。
当今国外认知语言学家对索绪尔“任意第一说”的批判甚多,国内学者如许国璋、沈家煊、严辰松等及笔者也发表了相关论述[18][19]。体认语言学接受了这一观点,且将iconicity 译为“像似性”,在原译法“象似性”的基础上,在“象”字上加了一个“亻”旁,以突显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人本观。目前,语言符号像似性理论已为大多学者所接受,它不仅为语言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同时也为语言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我们不能再过分强调“惯用法、死记硬背”了,而应努力依据像似性理论揭示语言如此表达、而不那样言说背后的认知动因,若能在教学中将有关语言现象的表达理据解释清楚,这对于语言教学必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内很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与程瑶田所提倡和坚守的“开拓精神”“挑战权威”“理论联系实践”的做法一脉相承。
需要特别正名的是,国内不少学者常以荀子作为“任意说”的代表,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他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三句话一气呵成,学界常有人喜欢只引用前两句来呼应索绪尔的任意第一说。这种三分之二的引用显然大有断章取义之嫌,是很不妥当的,也是极不严谨的⑧。若将这句话置于原文中反复阅读,仔细揣摩,会发现前两句话是在为第三句话作铺垫的,第三句话才是重点:具有理据性的名称才是“善名”,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再者,“约定俗成”与“任意性”绝非同义术语[20],前一个术语中还包含“如何约定、怎样俗成”的问题,有理据的名物词显然更易于被约定俗成。因此将荀子归入“任意说”的中国代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当予正之。学界不应当是“人云亦云”,一人有错,就误错一大片,以讹传讹要不得,而应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据实还实”“我思则我云”的程氏风格。
结语
常言道,“风物长宜放眼量”,若能继承程瑶田的勇于开拓之精神,就会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切实贯彻“跨学科、超学科”[21]的研究思路一定会给学界带来丰厚的科研成果。笔者这里用了“切实”二字,意在强调要见诸行动。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喊喊口号实在是太容易了,而真的落实在行动上,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是需要花时间、下功夫、费精力的。稍微回顾一下近几十年的历史,自20 世纪7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提上日程,逐步为学界所熟悉和接受,但这几十年来真的能做到“跨”与“超”的学者,相对于外语界和汉语界的高校教师队伍来说,为数不多。学界常有这样的情形:不少人往往是跟随一个导师,专注一位学者,主攻一部作品,就某一狭窄领域奋斗一辈子。如此作为当然是可以的,这与“专业”中的“专”是相通的,也与“钻”相吻合。但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学术在进步,倘若某一领域或专业(特别是文科)已被钻研了很多年,再向下探索已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当然能有新发现也是值得点赞),此时若再坚守寸地,就很值得商榷了。笔者[22][23]曾提出“纵横结合”的科研思路:既可横向深入,坚守某一学派,一辈子做到底,不断解读出新内涵;也可纵向发展,当某一学派已有一定年头难以深入时,可转向另一新学派,或进行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这就像在同一个地区挖掘矿藏一样,若长年累月地挖下去,总有穷尽之时,当再也难以挖出新名堂时,何不换个地点,拓宽视野,另辟蹊径?就像西方哲学家一样,若沿着同一思路研究难以深入之时,就发动一场“转向”运动,西方哲学就是在“四次转向”之中走到了今天的后现代时期[23]。因此,科研压根就谈不上“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柳暗花明又一村”总是有的。我曾采用仿拟修辞的方法,称其为“进一步则海阔天空”。
当前我国正大力倡导“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其核心就是要“打通文史哲,古今中外”,这为外语界同行认真研究程瑶田,反思国外理论,建构本土化语言理论提供了科研方向,有助于奏出中华民族敢于立世界学术之林的最强音。从上分析可见,程瑶田该书及其研究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在为《程瑶田全集》(共四卷)所作的“编印缘起”中所言:“编辑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7]同样,今天在学习《果裸转语记》时也应当牢记这一立场,注重历史,实事求是,继承其精华,指出其不足。对于外语界的同仁来说,既要学习外国理论,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也勿忘我族先辈,执行“古为今用”的方针,这便是本文冠名为“当代解读”的含义。
注释:
① 陈冠明(2008: 25)指出:由于学术界惰性惯势,学者于程氏《通艺录》仍处于陌生状态,尽管该书名声不小,只是吠影吠声而已,并未触及实质内容。因此,《通艺录》尚属于学术界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客观上说,对于程氏不太公平。
② 五千年的华夏有高度发达与无比辉煌的名物文明,历史上有关名物学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异彩纷呈。《周礼》首用“名物”一词,出现达19 次之多;《尔雅》为名物学研究的发轫之作,共收集专名344 条,分19 类(有3 类与语言有关,其余16 类都为名物类),有“转语”之实而无“转语之名”;扬雄(公元前53—公元后18)的《方言》从民俗和方言的角度广泛收集整理了同一事物因时空变化而出现的异名别称;许慎(约58—147)的《说文解字》主要依据形训法,对汉字本身的结构说解名物,尝试从语言角度研究名物,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刘熙(约160—219)的《释名》基于因声求义法(即以声训的方法:根据声符求义;或转语求义)来推求事物得名之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汉代名物学的发展。魏晋以降,古代名物学进入了多科边缘(如博物学、考古学、古玩研究、药物学等)研究的新阶段,从而将这门学科拓展到现实生活中所涉具体物质的综合知识。直至清代陈元龙(1652—1736)的《格致镜原》,古代名物学已臻其形,成就显著,乾嘉学者们(1736—1821)也对这门学科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其更趋成熟。国内外都有学者(如钱慧真、张桂丽、青木正儿)认识到,有鉴于当下名物研究较为沉寂的现象,提出应将名物学从训诂学中分离出来的观点,以期能另外形成一门像“语义学、语源学、语法学、修辞学、篇章学、校勘学”等的独立学科,并加以大力发展、深入研究、辨伪存真、系统梳理、形成盛况,以利于突显其在历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辉煌成就,这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能进一步彰显灿烂华夏之名物文化。钱慧真不仅持这一观点,还主张区分“名物学(持名找物)”与“博物学(持物找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研究“汉学”的专家青木正儿还于1946 年始而在京都大学、九州岛大学、立命馆大学等开设《名物学绪论》《名物学通论》的课程,为该学科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③ 商承祚(1902—1991)于1938 年在谈及后世难以考知古代文献中名物时,曾列述了3 个原因:(1)年代久远,器用更易;(2)方言名物,各有异别;(3)一物数名,易生眩惑。因此,学界虽用力,致力勤,通者不过三四,余复渺茫而莫决。
④ 陈冠明(2008: 32)指出,清代是“一声之转”学说之巅峰时期,尤其是乾嘉学者,如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等人,将此学说提升至“声近义通”的理论高度。
⑤ 程瑶田在《通艺录》中对于前人成说的批驳,可谓是俯拾即是。他敢于挑战诸如郑玄这样的权威经学大师,崇尚实事求是,不迷信“汉之经师”,发现他们常常犯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错,且数量还较多。程瑶田处处显现出“破字当头,勇立理论”的治学风格,参见陈冠明(2008: 51-52)。
⑥ “目验”二字在《通艺录》中出现频率最高。
⑦ 该书出于《周礼》,为先秦著述,是一本记述关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
⑧ 据笔者所知,胡适于1922 年最早在《先秦名学史》(英文版)中率先只引用前两句,而去掉了第三句,此后汉语界便有不少学者照此办理(参见王寅2007: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