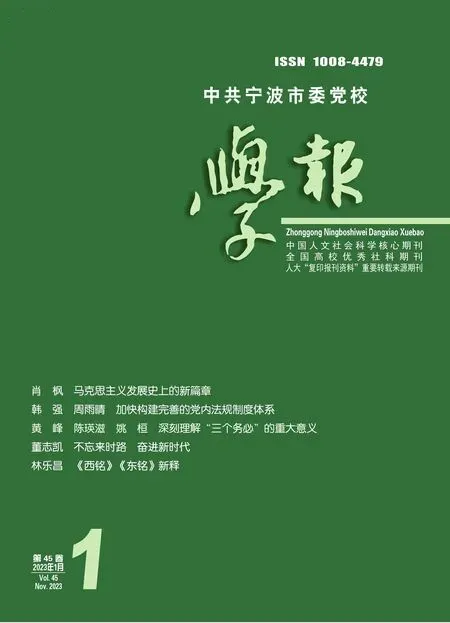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从历史源头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23-04-07肖枫
肖 枫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 100038)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中国“两个百年”交会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盛会结束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立即掀起了全面学习、精准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各大媒体期刊陆续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和见解。笔者在本文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源头出发,围绕“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关问题来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历史眼光”,学习领会这次历史性大会的伟大精神。
一、树立“历史眼光”,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历史眼光”“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2]69,“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70。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源头上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可进一步提高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15。理想信念如果丧失了,党心必散,民心必散,党和国家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共产主义事业,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这必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的任务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密不可分。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就是共产主义事业,每天的生活里面实际上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因素,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脚踏实地迈向共产主义。
二、“共产主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87毛泽东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5]686。这实际上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的。狭义的共产主义指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广义的共产主义则是指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二者既不可混淆,也不可割裂或对立。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个界限必须划分清楚,否则就要犯超越阶段的错误。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决不可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一切实际斗争和运动,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各不相同,但毫无疑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坚定选择、并终生坚守“共产主义”旗帜。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使用很讲科学性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将《共产党宣言》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呢?据恩格斯回忆:“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4]256—257但在19 世纪下半叶,由于一些欧洲国家还在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人政党需要参加并领导这一斗争,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都叫做“社会民主党”。对此,恩格斯解释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指“共产党”),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 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不确切的”。但是,恩格斯“容忍了”这一名称。他说: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它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让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也许可以过得去”[6]490。另一方面,在不需要使用“共产主义”概念的地方,恩格斯是不赞成使用的。考茨基曾于1894 年2 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就他和伯恩施坦准备出版一本“社会主义史”丛书向恩格斯征求意见,恩格斯于1894 年2 月13 日回信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7]203。这说明,恩格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并对使用“共产主义”概念的科学性十分注重。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历来不愿表示“预定看法”,而强调“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没有最终目标”。恩格斯在1893 年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6]628—629。他并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443。
共产党人要动员和组织群众为美好生活而斗争,长期以来只是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但要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种传统解释仍然难以让人了解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对于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难题的追问,但得到的答案不是学者式的抽象解释,就只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和描绘。
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条件论”和“过程论”
有论者强调以下观点,即《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对此有必要适当加以解释和说明。
究竟应如何认识和理解“消灭私有制”?简单地说,这是最终目标,而且是有条件的,决不能将其简单化。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4]239。后来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9]631。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阶级差别的消除”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9]273。这就是说,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正反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的正确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这表明,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我们当前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一致。
中国已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新涌现的“六个社会阶层”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①。在国际上,中国改变了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旧观念,树立起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新观念。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善于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从理论上讲,对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既是“条件论”者,也是“过程论”者。他们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划分,实现国家消亡,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目标,需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这就是说,除政治纲领还必须有经济纲领,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按唯物史观所作出的深刻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314(请注意,这里根本谈不上“自由人联合体”)。此外,未来社会在经济上还有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在那“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9]305,没有商品和货币,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做了相关的扣除后,“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9]304(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劳分配”)。在这里,事实上“不公平”的弊病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305—306。这就是“条件论”。
至于说“过程论”,马克思在“两个必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33。经过40 多年实践后,1895 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作了反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在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1]512—513。此外,恩格斯晚年还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有许多新的进步,他早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他强调,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策略要有新变化。这表明资本主义也会出现新特点,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的历史过程。
四、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中吸取经验教训
列宁是第一个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根据自己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吸取教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2]367。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并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从而改变了先前的做法,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这实际上是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靠“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来实行。列宁明确表示“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3]176。
1921 年,苏维埃政府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工业企业重新实行非国有化,承认商品货币作用,大力发展商业,实行租让制,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往。政府就是要实行“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并把握好“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认为对“物质利益原则”(或“同个人利益相结合”原则)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这是“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13]191。列宁由此认识到了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改变了“共产主义很快会到来”的估计,强调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作出过乐观估计。1920 年他甚至预言,现在15 岁的这一代人,“再过10—20 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14]311。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15]335,在经济建设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15]336。“‘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从资本主义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15]183。
同时,列宁在对外政策方面调整了“唤起世界革命”的战略,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明确提出要“与世界相联系”的思路。这为苏维埃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基本国际条件。列宁提出与世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客观基础,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5]167。列宁调整对外政策,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生存问题,但也包含了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他强调:“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6]170—171
五、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
邓小平在20 世纪80 年代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7]139在谈到中国过去的体制时,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18]77。所以邓小平主张中国要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以“苏联模式”为对象的,也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即“总体构想”。
邓小平讲的“苏联模式”与西方讲的“苏联模式”在含义上完全不同。我们严格区别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搞法”(即苏联模式)。中国反对苏联搞社会主义的那种做法(具体体制),但决不反对苏联搞社会主义本身,决不赞成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认为“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对于“具体体制”范围内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坚决、彻底、大胆地改;而对于“基本制度”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则是一再强调“坚持”,主张要“毫不动摇”的(这就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当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需要“改革完善”,但这与具体体制上的“推翻重来”,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绝不可能一次完成的。胡乔木1990 年谈到一百多年来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进步”时,曾相当概括和深刻地指出,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进步: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判断“由短变长”“由近变远”了;对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估计“由高变低”了;对“按劳分配”的认识由批它是“资产阶级法权”转到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再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等等。他认为,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还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而已。这些看起来是“倒退”的事情,其实是认识上的“进步”。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认识,更实事求是、更接近实际了,这对搞好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是必须的、有利的[19]665—666。
六、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但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非常响亮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非常科学又非常具体地回答了奋斗目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并付诸实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得人心不无关系。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言中强调:“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相互帮助不同国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3]336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433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也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与认同,进入了联合国、国际会议和一些国家政府的文件,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其实,从历史深层看,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们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巨大的全国联合体”。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
2013 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分六个时间段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讲话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紧密围绕“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苏联模式的历史性”“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 年’关系的辩证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等重大问题展开。讲话的“核心”是历史与现实结合,讲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从而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了我们拥护“两个确立”的信念,坚定了我们做到“两个维护”的决心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源于传统、扎根于传统,但已有别于传统、超越了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复兴中华的民族梦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相结合、相统一,这是伟大的创造。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2002 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出现的“六个社会阶层”。
② 参见胡振良、孟鑫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