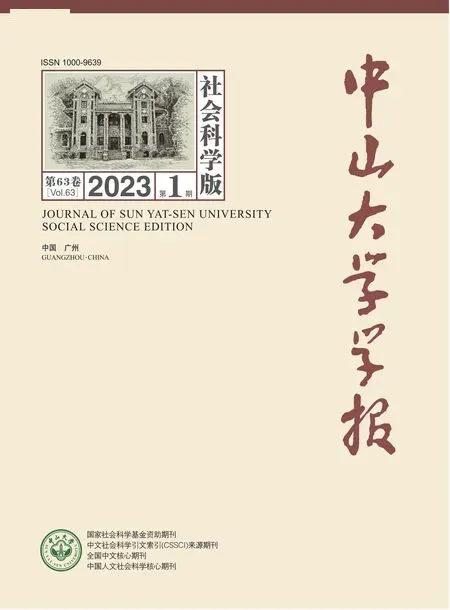静嘉堂本和国图本:两种完整传世的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的比较 *
2023-04-06景蜀慧
景蜀慧
《陈书》全书三十六卷,是唐初由宰相领衔官修的南北朝五史之一,记载了南朝陈王朝共三十三年的历史。笔者在近年主持点校本《陈书》修订工作中,对海內外现存的宋刊本《陈书》进行了深入的版本调查,在此基础上,对其中仅有的两种全本作了较详细比较,梳理了两者间的一些重要异同,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陈书》传世宋刊本简述
《陈书》成于唐初,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后因李延寿所著南北史删繁补阙,事增文省,更便于阅读,《陈书》与其他几部南北朝正史一样,不为当时学者所重,“世亦传之者少”①《曾巩集》卷十一《陈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5页。。一直到北宋嘉祐年间,朝廷始诏校雠,并加以镂板②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八朝史至宋始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宋本《陈书》,最早的刊本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浙刻本,又经过南宋中期补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宋版”。以下稍加简述:
北宋嘉祐六年(1061)八月,朝廷诏曾巩等负责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根据曾巩的《陈书目录序》,他所负责的《南齐》《梁》《陈》三书,在仁宗嘉祐八年(1063)完成校定①见《曾巩集》卷十一,第185页。,英宗治平年间送国子监镂版颁行。今存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南齐书》卷末,保留了崇文院治平二年(1065)六月开版牒文:“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同与管勾使臣选择楷书如法书写板样,依《唐书》例,逐旋封送杭州开板。治平二年六月 日。”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可以判断《陈书》在治平年间已刊刻成书,不仅“颁之学官”,并颁赐诸王②详论参见鲁明、胡珂:《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发微》,《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由于北宋国子监刊本雕成后主要“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复值靖康之乱,朝廷播越,颇多亡失。《郡斋读书志》卷五云:“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馀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此即所谓宋蜀大字本“眉山七史”。但北宋刊本南北七史今已无存,而南宋初之“眉山七史”,历代书目也均未见著录,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引用王国维、赵万里、长泽规矩也、潘美月、阿部隆一等学者的研究,主张旧称“眉山七史”之传本,实为南宋前期浙刊本⑤见[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五章《南宋刊南北朝七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之后在其版本基础上,南宋中后期又屡有补版递修。
南宋刊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未有重刊或覆刻,只在宋代书版基础上补版递修,明代仍之,直到嘉靖时期。故目前传世的宋本《陈书》,均为刻于南宋又经宋元明三朝递修的版本。《陈书》宋版经过元代到明初的几次补版,称为宋元递修本或宋元明初递修本;而最后经过明嘉靖前后的大规模补刊,尤其经过嘉靖年间补版的,称为“三朝本”。
因此,今所见宋刊《陈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递修到元代的版本,所保留的宋版叶比较多,尤其是还可见到一部分原刻版叶;第二类为递修到明初的版本,其特点是原刻版叶已基本无存,但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南宋中期补版叶和元补版叶,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在行款、字形等方面与宋元版有较大差异的明补版叶;第三类即是所谓“三朝本”,有大量的嘉靖年间补刊叶,也沿用了许多明初补版叶,所存留的宋代补版叶已经非常之少,北宋曾巩等校订《陈书》所保留在卷末的旧疏,也全部无存。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馀录》卷中说:“予案子固所谓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见,盖后来重刊失之矣。”四库馆臣孙人龙在《陈书》殿本后跋语也说:“今古本既不可见,国子监所存旧本舛讹殊甚,而巩等篇末所疏疑义,亦无一存者。”据此可见,清代学者能见到的《陈书》宋本,基本上只是三朝本。
比较而言,《陈书》的版本状况,在南北七史中是相当好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递修至明初为止的宋刊《陈书》,尚有六种,其中两种为全本,四种为残本。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现有两种,其中残宋本仅存十六叶,另一种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即再造善本之底本)为完整版本(《陈书》修订时简称“国图本”)。另外四种宋刻宋元递修本在海外,三种为残本,一种为全本,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此四种宋本均为当年张元济拼配百衲本的底本,其中包括在现存宋本中补版时间最早的“二十五卷本”(《陈书》修订时简称“宋甲本”)、存八卷本(《陈书》修订时简称“宋乙本壹”)、存五卷本(《陈书》修订时简称“宋乙本贰”)和另一种全本“静嘉堂本”。
静嘉堂本为宋刻宋元递修本《陈书》中唯一之完足本,尾崎康认为这一版本在南宋后期及元代经过多次补修,最后大规模补修在元中后期,印刷时间恐已入明代,但“仍有二叶原版叶别本皆无,仅存于此本中”①[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504页。。静嘉堂本之外的另一部宋刻足本便是国图本,考虑到静嘉堂本中尚存在若干空白版叶②按静嘉堂本存在若干空白叶问题,今所见所阙叶包括卷三第十三叶、卷十三第九、十两叶、卷十四第十叶、卷十八第五叶、卷三二第八叶、又卷三三第十叶等。这些空白叶版心页码与前后叶衔接,亦有每行之界栏,然而整叶空白无字。这些阙叶何时出现目前尚不可知。个人根据百衲本补版的情况猜测,有可能晚至中华学艺社借照之后。例如卷二第十三叶,各宋本皆无,静嘉堂本空白叶情况如前述;国图本和三朝本此叶不阙,上叶第六行第五字中书令之“令”皆讹为“合”,当为同版叶,百衲本此叶明显与三朝本有区别,“令”字不讹,其所据版叶疑仍为静嘉堂本。又卷十三第九、十两叶,各宋本皆无,静嘉堂本空白叶情况如前述;国图本和三朝本此二叶不阙,但版叶不尽同;百衲本此二叶明显与三朝本不同,但第十叶与国图本似为同版叶,疑其所据版叶仍应来自静嘉堂本。又卷十四第十叶,各宋本皆无,静嘉堂本空白叶情况如前述;国图本和三朝本当为同版叶,上叶第八行末字“归”均讹作“妇”,百衲本同此讹,疑此叶静嘉堂本若存情况亦同,百衲本所用版叶难以确定。其余各阙叶,因有其它宋本版叶存留,已为百衲本采用。的情况,甚或可以说,国图本可能是宋刻《陈书》最为完整传世的一个版本,但其递修的时间存在争议。此本版心无明代补版标识,因此198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均著录为“宋刻宋元递修本”。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以此本为底本,影印出版再造善本《陈书》三函十册,扉页记亦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影印”。但在此次《陈书》修订中,我们通过与《陈书》诸宋刻宋元修版叶详细比对,并结合所钤藏书印、版心刻工名等若干旁证,基本可以确定此本曾经明初国子监补刊,当定为“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相较于静嘉堂本以上宋元本,此本宋刻原版叶几乎完全无存③目前判断可能有一叶例外,分析见下文。,但南宋中期及元代补版叶尚存有相当数量,而其中的明初补刊版叶,则往往在行款字数、版心乃至字体字形上与宋元版有诸多不同。这些差异,为嘉靖时补版的三朝本所沿袭。
二、从藏书印看静嘉堂本和国图本的不同流传递藏途径
(一)静嘉堂本钤印情况
《皕宋楼藏书志》记云:“《陈书》三十六卷,宋刊宋印本,文衡山旧藏。”④见《皕宋楼藏书志》卷十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13页。《仪顾堂续跋》卷五云:“卷四、卷十四、卷二十二、卷三十六后有‘史西邨人’白文方印,‘子孙保之’白文方印,‘史鉴之印’白文方印,间有‘文征明印’白文方印。”⑤《宋椠宋印蜀大字本〈陈书〉跋》,《仪顾堂书目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7页。今检看静嘉堂本《陈书》,目录第一叶钤印两方,第一行末为一方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为长洲(今苏州)汪士钟藏书印(多数卷首行下端均钤此印);第二三行间下端钤“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白文方印,陆树声为陆心源第六子,此本曾为陆氏收藏,或陆树声经眼看过,故钤此印。卷三(纪三)篇末钤两方印,上一方为“朱氏井叔”阴文方印,下一方阳文方印漫漶不能辨识。第四卷篇末无字处钤三方印,由上至下分别为“西邨史人”⑥此印《仪顾堂续跋》卷五作“史西邨人”,按史鉴字明古,号西村,似作“史西邨”是,但此方印的排列方式,若横读则当为“西邨史人”,纵读则当为“西史邨人”,作“史西邨人”似有疑;又按篆书写法,“人”与“入”非常相似,此印末字“人”亦有可能为“入”。“ 子孙保之”“史鉴之章”,为明前期学者史鉴的藏书印。第五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第七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有“文征明印”阴文方印,之上有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应是文征明钤印在先,汪氏之印不得已钤于其上,遂压住此行“陈书七”三字的后二字。第九卷末叶第二行钤三印如第四卷末叶,在宋人旧疏前。第十卷、第十六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七卷、第三十四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第十九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有“文征明印”阴文方印;卷二十末叶倒第二行下端钤三方阴文印,由上至下分别为“西邨史人”“子孙保之”“史鉴之章”;第二十九卷末叶倒第二行下方钤四方阴文印,由上至下分别为“文征明印”“西邨史人”“子孙保之”“史鉴之章”;第三十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有“文征明印”阴文方印,之上有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亦应后钤,故压住此行“陈书三十”的后三个字。第三十四卷首叶第一行下端钤有白文长方印“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因为空白不够,压住了此行“陈书三十四”的末字;此卷末叶倒第二行钤有“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白文方印。第三十六卷末叶倒第二行钤三方阴文印,分别为“西邨史人”“子孙保之”“史鉴之章”。
(二)国图本钤印情况
观国图本所钤藏书印,目录第一叶第一至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九叠篆朱文大长方印①按同事刘勇教授指出:“按照当时的制度,‘礼部官书’不是印,而是“条记”。所谓‘长印’ ‘大印’,是后人的误解:‘长’ ‘大’,都是对其外形的描述,‘印’则是对制度的误解。当时称‘条记’,‘条’是对其外形之‘长’的描述,是相对于各品级的官印外形之‘方’而言的,‘记’则是对其对应的‘不入流’的本质的描述,是相对于品官之‘印’而言的。”,第四、五行下端钤有两方印,其上为“慧海楼藏书印”白文方印,其下为“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方印,第六行下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文篆体方印。此外此本钤印处,还有纪第一(卷一)末叶第二、三、四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纪第二(卷二)首叶第一、二行上端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方印,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纪第三(卷三)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纪第五(卷五)首叶第一、二行上端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方印,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纪第六(卷六)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一(卷七)首叶第一、二行上端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方印,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六(卷十二)首叶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第四、五行下端钤二印,其上为“季振宜印”朱文方印,其下为“沧苇”白文方印;列传第十(卷十六)末叶上半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十一(卷十七)首叶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第四、五行下端钤二印,其上为“季振宜印”朱文方印,其下为“沧苇”白文方印;列传第十五(卷二十一)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十六(卷二十二)首叶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第四、五行下端钤二印,其上为“季振宜印”朱文方印,其下为“沧苇”白文方印;列传第二十(卷二十六)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二十一(卷二十七)首叶第一、二行上端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方印,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二十三(卷二十九)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二十四(卷三十)首叶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第四、五行下端钤二印,其上为“季振宜印”朱文方印,其下为“沧苇”白文方印;列传第二十七(卷三十三)末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列传第二十八(卷三十四)首叶第一、二、三行下端钤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第四、五、六行下半部钤三印,上为“藏史之章”白文方印,中为“季振宜印”朱文方印,其印章尺寸大于之前各卷之“季振宜印”,字体亦不同,下为“沧苇”朱文大方印,有一半钤于界栏之外;列传第三十(卷三十六)末叶上半叶倒第三、二、一行下端,有“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下半叶第四、五、六行钤三印,上为“藏史之章”白文方印,中为“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下为“沧苇”朱文大方印,末行下方钤朱文小方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与目录第一叶所钤同。
(三)二本递藏线索
从书中所钤藏书印,静嘉堂本和国图本这两种宋本从明代以来的递藏线索依稀可见。
静嘉堂本:虽然《皕宋楼藏书志》号称“文衡山旧藏”,但最早收藏静嘉堂本的应非文征明而是明初吴江西溪人史鉴②《宋椠宋印蜀大字本〈陈书〉跋》,《仪顾堂书目跋汇编》,第327页。。《仪顾堂续跋》卷五云:“史鉴,字明古,吴江人,号西邨,隐居不仕,藏书画甚富,著有《西邨集》。”又据吴滔教授研究,史鉴生于宣德九年(1434),卒于弘治九年(1496),享年六十二岁。号“学有师承,识通世务”,著有《礼纂》《礼疑》《西村集》等书,“发贤儒之所未有”。《吴中人物志》载其“尤好藏三代秦汉器物,唐宋书画”,为吴中地区有名的隐士,与同时代的沈周等号“江南四大布衣”,又与曾为礼部尚书的吴宽相友四十年,其去世后吴宽为其撰写墓表①以上详参吴滔:《明代永充粮长与嫡长子继承——基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4期,又氏著《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文征明生于1470年,史鉴去世时文征明二十六岁,历史上黄溪史氏家族与长洲文征明交往颇多,或由此因缘,这部《陈书》后为文征明所藏。明后期到清前期流传情况不详,卷三末所钤“朱氏井叔”印,未谙其为何人。不过根据印章可以大致判断,此本从明代前期,即在江南苏州一带流传,其收藏基本不出其域。其后可以明确的是,清中叶此书为长洲富商汪士钟艺芸书舍所藏,而汪氏藏书,一部分或来自吴县人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有记载说黄氏晚年,其所收藏的宋元旧刻,分别为杨以增和汪士钟所得,不知其中是否有此书。汪氏卒年不详,太平天国之乱后,艺芸书舍藏书流出,此书遂为陆心源收入皕宋楼,故有“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陆心源死后,皕宋楼宋元版书为其子出售,最后流入日本静嘉堂。
国图本:和静嘉堂本相比,国图本的流传递藏过程有较多不解之迷。从钤印所见,国图本流传情况似乎并不复杂,最先应为明代内阁所藏。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云:“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馀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礼部官书”之印,在南北七史传世善本如《宋书》《南齐书》《梁书》③清丁丙辑:《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梁书》五十六卷宋刊明修本”条云“汪士经藏宋刻《梁书》,不避南宋诸讳,每册有礼部官印,版式极宽大,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5页。《魏书》等宋刻宋元修本中亦有见,按傅增湘、尾崎康等学者研究,此印乃明初所钤,疑明初国子监有补修七史书版之举,而南监修版后,礼部或遣人专印,用纸独佳,得新印本后钤藏④详参[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511页。。今按《明史》卷一三八《薛祥列传附赵俊列传》载,洪武中“帝以国子监所藏书板,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可知明洪武时,国子监确有古籍补版之事。据《赵俊传》,赵俊先为工部侍郎,在洪武十二年后任工部尚书,十七年免职,其奉诏监理古籍补版大致应在此期间,与《南廱志》卷一《事纪》一所载洪武十五年冬十一月“上命礼部官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时间相合。传中“帝以国子监所藏书板,岁久残剥”诸语,也正出自当时上谕“今国子监所藏旧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⑤(明)黄佐:《南廱志》卷一《事纪》一,民国景明嘉靖二十三年刻增修本。。又《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一○章《明南北国子监二十一史(附)》中引《南廱志》卷一八《经籍考》下云:“自后,四方多以书板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钦依修补。然板既丛乱,每为刷印匠窃去,刻他书以取利,故旋补旋亡。”⑥(明)黄佐:《南廱志》卷十八《经籍考》,并参[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169页。《明史》附录三王茀卿《明史考证捃逸》按云:“永乐二年,肃王楧奏求书籍药材,诏答曰:所求书有者,悉送去,惟十七史诸书俟印装,续送……见《明实录》。”此条记载云“十七史诸书俟印装”,或可以佐证明初之史籍补版因这类原因颇为延宕,持续时间甚久,至永乐初尚未完成重新印装。而明代颁赐诸王,例由礼部,所赐书籍经礼部过手,或即钤礼部官印。另《明史》卷六《成祖纪》二载永乐四年“夏四月己卯,遣使购遗书”。此事原委《明史》卷九六《艺文志》一所记较详,云:“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馀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清代官修《天禄琳琅书目》卷二云明成祖“尝命礼部尚书郑赐,择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遗而汇于一,且奉使者复命必纳书于库。缥缃之富,古未有也。郑赐当时官礼部,董其事,或所采之书,钤以礼部官印”。清以后诸家书目所著录的经史子集宋元善本,往往可见钤有“礼部官书”朱文长印者,可见明代礼部所过手善本甚多。同事刘勇教授专治明代学术史,他的推测是:“永乐四年命礼部尚书郑赐采集书籍时,优先就采集到包括南监在内的朝廷各机构的书,其中很自然地就有近二十年前修版印刷的《宋书》等书(成书或者是新刷印),礼部拿到后钤上‘礼部官书’。”
明中后期,内阁所藏善本大量散失,沈德符云当时内阁藏书皆“置高阁,饱蠹鱼”,“自弘、正以后,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特别是嘉靖以来,皇帝一心道教,不事朝讲,托以“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馀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将内阁图籍的收采藏贮及讲读诸事皆罢去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其后数十年,内府藏书“其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其散出的善本,有若干部为藏书家季振宜所得,今所见钤“礼部官书”印的《宋书》《魏书》等亦钤季振宜藏书印,此本亦有“季振宜印” “沧苇” “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诸印。清康熙十三年(1674)季振宜去世,其藏书流散,据学者研究,其后二十馀年间,所藏书已全部散去③吴永胜:《季振宜藏书考》,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散出的季氏藏书大致四个流向,即徐乾学、怡亲王府、内府及其他私人收藏④吴永胜:《季振宜藏书考》,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进入怡府和内府的善本近代以前一般很少有再流出,而此本则有可能进入了其他的私人收藏之手,目前唯一的一条线索是目录第一叶所钤的“慧海楼藏书印”,为季振宜藏书印后唯一之私人藏书印,藏书印主人为原籍山东海丰的查莹,按《清秘述闻》,查莹字韫辉,山东海丰人(当为浙江海宁人),乾隆丙戌(1766)进士,年辈晚于季振宜约百年。查氏从查莹祖父查昇(1650—1707)始就藏书甚富,《浙江通志·两浙輶轩录》载,查昇字声山,海宁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擢谕德侍读,晋少詹,兼侍读学士。负诗文盛名,尤工书法,圣祖屡称赏之。片楮只字,人皆宝贵”。乾隆三十七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征集民间藏书,查氏进书数种,可见其藏书颇有质量。可推测,在季振宜去世后,此本进入查氏之收藏。但从查莹慧海楼之后,此本基本湮没无闻,何时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不得而知。
从所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之印或可推测此本进入馆藏的大致时间。按为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最早名“京师图书馆”,1928年7月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1月启用“国立北平图书馆”关防⑤参见李镇铭:《京师图书馆述略》,《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4期。。到1949年6月27日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故今国家图书馆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时间,大体是从1928年7月到1949年6月期间。但日人桥川时雄、仓石武四郎大约1929年编拍的《旧京书影》中并未提到这一版本。1933年赵万里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也未曾著录此本《陈书》,似乎显示此本尚未入藏。张元济20世纪20年代拟影印旧本正史,遍觅善本。1927年致傅增湘信中曾提到影印《梁书》《陈书》“用北京图书馆残宋本。以三朝本补”⑥《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7,180页。。张元济对补配的三朝邋遢本质量很不满意,1927年11月19日信中说:“南北七史除南齐借自尊处,北周有涵芬楼所藏,尚称完善。其馀五史已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尽数照出,然所缺尚多。以三朝本补配,甚不满意,不知尚有别觅残宋元刊补入。”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7,180页。虽然如此,对补版时间早于三朝本且品相尚佳的此本,却完全不见有所采用。百衲本《陈书》号称是用二十一卷本(即今“二十五卷本”)与静嘉堂本拼配,但细为核校,可见到其中有少数版叶仍用三朝本而未采此本,其跋云宋本《陈书》“旧藏北平图书馆,存者仅二十一卷”。可知张元济当年应未曾见到此本。同一时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记《陈书》亦仅有一种,即“明史明古藏书”,亦即后为皕宋楼所藏,当时已入静嘉堂文库的静嘉堂本《陈书》。他在《藏园群书题记·校宋刊本〈陈书〉跋》中提到其校宋刊《陈书》,其所校宋本乃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宋刻元修本二十一卷,与之对校的版本乃馆藏殿本,亦完全不及此本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至尾崎康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其中列举的今所见宋版《陈书》,南宋前期浙刊并经宋元两代递修的版本共五种,但并无此本在内;其后又列宋刻宋元明“至嘉靖递修本”,其中包括了今国图所藏的三种,即十二册(张元济校)、八册两种全本和二册(存十卷,傅增湘校)的一种残本,此本也不在其内。傅增湘为赵万里1933年所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所作序中,尝提到该馆草创之时,充架者惟内阁大库旧藏,其中宋元秘籍仅数百种而已。经多年搜求,至编定此善本书目时,“综计先后所得,合以旧储,审定入善本库者,为书凡三千七百九十有六部,以卷计者,八千一百九十有九,而乙库所藏善本尚不与焉”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序》,第1079页。。从此叙述看,此善本目录所著录的版本,并不包括乙库之善本。但笔者推测,此本尚存于乙库,未为人知的可能性较小,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尚未入藏,故未编入目录。
此本在1987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1997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有著录,但由于其版心无明代补版标识,所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将此本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以此本为底本,影印出版再造善本《陈书》三函十册,牌记亦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影印”。在版心无明代补版标识方面,此本的情况与原由傅增湘所收藏的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南齐书》相当类同。后者亦因此故,最初曾导致傅增湘、缪荃孙、杨守敬、章钰等前辈学者判断其为宋刻元修本甚至“宋蜀大字本”,认为“绝无明补”。但赵万里、尾崎康等学者则根据对版心刻工名的研究,判断此本不仅“于元代经二次以上补修,又经明初补修”, 书中若干刻工名如毛原敬、李五、叶禾等,其名又见于明初版南北史等③[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497页。。这一判断后为版本学者普遍接受。而《陈书》此本因为诸前辈学者所未曾见,故对其版叶的实际情况并无分析,但经过与《陈书》诸宋刻元修之版本或版叶作详细比对,加上一些旁证,我们确定《陈书》国图本“宋刻宋元递修”这一年代认定同样可能有误。仅从此本与傅藏本《南齐书》在字体、版心、刻工上的简单比对,即可见两者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刻工,《南齐书》版心所见的明初补版刻工,有一些也出现在这部《陈书》的版心刻工之中,如刻工“李五”,《南齐书》卷十二第十七叶有此刻工名;《陈书》卷一第二十五叶版心亦为“李五”;又刻工“叶禾”,《南齐书》卷十六第十五叶、卷十八第十六叶有此刻工名,《陈书》卷六第十三、十四叶刻工亦为“叶禾”④按李五、叶禾为元末明初刻工,此说参考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三部《解题编》七《南齐书》。他认为原傅增湘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南齐书》“于元代经二次以上补修,又经明初补修。书中毛原敬、朱宗甫、江子名、李五、周受、张名远、陈士通、黄子崇、叶禾、罗恕等所刻叶有二十多叶,而此十名皆见明初版南北史等”。见其书第497页。在其书中所列元代补版刻工表中,又以星号说明李五等为参与元末明初补版之刻工。见第113—114页。。另一理由当然也和书中所钤“礼部官书”印有关,如前文所提及,此印在南北七史传世善本如《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中亦有见,乃明初所钤。
而更重要的证据,则来自此本的版叶与传世的诸宋刻宋元修本的差异。若将国图本与基本完整传世的静嘉堂本作一详细比对,两本间的差异和国图本明补的情况可能看得更为清楚。
三、静嘉堂本与国图本的版叶对比
(一)原刻版叶
笔者调查《陈书》各宋本,根据粗略统计,保留有明确刻工名的原刻版叶共九十七叶,刻工名脱或漫漶不清,但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原版叶的还有数十叶(尾崎康认为存世宋刻本《陈书》所存原版叶约一百四十馀叶)①因为手头现有的版本,除百衲本、国图本、残宋本能够完整呈现版心部分,其余各宋本都只能部分看到甚至完全看不到版心,相当一部分只能从版叶的字形、版心格式、避讳等条件判断其时代。。此一百馀叶原版叶,大部分存于宋甲本(存二十五卷)、宋乙本(两种,存八卷和存五卷)。静嘉堂本所保留原刻宋版叶,有刻工名者二十一叶,脱刻工名但可判断为原版叶者尚有若干叶,如卷三六之第七、第八叶等(按尾崎康之统计认为存世宋刻本《陈书》原版叶静嘉堂本仅存二十一叶)。其中,有三叶原刻版叶在其它宋本中已经不存,只有静嘉堂本存留(按尾崎康认为仅见于静嘉堂本的原版叶有二叶,谓“有二叶原版叶别本皆无,仅存于此本中”)②见[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504页。,分别为卷十二第十叶,刻工朱言、卷十六第四叶,刻工陈立、卷二三第七叶,刻工王太;另外还有八叶是其它宋本(主要为宋甲本)脱去刻工名,因此百衲本亦无刻工名,但静嘉堂本未脱,分别为卷二九第十叶,刻工朱言、卷三十第十二叶,刻工史忠、卷三十第十三叶,刻工朱言、卷三十第十四叶,刻工朱言、卷三十第十五叶,刻工田芽、卷三十第十六叶,刻工田芽、卷三五第七叶,刻工田水、卷三五第八叶,刻工田水。
至于国图本,原刻版叶基本无存,但可能有一叶为例外,即卷三六的第九叶。按传世的《陈书》宋本中,只有三种保存了第三十六卷,即宋甲本、静嘉堂本和国图本。第三十六卷为《陈书》最末卷,第九叶为该卷最末叶,无正文,仅上半叶第二至三行刊有宋人旧疏一条。静嘉堂本该叶已脱去,前人见到唯一保留此叶的是宋甲本,傅增湘并从此叶录得宋人疏语一条③当年傅增湘曾在北平图书馆旧藏宋本《陈书》残卷中见到此叶,并从中录出宋人疏语于《藏园群书题记》中,见《藏园群书题记》,第89页。。其上半叶第七行下端钤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下半叶为空白;其版心有残损,刻工名脱,但叶码“九”字尚可见。从版式字形判断,此叶当为原版叶,当年《旧京书影》摄有此叶图版,其说明云“宋刻残本”。后来百衲本此叶即取自宋甲本,故版心亦无刻工名。而令人意外的是,国图本不仅保存了此叶,且版叶较完好。上半叶宋人疏语具在,其末三行下端钤“礼部官书”朱文长方印;下半叶则钤有“藏史之章”“季振宜印”和“沧苇”三方藏书印,其末行下端又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文小方印;版心则同宋甲本,有页码无刻工名。大致可以判断,国图本此叶与宋甲本同为原版叶,而品相则国图本似更胜宋甲本。值得注意的是,宋甲本和国图本此叶,分别钤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印,应是提示了此二本入藏的不同时间和其它一些线索。总之,此叶很可能为国图本所存唯一之原版叶,可惜诸前贤当日均未见到,尾崎康也未加留意。
综上,静嘉堂本有原版叶二十馀叶,国图本有原版叶一叶,即是说,与《陈书》所存这一百多叶原刻版叶相对应,静嘉堂本有将近八十叶与之不同,而国图本除一叶外,基本上全部相异。两个版本这一部分版叶的异同如何呢?大略而言,两个版本与原版叶对应的版叶,基本上未见有南宋补版叶;静嘉堂本这八十多叶中,经鉴别比对,大约六十馀叶可以明确为元补版叶,有十馀叶为刻工名脱失或字迹不清;而国图本百馀叶异于原刻的版叶,可确定为元补的约五十馀叶,馀下版叶,大多版心格式潦草,无刻工名,可以判断为明初甚至更晚的补版。至于静嘉堂本和国图本这部分版叶异同如何,亦可加以留意。统计下来,两个版本版叶相同而均为元补版叶的大约有五十叶,另怀疑同为元末明初补版叶的有二叶,其中比较特殊的一叶是卷二八的第十二叶,静嘉堂本与国图本虽均为元补,但静嘉堂本刻工为周鼎,而国图本刻工为王文;馀下相异部分,静嘉堂本除去同原版叶者,还有大约十三叶为元补版叶;而国图本另有六叶为元补版叶,其馀基本上都为明补版叶,这些明补版叶,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版心无刻工名,格式潦草,字形松散单弱粗劣,每行字数不均,不少行款与宋元版叶有明显出入甚至相当大的差异,而且版叶常为三朝本所沿用。
以下试举几例:
如卷七第五叶,原版刻工杨和,静嘉堂本刻工章亚明,为元代早期补版;国图本无刻工名,行款与宋元版叶不同,宋元版叶每行均为十八字,国图本上半叶第四行为十七字,第六行为十九字,第九行又为十七字,故下半叶宋元版叶的每行末字,在国图本均为次行首字,至第七行为十九字,其后二行始与宋元版叶同。需要注意的是,三朝本此叶字形、行款和版心格式与国图本完全相同,但版心上端有“嘉靖八年补刊”字样,版叶字体的散乱粗劣更甚于国图本①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国图本用了三朝本,但个人倾向于判断更有可能是三朝本袭用了明初的补版,只在版心加镌了补刊的年号时间。。
同卷第七叶情况亦类同,原版叶刻工王能,静嘉堂本刻工王全,为元补版,国图本则无刻工名,字体行款都与宋元版叶不同,上半叶第四行,宋元版叶为十七字,以下各行为十八字,国图本第四行为十八字,第五行十九字,第六行十七字,上半叶末比宋元版叶多一字;下半叶宋元版叶第一行、第六行为十七字,第七行为十九字;而国图本第一行、第二行、第五行、第六行、第七行均十七字,第八行为二十字。同样,三朝本此叶版心格式、字形、行款均与国图本同,唯版心上端有“嘉靖八年补刊”字样。
再如卷九第十七叶,原版刻工田力,静嘉堂本为王㒷(即“興”字),元代补版,下半叶保留有宋人旧疏两条。国图本版心无刻工名,宋元版叶版心的“陈书传三”改为“陈书列传三”,上半叶第八行第三字宋元版叶之“淪”字刻作“”,当为明初补,两条疏语仍保留。三朝本沿用此叶,字形版心和讹字一如明初版叶,卷末疏语则已全部脱去。
又如卷十九第十五、十六叶,原刻版叶刻工朱言,静嘉堂本同为原版叶,国图本无刻工名,行款与原版叶颇有差异;同卷第十七叶,原刻版叶刻工王利和,静嘉堂本亦为原版叶,国图本无刻工名,行款亦与原版叶不同;国图本这三叶的行款、基本字形和版心格式,均为三朝本不加改动沿用,唯第十七叶版心上端三朝本镌有“嘉靖八年补版”字样。
最为典型的是第三十卷,从第十一叶至第十六叶卷末,静嘉堂本皆为原刻版叶,刻工分别为史忠(十一、十二叶)、朱言(十三、十四叶)、田芽(十五、十六叶),国图本相应版叶为明补,均无刻工名,从第十一叶下叶第一行开始,每行字数即有异于宋版叶。如第十六叶上叶末行,宋版叶为“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而国图本为“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宋版叶为十八字而国图本十七字,宋版叶“埸”国图本讹作“場”,且其字数出入有六字之多。其后三朝本的这部分版叶,虽有些叶为重刻,字形不完全同于国图本,但行款及上述讹误之文字,则完全与国图本同,沿袭的痕迹十分清晰。
(二)南宋补版叶
《陈书》所保存的南宋中期补版叶,笔者统计,可以根据刻工名完全确认的,共一百六十二叶,分别存留在二十六卷中,此外尚有若干刻工名脱或漫漶不清的版叶。在可以确认的南宋补版叶中,静嘉堂本有一百五十四叶,国图本有一百二十七叶,其中两个版本版叶完全相同者,有一百一十七叶。百衲本根据几种宋刊本所采用的南宋补版叶,静嘉堂本中大部分都有保存,还有一些南宋补版叶,百衲本所采用的版叶,其版心刻工名或残或脱,但静嘉堂本或国图本则保留完好。如卷十三第三叶,刻工刘昭,百衲本因所据静嘉堂本脱“刘”字,只作“昭”,国图本则刻工名完整;又如卷三十第二叶,刻工徐经,百衲本可能因为所据宋甲本脱刻工名,版心亦无刻工名,静嘉堂本和国图本则刻工名完整。卷三一第四叶和第八叶,存世的三种宋本即宋甲本、静嘉堂本和国图本,版心皆分别可见刻工朱梓和蔡邠之名,百衲本这两叶与这三种宋本的版叶相同,但未知何故,版心刻工名都脱去。卷三三的第九叶、第十三叶,也是类似情况。
国图本虽然保存的南宋补版叶比较多,但比静嘉堂本,还是少了近三十叶。通过比对,国图本这一部分异于静嘉堂本的版叶,大致呈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无刻工名或刻工名不相同但实际为同版叶,属刻工名残损或脱去。如卷二第八叶,静嘉堂本刻工为徐高,国图本无刻工,但识之与静嘉堂本为同版叶,版心格式亦同,可以判断是脱名。又卷十三第六叶,静嘉堂本刻工为宋琳,国图本作宋林,实为同一版叶,国图本“林”字笔划缺失。国图本这一部分版叶,仍然可以确定仍为南宋补版叶。
其二是有刻工名,分两种情况,一为可明确为元补版,如卷五第十二叶,静嘉堂本刻工为高寅,南宋补版,国图本刻工名徐爱山,按元代杭州刻工有徐艾山①见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徐艾山有时亦署徐爱山②参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5页。,当为大德前后补版。二为其名不在元代刻工名单内,亦有署为单字,不似人名者,且版心亦见差异。如卷一第三叶,静嘉堂本刻工为陆春,南宋补版,版心单鱼尾,国图本为雇,双鱼尾;同卷第九叶,静嘉堂本刻工为刘文,南宋补版,版心单鱼尾,国图本仍为雇,双鱼尾;同卷第二一叶,静嘉堂本刻工为沈仁本,南宋补版,版心单鱼尾,国图本仍为雇,双鱼尾;卷三第六叶,静嘉堂本刻工为杨昌,南宋补版,版心单鱼尾,国图本仍为雇,双鱼尾。按元代刻工有称雇恭者,无雇。明洪武三年刊《元史》亦见雇恭其名③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142页。,此雇或为元末明初补版刻工。国图本的此三叶,后来的三朝本版叶与之基本相同,但除了版心格式和个别字形有修改之外,三朝本还有一些重要的改动。如卷一第三叶上半叶第四行首字,国图本沿用宋本,为“换”,但三朝本改为“涣”,并为南监本以下明清版本所沿用④按原校记认为二字“音同而义亦相近”,但实际上换字匣母而涣字晓母,二字韵同而声、义本不同。;又如卷三第六叶,下半叶第三行倒第六字,国图本刻作“恉”,显讹,三朝本改订作“”,亦为南监本以下沿用,而此叶之版心上端,三朝本有“嘉靖九年刊”字样,似表明此叶为新刊,而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疑三朝本其实是利用明初补版叶,在其基础上,对其版叶的某些字有所校订和挖改。
其三是无刻工名,且仔细辨识非同一版叶,这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为元补版叶,刻工名脱失;二为明补叶,本来即不留刻工名。第二种情况较为多见,细观国图本全帙,多数无刻工名的版叶,皆为明补叶。如卷一第三四叶;卷二之第一叶、第六叶;卷三之第九叶、第十叶;卷四之第五叶、第六叶、第八叶;卷五之第二叶、第六叶等等。这些明补版叶的基本特点是字形较窳劣,间有脱误和改字,与宋元版叶差异明显。如卷三第九叶,静嘉堂本下半叶第一行末字和第二行首字避唐讳作“景辰”,国图本改作“丙辰”,这一改动后为三朝本沿用,但三朝本进一步变动了行款,将此二字都纳入第一行。又如卷四之第六叶,静嘉堂本上半叶第七行末字和第八行首字分别为“弗”“隔”,“弗隔”文义自通,国图本第七行末字讹作“卯”,第八行首字脱,其后三朝本或因“卯”字在此文义难通,其下字又有脱,遂将“卯”字断为“丱”字,下又补“角”字,宋本之“弗隔”一变为三朝本之“丱角”,因其义尚勉强可通,遂为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所沿用;此叶第八行第八、九字静嘉堂本为“衣车”,后人或不明“衣车”之义,故国图本改作“依车”,也为三朝本及以后之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所沿用。又如卷四之第八叶,整叶字形极为粗陋,其程度甚至于超过其后之三朝本。
其四是明确有明初刻工名,字形与宋元版叶异,甚至行款也有不同。如卷一第二五叶,刻工李五,此刻工名又见于《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史籍元末明初补版中①参[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113—114页。,当可定为明初补版。存有此叶的宋本只有静嘉堂本,百衲本此叶亦来自静嘉堂本,静嘉堂本版心刻工名脱去,但保留有南宋补版叶的单鱼尾格式,下半叶第三行倒数第二字“匡”字百衲本阙末笔,静嘉堂本此字末笔有较明显描补痕迹,当为藏者所为。从字形与避宋讳的情况,大体可判断此叶可能是南宋补版叶。国图本此叶不仅刻工为明初刻工,更重要的是行款与静嘉堂本不同,静嘉堂本上半叶第七行为十七字,国图本为十八字,而在此之下每一行,国图本的末字,都为静嘉堂本次行的首字,直到此叶下半叶的第九行,静嘉堂本为十八字而国图本十七字,这种情况才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三朝本此叶字形与国图本相同,行款也完全沿用国图本,只是三朝本版心上端,有“嘉靖九年刊”字样,下端则无刻工名。初步判断,这种情形,也应是三朝本袭用国图本明初补版,但在版心去掉刻工名而加上了“嘉靖九年刊”的标识。
四、国图本与三朝本之关系
在以上的分析比对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乃至明确发现国图本与三朝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最近,上海图书馆郭立暄教授做了详细的版本比对,发现此本中至少有十四叶与三朝本为同版叶,而且在三朝本中标有“嘉靖八年补刊”字样,包括卷七第五叶、第七叶、卷八第七叶、卷九第五叶、第六叶、卷一一第十叶、第十一叶、卷一九第十七叶、卷二一第五叶、第十五叶、卷二二第三叶、卷二六第四叶、卷二八第四叶、第五叶,其证据十分确凿。比如上文中已经述及的卷七第五叶和第七叶,这两叶三朝本和国图本一样,无刻工名,字形、行款和版心格式有异于宋元版叶,但三朝本版心上端加有“嘉靖八年补刊”字样,且版叶字体的散乱粗劣往往更甚于国图本。
而根据笔者调查,有这种情况的版叶可能还不止于此,像上文中提到的卷三第六叶、卷一第二十五叶,版叶情况亦与之相类似。又如卷一第八叶,静嘉堂本刻工疑为“嚴忠”(“忠”上面的字形为,暂难辨识,初步判断类似于“嚴”字之行草书体“”),若是,当为宋刻;国图本无刻工名,字体较为纤细,下半叶行款不同于静嘉堂本,第四行静嘉堂本为十七字,国图本十八字,第六行静嘉堂本十八字,国图本十七字。而三朝本此叶字体行款与国图本完全相同,明显版叶相同,但版心上端有“嘉靖八年补刊”字样。同卷第二十六叶,静嘉堂本刻工名脱,版心单鱼尾,避宋讳,疑南宋补版;国图本版叶版心为同向双鱼尾,三朝本版叶与之完全相同,但版心改为单鱼尾,上端有“嘉靖九年刊”字样。
以上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到,与国图本同版叶的三朝本,在版心上端加“补刊”字样有两种情况,一作“嘉靖八年补刊”,一作“嘉靖九年刊”,这种区别除了反映不同的补版时间外,还有没有其它寓意,或可进一步探究。除此之外,三朝本沿用国图本,还常见修改版心格式的情况,如第一卷第十三叶,静嘉堂本刻工名脱,版心为单鱼尾,疑似南宋补版叶,国图本版心双鱼尾,无刻工名,文字较之静嘉堂本颇有差异,上叶第一行首四字,静嘉堂本作“单舸走”,国图本作“車舸脱走”,“单”讹作“車”,“脱”字字形不同;第九行末字静嘉堂本作“仗”,国图本作“”,笔划多一点;下半叶第七行倒第五和倒第四字静嘉堂本分别作“轨”和“库”,国图本刻作“”和“”;第八行首字静嘉堂本作“尧”,国图本作“”,其余笔划出入还有不少,显非同版叶。三朝本这一叶讹字和笔划特征与国图本完全相同,应是袭用明初补版,但版心则作了修改,由原来的双鱼尾改成单鱼尾。该卷第二七、二八叶也同样存在这一情况,此二叶静嘉堂本脱刻工名,版心单鱼尾,避宋讳,疑为南宋补版叶;国图本版心双鱼尾,刻工“雇”;三朝本此二叶版叶与国图本同,但版心改为单鱼尾,刻工名的痕迹也刊去。又卷二第四叶,静嘉堂本刻工名脱,版心单鱼尾,但未避宋讳,疑元补。国图本此叶字形行款皆与静嘉堂本出入,上半叶第一行静嘉堂本十八字,国图本十七字,之后静嘉堂本每一行之末字,都为国图本次行的首字,一直到下半叶最末行国图本为十九字,二本才归于一致。至于三朝本此叶,除了更为粗糙,字形和行款也与国图本完全一致,但版心将国图本的双鱼尾改为单鱼尾。
关于国图本和三朝本同版叶的情况,还可以再作一些更详细的观察。总体而言,在将国图本和三朝本进行比对时,类似例证可以发现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悉数枚举。至于三朝本较普遍存在采用明初补版叶的情况,或许说明在嘉靖年间补版时,《陈书》三朝本所依托的版本可能并非一般所理解的宋元旧版,而是经明初补刊过的这一版本,其所沿用的,也不仅仅是其中的明初补版叶,还包括了这个版本所保存的宋元版叶。所以在三朝本中还可以发现的一种情况,即三朝本中某些加有“补刊”标识的版叶,甚至基本上就是宋元补版叶①三朝本的类似情况在其他正史中也有出现,皖西学院图书馆舒和新即发现该馆所藏的一部《三国志》三朝本(宋衢州刊本,元明递修)的卷十四尾叶刊有“右修职郎衢州录事参军蔡宙校正兼监镂版”“左迪功郎衢州州学教授陆俊民校正”两行文字,但版心仍刻有“嘉靖九年刊”字样。详见舒和新:《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目前笔者对三朝本补版问题暂时尚无更深入研究,仅仅根据一些已观察到的现象推测,三朝本《陈书》之所以呈现如此特点,可能和这一版本补版时所据的宋元版《陈书》版本状况有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图本这部有明初补版的宋本《陈书》,最早收藏于秘阁,在其后的辗转递藏中也保存良好,所以版叶残损的情况并不严重。而设想流传到民间的同一版本,经反复传刻,到嘉靖补版前,许多版叶的残损漫漶状态恐怕远远超过今之“国图本”。因此,三朝本的补刊,是在一个我们未知的基础上,所补的版叶,虽然今存之于国图本中的尚称完好,但当时补版者所见到的,则可能十分残破,需依样重刊。而三朝本之补刊,也未必整版重刊,仅补改版心或局部挖改的情况亦颇多见。有学者怀疑国图本与三朝本相同的版叶是前者袭用了后者,认为这些版叶实际上为明嘉靖年间补版叶,但笔者则倾向于判断此种情况更有可能是三朝本因种种原因(包括上文之推测)袭用了明初补版,并加上了嘉靖八年或九年补刊之标识。值得指出的是,三朝本在沿用明初补版叶时,不仅对部分版心标记和叶中个别字行做了挖补移动增改等处理,也对原来的明初补版甚至于宋元版叶中某些显而易见的讹字有所订正,这些订正,为其后的南北监本、汲本及清代的殿本所接受并得到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