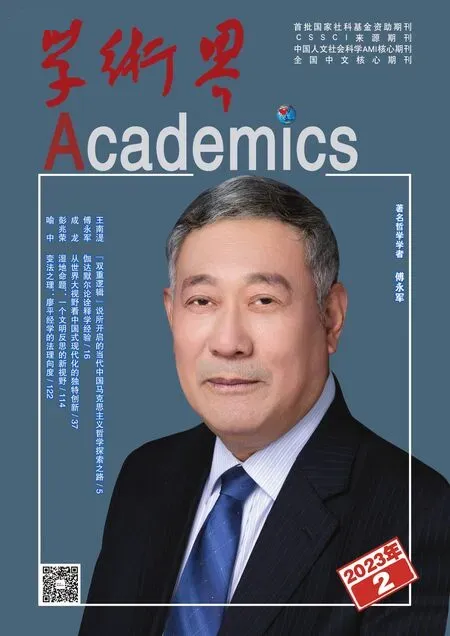桐城派之义法与佛教
2023-04-05程维
程 维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2)
桐城派以程朱理学立家,于义理上力求清真。文法上又尚“雅洁”,不喜佛氏语、语录语。方苞《答程夔州书》云:“凡为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则如涕唾之令人彀矣。岂惟佛说,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也。”〔1〕可能是因为这两点原因,我们总惯性地将佛教思想排除在桐城派学术之外。
然而,桐城有着悠久的佛教传统和持续浓厚的佛教氛围。唐大同禅师于此建投子寺,宋碧岩禅师建大宁寺,明清时期更是寺庙林立,如华严寺、大宁寺、龙门寺、梅城寺、谷林寺、梵天城、净士莲社、慈云庵、棠梨树庵、太平庵、法龙庵,均香火旺盛。又据省宗教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桐城县域内佛教寺庵数与僧尼数,在安徽全省各县中居首。高僧大德亦辈出,唐代有投子山大同、师会,宋有浮山法远、善悟、清觉、景祥,投子山道宣、证悟禅师,明有浮山宗繁、本智、郎目,投子山绍琦等等。域内享名的居士有李公麟、吴用先、余大成、马其昶、房秩伍、马冀平、李光炯、魏曙东等。若放大到整个安庆地区,佛教氛围更是醒目,据光绪四年《安徽通志》所载,安庆府于宋代建寺54座,元代建寺10座,清代建寺119座,在各州郡中一直居首位。
桐城学者与佛教徒的交游也极为普遍,如吴应宾之与憨山德清、博山元来、浮山郎目,方以智之与觉浪道盛,钱澄之与问西禅师,潘耒与迂庵上人,戴名世与唐西浦程师孔、钟山和尚,方苞与宗六禅师,姚鼐与妙德和尚、王文治居士等等,皆有史可考。
在佛教氛围如此浓厚的地域生长起来的桐城派,若说其学术思想与佛教毫不相关,确实令人无法置信。
一、儒释之辩与桐城佛学
方宗诚论桐城学术云:“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2〕是时桐城学术的主流是程朱理学,累叶敦儒,濯于忠节,对于佛教思想是整体排斥的。至麻溪吴应宾出,学风一变。吴应宾(1565—1634),号“观我居士”“三一老人”,主张援释入儒、三教合一,因而与以方学渐父子为代表的桐城主流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矛盾,从而展开了一场持续二十年的辩论。有学者称“吴应宾是桐城新学风的开创者,他为桐城学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桐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3〕
吴应宾最大的贡献即是以“宗一”之说,扩大了桐城学术的包容性。吴应宾认为儒、释、道在门户上虽“各一”,而在本质上是“共一”的。这种观念开启了桐城学术的兼容特征。此后桐城主流学术对于佛教之态度,大抵沿袭吴应宾的理路。此种路数,析而言之,可申之为三:
第一,桐城主流学术虽仍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但整体上已经对佛教思想兼容而不排斥了。吴应宾外孙方以智继承吴氏合三教而一的思想,主张儒、佛并弘,世称其“逃禅”。〔4〕其子方中通《上大兄议用牲醴合祭二亲书》云:
文忠公之出世也,遁世而非出世也。浅之乎视释氏者,谓崇儒自应攘释。……门庭各别,莫能合一,因议爪发、衣钵归法嗣,行释礼;肉身归子孙,行儒礼。〔5〕
方中通认为儒家与佛教不必生死不容,“崇儒自应攘释”之说是浅陋之见。
与方以智年岁相仿的钱澄之“三教总来无一字”(《同三一上人客胡氏草庐》)之句,本出自禅宗“不立文字”之旨,河南登封石刻《达摩持钵西来图》偈云“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而心学汲取了这种观念,王阳明称“悟后六经无一字”。钱澄之《赵母黄太孺人八十寿文》认为儒、释、道三教皆可贯通“无一字”之旨,又称“贯通三教,其要以孝弟为宗”。〔6〕其观念与吴应宾、方以智同辙。张英《文端集》中多处用佛理、佛事,其家训《聪训斋语》亦是融汇了三教思想,其引佛事如“佛家以货财为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国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盗贼,五曰不肖子孙”。
姚鼐有诗曰:“举目孰不改,身存心可碎。那择儒与佛,有得差为快。”(《同游累日,复连舟上金山,信宿焦山僧院,作五言诗纪之》)“有得”,亦是求“为己”;若能有得,何择儒、佛?方东树少时泛览诸子百家,而“晚耽禅悦”,据方宗诚所记:
先生老年屡遭横逆,而克己之功益至。尝借佛语谓门人曰:“人苟见性悟道,无内外、我人,即随所处秽浊凶危迷险,皆不见。但见无非清净道场、净土乐土,无复有烦恼、嗔恨、爱憎、取舍、忧惑、惧恐、佈罣碍之境,视身世一切患苦,都如云影,无喜无忧。”〔7〕
按照方宗诚的说法,方东树耽禅也颇有逃禅的意味。然而皮锡瑞批评其“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观方东树一生著述,其中涉关禅语佛法者极多,非止在晚年,可见皮氏所论也非捕风捉影。
第二,禅净兼修,不傍门户。吴应宾是云栖祩宏受戒弟子,称祩宏为“莲宗八祖”。〔8〕又《药地炮庄》载吴氏论佛语云“别传多互换说,妙以破执,而又破其破,则并心性亦扫矣”。“别传”即禅宗,吴应宾主张禅净双修,方以智评价其“圆三宗一,代错弥纶,集大成,破群疑”。〔9〕方以智受吴氏及觉浪道盛影响,更是如此,他“不喜立门户。不徒禅宗之内不应有门户,即所谓儒、释、道之界限亦应当‘泯’而‘统’之”。〔10〕姚鼐《与陈硕士书》曰:“《安般守意经》,吾所未见。然佛经大抵相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11〕方东树《冷斋说》一文自记云:“晚岁研说性命,因兼寻祖意缉成《金刚藏十书》,曰《初发心语》《金刚经疏记钩提》《无著菩萨十八住》《天亲菩萨二十七疑》《秦译直解》《般若五位细因》《唯识论举要》《大智度论》《乐说本法心证》《圣佛参同》,共六十四卷。”“后读《黄檗禅师语录》……不觉汗下。”〔12〕可见他对于禅宗、唯识宗等都有投入的研究。桐城派学者大都以儒学为根柢,因而其对于佛教各派能有兼宗与圆融的态度。
第三,区别心、迹两端而言佛。桐城之排斥佛教者多是排其“迹”。方以智《象环寤记》自称:“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苾刍’。……家训尝提‘善世、尽心、知命’六字,贵得其神,勿泥其迹。”〔13〕苾刍即比丘。方以智曾祖方学渐有家训:子孙不得从事比丘之业。然而家训中又有“善世、尽心、知命”六字,方以智认为对于佛教应当超脱于“迹”的层面。戴名世、刘大櫆对于佛老的排斥,是对于“迹”的排斥,而非义理的排斥。戴名世称“崇大其宫,衣食其徒,焚香膜拜,如醉如狂,而自以为得计。吾见佞佛之家,其家不旋踵而败,然则举宇宙而佞佛,宇宙又安得久存哉!”又谓“康熙四十三年,遣人入佛国观其风土,自君长以下,通国皆僧衣冠,无不诵经、念佛、膜拜,而无父子兄弟之伦,妇女人人与之合,人止知有母,不知有父,此可谓‘极乐世界’乎?”〔14〕所批评的都是关于佛教的光怪现象,很多是道听途说的。他认为:
吾道患者不在于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见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轮回生死之佛不易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讨贼之义,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还为儒,则佛之佛不攻而自破。〔15〕
其对于佛教的态度虽然还是以批评为主,但分“明心见性之佛”与“福田利益、轮回生死之佛”两端而言之,已不是一味贬低与批判了。
姚鼐称:“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远出乎俗学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为不必,而况身尚未免溺于为人之中者乎?”〔16〕姚氏执儒家“为己”之义以衡佛学,认为其绝非俗学,儒者不必以外在形式的异类而拒绝它。方东树《辩道论》曰:“吾今所为辟乎佛者,辟其言也。其法不足以害乎时,其言足以害乎时也。”〔17〕方东树也将佛教分言、法两端讨论,认为佛教之所以害时者,是“言”不是“法”。
综上而简言之,自吴应宾之后,桐城主流学术对于佛教的义理是兼容的。吴汝纶在答日本学者高木政胜问时甚至还提出:“欲使三国同心,则莫如起德教,欲兴德教,则莫如兴佛教”。〔18〕
这种兼容性的结果是佛教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桐城学术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包括桐城派古文。以桐城派“四祖”为例,戴名世自称:“余不为浮屠氏学,而尝好与浮屠游。余儒者,与当世所谓儒者异,以故当世儒者皆畏恶之,独一二浮屠氏不余忍弃也,贤余才而从之游。夫儒者弃之而见收于浮屠氏,然则当世儒者毋轻诋浮屠。”〔19〕方苞虽不研佛学,却常为佛教徒作序、记之文,如《廌青山人诗序》《赠介庵上人序》《沛天上人传》《重建润州鹤林寺记》《重修清凉寺记》等。刘大櫆《浮山》诗云:“山人野衲足伴侣,他日结庐归此中。”《金谷岩寺》诗云:“孰能捐尘累,世外同栖止?”可见其对于佛教生态的认同。姚鼐“以衰罢之余,笃信释氏”,“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20〕其《乙卯二月望夜与胡豫生同住憨幢和尚慈济寺观月有咏》诗曰:“文学俊才笔,禅悦亦所歆。余衰邈违世,慕道恐弗任。非徒遣烦虑,更当遗赏心。阇黎净业就,结习犹讴吟。共会忘言契,何嫌金玉音。”〔21〕毫不讳言对于其佛学的欣赏与投入。可见,桐城派四祖整体上对于佛教都是接纳的,或者说至少是不排斥的。
佛教思想本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又反过来影响桐城学术和桐城派。它开阔了桐邑的学术襟怀,也影响了桐城派的诗文创作和理论,桐城学术上的兼宗汉宋,诗学上的熔铸唐宋,古文上刘大櫆义理、书卷、经济并举,姚鼐义理、考据、文章并重,都是重要表现。
二、“声明之道”与“声音证入”
“因声求气”说是桐城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其受到“文气说”与朱熹涵泳理论的影响,学界已颇有讨论。〔22〕佛教也有声明之道,其对于桐城派有没有可能产生影响呢?
佛教有梵呗、唱诵之学。《华严经》曰:“演出清净微妙梵音,宣畅最上无上正法。闻者欢喜,得净妙道。”又云:
一切文字、一切言语而转法轮,如来音声无处不至故;知声如响而转法轮,了于诸法真实性故;于一音中出一切音而转法轮,毕竟无主故;无遗无尽而转法轮,内外无著故。……一切众生种种语言,皆悉不离如来法轮。〔23〕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继承这一思想:“如《阇尼沙经》说,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义,乃名梵音。又梵者,圆洁之谓,又如梵天普应等故名也。声者,是执受声,音者,明彼有诠表之韵,是故名也。”〔24〕指出梵音的种种功德。鸠摩罗什所译《十诵律》认为梵呗具有“五利益”,即“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疲劳”“声音不坏”“语言易解”。〔25〕因此佛教有“以音声为佛事”之说,古大德将梵呗称为“弘法之舟楫”。
因为梵音有如此多功德,成为修行的善巧法门,学佛者可以由此证入。如《大智度论》“四念处品”称“华严四十二字母”有二十种功德,即得强识念、得惭愧、得坚固心、得经旨趣、得智慧、得乐说无碍等。〔26〕郑樵《通志》谓“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又称“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故曰:‘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昔三摩提,尽从闻中入。’有‘目根功慧少,耳根功慧多’之说”。〔27〕因而佛教有“一音具足一切义,一义含摄一切音”,“悟道与否,听声即知”的说法。
佛教的梵唱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的吟诵之风。胡适说:“大概诵经之法,要念出音调节奏来,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后来传遍中国,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小孩念书,秀才读八股文章,都哼出调子来,都是印度的影响。”〔28〕陈炳铮也指出:“至于‘吟读’的‘吟’,则是通过一定的节奏,时而把有关字眼的音拖长,大体上形成一种比较单纯的腔调,类乎僧人之诵经。”〔29〕而张培峰认为佛教梵呗是中国失传的古乐传统的宗教延续,而吟唱是其世俗化的结果。〔30〕因而,从整体上讲,桐城派的文章声音之学是传统吟诵文化的延续,自然也是佛教梵呗影响的结果。
除此之外,佛教梵唱对于桐城声音之学有无直接的影响呢?我想提出以下几点边缘的证据:
其一,释德清、方以智与梵唱。吴应宾曾师事憨山德清,而德清对于音声证入之法门十分重视。其《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记》卷六云:
盖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由此界众生耳根最利,以声入心通,直达法性,最为甚深。故《楞严》拣选圆通,以耳根为第一。此经令修如实行者,以戒名言为第一。以此方入道,无过耳根为最胜,而障道亦无过名言为最胜故,所谓根尘同源,缚脱无二也。然凡夫虽依名言结业,而间有利根宿具般若闻熏者,能观言语性空、音声不实,如风号谷响,即入无生者有之。〔31〕
吴应宾的外孙方以智逃禅之后,便开始研究梵音。钱澄之《失路吟·行路难》描绘方以智:“五更起坐自温经,还似书声静夜听。梵唱自矜能仿佛,老僧本色是优伶。”自注曰:“愚道人既为僧,习梵唱,予笑其是剧场中老僧腔也。”〔32〕方以智对梵音的深刻研究与亲身实践,对于桐城后学一定有影响。虽然因政治因素,方以智较少为桐城后人所提及,但其在当地的实际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姚鼐就曾在其笔记中两次引用了方氏《通雅》,方氏的音韵之学想必不会被姚鼐忽视。
其二,刘大櫆颇好梵音。其《吴女诵经图》诗云:“绣佛斋中恰称身,白蕉衫子紫荷巾。金刚诵罢松煤滑,自署头衔善女人。”又《春日同诸公宴集寺院》云:“仙梵上浮林,佛香飘满殿。”《天门山》云:“梵响浮林杪,经香溢殿帷。”〔33〕皆可证其常接触梵诵。若将桐城派“因声求气”之法与佛教梵唱之方式进行对比,依稀可见其相承之处。吴立民总结密宗所传“声明之学”曰:
念诵得法,至为重要。念诵得法可通过气脉入音声海,一般来说,念诵方法,要点有三,即心气合一、声气合一、身心合一。……抑扬顿挫有致,高低平仄分明,节拍自然顺畅,而重点在于声音随着气机自然在体内任运转动,该高则高,该低则低,三部音轮回周流,声音保持一样,但是音调可以不同,随气自然而转。……华严字母每个字都有平上去入四阶,而平上去入中又有各之四音,练习纯熟的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唱,循以悟道,乃至方便度人,大有作为,妙不可言。关键是要念诵得法,就是要作到心气、声气、身心三合的境界,也就是要真做到“心一境性”,才能发生实效。〔34〕
对比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的两则文论:
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35〕
则相通之处至少有三:都要以气为主、声气合一;都重抑扬顿挫、讲究平仄节奏;都要求熟以悟道。刘大櫆《程易田琴音序》云:“有天地而数生于其间矣。……古者,钱刀以百八为贝,释氏之梵诵以百八为珠,其考钟,其击鼓,以百八为纪。百八者,十二其九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世,十二会,以及乐之六律、六吕,无非十二也。”〔36〕可见其对于佛教梵诵之音乐、节奏非常清楚。佛教的诵经本就是代佛说法,《观心诵经法》云:“观我能为法师传佛正教,为四众说想所出声,非但此一席众,乃至十方皆得听受,名为假观。”〔37〕而刘大櫆“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吐,皆由彼而不由我”,不正是假观之法吗?
其三,“中边皆甜”与“因声求气”。方以智《诗说·庚寅答客》曰:“姑以中边言诗,可乎?”〔38〕方以智所说虽为诗,而桐城派常常强调“诗文一理”,因而对于刘大櫆、姚鼐“言之精粗”之说不无启发:
从而叶之,从而律之,诗体如此矣,驰骤回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声,以此合拍,安得不齿齿辨当耶?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迻也,成语欲其虚实相间而熨帖也。调欲其称,字欲其坚。字坚则老,或故实或虚宕,无不郑重;调称则和,或平引或激昂,无不宛雅。是故玲珑而历落,抗坠而贯珠,流利攸扬,可以歌之无尽。如是者:论伦无夺,娴于节奏,所谓边也;中间发抒蕴藉,造意无穷,所谓中也。措词雅驯,气韵生动;节奏相叶,蹈厉无痕;流连景光,赋事状物,比兴顿折,不即不离;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边皆甜之蜜乎?〔39〕
虽自谓“中边言诗”,实际主要以讨论“边”为主。而在“边”的讨论中,主要以声律节拍为主,如“叶”“律”“驰骤回旋”“和声”“合拍”“齿齿辨当”“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逐”“调欲其称”“调称则和”“或平引或激昂”“抗坠而贯珠”“流利攸扬”“歌之无尽”“娴于节奏”,几乎语语不离音声。
方以智认为“边”为“中”之所寓,学者不可不屑于音节之“末事”,不能“以中废边”。此说与刘大櫆“文之精粗”之说几乎如出一辙。二人也都认为“节奏”是字句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中边”之说出自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人为道,犹若食蜜,中边皆甜。”宋真宗御注曰:“佛言:我所说经,犹如蜜味,若人食之,中外尽甜,更无二味。慕道之士,若悟经深旨,身心快乐,当证道矣。”〔40〕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北山集杜诗序》亦倡此说:
神气之为美也,贵服饰乎?诚如是,将毛嫱、西子而裸焉,亦足观矣。专尚辞,至趋藻艳,又或使事离奇,不务意之切当。本浮响曰宏亮,本浅薄曰深厚,本饾饤曰博雅,是何异嫫姆、厐廉而披珠玉锦绣也?是故中边兼到,而后可以语诗。夫中有一,意味是也。边有三:格律、声调、字句,皆辞之所属也。通乎四者,而后可以语中边。……中未始不假边而寓,逐边而生也。〔41〕
桐城诗学之间本就相互影响,如钱澄之“性情”说,方拱乾、方孝标、陈式、方贞观、方苞都颇有接受。假若刘大櫆受到方以智、方中通“中边”说的影响,也是间接地受到佛教的熏陶了。
“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42〕这是姚鼐的著名论断。“证入”“门外汉”是佛教用语,“声音证入”亦是佛教法门之一。总的说来,桐城派作者与佛教徒、佛寺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常常流连于佛寺之中,受到梵呗唱诵的启发,是不无可能的。而方以智对佛教声明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的桐城一邑,其对于后学的影响,我们不应小觑。
三、以禅论文与顿悟之梯
桐城派颇多以禅(佛)论诗、论文之语。兹列举数例以证之:
舍一无万,舍万无一。……世间所目,不过道德、经济、文章,而切言之,为生死性命。〔43〕
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才人之诗……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学人之诗……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诗人之诗……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方贞观《辍锻录》)〔44〕
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康乐貌似犯此,似沈滞平钝,气势不起;其实竟体空灵迈往,曲折顿挫,非静对久之,不能深解其妙。〔45〕
渡河香象声俱寂,掣海长鲸力自全。随分阿难三种法,个中觅取径山禅。(姚莹《论诗绝句》其六十)〔46〕
方以智天地一气、舍一无万之论,源于其佛学“圆∴式”的哲学观。〔47〕方贞观继严羽《沧浪诗话》“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后,亦析诗为三类,而分别以小乘佛法、律门戒子、禅宗心印相比附,从而推举心底空明、意味高远、不为物累的“诗人之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常用“佛氏所谓”“佛氏谓之”等语论诗,所举之例则是曹洞宗“死句”“死语”之论以言诗。姚莹《论诗绝句》中,“渡河香象”源自《优婆塞戒经》,“掣海长鲸”源自《庄子》与《华严经》,阿难陀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径山禅是南宋大慧宗杲禅师。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若细绎桐城以禅(佛)论诗、以禅(佛)论文的阐释面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位:
第一,借径。“径”,指修行入道的门径,即法门。《法华经·序品》:“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方以智《道艺》开篇便说:“心有天游,乘物以游心,志道而终游艺者,天载于地,火丽于薪,以物观物,即以道观道也。火固烈于薪,欲绝物以存心,犹绝薪而举火也。乌乎可?”〔48〕谓不可离径而觅道。
入古文之径甚多,姚鼐《与陈硕士书》称:“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49〕而桐城派所觅得之法门,便是“音节字句”。刘大櫆论文,在提出“神气”之说后,又称“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50〕其《张秋浯诗集序》又云:“气之精者,讬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退、疾徐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51〕自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韩愈提出“气盛则言宜”,文气论影响极大。然而气无迹可寻、无矩可守,对于那些资质平常的写作者,往往不得门而入。刘大櫆此说是示人门径。姚范谓“字句章法,文之浅者,然神气体势,皆阶之而见”,〔52〕与刘氏所论相近。
姚鼐称:“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深读久为,自有悟入。……夫道德之精微,而观圣人者,不出动容周旋中礼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53〕诗文之道精微而虚无,字句音节明朗而实在。因此若要“悟入”“证入”,总不离“声音”这一门径,舍此便无可窥寻。正如其门人陈用光所说,“余尝闻古文法于姬传先生矣,曰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古文之格、律、声、色,诗之音节也。不求于是,何以为古文,何以为诗?”〔54〕方东树《昭昧詹言》论诗云:
字句文法,虽诗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学,非先于此实下功夫不得。此古人不传之秘,谢、鲍、韩、黄屡以诏人,但浅人不察耳。〔55〕
谢、鲍、杜、韩,其于闲字语助,看似不经意,实则无不坚确老重成炼者,无一懦字率字便文漫下者。此虽一小事,而最为一大法门。苟不悟此,终不成作家。〔56〕
所谓“不传之秘”“一大法门”,也是以佛法来比喻桐城派所寻觅出的古文路径。郭绍虞称:“昔人论文,往往只重在最精处而忽其粗迹,但在海峰却说:‘论文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这是昔人未发之义。”〔57〕姚鼐《与陈硕士书》:“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说,皆陈陈耳。达摩一出,翻尽窠臼,然理岂有二哉?……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58〕从这个意义上讲,桐城派之与古文,正如禅宗之与佛教,“达摩一出,翻尽窠臼”。
第二,阶梯。佛教有所谓“四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一乘;又有果位之差等;佛说法每有所谓“次第”;此皆有阶梯渐进之义。禅宗渐门神秀有所谓“五方便门”:第一总彰佛体,第二开智慧门,第三显不思议门,第四明诸法正性门,第五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也是予人阶梯。桐城派以佛法言诗文,亦秉此法门。
刘大櫆将文事分“最精处”“稍粗处”“最粗处”三品:“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要从最粗处入门,渐次有得。又谓“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须辨之甚明”,〔59〕也是暗含层次的划分。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也承继了刘大櫆之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又谓“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60〕明确地指出了由粗入精、继而御精遗粗这一古文路径。
桐城派诗论亦是如此。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诗有似浮泛而胜精切者,如刘和州《先主庙》,精切矣;刘随州《漂母祠》,无所为切,而神理自不泛,是为上乘。比之禅,和州北宗,随州南宗。但不可骤得,宜先法精切者,理学家所谓脚踏实地。”〔61〕方世举“性好佛”,〔62〕他以禅宗的渐、顿二派比喻刘禹锡和刘长卿的诗歌。他认为顿悟虽上乘,但不可骤得,应由渐而顿,“登高自卑,宜先求其次者”。〔63〕这也是桐城派诗文理论的整体路径。蒋寅论姚范诗学云:
姚范论诗明显分体用两个层面,性情是体,精神、气格、音响、兴会、义意是用。论性情是为了知人论世,论精神、气格、音响、兴会、义意则是“核其诗而规其至”,即考察具体作品以估量杜甫艺术造诣的具体落着点。用生于体,体于用显。〔64〕
姚鼐认为学诗当由韩而入杜,即所谓“姚门师法”。姚鼐指点姚元之学诗,“须先读韩昌黎,然后上溯杜公,下采东坡,于此三家得门径寻入,于中贯通变化,又系各人天分”。〔65〕沈曾植认为:“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66〕寒碧《重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言:“一般而言,桐城家法是由苏、黄溯于杜、韩。”〔67〕钱基博称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68〕称方东树诗“由黄庭坚学韩愈以窥杜甫,力避俗熟,自是姚门师法”。〔69〕方东树论诗亦承此路径:
杜公如佛,韩、苏是祖,欧、黄诸家五宗也。此一灯相传。〔70〕
韩、苏并称;然苏公如祖师禅,入佛入魔,无不可者,吾不敢以为宗,而独取杜、韩。〔71〕
以禅宗“传灯”之典譬喻学诗入道的路径。而苏轼诗如同不立文字的顿宗,无阶梯可攀援,因而不敢以为宗。
第三,顿渐。以禅宗“顿悟”之说论诗、论文,并非自桐城派始。严羽《沧浪诗话》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几乎是宋代诗人的公论。然而,桐城派之论顿悟,自有其特色,即强调“悟”前之累积与指示“悟”之方案。钱澄之《书有学集后》论诗云:
吟苦之后,思维路尽。忽尔有触,自然而成。禅家所谓“绝后重苏”,庸非悟乎?〔72〕
“绝后重苏”之说来自禅宗语录,《五灯会元》载苏州永光院真禅师语:“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钱澄之“绝后重苏”之说一方面强调“忽然而触”的顿悟,更重视此前的深思苦吟、思维路尽。
姚鼐认为文章事有禅宗所谓“不可言说”者、不可着力处,然而此“不可说”的神妙之境,不可着力的非要紧之处,须从可说者、可着力者下功夫。若无此段功夫,则终身与顿悟无缘。因此,姚鼐十分强调“法”与“悟”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批评方苞,“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73〕告诫陈用光“必须超出此等见解者,便入内行。须知此如参禅,不能说破,安能以‘体则’言哉?”〔74〕但是他认为“有法”是“破法”的前提,“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75〕若无“法”,则何以变法呢?因而不由门径的超然无“法”的妙悟虽也让姚鼐神驰,却不为其所强调。〔76〕桐城派极重杜诗,正是因为杜诗在“法”与“悟”之两端皆可效法。方拱乾称“少陵之诗,化工也”,〔77〕“少陵无一处非法,而法之合乎天然”,〔78〕他批注《雨过苏端》一首曰:“作诗时岂字字照应,是绪真法老,便合天然。”〔79〕方贞观《辍锻录》评老杜诗云:“唯有多读书,镕炼淘汰于有唐诸家,或情事关会,或景物流连,有所欲言,取精多而用物宏,脱口而出,自成局段”,〔80〕姚鼐称“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81〕
大体说来,前人以禅论诗文,常常描述悟后之境,而桐城派则关心“悟”之路径;前人以禅论诗文,常常强调不破不立,而桐城派则强调要先累积“可破”之物,方有“立”的机会。
四、内在矛盾与调节之道
桐城派的学术思想是有着深层的内部矛盾的,而较少为人所揭示。桐城派在义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主,在诗学、古文理论上以“法”为核心。然而这“义”与“法”中间,颇有可争持之处。现申之如下:
其一,文事与道之抵牾。程朱理学认为道为本而文为末,必先修道而后言文,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程颐对于韩愈古文尚且如此批评,更遑论其他。程颐认为学问有“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而“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82〕朱熹称“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其批驳“文以贯道”之说云:“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83〕可见,程朱理学认为道为文之本,本立而文自生。若花费精神,在文辞上下功夫,则是舍本逐末了。桐城派本质上是文学流派,以“文”为主而“道”为济,故刘大櫆称“文人者,大匠也”,而“义理”不过“匠人之材料也”。这是第一层矛盾。
其二,技法与道之矛盾。在程、朱看来,文章尚且是末事,文章之法更不足道了。程颐谓“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对于在章句文法上下功夫的人直斥为“俳优”。朱熹论诗云:“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诗之高下,不在于诗法之工拙,而在于作者志德之高低。他批评苏洵古文“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84〕是以在程、朱看来,诗文之技法,并无益于诗文。而桐城派论文则言必称“义法”,辞必求“雅洁”,实际主要都是在“法”上下功夫。程、朱若与方、刘、姚同代,可想见其必不能与之同伍。
其实理学与辞章学之矛盾,自程、朱以来便一直存在,且日渐得以缓和——偏理学者以理学兼纳辞章,偏文学者则以辞章兼容义理。然而桐城派的问题是将二者共同标举、同时看重,如方苞“言有物”“言有序”之论,姚鼐“义理”“辞章”之说,曾国藩“道与文俱至”“道与文并而学之”之论。这就使得在桐城派学术内部,理学与辞章学的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了。
桐城派作者一方面继承了程、朱“道本文末”之说,认为文之深厚、雅洁、辉光,诗之高旷、广远、清澈,根本在于作者之心是否得道体之畀与,非“戋戋焉以文为事”“敝终身之力于其中”者所能达到。另一方面,桐城派事实上是以文事为根基,这与“道本文末”“先道后文”的观念恰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戴震批评古文家们“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85〕
又,桐城派以古文之“法”立身成名。然而钱大昕谓望溪之文未喻古文之义法,因“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86〕蒋湘南谓“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是,何有于法!”〔87〕罗汝怀驳“雅洁”之说云:“唐以前文以征实为主,朴茂典瞻,其弊也或失之芜杂;唐以后文,法愈密,意愈巧,词愈工,其弊也廓落枯寂而真意漓。”又云:“夫芜杂者文之病,脱略独非病乎?自雅洁之宗标,而文格高,而文品尊,而文律綦严,然因是而适成蹇弱者多矣。”〔88〕这些批评大体可以为程、朱代言。
尤其是桐城派提倡“摹拟”,更是与理学不合,一是离本趣末,二是蹑等伪求。所摹拟者,格律、声色、修辞也,戴东原所谓“等而末者”。又,为文须真,有此境界方能发此言,如方苞《答申谦居书》所言“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89〕姚鼐《与陈硕士书》所谓“此中自有真实境地,必不疑于狂肆妄言,未证为证者也。”〔90〕然而作文者胸中未有圣人境界,偏又“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使有”,“圣人愉,则吾亦与之为愉;圣人戚,则吾亦与之为戚”,无异于沐猴而冠。所以,从“摹拟”之说,可以窥见桐城派文论在文学本体与技法上的双重抵牾。
如何弥平这内部的双重矛盾呢?禅宗正好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资源。
首先,文事与道之所以抵牾,在于将“道”与“文”分本末、高下。朱熹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是之“道”高“文”下,道主动,文被动。王阳明心学指斥此种分别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认为“心即性,性即理”“心一而已”“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自心学之观点而推绎之,则“文心”与“道心”皆此百姓日用、七情六欲、兴观群怨之心。一无高下之分,二无主动被动之别。
心学在桐城本就颇有渊源,桐城学风的开创者方学渐就属于心学一派。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其学术渊源曰:“先生受学于张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91〕有《心学宗》一书阐其心学。其子方大镇、孙方孔炤、曾孙方以智皆能继守家学,玄孙方中通汇编其“家学相传,自明善先生至先君文忠先生四世理学”,为《心学宗续编》。刘大櫆自道其学术好尚云:“我爱新建伯(王阳明),术业何崇隆!七龄矢志学古圣,富贵于我浮云空。径从良知见性命,震磕天鼓惊愚蒙。卒其所就继孔孟,唱和如以徵应宫。后来小生肆掊击,连结鸡雌拜虎雄。擒濠立功在社稷,用由本出观其通。”(《奉题学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韵》)其《答吴殿麟书》云:“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慎始》云:“今夫嗜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也。夺其所甘,而易之以其所苦,势不能以终日。”〔92〕一派心学口吻。
姚鼐为刘氏弟子,自然受其影响。姚鼐论道与艺曰:
今夫六经之文,圣贤述作之文也。独至于《诗》,则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然是言《诗》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鬼神,反覆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于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几乎文之至者,则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觊天之或与之,无是理也。〔93〕
不但扬乎朝廷、光乎政事、道德修明、学术该备者,得之于天;田野闺闼之文、无可称述之人亦可以以文而达道,而圣人称颂之。则何必理达乎圣人,方能为圣文呢?所谓“道与艺合”,与朱熹“文便是道”完全不同,前者文为主动,所谓“所求以几乎文之至者,则有道矣”;后者文是被动,所谓“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与此类似的论述有:
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答鲁宾之书》)
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荷塘诗集序》)〔94〕
看似与程、朱“文道相合”之论相同,实际上悄悄将“文”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解决了道本文末的第一重矛盾。
姚鼐的这种思维可能受到心学的影响,也可能得自禅宗。而心学的这种思维也是来自禅宗。禅宗之与佛学心性论的发展,正在于其肯定众生之性即真如佛性,众生之心即清净本心,《坛经》云“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所以王阳明称“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坛经》称“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而王阳明亦曰:“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坛经》又云:“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古尊宿语录》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行住坐卧、屙屎送尿都可与道相合,文、艺自然亦可以合于道了。
其次,技法与道之所以矛盾,根本在于程、朱认为“技”之累积并不能达于“道”,“末”之累积不能达于“本”。而在禅宗看来,本与末是一体,本体与工夫也并无二事。《古尊宿语录》卷四云:“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云:“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知觉,亦不离见闻知觉。”是知文法亦是“本心”的显现,而文法亦不离于“道”。
刘大櫆称:“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则细技中存大道,有禅宗“一花一叶一如来”(《佛海瞎堂禅师广录》)“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之义。姚鼐论技与道曰:
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藉以达道。(《复钦君善书》)
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答翁学士书》)
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与王铁夫书》)〔95〕
在程、朱看来,文之技法无益于道,越专意于技法,反而离“道”越远,以至有“作文害道”之说。而姚鼐却认为技法之高者,可以藉之以达道。正是禅宗“道法不二”说的延伸。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铭》云:
顾其始也,判精粗于事与道;其末也,乃区美恶于体与词;又其降也,乃辨是非于义与法。噫!论文而及于体与词、义与法,抑末矣。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专家,旷百年而不一觏其人焉,岂非以其义法之是非、词体之美恶,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杂、冒而讬耶?文章者道之器,体与词者文章之质;范其质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无媸也,则存乎义与法。〔96〕
方东树也意识到程朱理学与桐城派在“义法”上的矛盾之处。他对桐城派的辩护是:所谓义法,所谓文辞,不也是“道”的体现吗?义法之不可昧而杂、冒而托,正如道之须证得真实境地。可知义法与道是一不是二。
姚鼐的“神妙说”也是对“技法”的本体性突破。姚氏所谓“通神领”“通乎神明”“通于造化之自然”“须有悟入”“天与人一”,“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皆是借用禅宗的顿悟之说,在“法”与“道”之间搭建一阶梯,从而解决“技法”与“道”之矛盾。
五、结 论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第一,佛教对于桐城派的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深入且长久的。桐城派文论中的一些思想与观念,实际上是在佛教思想长期浸润下形成的。第二,桐城派对于佛教的理解与运用,有其自身的特色。这是佛教思想与桐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桐城派在义理与辞章之学上本有矛盾之处,而佛教思想正可以调和此种矛盾,从而使桐城派在学术宗尚与古文追求上能够相安相得。
注释:
〔1〕〔89〕〔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6、164页。
〔2〕〔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柏堂集》次编卷一,清光绪桐城方氏志学堂刻本。
〔3〕参见丁诚际、李波:《明代桐城理学》,《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
〔4〕参见邢益海:《方以智的逃禅及其前两期行实》,《中国文化》2019年第2期。
〔5〕〔41〕〔清〕方中通:《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0-221、15-16页。
〔6〕〔72〕〔明〕钱澄之:《田间诗文集》,清康熙刻本,卷十九、卷二十。
〔7〕〔清〕方宗诚:《方植之先生学行续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12册方东树《大意尊闻》附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60页。
〔8〕〔明〕吴应宾:《莲宗八祖杭州古云栖寺中兴尊宿莲池大师塔铭并序》,〔明〕袾宏:《莲池大师全集》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504页。
〔9〕〔明〕方以智:《金谷葬吴观我太史公致香语》,《冬灰录》卷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10〕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8页。
〔11〕〔20〕〔42〕〔49〕〔53〕〔58〕〔69〕〔73〕〔74〕〔90〕〔清〕姚鼐撰、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3,9、23,120,76,120、94、138、134,138,133,224,94,76页。
〔12〕〔17〕〔96〕〔清〕方东树:《考槃集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61、225、332-333页。
〔13〕〔明〕方以智:《象环寤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4〕〔清〕戴名世:《戴名世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1、87页。
〔15〕〔19〕〔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133页。
〔16〕〔21〕〔75〕〔81〕〔93〕〔94〕〔95〕〔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6,493,114,49,49,104、51,291、84、289页。
〔18〕〔清〕吴汝纶:《高木政胜笔谈》,见《吴汝纶全集》(3),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770页。
〔22〕参见任雪山:《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2期。
〔2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4〕《大方广佛华严探玄记》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5〕《十律颂》卷三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6〕《大智度论》卷四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7〕〔宋〕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3、511页。
〔28〕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29〕陈炳铮:《中国古典诗歌译写集及吟诵论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30〕张培峰:《诗歌吟诵的活化石——论中国佛教梵呗、读诵与古代诗歌吟诵的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1〕〔明〕德清:《观楞伽经记》,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240页。
〔32〕〔明〕钱澄之:《失路吟·行路难》,《藏山阁集》,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327-328页。
〔33〕〔36〕〔51〕〔92〕〔清〕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7、397、603,50-51,88,438-439、118、20页。
〔34〕吴立民:《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佛教音乐之道》,《法音》2000年第2期。
〔35〕〔50〕〔59〕〔清〕刘大櫆:《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6,6,6、12页。
〔3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1081页。
〔38〕〔39〕〔明〕方以智:《通雅·诗说》第857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40〕楼宇烈主编,〔宋〕真宗皇帝、守遂、〔明〕智旭、〔清〕续法等撰,张景岗点校:《四十二章经注疏》,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17页。
〔43〕〔明〕方以智编:《青原志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4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36页。
〔45〕〔55〕〔56〕〔70〕〔71〕〔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9、15、20、237、219页。
〔46〕黄季耕:《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注》,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90页。
〔47〕参见武道房:《圆∴:方以智诗学的哲学路径》,《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48〕庞朴:《东西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46页。
〔52〕〔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清道光姚莹刻本。
〔54〕〔清〕陈用光:《吴兰雪游武夷诗序》,《太乙舟文集》,清道光二十三年重刊本。
〔5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3页。
〔60〕〔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6页。
〔61〕〔63〕〔清〕方世举:《兰丛诗话》,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83、771页。
〔62〕〔清〕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
〔64〕蒋寅:《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櫆》,《江淮论坛》2014年第6期。
〔66〕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页。
〔67〕〔清〕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页。
〔6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6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附录《读清人集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44页。
〔76〕参见王达敏:《姚鼐与钱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
〔77〕〔78〕〔79〕〔明〕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清康熙十一年岱渊堂刻本,卷首方膏茂本序、卷首方奕箴本序、卷六。
〔80〕〔清〕方贞观:《辍锻录》,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44页。
〔82〕〔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8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0、3307、3305页。
〔84〕〔宋〕朱熹:《沧洲精舍谕学者》,《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01页。
〔85〕〔清〕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5页。
〔86〕〔清〕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集》卷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6页。
〔87〕〔清〕蒋湘南:《七经楼文抄》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清同治八年马氏家塾刻本。
〔88〕〔清〕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清光绪九年刻本,卷十八、二十。
〔9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