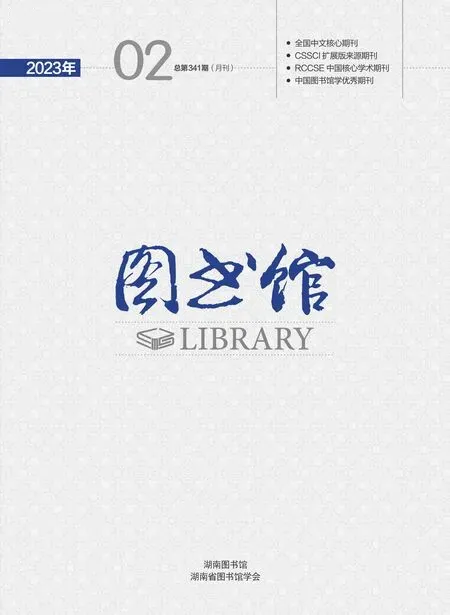《湖南文征》的编纂过程、特色与文献价值*
2023-04-05黄丽俐
黄丽俐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湘潭 411201)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学研究的兴起,与之相关的对中国古代、近代地域文学总集的研究亦引发了学界关注。《湖南文征》作为最重要的湖南文章总集颇受学界重视,“湖湘文库”收有《湖南文征》的影印本,202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由邓洪波等整理的点校本,但鲜有专文对它进行深入研究①。文章从编纂过程、特色以及文献价值等方面对《湖南文征》加以探讨,以期能被相关研究所借鉴。
1 《湖南文征》的编纂过程
《湖南文征》的编者罗汝怀(1804—1880),湘潭人,初名汝槐,字廿孙,一作念生、研生,晚年自号梅根居士。罗汝怀“自少异敏,能奋于学。甫冠,即饩诸生,旋得选贡。廷试不遇,归,遂绝意进取,视荣利泊如也”,与吴敏树、曾国藩、郭嵩焘等皆有往来。其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博通经史,尤好音韵、文字、训诂之学。
湖南地方总集的编纂发轫于宋代,龚元正的《桃花源集》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1]。经元代短暂沉寂后,明代湖南地方文集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出现了《朝阳岩集》《郴州文志》《岳阳纪胜汇编》等涉及湖南境内郡邑的文集。明末周圣楷编《楚才奇绝》三十卷,以楚地为收录范围,不限于湖南一省。
湖南省域总集的编纂始于清嘉道年间,唐开韶分修省志,征录湖南历代诗文三百余卷,惜“道光己卯被水,只存《诗征》”[2]5128,后经编选刊成《湘系》三十五卷。邓显鹤更是致力于湖湘文献的搜寻与整理,曾国藩称“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3]324,梁启超视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4]。邓显鹤编成一省之诗歌总集,经历了漫长的搜检过程,邓氏《资江耆旧集序例》曰:“三十年前,思萃辑湖以南文献为一书。念搜讨匪易,当自近始。因就耳目所易及者,先为掇拾,名曰《邵州耆旧集》。”[5]后经陶澍建议,其不囿于一郡文献,扩充为《资江耆旧集》,复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赅,自湖外诸郡,分隶湖南布政,其间巨儒硕彦,通人谊士,断璧零珪,湮霾何限”[6]4,于是奋力钩稽,广为搜罗,辑成涵括湖南全省的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
罗汝怀编纂《湖南文征》实际上弥补了《沅湘耆旧集》有诗无文的缺憾。邓显鹤虽比罗汝怀年长二十七岁,但他们相交甚笃,且罗汝怀还参与了《沅湘耆旧集》的辑录工作,二人有“忘年之谊”[7]302。罗汝怀在《湖南文征例言》中称:“近新化邓氏刊行《沅湘耆旧集》,以补正廖氏《楚风补》《楚诗纪》之阙失,足以芳风藻川,而未及古文,非意不及此,以有待也。是篇之作,盖继邓氏之志,亦冀诗古文辞兼行,庶六诗三笔不至偏废,而一方耆旧之专攻兼攻者得以并传焉。”[7]226-227可见,鉴于邓氏《沅湘耆旧集》专收诗而不及文,于是罗氏承继邓氏之志,辑成《湖南文征》,使湖南之诗、文并行不废,共同构筑湖南文脉的底色与基础。
从《湖南文征·姓氏传》的编写中也能窥见《湖南文征》对《沅湘耆旧集》的承续与发扬②。罗汝怀在各人小传之后皆用双行小字标明该作者收录文章的数量。如果作者同见于《沅湘耆旧集》,则先标注《沅湘耆旧集》中的存诗篇数,再注明《湖南文征》中的录文篇数,如陈鹏年小传后注云:“《沅湘集》录诗五十二首,今录文五十二篇。”[8]51李腾芳小传后注云:“《沅湘集》存诗十四首,今录文六十五篇。”[8]23此外,《湖南文征》不录生人、流寓,皆踵武《沅湘耆旧集》。
罗汝怀在承继和发扬《沅湘耆旧集》的同时,也对邓氏旧集做了一些补充和考订。一方面,对其疏漏之处进行增补和说明。如罗汝怀认为《沅湘耆旧集》之所以仅录入八首舒东诗,是因为邓氏没有看到舒东全稿,称:“作者受知姚雪门学使,时负盛名。今惟存《青芬山房文》一卷三十二篇,系道光己酉其孙翰刻行。据集中《答潘李二生书》云,除旧经宿迁沉舟湮失外,尚得诗千余首、古文百余篇。不知何以仅存三之一。邓氏仅录诗八首,亦由未见全稿也。”[8]86再如《湖南文征》收录永州蒲秉权文两篇,而《沅湘耆旧集》未收其诗,罗汝怀案曰:“所著《硕薖园集》久佚,只县志存疏二篇,及获全集残本,尚有可采,而兹编已成矣。其集诗多于文,《沅湘集》失采,未见其书也。”[8]34又如罗典小传后案语云:“先生诗文无刊本年久散佚,近从其家得古今体诗手稿一帙数十首,皆在《沅湘耆旧集》所录之外。”[8]70此外,郭焌、陈梦元、胡虞继等人小传后皆有此类说明。
另一方面,罗汝怀对《沅湘耆旧集》中的舛讹进行了订正。如《沅湘耆旧集》中“李廷柬”作“李廷简”,罗氏云:“廷柬,《耆旧集》作‘廷简’,误。其祖端天顺丁丑进士,知滦州,父邦宪弱冠领乡荐第一,皆见《一统志》,廷柬附见《省志·邦宪传》中。”[8]31又如指摘(康熙)《湘潭县志》(郭金台纂)误载周圣楷“失节”一事云:“皆道听途说并无实据……近得周少宰《系英笔记》云:‘闻诸先世长老言,献贼索名士作祷辞,掠伯孔置幕下,明晨祭江,索文甚急,先生两手持空纸宣读,语多丑诋,贼觉,怒而杀之’。家乘所载亦同,案此与陈诗‘碧血化燐’之说相合。”[8]42言之凿凿,皆可信据。
《湖南文征》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应时而生,它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统,使“诗征”与“文征”前后承续、相得益彰,诚如李瀚章所言③,两者“并垂天壤间,以无坠鬻熊、倚相、屈子、濂溪之流风遗韵”[8]3。
关于《湖南文征》具体的成书过程,罗汝怀、李元度等人有如下记载。
罗汝怀《复曾爵相书》:“徒以往所缀缉多未成编,未甘竟付一掷,而又力小任重,忠录之后,继续文征,编校之烦,责无旁贷……”[7]338-339
罗汝怀《湖南文征例言》:“是编出于纂录忠义之余。”[7]227
李元度《绿漪草堂诗集序》:“道光己亥、庚子间,元度读书岳麓,其时邓湘皋年丈方辑沅湘耆旧诗,而研生先生助之搜讨。……逾年先生归,当事聘撰褒忠,录军兴以来死者事,各为之传。书成,又裒湖外先正遗文为一集,曰《湖南文征》,皆不朽盛业也。”[7]473
裴荫森《湖南褒忠录初稿序》:“咸丰十一年,……是时……乃开设褒忠之局于省会,属湘阴郭筠仙中丞董其事。”[9]
何绍基《廿六七日大雨》:“‘咸丰辛酉秋,设局志忠义。先后两中丞,深心出评议。大夫来九能,识职各就次。’注:《忠义录》发端于前中丞骆制军,今中丞毛公始定议设局于抚署东偏之又一村。所延诸贤秉笔者陈雪庐、吴子澄、郭筠仙、丁果臣、罗研荪、吴屏南、邓小耘,提调者黄南坡,收掌者李仲云,共九人。”[10]
郭嵩焘《致罗研生》:“书局采访,茫无端倪。仆心烦且杂,不能专一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局务,以全神运量之。……故欲以采访事属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耳。”[11]
《湖南文征捐助刻资数目》:“是书自同治元年采缉钞誊,至四年秋稿本初具,始刻公启集资,由赵玉班方伯、李仲云都转两处收发。五年冬开雕,九年冬工竣。屡次校补,又经两年。初拟刷印千部,以广流布。未及百部,经费已完,尚待筹款。嗣有佽助,留版续列芳衔。”[8]3852
综上可知,道光十九、二十年间,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时,罗汝怀曾助其搜讨诗文。彼时罗氏已有意编纂《湖南文征》,然历时多年“所缀多未成编”。咸丰七年,湖南开设通志馆续修《湖南通志》,罗氏负责撰修其中的《艺文志》。咸丰十一年,湖南开设褒忠书局,由郭嵩焘董其事,罗汝怀等助之。是年,郭嵩焘致书罗汝怀,望其能主持书局局务,全力修书。约同治三、四年间,《湖南褒忠录》纂成(该书述事止于同治三年)。罗汝怀居局期间,《湖南文征》的纂辑并没有停滞下来,故能于同治元年得以誊钞,同治四年“稿本初具”。同治五年冬,《湖南文征》开雕,于九年冬完成,至同治十一年《湖南文征》刷印完毕。在其开雕至刷印的六年间,该文集又经过多次“校补”。据何绍基于同治八年重九所书题签“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可知,相较于最终的二百卷来说,后“校补”的份量较大。罗氏居局近廿年,虽然工作重点是撰修《褒忠录》《湖南通志》,但书局的工作条件(如图书资料、访书信息、人事安排等)对《湖南文征》的纂辑亦有直接助益。如李概(1824—1881,字仲云,李星沅次子)即在担任《褒忠录》编纂的“提调”之余,又负责《湖南文征》刊刻集资的“收发”工作。
此外,还需要说明《湖南文征》所录文章的采辑方法与途径。罗氏《湖南文征例言》认为,总集的编纂“编录非难,搜采为难”[7]227,《湖南文征》的主要成绩在于“搜辑散亡”[7]227。罗氏所撰《湖南艺文志序》也云:“(乡邦文献)然不及时董而理之,将散者益散,佚者益佚,而终至于不可究诘者,非势所必至哉。不佞措意文献有年,常苦册籍无从采辑,近岁文征之役,颇有不传之秘出乎其间,遂谓可为谋野之获。”[8]190自述《湖南文征》的编纂让其备尝采辑的艰辛,但也有获得秘籍的欣悦。
《湖南文征》收录的文章,多数源于别集、总集或方志,如据《圭斋集》录欧阳玄文二十二篇;据《谦谦斋集》录夏原吉文九篇;据《怀麓堂集》录李东阳文三十九篇,文章皆来自别集,搜集相对容易。至于没有别集存世者,其文章则另行搜检,如刘大夏家祠藏版中仅存诗,《滇南文略》存其文十余篇,收录在《皇明经世文编》中,方志中存文两篇,罗汝怀几经搜采,才得文十八篇。再如,为寻得《孤儿籲天录自序》的原本,罗氏颇费周折:“《籲天录》久无传本,往安化陶文毅公与新化邓先生显鹤谋为重刊,而不得原本,但见杨太傅玄孙文敏公超曾上疏辩诬,将原书进呈……汝怀搜采久之,始从长沙彭孝廉申甫借得,重刊有待,先为录其序例,以见梗概。”[8]2322
又如新化欧阳棻之文遍寻不得,其同邑人李长蕃出示一册,凡数十篇,才得录存。此外,对周大澍、罗典、杨山松等人文章的搜集,罗氏都进行过实地考索。
2 《湖南文征》的编纂特色
《湖南文征》是一部涵盖湖南全省、上起元代下迄清同治的地方文章总集,共201卷(含补编),共计作者789人(阙名未记),辑文4 068篇。《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总集编纂有两个原则,一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2]1685。在《湖南文征》的编纂上,就第一个原则而言,罗氏十分自信,而第二个原则,罗氏自认有所不足,故将文集命名为“征文”而非“选文”[7]227。但实际上《湖南文征》的编纂方式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衡文观念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文集体现了“湖南”这一地域观念。“湖南”这一地理名称和地域范围的确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湖南古属三苗、百濮与扬越之地,唐广德二年置湖南观察使,中国行政区划上由此开始出现“湖南”之名。宋朝时,湖南分属湖南路、湖北路(元丰中改为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元朝,湖南与湖北同属湖广行省;明朝,该地属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三年,中央置湖广按察使司,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均移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始单独设省④。雍正二年,偏沅巡抚易名为湖南巡抚。
一般情况下,流寓文人的作品都被视为地方总集的一部分来保存。如《粤西文载》列“迁客”一类收外籍文人文章,《成都文类》《吴都文粹》《吴都文粹续集》等,亦不限制作者籍贯。与这些地方文章总集不同,《湖南文征》所收作者仅限湘籍人士。它收文起于元代,汉之贾谊,唐之韩、柳,宋之胡、朱等流寓湖南的名家自然不在收录之列,而明代王守仁、袁宏道、何腾蛟等人同样不在收录之列。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可议之处。蒋寅认为,相对于籍贯而言,流寓意味着人与地域之间存在的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愈是文学史研究应予以关注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13]。流寓人士的文学活动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融,给地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可见《湖南文征》把湖湘文学从广义的楚文学的概念中剥离出来,突出了湖湘文学的独立性,但连流寓者之文一并不收,亦有所不足。
其次,兼顾时序与文体的编排方式。《湖南文征》全书由卷首、姓氏传、正文和补编构成。正文分为“元明文”和“国朝文”两个部分,分别为五十四卷和一百三十五卷,后者远多于前者。所收文章均按体裁分卷编排,有疏、策、议、解、说、论、记、序、跋、书、传、碑记、神道碑铭、墓志铭、祭文、杂文、尺牍、公牍、骈体、赋、表、颂、铭赞箴、释、考、辨、小序等。以文体或时序编排是文章总集编纂的常用方法,《湖南文征》先按朝代、次依文体的编排方式,彰显了在清代文章兴盛背景下湖南文章历史演变兴盛的情形,也使编者衡文的观念得到了恰当体现。
一方面,在同一文体之下,作者的编排大致以科举中式时间或科第高低为序。如《湖南文征》共录嘉庆十年进士六人,其中彭浚为“廷试一甲第一名”,何淩汉为“廷试一甲第三名”,故文章编排以此二人为先,聂铣敏、王泉之、蒋湘垣、符鸿排列在后。又如收录道光二十五年取得科名者三人,萧锦忠为“殿试一甲第一名”,排列在前,袁芳瑛、孙鼎臣二人在后。另一方面,同年科考的作者以进士科为先。如嘉庆十三年有科名者八人,其中五人为进士科,两名副贡,一名举人,石承藻以“廷试第一”排为先,其次为瞿家鏊、蒋舒惠、贺长龄、唐业谦,再次为方堃和秦关,最后是举人黄本骐。科第不可考或无科名者,则据其仕宦踪迹和交游时间穿插于科举榜次之间,如郭祖翼、罗文谦等皆属此类。此种编排方式清楚地表明了所收作者的科第榜次和科举时间,也为考察文人的科第情况提供了参考。
在文体的处理上,罗氏也富有眼界。比如作为文类概念的骈体,其文体多样,体类交杂,《湖南文征》对此的处理是得体的,即“元明文”在卷目上列有“骈体”,“国朝文”卷目则不再列“骈体”,而对于一些文体如序、记、公牍等则是先列散体,后标“骈体”。这种处理方式能够反映《湖南文征》所收文章体类繁多的特点以及明清时期文体演变的实际情况,且罗氏的“与为填砌之偶,则不如简质之单,而但为浅俚之单,又不如典丽之偶,若其适用,则各有宜”[7]228的骈散兼重的文章观念,也在文集编纂上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再如律赋向来被人轻视,宋姚铉编《唐文粹》,选唐赋而遗律赋,《湖南文征》则辑录律赋多篇,当然也对此有着严格的标准:“惟题取故实,文取典重,其侔色景物角力试场之作,虽具见巧力,未暇悉登。”[8]229
再次,融合了以文存史的文章观念。从罗汝怀所辑作品来看,其具有明显的以文存史倾向。其一,注重内容的史料性和客观性。《湖南文征》以“发明经史,敷陈政术,考见风俗,能说山川,可备掌故”为主旨[7]227,一些寿嘏之辞、谱牒之叙、时艺之弁言,罗汝怀有意不收,即使间登一二,也是因为其中有故实可征,或者作者之间可以相互考证。《湖南文征》的编录与地方史志关系密切,罗氏采文于别集之外,多来自各方志,而“志书所录,率皆山水祠庙廨舍津梁纪事之作”[7]228,所以《湖南文征》中存录“记”文最繁。其所编《姓氏传》中人物生平多直接从方志中引录,如李棠、廖希颜、车大任等明人籍贯履历皆来自《一统志》,徐大本、廖志灏、张汝治等清人事迹均来自各府县地方志。对于人物的评价,罗氏秉持客观态度,力求平实,不妄加褒贬。他说:“若近时巨公硕德未经志乘品藻者,不欲妄为扬诩,故但纪里贯仕履而已。”[7]229可见其撷取史料之严谨。
其二,注重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嘉庆《湖南通志》“艺文”类列目有三千余种,传流到同治时已不及百分之一,有些文献甚至“片楮无睹”[7]227。有鉴于此,罗氏更重视对“已经散落”的旧刻的收录,他在《例言》中明确说道:“登录多寡,初无成见,惟以新刻方在流传,无妨寡取,旧帙已经散落,所贵多收。”[7]228一些不以文著而以诗称者,录其诗的小引、小序(如《酬曹三茂才诗序》《渡江诗引》等),归为序文。以书著称者,则征其诸帖中之跋语。部分文章(如《天山赋》《圣驾南苑大阅恭赋》《漕河说》等)注解繁多,罗氏认为有益于考证,故皆依旧刻收录,有的篇后识语也一并录入。
最后,遵循不录生人的编纂体例。自萧统编纂《文选》以来,不录生人之例被总集选本广泛继承。《郡斋读书志》曰:“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所录皆前人作也。”[14]邓氏在《沅湘耆旧集》中有言:“今本以盖棺为定,差免诗社锢习。”[6]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南文征》收录作者的年代范围。罗氏虽未明确表明不收生人之作,但从《湖南文征》刊定时间和所收作者的卒年来看,足以证明其继承了不录生人的编纂体例。
《湖南文征》所录作者上起元朝,在此之前的作者不收,罗汝怀在《湖南文征例言》中说明了理由:“雅颂而后骚赋代兴,周楚之间文章卓著,然已炳焕千古流被寰区矣。若欧阳率更、李文山、刘复愚诸家,则《唐文粹》《全唐文》皆鸿编巨帙,裒录无遗,至于濂溪理学大儒阐道之书,世所传习,是皆无庸援入新编,故采辑托始元代。”[7]227
今考《湖南文征》所收作者卒年最晚的是罗萱(字伯宜,罗汝怀子),卒于同治八年。换言之,同治八年是《湖南文征》收文的迄年。
《湖南文征》共收罗萱文九篇。罗汝怀案:“是编甄录不欲徇私,如黎御史吉云、陈池州源兖皆作先严九十寿言,词意并美,嫌于藉自表襮,故悉未登。若萱为家儿,文不足称,岂宜厕名编内,而同人悯其殉难,嘱入数艺,此亦过而存之之列矣。”[8]100罗汝怀在《加赠太常寺卿江西补用知府长男罗萱死事状》中有言:“今同邑冯叟刻昭潭新帖,为摹入数简、文数篇附入《湖南文征》,诗词搜括得三百余篇,拟即编刻。呜呼!其为豹皮之留者,如是而已。”[7]453与罗萱在同一战役中阵亡的湘籍将领不少,曾国藩在《罗君伯宜墓志铭》中有言:“君与文武将领十八人者皆死。”[3]360其中邓子垣、荣维善等人著述鲜少,可能是罗汝怀搜罗不及而暂付阙如。黄润昌有《松筠山馆文集》和《黄茅山集》,罗汝怀的《复曾爵相书》曰:“亡儿实能与黄帅润昌同心一力,而史馆立传,必黄为主,而萱附见焉。”[7]339说明罗氏对黄润昌是有了解的,但《湖南文征》中亦未收录其文。此外,与罗萱同年去世的丁善庆,字伊辅,号自庵、养斋,清泉人,生于乾隆五十五年,道光二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各地考官,二十六年起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编纂《续修岳麓书院志》,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养斋集》等,郭嵩焘赞其诗赋“清蒨绵丽,怡神悦色,循之而无滞机,挹之而有余妍……高出唐贤应制诗赋之上”[15],然其文(包括赋)也未被收入《湖南文征》。丁、黄二人的文章,在当时不难搜觅,某些篇章如《李纲论》《汲黯论》《有文事必有武备赋》等,析论鞭辟入里,气象亦复恢弘,质量当不在罗萱之下,却不为《湖南文征》所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至于《湖南文征》不录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当世名公,虽难以完整体现近代湘人功业与文章之风采,但受不录生人的体例所限,自难苛责,且曾氏诸人文章可以期望,甚至有的已经为“世所传习”,自可“无庸援入”,与其收文不及元前湘人欧阳询、李群玉、刘蜕、周敦颐的道理是一致的。
总之,《湖南文征》的编纂方式,虽不无可议之处,但在总体上仍值得高度肯定。
3 《湖南文征》的文献价值
3.1 辑佚
《湖南文征》中有不少文章为他书所阙载。如蒋湘培的《定王台赋》、米之薿的《二酉藏书赋》、简自采的《上湘学宫赋》等均不见于他书,而为《历代辞赋总汇》所辑录。但今人整理的集子未检及《湖南文征》者仍复不少。例如:
蒋信,字卿实,明武陵人,著有《蒋道林文粹》,《湖南文征》元明文卷四十二存《赠兵部员外蒋公暨宜人万氏墓表》,此文为张灿辉、刘晓林校点的《蒋道林文粹》(岳麓书社,2010年版)失收。
刘三吾,名如孙,以字行,明茶陵人,后人辑其诗文为《坦斋文集》,《湖南文征》元明文卷三十四存《题钱舜举所图唐三学士围棋后》,但未被《坦斋文集》收录,正文后有罗汝怀案语:“此篇不见坦坦斋本集,今从李提举《云阳集》中录出一文一诗,他日可补入本集。”[8]813陈冠梅校点的《刘三吾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亦遗漏此文。
李祁,字一初,元茶陵人,著有《云阳集》,《湖南文征》元明文卷十三存《乐存说》,此文为王毅辑校的《云阳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失收,后《全元文》据《湖南文征》辑录此文。
李腾芳,字子实,明湘潭人,著有《湘洲全集》,《湖南文征》元明文卷五十存《马政条议》、卷五十二存《答心斋刘令》,皆为刘依平等校点的《李湘洲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失收。
龙膺,字君御,明武陵人,《龙太常全集》为其后裔重辑,《湖南文征》元明文卷四十八存《与王襄父书齿录》,为梁颂成、刘梦初校点的《龙膺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失收。
严如熤,字乐园,清溆浦人,著有《乐园诗稿》,《湖南文征》卷六十八存《陶山文录序》,冯岁平、张西虎整理的《乐园文钞》(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的《严如熤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均未收录此文。
汤鹏,字海秋,清益阳人,著述颇丰。《湖南文征》从其《浮邱阁文稿》录文十四篇,分别为《平回疆颂》 《祷雨解》《师说》《送聂蓉峰太守之官浙江序》《宜雁轩诗序》《送贺柘农侍御提学湖北序》《送郑芝泉出守襄阳序》《与陈芝楣书》《与陶制府书》《与陶云汀中丞书》《八先生传》《祭李兰卿都转文》《哀知己赋》《悼亡赋》,皆为今人刘志靖、王子羲整理的《汤鹏集》失录。该集包括《浮邱子》《海秋诗集》《海秋制艺前后集》,学界也多关注此三书,却不及《浮邱阁文稿》。笔者相信,通过对《湖南文征》的全面探究,未来学界会有更多的发现。
3.2 校勘
《湖南文征》还可用于文章字句之校勘。如《湖南文征》所收魏源《老子本义序》一文,相较于其他版本,文末多了一句:“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道光之初补叙于此。”[8]2748此句可为探究《老子本义》的成书时间提供参考。
《湖南文征》还收有彭维新《复修州学记》一文,此文亦见于光绪《湖南通志》,名为《茶陵州修复学记》,二者文字多有不同。如前者为:“撤而迁之南城内,内取其材以副速,工制率略。其地后临谺阬,无以流恶,前逼崇堞,虽凿城为门,仍属墙面,左右近介次,湫隘嚣尘均所不免。旧材易敝,上漏旁穿,频事缮集日甚,无益也。”[8]2054后者作:“撤而迁之南城内,其地后临谺阬,前逼崇堞,虽凿城为门,仍属墙面,湫隘嚣尘均所不免,士气郁陻,行道恻衋,人情怀旧久矣。”[2]1446比较二者,《湖南文征》所录内容更为完整,语意更为明确。
罗氏所收江忠源《告庐州府城隍文》与民国二十五年新宁县教育局重刻本《江忠源集》亦略有不同。前者为:“维咸丰三年,岁次癸丑,十又二月辛丑朔,越巳日,戊辰,安徽巡抚江忠源谨具清酌庶馐之仪,致告于庐州府城隍之神。”[8]3615后者作:“咸丰三年,岁次癸丑,十有二月戊寅,安徽巡抚江忠源谨以庶馐清酌致祭庐州府城隍之神。”[16]据查,咸丰三年十二月朔,非“辛丑”,当月也无“戊辰”,系《湖南文征》有误,故民国重刻本径改为“戊寅”(十二月初八日),按:是月丁亥(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战殁于庐州。以此考之,民国重刻本所述致祭时间可能是真实或者是接近真实的,但《湖南文征》所录文辞更贴近祭文形制。
3.3 考证
罗汝怀崇尚朴学,长于考据,《湖南文征》即有充分体现,其考证涉及人物、史实、地理等方面。
如陈中骐,字轶群,《湘潭县志》和《醴陵县志》皆有记载,罗汝怀案曰:“考其里居在渌口旁,近乃两邑毗连之地,相传渌口旧属潭邑,澧邑因收漕对换,故其籍隶两邑”[8]83,故将其归为湘潭人。又如《湘乡县志》“流寓类”记载衡阳夏汝弼早有文誉,并举于乡,罗汝怀通过考察《衡阳县志》发现其中并未记载夏汝弼举于乡一事,认为《湘乡县志》记载有误。再如“周南”,系多人重名,罗氏曰:“此郴人,外有嘉靖十年举人善化人,有正德甲戌岁贡新化人,此为何文简孟春之弟作记,当是郴人。”[8]19
最著名的是其对杨嗣昌相关事件的考辨。罗氏在杨嗣昌小传后有案语曰:“当时交劾者曰‘误国’,后世追论者亦曰‘误国’,岂谓明亡独在崇祯十年以后乎?至更据媒孽诬罔之辞,轻相诋毁,历二百余年犹然众喙一声,则道听而未加考察之故。”[8]27尤其是对于杨嗣昌与卢象昇“主款”或“主战”一事的考辨,史料皆因杨嗣昌“主款”、卢象昇“主战”而认为二人不和。罗汝怀在《军务正殷讹言可骇疏》后有附记,以杨、卢两人疏文相对照,意在说明军机事务非局外人可揣摩,且以卢氏疏文所言“臣原无浪战之意,枢臣亦无不战之言……忠臣谋国,取其异不必取其同,信之心不必信之众”[8]239,证明“主款”与“主战”皆以国事为重,二人关系并非如野史所云。
罗汝怀对地理方面的考证主要集中于湖湘地区的山川地貌,尤其是古今水道源流的分合情形。如《湖南文征》所收朱景英《潕水考》一文,对沅水和潕水的流域范围进行了详细考证,罗汝怀加案语云:“沅潕二水,混为一江。今武进李氏所刊《阳湖董氏图》,及天台齐氏《水道提纲》皆然。缘所据旧图,相沿已久也。其实沅江故在,而为清水江之名所夺,故并沅于潕。二考据水经析其二原,以今所称清水江者,为沅之上原,足正从来之误。”[8]1849罗氏所作补充,提纲挈领,条理分明。
此外,对于一些无法确切考证的内容,罗氏以存疑处之,以俟后考。如其根据志书所收谢文祥《培养君德疏》一文,虽内容与《明史》所载有异,然因证据不足,无法辨别真伪,只得存疑,由此可见罗氏考据之谨慎。
总之,《湖南文征》虽有些许不足,但它极大推进了湘人的文献整理事业,弥补了湖湘地域“有诗无文”的缺憾,其在省域文章总集编纂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参见章曼纯《湖南的地方艺文总集》、蒋江龙《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张晶萍《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研究》、夏剑钦《罗汝怀及其<湖南文征>》等论著。
2.邓洪波教授在点校版《湖南文征(全十册)》的前言中也有对二书承续关系的说明,文章在此基础上详加阐述。
3.《湖南文征》卷首有李瀚章序。按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五(清光绪六年刻本)有《湖南文征序代》,可知李瀚章的《湖南文征序》实为李元度代笔。
4.关于湖南单独建省的时间,学术界未有定论,主要有康熙三年说、康熙六年说、雍正元年说、雍正二年说、雍正七年说、康熙三年分治说、四步骤分省说、无明确时间说、未分省说。文章所谓康熙三年建省,参见周宏伟著的《湖南政区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