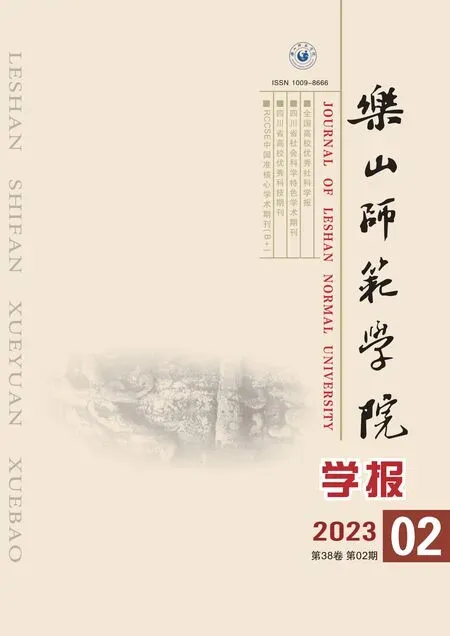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及其文学批评
2023-03-27蔡伦
蔡 伦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论诗绝句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独特样式,其以规范的绝句体式谈诗论艺。自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伊始,经历代诗人的书写与开拓,至清代已经非常完善与成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也更加精细,大到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格,小到某位诗人的一首诗歌,皆可作为其论述内容。从整体创作情况来看,以精辟的语言对有显著成就的诗人及其诗歌进行品评仍是清代论诗绝句最重要的创作形式。苏轼作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自然会被清人重点关注并成为其论诗绝句中重要的书写对象,这其中不乏新材料、新观点,但学界尚未对此有所关注与讨论。本文拟对清代论诗绝句中苏轼的人物形象、诗文创作批评以及所涉及与苏轼相关的文学话题进行考察与探讨,尽可能清楚地展现出清代诗人于论诗绝句中对苏轼的书写与评价,以期对苏轼的研究能有所补益。疏漏悖谬之处,祈望方家斧正。
一、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
苏轼以其卓绝的文才、极高的文学成就和高洁的人格品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他鲜明的人物形象也被历代文人书写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最不应被忽视的便是文论作品中对其形象的刻画,文论作品中对苏轼形象进行塑造的同时往往涉及其文学创作,因此解读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其人,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而且从清代论诗绝句对苏轼形象的描写中,我们也可进一步一窥苏轼及其诗文在清代的接受与传播情况。
(一)文才卓绝,文学成就卓著

并称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式中常见的一种,其中蕴含着对作者文学成就、文学特色的考量,见证着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文学风格的取向,对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就常在论诗绝句中把苏轼同前代大诗人并称来谈论苏轼的文学才能和文学地位,如“英灵名代各无俦,叵测人间学语流。李杜韩苏今接迹,君看壮缪是猕猴”[4]282(焦袁熙《论诗绝句五十二首》其四十九)、“诗家第一俗难医,烟月文章语太卑。李杜韩苏墙数仞,涪翁倔强亦肩随。”[4]360(陈启畴《与晴峰鏊论诗十首》其三)等其构思过程同叶燮《原诗》中的“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6]9、“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6]51无二,皆是把苏轼与杜甫、韩愈等诗坛巨匠并称,从而衬托出苏轼卓绝的文才和极高的文学成就。通过这种方式夸赞苏轼文才与文学成就的还如“妙笔奇才孰比肩,东坡人巧合天然。诗文两造华严界,远配蒙庄近谪仙”[4]1405(朱庭珍《论诗》其十一),该诗谈及苏轼的诗文创作追求自然、天成,能够达到法界观思想中所阐释出的融通无碍的境界,其诗文艺术高度在迩能与李白相匹敌,在远可直追庄子。诗中把苏轼与李白相提并论,这种提法在清代也颇被认可,另如毛瀚丰所言:“万古骚坛止二仙,老坡何必让青莲。弇州倔强终方悔,到死犹看手一编。”[4]1606(《论蜀诗绝句》其七)李白被誉为“诗仙”,苏轼亦有“坡仙”之称,这反映出晚生后学对李、苏二人文才之高下、文风之相似的考量,展现出后人对苏轼文才和其诗作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即使是持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一代文坛盟主王世贞,在病重期间,仍“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7]。
(二)尽忠于君,难易忧国之心
苏轼曾在《与王定国》书信中表示:“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今见定国每有书,皆有感恩念咎之语,甚得诗人之本意。仆虽不肖,亦尝庶几仿佛于此也。”[1]1517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后,仍效仿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可见其忠君报国、存心忠厚的一面,因而宋孝宗称:“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5]2385通过上述可以看出,苏轼不仅自表其忠君的心迹,且其忠诚得到了当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后代诗人对此也有清晰的认知,并于诗歌中对苏轼的这一品格给予赞扬,如“髯苏名节继欧公,谈笑犹生四座风。信有奇才能靖献,不忘君处见孤忠”[4]1066(王惟成《论唐宋诗绝句诗四首》其十一),言明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怀有高尚的节操,有着尽忠于君之心,即使身处困境,也希望能够为君分忧。又如“淋漓大笔是东坡,廊庙江湖足咏歌。爱国真心随处见,二程訾议竟何如”[4]777(王祖昌《论诗绝句》其二),谈及苏轼无论是身在庙堂之内,还是身处江湖之远,始终怀揣着一颗忠君爱国之心,颇似范仲淹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品格。另如“奇才早已动官家,泪落金莲烛上花。一样能知不能用,汉文皇帝贾长沙”[4]1328(王柘《读苏文忠公集》其一),该诗把苏轼与汉代名士贾谊相提并论,更多是考量到两人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均怀有赤诚之心。贾谊受到打压与排挤被贬后,仍然心忧家国、一如既往地上疏劝谏皇帝,不易其忠君爱国之心。王柘认为苏轼在这一点上与贾谊颇为相似,其虽不被重用,但忠君爱国之心并没有随着其被贬谪而消散,陆游曾评价苏轼:“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8]一如徐旭在《题东坡诗集》中所言:“四谪频频出翰林,江湖冰蘖苦沉吟。湘累骚谏公诗谏,不听原非圣主心。”[4]1696论说了苏轼即使被贬、身处窘境,也不忘像屈原一样以诗作来规劝皇帝。除上述之外,还如“鲲鹏奋击才如海,云水先摇似若仙。自是眉山诗格好,一生忠孝半生禅”[4]1648(许愈初《论诗绝句》其十三)、“东坡健笔挽千钧,独有涪翁许及门。尤爱斯人玉无玷,儒林循史亦忠臣”[4]1687(袁嘉谷《春日下睨小饮薄醉尚论古诗人漫成十二首》其七)、“海外何愁瘴疠深,华严法界入高吟。宣仁龙驭回天后,谁见孤臣万里心。”(沈德潜《书东坡诗集后》)等均揭示了苏轼的忠君爱国之心。
二、对苏轼诗文的批评
以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评价或阐释所论之人的诗风或诗歌特点是论诗绝句应当承担的文学使命,如杜甫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9]评点庾信后期诗歌健笔凌云、纵横开阖,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10]338议论陶渊明诗歌不事雕琢,清新自然的风格,皆始终秉持着论诗绝句这一文学批评的底色。清代论诗绝句明显继承了这一文学批评功能,其中对苏轼诗歌的探讨多集中于苏轼和韵诗的创作、佛学对苏轼创作的影响和苏诗风格。
(一)论苏轼和韵诗创作
黄维申在《病中读宋四家诗各题一绝》(其一)中论苏轼:“两宋骚场一老魁,少陵工力谪仙才。更从和韵论心巧,元白真从末座陪。”[4]1300诗中所谓“和韵”是古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指依照别人诗作的原韵作诗。按照徐师曾《诗体明辩序说》中所说:“按和韵诗有三体:一曰依韵,谓同在一韵中而不去用其字也;二曰次韵,谓和其原韵而先后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韵,谓有其韵而先后不必次也。”[11]三者之中以次韵诗最为难作,却也是古人和韵诗创作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苏轼的次韵诗就有七百余首,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黄维申于其诗中称苏轼和韵诗的创作成就已经超过了使此类诗歌达到初步繁盛的元稹、白居易二人,这并非虚言,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有言曰:“次韵一道,唐代极盛时,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陆,因难见巧,虽亦多勉强凑合处。宋则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长篇押至数十韵者,特以示才气过人可耳。”[12]是言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在次韵诗的创作上颇具技巧,但也有较多勉强凑泊之处,而苏轼以其卓越的才气弥补了元、白、皮、陆的不足,并且在次韵诗的创作上有较大的开创。总的来说,苏轼在和韵诗的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热情与精力,创作数量多是一方面,形式上也丰富多样,出现了又和、再和、重和、自和、追和古人等丰富的形式,如李呈祥言之“垂老投荒自和歌,渊明诗后有东坡。当时只酌杯中酒,最苦群贤议论多”[4]205(《亿与复阳论诗途次口占却寄》其八),便是谈及苏轼追和陶渊明之诗,苏轼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后,视陶渊明为知己,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进一步向陶渊明靠近,不仅在为人上“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于诗歌创作上也欲和尽陶诗乃已,因此创作了不少可称经典的和陶诗。清人徐兆英于《读东坡诗集》(其四)中亦有“便便腹笥世无伦,和韵天成叠韵神,自是才人爱游戏,后来莫作效颦人”[4]1430之语言及苏轼和韵诗的创作,他强调苏轼博学多才,把和韵诗的创作视为文字游戏,往往一套诗韵可次韵多次而不落俗套,一如南宋费衮所云:“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13]以叠韵诗创作之工衬托出东坡才大力雄。杨光仪在其论诗绝句中谈及此事时亦有言曰:“依永和声见化机,岂缘一字关新奇。东坡言语妙天下,开卷偏多叠韵诗。”[4]1235(《论诗五首》其三)言明了苏轼叠韵诗数量多的特征。由上述可见,苏轼的和韵诗数量多、创作技艺精湛的特点已为清代诗人所共识。
(二)论佛学对苏轼创作的影响
苏轼年少得志,其才能受到宋仁宗和欧阳修等人的高度评价,但后因政治斗争而一度被贬,使其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除了短时间的低落消沉外,其对待生命的态度总体上来说是旷达乐观、洒脱随性的,这与其接受佛老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反过来,佛老思想又对其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论诗绝句中对此亦有深刻地揭示。
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的苏轼,在黄州遭遇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在反思往昔、返观内照的过程中,他对佛学的接受较之前更进了一大步,其《黄州安国寺记》中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1]391-392言明自己愿意诚心归佛,洗净杂念、消除尘俗的妄想,成就自己的虚寂清净之心。其诗如“我老人间万事休,君亦洗心从佛祖。手香新写法界观,眼净不觑登伽女”[5]952(《送刘寺丞赴余姚》)、“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同万事非”[5]627(《和子由四首·送春》)、“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5]1326(《南都妙峰亭》)等皆借助《华严经》中“法界观”的佛学思想来阐释自己泯除机心后淡泊宁静、圆融无碍的精神境界,这也同样表现出苏轼把佛学思想援引入自己诗歌创作之中的现象,恰如周曾锦论诗绝句所言:“佛语为诗始长公,华严字字走霆风。后人翻被刀圭误,堕入泥犂第几重。”[4]1695(《冬日读书偶题四绝》其二)佛教华严法界观之于苏轼的文学创作而言,确有重要的影响,钱谦益有语:“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 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14]而清人在他们的论诗绝句中也表达了与钱谦益相同的观点,认为《华严经》等佛教经典对苏轼诗文创作影响深远,如朱庭珍言东坡“妙笔奇才孰比肩,东坡人巧合天然。诗文两造华严界,远配蒙庄近谪仙”[4]1045(《论诗》其十一)。又如“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年在,字字华严法界来”[4]237(《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其三),阐明苏轼被贬后受佛教“随缘自适”“随心任运”等观照方式的影响,其诗文常能够达到浑然天成的境地。苏辙评介其兄黄州时期诗作时亦曰:“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15]揭示了苏轼受佛老思想影响,诗文水平因此得以提高的事实。清人论诗绝句还如“海外何愁瘴疠深,华严法界入高吟。宣仁龙驭迴天后,谁见孤臣万里心”[4]382(沈德潜《书东坡诗集后》)、“华严楼阁笔端生,万斛源泉任意倾。更有大名兼李杜,乌台琼海任游行”[4]429(王昶《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四十六首》其十六)等谈到苏轼被贬海南后遭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磨难,他通过接受佛学思想来淡化精神上的悲痛,同时也积极把佛教思想与诗歌创作相结合,这使得其诗歌书写内容得以拓展、诗文思想愈加深邃,自身人格得以完善。
(三)论苏诗风格
清人论诗绝句还对苏轼诗歌风格进行了讨论与揭示,如“宗派江西总葛藤,横流沧海意难凭。苏豪黄劲都堪法,石滑崖悬要善登”[4]1070(《跋东坡先生诗后四首》其一),通过对比苏轼与黄庭坚的诗歌风格,突出了苏诗之“豪”。苏轼是“豪放派”大家,其诗歌常有豪放超脱、旷达不羁之作,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5]2366(《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诗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遇赦北还之时,全诗表现了其九死不悔的豪放气概和坚定自信之心,语中显有对昔日政敌的调侃和嘲弄,颇似刘禹锡“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16](《再游玄都观》)之语。另如“二苏文藻壮诗坛,豪气堪吞陆与潘。每笑世人徒耳食,谬将子美比都官”[4]1614(邱晋成《论蜀诗绝句》其六)、“泥沙俱下似黄河,苏氏文章霸气多。纯以气行得天趣,任他磨碣命宫磨”[4]1036(蔡寿臻《论诗绝句十首》其六)等都对苏诗豪放的一面进行了揭露。除此以外,清人朱庭珍还论及苏诗呈现“自然”“天成”的风格,其诗云:“妙笔奇才孰比肩,东坡人巧合天然。诗文两造华严界,远配蒙庄近谪仙。”东坡文才卓荦,作诗为文“随地而出”,“行止天成”,能够达到融通无碍的境界,他自己也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5]1525(《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认为天工自然之美是诗文、绘画创作的至高境界。鉴于此,朱庭珍在其诗中把苏轼与推崇“自然”“浑融”的庄子、李白相提并论。另有徐兆英《读东坡诗集》(其二)云:“诗成无缝似天衣,好句如珠世所稀。信口拈来君勿学,恐贻画虎不成讥。”[4]1429也是说苏诗浑然天成、不假雕琢,为世所重。并劝诫后来者如无苏轼之才,切勿盲目学习这种创作方式,不然恐留下“画虎不成反类犬,刻鹄不成终类鹜”的笑柄。此外,徐兆英还谈及苏轼诗词创作不拘成法,诗曰:“东坡著作文居首,次第诗词各擅长。诗妙原非拘格律,词高从不泥宫商。”[4]1429(《读东坡诗集》其一)是说苏轼作诗虽不拘格律,诗歌境界却高妙,作词不泥于音律,但词作艺术水平高绝,而这同样是建立在东坡才华横溢的基础之上的。
三、评述与苏轼相关的文学论题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围绕他自然会产生许多与文学相关的话题,后代文人多有对之进行阐释或论争的,清代诗人的论诗绝句就对苏轼“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历程和元好问对苏诗的褒贬态度等诸问题给予关注与讨论,这也值得我们留意并作进一步阐释说明。
(一)揭示苏轼“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言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7]612-613此文是欧阳修为梅尧臣所作,言其郁郁不得志,遂而忧思感愤郁积于胸,于是“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其诗因此能“披霜掇孤英,泣古吊荒冢。琅玕叩金石,清响听生悚”[17]54。阐释清楚了士人命途的偃蹇之于文学创作的正面影响,后人多以此语论及诗家,如苏轼就有“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何当暴雪霜,庶以蹑郊贺”[5]159(《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5]1750(《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等此类论调。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来,“穷而后工”似乎适合诗坛中诸多身处困窘而文学成就突出的诗人,但这一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宋代天才诗人苏轼?我们不妨从清人对苏轼的相关评价来探究这一问题。秦焕在《苏东坡》一诗中有言:“烛照金莲宠遇多,无端海外谪东坡。文章大得波涛助,才信沉沦是琢磨。”[4]1280苏东坡正值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因党争屡遭贬谪,而这苦难的贬谪经历使其诗文创作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只是该诗的最后一句用了“琢磨”一词,意义稍显不同,该词出自《诗经·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8]是谓卫武公研究学问、陶冶品行讲求精益求精,而秦焕用之形容苏轼,意指东坡诗歌创作水平本就高超,而曲折的经历使得其才能发挥得更为彻底,其作品艺术水准得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另有宫尔铎言:“儋耳归来两鬓丝,纵横健笔老尤奇。心同孤月明天表,一任浮云过眼驰。”[4]1459(《读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爱其文词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义漫成此作以质知音》其七)此诗既言明了苏轼虽历经沧桑却不改其忠君爱国之心,也通过“纵横健笔老尤奇”一句阐释出儋州困窘的经历使得苏轼本就卓越的创作水平得以更进一步,登峰造极。综合上述来看,以“穷而后工”来形容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其极高的文学成就间的关系是合适的。
白居易在《序<洛诗>》中有言:“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19]此论意在说明诗人数奇、多处穷困,而优秀诗歌又往往出于诗人困窘之时。难以否认的是,苏轼诗文艺术水平之高超、文学成就之突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在贬谪、迁徙的过程中尝尽苦涩、受尽冷落,内心郁积着悲愁、愤慨,待得喷薄而出形之于诗,往往是优秀的诗篇,恰如洪亮吉在《读史六十四首》(其四)中所言:“诗案曾留御史台,憸人亦转叹奇才。雄文却要蛟龙助,不枉先生过海来。”[4]635在洪亮吉看来,恰是不断被贬的悲惨遭遇使得苏轼卓绝的文才得以发挥出来,进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另如林思进于《论蜀诗绝句》(其七)中言:“坡老文章擅古今,南荒九死尚长吟。何人解向黄州后,一读华严辨浅深。”[4]1671苦难的经历不仅丰富了苏轼的人生阅历,改变了他对生命的思考方式,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创作理念与创作倾向。乌台诗案后,逃脱死地的苏轼并没有忘却自己在牢中的屈辱与惊恐,他在黄州对以往进行痛切反思,并在接受老庄佛禅思想的基础上从精神层面对自己进行超越,这种思想与精神层面的改变促进了苏轼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最明显的便是“随物赋形观”的提出,在此种创作观念的影响之下,创作主体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性,进入主客交融、物我合一的浑融境界,从而创作出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验之于诗,其于黄州所作之《红梅三首》《东坡八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诗,较被贬之前诸诗作,诗笔更显精致流利,诗境愈加清旷简远。
(二)解读元好问对苏诗的评价
元好问曾在其《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二)中评价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10]339现在看来,遗山此诗确有语焉不详之处,以致后人在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争议,争议集中体现于元好问对于苏、黄诗歌的褒贬态度上,而这一问题亦被清代诗人置于论诗绝句中进行讨论。譬如沈德潜在其《戏为绝句》(其六)中言道:“端明学士渭南伯,两宋才华此独优。后人嗤点太容易,沧海何妨有横流。”沈德潜在肯定苏轼为北宋诗坛中绝无仅有之诗人的基础上批评那些随意嘲笑挑剔前贤的后辈诗人。“沧海何妨有横流”一句是通过解释苏、黄开创新体对诗坛及以后诸家并不造成坏的影响来替苏轼推责,回护之意十分明显,此外,其在《说诗晬语》之中对此亦有论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元遗山云:‘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嫌其有破坏唐体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20]沈德潜不仅认为苏轼继韩愈之后又为诗歌开辟了新境界,而且不满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认可苏轼在突破唐体方面所作的贡献,此论与其上述论诗绝句互为表里。清人邓镕对此问题亦有言论:“横流沧海到坡仙,衣钵无人可更传。除却聪明真佛子,学来终堕野狐禅。”[4]1700(《论诗三十绝句》其二十一)邓镕针对元好问对苏诗的评价,不作“诗坏于苏、黄”之解,而是认为“沧海横流”之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后人没有苏轼之文才却亦步亦趋、专事学苏,甚至画虎类犬、东施效颦所致,便如翁方纲在《评陆堂诗》中言:“论诗唯元遗山于苏诗有沧海横流之虑,此与窦论褚书正同。”[21]所谓“窦论褚书”是指窦臮在《述书赋》中言称:“(褚)河南专精,克俭克勤,……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22]窦臮因褚遂良书法开唐代风气之先,就将后学末流浮薄书风之形成亦归责于褚遂良。翁方纲认为把宋诗“沧海横流”归责于苏轼,就如同把唐代书法乱象归罪于褚遂良一样,是不合理的。另有许愈初在《论诗绝句》(其十六)中云:“沧海横流事可嗟,江西社里太纷拏。论诗不拾苏黄唾,始信遗山是大家。”[4]1649不难看出,许愈初的论断与邓镕颇为相似,他认为正是由于江西诗派中人拾苏、黄之牙慧导致了宋代诗坛脱离正轨、纷乱混杂的局面,而元好问于苏、黄之后诗坛横流泛滥之际,不习苏、黄之遗韵,却能拨开迷雾,别开生面,此论颇似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二)中对江西诗派的鄙薄之语:“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10]398此外,如“狡狯神通骇世人,苏门真惜少功臣。横流沧海今谁挽,莫纵狂炎更益新”[4]1419(陈炽《效遗山论诗绝句十首》)、“文人自古爱幽锼,东野何妨唤作囚。一派苏门诗百态,争教沧海更横流”[4]447(陈启畴《论诗十二首呈裘慎圃邑宰》其六)、“宗派江西总葛藤,横流沧海意难凭。苏豪黄劲都堪法,石滑崖悬要善登”(李遐龄《跋东坡先生诗后四首》其一)等论诗绝句皆就这一争议展开解读与阐释。
四、结 语
清代诗人立于文学批评的角度利用论诗绝句言简意精、凝练含蓄的长处对苏轼及其诗文进行品评,并对前人已经发表了的关于苏轼的评论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与阐释,同时又有自己的见解与看法,虽是各抒己见,但也能够总结出共通之处,这对研究苏轼及其诗文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论诗绝句中有关苏轼的描写及文学批评对于当今苏轼研究来说还是较为新颖的材料,能够为我们研究苏轼提供新的视角与切入点,因此其具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