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中看梅娘小说的女性视角
2023-03-27白静
白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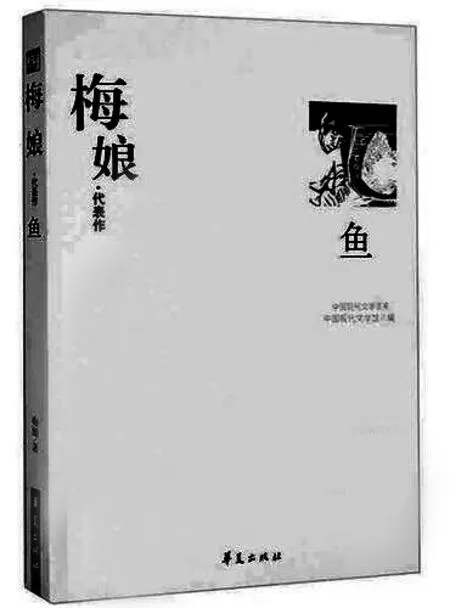
梅娘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优秀的女作家,她出生于东北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其父孙志远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生母遭到孙原配夫人的嫉恨,被迫出走。梅娘早早地遭受了“没娘”的痛苦,在继母的冷眼中郁郁长大。身世的辛酸激发了梅娘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更使她对当时沦陷区女性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关怀,并作出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带有梅娘自己的影子,有着相同的被压迫的命运。
在当时,梅娘应该是较为独特的一位。她既不同于冰心的“爱的哲学”的说教,也不同于庐隐的“恨的哲学”的哀鸣。她的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女人,却流出对人的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利,却流泻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利的向往和呼唤”。①梅娘关注人,更关注女人的命运,她的小说具有显著的女性主义特征,其代表作品“水族系列”之一的《鱼》则最能反映她的这种写作倾向。透过《鱼》,我们可以看出梅娘小说独特的女性视角。
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鱼》中的芬就读于女子高中:女孩子们被送来读高中,只不过是为了识两个字,高中毕业就等于失学。而高中生活如何呢?“住校的学生除了星期日和例假是不准出去的,即或出去也不过是买点东西看回电影。隔绝了一切和外面交接的机会,那样蓬勃地生长着的活泼的姑娘们,那样尼姑似的生活是怎样捆压了丰富的还没有经过折磨的纯洁的感情呀!”这就是当时的高中生活,女孩子们在压迫下“神经都尖锐着,听着一点爱情的故事便都借着别的话哄笑起来”。她们“因为生活圈子的束缚和年龄的要求,多半把没处发泄的蓬勃的感情倾向于年轻的先生们”。在梅娘的眼里,这一群要爱却无从爱起的女孩子是可怜的,她们刚刚迈入了社会,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却在这种流转变迁的时代,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日伪统治下文化高压政策的桎梏和压迫。和其他作家不同,梅娘不但看到了东北沦陷区人们生活的苦痛挣扎,更看到了新旧思想撞击给女性带来的精神阵痛。
再看看芬的家庭。芬上高中是因为母亲的一力主张,母亲去世后,“没有母亲的家庭比牢狱还苦”,芬感到自己像要被活埋了一样。她渴望工作,渴望自由的生活,却是不允许的。她渴望恋爱而不能爱,因为“她有一层门关闭着”——那就是家的阻挡。当芬忍不住恋爱了时,“一切比预料中还残酷的责难落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盘桓在死亡、被逐、饥饿、责打上”。②这一切,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那位“狂人”的处境。芬被命令嫁给父亲为她挑好的只知道遛狗的夫婿,这是接受过新思想影响的芬所不能接受的。她勇敢地走出了家门,走向了似乎可以给她提供一切的林。
林又给了芬什么呢?“我第一天的快乐就被打了折扣……我摒弃了一切的娱乐,我尽力爱他……我的丈夫对我一天一天地冷淡下去,常常不肯回来……这些天我受的剧烈的踢打都是为了这原因的……”②她从小生长在牢狱一般的家里,被送到尼姑庵似的高中仅为识两个字,高中毕业便要被安排嫁给一个只会遛狗的纨绔子弟。她就如同一只被圈养的小狗,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只能听从主人的安排,必要时被送上交易所换取主人的利益。但毕竟,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她说“我做的事情并没有错,我需要爱”,她从一个牢笼走向了另一个牢笼,她没有得到应该有“尊重、责任和了解”③的现代意义上的爱,而是上演了一场“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悲剧。在梅娘看来,女人的路总是窄的。这种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同样存在梅娘的其他作品中。
《蚌》中的梅丽,作为显宦巨贾白参议员家“庶出”的小姐,她提心吊胆地生活在种种勾心斗角之中,将自己缩了又缩,小心翼翼地渴望自己的宁静。中学毕业后在税局当职员,与同事琦偷偷相爱,却被父亲当作礼品许给了得了一身脏病的朱家少爷。家庭的阻挠、同事的挑拨离间以及小报舆论的飞短流长,终于导致梅丽爱情的破灭。《小妇人》中聪慧、美丽、坚毅的凤凰与袁良私奔,不久即有了孩子,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与窘迫的家庭经济中,消瘦了容颜枯萎了感情,日渐与丈夫发生矛盾,而丈夫的冷漠与外遇差点毁了那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家庭。《蟹》中那个对男子甚至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看法的小翠,虽知道男人对女人都抱着玩玩的心态,却最终没能逃出男人的魔掌,被父亲出卖给孙三爷当玩物。《小广告里面的故事》中的女子,被男友从母亲的怀中诱惑出去随即遭弃,因逃难投奔到姨爹家,结果却被姨爹用来征婚骗取钱财。她反对姨爹结果遭到毒打,却并没有放弃。她爱上了小祥,欲把“渴望爱情而不得的脆弱的女儿心”交给他,希望小祥能帮助她逃出姨爹的掌心。但是,懦弱的小祥能否给她以幸福呢?小说没有告诉读者她最后的命运,这恐怕也是梅娘在对女性命运关注的同时而为读者留下的最后一线希望吧!
正如《鱼》中芬所说:“我做的事情并没有错……我并没有侵害谁,我并没有给谁不便。我做的,都只有一条路可走的。”她们无意触怒谁,只是具有“人”的意识,想要争取“人”的生活,便被家庭、社会所不容。在父家,她们的归宿就只有被当作交易品送出去。逃离父家,走进夫家,一样无幸福可言。她们“从家里走出来,其实跟着就得走进另一个家去,一样地洗衣服、做饭,还得看孩子,到天边也得扮演受欺的角色”。就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④,她们在没有掌握经济权、不能摆脱男权意识及宗法制度时,出走也只是痛苦地挣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梅娘从自己的身世及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针对女性的命运问题,借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口,发出了“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的疑问。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鱼》中的芬可谓经历了两次觉醒,这首先表现在“人”的意识的觉醒上。
芬在家要规规矩矩地吃饭、陪姨娘摸牌,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小姐生活,不许和外界有自由的书信来往,更不用说自由恋爱了。她厌烦、痛恨这种无聊、沉闷的生活。她渴望自由,时常想去寻找另一种较为充实自由的生活。在人的基本需求中,芬缺少了“被尊重”,缺少“爱与归属感”,更不要说“自我实现”。她反对父亲为她包办的婚姻,反抗自己的从属地位,争取做“人”的权利,从而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父家的大门。这种抗争,是芬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是她的人生中自觉时刻的到来,也体现了梅娘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及人的意识觉醒的思考。
芬从父家走进夫家,受尽周围人的冷眼与丈夫的折磨,但只能忍气吞声,因为芬清醒地认识到“我是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一个做了人妻的女人,人们不拿我当人,只当我是林省民的一个附属品”,“这社会承认男人应有一切权益,压迫我,虐待我”。但最终,芬深刻地看到了自己回到林家后的生活,同时也明白了林所给予她的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如同富足的人随手施舍的面包一样,她决然地选择了另一条路。她说:“真正的生活不是依赖别人所能获得的。我不能忍耐目前的生活,就只好自己去打开另一条生活的路子。”她明白,“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出来杀头,不然就郁死”。所以她迈出了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中国妇女所不敢迈出的坚定的步子,她是现代中国又一个觉醒的更为进步的娜拉:“我要教育起我的儿子来,我要教他做一个明白人。这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女人就少吃一份苦。”这是芬的第二次觉醒,是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关注上,梅娘的思索是深刻的,她几乎喊出了女性主义的最强音。如《动手术前》中的女子所说的:“你们握着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横行,欺凌女人,逼迫女人,逼得女人不能不以她仅有的身体去换取生活的时候,玩弄她,嘲笑她,然后摒弃。然而你们是对的,没有一个男人承认自己是在间接、直接地摧残着女人……什么女人的贞操,让它见鬼去吧!”甚至如《蚌》中的梅丽所说:“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鸡,不如去做马路天使好呢。”梅娘清醒地观察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同时也在思考女性的出路。她说:“我不能走我娘、我大姐那生活中锦衣玉食、精神上备受欺凌的老路,她们全部的生涯证明:女人只不过是一条藤,只有依附男人,才能享受人世间的荣华。而她们的荣华,对我毫无价值。”⑤梅娘的这种思考与五四时代同步却又远远高于同时代,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对女性本体的审视
《鱼》中的芬不满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抛却一切,孤注一掷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却不想误入被爱情包裹的又一男权专制的牢笼,不但使自己的爱情美梦化为泡影,更使身心备受摧残。梅娘对她笔下如同芬这样的女子是爱惜的、同情的,但同时又有着很多的无奈和叹息——女性本身的软弱性。芬有反抗的勇气和行动,这是梅娘所赞赏的;但芬将自己所有的梦想寄托在一个相识不久却糊里糊涂相爱的男人身上,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从高中毕业而面临失学、嫁人,芬当时的心情可谓低至谷底,她急于求救,希望有一个机会,有一种力量使自己获救。这正是芬最为脆弱的时候,林省民轻而易举地俘获了芬的爱情,堂而皇之地使芬顺利落网,成为任他宰割的案上之鱼。芬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清,男权社会中几千年的熏陶,早已使年轻的、年老的男人掌握了控制女人的本领。即使落入不幸的婚姻,她也没有早早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却只是“努力做一个好的妻子”。这种将幸福婚姻视为人生全部目标的追求,正是芬人格不能完全独立的软弱依附心理的体现。庆幸的是,芬最终看到了一条自强不息的道路。
梅娘的这种惋惜、心痛在《蚌》中有同样表现。白家大小姐梅丽驾驭不了自己的感情,缺乏毅力去反抗、报复压迫她的一切,才导致了难堪的悲剧。而《夜合花开》中美丽的少妇黛黛,不满足于整日里无所事事的生活现状,厌恶眼里只有钱而缺少对她真正理解的丈夫日新,却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少奶奶”的富裕生活条件和身份;知道丈夫在外面捧女伶,非但不生气,反而有了“终于有理由找一个情人”的想法。这种自欺欺人的抗争,只能使她如同陷入蜜罐的蝴蝶,愈陷愈深而无法自拔。所以,她也只能徒然羡慕亲妹妹黛琳的热情和活力,自己继续留在锦衣玉食的小生活里自哀自怜。
梅娘的小说中,这些美丽纯情的女性,有新思想却也有着回归心态。不管是芬还是凤凰,她们虽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为追求个人幸福和爱情而毅然出走,却走进了以“爱”编织的牢笼。她们没有像娜拉一样要求将自己还给自己,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认。“寻找爱的家园只是现代女性在妇女解放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妇女解放的真正标志应该是妇女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实现。如果把自身的解放完全寄托在男性的承认和爱抚上,或者把男性的爱视为解放本身,只会导致新的人格依附。”⑥所以说,梅娘的视角是广阔深刻的,她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心痛,是悲天悯人的梅娘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自身更为深刻的思考。
结语
梅娘以自己幼年的经历为参照,用敏锐的目光和细腻的感情观察、体悟、思考五四前后沦陷区女性的命运及她们的出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个个都是她所关怀怜悯的对象。她们美丽、单纯、热情,接受过五四的洗礼,追求光明幸福的生活,却又受到男权的压迫。她们或如鱼,因为想要脱离苦海而被人捕捞,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或如蚌,“潮把它掷在滩上,干晒着。它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人家啄去了”②;或如蟹,“捕蟹的人在船上挂着灯,蟹自己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了已摆好的网里”。②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梅娘也肯定了这些女性珍贵的反抗意识,鼓励她们摆脱封建罗网的束缚,勇敢地走出来,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而战斗。但同时,梅娘并没有盲目地为她们的战斗唱颂歌,而是清醒地看到了她们作为女性本身的软弱性。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她们受“纤弱柔媚”的教诲,努力将自己塑造成“瑰丽飘逸、仪静体闲”的佳人。而这些,只能让她们于无形中将这些“标准”内化,把自己反抗的手脚捆住,成为毫无独立人格的牺牲品。梅娘不但看到了同时代女性的悲哀,还揭示了中国广大女性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她以温婉而不失刚强、朴实而不失深重的写作风格和独特视角,“敏锐地从姿态万千的社会表层透视两性的不平等及女性生存状态的艰难,截取并予以放大,以其中女性地位低下和命运的不幸来突出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长久以来的失衡”。⑦这是梅娘小说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