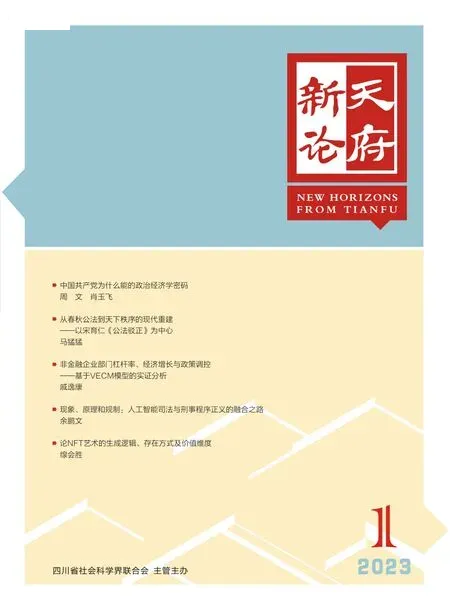数字社会下的审美泛化危机
2023-03-23危昊凌
危昊凌
新世纪以降,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美学讨论点燃了学术界对艺术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探讨热情。数字媒介护航下的大众文化一路凯歌,被纳入市场化进程之中的艺术与审美却叫人忧心忡忡。美在今日已降格至粉饰现实的胭脂粉黛,对美的追求亦不再是对精神超越与心灵自由的向往,而是跌落为一种提高生活品质的合理诉求为消费活动提供话语修饰,难怪有学者直言:“‘审美化’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把握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命题。”(1)金惠敏:《图像—审美化与美学资本主义:试论费瑟斯通“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及其寓意》,《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在数字社会被韩炳哲指认为同质化社会的当下,审美泛化所牵扯的诸多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资本、技术、大众文化等因素经由数字媒介的组织整合在经验与感受层面侵蚀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泛审美化”的讨论并未因时间的消逝而丧失理论张力,与此相反,数字生存困境与同质化社会的发展为这个问题的思考注入了动能。
一、纯审美的淡出与泛审美的打造
随着技术理性的高扬与资本市场的介入,固守“审美本质主义”的精神意愿在大众文化场域中显得孤立无援。数字时代迎来了快感中心主义的思想宰制,消费主义将一切视作可消费商品的同时也对艺术采取了降解式处理,超越性与先锋性必须以商业化妥协的代价换取进入文化消费市场的门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相持勾勒出当今时代的文化图景:形而上的追思与典雅的审美趣味成为少数文化精英的特权,对物质享受与感官愉悦的渴求则构建起芸芸众生的文化趣味,传统美学中对于审美超越与精神空间开拓的向往让位于泛审美化的快感体验,数字媒介的兴起点燃普罗大众文化热情的同时也为社会话语改写艺术提供了某种可能。当浅层次的物质文化与消费者的宣泄欲求出双入对,审美活动便在更多时候以消费性享受的形式出现,文化工业被确立为以机械生产方式来创造“诗意”表现的消费话语体系。
人们目睹审美消费化的转向后耽于狂欢也好,陷于漠然也罢,关于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追问不会因大众文化的虚假繁荣而终止。自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来,关于日常生活与审美的讨论就捕获了无数学者的视线,在其思想被引入国内后,更是出现了论争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美学热潮。在国内学界向西方世界寻求智识来源的过程中,詹姆逊与韦尔施的思想大放异彩。詹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诞生的后现代主义,其主要表现特征就是商品化。在商品化的力量逐步渗透个人的日常领域及文化生活的过程中,艺术与生活间的隔阂被刻意抹除,文化工业开足马力的后果就是主体迷失在形象井喷的视觉文化之中,如他所说:“现代性的巨变把传统的结构和生活方式打成了碎片,扫除了神圣,破坏了古老的习惯和继承下来的语言,使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原始的物质材料,必须理性地对它们加以重构并使之服务于商业利益,以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它们加以控制和利用。”(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68页。詹姆逊将日常生活视作无声的战场,现代主义对本质、意义的追问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消失殆尽,丧失深度的快餐文化将认知主体悬置于能指符号的汪洋之中。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揭露批判不同,韦尔施更加突出了当下社会的“美学转向”,生活的美学化意味着“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3)沃尔夫冈·韦尔施: 《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页。。时尚潮流对社会现实的粉饰催生出一种“美学经济”,被商业窃取的“美”为消费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对美的追求并非过错所在,意图美化任何事物的时髦潮流才是“平庸之美”的幕后元凶。这种机械复制的美化行为消解了崇高和优美的可能,流于烂俗的精致走向了平庸和浅薄。韦尔施对浅层审美化所作的诊断指出泛审美化的导向必然以服务消费主义为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审美麻木”的现象。流俗于精致与平滑的艺术品丧失了颠覆观者的冲击力,可消费的艺术品温驯地迎合观者,通过将每一个自在主体转化为消费者,消费主义以物欲的餍足防范着反思出现的可能。
以上两种理论范式都透露出对审美泛化的隐忧,艺术的平庸性与消费性上升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先锋性的消解。在如今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的购买选择不再出于使用价值,而是更多带有符号价值的考量,消费作为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化艺术活动的创作与传播。商业文化对艺术审美的规训似乎已成定局,但美与艺术不应满足于扮演一位商品推销员的角色,极尽迎合之能事,抑或亲自入场,将自身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求博得顾客青睐。诚然,在灯红酒绿的消费漩涡中保持自律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移动媒介的兴起让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大众对“美的占有”早已迫不及待。当大众作为新的文化阶级高调崛起之时,占有美便成为他们确立话语权威合法性的文化象征。对此大众文化的拥趸者可能会提出疑义:为传统美学摇旗呐喊,究其本质不也是文化贵族维护自身趣味话语的一次努力吗?
这样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布尔迪厄对“趣味区隔”的阐释揭露出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区隔的同时,也为社会等级制度的维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男用小便池似乎难逃被搬进路旁一个无名公厕的命运,但艺术家与社会话语的保驾护航却能使它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高居于艺术殿堂之上。这一切都取决于精英阶层的谋略,通过将自己的审美趣味合法化与正当化,传统审美发挥起维护社会区隔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功能。这样的说辞赋予了大众文化打破文化等级制的解放功能,却夸大了大众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当泛审美化的渗透撬动了艺术现实存在的常数,当流行音乐与短视频软件俘获了我们的视听体验,当《羊了个羊》 《合成大西瓜》等魔性小游戏的沉浮起落正批量式收割我们的休闲时间,当高雅艺术被大众文化放逐出境,我们是该将大众文化视作打破枷锁的解放者,还是被技术与资本操纵的提线木偶?虚拟现实从不吝啬于为我们提供感官刺激,可商业化艺术却无力为个体的完满指示精神路径,娱乐艺术只是借助艺术的“审美”形式来填充当代人贫瘠的精神荒原。意义消逝时代的精神困境为审美泛化的假象所掩盖,与数字媒介的合谋更是缔造出“泛审美化”的现代神话,对格调与品味的夸耀正在制造新的“趣味间隔”。我们不由发问:当美学遭遇数字社会,是急不可耐地投身于文化狂欢中邀宠,自甘成为消费的修辞艺术?还是高扬美的内核与超越性,自愿与肤浅的现实保持距离?
二、关键词的转变:从“麻木”到“平滑”
技术以及文化产业的裹挟几乎是将艺术强制架离了熟悉的无功利场域,对漂亮外表的重视制造出审美与消费间的化学反应,美学不再是对技术进步的反思,而是在技术的依托下追名逐利。为美明码标价的举动彰显出消费主体的精神空虚,附庸风雅或是文化作秀都为审美泛化贴上文化贫血症的标签,审美在追求形式的过程中花样频出,结局就是在现实中愈发乏力。如何理解泛审美时代下的艺术与审美?不触及问题本质的批判与反思无异于隔靴搔痒,理解审美泛化之下的这场精神危机需要我们对几个关键词进行梳理。
首先是“麻木”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要归功于本雅明与阿多诺的敏锐洞见。本雅明直言今日我们正驶向“灵光消逝的年代”,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兴起,艺术原作与摹本之间的鸿沟被人为抹去,崇拜价值让位于展览价值。本雅明在论述“灵光”这一概念时展现出他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本雅明叹惋于机械复制对“灵光”的戕害,但另一方面本雅明始终秉持着对科技进步的乐观立场。虽然机械复制的广泛应用威胁着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但本雅明依旧强调“去灵光化”的进步作用。在本雅明看来,“灵光”的消失固然将艺术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但恰恰是复制技术的兴盛拉近了人们与艺术的间距,这也使得“人群”在作为文化工业消费者基础的同时也孕育着革命的潜在力量。如果说本雅明还对大众文化抱有希望的话,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就是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最严厉的批判者。在其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文化与艺术的生产,当商品的等价交换机制渗入艺术创作过程中,一种受启蒙的“快乐”取代了传统的审美愉悦。对大众文化与科技的态度不同造就了阿多诺同本雅明之间的理论分野。在阿多诺眼中,本雅明高估了机械复制艺术以及文化工业的进步意义。对电影的过分期待让本雅明忽略了电影革命性与娱乐性之间的龃龉,荧幕上转瞬即逝的电影图像“绑架”了观众的注意力,而悄然渗透的意识形态更是杜绝了观众做出批判性反应的可能。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文化工业“启蒙”了娱乐,通过将娱乐需求转化为商品,缺乏思想深度的“庸俗艺术”成为大众逃避现实的麻醉方式:庸俗艺术“缩短了人类与艺术之间的距离,并且一味地迎合人类的欲念。庸俗的艺术是肯定这个世界的,而不是摆出一种反叛的姿态”(4)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8页。。在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之下,“麻木”成为某些文化意图塑造的结果。通过对技术与感官感知的批判,阿多诺发现在文化工业的世界中,“娱乐至死”习以为常,而麻木不仁也早已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塑造人们新的生存状态:“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迫使劳动者墨守成规,迫使劳动者对诸如压迫人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5)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振聋发聩,但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还是改变了此前的诸多文化图景,“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6)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62页。大众文化的狂欢运动表明文化早已被资本五花大绑,商业逻辑强调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来实现文化与资本的联动,韦尔施发现任何商品只要挂上所谓“美学”的名头就能售罄一空。精神的朝圣之旅因贪恋沿途风光而丧失原初视野,泛审美化所带来的后果并非传统想象中“完成我们在世间的任务,实现人类的终极幸福”(7)沃尔夫冈·韦尔施:《超越美学的美学》,高建平、张云鹏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页。。“美的滥用”是韦尔施对审美泛化的基本看法,在他眼中,传统美学对美的一味肯定阻碍了我们对审美泛化负面影响的考察。对美的追求原则上包含心灵感性的一切感受,而流行文化只能以精神按摩的方式舒缓现代人紧绷的神经,“媚俗”化的审美趣味日益绚丽耀眼,美却逐步失去滋养个体灵魂的功能。当美堕落为装饰性的“漂亮”与“精致”,肤浅的感官快感只能生产出千篇一律的审美经验,泛化之美不仅陶醉于平面化的符号表演,它还要在日常生活的建构中显现和把玩自己,重复大量的感官刺激异化了真正的美,它所带来的只有麻木。
如果将20世纪看作灵光消逝的机械复制时代,那么新世纪便是数字技术的纪元,从机械复制到数字技术的“超复制”,大数据俨然成为俘虏人心的“世俗宗教”。大数据筛选为用户打造出数字伊甸园,身处其中的人们不断重复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根本无法遇见具有冲击性的他者,他者的消失带来了同质化暴力的肆虐,韩炳哲指出我们已步入积极社会的掌控之中。“平滑”作为积极社会的时代标签,谄媚式的“顺从”与“不抵抗”颠覆了对立他者的存在意义,通过消除否定性与颠覆性所带来的冲击,美也变得平滑起来。“平滑”在此处被赋予了与“麻醉”相近的含义:“它使感觉变得迟钝。欣赏杰夫·昆斯作品时的那声‘哇哦’也是一种被麻醉后的反应,这种反应与那种碰撞与被推翻带来的否定性体验完全不同。后一种美的体验在当今是不可能有的。只要喜欢、点赞跻身主流,那种只有在否定性才能带来的体验就会逐渐消失。”(8)⑤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红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页,第3页。“平滑”与“麻木”虽有诸多相似,但韩炳哲并非简单地沿袭前人故智,平滑不仅被其针砭为麻痹灵魂的诡计,还被视作积极社会中的个体存在模式。韩炳哲在此对数字社交媒体做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分享”与“点赞”是使交际平滑化的手段,避开消极性的感知意味着愉悦与舒适,否定性的抽离使“超交际”在同者间飞速运转,交际、信息的顺畅流通为资本加速循环制造了可能。
否定性是构成艺术内核的关键。在伽达默尔眼中,艺术的否定性是超越“自己臆想出的感官预期”的存在,艺术作品迫使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每一次艺术体验都是作品同主体的对峙与颠覆。韩炳哲指出以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为代表的平滑美学旨在展现平滑的表面与直接的效果,由于缺乏引起距离感的否定性,观者面对平滑表面的雕塑时会产生一股触摸的“触觉强迫”。平滑的积极性消除了美学批判的静观距离,昆斯的作品拥抱任何一个欣赏作品的人,这类平滑艺术显然“无需评判、解读、注释、自省和思考,并且刻意保持天真、平庸、绝对放松、卸下武装、忘记忧愁的状态,没有任何深度、奥妙和内涵。”(9)⑤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红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页,第3页。平庸之美的流行无疑是对自律艺术的一次“祛魅”,批判性与自治性被赤裸裸的资本排挤在外,具有“平滑”属性的艺术温驯地迎合观者,具有独立性的艺术家也摇身一变成为生产艺术商品的员工,讨好式的快感生产取代了反思性的艺术创作。
正如韩炳哲所分析的那样,今天我们面临的审美危机并非是美的缺乏,而是审美泛化下美的消费与滥用,消费社会以一种“充满肯定性的欢愉”将美打磨平滑。消费资本的兴风作浪离不开技术的推波助澜,韩炳哲在将“平滑”美学纳入自身批判体系的同时也显露出对数字技术的隐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将媒介看作人的延伸。在今天,以交互、智能、联网为基本特征的数字媒介重塑了个体的感知方式与交际形式。韩炳哲将信息视作知识的“色情”形态,知识存在于横跨过去、未来的时间结构中,对它的获取是一次日积月累的提炼过程,认知不是简单地了解信息,而是与外在他者互动并生成对世界的崭新认识与体会。而信息却没有知识所具有的内在性,信息只存在于当下“被刨平”的时间之中,简单的信息交互无法生成对世界的感悟与认知,数字社会中的信息化潮流阻碍了知识的获取。避开创伤消极性的社会要求也促生了“点赞”,类似“拍砖”式的否定性互动只会影响交际效率:“肯定社会避免一切形式的否定性,因为否定性会造成交际停滞。交际的价值仅仅根据信息量和交换速度来衡量。大规模的交际也增加了它的经济价值。否定的评判会妨碍交际。”(10)③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14页,第15页。同者间的大声嘈杂遮盖了他者的窃窃私语,信息、交际与资本的加速循环制造出一个没有他者、缺乏否定性的世界。
三、同质化批判:泛审美化的危机所在
“麻木”与“平滑”的概念迭代为我们理解审美泛化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商业艺术的批量生产,公共空间的装饰美化,私人身体的外科美容,种种行径为艺术与审美“祛魅”的同时又试图为日常“附魅”。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审美化”同“审美日常生活化”来解释这种现象——审美泛化亦隐含着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的倾向。然而,如果将审美泛化的危机置于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之中,韩炳哲更倾向于将这种症状诊断为同质化暴力对审美领域的攻陷。
审美所肩负的责任使它必须“从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或是一种技术效果引入生存原则,视作生存的范畴之一。”(11)南帆:《南帆文集2·冲突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页。对理性生活的感性突围被视作维系审美基因清澈性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我们默认审美艺术需要与生活、与观者保持距离以避免其溺毙于现实的泥沼之中。从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到布莱希特的“间离化效果”,艺术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突围姿态,困囿于现实生活被视作无法改变的事实,艺术家时刻处在“精神返乡”的路途上。艺术对距离的要求并不局限于对创作的要求,观者与艺术间的距离也需要得到保证,承认艺术他异性存在的“静观”就成为欣赏艺术的最佳方式。但随着本雅明带电影逃离了层层把守的艺术珍藏馆,面向大众的电影开始重展览价值而抑制膜拜价值。传统艺术往往被置于玻璃柜中或是封锁于常人所不能及的单间,这种“隔离、划界及封锁的否定性是膜拜价值的根本。”(12)③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14页,第15页。而空洞的平滑艺术却力求消解距离,光滑舒适的感觉甚至会产生“触觉强迫”,罗兰·巴特认为触觉是最能消除神秘感的器官,触觉的触碰消解了视觉所建构的距离感,距离的消解意味着神秘感将不会产生,艺术的祛魅杜绝了向精神维度乞灵的可能。
当大众艺术投入“心神涣散”或是“心不在焉”的怀抱,“凝神专注”式的鉴赏就仅限于孤芳自赏。高歌猛进的平滑艺术与少数精英所操持的先锋艺术拉开了差距,回音室内的人潮喧闹掩盖了思想精英的窃窃私语,艺术内容开始走进“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时代。展现日常生活趣味的艺术讥笑先锋艺术的古板冷漠,将日常生活编入自身的创作代码,竭力揣摩受众的兴趣所在是走向商业化成功的诀窍。作者身份的跌落也为“审美日常生活化”出力良多,数字媒介虚化了作者与受众的距离,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与传播者,“抖音”与“朋友圈”的风靡昭示着大众创作的时代已然到来。对朋友圈或好友圈的苦心经营成为许多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对虚拟自我的无效装饰只为寻求好友的“点赞”,九宫格图片或短视频难以成为意义的合格载体。人们的分享与点赞只为追逐快乐,寻求同者之肯定的积极逻辑贯穿日常生活的始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1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的时代。
“所谓色情,可以说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巴塔耶试图从被排斥的色情中寻找至高无上的意义;韩炳哲却将色情化视作透明社会的帮凶。当然,韩炳哲口中的“色情”并非沉溺于男欢女爱的粗劣肉欲,“色情”在他眼中,更多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将自身置于过度照明下的强制展示:“透明社会将所有距离视为亟待消除的否定性。距离是加速交际和资本循环的障碍。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透明社会排除各种形式的距离。”(14)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4页。一种趋近透明化的社会要求将展示价值捧上神坛,距离的消解为各类形象画上平面化的脸谱,展示价值挤压了意义的生存空间,在“色情社会”中,一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以赤裸的姿态呼唤着观者的到来,缺乏“引发映像、审视和思考的不完整性”的触觉式体验即“色情”。韩炳哲对“色情”的思考为我们检视审美泛化危机提供了智识来源。应当指出,“色情”与泛审美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当代人想象力的萎缩,毫无保留的裸露呈现与装点一切的美化行为看似格格不入,却在本质上殊途同归。消解距离的急迫容不得想象叙事的辗转迂回,追求清晰的过度聚焦将想象溺毙于符码的乱流之中。
对同质化社会的担忧并非韩炳哲的独属,已有相当部分学者对同质化社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韩炳哲对同质化的思考独树一帜,通过对“暴力”的知识考古,韩炳哲以“他者的消失”为锚点,为我们揭示出同质化社会的运作逻辑。暴力最初以否定性、排斥性的面目出现,通过构筑两极化的紧张关系,暴力以一种毫无遮掩的姿态公开亮相。彼时的排斥性暴力更多以统治阶级展示其血腥权力的舞台表演出现。但杀戮暴力在现代已失去其合法效力,暴力的拓扑式置换使暴力不再讲求鸣锣开道地铺张排场,公开展演让位给皮下的毛细渗透,暴力不再仅仅表现为过度的排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对公开处刑与犯人作息表的对比暗含着这一暴力演变,内向化的暴力闯入主体的神经轨道和肌肉纤维,通过将统治机关移植到服从主体的内心,“纪律”和“操练”制造出驯顺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相较于规训社会的情态动词“不允许”和“应当”,韩炳哲注意到当今社会对“能够”的推崇。充满积极意味的“能够”具有打破边界与距离的潜力,“是的,我们可以做到”这句话的背后,是积极性的扩张式暴力对边界与距离的消解与冒犯。在韩炳哲眼中排斥暴力建立在二元关系上的免疫结构之上,例如鲍德里亚的敌对关系谱系学就认为敌人将以狼、老鼠、甲虫和病毒的形式出现,而对抗、入侵与渗透必然激活主体的免疫机制。随着社会同质化趋势的加重,暴力形式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暴力并非来自主体外部的强迫,而是生于内在的扩张。肯定性通过内在的扩张将主体解散,并实现对他的去内在化,表现为“商品化的过剩、超量、城市化的扩张、耗竭、生产过剩、过度囤积、交往过度、信息过剩”的扩张暴力不会激活免疫系统的抵抗,但循环系统的堵塞与积聚使肯定性的暴力以梗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没有对手的战争将以梗阻导致的瘫痪收尾。
四、美的救赎:重构否定性经验
面对审美泛化的讨论激起的层层波浪,理论家们的振振有词在客观现实前显得软弱无力,对解决之道的探讨大多浅尝辄止,批评家手里虽然多了几个概念,但一种新的思维结构并未同时产生。理论家们为美的平庸化奔走告解,殊不知审美泛化的危机背后隐藏着同质化的威胁。既然美的乏味与平庸化已成既定事实,如何对抗“平滑”以实现美的救赎?韩炳哲的回答是重视美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部分,崇高、遮蔽、他异性,他者的复归才能带来审美的解放。
针对透明社会的“色情化”问题,韩炳哲也给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直言美是一种遮蔽,“遮挡、延迟和分散注意力也是美的时空策略”(15)②③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页,第99页,第90页。,美的本质栖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性之中。褪去自身的遮蔽物,以赤裸的状态展示自身的“色情”行为无法造就距离的美感,制造诱惑的把戏在于“让自身成为他者永远的秘密”,而“色情”的展示却有如将自身置于商店的橱窗中标价待售。类似的观点在莱辛的《拉奥孔》中也有出现,造型艺术必须找到最具生发性的瞬间并加以表现,在感情上避免激情顶点的顷刻,为想象的空白留有余地,这也就是拉奥孔为何在雕刻中不哀嚎的原因。数字社会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模式,信息不再追求深度与广度,而是以当下直接呈现的叠加形式抛头露面。韩炳哲将美视作“具有叙事性的关联”,数字社会中单纯的信息串联无法搭建叙事的桥梁,叙事关系需要“隐喻”的附魅,事物散发芬芳的本质需要漫长的回味才能展露出美的姿态。美不是霎时的光芒耀眼,“隐喻”的遮蔽性延伸了美的存在实践,因此作家的工作即“隐喻世间万物,也就是去诗化世界”(16)②③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页,第99页,第90页。。
韩炳哲认为,近代美的感性学以平滑美学作为起点,平滑之美以一种“肯定性的欢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从表面上看,“愉悦”似乎成为审美与感官享受之间的共同点,但在韩炳哲看来,将美视作快乐、满意的代名词意味着美正走向凋零。痛苦的否定性被视作谋害美感的鸩酒,哪怕是粗糙的表面与尖锐的棱角都会使美黯然逊色,美似乎应该理所应当地披上小巧精致或是轻盈细腻的外衣。但将美限制在积极性的范围内无疑使人“昏昏欲睡”,韩炳哲将目光放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求解决之道。通过对柏拉图与朗吉努斯的援引,“崇高”的重新发现为韩炳哲对抗平滑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朗吉努斯反对因标新立异而产生的浮夸、幼稚和矫情,崇高与优美不同,它与庄严、伟大、激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伯克也在美与崇高的思考中,将崇高视作否定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复杂的审美体验,崇高最初以痛苦与惊惧构成,但这种“刹时的抗拒”只维持短短的一瞬,对崇高之物的敬仰与自我持存的欣喜使得主体心潮汹涌,回归理性的内在性让恐惧和压抑重新转化为愉悦感。优美所带来的欢愉不过是确证主体自主性与自满性的注脚,崇高所拥有的否定性能够唤回他者之美。韩炳哲呼吁将美与崇高重新结合,实则是为否定性之美正名。
仅仅将“平滑”视作一种麻醉也是不够的,否定性的消失也意味着他者的消失。数字社会中一切事物都是被拍照、记录、存储的对象,科学求知精神手持猎巫运动的火把将所有谜团与神秘逼到无影灯下,消费逻辑捕捉具有他异性的他者并以分类的形式将其置于某纲某目中,殊不知分类与比较在创造他者的同时也摧毁了他者身上神秘的他异性。真正的他者消失了,丑陋被圈养在马戏团或综艺节目中哗众取宠,猎奇心理则在消费的庇护下得到餍足。缺乏具有陌生性、差异性的他者,艺术被指认为一场带有异国风情的假面舞会,新奇的形式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却无法激起心中的层层涟漪。因此,他者的复归便是美的救赎最重要的一环,在韩炳哲看来“艺术的任务就是去拯救他者,拯救美就是拯救他者,艺术通过反对将他者固定在其固有状态来拯救他者。”(17)②③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页,第99页,第90页。s美游走于严丝合缝的消费主义架构之中,身上沾染世俗烟火的污渍也不足为奇,重点是如何洗净扎根于美之上的商业标签。韩炳哲将希望寄托于他者之上,倾听者的出现能够帮助交际从信息交换维度重返更深层次的意义维度,拥抱他异性与否定性也为美制造了新的可能,囿于“平滑”的泛审美危机劝诱着趋于精致与娇柔的美自甘堕落为可消费的装饰品,充满神秘与隐喻的他异之美却将人们引入深度思考的境界。
五、结 语
韩炳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对人的新异化现象的关注是构成其理论光谱的重要部分,自我剥削、透明展示、自恋指涉等理论都显示出韩炳哲对当代人生存状况的密切关注。面对数字化社会中的审美危机,韩炳哲力图说服读者,与否定性画上等号的他者有望成为解决这场审美危机的救赎方案,因为它携带着反思、神秘与叙事结构的基因,能够对抗审美泛化现象下的时弊。以否定性的审美经验来解放被数字技术操控的审美感知,以他者的复归来对抗消费社会所提倡的审美泛化,尽管韩炳哲的救赎方案无异于一次乌托邦式的救赎,但他的思考无疑为我们摆脱审美泛化的精神危机指引了一条反思路径。
社会语境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审美无功利的观念,在此处自律之美与迎合之美分道扬镳。通过切割审美的手术,审美泛化尽可能地避免任何带有否定性的他者将形而上的反思重新携入同质化的单调语境,“迎合”与“媚俗”的文化潮流催化出新时代的审美主体。审美与艺术如何在数字时代超脱刻板的日常生活?效率至上的时代里审美又该如何“慢”下来?数字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又是否会迸射出新的火花?接踵而至的问题拷打着我们的思维极限,毋庸置疑的是艺术自会在数字社会的变革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境遇的安逸不该挫伤理论锐利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