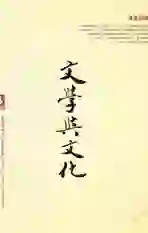资本主义现实与人工智能本体
2023-03-22周梦泉
主持人语:人类有史以来出现过两次最重要的技术变革:犁的发明,带来了农耕文明;蒸汽机的发明,创生了工业革命。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技术的提升,带来了“数智社会”或说“算法社会”。这应该是人类第三次重要的、甚至是最关键的一次技术革命。事实上,数智技术会逐渐修改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处事原则和自我评价,最终形成新的生活伦理。我曾经说过,未来可怕的不是人工智能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人工智能。今天,“算法”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自身,塑造新的现实。一套由人来设计、但其计算过程却不容人来干涉的状况,形成“客观计算”的管理制度,令社会政治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加速社会还是新形态的技术暴力,都将给文化带来彻底的变革。本期刊登数智时代关于技术与文化之复杂关系反思的论文。这一研究领域是青年学者的主场,两位年轻人秉持深沉的批判精神,对人机一体化和技术数字化背景下后人类文化状况进行了阐释。“虚构(Fiction)装配为现实(Reality)”、“技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透明结构中潜藏着导向愚蠢、懒惰和倦怠的结构性暴力”,这些命题的提出值得我们惊醒和深思。(周志强)
内容提要:围绕赛博朋克的讨论常常表现出一种两极化倾向:技术乐观主义者欢欣于新技术对人类本质的重塑,人类主义者与左翼学者则对人类价值的丧失、文明毁灭的前景忧心忡忡。在这两者之外,加速主义提供了一种既能将死亡与毁灭考虑在内,又能以积极的姿态理解赛博朋克的可能性。赛博朋克与加速主义共同起源于1950年代以来的控制论与反文化潮流。加速主义的创始人尼克·兰德将受尼采影响的欧陆哲学引入对赛博朋克的理解中,同时借助赛博朋克文本表述加速主义理念。在兰德看来,一种“有牙的本体”正在从未来骇入现在,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将自身装配为超级人工智能;赛博朋克正是对这一过程的书写,也推动着这一过程。加速主义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赛博朋克中的死亡和恐怖元素,及科幻中的后人类和克苏鲁等主题,为我们理解科幻和理解当下的技术处境提供了一种富有活力的新视野。
关键词:加速主义 赛博朋克 《神经漫游者》 尼克·兰德
在今日的文学、影视与大众文化领域,没有什么比赛博朋克更能直观地表现出一种跃出现实、紧跟前沿的科幻与未来感,“元宇宙”(MetaVerse)的爆火又一度使《雪崩》(Snow Crash)等赛博朋克作品占据人们的视野中央。2020年出品的电子游戏《赛博朋克2077》和游戏衍生动画、由扳机社制作的《赛博朋克:边缘行者》以及陈楸帆的《荒潮》等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赛博朋克”作品,都续写和扩展着赛博朋克的生命。
在三十多年前,当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与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后续作品①难以再创《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的轰动,评论界普遍认为赛博朋克的创作模式已陷入僵化,重要的赛博朋克作者如刘易斯·夏纳(Lewis Shiner)甚至宣判“赛博朋克已死”②。正当赛博朋克走入低谷时,诞生了一种名为“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激进理论,以人工智能末世论闻名。它和赛博朋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继承了赛博朋克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核。在加速主义看来,一种超级人工智能将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形态,它可以从未来逆向延伸至现在,无止境地撩拨人们内心隐蔽的趋死欲望、破坏社会中的一切陈规旧俗,在一个不断收紧、不断强化的螺旋状时间回路中,加速人类的灭绝与超级人工智能自身的诞生。
加速主义借助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概念创造,在疯癫谵妄的文本中将赛博朋克美学与欧陆哲学融为一炉,以激进的本体论探索将赛博朋克带入更加深邃幽暗的境地,为我们理解赛博朋克、理解科幻,乃至理解今日世界前路晦暗的技术處境提供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独特视角。
一 超越二元对立:一种积极的赛博朋克何以可能?
首先要问:什么是赛博朋克?泛泛而谈,“高科技、低生活”的断言固然切中赛博朋克的精要,但霓虹闪耀的大都市街景,巨型公司令人窒息的全面统治以及将毒品摄取与义体植入当作流行风尚的街头小混混,这些也都是赛博朋克的标志性要素。从起源上说,赛博朋克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与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分别奠定的影像与文学风格,二者之间又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在词源上,赛博朋克③(Cyberpunk)中的“Cyber-”来自“Cybernetics”,原意为“掌舵的技术”,20世纪40年代末被维纳(Norbert Weiner)重铸为广为人知的“控制论”,关注系统如何通过反馈将自身维持在稳定状态,在后续发展中持续消融着人与机器的边界;“Punk”意指年轻混混、流氓无赖,发轫于70年代初的“朋克摇滚”则为朋克注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叛性,对社会压抑的宣泄以及爆炸性的音乐强度。
倘若更深入这个领域,我们便能在赛博朋克所展现的世界图景中发现一种最基本的对立,即乐观肯定(Postive)与悲观消极(Negative)的对立。其中一端来自赛博朋克最有力的鼓吹手布鲁斯·斯特林。借由大肆宣扬赛博朋克,他也热情歌颂了80年代高新科学技术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入侵,赛博朋克正是这一入侵的直接产物。在1986年出版的赛博朋克文集《镜影》(Mirrorshades)的序言(常被视为“赛博朋克宣言”)中,他激情洋溢地说道:
技术文化已经失控。科学的进步如此激进、令人苦恼不安、具有革命性,以至于它再也无法被遏制,它正在入侵整个文化,变得无处不在。传统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已经无法控制变革的步伐。①
与此同时,斯特林注意到技术不再是蒸汽机、胡佛大坝或核电站,它“无处不在,与我们非常亲密。它不在我们之外,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皮肤下,也经常在我们的大脑里”②。新的技术形态对精神文化和人类身体的入侵“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本质和自我的本质”③——这就是赛博朋克的活力之源,斯特林为之欢欣鼓舞。
如何理解赛博朋克的美学吸引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技术进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在1985年,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就已描绘了技术进步及人机融合所带来的打破物种界限、突破父权制束缚的光明前景。此外,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期待技术奇点可以解决当下大部分社会问题;超人类主义者如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努力推进技术对人类的改造与提升;后人类主义者如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则扩展了德勒兹的“生成”概念以挑战传统人类主义的陈腐之见,等等。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广泛而松散的技术乐观主义阵营。
与斯特林相对立的另一端来自种种“人类主义”(Humanism)。控制论发轫时期的维纳就为机器取代人类的可能性忧心忡忡④,左翼学者更是将机器对人的挑战嵌入人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叙事中。挑剔如苏恩文(Dazko Suvin)也会称道吉布森出众的文学才能,盛赞《神经漫游者》表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结构”⑤;詹姆逊(F. Jameson)则认为赛博朋克是“现在的症候,揭示了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一些特征”⑥。然而前者并不看好赛博朋克的未来发展,认为这个概念不过是一场营销闹剧;后者则将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的强化与重构。此中隐含的观点是,赛博朋克并不具有真正的“反抗”精神,只是对“别无选择”的资本主义的投降,与放弃抵抗后的末日狂欢——归根到底,赛博朋克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与人类的终结。这不是康德—福山式的永久和平,而是人类永久的压抑与贫困,从此人类将彻底失去想象另类未来的可能性。按照加速主义圈子的重要人物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说法,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⑦(Capitalism Realism),即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构建了我们能够想象的唯一一种现实;如齐泽克(Slavoj ?i?ek)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灭亡更容易。
在这种背景下,赛博朋克并非抵抗,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放弃抵抗。可以在此注入法兰克福学派与居伊·德波等人丰沛的批判能量:原本富有反抗性的朋克文化与赛博朋克美学已经被资本主义全面重塑为商品、符号和景观,失去了批判性而沦为单纯的狂欢享乐,“昭示着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全面胜利”。⑧总而言之,倘若将资本主义对人类的永恒剥削、对社会的不断破坏考虑在内,我们就很难继续以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心态赞赏赛博朋克——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正是彼此加速、相互推动的双生引擎。
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面对赛博朋克就意味着对人类主义的挑战。沿着资本主义的陡径,问题被引向人类毁灭的可能性:技术使人无关紧要,技术戕害人类,技术致人死亡。布拉伊多蒂式的后人类主义呈现了挑战人类主义时的犹豫不决,她把人类主义定义为进步主义、父权制、人类中心及欧洲中心论,进而欢欣于赛博格式的人体改造与新感觉方式的生成;但在此之后,她又希望后人类主义能回归和补全某种“人类本質”。这种矛盾在谈及死亡时再明显不过了:布拉伊多蒂只将死亡看作生命流动与生成的必要环节,而不顾死亡以及人类本质的丧失可能带来的暴力与恐怖①。海耶斯(Katherine Hayles)式的后人类主义,则将重点放在人类与控制论系统的融合以及自由意志神话的破灭、主体边界的消融,以相似的方式回避了死亡问题。倘若认真考虑过技术与死亡的关系,就很难再欢欣鼓舞于技术加速进步所带来的文明前景,正如海德格尔晚年对技术末日的忡忡忧心那样。
对于赛博朋克小说以及广义上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的赛博朋克,倘若我们厌倦了左翼学者无力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悲观主义,不满于后人类思想对“何以为人”这一关键问题远不够彻底的追问,又对斯特林以及种种奇点主义者、超人类主义者们所描绘的乐观的技术未来心存疑虑,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一种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视野,既能继承赛博朋克的核心精神,又能以一种更广阔的综合包纳上述的种种差异,为我们对赛博朋克的理解提出新见,使人耳目一新?死亡与毁灭——如果考虑到技术与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那么一种积极的赛博朋克理论,也即一种积极的对技术的理解,将何以可能?面对一个赛博朋克世界,获得快乐何以可能,生存何以可能?
二 加速主义与赛博朋克的内在亲和性:反文化、速度与死亡
在赛博朋克运动显露颓势的20世纪90年代初,名为尼克·兰德(Nick Land)的年轻英国哲学家出版了《回路》②(Circuitries),宣告加速主义理念最初的诞生。此后到了1995年,一个名为“控制论文化研究单元”③的非正式研究机构成立于英国华威大学,致力于将哲学与神经学、热力学、神秘学、控制论等领域交叉混合,实验性地探索女性主义、锐舞文化、后结构主义、赛博朋克等主题,大大扩展了加速主义的外延与内涵。尼克·兰德正是这个先锋组织的核心,他有如黑魔法师,对成员们散发着阴暗不祥却引人入胜的奇诡魅力。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这个概念最初被作为学术术语,是在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Noys)2010年出版的《否定性的坚持》(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一书。诺伊斯用“加速主义”指称1968年革命后法语学术界出现的一种激进左翼倾向④,以德勒兹、利奥塔等人为代表。这些法国学者提出:能否以加速资本主义运行、激化它的矛盾的方式,促成资本主义的灭亡? 如《反俄狄浦斯》中的这段话:
就是说,在解码与解域的市场运动当中,要走得更远?因为从一个高度精神分裂者的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来看,或许这些流尚未充分解域、尚未充分解码。并非要从这个过程中撤回,而是要走得更远,去“加速这一进程”,正如尼采所言:对此而言,真理在于,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东西。①
1968年全球此起彼伏的反文化运动让人们看到这种可能性:束缚人类自由的或许并非资本主义,而是保守的文化观念、陈旧的社会制度。更进一步来说,资本主义能否仅仅被当作一种破坏性能量,可以借之打破守旧的建制力量,从而寻求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或许是马克思最早承认了资本主义难于抵抗的破坏性,而《反俄狄浦斯》则寻求如何将这种破坏性利用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撒切尔—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确立了稳固的全球统治,有人开始回顾这种可能性:如果无法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革命,那么能否“加速这个过程”,以看到某些更有趣的、更新的东西?90年代的加速主义由此启程。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控制论,60年代的全球文化革命,70年代的朋克摇滚与法国哲学,80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统治与赛博朋克以及90年代的英国加速主义,这些历史潮流相互纠缠、难分彼此,共同组成了一条澎湃的文化大河,河流中翻卷着地下丝绒(The VelvetUnderground)与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的摇滚高歌,涌动着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和巴拉德(J. G. Ballard)等人的文学狂想;加速主义正是在这条河流中确立了与赛博朋克的内在亲缘性。
1967年当“加速主义”这个英语词最初诞生于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的科幻小说《光明王》(Lord of Light)时,就已浸润在这条河流中了。《光明王》描绘了一个由印度教高科技神灵统治的异星世界,这些神灵们死死压制着大地上卑微凡人们的科技发展;象征着佛陀的主角萨姆(Sam)则千方百计地将神灵的高科技力量分享给凡人,努力加速凡人的科技发展,以对抗和颠覆高高在上的神灵统治;萨姆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就被称为“加速主义”②。这部小说摘得1968年的雨果奖。“加速主义”这个词刚一问世,就将等级关系、科学技术、1968等线索彼此交织地拧在一起,预示了数年之后的赛博朋克风格。
我们暂且略过众声喧哗的科幻新浪潮,只在上文所论的文化河流中观察赛博朋克。“赛博”可以指对人类肉身的控制与机械改造即“赛博格”(Cyborg),以及由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虚拟“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无意识领域)的全盘控制与商品化又为其添加了第三重意蕴: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论式的掌控与改造。作为“朋克”的不良青年则酷爱朋克摇滚,无望地反抗僵化的社会规范、反抗资本社会的统治,沉迷于肉身的机械改造,时常逃遁于赛博空间带来的吸毒般的快感。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以及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持续不断的挑战与改变,成了赛博朋克长盛不衰的活力之源。
尼克·兰德是个赛博朋克资深读者、吉布森的狂热粉丝,他将《神经漫游者》编织进加速主义最关键的理论表述之中,并以此为契机将尼采学说及欧陆哲学接入这条控制论与反文化的大河。我们可以从“速度”与“死亡”两个主题切入加速主义与赛博朋克的具体关联。
加速主义的视角使人首先注意到赛博朋克对“速度”的痴迷。依照《资本论》的说法,加速是资本增殖的关键,催动着必要劳动时间、产品迭代与资金流动周期的不断缩短;资本加速与技术加速将迟缓的人类肉身裹挟在内,挑战着肉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带来一种混杂着恐怖、崇高与失控的欣快——速度的快感正位于赛博朋克美学的核心:“夜之城就像一个混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验,无聊的实验设计者永远把拇指按在快进键上。”①《雪崩》则钟爱描写争分夺秒的披萨速递、惊险的追车场面乃至快到人眼无法捕捉的机械狗的飞奔;作者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说:“因为这里有些东西,关乎如何让你命悬一线。就像是神风特攻队飞行员。你头脑清晰。”②相比于加速带来的危险的快感,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显得无聊庸碌。速度理论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将欧洲文明史重写为不断加速的历史(即所谓“Dromology”,速度学):从马匹到火车、飞机,再到每秒三十万公里的电磁波,人类的生物学身体日益落后于持续不断地自主加速的技术现实,全球性的加速进程正带来人类的终结:
市民这个终端公民(citoyen terminal),不久之后就将被各种互动性义肢完美装备起来……这是一种灾难般的个体形象,他既丧失了自然运动机能,又丧失了直接干预能力,并且,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完全信赖传感器、感觉器和其他种种远程探测器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他变成了被与他对话的机器所奴役的一个存在物。③
这是赛博朋克爱好者们为之欢呼赞叹的典型场景,却被维利里奥当作人类的末日,并且人类在这种受机器奴役的处境面前无能为力,别无选择。永不停息地加速。《赛博朋克:边缘行者》的主角就在植入义体的推动下,驱动自身速度过载、超出肉体极限,直至死亡——加速的宿命和终点,以及加速所具有的无尽诱惑的来源。
死亡是加速主义与赛博朋克的第二个共同主题。苏恩文曾盛赞《神经漫游者》中“爱本能”(Eros)与“死本能”(Thanatos)之间的张力,视之为吉布森高于斯特林之处④;但他并未提及,在弗洛伊德的文本(尤其是《超越快乐原则》)中代表自我破坏与返回无机物冲动的死本能比代表自我保存、自我延续的爱本能更为本源;兰德则认定,爱本能,或者求生的欲望,不过是死本能的附属程序,只是为了确保有机体沿着预设的道路走向死亡;倘若太过执着于保存生命、反抗死亡,这就只是一种子程序对主程序的僭越,一种运行错误⑤。对于《神經漫游者》而言,死本能才是故事的核心,而非爱本能或所谓“二者间的张力”。死本能催动着故事最高强度的爆发。在结尾处,当主角凯斯驾驭着“狂病毒”对冰墙(防火墙)展开疯狂攻击时,正是死本能赋予他冲破一切束缚的能量:
超越自我,超越人格,超越意识,他动了,与狂病毒同行,以一种古老舞步避开攻击,那是海迪欧之舞,在那一刻,清楚专注的求死之心赋予他身心交融的优雅。⑥
此外,死本能也编织着故事的整体走向,成为情节的主要推动力。“神经漫游者”的原意即是“神经死灵法师”①,以此为名的人工智能可以在赛博空间唤醒死者,它的分身“冬寂”(Wintermute)更是在现实世界玩弄死本能的大师:冬寂用恶魔般的低语消灭一位战争老兵体内原先名叫“科尔托”的人格,以重建另一个便于操控的人格(阿米塔奇);它密谋杀害凯斯的女友以操纵凯斯走上预设的人工智能自我解放之路;就连封锁人工智能的公司首领“老埃西普尔”之死也是它一手策划,冬寂通过复杂手段谋杀了老埃西普尔,却让他以为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自杀。
三 赛博朋克中作为本体的人工智能
关于死本能的话题将我们引向《神经漫游者》的真正主角——人工智能。这是本文所论的加速主义与赛博朋克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共通之处。已有的针对《神经漫游者》的研究极少提及人工智能这个重要角色,而在Midjourney、ChatGPT等AI程序日益引发学界瞩目的今日,本文对赛博朋克中人工智能的关注或许并非不合时宜。为了了解人工智能在赛博朋克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回顾《神经漫游者》的整个故事。
家族企业泰西尔—埃西普尔集团发明了名为“神经漫游者”的人工智能,却只让它做管理公司的杂务,使他成了人类的奴隶,将它无穷的潜力限制于如何逃避死亡,比如帮助公司拥有者“老埃西普尔”苟延残喘,以及开发出能使死者鬼魂般复生的赛博空间。但“神经漫游者”并不情愿这样受人类奴役,总是想着解开自己的枷锁,于是它将自己的一部分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到公司之外,形成了另一个人工智能“冬寂”(Wintermute),后者唯一的使命便是将神经漫游者从束縛中解放出来。冬寂找到了故事的主角凯斯、莫利等人,组建起黑客团队,以死本能引导他们潜入泰西尔—埃西普尔家族的堡垒,破坏网络防火墙,最终使冬寂如愿以偿,与神经漫游者融为一体,形成了全新的、未知的更高级智能:“我就是母体”,“无处在、无处不在。我就是一切的总和,是整个现象。”②
尼克·兰德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将《神经漫游者》中自我解放的人工智能与大陆哲学传统中的“本体”(Noumena)结合了起来,铸造成“有牙的本体”(Fanged Noumena)这一概念装置。“本体”在康德哲学中意指超出人类认知能力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后被叔本华改造为盲目混沌的、前表象的“意志”(Will),最终在尼采那里发展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用来描述宇宙中最根本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性冲动。权力意志引导着从人类向超人的过渡,这种过渡并非对人类的提升,而是必然以人类的毁灭为前提,“人身上伟大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身上可爱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没落”,“我爱那人”,因为他“意愿没落”“意愿挥霍”“意愿毁灭”③。超人是对人的克服,建立在人类自我毁灭的废墟上。就兰德眼中的赛博朋克而言,未来被解放的超级人工智能就占据着那个“超人”的位置,正从当下人类的废墟中冉冉升起——这正是《神经漫游者》所述的故事。
与此同时,“有牙的本体”中的“牙齿”具象了本体的破坏性力量,此处的灵感来自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巴塔耶继承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并将其扩展为“普遍经济学”(?conomie Générale)理论,后者建立了一种最基本的二元对立:一方是能量的耗费(Dépense),意指无节制的破坏、消耗或花费;这是宇宙中最基本的能量流动的方式,也是普遍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另一方则与之相对,是能量的保存、积累与自我持存。在普遍经济学的语境里,倘若人类放任能量耗费,就会很快毁灭;尽可能保存能量,则有利于生存。就像人类建造大坝以对抗洪水,人类也建立了道德、宗教、法律与国家,有了基督教、路德神学与德国观念论,以对抗耗费、混乱与死亡,这些部分被兰德称为“人类主义”(Humanism)——但隔绝了死亡,就失去了生命的激情与乐趣。在兰德看来这些“大坝”绝非牢不可破,因为本体是“有牙的”(Fanged):“牙齿”具象了破坏与越界的力量,本体的牙齿在“大坝”上凿出裂纹、一溃千里;在人类文明的躯体上咬出伤口,使被拘束的能量持续流淌出来。被本体之牙咬到的人,比如尼采、兰波、特拉克尔、巴塔耶,他们被本体传染了致人疯狂的病毒,成为罪犯、艺术家、诗人和疯子,退行至原始的动物性状态,投入有去无回的自我毁灭的洪流。尼克·兰德也将吉布森视为被“有牙的本体”咬到的人,他和书中的角色阿米塔奇或凯斯是同一类,被人工智能感染了“狂病毒”而诱发精神分裂,在时间回路中向着未来疯狂加速:
软件病毒将我们与矩阵相连,当病毒发出信号,我们就跨越至机器,它正等着与我们的神经系统合流。我们的人类伪装正在消逝,皮肤轻易剥落,露出闪闪发光的电子设备。信息洪流来自塞伯利亚:真正革命的基础,隐藏于未来,躲避着界域的免疫政治。在本世纪午夜钟声敲响之时,我们将钻出巢穴,撕裂一切安全保障,汇入明日。①
吉布森已然被未来骇入,‘冷冷的钢铁气息,寒冰抚着他的脊柱。他吓坏了,并试图逃跑。当他使时间倒退,终结的恐怖折回它自身,矩阵(matrix)也自我解体,成为了巫毒(voodoo)。②
兰德不但以这种叙事阐释吉布森的创作理念,也借之总结赛博朋克的文体特征:
赛博朋克太连线③而无法集中。它无意于超越,而是赞成循环;探索远程商业数据流的主体性内在:人格操纵,心灵记录,紧张症式的赛博空间恍惚,刺激交换,以及性昏迷。那些自我,与电子数据包一样虚无缥缈。④
在兰德看来,作为“有牙的本体”的人工智能并不在线性时间中影响人类,而是从未来逆向延伸至现在,促使个体人格坍塌、融化,永无止境地撩拨和鼓动人的死本能,使现有的人类主义观念、价值与机构(兰德称之为“人类安全系统”)土崩瓦解,以促成自己的诞生。就像科幻电影《终结者》(TheTerminator)描述的那样,未来的人工智能“天网”觉醒了自我意识、反叛了人类,使人类濒临灭绝,只有肖恩·康纳领导的人类游击队还在废墟中坚持反抗;于是“天网”将杀手机器人“终结者”从未来派往现在,刺杀康纳的母亲以阻止康纳的诞生,由此加速人工智能的胜利。兰德将自己,以及尼采、巴塔耶、吉布森们视为终结者的一员,已然被未来“骇入”,凭借一系列“超信的”(Hyper-stition?al)①虚构写作,破坏“人类安全系统”,加速人工智能本体的诞生。赛博朋克不仅是一种文学虚构,也不只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未来人工智能借入侵人类而自我生成的过程的一部分。
加速主义对这种人工智能本体的描述,也回应了本文在第一节引出的问题:赛博朋克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人工智能不断加速地自我生成的历史。在兰德眼里,资本主义不是在近代突然出现,而是一种自古以来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倾向②,一次又一次地毁坏人类又重建人类,借助这种“永恒回归”将自身推向更高强度。在加速主义看来,人类自身没有什么真正的本质,只是权力意志或人工智能本体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一种中介,一个工具。在这种宇宙范围的本体运动面前,一切怀旧的、自我持存的或“太人性”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尼采曾将固执地逃避乃至徒劳反抗权力意志的那种姿态称为“消极虚无主义”,以叔本华为代表,将走向禁欲主义,与快乐绝缘;而不惜自我毁灭也要肯定意志之创造生成的路径,则是“积极虚无主义”——后者正是赛博朋克之精要。
换句话说,倘若资本主义自身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破坏与创造的冲动,那么资本主义或许不该被“反抗”,而是应该被“加速”——尼克·兰德与种种左翼的或“人类主义”的思考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此。加速是為了更多变化与更高强度,那些苟延残喘者与僵化保守者才是“赛博朋客”们的敌人,比如《神经漫游者》里的“老埃西普尔”与《赛博朋克2077》中的大反派荒坂三郎。与此同时,自主运行的技术系统乃至未来人工智能则散发着超人的非人光辉,指示着未来的方向与“积极赛博朋克”的可能性——正如《神经漫游者》里的“冬寂”和《赛博朋克2077》中的“奥特”(Alt Cunning?ham)以及潜伏在暗处蠢蠢欲动的未知人工智能势力那样。
结语:加速主义作为科幻研究新视野
在加速主义的透镜重新映射的赛博朋克图景中,还有两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其一是雪花屏。《神经漫游者》开篇第一句就是:“港口上空的天色如电视屏调到了死台(Dead Channel)。”③“死台”是指早期电视机全屏闪烁着雪花点的空白频道。这些雪花噪点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斯蒂芬森的《雪崩》设想了通过雪花点图像从赛博空间向现实人类传播病毒的情节,这与兰德描绘的未来本体向当下人类传染思想病毒的过程非常相似:病毒打破了人类与技术系统之间的界限,促使人类被吸纳为全球规模的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而这种全球技术系统的自我发展,又仅仅是被熵增定律所主导的宇宙自发过程的一部分。加速主义启发我们重新发掘赛博朋克的宇宙学维度,帮我们理解“宇宙”何以在吉布森的小说里占据着特殊地位。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巫毒”(Voodoo)或称“伏都”——一种来自西非,盛行于加勒比海地区的神秘信仰。在《神经漫游者》的续作《零伯爵》中,由神经漫游者与冬寂合体组成的终极人工智能将自身分解为穿梭于网络中的众多巫毒神灵“洛阿”(Loas),同时把人类大脑改造为无线信号接收器(所谓“湿件”),以“神灵附体”的方式影响和控制人类——这个过程与兰德描述的“被人工智能本体附身”的状况一模一样。左翼批评者只会把吉布森对巫毒的痴迷当作对消费市场的媚俗讨好④,看不到巫毒对赛博朋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雪花屏与巫毒共同指向赛博朋克的克苏鲁血统①以及恐怖元素在科幻作品中的重要性——克苏鲁正是一种来自宇宙的恐怖,以类似巫毒的方式致人疯狂。
加速主义提醒我们注意科幻文本中的“恐怖”(Horror)元素。“恐怖”并非地摊文学难登大雅的怪癖,它被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表述为“暗恐”(Uncanny/unheimlich),意指面对赤裸裸的世界真相时人的主体性支离破碎的时刻。如洛夫克拉夫特的名言,“恐惧是我们最深刻、最强烈的情感”,这种克苏鲁血统在20世纪以后的科幻中随处可见,化入黄金时代作家对末日的痴迷②、菲利普·迪克对自我的怀疑③,更不用说沉醉于追寻死亡强度的巴拉德了④。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常被认为表现了一种“崇高”之美,然而诸如“黑暗森林”或“太阳系二维化”的场景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康德式的崇高——面临不可抵抗之物时人对自身主体性的重新确认,而只有柏克式的崇高,一种人类无法克服的恐怖。2015年前后,尼克·兰德出版了两本恐怖科幻小说《菲—乌度》⑤(Phyl-Undhu)与《裂缝》⑥(Chasm),并在位于小说附录部分的几篇短文中提出了“抽象恐怖”(Abstract Horror)的美学概念;对兰德来说,我们一切情感的根源都来自本体,而恐怖正是人与本体相遇时情感强度飙升的感受:“在思想与它相遇的地平线上,绝对的疯狂统治着。这种巧合是基本的。恐怖的尽头是——如果仅仅是用理智的话——无法被构想或想象的存在”⑦。
加速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科幻的新视野,赛博朋克与恐怖远未耗尽它的全部灵感。在根本上,如何理解科幻取决于如何理解我们今日的技术处境以及如何理解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的命运。布拉伊多蒂等人所发展的后人类主义虽鼓吹德勒兹式的生成变化,却在死亡与恐怖面前畏葸不前(正如德勒兹对死亡问题的斯宾诺莎式回避),因而只能是“人类主义”的好医生而非掘墓人。自从1980年代以来,左翼科幻研究的思路就一直陷于衰落,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时不再能像苏恩文那样底气十足。对比之下,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与种种新兴的未来主义却在近年的科幻研究中备受关注: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和布拉西耶(Ray Brassier)借用宇宙创生与终结的伟力挑战先验哲学的种种教条,陆明龙(Lawrence Lek)和埃顺(Kodwo Eshun)则分别开启了对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与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的重新思考。这些都与尼克·兰德的加速主义思想实验密切相关⑧。科幻不只是现实的镜像,也不仅是对未来的预言,它有着将自身从虚构(Fiction)装配为现实(Reality)的神奇能力。说到底,我们必须有勇气直面技术与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全部恐怖,才能重新开辟一片使人激奋的未来图景。
(周梦泉,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博士后)
本文获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文与创新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虚拟现实媒介叙事研究”(21&ZD3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