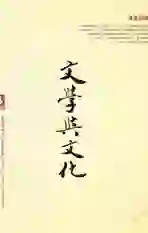《新闻报·艺海》:从“ 艺术副刊”到“ 商业电影副刊”
2023-03-22石娟



主持人语:本辑发表的四篇论文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文艺副刊(1898—1949)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孕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图书、期刊、报纸文艺副刊是支撑其向纵深发展的三大出版平台。但与图书、期刊研究和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相比,报纸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数据库建设及整体研究相对滞后,这是与文艺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相匹配的。针对这一现状,课题组试图从文献整理、研究、数据库建设等几个方面入手,全方位地呈现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石娟的《〈新闻报·艺海〉:从“艺术副刊”到“商业电影副刊”》对《新闻报》艺海副刊的风格变迁做了历时性的考察,讨论了它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张童的《史传”传统与时间意识:论五四时期〈晨报〉第七版的文学生产》从史传传统与时间意识入手,对晨报副刊与新文学间互动共生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郑恩兵、梁晓晓的《〈晋察冀日报〉副刊的概貌与表征》全面梳理了《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对其基本特征及其与解放区文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王尧、李锡龙的《焦菊隐谈〈一年间〉的导演》则从一篇佚文入手,对焦菊隐与《一年间》的关系及其对导演艺术的理解进行了深入讨论,对研究焦菊隐的导演艺术有重要价值。(李锡龙)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新闻报》的电影副刊“艺海”与《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齐名,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作为商业电影副刊,“艺海”重在“经营”。迄至今日,“艺海”及其主编吴承达在电影史书写中一直“失语”。事实上,“艺海”创刊于1925年5月16日,初定位为艺术副刊,1926年4月1日停刊。1933年,“艺海”复刊,转型为“商业电影副刊”,继承了“一·二八”以前的电影批评话语,以貌似“旧”的电影批评,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从技术、内容、形式乃至艺术的对话,肯定了中国本土商业电影的盈利模式,培育了电影市场,为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商业电影的自由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艺海”的副刊风格从“艺术”向“娱乐”、从“教育”到“代言”的转变,副刊读者从“小众”到“大众”的文化实践,形塑了电影在中国从“艺术”向“文化工业”的流变轨辙,为彼时电影批评带来活力与张力的同时,也保证了诸副刊之间批评话语的多元,表现出差异化的文化政治。正是这些丰富的“差异”,使我们得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产业生态,亦托举起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新闻报·艺海》 商业电影 副刊 吴承达 严独鹤
1934年,《良友》100期的影像特刊中刊出了一组珍贵的照片,《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民报》《晨报》《时报》《中华日报》电影副刊主编悉数亮相。①同年5月26日至6月5日,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左翼电影副刊《民报·影谭》亦连载了“离离”的《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除《电声日报》外,亦评价了彼时颇有影响力的六大电影副刊:《时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新夜报》的“黑眼睛”、《时事新报》的“新上海”、《申报》的“电影专刊”、《新闻报》的“艺海”以及《民报》的“影谭”。《良友》100期的盛举以及《民报·影谭》对《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的连载都发生于1934年绝非偶然,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
作为承载了一个时代观影情绪的历史载体,电影副刊以多元混杂的面目,呈现了彼时电影业的文化生态。经历了1933年的“电影杂志年”之后,至1934年,电影副刊亦呈繁荣景象——除现在学界已经注意到的《晨报》的“每日电影”②和《申报》的“电影专刊”之外,20世纪30年代,仅在上海一地,在市民中影响力较大的电影副刊即还有《民报》的“电影”“每周电影”“影谭”,《时报》的“电影时报”,《时事新报》的“电影”③,《新闻报》的“艺海”,《中华日报》先后创刊的“星期电影”“电影界”“银座”“艺坛情报”,《大晚报》的“电影专刊”“火炬”“三六影刊”,《上海商报》的“银总会”“电影周刊”“电影新地”,以及电影專题报纸《电声日报》,等等。④但由于时代、政治、历史、观念及文化等原因,迄至今日,除《晨报》和《申报》的相关副刊有部分研究⑤,其余电影副刊的系统研究较少,尚有大量基础性工作有待展开。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电影从业者、影评人、观众频繁发声,或作理论探讨,或作艺术分析,或作技术指导,标明“公共领域”的电影评论及阅读群体已然形成并日臻成熟。电影副刊的繁荣,客观上拓展了电影批评的“公共空间”,使普通观影者的批评意见得以展示,观影者的主观感受获得分享,同时,电影从业者、专业影评人与普通电影观众之间也藉此获得了直接对话的可能。尽管各个副刊受报纸办刊定位、经营方针或副刊主编个人的艺术趣味、批评立场、批评观念等影响而存在差异,但恰恰是这些差异,使得彼时电影生产与消费链条上的各种讨论呈现出“众生喧哗”之态,一个时代的“盛景”得以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副刊的繁荣,不仅是彼时电影业繁荣的风向标,更成为时代观影感受及观影情绪的历史记忆。近年来,经李少白①、李道新②、李多钰③、丁亚平④等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电影史书写已大为改观,但部分电影副刊依然“失语”,这直接导致了电影史的书写受到遮蔽⑤。书写出来的电影史与20世纪30年代作为“实况”的电影史事实上存在多大的差距⑥?还有哪些图景已经或正在被当下的历史书写所忽略、所遗忘?这些被忽略的历史书写,从“弱势电影”⑦的视角来看,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本土电影“狂飙突进时代”事实上“安稳”的“底子”⑧ ,抑或“默默的强势”⑨?
必须承认,在彼时众多电影副刊中,《良友》100期“盛举”中的“头牌”,亦被《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点名“有待纠正”的《新闻报·艺海》的确是一个异类——在热闹异常的“软硬之争”“凤鹤之啄”等重要电影史事件中根本找不到它的存在,与左翼电影更是完全搭不上边。可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读者而言,“艺海”的知名度并不弱于《晨报》的“每日电影”和《申报》的“电影专刊”⑩。时至今日,“艺海”一直以“金钱主义”“落后”乃至“陪客”的面貌出现在电影史中,模糊不清,有“艺海之花”①“吴艺海”之称的时代“闻人”、主编吴承达(见图1),在一些大部头的电影史专著中,几乎未见。“一·二八”之后,众电影副刊纷纷以“新的电影批评”进入“新的阶段”,《新闻报》的“艺海”却以“更忠于广告,更不敢得罪广告主人”的面目和“旧的电影批评”,获得了“更广大更一般些”②的读者的青睐,以致被要求“有待严厉纠正”。③然而,就在同期即有声音称:“艺海”上面的影评,“名家专家所撰,相当精彩,本国艺坛情报,亦很生动,中西合璧,美具难并,颇收牡丹绿叶之妙”④,亦有读者为主编吴承达“抱不平”,责备“电影新地”的编者骂了“老实的”“好好先生”⑤……“艺海”究竟是怎样一份副刊?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生态中,“艺海”价值何在?“落后”和“金钱主义”是否是“艺海”唯一的历史价值?在“进步”的标准之外,“艺海”对于中国电影是否有所贡献?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及再分析,不仅出于还原历史“实况”的必要,亦可管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乃至文化生态之一斑。
一 1925:严独鹤与“艺术之海”
与20世纪30年代许多电影副刊不同的是,《新闻报·艺海》1925年即已创刊,只是不到一年即告停刊⑥,至于1933年的出现,属于复刊。复刊后的“艺海”之所以以“旧的电影批评”和“更忠于广告”⑦的方式安身立命,应该与其1925年创刊后因副刊定位于“艺术副刊”,曲高和寡,导致经营不善很快便被停刊的教训有关。
“艺海”创刊于1925年5月16日(见图2)。创刊之初,严独鹤在发刊词中对副刊主旨有三点说明:
(一)为艺术界介绍作品。比来中国各艺术,突飞孟晋,气象至为蓬勃。同时关于批评艺术或指导艺术之作品,亦应时而起,日见其多,但往往散见于报章杂志,东鳞西爪,犹病阙漏。本栏拟汇集各专家作品,按日刊载,俾使阅者,其所论列,或本诸经验,或根于学理,要皆足为艺术界之先驱,供艺术家之参考。(二)为艺术界传播消息。艺术界之事业愈进步,则艺术界之消息,自愈见其多,而社会人士对于艺术消息之注重,亦愈见其切。尔来“快活林”中亦尝设“游艺消息”一栏,记载各方面之事实。顾限于篇幅,不无挂漏,每引以为歉。自今以始,当可藉“艺海”一栏,使各种游艺消息,得以尽量发表,供各界之快观。(三)引起民众对于艺术之兴趣。艺术界不能不与社会民众发生关系,使民众对于艺术,兴趣淡薄,则纵令艺术界本身努力振作,欲求艺术前途之发展,终不免事倍功半。本报于此(?),愿为艺术界竭其鼓吹之责,使社会人士,对于艺术,咸具有欣赏之精神,与研究之意味。总之艺术之为用,自其大者言之,实具有培养国民德性与宣扬国家文化之力,使各种艺术,能昌明至于极点,其收效或且视教育为尤普。此则本报对于艺术家之希望,窃愿尽其辅助之责也。①
《新闻报》的“快活林”和一年以后创刊的“本埠附刊”在发刊时,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刊词,读者只能通过创刊当天《本刊征稿启事》之类文字了解副刊的内容、倾向和性质。但“艺海”完全不同——创刊号上“发刊词”三个大字耀眼夺目,严独鹤的开宗明义,从中不仅看得出报馆的重视,同时,强大的作者阵容和充实饱满、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稿件亦反映出“艺海”的创刊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艺海”的主旨概括了副刊的三方面功能:汇总艺术批评和作品;发表艺术界消息;对民众进行艺术教育,以期实现促进艺术发展,“培养国民德性与宣扬国家文化”的最终目的。于是,创刊号上,我们看到了一批剧界、电影界的“闻人”:独鹤、海上漱石生、天台山农、洪深、郑正秋、谷剑尘、任矜苹……接下来的几天,副刊上亦陆续看到马二先生、周剑云、姚民哀、丁悚、张舍我、余空我等人的力作。這些文章,细致勾勒了严独鹤在发刊词中反复强调的“何为‘艺术”,这里且以创刊号为例(见表1)。
不难发现,创刊之初,“艺海”关于电影的讨论并不多,更热衷于戏曲,作者也多为报人作家或传统知识人。值得玩味的是,在“艺海”上,其作者呈现出的奇异的张力:这边海上漱石生、天台山农和老拙悠然自得地谈论着酒在戏曲表演中的功能、上海听戏的好去处以及名角程艳秋的表演,那边新剧界的洪深和谷剑尘热烈地讨论莎士比亚和《傀儡之家》,任矜苹和陈寿荫则神情严肃地思考着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国电影市场的欧美影片电影剧本、滑稽表演艺术。由严独鹤来提倡艺术,似乎有些名不副实,然而彼时已是明星公司编剧,且此时尚活跃在新剧界的郑正秋在创刊当天却兴奋地称:
快活呀!快活呀!社会向来不甚重视的戏剧家,居然有销数最多的《新闻报》,趣味最浓的“快活林”,声望最隆的严独鹤,起来提倡,替我们登载消息,替我们登载评论,我们得到一位替艺术界开辟新大陆的健将,我们非但希望这个新天下要打得开,而且要希望彼长久而越放越大。天下打得开打不开,全在我们争不争气。……所以我开头第一篇,就抱一百二十四分的热忱,向我戏剧界诸同志请愿,一句总话,就是诸同志一同来争一口气,替报纸做戏剧评论,和报告戏剧家的消息。①
不仅没有“屈就”之姿,反而异常激动和兴奋,心存感激。在“艺海”创刊十年之前,也就是民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正值郑正秋与戏剧的“热恋”期,他每天都会做戏剧评论、报告戏剧家的消息,十年之后,历尽世事,被邀重操旧业,心中难免五味杂陈,称自己不是“懒动笔”,而是“怕动笔”,因为怕惹到“邪气洋气酸气土气奴气客气的几种”,同时亦指出,戏剧在中国的不能繁荣,这几种“气”有着相当大的责任。直至停刊前,“艺海”主要以戏曲、戏剧、电影乃至说书等四方面内容为主,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新旧雅俗,各得其所。
值得注意的是,刚在中国立足不久的新剧界,已经有人开始反省发源于西方的戏剧难以在民众中普及的原因,并且谋求其与旧形式如戏曲、说书等和平共处的可能。反观文学界,新文学的矛头彼时正激烈地指向“鸳鸯蝴蝶派”,“艺海”却“风景这边独好”:在趣味的表象之下,电影与戏剧同样具有宣传艺术和教育社会的双重功能——郑正秋等人与严独鹤达成了共识。有趣的是,从创刊至停刊的一年内,我们看到了同是明星公司重要成员的郑正秋、洪深、任矜苹等人,却没有看到张石川,除去人际交往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张石川此时“处处惟兴趣是尚”②与郑正秋、洪深、任矜苹等人的“以正剧为宜……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的制片主张相悖,同时亦有悖于“艺海”藉戏曲、戏剧以及电影等艺术形式“培养国民德性与宣扬国家文化之力”的主旨。③
但是,由于《新闻报》“在商言商”的办刊宗旨以及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读者定位④,极力提倡“艺术”的副刊不仅很难融于报纸的整体风格,艺术的小众化特征,也完全背离了报纸的大众化诉求。就在“艺海”创刊一周左右,署名“天平”的作者就在《晶报》上对“艺海”将戏剧、戏曲和电影等都归于艺术产生质疑,对其能否办得长久并不乐观,“很望他能如《快活林》之长久快活”⑤。一语成谶。“艺海”创办的时间,恰也如“天平”所质疑的那样,在1926年4月1日“本埠附刊”创刊之时,被其并入。我们不仅可以从“本埠附刊”创刊号的内容上看到这一点①,而且从“本埠附刊”的征稿启事《本刊之三种征求》中也可以看出端倪。②严独鹤创刊之初所抱持的“引起民众对于艺术之兴趣”,其实恰恰暗示了“艺海”上的“艺术”在当时市民中并没有市场。创刊之初的“艺海”作者完全是“圈中人”,阵容堪称豪华,然而自始至终,在偌大的副刊版面上,几无读者的参与和互动,它是清高的,亦是孤独的。
二 1933:吴承达与“电影特质批评”
1933年1月12日,在“本埠附刊”的末尾处,“艺海”“悄然”登场。之所以称其“悄然”,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艺海”出现之前没有任何报道,复刊当天也没有任何发刊词;二是“艺海”内只有一篇短短不到两百字的《苏联影片在沪开映消息》,更像是一个“专栏”④(见图3)。但与1925年的“艺海”相比,此时的“艺海”却传递出清晰的定位——电影副刊,尽管这种悄无声息与当时电影市场的如火如荼如此不相称。“艺海”复刊的初衷只是为了在电影市场里分一杯羹,所以主体“完全给流动的广告支配着”⑤,文字为次,相当于补白。创刊后的几个月内,“艺海”每天都只有一到两篇电影消息,相比于1925年的规模庞大、阵容齐整,复刊显出准备不足、尴尬与局促,或许,这与此时报馆尚未找到合适的编者有关⑥。直到吴承达和陈灵犀的影评出现,“艺海”方才现出副刊的样貌。
复刊之后的“艺海”转变了办刊方针,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它几乎张开双臂拥抱市场。如《新闻报》的“本埠附刊”一样,“艺海”的复刊是受到1933年前后其他电影刊物的纷纷创办尤其是《电声日报》的启发。①1934年5月,《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一文指责“艺海”的编者②以通俗的文字传布,把“艺海”当作投资而活动,不自觉地被它影响的是“一般落后的市民”。③“艺海”的读者是否为“一般落后的市民”或可商榷,但它此时投资的倾向也即市场意识不容置喙。几乎1933年全年,复刊后的“艺海”都是作为“本埠附刊”的一个子栏目出现,内容刻板,全部为电影的绍介、即将上映或正在上映的电影本事、电影公司新片消息以及影人轶事等。从这个意义来说,此时的“艺海”只是电影广告的副产品④。1934年之后,增加了“艺海谈座”“银亭随笔”“影评人日记”“杂碎馆”等专栏,副刊的内容才日渐丰满。值得一提的是,“艺海”的影评在形式上也呈现出鲜明的商业特色——新片上映的当天或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吴承达、叶逸芳、蝉衣等人的影评,几乎全部为第一篇,既是评论,更是宣传,亦与电影广告遥相呼应。特别是吴承达,他去影院,常常自己购票,《新闻报》所谓的“无党无偏”的宗旨,在吴这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其影评中的立场和态度,日益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但是,如果我们对“艺海”的理解仅仅停留于“金钱主义”,就很难解释1933年“艺海”开始即刊登的侯枫等人关于电影技术、理论、理念、内容及美学等层面的学理思考,如果“艺海”的读者均为“一般落后的市民”,就更难理解为何日后的左翼电影亦可进入该刊,并一度成为副刊的主角⑤。复杂的电影技术以及理论怎样才能赢得“一般”的市民的关注?“落后”的观众如何接受格外强调“内容卫生”①的左翼电影?复刊后的“艺海”的“投资倾向”或者说市场意识,是否能够如“启蒙运动的生意”②那样,在生意之外,给予电影史以意外的收获?
复刊后的“艺海”的第二个特征,是关注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其实,在《“艺海”新话》一文中,吴承达即明白告诉读者,与当时一众电影刊物一样,“艺海”也是负了“特殊”使命的——“期望着竭尽笔杆上的能力,以唤起读者对电影的注意与认识。一方面藉以督促我国影业之前进……”③而引起一般人读电影刊物的兴趣,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赚钱:
把“电影”为一栏的中心,先以有趣消息报告读者,以引起一般人读电影刊物之兴趣,已而乃介绍各个专门学识及新片,作进一步之探讨。间或亦刊登电影小说影人笔墨及照片插画等以资调剂,体裁不限,纯以一般人对精神上粮食之转移为对象。④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一般人”,一是“转移”。“艺海”的读者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吴承达所界定的“一般人”是哪一类人,是“一般落后的市民”吗?
1933年5月,上海各处的童子军发起了为空军募捐的行动。5月13日,吴承达在《为童军募空经费敬告一般电影观众们》一文中呼吁看电影的人们,不要“迟疑地不解私囊而‘一毛不拔”,因为在电影院中,“至少都是中产阶级,虽是二角大洋的电影,在这生产力大减的时代,也总不是无产阶级所能光顾的……”⑤不难判断,1933年前后电影院的观众主体,很大一部分人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职员,因为“对于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来说,一般不难得到优厚的收入”,而“新式职业领域的职员一般不难维持中等水平的小家庭消费”。⑥这样一个群体又具有怎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观影趣味呢?1933年9月6日起,“艺海”增加“观众意见”专栏,开始刊登众多读者的“我评”,从这些文章里,“艺海”读者的观影趣味、审美倾向得到了多元表达,即便这些文字经过了编辑的择选和处理。1933年9月14日,由邵醉翁导演,袁美云主演,天一公司出品的第一部无声片《飞絮》在北京大戏院首映。无论是《申报》的“电影专刊”还是《新闻报》的“艺海”,專业影评人都对影片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后半部分的情感处理以及袁美云的表演大为赞赏,观众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9月17日,承鏊、礼忠、墨一、雪华四位观众在“艺海”上发表了《〈飞絮〉我评》。除了承鏊与专业影评人的意见相似⑦,其余三人均持不同意见:礼忠、雪华从生活细节出发,批评“乡下妇女会怕牛”“童养媳不懂挑水”“油灯点全夜”以及“几个佣仆被招入时,好像约齐而来”等细节失实。《飞絮》在广告中称,影片的主题是“为被压迫的女性呐喊,向旧社会的壁垒冲锋!”①阶级态度极为分明,而观众“墨一”看到的却是影片的失实:“在目前农村破产的危险时代,这一部完全根据农村作背景的《飞絮》,可惜放过了穿插农业惨状的一点。譬如当秀贞将去做婢女的时候,画面上可以反映出一些颓败的形状。否则,在银幕上至少好添上秀贞母亲的说话:‘秀贞,你放心去吧,种田是靠不住了,何况又一个多月不下雨呢?这样不是使《飞絮》有了很好的侧面立场?”②这些批评虽不够专业,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与专业影评人殊途同归,甚至更为细致,更真实地反映了“一般人”的观影感受。③而这些“普通”的观众,观影的重点也并不仅止于感官上的享乐和刺激,他们有相对独立、客观、理性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海”观众的影评中,没有如《晨报》早期的“每日电影”、后期《民报》的“影谭”那样话语阶级化,或者因“软”“硬”之别而呈现出剑拔弩张之态,它的话语空间一直呈现出平和、多元且开放之态。
至于吴承达所称“精神上粮食之转移”,如何转移,向哪里转移,亦值得关注,它直接关系到“艺海”的办刊宗旨。1931年到1932年之间,明星、联华、天一等电影公司纷纷转向,左翼电影的时代大幕徐徐拉开。此时的“转移”是如1925年“艺海”创刊时严独鹤所说的“引起民众对于艺术之兴趣”,还是将观众完全导向左翼电影特别强调的“进步”之中,抑或其他?
1934年2月14日,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有声影片《姊妹花》在新光大戏院首映,受到热烈欢迎,连映60天,打破了中外一切影片的卖座纪录,一举扭转明星公司的负债局面。2月17日,“艺海”刊出吴承达和叶逸芳同时为《姊妹花》所作的影评。吴承达开篇介绍《姊妹花》的剧情梗概,第一句为“爸爸把妹妹卖给军阀做姨太太”,将其叙述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八卦故事。对于票房表现出来的热情,吳承达却选择了冷静克制的批评:一是主题与结局的处理相矛盾。《姊妹花》的主题是“要把‘富人与‘贫人的生活悬殊,作一强有力的讽刺的,然而……那个姊姊的从贫苦中得到生路,结果却还是仰仗于她富贵的妹妹”,不仅对贫富描写失实,而且“不啻在替因果说教着”;二是巧合过多而失实。“假使那爸爸不卖女儿做官太太,假使第二个女儿不凑巧到那官太太——也就是妹妹的家里做乳娘,假使乳娘偷金锁片不恰巧给小姐看见,假使看见了小姐不那么会动武地拿出刀来刺乳娘,假使乳娘抵抗时不凑巧那花瓶掷死了那小姐,假使她妈妈探监时不凑巧碰见了她丈夫……”吴承达认为“小小的巧合也足以破坏完善作品的整个”;三是《姊妹花》对于军阀的恶暴露得不够彻底,革命运动之“正大”表现得不够深刻。吴承达唯一肯定的是“昏聩的父亲的出卖女儿”是极精警的。借此,吴认为电影不能只一味迎合“一般”心理,更不能当“儿戏”④,承认了电影的教育功能。不难看出,吴氏的批评既注意影评的趣味性及可读性,亦不回避革命话语,更有电影教育功能的认可,与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批评均判然有别。
从《姊妹花》至《渔光曲》问世,这一批评话语一以贯之。郑伯奇在批评《渔光曲》时开篇便称:“这是一部……典型的小市民电影。”其中的“小市民”颇勘玩味:
作者的观点是非常动摇的,他同情穷苦的人们,如小猫的一家和他的舅舅等,但他也同情赵大户和他的儿子。同情穷人是因为他们穷苦,同情赵大户是因为他上了都会里坏人的当。在全剧中,一切的罪恶似乎都聚集在袁丛美和谈瑛所扮的那一对“坏坯子”身上。假使没有这坏人的偶然登场,那么,穷苦人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合理,这一切的责任将要归结到无可如何的运命么?尤其是赵大户的性格,因为作者观点的动摇,简直形成前后矛盾,判若两人。在前半,他是一个刻薄残酷的地主,到后面,竟变成了一个单纯善良的可怜虫了。至于罗朋所扮的儿子,俨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人物。这些动摇、矛盾和超现实等等缺点是《渔光曲》的致命伤。①
再来看吴承达的影评:
这确是继《人生》后联华的一部力作。
在这悱恻的诗般的画面开展中,由那恬静的情调逐渐地吟出了它底哀曲。只觉得一阵一阵的辛酸逼上每个观众的心头来!
……
写在大自然底怀抱中,渔人们的痛苦和挣扎……一对流浪的孩子们,在饥寒交迫的母亲怀里产生了后,丧失了他们的爸,而又剩了一个目盲的妈。农村的破产,租主的残忍,他们只能从那非人的生活的农村里奔投到幻想着美满的都市里。但是贫人总是贫人的世界,在今日的乡村里是如此,在现实的都市里也未尝不是如此。反之,富人还是富人的世界,农村的破产动摇不了他们,他们一般的可以逍遥在都市里。②
郑伯奇与吴承达的影评呈现出鲜明的“参差对照”:郑伯奇笔下的“小市民电影”“都会里的坏人”“穷人”等,在吴承达笔下是“力作”“富人”“贫人”。偶然性的强调,在郑伯奇笔下是“小市民倾向的又一个特点”,根源在“小市民”信奉的“命运论”“神秘论”③,吴承达却从电影叙事学和美学立场出发,认为它恰恰是破坏影片整体性和艺术性的关隘④,无涉阶级。二者笔下,同一部电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话语政治:从微观层面,我们看到了表达的差异;从宏观层面,却看到了电影批评的多元生态。吴承达的电影批评是在电影技术和艺术、观众的审美期待和社会文化视野中去理解电影,评点电影,并将个人化的观感传递给电影观众和剧作者——在面对电影这一现代文化工业产品时,他并不喜欢以“进步”与“落后”,“资产阶级”“小市民”“无产阶级”等意识形态性的话语阐释和批评作品,而是以一位职业影评人的身份撰写影评,注重从“一般人”的观影感受出发,为“一般人”代言。与郑伯奇的阶级立场或者说“教育”目的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吴承达认为镜头中呈现的诗意以及导演深谙电影艺术的叙事手段功莫大焉:
那恬静的东海,在晨光熹微之中,闪闪作光,叹为奇观,即在风和日暖的氛围也是水天一色,绝好的诗意画意。以这样幽美的外景,演奏着这么一首哀歌。前半部的空气严肃先予观众以深刻的感动,到后来写到了这繁荣的都市,它又用着最好的对比,以三盅威士忌淡入三碗熟煮的山芋皮,复以在嬉笑情形之被掷出一酒瓶而接写流浪者之争夺……
导演者竭尽了冷嘲热骂的能事,其手法的简洁有力,更是难得。①
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对《姊妹花》及一系列左翼电影的差异化理解、态度以及观感,恰如李多珏女士所强调的左翼电影在技术、理念对世界电影的真正贡献那样,在“吴艺海”这里,无论是左翼电影、商业电影还是教育电影、国防电影……技术、艺术和叙事上的突破是影评的重心。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我们看到,吴承达的电影批评,没有以“启蒙者的姿态来帮助电影作家创造能够理解艺术的观众”②,而是基于商业的考量,同时亦非全然的“金钱主义”,从《电影的构造》(白幔,1933年8月2日~22日)、《电影艺术的本身》(逸芳,1933年8月8日)、《今后的国片》(仍我,1933年8月30日~31日)、《电影教育之意义与价值》(黄影呆,1933年9月5日)、《转变期中的中国电影》(翰笙,1933年10月12日)、《苏俄影业的新动向》(元剑、秋晓合译,1933年11月19~30日)、《有声电影论》(侯枫译,1934年1月1日~23日)、《美国电影界之病态及补救》(罗树森,1934年1月25日~29日)、《音乐及其他》(达,1934年2月3日~6日)、《电影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侯枫译述,1934年3月4日~27日)等文章也不难看出,“艺海”的内容选择多基于对电影技术、艺术及观众欣赏能力的提升为核心,以李道新先生所确立的“电影特质批评”为特色,目的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电影有所作为,并不止于“一般人”的消遣。③与“每日电影”“电影专刊”相比,“艺海”对左翼电影阶级话语的阐释“力度”的确有所“弱化”,它对左翼电影乃至其他各类电影的发力处,在“隐身于意识形态内容中的机巧、实验和各种技术及理念的发展可能性”④。
1935年年底,“电通”被迫解散;1936年1月27日,《晨报》被勒令停刊,不久,左翼作家联盟宣告解散,成立了上海剧作者协会。6月,中国文艺界协会成立,鲁迅、茅盾、巴金等四十二人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叶圣陶、包天笑、周瘦鹃等二十一人共同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内忧外患之际,“软硬电影之争”落下帷幕。就在此时,从产业及资本角度,吴承达从美国电影摄制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内容生产的娱乐性出发,反思了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发展的方向:
一层是它们的摄制技术,其进步实在惊人。“以它们一部五彩短片,足抵中国十部巨片。”这句话绝非信口雌黄,实在美国电影从声、色、立体以至未来的嗅觉等,太使人叹奇和折服!他们有这些可以完美形式上一切的主要条件,为什么不可一跃而站在世界电影的最前线呢?
另一层,美国电影内容,什九属于娱乐性质的,我们指说他们软性,他们糜乱,在他们自己,正有何妨?美国国民性的乐观主義,我相信多少和他们的影片有相当关系。在他们的国家中,具有着一切完备的行政和教育,原是不一定需要向电影这一部门借重。虽然今日美国电影也已感到了在这暴风雨的前夜,电影也有转变一下的必要,因此年来尽多战争历史等片的摄制,不过在美国国民,以娱乐为原则,软性很好,硬性也无不好。⑤
乍一看,这一论调与软性电影论似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但与刘呐鸥、黄嘉谟等人鲜明的软性立场不同的是,吴承达在软与硬之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从上面《渔光曲》的影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样的立场在吴氏的影评中一以贯之——他更关注电影的文化工业属性,更重视技术与资本在电影发展中的保障地位,左右票房的观影人群的趣味及电影的娱乐功能在这里显出其重要,与洪深不同,“内容是否卫生”并不是吴氏关注的前提和中心。吴氏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精通多国语言,英文尤其好,加盟“艺海”之前,曾译英美刊物文章为“快活林”投稿,亦可流利翻译外电为要闻版投稿;加盟“艺海”之后,副刊上的“‘好莱坞银色动态、明星生活、百老汇戏院状况、歌舞曲谱”,都是吴承达通过浏览英美杂志而后译介过来,被时人称赞“椿椿件件介绍,海外之部,可说尽善尽美”①。在分析美国电影将娱乐性奉为首位的原因时,吴氏特别强调美国电影并不以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即“教育”为责任,因为美国“具有着一切完备的行政和教育”,因而“软性也好,硬性也无不好”,或许就是这样的影评立场,导致了他与“一般影评人”“情感不甚和洽”②。而“年来尽多战争历史等片的摄制”,也是因为彼时国际形势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完全以大众的观影心理也即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标准影评”③视之实为不谬。虽然被“离离”在《民报》“影谭”上批评为“当作投资而活动”④,事实上,其以“经营”为核心的电影观与其现实的人生追求的确实现了彼此成全⑤,但从技术、艺术、叙事等角度视之,秉持“经营观”的“艺海”,除了“金钱主义”之外,在中国电影史书写中是否有贡献,如果有,贡献何在?
三 被“遮蔽”的“传续”:中国电影批评多元生态之一隅
日本著名左派电影评论家、理论家岩崎昶曾指出:“把艺术这话,当作一种表现形式时,自然电影是艺术。但真正理解电影的,他知道电影首先是一种商业、企业,为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的产物。”⑥岩崎昶的电影理论无法摆脱他本人的政治倾向以及时代的烙印,但岩崎昶的客观在于,他首先承认电影是以现代企业形式和商业生产机制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无独有偶,半个多世纪之后,李多钰女士在撰写《中国电影百年:1905—1976》一书时,“前言”中亦开门见山:“电影史也是一种需要金钱堆砌的昂贵历史。”⑦迄今为止,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一代风流,似乎尽由“左翼电影”独揽,然而,这种以“主题”“主流”为入口的历时性历史叙事,部分遮蔽了电影的文化工业属性,亦难以全面展示左翼电影对世界电影的历史贡献。李多钰女士指出:
……为左翼电影设立的这个神圣的祭坛渲染了“左翼”一词最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面,却掩盖了它对中国电影的真正贡献。如今看来,那些隐身于意识形态内容中的的机巧、实验和各种技术及理念的发展可能性令人无法不联想到十年后才诞生、却影响了世界电影发展走势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①
左翼电影自身所拥有的丰富性,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巨大贡献,恰恰不是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的“左翼”,而是对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承上启下,从电影技术、电影艺术乃至电影理念等方面作出的开创性的探索和尝试,譬如《狂流》电影叙事与纪录片的接榫、《春蚕》由跟摄镜头建构的“生活流”的记录风格及电影叙事的散文化、第一部有声片《桃李劫》中大段音响的叙事表达以及对本土电影盈利模式的探索,等等。左翼电影命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软性电影”“民族电影”“教育电影”“国防电影”,乃至不可胜数的商业电影。事实上,作为一种艺术门类,也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华图景,是由各类电影共同绘制的,然而,始终以“阶级”“进步”“革命”为主轴的电影史书写,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类型电影,特别是占据着大半壁江山的国产商业电影如《白金龙》②《飞来福》③《貂蝉》④《木兰从军》⑤等,在中国电影史上或前无古人、或承前启后的历史贡献,始终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承认,成为历史书写中的“弱势”。而左翼电影自身,亦与商业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⑥。窃以为,电影史对这些细节的相关探查,尚不充分。不满足于人为地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所谓的“主流”或有意或无意漠视那些以此为参照的“边缘的”“支流”,还原历史的丰富性,确立多元史观,从共时叙事的立场“重写”电影史,此刻显出意义。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宏阔图景,迄至今日,在有意与无意间,依然部分地受到遮蔽。⑦这一方面来自基础研究不足导致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与“中心—边缘”史观带来的聚散效应有关,当然政治导向、时代风气、教材编写以及研究者的兴趣等,也都与“遮蔽”脱不了干系。“艺海”历史书写的缺位及其评价与历史本然之间的差距,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艺术副刊”到“商业电影副刊”,《新闻报》的“艺海”实践了一条对接市民观影趣味并引之导之的探索之路。从1926年到1933年,虽然暂停了七年,“艺海”却意外经历了中国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转型,影像叙事从“文字”转向“声音”①、从“艺术”转向“娱乐”,观众从“小众”转为“大众”的划时代变革。同时,以“代言”而不是以“批评”“教育”,以电影本体技术、现代观念为目的而不是以“浓郁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话语转变,亦成为1933之后“艺海”一以贯之的副刊经营理念,进而形成自己的平民视角及兼容并包的副刊特色,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晨报·每日电影》《民报·影谭》等电影副刊的“进步”判然有别②。而“艺海”对“一二八以前的旧的电影批评”③有所坚持的真正历史贡献或许在于,它在事实上肯定了中国本土电影自《难夫难妻》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孤儿救祖记》《空谷兰》《火烧红莲寺》等系列故事片确立下来的中国商业电影盈利模式,更包括其“批评空间”——电影本事、电影批评、电影叙事等——的传续和发展,并以此为前提,见证了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艰难成长,推动了中国电影迅速步入现代化的世界轨辙,与世界电影对话,为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商业电影时代的“自由与繁荣”④奠定了基础:积累了资本,培育了消费市场及专业化的电影制作队伍,在“孤岛”这一特殊的地缘时空中,中国本土电影得以保持前期的活跃态势,不断前行。在这个意义上,“艺海”从“艺术副刊”到“商业电影副刊”的转型,副刊风格从“教育”到“代言”的转变,副刊读者从“小众”到“大众”的文化实践,在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中,无疑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恰是在“历史和传统的面貌”⑤底下,“艺海”以貌似“旧”的电影批评,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从技术、内容、形式乃至艺术的对话,为彼时的电影批评带来张力的同时,也保证了各副刊之间批评话语形态的多元,表现出差异化的文化政治。而恰是这些丰富的“差异”,使我们得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产业生态,亦托举起中国电影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石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报纸文艺副刊(1898—1949)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20&ZD285)的阶段性成果,上海大学“影视文学创意与资源开发”创新团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