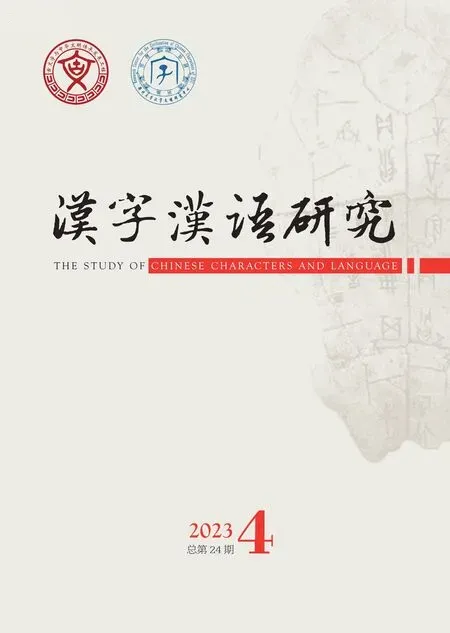域外汉字异体字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以日本汉文古辞书《倭名类聚抄》为例
2023-03-22刘寒青
刘 寒 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提 要 本文站在汉字发展史的视角下,将域外汉字异体字的发展情况纳入整个汉字系统的研究当中。以日本汉文古辞书《倭名类聚抄》为例,穷尽性整理《倭名类聚抄》不同时代抄本中异体字的情况,并且参照同时期其他日本汉文古辞书。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日存变体”这一概念,并总结出域外汉字异体字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几种趋势与特征:1.继承性和保守性;2.字形变异程度加剧;3.类化原则影响加深;4.增补汉字异体字发展材料。
域外汉字所呈现的汉字使用与发展情况,是汉字系统庞大根系伸向域外的一根枝条,它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汉字发展情况,又产生新的变化,具备新的特征。日本汉字是域外汉字中重要的一脉分支,从传入日本开始,汉字便在日本生根发芽,汉字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日本,经历了“接受—使用—改造—融合”这样逐渐深化的过程。本文站在汉字发展史的视角,将汉字的域外发展情况纳入整个汉字系统的研究当中,分析汉字在域外汉文典籍中表现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而研究日藏汉文典籍中域外汉字异体字的使用和发展情况,是了解域外汉字发展的必经之路。
《倭名类聚抄》是日本汉学家源顺于日本平安时代承平初年编纂的百科全书式汉和辞书,通篇以汉语写成,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意义分类辞书。流传至今的《倭名类聚抄》抄本种类丰富,从平安时代到明治时代都有抄本传世。《倭名类聚抄》版本系统中最古的两个抄本是高山寺本①高山寺本是二十卷本系统中最古老的抄本,藏于日本天立图书馆。该本为残本,现存五卷,即卷六至卷十。和真福寺本②真福寺本是十卷本系统中抄写年代最早的本子,藏于日本名古屋市大须宝生院。真福寺本残损非常严重,只剩余卷一和卷二的部分内容,卷一为完整的一卷,卷二为残卷。,高山寺本为平安时代抄本,大致相当于我国晚唐五代时期;真福寺本为镰仓时代抄本,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南宋时期。伊势十卷本、二十卷本《倭名类聚抄》的抄写年代均为室町初期,相当于我国的元朝初年,是除了高山寺本和真福寺本之外,年代较早的抄本,天正本则为室町中期的抄本。
虽然《倭名类聚抄》的不同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跨度,但其中所体现出的文字问题却是相互关联的。远离了汉字使用的本土环境,域外汉字的发展状况并不与中国本土的汉字发展同步,其存在着四种鲜明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1.继承性和保守性
1.1 继承性
《倭名类聚抄》各个抄本中使用的异体字,见于中国字书、韵书,或其他文字材料中的占了绝大部分。经过系统对比,《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的异体字与汉魏碑刻及敦煌写卷中的字形有着极高的吻合率,尤其是敦煌写卷。《倭名类聚抄》抄本中那些不常见于传世字书、韵书中的异体字字形往往能在敦煌写卷中找到对应关系。
《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异体字与汉魏碑刻及敦煌写卷的字形吻合,不仅是一字一形的,更是在变异方式和变异类型上存在一致性。《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异构字义符和声符的替换、增删等都与敦煌写卷中的异构字特征一致。例如,《倭名类聚抄》中异构字的声符换用体现出西北方音的特点。如《倭名类聚抄》中的“院”常写作“ ”,这种情况在敦煌写卷中也较为常见。“ ”是“院”改换声符的异构字,“院”字为云母,“宛”为影母,影母归入喻母,与云母相谐,是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存在的现象。
相比异构字,异写字的随意性更强,因时代、书手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但在《倭名类聚抄》和敦煌写卷中,不仅异构字有着相似的变形规律,异写字的变异也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走向。
1.2 保守性
《倭名类聚抄》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承平初年,相当于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这个阶段《倭名类聚抄》中使用异体字的情况自然受到中国本土通行的异体字的影响,与敦煌写卷和更早期的汉魏碑刻呈现出一致性。但就如同离开躯干的枝条无法继续生长,随着日本逐渐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两国之间交流逐渐滞缓,平安时期之后日本汉字的使用与发展情况逐渐显现出保守性与滞后性。《倭名类聚抄》不同时代抄本中使用异体字的情况并不与同时期的中国本土的汉字发展情况直接相关。
因避讳而产生的异体字时代特征最为明显。《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因遵循唐代避讳规则而导致的异体字十分常见。敦煌写卷的唐代文献中“世”字和一系列以“世”为构件的字如“牒”“葉”“棄”②“棄”字中的构件并非“世”字,但因中间的部分与“世”字相近,也常因避讳而改写。等,常因唐太宗李世民而避讳改写,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世’字因唐太宗讳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从‘云’。”这样的避讳规则同样在《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发挥着作用,并且这种避讳字的书写习惯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消失,室町早、中期(相当于我国的元朝早、中期)《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的“世”字,包括以“世”为构件的字依旧因循着和唐代一样的避讳写法。如“世”字的缺笔,《倭》卷八“久世”③久世,地名。地处美作乡大庭郡。,其中“世”字天正本作“”。《倭》卷十三“葉椀”,其中“葉”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三“牒”,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除了避讳字之外,《倭名类聚抄》抄本中还有一些时代性非常鲜明的异体字。如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初期的《倭名类聚抄》抄本中,武周新字依旧偶有使用,如“国”写作“圀”等。
《倭名类聚抄》不同时代抄本中使用的异体字,见于中国字书、韵书,或汉魏碑刻及敦煌写卷等文字材料中的占了绝大部分,这是受到日本平安时期汉字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日本较为保守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的汉字学习者和使用者会尽量维持汉字字形的原貌。所以《倭名类聚抄》在编纂和抄写的过程中较为忠实地记录和摹写了中国文字材料中的异体字字形。然而包括日本汉字在内的域外汉字,因远离汉字使用的本土环境,容易形成“孤岛型”的封闭使用环境,从而使域外汉字的异体字发展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
2.字形变异程度加剧
除了继承自中国文字材料中的异体字,《倭名类聚抄》抄本中还存在部分并不常见于中国的字书、韵书,或其他文字材料中的异体字。然而中国不仅传世文字材料卷帙浩繁,出土文字材料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在实际考察中很难做到对自古至今所有的文字材料进行穷尽性、彻底的排查。所能依靠的是对各类文字编、异体字字典和数据库进行检索,对在上述范围内依旧未检索到的异体字,本文提出了“日存变体”这一概念。“日存变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执着于讨论这部分异体字是否产生于日本,而是突出这些异体字在中国本土异体字发展序列中的非典型性。
虽然称之为“日存变体”,但它们依旧与中国文字材料中的异体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很多“日存变体”类异体字是在中国文字材料中常见异体字的基础上加深了变异的程度。“日存变体”中异写字占绝大多数,这种现象说明在印刷时代之前,汉字规范的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构件层面,对于非汉语母语的学习者来说,他们在使用汉字时主要容易在笔画层面发生书写变异。例如:
《倭》卷六“缀喜”①缀喜,地名。地处山城乡缀喜郡。两见,其中“喜”字高山寺本皆作“”。《倭》卷八“久喜”②久喜,地名。地处长门乡厚狭郡。,其中“喜”字高山寺本作“”。《说文·喜部》:“喜,乐也。从壴从口。”“”字为构件“壴”发生了笔画上的变异。从《倭名类聚抄》中保留的“喜”字的其他异写形体,我们能够看到从“喜”到“”的笔画变异过程,《倭名类聚抄》中“喜”亦常写作“”,这个字形在汉魏碑刻和敦煌写卷中也十分常见,如北魏《司马王亮等造像记》“喜”作“”,北齐《居士讳道明墓志》“喜”作“”,甘博003 号《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喜”作“”,敦研016 号《自在王菩萨经》中“喜”作“”。在此基础上,“”字中与“口”相接的短竖进一步拉长歪斜之后,变为一撇,导致整体字形的变异进一步加深,则有“”形。
《倭》卷十二“帼,妇人喪冠也”,其中“喪”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是“喪”字构件简省和笔形变化形成的异体字,其字形的由来并非无迹可寻,《倭名类聚抄》中“喪”的形近字的异体变化形式为追溯“喪”字的异体字变化轨迹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如《倭名类聚抄》中“囊”多写作“”,《倭》卷十二“袋,囊名”,其中“囊”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囊”字又写作“”,《倭》卷十三“漉水囊”,其中“囊”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倭》卷八“美囊郡”,其中“囊”字高山寺本作“”。《说文·㯻部》:“囊,橐也。从㯻省,襄省声。”《干禄字书·平声》:“囊”,“上俗下正”。“囊”字上部构件本是“㯻”字之省,因书写变异而成为“”,《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的短竖变为一撇,并发生相对位置变化,则成为“”,“”进一步减省构件“口”,则有“右”“古”等构件。“”与“喪”字上部构件同形,两个同形构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共享同样的变异轨迹,受到类化原则的影响,《倭名类聚抄》中“喪”字亦常写作“”。
【刄】
《倭》卷十三“叉,两歧铁[叉]②[ ]内文字为《倭名类聚抄》底本中有脱文,根据他本或上下文义补足,下同。,柄长六尺”,其中“叉”字伊势二十卷本及天正本作“刄”。中国字书、韵书中未见载有“刄”“叉”二字之间的异体关系,《宋元以来俗字谱》收录“刄”为“刃”之异体,与“叉”字无涉。汉魏碑刻及敦煌写卷中也少见“叉”字写作“刄”的实例。“叉”写为“刄”是笔画类型发生了变化,点画变为一撇,《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叉”写作“刄”并非孤例,且抄本中其他以“叉”为构件的字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异,如靱(靫),(刈)等。《倭名类聚抄》抄本中“靱”为“靫”之异体,表示“箭袋”之义,与“韧”之异体“靱”为同形异字,音义无涉。《倭名类聚抄》中“”为“刈”之异体,《倭》卷十七“穧,刈[禾]把数”,其中“刈”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五“刈”,其中“刈”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通过上文例字,可以看出从“刈”到“”的演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为中间过渡形体,“”字中的构件“刄”仍是从“叉”变异而来,刈——形成了“刈”完整的异体字发展轨迹。
《倭》卷十五“辘轳,圆转木机也”,其中“圆”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字是构件记号化形成的异体字,中间一笔为“纯符形体”,起到减省笔画的作用,“纯符形体是隶书之后汉字中出现的新的形体现象,是汉字不完全追求构形意图及形义统一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情况一直传到了楷书中”(王贵元,2016:158)。“”字进一步发生变异,则成为日本常用的和制汉字“円”。造成纯符形体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字体之间的转写,包括篆隶转写和草楷转写两种。篆隶转写发生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草楷转写主要发生在楷书的定型期。二是趋于简化的汉字字形发展趋势,“书写便捷”是贯穿整个汉字发展史的内在驱动因素,脱离象形阶段之后,汉字发展中一直存在用笔画简单的记号构件替代原有字形中的声符、义符的现象。使用记号构件来实现笔画减省的情况,在域外汉字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屡见不鲜。如,《倭名类聚抄》抄本中,除“圆”字外,仍在其他字形中有不同的构件被省写为一撇或短竖,如(风)(面)、(同)等。
《倭》卷六“尾张乡”,卷七“真张”①真张,地名,地处下野乡山田郡。,卷十二“开张以臂屈伸”,卷十三“张华《博物志》”,其中“张”字高山寺本、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日本同时代较早期的汉文字书《新撰字镜》中“张”字亦写作“”。构件“”并非源自构件替换,而是“弓”的异写形体。敦煌写卷中作为构件的“弓”常写作“”“”等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生形变,变连笔为断笔,即“”形。我们从《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张”字其他的异体字书写时留存的笔道也可以看出从“弓”到“”的发展轨迹,如(张)。除了“张”字外,《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其他从“弓”的字,也发生了一致的变异,如(引)、(弘)等字。变异后的“弓”与“方”形似,这就导致了在《倭名类聚抄》抄本中“方”和“弓”两个构件的替换是双向的,《倭名类聚抄》抄本中“方”在作构件时也常被写作“弓”形,如《倭》卷二“《九族图》”,其中“族”字伊势二十卷本作“”,天正本作“”,中国文字材料中少见“族”字的此种写法。
《倭》卷十五“以食诱鱼鸟也”,其中“食”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六“宜食白饮”,其中“食”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说文·食部》:“食(),一米也。从皀亼声。或说亼皀也。”《字汇·食部》:“,食本字从㿝,古香字,米之气味也”。“”“”在汉魏碑刻和敦煌写卷中均是较为常见的字形,如北魏《元怿墓志》“食”作“”;敦研032 号《四分律》“食”作“”。构件“厶”“匕”进一步发生书写变异成为“八”,则形成了《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常见的“”字。
《倭名类聚抄》中很多从“埶”的字其中的“坴”都写作“生”。《倭》卷八“安藝郡”,其中“藝”字高山寺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三“勢似飞来”,其中“”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六“食熱腻物”,其中“熱”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倭》卷十四“褻器”,其中“褻”字伊势二十卷本、天正本皆作“”。从“坴”到“生”并非构件的改换,而是受到类化原则的影响而导致的构件趋同。敦煌写卷中“勢”字常写作“”或“”,构件“坴”因笔画减省变为“圭”,继而因形近与“主”发生混同,“主”又因与“生”形近而发生形混,遂有《倭名类聚抄》中常见的“”形。
从上述字例可以看出,很多“日存变体”类异体字是在中国文字材料中常见的异体字的基础上加深了异化的程度,如食——,囊——等。在汉字的原生使用环境中,很多字形如果过度变形,容易与其他汉字的异体字发生混淆,例如“”字很容易与“贪”的异写字“”①字形见于《汉隶字源·平声·覃韵·贪字》引《巴郡太守张纳功德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年。相混淆。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汉字构形系统的别异性原则会制约着汉字形体的过度异化,而当汉字作为外来文字进入其他国家的语言环境中时,这种制约性相对地被削弱了,导致部分异体字的变异程度进一步加剧,形成了本文所说的“日存变体”。
3.类化原则影响加深
类化原则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影响异体字的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原则之一。因类化原则而形成的异体字,通常都是受到形近字、前后字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使用语境的影响,增减或改换构件,与其他汉字字形趋于一致。部分类化字是不符合汉字构形规律的,是无理据的形体,所以这部分类化字具有临时性和条件限定性,而受到汉字构形系统性和表意性的制约,汉字系统本身不容许存在大量的不符合其构形理据的类化字。
《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类化原则同样发挥着作用,且因为脱离了汉字的原生环境,汉字构形系统性和表意性的制约力减弱,类化原则在域外汉字异体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例如:
《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类化原则影响的往往不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汉字字形,而是一系列字。如敦煌写卷中从“卯”的字,常见的变异方式是变“卯”为“夘”,如“柳”字的异体作“栁”,“卿”字的异体作“”。而《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很多与“卯”无涉的字,受到类化原则的影响,其中的部分构件也都趋向于写作“夘”或“夕(歹)”形。如,《倭》卷六至卷九“鄉里部”地名中涉及的“鄉”字,高山寺本多作“”,天正本多作“”。《倭》卷十“弘徽殿”,其中“徽”字高山寺本作“”,天正本作“”。《倭》卷十“孙炎”,其中“孙”字高山寺本作“”,除此之外还有(辨)、(斑)等字。这些汉字中不同的构件如“乡”“系”“文”“子”等,本与“卯”字无涉,但因构件间的趋同效应,均变异为“夘”或“夕(歹)”,这是类化原则加深造成的趋同。
《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类化原则的加深,不仅体现在其带来的更大范围的不同构件之间的趋同,也体现在趋同后的独体字在参加构形时所产生的影响。《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土”字存在“土—圡—”这样的变异路径,中国文字材料中虽然存在少量“土”写作“”的例子,如唐《开业寺碑》中的“土”字作“”,但以“土”为构件的合体字则少见以“”构形的,大多是以“土”“圡”作为构件。而《倭名类聚抄》抄本中,从“土”的字以“”构形和以“土”“圡”构形的频率几乎是一样的,如(壁),(堂),(塞),(塾)等。究其原因,除了字形变异程度的加剧,也是受类化原则的影响,受到“云”“尝”“去”“丢”等字中形近成分的影响。相较于“圡”字,“”变形过度,容易与其他字形混淆,如“去”,“立”的异写形体“”等,所以在中国文字材料中“土”作为构件最多变异至“圡”的程度,这是汉字构形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别异性对于字形变异程度的约束。但在《倭名类聚抄》中,因为离开了汉字本身的原生环境,这种约束性遭到了破坏。
与“异化加剧”主要针对同一汉字纵深发展不同的是,“类化加深”是发生在一系列具有相同或相似构件的汉字中间的。归并形近构件,用形体相对简单的构件同化复杂构件,减少记忆与书写的负担,是域外汉字异体字发展中类化原则影响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4.增补异体字发展材料
《倭名类聚抄》中留存的字形,可以为汉字异体字发展提供补充材料。汉字字形的发展往往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断裂式的发展是比较少见的,一些看似无理或无法厘清变异脉络的异体字形,大部分是因为缺少了中间一环的字形,《倭名类聚抄》中留存下来的一些异体字形恰好能够弥补部分缺失。如《龙龛手镜》卷四“,古文,音峻”,“”字于中国字书、韵书中少见,《汉语大字典》未收,《中华字海》仅收录字形、字音,而字义未详。结合《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留存的相关字形及其他文字材料,可知“”当为“囟”字之异体。《说文解字·囟部》:“,头会,匘盖也。象形。”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脑会。亦。”《倭》卷三“会”条目下,收录了“囟”的不同写法,真福寺本“会”,“字亦作”;天正本“会”,“字亦作”。其中“”“”皆为“囟”的异写字,结合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中的字形“”,可知“”为“囟”的异写字无疑。《倭名类聚抄》抄本中留存的字形“”“”与“”“”一起,构成了“囟”的异写字发展序列。
5.结语
《倭名类聚抄》抄本中异体字所呈现出的特点,与中国文字材料中的异体字一脉相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当汉字进入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环境时,汉字系统所具有的表意性、别异性等原则的制约能力会有所减弱,以致域外汉字在发展中常见字形变异加剧、类化原则影响加深等现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倭名类聚抄》等域外文献作为远离汉字原生土壤的域外汉字材料,不仅有助于研究汉字域外传播的各类现象,也可以通过对比研究来反观汉字自身,那些原本仅从汉字原生材料视角难以发现的现象,在域外汉字材料的对比之下得以呈现。利用域外汉字材料进行异体字字形、字用方面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在汉字构形理论和汉字发展史理论观照下的域外汉字研究仍是目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学术领域,也是有待形成系统性理论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