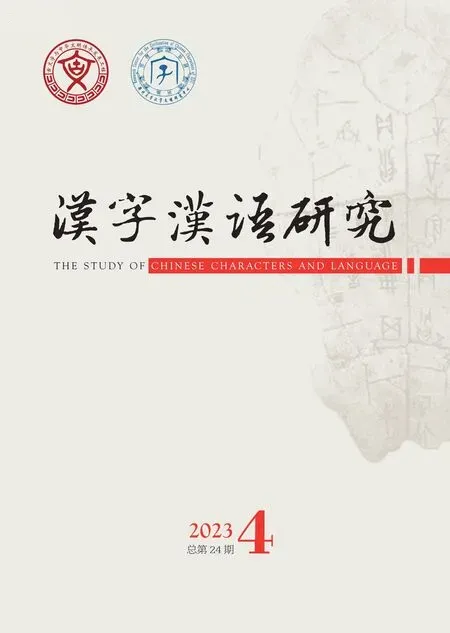从历代字书比较看汉字发展传承的路径与特点*
2023-03-22姚权贵史光辉
姚权贵 史光辉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2.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提 要 汉字的发展传承,在不同的文字资料中有不同的体现。历代字书在收字、析字方面,直观反映了汉字发展传承的一些路径及特点:汇辑历代字书韵书文献及其字形资料;呈现各时期汉字书写类型;揭示汉字源流演变与规律;文字的广泛搜集与集成处理;再现汉字使用的历史层次;考俗正讹,规范异体;不断强化正字观念。
1.引言
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到《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康》),历代字书在收字、析形、注音、释义和举证等方面贮存了大量汉字信息,它们为字书编纂、汉字史、汉字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材料。相较于其他文字资料,汉语字书所记载的汉字形音义、字际关系、字词关系、字用情况、文字观点等现象和问题无疑是最全面、最直观的。比如“響”字,《康·音部》:“古文、。《说文》:‘声也,从音乡声。’《玉篇》:‘应声也。’《集韵》:‘或作㗽。’《韵会》:‘又作鄉。’通作嚮、饗。”(戌集中54)①本文所用《康熙字典》为中华书局1958 年影印同文书局原本。这个本子编排上每卷都重新分页,故引文后皆用括号分别注明卷次和页码,引用格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康·人部》:‘使,……’(子集中11)”,第二种是“使,……(《康》子集中11)”,都表示“使”字出自《康》子集中人部第11 页。文中与“響”字演变存在关系的至少有6 字,《说文》只训“声”;《集韵》依俗改从口作“㗽”,《宋本玉篇》(以下简称《玉篇》)同之,故训“应声”(103)①为便于稽核,本文征引文献皆于引文后直接加括号标注页码、栏次等,引书一般使用简称。,则形义皆已有别;《韵会》又作“鄉”者,盖同声借之,从其简俗;通作“嚮”“饗”者,则以古文通假言之;而《康》所谓古文“ ”盖据《集韵》(414),“ ”则据《字汇补》(507B),皆楷书讹体,不可从;“響”字《古文四声韵》作“”“”等形,更甚有作“蜜”者(参看沈康年,2006:200A),皆讹也。汉字发展演变之多端,可见一斑。但正是通过历代字书收字、析字的比较,我们看到了汉字在字体、结构、体系、数量和使用情况等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发现了更多汉字传承演变的路径与特点。
2.汇辑历代字书韵书文献及其字形资料
承录前代字书、韵书,是后世字书收字的一大来源,也是汉字数量大幅增长的显征,其价值在于不仅钩稽了大量字书、韵书文献,并且将从前累积的字形完整保存下来,大大丰富了汉字文献及其字形资料,能补各类辑字文献及现行字书之不足。
又如“寶”字,我们先来看字书收录字形的情况:
(3)寚,《玉篇》:“古文寶字。”(《康》寅集上14)
(5)寳,《正字通》:“俗寶字。”(《康》寅集上17)
(9)珤,《玉篇》:“古文寶字。”(《康》午集上7)
(11)靌,《龙龛》:“同寶。”(《康》戌集备考39)
3.呈现各时期汉字书写类型
汉字书写类型丰富复杂,张涌泉(1996:177-232)整理敦煌俗字40 余种类型,又归纳俗字13 种基本类型(2010:44-121);曾良(2006:52-167)考辨古籍文字相通、相混类型共81 种,这些“类型”“通例”都能从历代字书中找到印证。
例如汉字书写从“妥”从“委”恒混,古籍文献颇多用例,如《可洪音义异体字表》(韩小荆,2009:659)“捼”或作“挼”,《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石榴㮃子”条脚注“㮃”或作“桵”(T54/480c)①本文凡引佛经语例,皆据《大正藏》影印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年。引文后用“(T 册/页栏)”标注出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三《菩萨问明品》:“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如有生王宫,而受餧与寒。”(T10/68a)“餧”异文作“馁”。又《蕤呬耶经》卷二《奉请供养品》:“隐摩豆唎迦香,胡荽香,诸树汁类香,如合香如法相和,随所合香皆置龙脑。”(T18/767b)“荽”字异文作“”(疑为“䔀”之讹),皆其例。而“妥”“委”二旁相混,能在字书中找到更多直观的印证,如:
(1) 娞,《广韵》“奴罪切”,《集韵》“弩罪切”,并“同婑”。娞,妍也。或从委。(《康》丑集下18)
(2) 挼,《唐韵》《集韵》并“奴禾切”,同捼……又《集韵》《韵会》并“奴回切”,音,义同,亦作捼。又《唐韵》《集韵》并“儒谁切”,音蕤,与捼同。(《康》卯集中22)
(4)浽,《博雅》:“浊也,或作涹。”(《康》巳集上23)
(5)绥,又《集韵》“:儒佳切,音蕤,緌,或作绥。”……《礼·王制》:“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注》“:绥当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康》未集中11)
(6)荽,《集韵》:“与萎通。”(《康》申集上16)
(8)餧,《广韵》《集韵》《韵会》并“于伪切”,音委。《玉篇》:“餧,饲也。”……按:餧、馁古通,今相承以餧为餧饲之餧,以馁为饥馁之馁,遂分为二。(《康》戌集下24)
(9)鮾,《广韵》“奴罪切”,《集韵》“弩罪切”,并音馁,与鯘同。鱼败也,通作馁,亦作鯘。(《康》亥集中6)
(10)鯘,《集韵》《韵会》并“弩罪切”,音馁,鱼败也……《类篇》:“或作馁。”(《康》亥集中8)
这些字例反映了各时期部件妥、委相混的情况,它们之所以混用不别,除了形体极为相近外,亦有音义方面的原因。《说文》“妥”字本逸,《说文解字注·女部》:“妥,《说文》失此字,偏旁用之,今补……若《檀弓》‘退然如不胜衣’,退或为妥,则二字双声。妥与蜕、脱、毻声亦皆近。”(626A-B)《说文逸字·女部》“妥”字考云:“本书‘馁’‘桵’‘挼’‘绥’皆从妥声,今‘馁’‘桵’讹从委,段氏已改。”(113)《篆隶万象名义·女部》(以下简称《万象名义》):“妥,汤果、汤回二反,安坐也。”(27B)《玉篇》注音相同(67),则“妥”字实有两读,今音分别为“tuǒ”和“tuī”。《集韵》平声灰韵通回切:“妥、绥,安坐也。”(108)《康·糸部》:“绥,《集韵》通回切,音推。妥,或作绥,安坐也。”(未集中11)与《万象名义》音义相同。又查《万象名义·女部》:“委,纡诡反,安也。”(25B)则与“妥”音相谐,义相近,此盖“妥”“委”相通之由。但《广韵》“妥”字未收“汤回”(tuī)一读,今《汉》(1105B)、《字海》(683B)注音一依《广韵》,自亦失载。
4.揭示汉字源流演变与规律
对汉字的形音义溯本清源,是字书的一大目标,例如《康》释字力求“穷流溯源,备载某书某篇,根据确凿”(凡例3),虽未必做到“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永瑢等,1965:355),但通过字书的辗转传录,能为考察单个字形的源流、汉字演变的普遍规律提供大量线索。例如:
(4)愍,《集韵》又眠见切,音面,元愍,混合也,或作惽,亦省作泯。(《康》巳集上35)
(5)漘,《集韵》:“或省作浱。”(《康》巳集上43)
(6)灕,又淋灕,秋雨也,亦省作漓。(《康》巳集上61)
(11)绰,古文繛。《说文》:“繛或省作绰。”(《康》未集中14)
(14)膻,《集韵》:“或省作胆。”(《康》未集下23)
按:裘锡圭(1988:28)指出:“从形体上看,汉字主要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据上15 字例可见,汉字形体简化是一大趋势,具体而言,又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简化方式。如例(4)愍→泯、(5)漘→浱、(6)灕→漓、(7)燪→㷓、(9)糷→→、(14)膻→胆等都是把原来比较繁复的声符变成形体简单的声符,即声符形体简化。有些是隶定带来的形体上简便,如例(10)“”隶省作“素”;有些则是通过形旁代换,换为更为精简的义符,如例(11)繛→绰、(12)→缓,《说文》中已明言其“或省”,就是把“素”换为形体简洁的“纟”,这一简化过程可递推为“→素→纟”。有些则是通过声旁替换,换为更为精简的声符,如例(13)→。还有一些简化是常见的俗写现象,如例(2)→洭、(3)→汪、(8)→軖的规律是“、㞷()→王”。
5.文字的广泛搜集与集成处理
历代字书不仅收字渠道广、字符样式多、字形数量大,还通过相承转录,将一个个汉字的古今形体、正俗异体、通用假借、传写讹误等各种情况完整呈现出来,实现汉字的集成处理,从而为建设大规模的汉字数据库提供帮助。例如:
6.再现汉字使用的历史层次
臧克和(2007)指出:“字书传抄变异过程,往往伴随着形音义的系统调整,体现出某种时间层次。”字书对各时期汉字使用情况有详细记录,通过字书比较,可以对“形音义的时间层次”有更深的探究。
例如“觸”字,《康》辑录相关字形如下:
(3)觕,又《广韵》:“尺玉切,与觸同。”(《康》酉集上8)
按:根据字书所载,能对“觸”字形音义的历时变化作一梳理。“觸”字战国文字从牛从角,如作“”“”等形,会牛以角抵人之意,据形隶定即作“”,秦汉文字改从角、蜀声,变为形声字(参看季旭昇,2010:373),故《说文》作“触”训“抵”。汉魏以来多以“”为“触”字古文,俗又变体作“觕”,《万象名义·角部》:“觸,先烛反,抵也,突也。,同上,古文。觕,同上。”(265B)例(4)《玉篇》作“”,例(3)《广韵》、例(6)《集韵》皆作“觕”即其证。唐宋以来,“觕”又偏旁易位作“”,《龙龛·角部》:“觕、,二或作,、觸,二正。”(512)例(4)《字汇补》、例(8)《篇海类编》皆作“”亦其证。而例(7)引《川篇》作“”则又为“”的简化俗字,例(9)引《搜真玉镜》作“”则为“觸”的繁化俗字。至于例(1)引《五音篇海》作“”,例(2)引《龙龛》作“”,盖流俗所用俗体会意字。查《龙龛·女部》:“、、,《旧藏》作觸,又郭氏音麁。”(284)或体作“”,《篇海·女部》引《搜真玉镜》:“,音麁。”(341B)俗又作“”“”,《龙龛·女部》:“、,二俗,音麁。”(280)诸字形近音同,皆一字之变。张涌泉(2000:519-520)认为“”“”疑即“麤”的俗字,以音求之,其说可信,但《龙龛》“”“”又音“觸”,且引《旧藏》正作“觸”,只认定为“麤”字之俗,或失于片面。据《康》所载,“麤(麁、粗)”与“(觸)”或可相通,故字有两音。《康·角部》:“觕,《公羊传·庄十年》:‘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注》:‘觕,麤也。’又通作粗。《礼·月令》:‘其器高以粗。’《吕览》作觕。《前汉·艺文志》:‘庶得麤觕。’又《叙传》:‘觕举僚职。’师古曰:‘觕,粗略也,大略也。’《正字通》:‘《说文》本作麤,俗作麄、粗,非。按《通雅》曰:世皆以觕为麤字。古盖各造粗字,至汉分之,麤为尘起之粗,平声。觕为一切之粗,上声。故班固《汉书》连用则异声,分用则同字。’”(酉集上8)又鹿部:“麤,按:《六书正讹》俗作麄觕,通用粗。”(亥集下6)又米部:“粗,《集韵》:‘或作觕,通作麤,俗作。’”(未集上31)皆可证。又“觸”今简化作“触”,刘复、李家瑞(1930:136)引《金瓶梅》作“”,引《岭南逸事》作“触”。但《康》并未收录简化的“触”字,例(5)“触”字,以音义求之,实为“”字错讹,《康·鱼部》:“《古今注》:‘白鱼赤尾者曰,一曰魭。或云雌者曰白鱼,雄者名。’”(亥集中4)音义全同,则《康》失收“觸”的简俗字“触”。再看音义的变化,例(6)引《唐韵》“尺玉切”、《集韵》“枢玉切”当音“觸”,《康》读“冲”入声疑有误。《说文》“觸”只训“抵”,《万象名义》增“突也”一训,考“突”本有“冲撞、触犯”之义,与“抵”可通。而又引《玉篇》训“据也”,“据”实为“揬”字形近之误(胡吉宣,1989:5187),则与《万象名义》训同。又引《增韵》训“污也”,《字汇·角部》:“觸,污也。”(233/252A)亦同训,盖六朝以来,“觸”多假借为“浊”,故有“污、浊”之训。
7.考俗正讹,规范异体
对汉字的正俗、异体、变体、错讹进行考释与规范,是衡量字书编纂水平的重要标准。在这些方面,后出字书总是在检讨前代得失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
一是考俗辨讹。传世字书如《玉篇》《龙龛》《篇海》等已收录了大量流俗字形,至《正字通》《康》不仅据时俗增收了很多字形,还对大批俗讹字进行了考正,今《汉》在辨析形近易讹字时,亦多引历史字书之成说,如“”(1648B-1649A)、“”(3236B)、“”(3370A)、“”(3634A)、“”(3630A)、“”(3697B)、“”(3699A)、“”(926B)、“”(3345A)、“”(2989A)、“”(3822A)、“”(4412A)等字,皆转录《康》之旧说为之解,足见其辨讹之功。
还有些字形的辨析,显示了对汉字俗写规律的正确认识,如《康·网部》:“,《字汇补》音义同。按:即字之讹。”(未集中33)认为“”为“”(“罶”之省形)字之讹,俗书“网(罒)”或异写作“”“冈”“”,例多不复举,故“”讹作“”。而“”字上从“”既为“网(罒)”之异写,《康》收在“网”部是,《汉》收在“夕”部(926B)欠妥。有些字例的考证,得到了现代学者考释结论的印证,如《康·鼻部》:“齀,张协《七命》:‘齀林蹶石,扣跋幽丛。’李善注:‘五忽反,以鼻摇动也。’按:音义与鼿同,疑即鼿字之误。《篇海》又入马韵,作五寡切,尤误。”(亥集下24)认为“齀”为“鼿”字之误,今《汉》“齀”(5095A)字引胡克家之说,与《康》说同旨。在考辨字形的同时,对一些错讹的音义信息亦作了考证,如《康·糸部》:“䌮,《玉篇》:‘色庄切,义阙。’按:《篇海》 云色庄貌,盖误以切音为训,非是。”(未集中29)认为《篇海》乃误以《玉篇》“色庄切”为训,其说可信,今本《篇海》正作“色庄切”(375B)。又如《康·豸部》:“,《篇海》:‘师闲切,音山,恶健也。’按:《说文》:‘狦,恶健犬也。’,即狦字。《篇海》止训曰恶健,非是。”(酉集中12-13)查《篇海·豸部》引《川篇》:“,所奸切,恶健也。”(339B)《新修玉篇》注引同(197B),《康》引作“师闲切”,恐据别本。以音义求之,并参考字形,“”殆即“狦(㹪)”字之讹,“狦”字《说文》训“恶健犬”,《篇海》类字书残误。
二是规范异体。字书从纷繁复杂的字际关系中,厘清构形部件的书写变易,正字异体的演变关系,从而对大量异体进行认同与规范。例如“表”字,《说文》篆体作“”,后世字书、韵书,《玉篇》《广韵》收,《集韵》收、,《类篇》收,《篇海类编》收,《字汇补》收,《康》据《直音》收,产生了7 个异体,从字形上看,基本上都是“表”字古文之变。《说文·衣部》:“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古文表,从麃。”其说已详矣。其中,“表”与“”,“”与“”形体相近,皆为一字变体。毛远明(2014:43)认为:“‘表’字作‘’,从‘毛’及其变体者均为隶古定字,由此不断简省讹变,形成正字‘表’,其他均为异体。”而字书中“”与“”显然又是“”的讹俗字;又“”“”“”“”形体相近,为一字之变,其中“”是《说文》所载“表”字古文,余例皆俗写变体。
8.不断强化正字观念
越到后来的字书,“正字”思想越强,其判定正俗、正或的重要标准,就是《说文》以来的字书、韵书是否见收。尽管在以简俗字为主流的近代汉字中,这种观念失于片面,但以此来整理异体、认定正体、厘清正俗关系、推行规范字,对于字形变化多端、关系纷繁错乱的近代汉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正字作用。例如:
(4) 吋,《字汇》:“徒口切,豆上声,叱也。”按:吋字诸韵书皆不载,止见《篇海》。《正字通》斥为俗字,是也。(《康》丑集上3)
(7)皩,《正字通》:“皝字之讹,《晋书》本作皝,俗加日,非。”(《康》午集中21)
(8)瞇,《集韵》:“母婢切,音弭,眇目也。”按:《字汇补》讹作,改音弥,亦训眇目,非。(《康》午集中45)
(11)緫,《集韵》:“麤丛切,音怱。繱或作緫,帛青色,一曰轻绢。”按:《五经文字》云:“緫从怱,作者讹。”今緫与混,当正之。(《康》未集中17)
(12)羗,《字汇补》:“与羐同。”按:即俗羌字。(《康》未集中37)
(16)觃,《广韵》:“于剑切,腌去声。觃口,墟名,在富春渚上。”按:《字汇补》一作,注见《集韵》,误。(《康》酉集上1)
(17)覝,《说文》:“察视也。”按:《说文》本作覝,从见声。俗作,非。《字汇补》一作,亦非。(《康》酉集上3)
按:上引20 例,《康》通过对“正字”的认定,辨析了一批俗字、讹字,从这些字形的来源看,《康》辨俗、辨讹的对象主要是《篇海》《字汇》以来收录俗字异体较多的字书、韵书,因为它们大抵都有“重收录轻考证”的缺点。从文字规范的角度看,《康》的观点基本正确,有些字的确是应该淘汰的不规范字,如例(2)中,近代汉字“休”多讹作“”,盖俗写有赘点或增笔的习惯。又如例(6)“”字,因为“足”字古文作“疋”,作“”既可能是“”的增笔字,亦可能是“足”字上口书写脱节产生的俗字;又“疋”字本是个同形字,古文可作“正”“足”字,近代又是“匹”的俗写,故上增一横以特作“足”字亦未可知。总之,今“足”“正”“匹”各有正字,俗体“疋”尚可保留,而“”则实在没有继续使用的必要。又如例(13)“巸”讹作“”字,恐张自烈据古文臆改。又例(15)“吞”讹作“”,盖古文“口”字两旁竖笔可上下出头,遂与“月”字形近而讹,这直接导致《康》《汉》(2194B)和《字海》(898B)等大型字书将字收在了“月”部,不得不说是一种误导。从上述例子可知,《康》论字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前代典籍(主要是字书韵书)是否收录,如例(1)认为“”字诸书无据;例(2)“”《玉篇》未收;例(4)“吋”诸韵书皆不载,止见《篇海》;例(19)“”诸书皆无,故皆为俗讹之字,当予以删汰。同时又以前代典籍收录的字形为规范正体,如例(10)《篇海》作“”,《广韵》作“”,故认为“”为正字,实际从字形上看,“”的确是由“”直接讹变来的,但“”实为“”字之讹(周祖谟,1960:255),亦非正体。又如例(16)“觃”《广韵》已见,《字汇补》引《集韵》一作“”,《康》以为《集韵》并无“”字,当从《广韵》为正。今考“”在《五音集韵》去声梵韵于剑切(187B),《字汇补》谓出《集韵》,盖其省称。又如例(17)“覝”字《说文》已见,俗作“”“”“”(皆见《龙龛》344)等,显即一字之形近讹误,当从《说文》正之。二是与汉字发展规律是否相符,从对文字的说解中,可看出《康》对汉字的书写变异规律有自身的认识与原则。如例(8)“瞇”字《字汇补》作“”,俗写“辶”多变作“”,概因手写疾书,或据草书形体楷定而来,但《康》认为这种变化实际是字形的讹变。又如例(11)“緫”与“”相混,是常见的俗字现象,但《康》以为当分别正之,这是与《五经文字》之类的字书相同的正字观念。又如例(20)认为《五音集韵》“”为“”之讹变,与今宁忌浮(1992:32)、《字海·食部》“,的讹字”(1620B)观点相同,显示了对文字形音义的准确认识,而《汉》“”(4948A)与“”(4954A)尚未沟通关系。有些字如果前代如《字汇》《正字通》《字汇补》等字书的论断符合自身对文字的观点,《康》则直接采录其说法。如例(4)“吋”字、例(7)“”字、例(14)“”字、例(15)“”字、例(18)“”字皆其例。其结论多可信从,如例(18)引《正字通》认为“”为“”(今作“阴”)字之讹,“”字见《说文》,作“”形近之误也。又《广韵》或体作“”,周祖谟先生校订作“”(222),考论相同。又俗还有作“”者(参看《汉》4337A),皆一字变体,当从《说文》正之。此外,对有些因字书编纂失误而衍生的多余字形,也作了删汰,如例(5)“”字《字汇》《正字通》字头重出,《康》删存其一。当然,《康》的这种正字方法亦颇可商榷,有些判定正俗的观点与今天的俗字观存在差异,如例(3)“”字斥为“讹增”,实际是个增旁俗字;又如例(7)“皝”作“皩”,繁化俗字也,《康》以其为非;又如例(9)“箌”或作“”,今以为部件位移俗字,《康》认为“宜删”;又如例(19)“”或作“”,俗书韦、革二旁相乱,产生的俗体甚多,《康》认为当以从“韦”为正,从革者“应删”。这些观点与常见的俗写规律是相违背的,但从字书编纂和文字规范的角度看,这些一字变体的确不能当作两个字来处理,那些来路虽明,但使用频率较低的俗字异体是可以淘汰的,以此来减轻字书的负担。此外,不少字形的考辨仍有未尽,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证。如(12)认为“羗”是“羌”字之俗,其说不误,但所引《字汇补》“与羐同”者实为“”的俗字,与“羌”俗作“羗”者同形而异字。又如例(20)虽已指出“”为“”字之讹,然“”实亦俗字也,杨宝忠(2011:444-445)已考证“”为负雀之“负”的增旁俗字。《康》所做的这些文字辨正工作,即便对今天的文字整理与规范,仍有参考意义。
总之,对历代字书收字、析字进行比较及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入考察汉语字书相承传写的渊源与传统,书写更为完整的汉语字书史;还能揭示更多汉字发展传承的现象、特点及规律,为汉字的搜集、整理、理论研究、信息处理和数据库建设等提供新的资料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