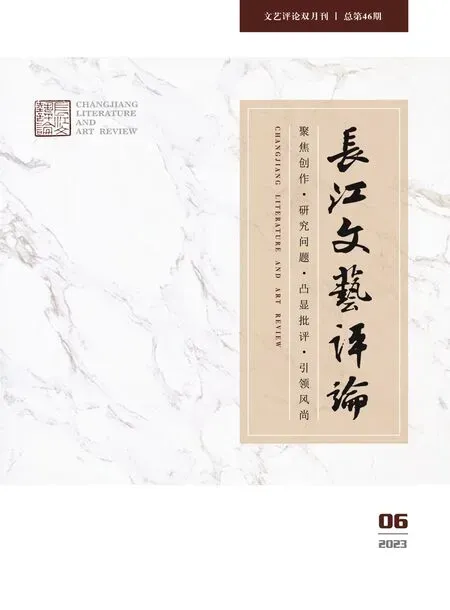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情欲书写
——关于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
2023-03-22王春林
◆王春林
先后两次在不同的时段阅读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载《收获》长篇小说2022 年春卷),我从其中所获得的一种真切阅读感受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路内的这部长篇小说理解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与纳博科夫《洛丽塔》二者叠加之后的一种文本结果。只要是熟悉普鲁斯特的读者就都知道,作家的全部人生回忆都是由那个标志性的小玛德兰点心所触动的:“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如此一种凝结着主人公浓厚情感记忆的“物”也即茶点,是童年时期的他曾经在姨妈的住所里品尝过的。正因为小玛德兰点心有着非同一般的特别味道,所以,伴随着这种味道浮现在心头的便一定是那些如烟往事:“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对此,叙述者曾经展开相应的分析:“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消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体回忆的大厦”。就这样,正是在小玛德兰点心那种特别味道的牵引之下,主人公曾经长期居住的贡布雷的那些大街小巷、花园以及往事才都一时蜂拥在他的眼前。其实也不仅是这样一个别致的开头,放眼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不难发现,无论是那一缕映照在教堂钟楼上的阳光,还是那一句动听的乐曲旋律,甚或雷雨后的傍晚嗅到的丁香花浓烈的香味,都可以牵引出主人公对逝去岁月的真切回忆。总之,一种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借助于某物的出现,由此物的味道、旋律、气味等饱含情感地勾连起既往的人生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语法。然后,我们再来看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的开头部分男主人公李白与自己的初恋女友曾小然多年后重逢的情景:“‘他乡遇故人,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在2006 年出版的《青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了这句话。十二年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后轻拍他的肩膀。”所谓“他乡遇故人”,更切合习惯性表达的,其实应该是“他乡遇故知”,是令中国人高兴的四件人生大喜事之一。诚如李白所言,或许与如此一种情形中隐含着某种普遍的人生真理有关,很多小说作品都会以故人相逢为起点来开启自己的小说叙事。但其实,李白和曾小然天各一方的时间,却要远远地超过十二年。比李白大两岁的曾小然,是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突然从他的生命里消失的。等到他们俩在上海的这家咖啡馆意外重逢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的二十六年。但在这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他们俩却一直都未能忘怀对方。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李白头上的那个Z 字形伤疤上。首先是曾小然的一句话:“你脑后的伤疤仍在。”然后是李白的强烈感觉:“是的,为了遮住这道Z 型的伤疤,整个青年时代他始终留着长发,或齐耳,或披肩,或扎马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被定义为流氓、艺术家、潦倒鬼、性倒错。”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会去掉这个伤疤。原因在于,“想当年,在必须剃板寸的学生时代,闪电型的Z代表着他对曾小然昭然若揭、轰然落地的爱。Z,不是张,不是钟,不是周,不是赵,而是曾。”如此一种情形,端的是怎一个“Z”字了得。在这个“Z”字形的伤疤中,所深度凝结的,正是天各一方的他们俩之间的彼此牵心。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当李白意欲扫码加曾小然微信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行熟悉的签名:曾经小小地不以为然。那是他十七岁时献给曾小然的情诗。”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有着太过真切的情感记忆,曾小然也根本就不会把26 年前李白的一句诗用作微信的签名。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曾小然离开后,李白却依然沉浸在对曾小然,对过去那些如烟往事的回忆之中:“四十五岁的曾小然扎着高马尾辫,双颊虽生出细纹,但唇齿之间仍然湿润丰盈,这一微妙的生理特征(也可能是生理缺陷,例如玛丝洛娃的斜眼,小王爵夫人的短嘴唇)曾经被中学教导主任视为淫荡的象征,与此同时,女教导主任本人那两条微微叉开站立的圆规腿也突然出现在脑海,那是被一众青少年反复观摩、普及、分析过的无意识姿态,以至于大家曾经迷糊,到底是汁液丰沛的曾小然更放荡,还是严厉到合不拢双腿的教导主任……”请一定注意,当李白情不自禁地因为与初恋女友曾小然的意外重逢而陷入到回忆之中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竟然是由曾小然唇齿之间“湿润丰盈”的生理特征进一步联想到了当年关于“放荡”问题的讨论。这一细节,其实已经指向了我们稍后将要论及的情欲书写主题。紧接着的叙述话语就是:“天哪,我走神了,全是往事的碎片,而刚才的重逢犹如单行道上的车祸,往事正接二连三追尾。”既然往事已经处于纷至沓来的状态,那“关于告别的一切”也就正式开始纳入到了叙事的轨道之上。事实上,只有在认真读过小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路内之所以要把这部小说命名为“关于告别的一切”,主要因为其中充满了“告别”的各种人生场景。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告别”看作是小说文本最核心的“关键词”。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正如同“告别”的反义词是“相逢”或者“重逢”一样,这部小说中,与“告别”同等重要的另外一个潜在关键词,其实就是“重逢”。也因此,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路内的作品是一部关于“告别”的小说,但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重逢”的文本。即以小说的开头为例,作家所首先书写的就是李白和曾小然久别后重逢的场景。既如此,一种客观存在的文本事实就是,正是“告别”与“重逢”这样一种看似悖反的存在情形,从根本上支撑起了路内的这部长篇小说。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借助于小玛德兰点心打开了自己回忆的闸门,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则是通过李白和曾小然的意外重逢使得那些如烟往事以失控的状态纷至沓来,二者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无论如何都不可轻易否认。
然后,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路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洛丽塔》,一个标志性的因素出现在小说开始不久的第一卷第五节中:“‘他想看的是曾小然。’十一岁的钟岚告诉李白。到二十岁时,她又这么说了一次,是在他被窝里。那时李白感到自己又经历了一次轮回,曾小然已经变成前生认识的人,记忆消散后凝结成一些怀念,落在窗前。他用吴里方言困惑地念着她的名字,曾小然,舌尖轻轻摩擦门齿内侧三次,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曾zeng。小sie。然zeou。”由曾小然微信中关于钟家父女的提问,李白不仅联想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位女性钟岚,而且还进一步联想到了钟岚的父亲钟高强。因为钟高强曾经被人们误以为试图偷看邻居俞莞之(俞莞之乃曾小然的母亲)洗澡,这样也才有了钟岚对父亲行为实质的揭穿:“他想看的是曾小然。”而李白,自然也就由钟岚的这种揭穿进一步联想到了纳博科夫《洛丽塔》那个著名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从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虽然不是亦步亦趋,但李白的刻意模仿《洛丽塔》,却还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尽管如此,路内的小说与《洛丽塔》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说纳博科夫通篇都在表现一个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中年男子亨·亨伯特出于无以自我克制的恋童癖,迷恋上了女房东年仅12 岁的女儿洛丽塔,与洛丽塔发生了不伦之恋的故事,那么,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虽然也会对跨越年龄界限的不伦之恋偶有涉及,但其主旨却并不在这一方面。倘若一定要找出二者之间的共同处,那么,我觉得,大约也就一定只能是情欲书写。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洛丽塔》的理解和定位。即使是亨·亨伯特这样一个“恋童癖”的不伦之恋的故事,其前提也只能建立在更大范围的情欲书写的基础之上。而这也就意味着,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与纳博科夫《洛丽塔》一个共同的思想艺术旨趣,便是对情欲问题的关注与表达,也即所谓情欲书写(我们之所以要指认《关于告别的一切》是一部情欲书写的长篇小说,也与小说开头处这样一个情节的设计紧密相关。那就是,当李白与曾小然偶遇后开始回忆人生的时候,他首先想起的竟然是他们俩当年在吴里那个蓝莲咖啡馆的一次“冒险”经历。在那个深秋季节的咖啡馆里,李白对曾小然说“咖啡加盐是壮阳的。”然而,由于旁听到邻座一对男女的聊天,那位男人在向女友讲述自己性功能障碍的情况,李白一时按捺不住,也向隔壁的中年人说了一句:“滚烫的咖啡加盐,最最壮阳。”中年人一时盛怒,亏得有他女友的及时提醒,懵懂无知的李白方才侥幸逃过“被掐着脖子喝下一杯加盐的咖啡”的厄运。一部具有“追忆似水年华”性质的长篇小说,回忆初始就是这样一个与“壮阳”紧密相关的生活细节,其情欲书写的意旨,自然就非常明显)。也因此,当我们试图指认《关于告别的一切》可以被看作是《追忆似水年华》与《洛丽塔》某种叠加的结果的时候,就意在强调路内的作品乃是一部以情欲书写为核心的回望生命来路的带有一定成长叙事色彩的长篇小说。
既然在此前的论述过程中,情欲书写已经一再被我们提起,那紧接着进入分析视野的,首先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看待情欲以及文学艺术中的情欲表现的重要问题。这一方面,一种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随着人类社会总体上的文明进步,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关注表现情欲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实。比如,当代美国以对情欲的关注和表现而著称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一部题名为《安迪·沃霍尔》的著作中,我们就曾经读到过这样几段颇有启迪性的论述:“艺术,对于安迪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手段。它还是性爱的一种方式。‘升华’一词就恰巧还原了这类现象———暗示性才是核心,艺术不过是次一级的副产品。弗洛伊德断言,升华推动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安迪——有时候人们认为他是个幼稚的艺术家——凭他对文明的集中表现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将所有的冲动、性欲和其他东西导入了艺术作品中。然而,升华无法解释他的方法。安迪没有升华性欲,而是简单地扩展其管辖权,让它支配每一个进程、每一次消遣。对安迪来说,一切都与性有关。沉思也罢,运动也罢,静止也罢,都有性。观看与被看同样有性。时间也一样与性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阻止时间。安迪的艺术就是‘性感化’的身体,而他实际的身体其实是拒绝‘性感化’的。”[1]因为总是与“性”有关,所以,“一些安迪最好的作品都擦着色情描写的边,至少按20 世纪60 年代的标准看是如此;他面不改色、津津有味地贩卖带有性意味的意象和内容。他的艺术趋向色情,这并不妨碍他的艺术具有崇高的性质。终其一生,从九岁时拿起布朗尼相机,到去世前几天以时装模特的形象出镜,他都在努力将色情冲动改装成对事物本质神圣的、严肃的探求——通过观看(还有复制)他人的身体,特别是那些有吸引力的男子的身体(处于运动或休息状态),一步步逼近肉体世界的神奇核心。”[2]更进一步说,因为这种内蕴的“神圣”而“严肃”的探求,所以其中竟然也会有某种宗教性质存在:“在当代关于色情作品的争论中,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义忽略了那些露骨的色情形象所包含的虔诚的、近乎宗教的动机:好奇心,即不满足于眼之所见的那种值得赞美的欲望。哲学家和圣人追求善。对安迪而言,善就是男性身体。他想去看、画、拍摄其极致的状态和散发出来的事物。他希望有一种观看模式,能够触摸到肉体的本质并理解它的局限。面对执拗的肉体,他的眼睛总有无限的耐心。”[3]尽管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写作者也会不时地提及社会总是会把安迪的作品和色情联系在一起的理解方向,但其实,安迪总是在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严肃地探究思考情欲以及附着于情欲之上的那些“神圣”和“严肃”的意味。
但尽管如此,中国这一方面的情况却并不乐观。或许与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过于道德化的思想观念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似乎总是更多地会赋予情欲这一语词一种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负面化理解。无论是谁,一旦与情欲发生关联,那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好像就存在什么问题似的。但其实,正如同古老的典籍《礼记》中所强调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那样,对于人的基本生存来说,饮食也即吃饭问题,男女也即性欲或者情欲问题,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倘若离开了所谓的“饮食男女”,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整体,其生存繁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之情欲就应该被看作是生命某一层面的必然存在状态。如果说人类生命的其他层面,比如婚姻、爱情、事业、奋斗、失败等等,都可以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得相应的观照与表现,那么,如同情欲这样更为根本的存在层面就更应该获得相应的观照与表现。遗憾处在于,由于受到道德观念强力抑制的缘故,无论中外,只要是明显涉及到情欲描写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少不了因为被视为“诲淫诲盗”而禁的命运,典型的如中国古代的《金瓶梅》,西方现代的《尤利西斯》《洛丽塔》。一方面,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都是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文学杰作,都有着不容轻易否定的思想艺术价值,但在另一方面,它们的长期或一度被禁却又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贾平凹那部堪称杰作的长篇小说《废都》的一度被禁。《废都》之所以在出版之后不久就被禁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不仅有着过多的性描写,而且也还有那些作家故意设定的接连六个方框,然后是括号里的“此处删去多少字”。既如此,当我们试图谈论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这部以对情欲的关注和描写为其鲜明特色的长篇小说的时候,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为情欲这一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状态的语词正名。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必须以一种相对平和、理性的心态来理解看待情欲。
从根本上说,我们之所以会认定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乃是一部以情欲书写为核心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同时承担着视点功能的主人公李白回忆自己长达四十四年(以故事结束的2019 年为界)的人生的时候,聚焦点集中在了自己以及他者的情欲世界这个人性层面上。细究文本,我们固然也可以在其中发现,比如对产业工人李忠诚因企业倒闭而被迫下岗状况的描写,比如曾经长期生活在吴里的李白对数十年间吴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描写,再比如对个体经济经营者冯江如何经营广告公司的描写,但所有的这些,与处于文本中心位置的情欲书写相比较,恐怕都只能算是浮光掠影的小巫见大巫。无论是李白前半生中以“告别”之名所不断遭遇的那些异性情侣,抑或还是他人生路途上所遭遇的那些他者的再度人生遭际,其实际的聚焦点都脱不开情欲(请一定注意,此处之情欲既非褒义,也非贬义,乃是一种中性描述)二字。
对于李白自己,首先是他那充满了屈辱感的童年记忆。他的屈辱感,主要来自于母亲白淑珍的离家出走。白淑珍离家出走的时间,是李白九岁的那一年,也即一九八四年。那一年,李忠诚已经因为救火不仅成为英模,而且已经被提拔为副科长。在一场海啸式的激烈争吵之后,白淑珍毅然与人私奔。尽管那时候的李白连什么是绿帽子都搞不清楚,但这一事件对他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他们喊你李乌龟,连累了我。’他将这一消息告诉父亲,这极其自虐,在痛苦的时候他会以这种方式要求一顿暴打,但这次他看到的是李忠诚瘫软在饭桌上。夜里,李白听到父亲在床上嘀咕:我要让太子巷所有的男人做乌龟。后又改口说:所有适龄已婚男人。后又开解自己:太难了,睡吧。自从白淑珍走后,李忠诚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是安慰自己落在墙上的影子,有时是和房间里弥漫着的某种气息对骂。”由以上这段叙事话语可知,与李白相比较,白淑珍对李忠诚的伤害程度同样非常严重。无论是他对太子巷其他无辜男性的恶毒诅咒,还是他这种自言自语习惯的养成,所说明的都是这一点。但其实,从根本上说,李忠诚和白淑珍的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对父母亲婚姻的错误性质,李白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从外公白致远那里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原来,发生于一九七四年的这件往事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复杂。那时候在A 研究所工作的白致远整日无所事事,但长女白淑珍却已经不仅在安徽插队六年(请一定注意,白淑珍的下乡插队与白致远有着直接关联。早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由于身为积极分子的白致远的主动替长女报名,也才有了她下乡插队事实的形成),而且已经对这种生活彻底失去了耐心。也就在这个关节点上,有人给白致远建议可以把长女嫁到吴里:“原因有三:吴里离上海极近,方便于探亲;吴里的男人比较势利,相当尊重上海女性;吴里稻米水产丰富,至少饿不着。”因为白致远自己那个时候也已经对世界失去信心的缘故,所以,他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尽管如此,李忠诚和白淑珍的这段错误婚姻也仍然是李代桃僵的一种结果。媒人原本介绍的那个男人名叫朱头三,是农机厂的钳工,“出身好,念过完整的初中”。想不到的是,事到临头竟然发生变化,说定要去安徽相亲的当天,一方面是内心里感觉有点不靠实,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突然发作了盲肠炎,朱头三无法如期履约。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忠诚只好李代桃僵:“媒人想了想,紧急拉了正在休假的李忠诚,乃因他父母双亡,家中两间平房一个院子,独吃独用,不但拿得出粮票,还能买下朱头三的火车票……最关键的是,李忠诚稀里糊涂,家中没个人可以商量事情,他什么当都愿意上。”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李忠诚除了知道自己迫切地想要一个女人之外,也还的确是处于懵懂的状态之中:“他想要一个女人。他想要一个女人简直想疯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想到,他在安徽一见到白淑珍,就不管不顾地喜欢上了这个女人:“李忠诚的原话是:我看见了她,一见钟情,整夜都睡不着,我想明天就娶她。”关键是白淑珍的态度。一方面,叙述者口口声声强调“没有人能解释白淑珍为什么决定嫁给他”,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做出了这样的一些交代:“一九七四年秋天,她给远在上海的白致远写了封信,谈到同宿舍的女知青生下一个死胎,谈到她十八岁下乡的情景,如今二十四岁,有人托关系顶替了她的名额去念工农兵大学,谈到自己的牙齿,秋天掉头发,一个当地干部的儿子试图接近她,如此等等。她最后严厉地提醒白致远:请不要再指责我落后。”毫无疑问,正是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发生作用,才使得白淑珍最终嫁给了素昧平生的李忠诚,就此铸成了一段长达十年之久的错误婚姻。这一场错误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其实首先是李忠诚自己。某种意义上,他此后一切悲催的遭际,无论是对俞莞之最终无果的疯狂追逐,还是他在皇后饭店的嫖娼行为,抑或是他晚年时因为所谓的舞蹈教学而被诈骗七千五百元,甚或他最后所罹患的日益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全都肇因于那一场错误的婚姻。认真思考李忠诚人生悲剧的酿成,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固然不可否认,但他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却也不容推卸。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李白才会做出这样的一番反省:“他们一开始是幸福的,李白说,但在其后的日子里,大历史先于个人命运给出了答案,在一个较好的时代,他们反而过不下去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坏蛋,他和白淑珍的差距在于,他本质上对于自己能够侥幸活下来感到十分满足,而她憎恨这种满足感。”道理说来其实也简单,那就是,李忠诚能娶到白淑珍,绝对是一种高攀的结果,如果不是自身处于万般无奈的状态,上海人白淑珍根本就不可能下嫁吴里农机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反过来,从白淑珍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她当初下嫁李忠诚是一种无奈之举,那么,等到社会和生活发生明显的变化后,她对原本就没有进入过自己心里的李忠诚的彻底弃绝,也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如同李忠诚一样,这场错误婚姻的另外一个被迫承受者,就是李白自己。对此,成长后的李白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十年婚姻,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差不多就是我过去十年的经验。然而在体感上,我无法代入进去。准确地说,我无法承认他们是幼稚的———就像我一样幼稚。我无法承认自己是一场幼稚婚姻的弃子,无法直观那个曾经神经质的爸和妈实际上才二十三岁。童年期被人喊乌龟的儿子或婊子的儿子,这是一种创伤感,但它真正造成的恶果是困惑,过早的困惑使我变成了一个既不相信个人命运也不相信大历史的人。”尽管无法得到相应的确证,但如果按照小说所提供的相关情节,我们也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出身于吴里的青年作家之所以一直到四十四岁(2019 年)的时候,仍然处于单身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父母婚姻悲剧影响的结果。因为受到父母婚姻悲剧的影响,李白内心里便不再信任婚姻。当然,这里所潜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李白对曾小然和批评家方薇长期或者曾经一度的追求最后竟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先来看曾小然,尽管说从十七岁时的那一次见面,到他们后来的意外重逢,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但最起码在李白(曾小然的情况恐怕也是如此。因为叙述视角局限的缘故,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李白的真实心理状况)心里,他从未忘怀于曾小然。也因此如果不是各种阴差阳错,他们俩走到一起的几率应该很大。关于他对曾小然那种刻骨铭心的念念不忘,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到了第63 节结尾处的这样两句话:“但是,与我一样,与李忠诚一样,他也无法见到一生中最爱的人。我们就是带着童年时的尿道弯曲症,以为自愈,活到了老。”这里李白“最爱的人”,指的就是曾小然。然后是方薇。关于方薇,第61 节曾经有过这样的叙事话语:“李白曾经认为会和方薇发生一段震慑灵魂的爱情,结果她嫁给了别人。”尽管叙述者没有作更明确的交代,但从对方薇嫁给别人这一细节的强调,所透露出的意思似乎是,如果方薇不嫁给别人,那他们之间还是有可能以婚姻的方式走到一起的。换个角度说,正因为李白一直处于没有婚姻的单身状态,所以也就有意无意间为路内的情欲书写留下了极大的叙事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李白的单身更应该被理解为路内的刻意安排)。粗略计来,在李白所先后遭遇到的十大几位女性中,与他发生过情欲关联的就有九位之多,绝对超过了半数。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所有的这些女性,对于和李白发生情欲关系所持有的都是类似于“周瑜打黄盖”那样的一种自愿心理,没有任何一位带有强迫的意味。尽管说其中也会有个别女性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些许醋意,比如由李白破了处的那位钟岚,就曾经表达过对曾小然的嫉妒之情:“爸爸是不能背叛她的,而李白可以,因为李白背叛了所有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交情中,她唯一不能释怀的是曾小然的出现,后者取代了她青梅竹马的位置,差不多六岁那年她就失恋了。其后在二十岁时,他又一次让她失恋,他的背叛是无穷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或许与这些女性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有关,我们在其中基本上没有看到过那种“狗咬狗一嘴毛”的争风吃醋现象。需要注意的是,李白的漫长情史中,有一些女性的确带有突出的萍水相逢性质。比如,那位来自于北方的女读者。这位来自北方的热情女读者,曾经在给李白的信中表示:“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我下星期去上海,途径吴里,来看你。”在李白的记忆中,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他留在了她的住处,太子酒店副楼朝北的一间房,暗红色的丝绒窗帘遮挡了一场大雨。”这里,更值得揣摩的是“途径”二字。因为吴里地处主干道的分岔小径上,去上海根本无法“途径”,所以,只能是专程的一种拜访,以及由这种拜访进一步携带出的一夜情:“他们平静地诋毁,以至于谈论爱情也变得有点难,事后,他们一致建议拉开那道暗红色的帘幕,坐在床上看大雨,像看电影。”接下来,就是那位北方女读者表达的失望之情。对此,李白的感觉是:“李白想起冯江说过的:一夜情,总是建立在某种遭到压抑的失望情绪下。正是失望,使人们掐断了情感的延续可能,将成本降至最低,也正是失望使人们想要获取一点什么。”再比如,那位住在南京的通信姑娘。在李白二十岁出头时,曾经遇到一个通信长达两年的姑娘。这个通信姑娘曾经声称,只要李白有一套房子“我就嫁给你”。后来,这个姑娘在南京租了一间带阳台的屋子,李白专门去南京见她:“这是首次见面,他们在街上简单地吃了点富含味精的鸭血粉丝汤,又去逛了碟店,决定做爱。他往CD 机里塞了一张《再见社交会》,两人从卧室做到客厅,从客厅做到厨房。在卫生间的洗衣机上李白建议去阳台,姑娘大笑起来。”但在阳台上“依偎了一整夜看星之后”,他还是走了。从此不仅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且还彻底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形,当然是一种典型不过的“一夜情”。虽然谈不上有多么用情之深,但你如果说李白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用过情,却也并非客观事实。其中,很可能潜藏着如同李白他们这样一代人某种迥异于传统的性爱观。
当然,与这两位萍水相逢者相比较,李白情史上更多的却是那些同时携带有“告别”与“重逢”色彩的异性情人。其中有一些,甚至会带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深度。比如,那位第一次带给李白性爱体验的周安娜:“这不是色情,而是道德上的震惊——我千百次梦见的是曾小然,但我的某种第一次竟然给了周安娜。”他和周安娜是在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时结识的。那一次,在一个大风的夜晚,他们俩有过短暂的交集。两个人慢慢熟悉起来后,周安娜曾经向李白透露过一个自己身体的秘密,那就是她脑袋里竟然长了一个瘤,按照医生的说法:“需要手术摘除。手术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周安娜有一种自己随时都可能挂掉的感觉,所以在她和李白的情欲关系中,从一开始就飘荡着某种死亡的气息。那一次,在她们全家都外出旅游后,周安娜在自己家的蚊帐里和李白结合在了一起:“我预感到初夜将会是一个落雨的下午,而不是夜晚。夜晚太过成人化,饱含情色意味,而初夜是我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划动小舟,奋力并慌乱,接着,洪水从高处涌下,我的一点点羞愧之心将被快乐淹没。在那个所谓的旧时代,我曾经怀疑自己是否充当了谁的替代物,谁的替死鬼,我被她即将死去的念头卷入漩涡后迅速甩出去。瞬间的念头来不及被我辨识,奔流而来的确实是爱情。我感到最终是爱情将我和她隔开,而不是其他。当一切结束后,我们抽了同一根烟,她告诉我,避孕套不是她爸爸的,而是她爷爷的。”没想到的是,等到曾小然和周安娜双双到上海去读大学之后,李白所犯一个阴差阳错的低级错误,竟然是把致安娜的情诗寄给了曾小然,而把写给曾小然的三千字散文寄给了周安娜。对此,叙述者给出的评价是:“这一错误犹如李白的本质之光———发自内心,挥洒而就,衰得离谱。”关键的问题是,等到李白大专毕业成为失业青年后的某一天,他竟然接到上海一个名叫费奖的自称已经和周安娜恋爱十六个月的大四学生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俩谈恋爱)十二个月后,费奖发现周安娜与不同的男性保持着性关系,他窃取了她的通讯录和日记本,并实施跟踪四个月,最后锁定的男性名单有五十二个。”获知了相关情况后,失业青年李白第一时间赶到了上海,踏进周安娜就读的F 学院:“失业青年李白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浪游始于一场劈腿大混战,而非基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多年后的一些访谈中,他声称自己落拓不羁什么的(出世型的写作者是出版市场永远的宠儿),离开闭塞的县级市追求某种事物。‘我总不能对着媒体大谈初夜情人引爆火药库的故事吧?’”要害之处在于,周安娜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如此这般的“滥情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却是与那个时刻威胁着她生命的脑瘤也即死亡阴影的存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对于这一点,李白心知肚明:“李白忽然间问不下去了,他望着她,关于她,汽车上嚼泡泡糖的她,舞台上吹笛子的她,风雨中的她,席子上的她,多重印象叠加在一起,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拼在一起却失去了维度。那时候她说过,脑瘤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每长一毫米就会让她变身一次,等到它被切除,又会彻底改变她。”很大程度上,周安娜所有看上去惊世骇俗的行为,全都是拜那个一点一点在长大的脑瘤所赐。换个角度说,早就对生存充满绝望感的周安娜,其实是在以貌似无度的纵欲方式来尽可能地对抗着那个巨大的死亡阴影。惟其如此,她在上手术台之前对李白所讲的那两句话才让人听来特别心酸、非常伤感。一句话是在把笛子送给李白后:“就当我自杀之前给你的留念,请好好保存。”另一句话是:“如果不是因为动手术,我还挺想和你做爱的。”那种对既往的怀想,与对生命的留恋,可以说溢于言表。
当然,更多时候,李白和女性的上床仅仅只是出于彼此间的喜欢或者也可以说就是身体的需求。比如,他和那位不仅已经有男朋友,并且还多少有一点虐恋倾向的叶曼。“在他与叶曼短暂欢爱的日子里,南方似乎已经变得不可相认。”“在这场短途旅行中你一再变身,一个古典的人,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属于今夜的情人,一个事后抽烟的没有年代感的人。”紧接着,在一番围绕爱情的对话后,就是虐恋场景的呈现:“在双手被绑之前,李白还是保持这一论调。叶曼换了个灯,变成粉红色,她脸部的对比度变强。李白要求把内裤穿上。”“并不是所有要求都会被答应。‘你真没劲,我以为你会要求穿上我的内衣。’叶曼让他站在床边,用两根尼龙绳将他的双手分别绑在床架上。李白试了一下,无可挣脱,除非喊救命。‘我会被知识分子耻笑的……’他嘟哝道,‘那些灵魂的翅膀被长久束缚在架子上的人,他们见不得这个。’”“‘M 是不许骂脏话的!’她抡了一皮带在他的后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皮带,并联想到冯虎和冯江。”“李白扭过头去试图看见她,‘这时间要是火灾地震,我只能扛着床架子往外跑,我会被门框卡住的。’他感到后颈一阵剧痛,叶曼扔了皮带,咬住了他。”这其中,特别耐人寻味的,就是那句挖苦知识分子的“那些灵魂的翅膀被长久束缚在架子上的人”。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为了避免成为“灵魂”被“长久束缚”在架子上的人,李白才宁愿自己的身体被情人叶曼绑在架子上。
关键的问题是,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李白漫长的情史上曾经先后遭遇或者说拥有过很多位异性情人,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登徒子或者西方的唐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与钟岚之间的关系上。尽管从六岁起钟岚就曾经因为曾小然出现在李白的身边而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失恋的状态,但这却并没有妨碍她成年后的上当受骗。或许与内心里某种潜在的移情作用有关,钟岚之所以会委身于曲冰,主要因为她由曲冰而联想到了李白的缘故:“他和你一样,也写点小说(没发表过);他和你一样,也没工作(但比你会花钱);他和你一样,让人动心(嗓音比你有磁性)。”诚所谓,“日常生活的伸缩性就像小说,一个女人上了当,可以是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可以是连载长篇,也可以缩减为一句话。”总之,钟岚动了心,上了当,“引狼入室”。没想到,后来的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的结局是钟岚发现曲冰不仅猎获了一头母鹿,还顺便打了兔子,这一天她撞见他在厨房里和爱玲亲嘴。这个有着《三言二拍》气质的故事,现在换了主人公。曲冰带着爱玲回上海了。”这里,需要停下来与路内展开讨论的一点就是,在面对李白和曲冰这两个人物形象时,作家似乎在无意识里采用了双重标准。除了曲冰曾经致使钟岚不慎怀孕这一点之外,他背着钟岚和爱玲的出轨行为,与李白差不多同时与很多位女性发生情欲关系(比如,就在钟岚怀孕期间,他就和医院里一个名叫程一尘的放射科医生打得火热:“三个月后,孩子出生,李白和程医生的恋情差不多也走到了尽头。”),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为什么在李白这里构不成问题,到了曲冰那里却似乎就罪不可恕呢?钟岚因为曲冰不仅怀孕,而且还生下李一诺,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仅如此,等到钟岚后来因癌症不治而亡的时候,她给女儿找到的委托人,居然就是李白:“钟岚去世前,将属于李一诺的那份钱交予李白管理(还有一位穿得脏兮兮的本地律师),证明了他是她唯一信得过的人,亦证明了情谊永恒(她单独留给李白五万块)。”钟岚能够在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李白,所说明的,正是她对他的完全信任。事实上,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钟岚去世后,在如何想方设法抚养教育李一诺这件事情上,李白果然没有辜负钟岚的托付。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李白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由以上对主人公李白,以及由他而进一步牵系出的其他人物在文本中的表现,我们就不难断定,路内的这部不断地“告别”也不断地“重逢”的《关于告别的一切》从本质上说,毫无疑问就是一部情欲书写之书。但在行将结束我们的论述之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关于告别的一切》给出一种恰当的理解和定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恐怕有以下三个维度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其一,在既不了解路内的具体写作动机,也不清楚其他读者阅读感受的前提下,我个人由路内的这部小说,尤其是其中那位似乎处处留情的主人公李白,情不自禁联想到的竟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其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一口咬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生活在大观园一众姐姐妹妹、莺莺燕燕之间的贵族公子贾宝玉,就其本性而言,既是一位“泛爱主义者”,也是一位女性崇拜者。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否定他和林黛玉之间真实爱情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他几乎对身边所有的年轻女性都有某种强烈的兴趣。既如此,我们也就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成人后的贾宝玉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很有可能非常类似于路内笔下的李白。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李白看作是成人版或者说现代版的贾宝玉或一方面的“借尸还魂”者。其二,由路内小说中所聚焦的情欲书写命题,我所联想到的,还有西方现代一位名叫马尔库塞的德裔美籍哲学家的一部名为《爱欲与文明》的杰出论著。在这部旨在对弗洛伊德的相关思想展开哲学探讨的著作中,马尔库塞明确提出了一种带有突出批判色彩的文明理论。在马尔库塞看来,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长期遭受压抑的历史,愈是处于成熟阶段的文明,愈是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压抑。也因此,我们通常所强调的“人的解放”的命题的一个根本之处,毫无疑问就是爱欲的解放。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爱欲的解放呢?马尔库塞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寄托到了对劳动的解放上。与此同时,因为他还进一步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被压抑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上,所以,他认为要想产生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必须突破劳动被异化的藩篱。一方面,我并不知道路内是否熟悉马尔库塞的这部著作中的相关思想,但在另一方面,除了后面关于劳动异化问题的思考与路内的小说无涉外,这部《关于告别的一切》的确以其突出的情欲书写,深度触及到了人(或人性)的解放与爱欲解放的命题。其三,如果说在一个过度道德化的现实社会里,一个作家对情欲的大胆书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性的解放与“人文精神”的确立,那么,回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自然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欲书写谱系的隐然存在。那就是,从1980 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其《岗上的世纪》,再到贾平凹的《废都》,孙甘露的《呼吸》,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一直到路内这部聚焦于情欲书写的《关于告别的一切》,正是这一系列作品,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脉。也因此,在结束本文的分析之际,我以为,伴随着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的问世,我们的确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对人类的情欲,以及文学主要是小说中的情欲书写能够尽可能给予客观、理性、公允评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