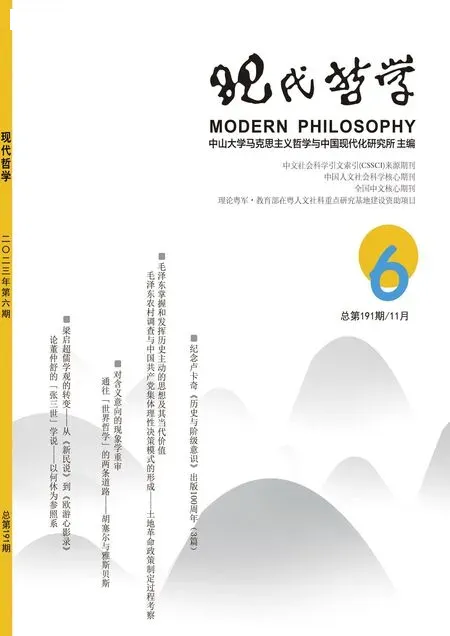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
——以何休为参照系
2023-03-21郭晓东
郭晓东
汉代经师多有《春秋》“三世”之说,东汉的宋均与何休均将“张三世”说视为《公羊》核心义旨之“三科九旨”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均“张三世”说的具体内涵我们不得而知,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则对“三世”说做了相当系统的表述。何休的“三世”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张三世”学说被认为是《公羊》学最重要的义理之一,清代刘逢禄作《春秋公羊何氏释例》,首录“张三世例”(1)[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页。,康有为则称其为“孔子非常大义”“《春秋》第一大义”。(2)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2,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然而,清末苏舆作《春秋繁露义证》时,引用钱塘的说法曰:“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苏舆又说:“何氏三科九旨,所谓‘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三代改制篇》;‘异外内’,见《王道篇》。”(3)[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页,标点有改动。可见,苏舆与钱塘俱以为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有了“张三世”说,何休之“张三世”实本之于董仲舒。不过,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只字未曾提及董仲舒,对于董仲舒的“三世”学说,后世学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我们不能不追问:董仲舒的《公羊》思想中有没有同于何休的“张三世”学说?若诚如苏舆、钱塘等人所说,何休的“张三世”学说本之于董仲舒,那么董、何有关“张三世”说的异同到底如何?鉴于何休对《春秋》的“张三世”思想已有成体系的论说,而董仲舒那里只有若干零星的表述,因此不妨以何休的“张三世”说为参照系,来具体考察董仲舒的论述。
一、董仲舒与何休论“三世”之断限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楚庄王》曰: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9-10页。
这里董仲舒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三等”,即“有见、有闻与有传闻”。“有见、有闻与有传闻”的说法,本之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与哀公十四年分别提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语,这大概是后世“三世”说的最早雏形,尽管董仲舒没用“三世”而用“三等”。又《春秋纬·演孔图》曰:
昭、定、哀,为所见;文、宣、成、襄,为所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4页。
东汉何休于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注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6)[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由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董仲舒、《演孔图》与何休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将鲁昭公、定公与哀公的时代定为所见世,将文、宣、成、襄定为所闻世,将隐、桓、庄、闵、僖定为所传闻世。其后董仲舒后学颜安乐,将所见世的起始时间断自孔子出生的鲁襄公二十一年,理由是孔子出生之后,就应该属孔子所见之世。对此,徐彦指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7)同上,第5页。又有东汉郑玄根据《孝经援神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的说法,认为“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8)同上,第4页。。其后,徐彦反驳说:“尔时孔子未生,焉得谓之所见乎?”“《援神契》者自是《孝经纬》横说义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9)同上,第5页。就《公羊》学说史而言,颜安乐与郑玄的说法并不为后人所普遍接受。(10)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外是清中叶孔广森所作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对于三世的断限,采用了颜安乐的说法。(参见[清]庄存与、孔广森撰,郭晓东、陆建松、邹辉杰点校:《春秋正辞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从上述诸材料看,《演孔图》与何休对“三世”之断代同于董仲舒,虽然两汉时期对“三世”之断限有其他歧说,但董、何应该代表着当时主流的说法。这种共同的看法虽然不足以表明何休之说渊源于董仲舒,但多少可以表明两汉经师对“三世”之断代应该有一共同的师说源头。
二、从“缘情制礼”的精神看董仲舒与何休论“三世异辞”的共同点
就“三世”说而言,光是“三世”之断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既然“三世”之划分本之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那么更关键的是要说清楚“三世”何以“异辞”。《春秋繁露·楚庄王》又进而论所见、所闻与所传闻曰: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1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0-11页。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12)[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004页。鲁昭公要逐季氏而力所不及,为季氏所逐,《春秋》为昭公讳而称“又雩”,所以董仲舒称“微其辞”。庄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般为鲁庄公之子,子赤为鲁文公之子,俱为未逾年之君,俱为臣子所弑,然而前者书日而后者不书日,为什么会有这一书法上的差别呢?对于子赤卒不书日,《公羊传》作出了解释:“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13)[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92页。也就是说,子赤被人所弑,《春秋》为是子隐痛而不忍书其日,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弗忍书日”,是所谓“痛其祸”。至于子般卒为什么《春秋》忍书“乙未”?《公羊传》对此未作解释,而董仲舒认为是“杀其恩”,即相对于子赤而言,在情感上有所降杀。之所以如此,董仲舒认为,子般卒于所传闻之时,而子赤卒于所闻之时,所闻之时近于所传闻之时,所以恩有所降杀,此即“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之意,就如陈立所说的“近者亲,远者疏,亲者恩深,疏者恩杀”(14)[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96页。,所以董仲舒认为《春秋》于三个世代的书法各不相同,是“与情俱也”。
为什么“三世”所以异辞是“与情俱也”?董仲舒只是说“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不过如果以何休的说法为参照系,则可以对董生之说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
如上节引文所见,何休将所见世具体为自己与自己父亲的时代,所闻世为祖父的时代,而所传闻世为高祖、曾祖的时代。之所以将《春秋》三世与自己的父祖曾高的时代相对应,何休认为这里面体现了“缘情制礼”之义。他说:“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15)[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8页。就丧服制度而言,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为祖父母服期,为曾祖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越近于己所服越重,越远于己所服越轻。其所以如此,礼家认为,从“亲亲”的角度来讲,“立爱自亲始”,每个人与父母的情感最深,其次是祖父母,再次是曾祖高祖父母,从父母到曾祖高祖父母,其情渐次降杀,此即《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亲亲”之“上杀”义。(16)《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孔颖达疏曰:“上杀者,据己上服父、祖而减杀。”([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6页,标点有改动。)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提到“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何休说得这么明确,不过《春秋繁露·奉本》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的说法,多少也具有以隐桓时代为远祖时代即高祖曾祖时代、定哀时代为自己与父母之时代的意味,就此而言,董说与何休事实上相差并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三世”既然对应于父祖曾高的不同时代,那么由于“亲亲”之等级不同,“三世”就有“异辞”,即所谓“‘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17)[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8页。何休举例说:
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18)[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125页,下册第1196页。
何休这里的说法与前引董仲舒的说法几乎没有区别。子般卒日,子赤不日,就是因为所传闻世较所闻世而言恩情有所杀减,此即董仲舒所说的“于传闻杀其恩”之意。所见世所以“微其辞”,董仲舒举昭公逐季氏而言又雩为例,又称“与情俱也”,则“又雩”之为微辞,是为昭公讳恶。何休亦言:“不书逐季氏者,讳不能逐,反起下孙,及为所败,故因雩起其事也。”(19)[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004页。昭公在所见世,如何休所说,君父于臣子恩深义重,是以凡君父之恶,不忍直书而为之讳,故多“微辞”。
《公羊传》于定公元年又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休注曰:“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20)同上,第1050页。于何氏而言,所见世所以“微其辞”,又有畏时君而辟害容身的考虑。于此可以对照董仲舒的说法:“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2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2-13页。“近者以智畏”,即何休所说“畏时君”;“义不讪上,智不危身”之类的说法,即何休所说的“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世逾近而言逾谨”,即何氏“慎之至也”之义。可见,所见世之“微其辞”,从情感上讲要为君父讳以隆恩,从现实上讲要畏时君以远害,董仲舒与何休之说都没有多大差别。
三、何休“张三世”说中的“三世治法”义
由上文看,就缘情制礼的角度说,“三世”所以“异辞”,是何休所说的“恩有厚薄,义有深浅”,亦即董仲舒所说的“与情俱也”。但这只是所以“异辞”一个方面的理由。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则“张三世”学说只是一种书法体例而已,何以自汉代以来就被视为《公羊》学最核心的义旨呢?“三世”说于《公羊》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何休对“三世异辞”的解释中发挥出一套由“衰乱世”经“升平世”并走向“太平世”的“三世”之治法。《公羊传》哀十四年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22)[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199页。,在何休看来,孔子作《春秋》是要“以《春秋》当新王”,从而完成其拨乱反正的使命。因此,“三世”所以“异辞”者,就是如何休所说的是孔子“制治乱之法”。(23)[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8页。在这个意义上,何休从三世治法之不同来看“三世异辞”: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24)同上,第38页。
在何休看来,《春秋》之“新王”在受命之初为“衰乱世”,此时王化秩序尚未建立,王者“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所谓用心之“麄觕”指治理这一世代,用心不宜过细,治法不当过严。这具体体现在书法上则是内外有别,以鲁国为内,诸夏为外,鲁国的小恶详而书之,诸夏之小恶则略而不书,以此来表明先治鲁国而后治诸夏的道理。到了“所闻世”,王化秩序在鲁国已经建立,同时普及到诸夏国家,只有夷狄尚未被及王化,所以内外之别变成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书法上就表现为详于诸夏、略于夷狄,这就是先治诸夏而后治夷狄的意思。何休称这一阶段为“见治升平”,升即进的意思,徐彦称之曰“稍稍上进而至于大平”,所以又称之为“升平世”。第三个阶段是“所见世”,何休称“著治太平”(25)所谓“著治太平”,徐彦称“当尔之时,实非大平,但《春秋》之义若治之大平于昭、定、哀也”。(同上,第40页。),所以称“太平世”。这一阶段太平的王化秩序已经普遍建立,不再有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所以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此即皮锡瑞所说的:“外内无异,则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26)[清]皮锡瑞:《春秋通论》,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02页。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被设想成为人人都能够讲信修睦的时代,被设想成为一个无恶行可讥可责的时代,从而“衰乱世”与“升平世”的治世方法在这一阶段都不再适用。这一世代治世的特点是“用心尤深而详”,即治法较衰乱、升平二世为严为详,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公羊》的“讥二名”之说。所谓“讥二名”指的是在“太平世”已经“文致太平”,这时王者治定,没有什么可讥可责,只有取名字取两个字的做法略有非礼之处,便要予以讥责。(27)定公六年《公羊传》曰:“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088页。)
一般治《公羊》者认为,“张三世”说最有意义的便是何休对“三世”作出“衰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发挥。(28)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不过,学者们往往将何休的这一发挥视为一历史哲学,认为何休阐释了一种理想的社会进化理论。(29)参见黄朴民:《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65页;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193页。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何休说“衰乱、升平、太平”,目的并不是要说一种历史哲学,而是阐述一种如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哲学。当然,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确实寄托了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认为历史应该如是而向前发展。正如赵伯雄所说:“何休的真意不在于要说明历史曾经是怎样的,而在于说明王者应当是怎样的。他的三世说,只是借历史来表达政治理想。”(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与之相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董仲舒那里,对“张三世”之论述并未达到何休这一高度(30)如赵伯雄认为,在董仲舒那里“绝没有后来何休所说的什么‘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135页。),或者仅仅是认为董仲舒的说法只是开启了何休说之肇端。例如,李威熊先生说:“这是董氏对‘三世’的批评立场,他本着儒家亲疏远近的大义,朝代近者,只有‘微其辞’,但对于朝代愈远者,则批评的态度越为苛严。这或许是后来公羊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理想进化社会之说的肇端。”(31)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103-104页。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中已具有何休这一“张三世”的变易观。(3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6-69页。但这一说法受到黄开国先生的反驳。(33)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194页。那么,董仲舒的“三世”说到底有没有何休这样一种“衰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内涵?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
四、以何休为参照系看董仲舒之“三世治法”义
之所以对董仲舒的“三世”学说是否具有何休所说的“衰乱、升平与太平”之义有所争论,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董仲舒那里并没有像何休那样明确地提出“三世治法”的系统性理论。然而,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还是有诸多文字涉及 “三世治法”,只不过董仲舒的文字相当晦涩,粗看上去,似乎很难读出其中包含有“衰乱、升平与太平”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将董仲舒的这些论述衡之以何休的“三世治法”说,那么这些貌似晦涩的文字或许可以昭然大明,而董仲舒的“三世”说就可以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3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12页。凌曙与苏舆的注都引用了《公羊》成公十五年传及何休注。(35)参见[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137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12页。在凌曙与苏舆看来,对《公羊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解,董仲舒与何休并没有什么差异。何休隐公元年注“公子益师卒”,称所传闻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称所闻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世,则“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与之相似,徐勤也指出:“盖至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远,详内略外,等差秩然者,势之所不能骤变者也。”(36)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415页。所谓“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如果据何休的说法,显然指的是“太平世”;所谓“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衡之以何休,则指三世书法之不同。《俞序》篇曰:“《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37)[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58页。所谓“详己而略人”,就是何休详内略外的书法,即所传闻世,“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之类。“因其国而容天下”即何休托鲁国为京师,所谓有“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也就是徐勤所谓的“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
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麤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俞序》篇)(38)同上,第160页,标点有改动。
《俞序》篇这里两言“终”“始”,那么这里所谓“始”与“终”到底指的是什么?可以合理的解释是,“始”即《春秋》之始,“终”即《春秋》之终。《春秋》之始言“大恶杀君亡国”,又言“始于麤粗”,如果不从何休对“衰乱世”描述来加以解释,就难以说得通。“大恶杀君亡国”是对“衰乱世”的描述,“始于麤粗”也就是何休隐公元年注所说的“用心尚麤觕”之意。(39)卢文弨指出,何休隐元年“用心尚麤觕”,就根据于此。(参见[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60页。)“终言赦小过”,又“终于精微”,又“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又曰“讥二名”,则显然与何休对“太平世”的说法若合符契。(40)苏舆注“亦讥二名之义也”,即引何休定六年及隐元年的注,得之。钟肇鹏称:“‘讥二名’,所谓‘终于精微’也。”此皆以何休论“太平世”来解释董仲舒。唯苏舆对“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一语的解释引成公十五年“会吴钟离”何注,即“至于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如果按苏舆之意,则“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指的是“升平世”,恐不是太妥。成公十五年何注是特指楚庄王“卓然有君子之行”,故楚国入升平世不殊会,而非董仲舒所说的“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董仲舒所说的是“太平世”人人有君子之行,无可讥责,故唯二名可讥。(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第370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60-161页。)
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奉本》篇)(4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4-276页,标点有改动。
陈其泰先生指出:“董氏这段论述,概括了所见、所闻世、所传闻世书法之不同。”(4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第67页。段熙仲先生也称本段讲的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不过据段先生所举例,则段先生实际上认为本段讲的是“太平世”。(43)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7页。蒋庆先生则认为以上是董子述“太平世”的文字。(44)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256-257页。下面我们就随文对这段材料作一个详细的解读,进一步从中考察董仲舒“三世”说的意含。
“离不言会”,分别见于《公羊传》桓公二年与五年。那么,为什么称“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卢文昭据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及传文“离不言会”,认为“此齐宋当作齐郑”(45)[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4页。。在何休看来,所传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齐、宋相对于鲁国为“外”,所以大国如齐、宋亦离不言会。如果就所传闻世来讲,这是读得通的。但正如卢文昭所说,“此在所传闻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见之世,文不相蒙”(46)同上,第274页。,因此这里恐怕不能所传闻世讲。何休于宣公十一年注曰“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47)[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657页。,意谓到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可以书外离会,则可以说“大国齐宋,离言会”。至于所见世,如苏舆所说“所见闻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外离会’审矣。此文盖衍‘不’字”(48)[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4页。,则所见世齐宋亦当书离会,则确实如苏舆说“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应该读为“大国齐宋离言会”,故段熙仲先生举例云“定十四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49)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87页。,是也。
所谓“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者,据何休的观点看,在衰乱世,录大略小,大国之君卒日葬月,小国之君不书卒葬;到了升平世,相较于衰乱世书法略详,小国国君卒月葬时;到太平世,大国小国被一视同仁,都卒日葬月,所以董仲舒称之曰“录而辞繁”。凌曙、苏舆注俱据哀公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并引何注曰“哀公著治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50)[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349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5页。,则凌曙与苏舆亦据何休之说,认为此句是董仲舒述“太平世”的文字。
所谓“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者,苏舆引昭公十五年何休注曰:“戎曼称子者,入昭公,见王道太平,百蛮职贡,夷狄皆进至其爵。”(5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5页。根据何休,衰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不及于治夷狄;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治夷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夷夏混同为一,不再以“外”视夷狄,所以说“远夷之君”可以“内而不外”。
“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此时即所见世。哀公八年,《春秋》记“吴伐我”,十一年“齐国书率师伐我”,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所传闻世的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以及所闻世的成二年“齐侯伐我北鄙”。两相对照,则所见世之哀公时代不言伐我鄙疆,而直言“伐我”,这就是所谓“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然而,董仲舒何以特别强调所见世“鲁无鄙疆”?关于哀公时代直言“伐我”而不言伐我鄙疆,何休并不认为有什么深意。哀公八年注曰“不言鄙者,起围鲁也”(52)[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164页。,意谓非仅仅伐我边鄙之地。尽管如此,衡之何休对太平世的描述,“鲁无鄙疆”之说则有更多的意味。何休又从《公羊》“王鲁”义出发,其于成公十五年注中称“假鲁以为京师”,又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53)同上,第758-759页。。“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对应的是所传闻世;“诸夏正,乃正夷狄”,指的是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则自然鲁国无鄙疆界域可言。因此,鲁所以“无鄙疆”,则如凌曙所云“无鄙疆,言王化所及者远”(54)[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349页。。苏舆则曰:“所传闻之世,来接内者书其小恶,其不来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则内外渐进而从同矣,故云‘无鄙疆’,此所谓王义也。”(55)[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5页。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书“邾娄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邾娄是小国,本不当书大夫,《公羊传》襄二十三年称“以近书也”。何休注曰:“以奔无他义,知以治近升平书也。所传闻世,见治始起,外诸夏,录大略小,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所闻之世,内诸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故小国有大夫,治之渐也。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56)[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857页。在此意义上,董仲舒说,“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即邾娄虽非鲁之亲,但邾娄庶其、鼻我来奔之时,方入升平世,故何休解解为“治近升平”,因此而得以书。(57)凌曙注全引何休襄二十一年注文。(参见[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450页。)按:邾娄庶其来奔,《公羊传》称“重地”之故而书其大夫,何休以为“恶受人叛臣邑,故重而书之”,传文及何注均与董说有所出入。卢文弨疑“邾娄庶其”为衍文。如果立足于董仲舒现有的文本而强为之说,则庶其来奔在襄二十一年,与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相接,亦或可以从中引申出“近于升平”义。(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854页;[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5-276页。)
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不书日,《公羊传》称“远也”。何休认为,从“恩有厚薄,义有深浅”的角度看,“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58)[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8页。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认为这是大恶,而《春秋》不为之讳,是“远也”。何休认为,“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59)同上,第125页。,故不为桓公讳。虽然董仲舒说隐、桓是“亲《春秋》之先人”,但因为时代久远,所以大夫卒不书日以略之,国君大恶不为之讳,这就是所谓“远外”。
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认为,书“晋侯及吴子”,是张两伯之辞。(60)《公羊传》曰:“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何休注曰:“晋序上者,主会文也;吴言‘及’者,亦人往为主之文也。方不与夷狄主中国,而又事实当见,不可醇夺,故张两伯辞。”(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1182页。)董仲舒称“言不以为外”,指吴是夷狄,本来应该“外”之,而不当以诸夏之子爵相称,但《春秋》仍然书“吴子”,于董仲舒而言,此即“近近”之意,故称“以近内也”。苏舆解释说:“董意以吴进称子,为远近大小若一之征。”(61)[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76页。此亦即以何休的“太平世”解董仲舒。
总之,从上述《王道》《俞序》《奉本》诸篇文字看,董仲舒所论者,皆何休后来所阐发的《春秋》“三世”之义,只有从何休的视角来看董仲舒,则董仲舒“三世”说的内涵才真正得以显明,由此亦可见董、何之不异。
五、小 结
清末魏源作《董子春秋发微》七卷,颇不满于何休对董仲舒只字不提,从而试图将《公羊》学的核心义旨直接追溯到董仲舒那里,可惜其书未曾刊刻,以至于没有流传下来,今仅存《董子春秋发微序》一文。不过,在序文所胪列的目录中,认为阐发“张三世例”的,有《蕃露》《俞序》与《奉本》三篇。(62)[清]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5页。魏源所说的《蕃露》篇即今通行本之《楚庄王》(63)魏源指出,“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撮三科九旨,为全书之冠冕,故以繁露名其首篇”。([清]魏源:《魏源集》上册,第135页。),一般认为董仲舒论“三世”,即体现在该篇中,正如钱塘所说的。而魏源所称《俞序》与《奉本》诸篇则较少被人所关注,就此而言,魏源可谓慧眼独具。
刘逢禄在《释三科例上》中指出:“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64)[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4,清道光十年思误斋刻本,第1页。此为传统《春秋》之“张三世”说作了言简意赅的归纳。以刘氏所述“三世”之第一义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本之董仲舒,而何休说“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此与董氏之说全同。刘逢禄所说第二义,即“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这是对何休的总结,然而我们也从《王道》《俞序》《奉本》诸篇中可以绎中何休的这一层含义。因此可以说,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遂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从而可以认为董仲舒与何休之“三世”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至少可以说董仲舒已经开了何休“三世”说的先声。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何休之“张三世”说,呈现的是一完整的有体系性的理论形态,并成为理解《公羊传》的根本大例之一;(65)参见[清]刘逢禄、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第5-9页。而董仲舒的“张三世”思想虽然并不异于何休,却没有像何邵公那样得到清晰的表述,也没有如何氏那样具有一种理论的系统性。当然,关于何休的“张三世”思想是否因此可以直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则未必有明确的证据。正如笔者曾经说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及《公羊》经义不可能没有在宏观上的共同理解。如果从正统公羊家的角度来说,董、何所诠释的公羊微言大义,正是先秦以来师师口传的结果,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与思想渊源。董仲舒与何休年代未远,源流相接,虽然未必密合无失,但大旨应该相差不远。”(66)郭晓东:《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外内”——以何休为参照系》,《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就此而言,何休诸说在董仲舒那里见其端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方法论上讲,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来理解董仲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67)正如黄铭所说:“如果从公羊学的理路出发,从内部理解董仲舒与何休的学说,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合法的,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董仲舒后学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与其另立新解,不如从时代相近的《公羊解诂》去诠释董仲舒的春秋学,不必刻意夸大董、何之间的差别。”(参见黄铭:《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海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