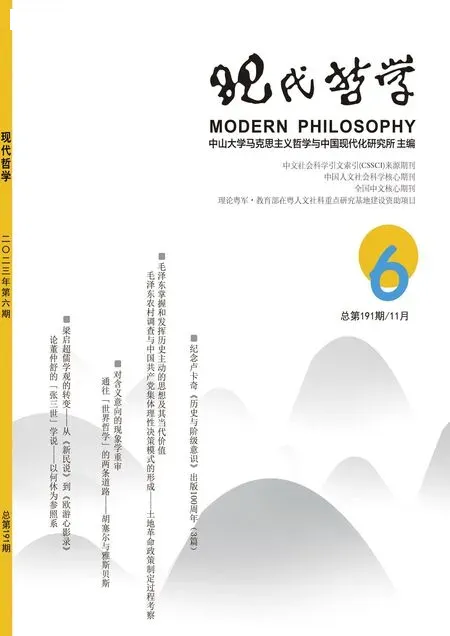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2023-03-21韩燕丽
韩燕丽
中国儒家哲学是在不断重新诠释前人经典的过程中获得进步与发展的。如何从当代和全人类的眼光(包含中西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儒家伦理思想,推陈出新,以彰显中国儒学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成为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儒家伦理研究的一种趋向。随着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与发展,何种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可以适用于儒家,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内外儒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国内外研究美德伦理学的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无论是赞成抑或否定美德伦理学研究进路,对于“美德伦理学”和“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已逐渐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美德伦理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概念为其基本概念的伦理学或者美德概念,或美德问题具有首要性(primacy)的伦理学,相对于基本的或首要的美德概念或美德问题,其他的伦理学概念或问题都是派生的、从属的。而采取康德主义、后果主义或其他研究进路研究美德的伦理学是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因为美德或美德问题在他们那里都只具有从属的或派生的地位。由于任何进路的伦理学都可以研究美德,因而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关于儒家伦理学(包括孟子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争论,实质上应当是关于儒家伦理学是否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儒家究竟有没有作为伦理学的基本或首要概念的美德概念?如果有,这种解读能否完整地表达儒家对这个世界究竟应当怎样的看法。
本文聚焦近年来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重新梳理,证成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适用于儒家伦理学。首先,对学界已有讨论进行归类阐述,指出目前存有诸多争论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儒家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的争论实质。接着,逐步分析和批判儒家美德伦理学不可以成立面临的各种指责,指出各种指责背后隐藏的各种理论预设以及各个理论预设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发现,美德伦理学适用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关键是如何设置讨论标准,儒家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或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亟需给出阐释。
一、关于儒家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争论的实质
随着美德伦理学的发展,儒家美德伦理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英语世界中中国哲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哲学自身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哲学如何以一种合适的身份或诠释方式被世界哲学体系所熟悉以及认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美德伦理学由此而蓬勃发展。具体来说,儒家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历经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争论的第一阶段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影响至今。这一阶段争论的典型特征是,双方都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美德伦理的范本,来谈论儒家伦理是否是美德伦理。一派主张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亚氏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亦译为德性伦理学或德行伦理学),如沈清松、潘小慧、蔡信安、余纪元、万百安(B. W. van Norden)、沈美华(May Sim)等;另一派则主张不是,如安乐哲(Roger Ames)、罗斯文(Henry Rosemont)、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等。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专著性成果当属余纪元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他将孔子与亚氏伦理学进行比较,表明儒家也有自己的美德伦理学。但他所参照的美德伦理学范本是亚氏伦理学,而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亚氏伦理学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德伦理都是成问题的。(1)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学界存有争议。(参见黄勇:《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是朱熹?》,《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据此来说明儒家伦理可以是一种美德伦理,会遇到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至多只能说明儒家伦理是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这将大大削弱儒家学说美德伦理解读的理论价值,也不利于儒家美德伦理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进行对话与交流。
争论的第二阶段大致发生在近十年,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美德伦理学是否可以涵盖儒家伦理学的全部。毋庸置疑,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一样都重视美德品质,但重视不等于可以涵盖儒家伦理学全部。陈来在《儒学美德论》一书中对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将美德做出各种解释以及分类的方式来说明儒家对美德的推崇。他指出,“所有美德伦理的优点儒家伦理都具备”(2)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84页。,儒家伦理作为美德伦理无可置疑,问题只在于如何解读,以及这种解读是否可以涵盖整个儒家伦理思想。杨国荣则指出儒家思想基于仁和礼的统一,既不同于亚氏的德性伦理,也有别于康德的规范伦理,“仅仅从德性伦理的角度考察儒学,似乎不足以把握儒学的全部”(3)杨国荣:《再思儒学》,济南:济南出版社,2019年,第28页。。刘余莉、黄藿也给出过类似的观点(4)参见刘余莉:《儒家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值得注意的是,陈来的《儒学美德论》一书尽管高度肯定认可对儒家美德伦理进行解读的意义和价值,但该书的重心不在于发展和捍卫儒家美德伦理,而是旨在通过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儒家美德理论和道德思想的理解”。(5)陈来:《儒学美德论》,第2页。该书认为儒家美德伦理并不能涵盖全部儒家伦理思想,实际上对将儒家伦理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德伦理能否涵盖陈来所说的“五个统一”(6)这“五个统一”主要是指原则与美德的统一、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一。(参见陈来:《儒学美德论》,第300页。)?能否解释杨国荣所说的仁与礼的统一?
第三阶段大致起于本世纪初并延续至今。双方不再以亚氏伦理学为美德伦理的唯一范本,也不再聚焦于两种伦理学是否可以完全等同,争论的重点转向儒家伦理可否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支持者主要有斯洛特(Michael Slote)、詹世友、黄勇、唐文明、邵显侠等。反对者主要有李明辉和萧阳,与以往的反对者不同,他们并不反对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但反对儒家有严格意义上的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在这一争论中,关于儒家美德伦理研究成果也不再是亚氏意义上的美德伦理。例如,詹世友强调孟子伦理是由内心亲证善端,而非把规范作为前提的美德伦理(7)詹世友:《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其现代省思》,《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3期。;邵显侠强调孟子和儒家伦理是一种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黄勇则认为朱熹的伦理思想比亚氏伦理学更符合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此方面的杰出代表无疑是黄勇,其《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一书讨论的儒家美德伦理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黄氏在“导论”中提出了美德伦理的理想形态和历史形态的概念,并以朱熹为例,证明儒家伦理比亚氏伦理更符合理想形态的美德伦理,是一种更本真的美德伦理。但正如黄氏所言,该书不是试图阐述一种完备的本真的儒家美德伦理,而是重在讨论儒家对当代美德伦理可以做出的贡献,该书也没有具体讨论在儒家美德伦理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美德伦理。事实上,儒家伦理学可以进一步建构更完备、更系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德伦理体系,这一体系绝不止是黄勇所说的分类意义上的,而是表达这个世界应当怎样的不可或缺的体系。总之,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美德伦理就其本意而言是将美德概念视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伦理学的其他概念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它们得到解释和回答。儒家伦理学需要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正面回应。
二、儒家可不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事实上,很多学者并不反对儒家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但反对儒家有严格意义上的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更多地这种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一种符合诸多规范伦理学家期许的美德伦理学。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论点表明儒家伦理学需要对学界给出他们为何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关于美德伦理学的正面回应。面对以往规范伦理学的各种批评,儒家美德伦理学要想真正得到学界认可,不能“只破不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以往规范伦理学批评回应的层面上,必须援引儒家伦理学基本概念的自身合理性来对其可行性给出进一步分析。换言之,想证明儒家美德伦理学并非关于美德的理论,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就不仅要说明儒家重视美德,而且需要证明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且仅是美德,由美德概念能够完整地演绎出该伦理学的全部内容。
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在演绎各自立场的过程中仍有不少争论。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儒家美德伦理学是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表示怀疑。有学者依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家赫斯特豪斯(R. Hursthouse)对何为美德伦理学的概括性表述清单(8)赫斯特豪斯此处的清单原文表述是:美德伦理学被描绘成许多样子。它被描述为:(1)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2)它更关心“是什么”,而不是“做什么”;(3)它着手处理的是“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应当采取怎样的行为”;(4)它以特定的德性概念(好、优秀、美德),而不是以义务论的概念(正确、义务、责任)为基础;(5)它拒绝承认伦理学可以凭借那些能够提供具体行为指南的规则或原则的形式而法典化。(参见[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李义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7页。),一方面延续弗兰克纳(William Frankena)对美德伦理学的批评,认为“每一种美德的定义都依赖相应的规范伦理学理论”(9)邓安庆:《美德伦理学:历史及其问题》,邓安庆主编:《伦理学术第7辑:美德伦理新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页。,另一方面指出目前众多美德伦理学理论中依赖于互相排斥甚至互相对立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美德伦理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前者值得商榷:作者误解了赫斯特豪斯清单的真实意图及立场。赫斯特豪斯在清单引文的下方明确指出:“我之所以列出上述清单,是因为对美德伦理学的这些描述实在太常见,而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好。相反,我认为就其粗糙的简短性而言,这些描述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当然,它们各自包含一定的真理(这正是它们如此常见的原因),而随着我们的推进,我也会返回这些描述,指出他们可能包含哪些真理以及限定条件。”(10)[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第27页。换言之,赫斯特豪斯列出上述清单的目的不是完全否定这些陈述,只是因为这些陈述的简短性表达,容易引起人们对美德伦理学界定的相关误解。这些清单包含一定的真理,但这些真理涉及一定的限定条件,需要对这些真理适用的范围给出进一步的限定性说明。后者也可以被完全反驳:在今天的美德伦理学语境中,儒家美德伦理学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他们之间甚至对某些问题存有纷争,但我们不能据此说明美德伦理学不具有独立性,或儒家伦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争论与反驳中愈加成熟完善。
再如,在《警惕“美德伦理学”的僭妄》一文中,邓安庆犀利地指出“美德伦理学复兴”的过程中表现出“美德的僭妄”,“原因就在于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为了把‘美德伦理’阐释为与功利主义后果论和康德主义道义论相对立的唯一合理的伦理学类型,为自己提出了根本无法完成的一个任务,即将‘美德’(virtue)阐释为伦理学的元概念,不从一个人的行为及其行动原则出发,不以规范性概念为媒介,而仅仅注目于德性本身,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非衍生性的概念,来阐明什么是善,什么是一个善的行为,什么是一个好人”(11)邓安庆:《警惕“美德伦理学”的僭妄》,《伦理学术第11辑:美德伦理学的重新定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主编导读部分。。事实上真的如此么?美德伦理学的美德之所以不能是一种基础性的元概念,是因为美德在古希腊哲学中是一个功能概念,但美德的功能发挥之后,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获得幸福,实现人生的兴旺发达状态。亚里士多德通过聚焦培育美德来阐述道德行为者怎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兴旺发达。再者,邓文初始阶段就假定了性善论的谬误性,认为将美德视为天生、生而具有的道德品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美德并不完全是反乎自然的,如《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讲的“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页。。用孟子的话说,这种人特有的美德能力就是“端”。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德的实现层面,忽视了它潜在可能性层面。美德不仅仅是为道德典范所具有的、静态的道德品质或品格,更是在道德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的动态概念。
邓文还指出,斯洛特没有给出文本证据,说明亚里士多德需要用有美德的个体来说明好的行动。但这样的文本在亚氏文献中并不在少数。例如,“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为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13)同上,第42页。。这句话较为清楚地表现出行为者为中心的立场。再如,“究竟选择哪种行为更好,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具体情境中有许多差异”(14)同上,第60页。。在解释这句话时,亚里士多德引入各种具体的美德,如勇敢是一种美德,勇敢的人是出于高贵而面对死的人。亚里士多德又区分了各种“算不得真正勇敢”的情形,从无知的勇敢、乐观的勇敢、愤怒的勇敢、经验的勇敢到公民的勇敢。这几类勇敢者在面对通常的情境时,表现得与真正的勇敢者没有区别,因此在有效的道德情境出现之前,从行为上无法区分这几类勇敢与真正的勇敢。问题在于,如果在日常情境中无法区别真正的勇敢者,那么等到面临突发情境时,理论上人们是无法判断这些勇敢者中哪个做出真正的勇敢行为。人们的判断只能依据之前被公认为真正的勇敢者(在希腊语境中即英雄)在此种情境中的选择来进行。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面对已预见到的危险而如此的表现,可以是出于推断和逻各斯的,而面对突发的危险而如此表现则必定是出于品质的。”(15)同上,第86页。可见,真正勇敢的行为是出于勇敢这一美德的。总之,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在今天的美德伦理学语境中,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但支撑斯洛特的观点的文本证据不在少数。按照这种理路,邓安庆大概会认为要更充分地证明一种儒家作为严格美德伦理的依据和可能性,必须要说明儒家思想是否能够充分证明美德是一个元概念,以孟子为例的话,仁与义在孟子这里不依赖于礼的规范性是否可以得到阐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除了意味着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中美德可以以概念还原的方式作为一个元概念,解释推衍出其他概念,还意味着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像罗伯特·罗登(Robert B. Louden)等指出的那样,在一元论策略下以美德作为基本概念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德伦理学家试图证明美德伦理学具有与其他伦理道德理论一样的“等级结构”,但反对者们试图证明美德伦理学的“等级结构”并不成功,以此来攻击美德伦理学。
不妨进一步考察对这一观点最成功的论证。萧阳指出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标准美德伦理学具有总体上的“等级结构”,萧阳对“总体的等级结构”的定义是:概念X是伦理学E中的基本概念,当E是基于X的伦理学,即X逻辑上先于并独立于E中的其它概念,并且这些所有其它概念都从X中衍生而来,那么E具有以X概念为基础的“总体的等级结构”。他认为孔孟的学说更接近一种具有总体上的非等级结构,存在“局部性的”基本概念,但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基本概念的非标准伦理学理论,这意味着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美德伦理学,只是一种关于美德伦理的理论。为了说明这点,萧阳试图从“礼在其生活领域中的基础地位”“人伦在孟子伦理学中至少要与美德平等的基础地位”“仁政并不要求仁作为必要条件”(这是最弱的角度),来说明儒家伦理学的非等级结构特征。用他的话说,儒家伦理学在某些生活领域的局部亚结构可能是有基本概念的等级结构,但“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基础概念”(16)参见萧阳:《论“美德伦理学”何以不适用于儒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所以儒家伦理学不可能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当萧阳指出美德伦理学“模仿了另外两种伦理学”时,似乎暗示美德伦理学存有不模仿另外两种伦理学的空间,或者说存有基本概念的可能。在“好礼”论证中,萧氏认为“礼”在儒家伦理学中是先于“好礼”的基本概念,但“礼”不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概念。“《论语》中伦理学的总体结构并不将礼当作‘总体上’的基础概念,因为并非所有其他概念都能通过礼的概念来得到定义,所以说,《论语》中伦理学理论的总体结构依旧是‘扁平’的,尽管其中存在着局部的‘等级’亚结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引入一种“总体上的等级结构”,为美德伦理学提供一种更合适的底层结构。他认为存在两种可能的“总体上的非等级结构”,一种是简单的不存在可以衍生出所有其他概念的基本概念,另一种是不存在基本概念,但存在具有不同基本概念的等级亚结构,而儒家伦理学的“礼”就不是一种总体上的基本概念。“人们最终应该获得许多美德,‘好礼’就是其中的一种美德。但是,这个美德不是基础概念。至少就好礼这一美德来说,‘礼’是基础概念,礼是在独立于好礼这一美德的条件下先被给出的,再从‘礼’这个基础概念衍生出来‘好礼’这个美德概念:那些使人喜好礼的品性特质就是‘好礼’的美德。”(17)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对此,黄勇指出,仁是目的,礼是手段,所以礼不是真正的基本概念。但黄勇并没有直接回答萧阳文中“好礼”这个美德的问题,在黄的论证中,“好礼”是次级美德,“礼”是行为规范,而“仁”是基础美德(cardinal virtue),这种关系类似于“守法”“法”“义”的关系。这样的话,“好礼”在儒家美德伦理的美德表中占据的还是次要地位。萧氏指出,“《论语》中伦理学的总体结构并不将‘礼’当作‘总体上’的基础概念,因为并非所有其他概念都能通过礼的概念来得到定义”(18)本段萧阳相关观点,参见萧阳:《论“美德伦理学”何以不适用于儒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这一观点的完整表述也许是,礼在人伦这一生活空间内是基本概念,且不可化约为仁义。如果进一步引用黄勇对广义美德伦理学、狭义美德伦理学的分类(19)参见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结合萧阳的分析理路,尤其是“好礼”中礼的基础地位的思路,他将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在《论语》的狭义伦理空间中,仁是唯一的基本概念,且仁是美德。这就相当于至少在狭义的伦理空间中,萧阳已经承认儒家美德伦理学具有基本概念,儒家美德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其他的生活空间中进一步扩展仁的基础性地位,或者将那些非美德的基本概念解释为美德;同时应注意到,“好礼”论证不是文章的论证核心,而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的等级结构特征。至于“人伦”论证,孟子伦理学是以“人伦”为基本概念的关系伦理学这一说法并不充分。就像黄勇反驳的,没有充足的文本证据可以证明“人伦”的基础性地位。在《孟子》中,“人伦”一词共出现6次,加上“大伦”的相关表述也只有9次。萧氏对“人伦”的理解似乎局限于“人际关系”。但孟子在有的文本中,例如“饱食”“暖衣”而无“人伦”,“近乎禽兽”(《滕文公上》)中使用“人伦”时,其实表示的是“一种好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黄勇亦歪曲了萧阳的论证。
事实上,对于儒家伦理学的“等级结构”问题,萧氏所有关于“等级结构”的结论所蕴含的假设是,儒家伦理学并不具有功利主义、义务论那样的“等级结构”,所以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值得商榷。“等级结构”之所以是儒家美德伦理学存在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大家潜在地认为一种伦理学若要有独立性,必须有自己的基本概念,且基本概念推演出其他派生概念,其他派生概念可以通过概念还原主义还原为基本概念,进而构建伦理体系。但是基本概念与派生概念的关系并非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单维度的推演关系,基本概念可能是一系列较为丰富的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概念系统,源头的或者优先的基本概念一定是极少数的几个甚至是一个概念,这并没有定论。但是萧阳在论证过程中显然是忽略了基本概念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概念还原也不是萧阳理解的那样,必然是一种严格的概念还原体系,有时人们在反思或思考伦理问题时,优先会想到一些作为参考的概念,人们优先想到的、作为参照的概念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优先关系”而被人们获得,甚至作为基本概念。这种“优先关系”在思维体系中被等同于“还原关系”。(20)参见韩燕丽:《也论基本概念》,《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儒家美德伦理学中基本概念与概念还原的关系类型,而不是对儒家美德伦理学等级结构进行盲目否定。毕竟,儒家伦理学拥有自己的美德基本概念体系,不一定完全与义务论、目的论的基本概念体系一致。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这一论断并不成立。
三、儒家为何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具有自己的基本美德概念且追求理论自足性的伦理学。这一观点尽管未被明确提出以及讨论,但从未被学界遗漏。有些学者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儒家美德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但在阐述相关理论时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角度展开讨论的。西方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就曾将美德伦理学定义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必须将德性论概念(如‘好’或‘卓越’)而非道义论概念(如‘道德上错误’,‘应该’,‘正当’与‘义务’)作为首要的,而且它必须更多地强调对行动者与其内在动机和品质特质的伦理评价,相对于对行动和选择的评价来说。”(21)[美]迈克尔·斯洛特:《从道德到美德》,周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斯洛特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它必须满足两个核心的、彼此紧密联系的要求:第一,基础性要求,即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亦即基础概念)是且仅是美德;第二,完备性要求,即由美德概念能够完整地演绎出该伦理学的全部内容。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证成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至少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完全可以满足基础性要求,即儒家的诸美德概念完全可以成为儒家伦理学的基础或基本概念。所谓基础或基本概念,是指“一个理论中无法通过其他概念加以解释或定义,但却可以用来解释或定义其他概念的概念”(22)陈真:《何为美德伦理学》,《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对儒家伦理学来说,美德概念作为其基础概念就意味着,美德概念是整个伦理学架构以及价值取向的主要概念,且美德概念可以产生一系列次阶概念,基础概念和次阶概念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建构起可以与以往规范伦理学相抗衡的伦理学框架。反对将儒家伦理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或基础概念是可以通过规则加以表达的义务或礼,而美德不过是遵守义务或礼的心理倾向,因而儒家的美德概念只是派生的,礼和义务才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概念。(23)典型的如李明辉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一种美德伦理,而是一种义务论。(参见李明辉:《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
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我们对儒家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直觉。人们常常称孔子的哲学是仁学,此处的“仁”显然是一个美德概念,由此可以派生出关于“仁”的义务或行为规范。蒙培元曾经多次给出过类似的表述。比如,在《孔子‘仁’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蒙培元明确指出,“仁并非是‘是什么’,而是‘要如何’,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目的性的过程”,“仁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24)蒙培元:《孔子“仁”的重要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对于道德行为者而言,仁是一种存在状态,是一种内在德性品质。《论语·述而》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里的“我欲仁”就是道德行为者想要践行美德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斯仁至矣”就是道德行为者真正拥有仁这种行为准则。再如,《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显然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心理状态(即美德),将其表达为规则是“应当爱人”,这显然是美德规则,亦即包含美德概念的行为规则。可以说,我们很难将孔子的“仁”理解为一种仅仅是为了遵守“爱人”规则的心理倾向,或者我们很难理解为先有“爱人”的规则,然后才有遵守此规则的心理状态“仁”。所谓“仁者爱人”,“仁者”是一个美德概念,只有具有仁之美德的人才会有爱人之行为,而不是先有爱人之义务,后有仁者。儒家伦理学中关于仁的另一种主要观点是“为仁由己”,它强调的依然是行为者值得称赞的心灵状态(即美德)是首要的,它甚至无需规则,直接可以导致仁的行为,即便有规则也是包含美德概念的行为规则。
孟子的“四端说”更为明显地表明了儒家诸美德概念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四端之心”无法还原为规则、义务等,因为它们就是值得称赞的情感状态或心灵状态。这种情感状态是对外部环境刺激下的直接的情感反应(25)学界对于“四端之心”为何是一种本然的情感状态有着很多分析。比如,曾海军指出:“孟子通过反思得出恻隐之心非因任何后天经验的结论,由此将恻隐之心落实在本然之心上。”(曾海军:《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理论学刊》2023年第3期。),没有任何规则或义务作为中介。“四端”就是发端、起源、源头之意,用现代伦理学的术语就是:它们是基本的、首要的。四端之心,如不忍之心就是一种值得称赞和肯定的心灵美德状态,它很难是一种规范或义务或礼,但它们却是所有行为规则之源头。
源于四端之心的仁义礼智,首先是美德意义上的伦理学概念,然后才是体现美德要求的行为规则(即所谓义务)的概念。相对于四端之心,它们是派生的美德概念;相对于行为规则,它们又是更基本的伦理学概念。邵显侠就曾指出,孟子伦理学的“四德”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称谓或概念符号,而是一种关于人心的应然性美德规范,这种美德规范规定了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这种美德规范是人性的评价性概念,而不仅仅是以往规范伦理学类型中的确定不变的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学中的仁义礼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给出不同形态的行为规范。(26)邵显侠:《论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黄勇在回应萧阳的批评时也指出,《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讲“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在实际生活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但如何保证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如何确定什么是好的人伦,最终还要取决于五种美德“亲、义、别、序、信”,这事实上证明了美德概念(好人)较之于人伦概念的首要性,美德概念是一种基本的伦理学概念,或者用黄勇的话说“这五种关系是有五种美德规范的,因为不可能比这五种美德更根本,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基础概念”。(27)黄勇:《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其次,儒家伦理学能够完全满足完备性的要求,即儒家伦理学中所有其他的非美德的伦理学概念,如以礼为代表的行为规则、义务概念、社会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等,都可以从儒家的诸美德概念中推导或演绎出来。从四端之心派生出的伦理学概念,首先是美德概念(如仁义礼智),其次才是包含美德概念的行为规则,二者逻辑上无法分开,但内容上则是美德为本、为源,规则义务为辅和派生的。赫斯特豪斯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美德伦理学中可以存有提供大量的美德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来源于美德或恶德的术语,这些术语暗含的行为规则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尽管这些规则要“通过在某种或某些意义上必然具有评价性的术语或概念来表达”;她还进一步举例说每一种美德品质都有着对应的行为规则,比如诚实是美德概念,从这一美德概念中可以衍生出两条规则,一是“不要撒谎”,二是“要说真话”。(28)[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第41、43页。遵循这一逻辑,儒家伦理学中的美德概念(如仁义礼智)也延伸出一些派生的美德规则。美德概念系统能够派生出行为规范内容以及能够派生出价值评价内容。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五伦”,它首先是美德,然后是体现美德或表现美德的行为概念或行为规则。
关于社会政治理想,孟子以“不忍之心”为基本美德概念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想,包括其社会经济理想,本质上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道德政治学说。在孟子的理想政治社会中,统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美德品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践行“民贵君轻”民本主义,推行“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才能真正实现“贤人”作为一种美德概念的贤人政治。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他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的结果,“四端之心”是能够实现贤人政治的根本保证。詹世友曾指出在孟子的道德学说中,君主必须“德能称其位,一旦失德,君主就是独夫民贼”,“王道政治就是基于美德的政治秩序”。(29)詹世友:《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其现代省思》,《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3期。白彤东也对孟子道德学说中的贤能政治给予认可态度,并依据大人小人的理解,指出“这一政体引入和强化了那些有能力、有道德的贤能者的作用”,得出“治权在贤”的结论。(30)白彤东:《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文史哲》2013年第3期。
综上,儒家伦理学不仅可以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且这种解读比康德主义等其他的解读似乎更为符合儒家伦理学的本来面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解读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具有首要性的美德概念应具有合理性,如何说明儒家美德概念自身的合理性,避免因采用其他概念的解释而将其变成派生性概念?再如,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中的美德概念与其他非美德的伦理概念之间的关系多是演绎推理的,而儒家的思维方式多是比喻类比或解释性的,我们如何按照非演绎的方式重构儒家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评价体系?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将儒家伦理学解读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是对儒家伦理学研究的创新与推进,可以进一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德伦理学体系,尽管这条道路上会有一些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