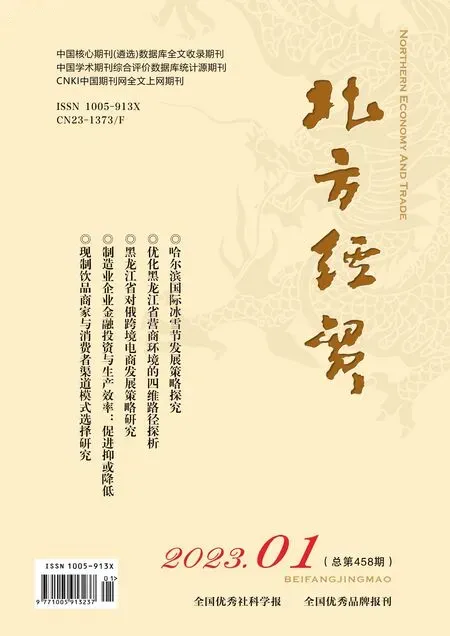产业双向转移协同与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2023-03-21廖双红
廖双红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一、问题提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升级”主要方向。为此,湖南省专门发布了《“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坚持“积极引入高端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高端发展”的基本原则,把“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畅通内外循环体系”做为“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推进举措。产业转移具有提升区域分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产业关联等作用,被认为是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实践中,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产业“引进与转出”的双向转移过程中实现了产业升级,是国家产业创新发展成功的关键。《2020年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正加速转入中国”,与此同时,《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表明,“中国服务业与低端制造业正加速走出去步伐”,显然,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产业双向转移发展机遇,但与日本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具有大国经济发展优势,区域间产业转移浪潮趋势明显,区际产业“引进与转出”双向转移同样有利于产业升级。立足于湖南,作为中部地区主要省份,长期在产业转移和国家价值链构建中承担“承东启西”枢纽作用,“产业承接与转移”面临着国际与国内多重双向机遇,因而从产业双向转移协同角度提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及路径,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产业转移方向及其产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1.基于产业转移方向讨论的理论总结及新兴产业创新理论提出
从国际产业转移兴起之时,国内外学者大致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比较优势”作用下,边际产业会从先发地区向后发地区渐次转移形成“梯度分工”升级模式,带动双边产业升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梯度转移容易导致“中心-外围”分工模式,造成后发地区“低端锁定”,因此,后发地区为了避免这一“路径依赖”,可在技术创新引领下主动承接高技术产业,突破分工锁定,实现跨越式发展。后一种观点为后发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区位机会窗口”与“区域产业分叉”理论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区位机会窗口”认为,新兴产业在产业体系上不连续、生产环境上有新要求,以及受偶然事件影响巨大,其产生区位是相对自由的,因此,在产业承接和升级中相对不受“梯度分工”的制约;而“区域产业分叉”理论则认为,新兴产业更有可能脱胎于地方现有的产业体系,原因在于新技术的空间溢出和外部扩散效应,使得地方可通过依托本地知识储备或获取外部知识实现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1]可见,产业“引进与转出”均可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机会窗口和产业分叉”发展特点又为后发地区高端要素引进、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可能路径。立足于湖南,作为相对后发地区,上述产业转移与承接理论为区域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支持。
2.基于价值链式产业转移方向讨论及升级效应研究
21世纪以来,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式产业转移及其升级效应成为研究主流。中国作为全球化积极参与国家,开始出现国际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沿海产业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内地转移的“梯度”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对外逆向技术投资、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等“反梯度”现象凸显,加剧了产业转移方向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产业转移的多重双向性特征及其价值链升级效应成为研究焦点。学者们围绕“双向FDI及中国双向产业转移”“‘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中国区域内产业转移”等主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由于选取指标、测度方法、研究区域和行业等的不一致,认识并不统一。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国际产业转移上,部分观点认为产业“引进来”能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走出去”能构建以中国为“链主”的产业价值链,二者双向协调发展能推动产业链创新升级;[2]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会出现“引进来”的产业价值链“低端分工锁定”、“走出去”的国内“产业空洞化”及产业链断裂等现象,不利于产业价值链升级。[3]因此,一些学者实证检验认为“双向FDI协同”发展才能显著促进价值链升级。[4]二是在国内产业转移上,一些学者认为沿海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趋势明显并带来价值链升级效应;[5]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梯度”趋势不明显甚至具有部分“反梯度”特征,如中西部部分先进制造业有进一步向沿海集聚的趋势,而且顺梯度转移可能并不利于整个国家价值链升级。[6]
(二)关于新兴产业内涵及创新发展研究
中国自2009年提出发展新兴产业以来,发展新兴技术与产业创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1.新兴产业创新内涵特征及行业界定
Porter(1980)最早提出新兴产业概念,认为是新形成的或在原有产业基础上重新形成的产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相对生产成本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经济社会变化带来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等潜在商业机会等是其产生动因。然而,国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等角度对具体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因素进行研究。国内在新兴产业概念基础上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概念,因而,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创新形态构成其主要内涵特征,也导致新兴产业的行业界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带来“未来产业”概念。
2.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及路径选择研究
学界围绕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模式选择及路径设计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结论较为统一。具体来看:第一,在创新能力指标构建及评价方面,认为政府行为、市场环境、技术创新、企业战略、资本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等构成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围绕“产业政策”“市场化改革及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创新网络”“金融支持”“人才引进”等主题开展创新能力评价、创新效率测度、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及构建等理论与实证研究,其创新能力评价结果显示,湖南处于全国中等创新水平,其中国际贸易水平较低、本地知识创新能力较强,[7]亟须寻求对外开放创新模式。第二,在创新模式与路径选择方面,根据创新要素的影响程度及传导机制差异,学者们提出政府支持型、技术引领型、市场推动型、企业驱动型等不同创新模式,相关“关联产业集群”“产业项目群集聚”“技术合作、转让及引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整合创新资源”“纵向和横向产业链发展”等构成主要实现路径。可见,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可通过获取外部资源用以重新整合内部创新资源,进而推动产业链高端迈进。不难看出,产业转移战略无疑是新兴产业重要的创新路径,尤其是对于湖南这样相对创新能力较低的后发地区,就创新战略选择而言更为重要,因此,一些学者从全球产业转移视角探讨了新兴产业创新动力获取与路径选择等问题,认为国际双向产业转移策略对于新兴产业做强做大有决定性支持作用,如引进先进技术与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并重。
整体而言,产业双向协同转移是后发地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及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大国雁阵升级”的特有模式。从二者的文献综述来看,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到二者的融合研究,但仅停留在定性和制度分析层面,需要更多的理论探讨及定量研究。本文为今后开展研究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