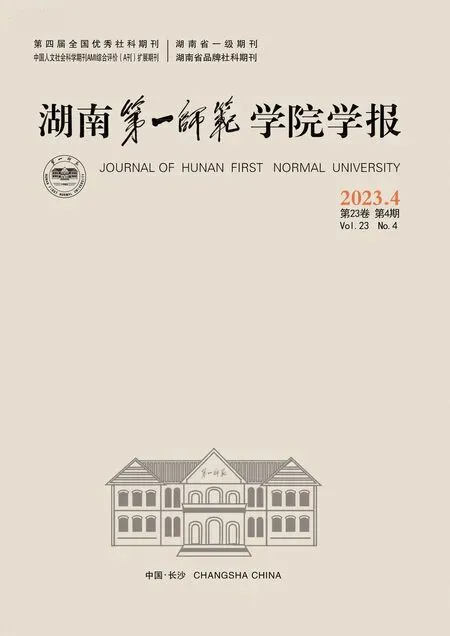清末民初典型理论嬗变探微
2023-03-12杨旭
杨 旭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典型理论是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互相碰撞、渗透、交融的结果。不过,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虽与日俱增,但由于社会根本结构未发生改变,传统文化仍然在惯性的作用下运转。1894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与影响,也引发了文坛剧变,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由此产生,典型理论也开始萌芽。1897 年,《国闻报》所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高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同时对典型开始最初的探索,讨论了文学形象的产生、形象与生活的关系、形象的生命力等问题,这可看作是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兆始。直到1917 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文学革命,中国典型理论由此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历史上看,1897—1917 年正是清末民初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典型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起始(1897—1906)、发展(1907—1910)、和深化(1911—1917)三个阶段。下面拟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理论①,试对其发展、内涵和特点做一点探讨。
一、小说革命的催发(1897—1906)
起始阶段的代表性小说理论家以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狄葆贤等人为主,以1902 年创刊的《新小说》为中心,可命名为“新小说派”。重要理论有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夏曾佑的《小说原理》、新小说派众人的《小说丛话》等。
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典型理论的基本前提。新小说派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存在着政治期许与文学功能间的脱节。在政治维度,新小说派认为文学高于生活,小说对社会有决定作用。1902 年,梁启超倡导和发起了小说界革命,主张著译为维新改良服务的政治小说。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一,彻底否定了旧小说,认为旧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1]370,“含有秽质和毒性,它们毒害了人群,导致社会腐败”[1]53;其二,过分夸大了新小说的社会作用,把新小说当成了解救社会时弊的灵丹圣药,得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722的唯心结论。这是政治意图对小说审美功能的僭越,忽略了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决定的意识形态。
在文学维度,新小说派从注重小说的社会作用出发,开始实际接触和创作小说。这引发了他们从传播、创作、读者、文体等角度理性思考文学与生活之关系。直到1905 年曼殊发表《小说丛话》,这一关系才得以明确。从传播角度看,严复、夏曾佑认为:“必其所言服物器用,威仪进止,人心风俗,成败荣辱,俱为其身所曾历,即未历而尚有可以仰侧之阶者,则欣然乐矣。”[4]11人们只对经历的或可以想见的生活发生兴趣。从创作角度看,夏曾佑认为小说创作中“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5]12,原因在于作者在创作时推己及人,君子、大事、富贵,超出认知,容易失真;小人、小事、贫穷,切身经历,有感而发,因而栩栩如生。从读者角度看,觚庵认为,小说来源于人们的日常见闻,读者对其经历越深则感触越深。从文体角度看,楚卿认为,“小说则与诗词正成反比例者也”,诗词贵含蓄,小说重发泄,强调直接、透彻地反映生活,深切洞察社会人生。读来,“如扁鹊所谓见垣一方人,洞悉五脏症结,如温渚然犀,罔两魑魅,无复遁形”[3]819。直到曼殊在《小说丛话》里明确地提出社会是小说形成的范本,内容不能脱离社会的范围。两者关系紧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4]79。
新小说派注意到典型形象的一些基本特征。(1)代表性。“今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型”“式”即模板和范式,典型人物被推立出来作为效法的典范,要有一定的代表性。(2)理想性。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可以不受限制,“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4]77,自由无碍,寄寓心中理想。(3)特殊性。典型人物“必其人有过人之行,偏胜独长之处,而使天下之人怪叹骇汗,怨慕流连,不能自止者”[4]2,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跨越时空,让人如见其人。今人惋惜的是,新小说派对形象的代表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认识不够辩证,对理想性的认识稍显稚嫩。总体而言,这些理论较为零散,还未达到体系化的程度。
典型化是典型塑造的手法。新小说派的典型化主要体现在虚构、细节描写、倾向性三个方面。
(一)虚构。严复、夏曾佑认为,世事常与人心相违,因而人们希望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获得“情理之真”。即便有时情理之真难免沦落为惩奸除恶、因果报应的“大团圆”,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至少表明小说的虚构性已成为他们的一种认识自觉。“若其事为人心所虚构,则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若稍存实事,略作依违,亦必嬉笑怒骂,托迹鬼神。”[4]11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将小说分为写实派和理想派,“理想派”是指“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3]719。“他境界”即虚构的理想世界。理想和写实是分立的,虚构和现实自然也是分离的。浴血生进一步认识到虚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创造,“悄思冥索,设身处地,想象其身段,描摹其口吻,淋漓尽致,务使毕肖”[4]70。
(二)细节描写。事物刻画的详略程度和语言的繁简密切相关,精确地运用恰当的语言能充分展现事物各个侧面,利于典型创造。“简法之语言,以一语而括数事。……繁法之语言,则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读其书者,一望之顷,即恍然若亲见其事者然。”[4]10简法之言与繁法之言各有其特点,简法之言,语简事阔,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众多事物;繁法之言,事简语繁,详细地描绘事物的情状,展现事物的细节,达到繁言如画的效果。“同一义也,而纵说之,横说之,推波而助澜之,穷其形焉,尽其神焉,则有令读者目骇神夺,魂醉魄迷,历历然、沉沉然,与之相引,与之相移者矣。”[3]818楚卿认为运用繁法之言可以对表达对象展开全方位、多侧面的描写,“穷其形”且“尽其神”,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倾向性。新小说派提倡的政治小说,往往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直接宣传主张或发表议论,缺乏艺术性,枯燥乏味。梁启超自评《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6]5620政治小说的艺术水准可见一斑。在此情况下,夏曾佑敏锐地察觉到政治意图过强对小说艺术性带来戕害,从而转向对小说本质的探寻。他认为,“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5]13。他意识到小说与《经世文编》不同,小说是通过人物形象来表情达意的,过多发表议论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夏曾佑的观点是当时新小说派倡导小说革命的众多急切主张中一种难得清醒的声音,达到了新小说派对倾向性认识的最高水平。
新小说派十分重视典型的作用,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典型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榜样的作用。“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代表性人物的行为举止可以树立榜样,引领潮流,使人们争先效仿;二是能带给人自信。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能给予理想不坚定的读者精神上的力量,增加读者的自信。“小说作,而为撰一现社会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示之,于是向之怀此思想而不敢自坚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三是能提供情感慰藉。读者通过阅读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获得情感慰藉。“虽昌言之不敢,而悱恻沉挚,往往于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则或因彼之知我而怜我也,而因曲谅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怜彼,而相结之情乃益固。”[4]77-79
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使小说理论得到关注。新小说派典型理论是小说研究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转变的阶段性产物。时代所致,有浓厚的功利性色彩,但典型的审美性也得到了初步关注,如典型形象的特性、倾向性等,是新小说派初步探索的结果。
二、小说林派的发展(1907—1910)
第二阶段,以1907 年创刊的《小说林》为标志,徐念慈、黄人等人为代表。重要理论有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话》等。代表人物、重要理论均与《小说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命名为“小说林派”。小说林派从新小说派得到理论启示的同时,突破和纠正了其偏颇之处。
小说林派批评了论者往昔对小说“失之过严”及今时对小说“誉之失当”的两种错误倾向,认为小说既不是致命的“鸩毒霉菌”,也不是“国民进化”的唯一动力。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和新小说派小说观的双重纠偏,对小说地位有了清晰的定位后,小说林派表达了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他们认为文学和生活不能“沟而分之”“阙其偏端”,二者互为因果。小说通过“人生的起居动作,离合悲欢”的“形式”来记录人类的“事迹”,内容不能超越社会的发展和欲望的生长,同时小说的娱乐、启迪、审美作用又可促进社会的发展[5]48。社会风尚和小说双向互动,互相作用。南北方不同的风尚造成了南北小说的不同内容,“北方各行省,地斥卤而民强悍,南人生长膏沃,体质荏弱,而习为淫靡,故南北文学……各据其所融冶于社会者为影本”,“原其宗旨,未始非厌数千年专制政体之束缚,而欲一写其理想中之自由”[4]245,而不同的内容表现了人们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愿望。
徐念慈主要借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1770—1831)和邱希孟氏(Kirchmann,1802—1884)的美学观点来探讨典型问题。(1)醇化于自然。“‘艺术之圆满者,其第一义,为醇化于自然’。简言之,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3]924黑格尔这句话的原意是“使人感到快乐的表现必须显得是由自然产生的,而同时又像是心灵的产品,产生时无须通过自然物产生时所须通过的手段。这种对象之所以使我们欢喜,不是因为他很自然,而是它制作得很自然”[7]210,意在强调形式的自足性。徐念慈将其理解为小说通过艺术世界,满足人们的欲望,使人感到圆满,没有遗憾。他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中国“团圆说”色彩。戏曲《荆钗记》中的团圆、《杀狗记》中的封诰、《千金记》中的荣归、《紫箫记》中的巧合等情节安排,都是这种圆满的体现,合乎理性,符合生活规律。(2)形象性。“‘美的概念之要素,其三为形象性。’形象者,实体之模仿也。”[3]925徐念慈接受了邱希孟氏的观点,认为形象源自对具体实物的模仿。早期的神仙、鬼怪、恶魔,大受欢迎,就因其具有形象性,“《长生术》《海屋筹》之兴味,不若《茶花女》《迦因小传》之秾郁而亲切矣”[3]925,因为《长生术》《海屋筹》等医学养生书籍,不具有形象性,而《茶花女》《迦因小传》具有亲切可感的形象,受到读者喜爱。(3)具象性。“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3]925徐念慈将个性呈现的丰富理解为人物和故事的繁复,“事迹繁,格局变,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拙奇正杂陈,其首尾联络,映带起伏,非有大手笔,大结构,雄于文者,不能为此”[3]925,强调人物、事件的密度,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黑格尔的本意侧重事物呈现的深度,“理想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是通过外在现象的一切个别方面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个别方面无不渗透着这种意蕴,每一种形式都和所要体现的那种普遍的意蕴密切吻合”[7]221,符合“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命题。徐念慈的理解与其大相径庭,“他是用‘古目’来理解黑格尔的‘新制’的”[8]17,文化上的误读使我们与黑格尔的“个性化”思想失之交臂。(4)理想化。“‘美之第四特性,为理想化。’理想化者,由感性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之谓也。”[3]925徐念慈对邱希孟氏的“理想化”作了解释,认为小说创作并不是把生活中的事物和盘托出,而是对感兴实体加提炼、筛选、概括、通过创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5)情感性。徐念慈注意到典型的情感作用,认为以“实体形象而起”[3]925的小说,能带给人美的快感。《水浒传》《野叟曝言》《花月痕》《三国志》《西游记》《济公传》以及外国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马丁修脱探案集》等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作品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
与徐念慈借鉴西学不同,黄人的典型理论来自对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经验的归纳总结,具体而微,体现了典型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要做到真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4]239人物描写可以将人物理想化,但是有一定界限,一味地求全责备,反而会失掉人物的真实性。《水浒传》中的宋江、《石头记》中的贾宝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恰是这些缺点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心生敬佩。《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十全十美、全知全能,过于理想化和圣神化。因此,读者读之如同嚼蜡,索然无味。作者还指出,只要描写得真实,即使描写的是像《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一样“人格,可谓极下矣”的反面人物,同样能受到读者赞赏。
(二)作者论断的掺入就如戏剧中的预言人物品性的“定场白”是横加于作品的,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性,使作品淡乎寡味。“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掺入作者论断。”[4]238黄人主张作者在描写人物时,放弃主观情感,成为一面镜子。唯其如此,作者才能忠于客观事实,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描写。黄人的观点乍一看很符合19 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实际上,这一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优秀小说丰富的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4]238“妇孺能辨”在于作家是通过自然发展的情节和合乎逻辑的人物行动来呈现人物性格的。只有这样,人物才有生命,才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被大众所接受。
(三)精准的细节描写有利于塑造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水浒》鲁智深传中,状元桥买肉,妙矣,而尚不如瓦官寺抢粥之妙也,武松传中,景阳冈打虎,奇矣,而尚不如孔家庄杀狗之奇也。何则?抑豪强,伏鸷猛,自是英雄本色,能文者尚可勉力为之;若抢粥杀狗,真无赖之尤矣。然愈无赖愈见其英雄,真匪夷所思矣,而又确为情理所有者,此所以为奇妙也。此种颊上添毫手段,惟盲史有之,史迁尚有未逮也。”[4]241黄人认为,鲁智深状元桥买肉,武松景阳冈打虎,抑豪强,伏鸷猛是英雄的普遍性特征,具备一般写作经验的人也能描写出来。但是鲁智深瓦官寺抢粥、武松孔家庄杀狗,这类从生活里捕捉、选择、提炼出来的细节,蕴含了人物的特有内在精神。这样微处传神、颊上添毫的细节描摹,一经写出,便可达到“愈无赖愈见其英雄气概”的艺术效果。
小说林派回归文学自身,注重对文学内部创作规律的揭示。他们的典型理论兼顾小说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一方面将西方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小说创作实际相结合;一方面从中国传统优秀小说中提炼、总结人物塑造的经验,拥有自觉的本土化探索意识。某些见解新颖独到,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学理性,这标志着清末民初典型理论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三、综合派的深化(1911—1917)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随即取代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小说理论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典型理论仍沿着晚清道路继续发展。直到1917 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标志着古典文学结束、现代文学兴起的文学革命,才逐渐建立起不同性质的典型理论。鉴于此,我们将1911—1917 年的典型理论归入清末民初典型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深化阶段。深化阶段以管达如和吕成之为主要代表人物,《说小说》和《小说丛话》为重要理论。他们的典型理论发展并深化了起始、发展阶段的理论资源,可命名为“综合派”。
综合派对文学的主动性、创造性有深刻的体会,认为文学创造了“第二人间”“第二社会”。“夫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使社会上无此等人物,此等事实,则小说诚无由成。然社会者,又小说之反映也。因有小说,而此等心理,益绵延于社会。然则社会也,小说也,殆又一而二,二而一者矣。”[3]1003-1004“小说者,第二人间之创造也。第二人间之创造者,人类能离乎现社会之外而为想象,因能以想化之力,造出第二之社会之谓也。”[9]471管达如认为,小说和社会互相影响,小说记录的是理想界的事实,事实界不能有的“仙人”“鬼神”“绝对之快乐”“绝对之苦痛”,理想界都可以存在,因而小说比生活拥有更多创造性。吕成之认为,小说之美在于“第二人间的创造”,通过想象创造自成“一个人间”“一个社会”,拥有自身的独立性,深度契合小说的美学规律,这是对前两个阶段认识的深化与超越。
综合派的典型化手法,比起前两个阶段更具系统性,内涵更加丰富,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美的制作。吕成之认为任何“美的制作”都需经过模仿、选择、想化、创造四个阶段。一曰模仿,“见物之美而思效其美之谓也”[9]470。人有辨别美丑的天性,对美的事物主动观察、学习、效仿。二曰选择,“去物之不美之点而存其美点之谓也”[9]471。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光怪陆离,色有优劣,音有高下,作者要在纷杂的事物中留存美的事物,摒弃丑的事物。三曰想化,“想化者不必与实物相触接,而吾脑海中自能浮现一美的现象之谓也”[9]471。在完成模仿、选择阶段之后,就可以进入想化阶段。想化有两种方式:一是离开实物的想象,一是在实物基础上进行增删,大致等同于幻想和联想。四曰创造,“能想化矣,而又能以吾脑海中之所想象者表现之于实际,则所谓创造也”[9]471。将想象中的事物实际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经此四个阶段,美的制作诞生。虽在论述美的制作的四个阶段实际上与文学典型生成的过程相一致,前后衔接颇具条理性和系统性,代表了清末民初典型生成理论的最高成就。
(二)细节描写。吕成之认为小说描写社会、人物的特点——“小而深”,同样也是细节传神的根本原因。“何谓小?谓凡描写一种人物,必取其浅而易见者为代表,描写一种事实,必取其小而易明者为代表也。”[4]431小说描写人物在小,其目的在于“以小见大”。吕成之举《红楼梦》来说明人生在世,永不能满足的痛楚。曹雪芹在人生众多不能圆满的事件中选取了男女之爱为代表,在男女之爱中又选择贾宝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为代表。男女之情为人所共有,宝玉、黛玉之情又凄婉诚挚,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宝玉、黛玉“意难平”的爱情悲剧是表达这种理想最合适的代表。“何谓深?凡写一事实,描一人物,必较实际如重数层是也。……惟单纯也,对于他种事项皆一不错意,然后对于其特所注意之事项,其力量乃宏。如酿酒然,水分愈少,则力愈厚。”[4]431这一看法接近于对人物性格进行“蒸馏”“提纯”,通过重描使人物的某种特性“显著”“集中”呈现,但“富有个性的具体存在作为现实存在,一旦无限夸大,恰恰会走向现实性的反面,同自己所反对的普遍概念一样成为纯粹观念,或诗意想象”[10]9。
小说描写人物小而深的特点,实质上和小说创作过程密切相关。“凡文学,必经选择及想化二阶段。小说所举之代表人物,必缩小其范围者,以小则便于想象,大则不便于想象,作者读者,皆如此也。所以必如重几层,则基于选择之作用。盖有所加重于此,必有所割弃于彼,正所谓去其不美之点,而存其美点也。”[4]432“小”是为了便于“想化”,“深”是“选择之作用”。“小而深”实际上是说艺术形象是通过对具体的“代表”细致深入地描写来反映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本质,是代表性和特征性的统一。虽然这种特征性有流于类型化的缺点,但它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初步统一。
(三)人物安排。吕成之将小说按叙事繁简分为单独小说和复杂小说,认为复杂小说的作者独立描写许多主人公,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写某一个主人公,主人公只起到了串联叙事的线索作用。而单独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其余的人物都是陪衬人物,陪衬人物有关主人公就描写,无关主人公者就不描写。描写陪衬人物的目的在于刻画唯一的主人公,“故单独小说者,以描写一人一事为主义。”[4]417注意到了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之间的关系,主人公和其他人物间的主次关系。以主人公为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为陪衬,有详有略、主次分明的向心型人物安排,有利于创造典型。
(四)主客合一。小说倾向性的最佳状态是主客观合一,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吕成之认为,文学有主观、客观之分,主观主抒情,客观主叙事,二者各有优长,各有偏向。小说和戏剧因体例特殊,能取得主客观合一的效果,是最精妙的文学样式。内容上,“能将主观一方面之理想,亦化之为事实”[4]451。小说与戏剧的主人公,代表着作者的理想,是主观的。其余人物是次要人物,代表着主人公周围的事物,是客观的。功能上,“诮其客观形式,而主张客观其精神”[4]451。小说戏剧提供了自然繁复的事实,作者情感是组织事物的天然线索,使表达内容集中、有条理。作者通过这种主客观结合的方式,以事实发表理想,自然流露倾向。他指出,大发议论、书中插话、场外按语等表达作者倾向的方式,“均非所宜”[4]451。吕成之从西方思维方式——主观、客观两分再结合的角度认识典型的倾向性,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难能可贵的是,管达如首次系统地提到了小说作者应具备的一些条件:第一,道德心充足;第二,智识完备;第三,阅历广博;第四,表达文学。吕成之同样认为,小说作者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理想高尚;第二,材料丰富;第三,组织精密。综合两人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归纳出综合派对创作主体的要求有五点:一是理想高尚;二是智识完备;三是阅历广博;四是组织精密;五是表达文学。综合派提出创作主体这一维度,典型理论的探讨就有了客观事物、文学典型、创作主体三个维度,推动了典型理论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综合派的典型理论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典型的生成过程,分析揭示了细节传神的根本原因,触摸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重要内涵,代表了五四之前典型理论的最高水平。
四、结语
整体来看,清末民初的典型理论经过三个阶段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富有学理的成就:典型理论的基本前提——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经历了文学与政治、生活的矛盾性认识,文学与生活二者互为因果,文学创造了“第二人间”“第二社会”。典型形象由孤零的代表性、理想性、特殊性,到真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再到代表性和特征性的统一,触碰到了典型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内涵。典型化手法由简到详、由粗到精得到持续更新和发展;细节描写沿着语言繁简与事物描摹的详略、细节描写的作用、细节传神的根本原因等环节持续深入;倾向性由破坏小说美感到中国传统小说作者的“零度叙事”再到西式思维的主客观合一,内涵不断丰富;典型作用含纳社会作用、审美作用,与时俱进,日益完善;综合派提出的典型创造主体维度更是开拓了典型理论探讨的新领域,推动了典型理论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清末民初的典型理论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典型形象的具体内涵认识还比较简单,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很少论及,只是浅层次触碰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统一的内涵,典型理论仍纠缠杂糅在小说理论这一母体之中,还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但在西学东渐的特殊时期,理论家为建构早期中国典型理论所做的积极探索,为发展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一,处理好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是典型理论存在的必要环境。政治压倒文学,会损害文学审美性;一味追求审美,会削弱文学的现实关怀。只有良性互动的内外关系才是典型理论生根发芽的适宜土壤,新小说派和小说林派的理论差异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正确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典型理论形成的基本前提。理论家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决定了典型理论的存在样貌和发展方向。随着新小说派到小说林派再到综合派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认识不断深入,他们的典型理论不断得到深化。其三,尊重典型的发展规律,勇于探索。典型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要尊重文学自身的性质,合乎文学发展规律;一方面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开辟新的理论域。综合派理论家吕成之和管达如就开辟了创造主体的新维度。其四,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理论的发展要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借鉴古今、中西优秀的文化成果。徐念慈借鉴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传统小说的中国化尝试,黄人总结中国优秀传统小说写人艺术的本土化探索都是优秀的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讲道:“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11]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再次讲道:“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12]可见,文艺需要典型,时代需要典型,人民需要典型,典型理论的研究,切合时代的脉搏和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力作、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因此,我们考察清末民初的典型理论,学习、借鉴三个阶段理论家的探索经验,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有益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有益于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典型,彰显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典型理论认为: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是典型理论关注的主要内容;刻画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的人物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其基本内涵;典型化手法即概括、虚构、细节描写、倾向性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美学的历史的和谐统一是其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