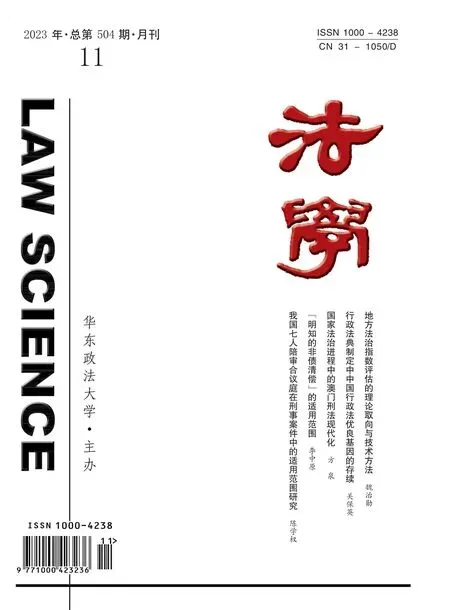“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之检讨
2023-03-10李中原
●李中原
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将“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列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除外(或排除)事由之一。该项主要参考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1〕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14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0 条第3 项。理论上通称为“明知的非债清偿”。〔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工作实施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第4 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04 页;王轶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687 页。由于我国法首次对此作出规定,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均不充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该项除外规则的适用范围问题。因为仅就该项规定的字面含义而言,裁判者必然会面临解释和适用上的以下困局:既然给付人在客观上无债务且在主观上对此明知,那么其所实施的给付行为还能算是“债务清偿”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明知的非债清偿”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意味着给付人在明知无债务的情况下实施的给付行为都属于《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之“明知的非债清偿”?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对该项规则的理论背景和规范构造展开全面的考察。
一、“明知的非债清偿”的理论渊源和现代模式
欲理解“明知的非债清偿”,须从“非债清偿”入手。“非债清偿”(solutio indebiti)作为不当得利制度的重要类型,源自罗马法上的“返还诉”(condictio)。优士丁尼立法将古典罗马法上以请求返还财产为内容的各种“返还诉”(condictio)固定为一些具体的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类。〔3〕意大利学者斯奇巴尼教授关于罗马法上返还诉具体类型的介绍,可参见《罗马法民法大全翻译系列·学说汇纂(第十二卷):请求返还之诉》,翟远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序言,第14-21 页。另请参见[德] 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520 页以下;[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98-399 页。
其一,“非债返还诉”(condictio indebiti,D.12,6)。这是返还诉中最主要的一种类型,即在债务自始不存在或者自始无法实现的场合,行为人由于错误地认为自己负有债务或者缺乏抗辩权而实施债务清偿,则该行为人可以主张返还。其主要特点有三。首先,只适用于以清偿债务为目的(solvendi causa,causa solutionis)的给付行为。其次,要求在行为人实施给付时债务已不存在(包括不成立、无效、消灭以及超额给付的情况)或者因遭到永久性抗辩而无法通过诉讼实现。最后,要求行为人的给付乃基于善意或者可原谅的错误。就此而言,“非债返还诉”也可译作“错债返还诉”。〔4〕例如,黄风教授就坚持将“condictio indebiti”译作“错债索回之诉”。同上注,彼德罗·彭梵得书,第399 页;[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1 页;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8 页。但如果给付人明知没有给付义务则不得提起此类返还诉(D.12,6,1 和D.12,6,50),此即“明知的非债清偿”规则的历史起点。
其二,“给付目的不达返还诉”(condictio causa data cuasa non secuta,D.12,4)。这是返还诉中的另一重要类型,区别于非债返还诉,该类型的适用不限于债务清偿领域的返还诉求(比如一方在给付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对待给付,则可据此诉权主张返还),还可以适用于非债务清偿性质的给付行为(比如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给付嫁资,如果婚姻未达成,则给付人可据此诉权向受领人主张返还)。
其三,“无因返还诉”(condictio sine causa,D.12,7)。该类型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与非债返还诉、给付目的不达返还诉均存在竞合。但其最具特色的一种亚类型则是“原因嗣后消灭返还诉”(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D.12,7,2),是指债因在给付时存在但后来消灭了。例如,染坊主因丢失了客人交由漂洗的衣服而向客人赔偿,但后来这些衣服又被客人找到了,则赔偿原因就此消灭,染坊主可据此诉权主张返还。
其四,“卑鄙或不正当原因返还诉”(condicti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D.12,5)。该类型旨在解决基于秽行(即卑鄙或不正当原因)而实施之给付的返还问题,此处的秽行相当于近现代民法上违背公序良俗或者违法的行为,既可以存在于当事人双方,也可以仅存在于其中任何一方。
以上述罗马法上的返还诉形式为基础,近现代民法形成了有关“非债清偿”的三种立法和法教义模式。按照适用范围由小到大的顺序,这三种模式分别是德国模式、法国模式和意大利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下,“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德国民法最为忠实地承袭了优帝立法的类型化体系,将上述四类返还诉分别发展为德国民法上“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四种形态:将非债返还诉的内容直接发展为“非债清偿型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第1 款第1 句第一种可能和第813 条第1 款第1 句);将给付目的不达返还诉限制适用于非债务清偿领域,从而形成了“给付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第1 款第2句第二种可能);将原因嗣后消灭返还诉的适用扩展至合同在债务人清偿后被废止的领域,从而发展为“原因嗣后消灭型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第1 款第2 句第一种可能),债务人据此可主张返还;将卑鄙或不正当原因返还诉发展为“不法原因给付型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5〕参见[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8-531 页;[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 页以下。因此,在德国模式下,“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法上的非债返还诉,也可称为“错债清偿”。相反,“明知的非债清偿”则被作为排除返还诉的法定事由之一(《德国民法典》第814 条)而成为与“非债清偿”相对立的范畴。除了要求给付人在给付时明知没有给付义务之外,〔6〕同上注,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38 页。“明知的非债清偿”在适用范围上尚有如下限制。其一,只适用于以清偿债务为目的(solvendi causa)的给付行为。因其他目的(ob rem)的给付行为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分别归属给付目的不达、明知的给付目的不达(《德国民法典》第815 条)或者不法原因给付的规制范畴。其二,只适用于“原因自始不存在”的情形,包括在行为人实施给付时债务已不存在或者已存在永久性抗辩。根据德国法学界的主流理论,“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排除规则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适用于原因嗣后消灭型不当得利,因此,如果行为人明知合同可撤销、可解除仍然履行合同,在德国法上不构成“明知的非债清偿”。〔7〕[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29 页;同上注,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38 页。但作为例外,在合同因欺诈或胁迫而可撤销的场合(《德国民法典》第123 条),依《德国民法典》第853 条的规定,通过欺诈或胁迫这样的不法行为(或侵权行为)取得对受害人的债权,受害人自始享有永久性抗辩权,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受害人的清偿行为构成“非债清偿型”(而非“原因嗣后消灭型”)不当得利;如果受害人明知存在该抗辩权仍为清偿亦得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14 条“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排除规则。〔8〕同上注,汉斯·约瑟夫·威灵书,第25-26 页。相关理论和规则间的龃龉由此显现。继受德国法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主流理论则勉强将“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排除效力扩张至所有的可撤销合同领域。〔9〕参见[日]我妻荣:《民法讲义·债权各论》(下卷一),冷罗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8 页;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3 页;黄茂荣:《债法通则之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3 页。
在法国民法上,不当得利法被划分为“非债清偿”[paiement de l’indu,或译“不当给付”,《法国民法典》(2016 年修订)第1302 条]和“狭义的不当得利”[enrichissement injustifié,《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第1303 条]两个部分,后者乃作为前者的补充。由于法国民法的奠基人朴蒂埃(Pothier)仅沿袭了罗马法返还诉的一种形式,即优帝《法学阶梯》中的“非债返还诉”(I.3,27,6),〔10〕See M. Pothier, Treatise o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or Contracts, Volume I, Translated by William David Evans, Robert H.Small, 1826, p. 61[113].因此,深受其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继受罗马法返还诉的其他形式。相对于罗马法上的非债返还诉,法国民法上的“非债清偿”同样只适用于以清偿债务为目的的给付行为。〔11〕《法国民法典》(2016 年修订)第1302 条(2016 年修订前第1235 条)规定,非债清偿“须以债务为前提”。法国相关判例和学说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8 页,第1376 条之判例[1];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9 页。其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国民法上的“非债清偿”既包括实施给付时债务已不存在或者无法实现的情形,也包括债因嗣后消灭的情形。〔12〕同上注,罗结珍译书,第1068-1069 页(第1376 条之判例[3B]);同上注,张民安书,第440 页;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84 页。须说明的是,作为“非债清偿”之典型情形,合同无效(包括可撤销)后的返还在法国既往的判例中被认为不属于非债清偿,而是属于专门的无效规则范畴,〔13〕同上注,罗结珍译书,第1069 页,第1376 条之判例[3C];[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1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1:101 条之注释18。主要区别在于适用无效规则的时效期间是5 年(2016 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304 条),非债清偿则适用30 年一般时效(2008 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2262 条)。但在2008 年诉讼时效制度改革后,一般时效也缩短为5 年;根据现行《法国民法典》(2016 年修订)的规定,无效返还(第1178 条第3 款)和非债清偿返还(第1302-3 条第1 款)都适用第1352 条到第1352-9 条之统一的返还规则,返还请求的消灭时效也被统一为5 年(第2224 条)。由此可见,两者在返还和时效规则上已完全统一。因此,目前来看,合同无效(包括可撤销)后的返还同样属于非债清偿范畴。其二,“非债清偿”不限于错误给付,即使给付人明知没有给付义务,甚至给付原因非法,也可依“非债清偿”主张返还。〔14〕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以下;同上注,罗结珍译书,第1069页,第1376 条之判例[4]、[5];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41 页。因此,在法国模式下,“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涵盖了债务清偿领域的各种给付型不当得利,但“给付目的不达型”或者“不法原因给付型”不当得利如果发生于非债务清偿领域,则不属于“非债清偿”,而是由“狭义的不当得利”调整。相应地,在法国模式下,“明知的非债清偿”也呈现出不同于德国模式的三个特点。(1)“明知的非债清偿”不再独立于“非债清偿”之外,而是被归入后者。(2)“明知的非债清偿”同样适用于原因嗣后消灭的情形,因此,如果行为人明知合同可撤销、可解除仍然履行合同,亦构成“明知的非债清偿”。(3)“明知的非债清偿”并非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定事由,这是法国模式与德国模式最大的区别。虽然法国的判例和学说也曾将“明知的非债清偿”作为排除返还的理由,但该观点在当代法国民法上已经被抛弃(详见下文)。
在意大利民法上,不当得利法亦被划分为“非债支付”(pagamento d’indebito,《意大利民法典》第2033-2040 条)和“无因得利”(arricchimento senza causa,《意大利民法典》第2041-2042 条)两个部分,前者中的“支付”泛指包括金钱在内的任何财产给予,〔15〕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V. La Responsabilità, Giuffrè, 1994, p. 794.后者同样是作为前者的补充,在学说上也被称为“不当得利”(ingiustificato arricchimento)。〔16〕同上注,第809-810 页。意大利法上“非债支付”的范围更为宽泛,除了以清偿债务为目的的给付之外,非清偿性质的给付甚至是非给付性质的利益转移也都被纳入“非债支付”范围。比如,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2040 条的规定,(合法或非法的)占有人对占有物进行维修、改良之费用的返还请求权也属于“非债支付”范畴;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189 条第2 款的规定,债务人向表见债权人(即真正债权人的表见代理人)清偿后,真正的债权人得依“非债支付”(第2033 条)向表见债权人主张返还得利,理由是真正债权人乃依法代位行使债务人之“非债返还请求权”(ripetizione dell’indebito)。〔17〕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V. La Responsabilità, Giuffrè, 1994, p. 798.此外,意大利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还将因失误或者技术操纵所导致的资金的电子划转也归入“非债支付”范畴。〔18〕同上注,第794 页。这些发生在返还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转移并不完全符合“给付”的意思表示属性。根据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不当得利法中的“给付”概念(比如“给付型不当得利”),泛指有意识、有目的地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19〕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3 页;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0、119、135 页。显然,上述利益转移在德国法上大多归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范畴。与德国法相比,意大利法上的“非债支付”涵盖所有“给付型不当得利”,同时涉及某些“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情形(既有“费用返还型”,也有“权益侵害型”),〔20〕与意大利的宽泛做法类似的还有荷兰,《荷兰民法典》第6:203 条之“非债给付”(Onverschuldigde betaling)的范围也不以上述“给付意图”为限。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5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1:101 条之注释25。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中对不当得利法中“给付”的范围也存在从宽认定的特点,例如将“侵占他人土地加工开垦”也纳入其中(同上注,王泽鉴书,第134 页)。显然,侵占人的加工开垦行为乃基于自己的利益,并无增加他人财产的“意思”。这一从宽认定与意大利、荷兰的做法类似。其与《意大利民法典》上作为兜底性补充条款的“无因得利”(第2041-2042 条)之间的区分亦非严格。比如与前述占有人的维修、改良费用返还请求权属于“非债支付”不同,如果占有人系在他人土地上建造工作物,依据《意大利民法典》第936 条第2 款或第937 条第3 款所发生的建造材料费等费用补偿请求权在主流学说上则被归于“无因得利”范畴。〔21〕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V. La Responsabilità, Giuffrè, 1994, p. 810.显然,建造工作物与维修、改良均非以“给付”意思为限,而且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也有意见主张将《意大利民法典》第1189 条第2 款的返还请求归于“无因得利”范畴。〔22〕Pietro Trimarchi, Istituzione di Diritto Privato, Giuffrè, 2014, p. 347.因此,意大利民法上有关“非债支付”和“无因得利”的区分是一个相对粗糙的立法设计。在此模式下,“明知的非债清偿”可以被进一步扩张为“明知的非债给付”,适用于受损人明知无义务的任何给付行为[包括基于“清偿(或偿债)目的”和非基于“清偿(或偿债)目的”];之所以不扩张至“非给付”领域,其原因在于受损人明知无义务仍主动向对方转移利益的行为通常限于“给付”,非给付型的利益转移不宜纳入“明知”范畴。除此之外,意大利模式的其他特点与法国模式类似。
二、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在三种模式下的解释效果
根据上文,“明知的非债清偿”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哪种解释模式更适合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需要逐一进行考察。
(一)德国模式的解释效果
此种模式是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在立法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其与该项的文义表述也最为贴近。但是,采用该解释模式,《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在司法适用中将遭遇巨大的证明障碍。假设原告向被告提起不当得利的返还诉讼,原告举证证明了其向被告给付利益的事实,并证明了自己对被告不负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给付义务,如果被告欲依《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进行抗辩(即排除原告的返还诉求),依据证明责任的基本规则,被告须对该项的构成条件负主要证明责任:首先须证明原告对于无给付义务主观上构成“明知”,其次须证明原告的利益给付构成“债务清偿”行为。前者在举证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被告提供签约过程的对话记录或者往来文件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属于通谋虚假(合同无效)或者原告知道合同尚未达成。但须指出的是,此处的“明知”应当排除任何认识上的“错误”。在合同尚未达成的场合,如果原告因为知道合同成立或生效所欠缺的手续(比如审批)正在办理中或者欠缺的要件(比如监护人的认可)事后可以补办而提前履行了给付,但该手续或要件最终没有达成,此种情况应认定为原告系“误认”自己(即将)负有债务,不宜以“明知”无给付义务加以认定。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证明原告给付利益的行为构成“债务清偿”则须先解释清楚究竟何为“债务清偿”。
民法上的“债务清偿”行为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基于清偿(或偿债)目的进行给付,此之谓“真正的债务清偿”;其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债务人误认为存在而基于清偿目的进行给付,此之谓“不真正的债务清偿”,也就是前文所述之“错债清偿”。〔23〕正因为如此,在不少民法典中,债的“清偿”(或“履行”)章节往往设有“错债清偿”的个别规定(2016 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235 条第1 款、巴西新《民法典》第309 条),甚至有关“错债清偿”的规定被完全置于债的“清偿”(或“履行”)章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431 条以下、阿根廷共和国最新《民法典》第784 条以下)。总之,这两种情况都要求给付人在主观上基于清偿目的。有争议的是,如果债务人A 错把给B 的投资款打到了债权人C 的账户上,基于A 对C 确实负有债务,尽管A 的给付并非基于清偿目的,这同样会产生“债务清偿”的效果(债的消灭),但须澄清的是,该效果的产生并非基于债法上清偿之法理,而是A 与C 之间原有的债务与错误打款导致的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之间的抵销。基于此,该情况中A 非基于清偿目的的给付并不属于“债务清偿”范畴。
因此,在诉讼中要证明原告的给付构成“债务清偿”,实际上就是要证明原告的给付行为乃基于“清偿目的”,但在原告明知自己没有给付义务的场合要证明此点,由于违背诉讼认知的常理基础(依常理此种场合下的给付应有清偿以外的其他目的),该证明一般不可能成功。作为佐证,在德国法的理论和实践中,真正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14 条“明知的非债清偿”的实例极度缺乏,法教义学上列举的众多案型恰恰都是排除该条适用的情况。〔24〕参见[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 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38 页。但是有两种情况例外:其一,原告系“自愿替他人还债”;其二,原告系清偿赌债。前者系原告明知自己无给付义务而为他人清偿债务。对于后者,需要说明的是,赌债清偿者虽然具有“清偿目的”,但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下,排除其返还请求权并非基于“明知的非债清偿”,而是基于以下理由:赌博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构成犯罪的,赌资当依法收缴或者没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 条、《刑法》第64 条),并无返还必要;此外的赌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在国内学界尚存争议,清偿此类赌债在理论上要么被归于“履行自然债务”,要么被归于“不法原因给付”,两者均排除返还。〔25〕参见覃远春:《论“赌债”分离可能性及其司法处理——自然债之于传统问题民法新视角的贡献》,载《河北法学》2011 年第9 期,第96 页;许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3 期,第164-165 页;杨德群:《论赌债的性质》,载《特区经济》2020 年第9 期,第133 页 。因此,清偿赌债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规定之“明知的非债清偿”范畴。
简言之,如果采用德国模式作为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解释基础,那么符合该项条件的只有一种情况,即“自愿替他人还债”。
(二)法国模式的解释效果
较之于德国模式,法国模式将“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扩及原因嗣后消灭的情形。如果采用此种解释模式,则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适用范围将扩张至一种重要的情形,即债务人明知合同可撤销或者可解除仍进行债务清偿,之后合同被依法撤销或者解除。但对此种情形可否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须区分两种情况予以分析。
首先,如果撤销权或者解除权属于债务人本人,则理论上有观点认为,此时债务人坚持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被视为抛弃撤销权或者解除权(或是对可撤销或者可解除之行为的承认),〔26〕参见黄茂荣:《债法通则之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3 页;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3 页。须说明的是,黄、王二位先生的观点仅针对合同撤销权,但如该推定之法理成立,则在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权领域亦可准用。因而与作为“明知的非债清偿”排除返还的法理基础“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相吻合。〔27〕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38 页;同上注,王泽鉴书,第112 页。对于“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法理基础,德国法学界在此主流理论(“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学说(参见[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26 页),但尚不足以替代前者。但此种“弃权”推定不完全符合交易常态和通常理性人标准,依此标准,明知有撤销权或者解除权的债务人坚持履约通常具有其他在客观上可识别或者可证明的原因或目的,比如受到了胁迫,为了获得合同外的利益回报,以及为了达到其他合同外的目的。在这些场合,债务人要么无弃权之意思,比如受胁迫场合;要么顶多是附条件弃权,比如在后两种场合下,一旦合同外的利益或者目的落空,则债务人仍保留撤销权或者解除权。因此,这些情况不能作为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事由。
其次,如果撤销权或者解除权属于合同相对人,则债务人在相对人撤销或者解除合同之前履行给付通常是基于对相对人实施对待给付的期待,与“弃权”无关;即使债务人乃基于欺诈、胁迫等不法目的实施给付,那么该给付排除返还的理由也是债务人的“给付目的不法”(或不法原因给付),而非“明知的非债清偿”。
综上,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债务人明知合同可撤销或者可解除仍进行债务清偿尚不足以成为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事由。因此,采用法国模式作为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解释基础较之于德国模式并无实益。
(三)意大利模式的解释效果
如果采用意大利的解释模式,则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适用范围将扩张或类推至“明知的非债给付”,即较之于法国模式,行为人明知无给付义务且非基于清偿目的的给付行为也被纳入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生活中的送礼行为。送礼的法律效力较为复杂,在发生讼争时,给付人多会主张送礼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在最终目的没有达到时能否主张返还须根据社会习惯区别对待:如果数额较小或者依善良风俗不宜返还的,通常推定为赠与(下文称之为“习惯上的赠与行为”),不得主张返还;〔28〕以恋爱为目的的财物给付,对“数额较小”的认定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恋爱期间的财物给付数额累计达到数万元的,也可按照赠与处理。参见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2021)晋0781 民初206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11 民终504 号民事判决书。但如果数额较大或者给付时有明确的目的或者存在其他依社会习惯应予返还的情况,比如男方向女方给付彩礼是为了缔结婚姻,〔29〕依现行法,此类送礼行为属于“附义务的赠与”(《民法典》第661 条)。如果所附义务没有得到履行,则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 条第1 款第3 项)。则一旦目的没有达到即可构成上述之“给付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给付人可以主张返还。此外,下列传统事由亦属行为人明知无给付义务且非基于清偿目的的给付行为,但均不足以排除返还。
其一,不法原因给付。在意大利模式下,不法原因给付也属于非债给付中排除返还的法定理由(《意大利民法典》第2035 条)。不法原因给付即基于不法原因(或不法目的)的给付,在近代民法传统上乃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项基本理由。其要求给付人具有不法目的(比如行贿),如果不法性仅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比如胁迫)则不得排除返还。〔30〕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035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0 条第4 款。但是,单纯以给付人的目的不法为由排除不当得利返还在当代德国法学上受到了重大质疑,被认为“带来的困难是最大的”,甚至被认为是“失败的”。〔31〕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39 页。比如,根据德国的判例和学说,出租房屋用作妓院或赌场的,违法出租人仍然可以主张返还出租房。〔32〕同上注,第542 页。对此,王泽鉴先生认为在租期内不得主张返还。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3 页。又如,在高利贷场合,违法放贷人的贷款本金甚至是适当范围内的利息都是可以主张返还的。〔33〕根据德国的通说,高利贷合同无效,依《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句,违法放贷人在贷款期限内不得主张返还贷款,在贷期届满后仍得主张返还贷款本金,但不得主张任何利息;另一种学说(为梅迪库斯所赞同)则主张符合市场价格的利息(或通常水准的利息)仍应得到支持。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40、544-545 页;[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45 页。我国法院在高利贷问题上的处理方案与此类似。〔3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第26 条。再如,打黑工虽然也属于不法原因给付,但考虑到打工者的弱势地位,对于其已经提供的服务或工作不给予任何补偿的做法在德国的理论和实践上也受到了质疑。〔35〕德国的判例认为此处应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句以排除补偿不公平。参见[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 页;[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08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6:103 条之评论。在我国类似的情况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违法承包或者转承包建设工程是无效的,但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93 条,违法施工人仍然可以获得工程价款的补偿。实践中也有法院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57 条有关无效返还请求权的规定给予施工人补偿。〔36〕参见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2021)浙0114 民初4915 号民事判决书。此外,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7 条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均应当予以返还。据此,欺诈方隐瞒了产品的重大缺陷实施给付,或者合同一方明知相对人存在重大误解,但为了促成相对人犯错或者仅仅是为了趁机渔利仍然实施给付,对这些具有欺诈性的给付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往往允许在合同撤销后予以返还。〔37〕参见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22)鲁0612 民初2868 号民事判决书。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7 年台上字第1092 号判例认为,为达到欺诈目的所为之给付系属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但王泽鉴先生认为,欺诈非无效,是否纳入不法原因存疑。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4-125 页。因此,不法原因给付并非都能够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有“特定场合下的不法原因给付”才可以排除返还,比如毒品或军火交易、行贿、嫖娼、销售犯罪器材、借钱给他人购买毒品等,但目前在比较法上该范围并不确定,也难以统一。〔3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40 页;[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07 页以下,《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6:103 条之评论和注释。
其二,明知的给付目的不达。德国法上所谓“明知的给付目的不达”也在“明知的非债给付”涵摄范围之内。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15 条之规定,前者也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排除事由。但是,该立法例即使在德国法系也未得到普及,瑞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未予采纳。以男方明知女方拒婚仍然给付彩礼为例,该事实就足以确定给付人欲达到之结婚目的不能实现吗?事实上女方在接受彩礼后完全可能回心转意;就算女方已与第三人有婚约或已结婚,也不排除其解除婚约或者离婚后接受该案男方之可能。此外,即使此处的“给付目的不达”是指“可能不达”,据此排除返还也是不合理的,因为给付人明知给付的目的可能或很可能落空仍为给付,其期待发生“反转”或者“奇迹”的心理最多算作“侥幸”,并非恶意,在与受领方无理由得利的权衡中仍然更值得法律的保护。纵使发生男方明知女方死亡仍然给付彩礼的极端事例,从通常理性人的标准出发,此类给付人也往往具有婚姻以外的其他原因或目的,是否返还须针对不同的原因或者目的分别处理,赠与虽然也是可能的目的,但绝非此类给付之常态,不宜作为推定标准。因此,“明知的给付目的不达”尚不足以成为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事由。
其三,明知合同无效场合下的给付。如果合同一方明知合同无效但为了获得合同外的利益而向对方给付(但最终该利益并未实现),这也构成“给付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而在明知合同无效的场合下给付方由于受到胁迫而给付,则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于不法并非来自给付方,给付方仍然可以主张返还。
相反,在行为人明知无给付义务且非基于清偿目的的给付行为的范围内,可以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事由除了上述习惯上的赠与行为和特定场合下的不法原因给付外,还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强迫交易。即行为人明知对方反对仍为给付,对方有权拒绝却没有拒收的机会或条件且该给付的性质导致其无法原物返还,行为人据此要求补偿。比如,电信公司在用户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擅自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用户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受”了此类服务;又如,房主在旧房四周的外墙上均粉刷了“拆(迁)”字样,行为人却在房主外出度假期间自作主张对旧房进行修缮。在上述场合,用户和房主均不构成不当得利。强迫交易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对方(被给付方)的“反对”或“拒绝”应为明示或者采用习惯上足以为行为人(给付方)知晓和理解的形式。前者例如用户的明确拒绝,后者例如在旧房外墙上粉刷“拆(迁)”字样。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行为人系明知对方反对。需要说明的是,“强迫交易”(forced exchange)的概念出自英美法,旨在对抗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原本涵义较为宽泛,〔39〕See REST 3d RESTI § 2(4), § 10.但当代英美返还法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倾向于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行为人“明知本人未请求且不希望其介入”的场合,而对于此外的介入行为(大量系基于行为人的错误)则逐渐放松了对行为人返还(或补偿)请求的限制。〔40〕See Gareth Jones (ed.), Goff & Jones The Law of Restitution, 7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7, p. 71.这一趋势也与大陆法系在“给付型不当得利”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更为契合。
(2)对方须有权拒绝该给付。如果对方无权拒绝,则不构成强迫交易。这主要针对的是自愿替对方还债的行为(参见上文)以及具有客观正当性的无因管理行为(比如行为人系为对方履行扶养义务,或为对方尽公益上之义务)。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方(债务人或义务人)无权拒绝行为人给予的利益。
(3)对方须没有拒收的机会或条件。比如,电信公司、美容机构等服务方在客户不知晓的情况下擅自增加某种形式的服务,或者行为人在房主外出度假期间自作主张对旧房进行修缮,这属于客户或房主没有拒收的机会。如果在行为人实施给付时,对方在有机会拒绝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或者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错过了拒绝的机会,比如在电信公司擅自增加服务项目或者行为人自作主张对房主旧房进行修缮的示例中,如果有证据证明客户在发现该增加服务项目后或者房主在发现修缮行为后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向电信公司或者修缮行为人提出异议(或者进行制止),那么从其发现之日到其正式提出异议(或者进行制止)之日的期间内的增加服务项目或者修缮作业在法律上将被视为客户或者房主“默示接受”的交易(或合同)而非强迫交易,该客户或房主不得拒绝付费。这在英美法上也被称为“自由接受”(free acceptance)。〔41〕参见[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4-65 页。根据博克斯的观点,电信公司或者修缮行为人就增加服务或者修缮作业享有的付费请求权系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在我国的法教义学体系下,合同请求权说更具说服力。此外,在上述示例中,如果客户或者房主在发现后提出了异议但无法阻止电信公司或者修缮行为人一意孤行,则属于没有拒收的条件,同样应以强迫交易论。
(4)该给付的性质导致其无法适用或类推适用原物返还。如果行为人强行给付之标的是可以原物返还的财物或者类推原物返还的金钱(或者粮、油等可替代物),比如行为人不顾对方反对,乘对方不备将财物放入其家中或者将钱款直接汇入对方账户,那么即使符合以上三个条件,仍不得依强迫交易排除返还。〔42〕《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将此种不当取得的财物或者钱款归于“可转移之得利”(transferable enrichment)。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52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5:101 条。美国《返还法重述(第三版)》则将此种财物或者钱款称为可以“实际返还”(specific restitution, returnable)的利益。See REST 3d RESTI § 1, Comment e(1).因此,强迫交易通常表现为服务型给付:行为人强行提供服务,比如电信服务、美容服务或者修缮服务,然后向被服务者索要价值补偿。在这些场合,给付之标的体现为单纯的服务(比如电信服务)或者与被服务者的人身或财产不可分离的财产(比如美容服务中使用的护肤品,旧房修缮中使用的工件材料),其性质决定了无法原物返还,如果强迫被服务者给予经济补偿,不仅会严重侵犯被服务者的选择自由,而且会给被服务者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行为人强行提供的财物因消费或灾害等不可归责于受领人的原因而灭失,此时无法原物返还并非给付的性质所致,对此,受领人在美国法上仍可诉诸强迫交易而拒绝行为人的补偿请求,〔43〕See REST 3d RESTI § 2, Comment e.但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下则无此必要,我国《民法典》第986 条有关善意得利的返还限制规则即可应对。
其二,主观无价值的给付。这是指给付虽然在客观上有价值,但对受领人而言无价值,比如承租人对住房进行了装修,但房主计划在租期届满后将该住房改建为展厅,原装修须全部清除。此种情况下的排除返还可以解释为不符合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所规定不当得利的“得利”要件。不当得利之“得利”须接受主观价值评估乃当前德国和英美法学上的通说。〔44〕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56 页(注释②)、第257 页(注释①);[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0 页以下;REST 3d RESTI § 49, Comment d, Reporter’s Note d; Andrew Burrows, The Law of Re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4-47.这一学说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有学者一致认为,如果因添附所受利益与受益人的主观愿望不符,应当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受益人可以主张主观无利益的抗辩,免除返还或补偿责任;〔45〕参见梁慧星、陈华彬:《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545 页;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03 页,第396 条之说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观无价值或者主观贬值的观点也被有些法院用以驳回原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求。〔46〕参见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3 民初2907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 民初5373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1466 号民事判决书。
其三,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这是指在给付完成后,给付人自己违背诚信阻碍目的的成就,比如男方在给付女方彩礼后又与其他女子订婚或结婚。此种情况下的排除返还可以通过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反向推定规则予以解释。以彩礼案为例,对彩礼的给付依习惯可以推定在给付双方之间达成一项“附停止条件的协议”:如果婚姻无法缔结,则男方可以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此处的“(停止)条件”体现为“婚姻无法缔结”,相当于“给付(彩礼的)目的不成就”。据此,如果给付方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在上例中表现为男方背信导致先前允诺之婚姻无法缔结,则构成《民法典》第159 条后段之“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依该条后段之规定应当“视为条件不成就”,即在上例中体现为“视为婚姻已经缔结”。因此,协议不产生效力,给付方(男方)不得主张返还。
综上,在意大利模式下,“明知的非债给付”除了“自愿替他人还债”之外,还新增了上述五种可以排除返还的情况(或事由),除此以外,对“明知的非债给付”仍然可以主张返还。据此解释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不仅须将“债务清偿”扩张至或类推至所有“给付行为”,还须将该项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上述六种情况下,这与法条的文义存在距离。更重要的是,这些情况(或事由)在两大法系的传统上均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彼此之间相异性远大于共性。比如,不法给付在德国和意大利是排除返还的独立事由,〔47〕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035 条。在美国同样是排除返还的独立事由,在衡平法上也称为“污手”(unclean hands)原则。〔48〕See REST 3d RESTI § 63.强迫交易和主观无价值的给付在德国和意大利则属于“强迫得利”(Aufgedrängte Bereicherung,arricchimento imposto)范畴,〔49〕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55 页;Paolo Gallo, L’Arricchimento senza Causa (Artt. 2041-2042), Milano, 2003, pp. 109-159.在美国两者则是返还法上两项独立的范畴。〔50〕强迫交易规则参见REST 3d RESTI § 2(4), § 10. 主观无价值(subjective devaluation)理论参见REST 3d RESTI § 49,Reporter’s Note d.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在德国是排除返还的独立事由(《德国民法典》第815 条),我国台湾学界则采前文之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反向推定规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1 条)来解释该排除返还事由。〔51〕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99 页;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72 页。在英美,该事由则应归入“禁反言”(estoppel)或者“境况改变”(change of position)的抗辩范畴。据此,将这些异性远大于共性的情况(或事由)统一纳入“明知的非债给付”范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依意大利模式进行解释难度较大。
总体来看,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在三种模式下的解释效果均不理想,采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会陷入适用范围过窄的困境,采意大利模式则解释难度过大。
三、相关比较法趋势和国内法实践
从比较法上的状况来看,将“明知的非债清偿”排除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外乃民法法系的历史传统,即使在当代仍为众多法域所遵循。〔52〕除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外,还可参见《瑞士债务法》第63 条第1 款、《日本民法典》第705 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432 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09 条第4 项、巴西新《民法典》第877 条、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第1267 条和第1273 条、《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2299 条。转变发生在法国、意大利等法域。〔53〕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荷兰。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5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1:101 条之注释25。法国的主流判例和学说在1993 年之前也要求非债清偿必须基于给付者错误的认识才可以主张返还,而将明知的非债清偿推定为赠与以排除返还。但法国最高法院在1993 年转变了立场。根据法国的法教义学理论,非债清偿首先被划分为“客观非债清偿”(或绝对非债清偿)和“主观非债清偿”(或相对非债清偿)两类。“客观非债清偿”是指债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包括自始不存在和嗣后消灭),即给付方并无债务,受领方亦无债权。“主观非债清偿”则是指债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只是仅对受领方不存在或者仅对给付方不存在。其中,前者被称为“受领方的主观非债清偿”(或不完全相对非债清偿),即受领方并无债权,但给付方则负有债务,典型情况是债务人搞错了清偿对象;后者被称为“给付方的主观非债清偿”(或完全相对非债清偿),即给付方并不负有债务,但受领方则享有债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给付方清偿了他人的债务(或“自愿替他人还债”)。法国最高法院的转变发生在一起针对“客观非债清偿”的案件中。在该案中,法国最高法院确立了此后新的裁判方向:“客观非债清偿”必须返还,给付人无须证明其清偿是否基于错误认识。2016 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则更为彻底地实现了这一转向:明确将旧法第1377 条的主观错误要件限定于“清偿他人债务”领域(即“给付方的主观非债清偿”,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02-2 条),而对于“客观非债清偿”和“受领方的主观非债清偿”,无论给付人是基于错误还是明知,均须返还(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02-1 条)。〔54〕相关背景介绍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88-89 页;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40-441 页。意大利1865 年旧民法典直接移植了1804 年《法国民法典》第1235、1376、1377 条关于“非债清偿”的规定。1942 年颁布的现行《意大利民法典》关于“非债支付”的规定系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现行《意大利民法典》第2033、2036条和此后的主流学说则率先采用了与2016 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类似的方案,只是该方案的适用范围由“非债清偿”扩张至“非债支付”,而且非清偿(或非偿债)性质的“支付”集中在“客观非债”领域。据此,针对“客观非债支付”,即使支付方构成“明知”也适用返还请求权,“受领方的主观非债清偿”准用“客观非债支付”规则;针对“给付方的主观非债清偿”,如果给付方构成“明知”(即“自愿替他人还债”)则不得向受领方(即债权人)主张返还。〔55〕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V. La Responsabilità, Giuffrè, 1994, pp. 793-795, p. 803.
由上可见,在当代法国法和意大利法上,只有在“给付方的主观非债清偿”领域,也就是“替他人还债”领域,“明知的非债清偿”才可以排除返还。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排除的是“明知”的给付方针对受领方(即债权人)的返还请求权;至于给付方与真正的债务人之间的返还关系在法国和意大利则不属于“非债清偿”或“非债支付”的规制范畴,而归属于其“不当得利(或无因得利)”和“代位清偿”制度的调整范围,对此本文不予展开。
英美法系不存在“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概念,但“明知的非债清偿”排除返还的法理基础(“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则与英美返还法上作为传统抗辩理由之“禁反言”(estoppel)如出一辙。〔56〕民法法系的“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和英美法系的“禁反言”(estoppel)在目前国际商事统一法领域被统称为“禁止不一致的行为”(prohibition of inconsistent behavior)。See The Lex Mercatoria (Old and New) and the TransLex-Principles, I.1.2, http://www.trans-lex.org/principles,last visit on May 20, 202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8 条,中译本参见张玉卿:《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 年版,第93 页。但根据英国返还法和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皮特·博克斯(Peter Birks)和安德鲁·巴鲁斯(Andrew Burrows)的一致意见,“禁反言”在返还法领域尤其是在排除返还上的实际作用已经式微,法院现在已不大情愿让禁反言在这一场合发挥作用,禁反言在排除返还领域的传统地位已经被“境况改变”(change of position)的抗辩所取代。〔57〕参见[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69-270 页;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Unjust Enrichment, Oxford, 2012, p. 123.作为例证,美国《返还法重述(第三版)》也没有将“禁反言”列入“返还的抗辩理由”,取而代之的是“境况改变”。〔58〕See REST 3d RESTI, Part IV, Chapter 8 and § 65.而所谓“境况改变”则侧重于对得利人(或受领方)之主客观境况的考察,比如基于不可归责于得利人的原因,得利已经被转移、被消费或发生灭失,或者得利人基于对该得利的合理信赖而放弃了其他获益的机会。在这些情况下排除返还显然不是基于“给付方行为的自相矛盾”。
代表了当代欧洲民法学者集体智慧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契合了两大法系的共同趋势,即没有将“明知的非债清偿”或者“禁反言”列入不当得利的一般“抗辩”理由。〔59〕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84 页以下,《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6:101、7-6:102、7-6:103 条。
从我国《民法典》实施后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法院明确参引其第985 条第3 项作出裁判的案件并不多。排除错判〔60〕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22)新0109 民初4596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被告以原告的字号经营货运并发生事故,原告对客户进行赔偿系因对外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而非“明知的非债清偿”,因此法院依《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追偿请求是错误的。和判决不构成《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案件,〔61〕参见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6 民初259 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构成该第985 条第3 项“明知的非债清偿”的案件涉及两种类型:其一,“自愿替他人还债”,即第三人在自愿替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又向债权人主张返还;〔62〕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2 民终5495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川0191 民初3101 号民事判决书。其二,恋爱期间的自愿给付,即恋爱期间的财物赠与或日常消费支出。〔63〕参见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2021)晋0781 民初206 号民事判决书。对后一种案型是否需要返还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存在争议,主要取决于法院对公序良俗的判断。但在法院驳回返还诉求的案件中,以“明知的非债清偿”作为判决依据的很少,大多数判决认为此类给付是恋人之间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应按照赠与处理(即前文所谓的“习惯上的赠与行为”)。〔64〕参见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21)川1323 民初2161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1)鲁1082 民初5634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11 民终504 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此种案型在我国目前以及今后的审判实践中将会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规范基础:一是《民法典》第657 条关于赠与合同之规定;二是《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关于“明知的非债清偿”之规定。两者效果相同,相形之下,前者简捷而准确,后者则须借助漏洞补充(将《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适用范围扩张至或类推至非清偿性质的给付领域),以后者作为此类案件的裁判依据显得低效甚至多余。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其一,“明知的非债清偿”排除返还的无争议案型仅限于“自愿替他人还债”;其二,一般性地将“明知的非债清偿”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除外(或排除、抗辩)事由在当代并非先进方案。
四、“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方案
行文至此,对于文首提出的问题,恰当的回答是,给付人明知无债务(或无给付义务)而实施的给付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构成《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债务清偿”,而且该范围还取决于对“债务清偿”的解释。据此,如果对“债务清偿”采严格解释,则《民法典》第985条第3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自愿替他人还债”,自愿替他人清偿债务者不得向债权人(即给付的受领人)主张返还;而如果借鉴比较法上较为宽泛的模式,将“债务清偿”扩张至所有“给付行为”,则该适用范围还可以涵盖其他五种情况,即习惯上的赠与行为、主观无价值的给付、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特定场合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以及强迫交易。
基于我国现有的规范体系以及对司法适用效果的考量,对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的适用范围宜采严格解释,其他宽泛意义上的五种情况则应当尽可能纳入我国既有规范的解释与适用范围,无法纳入的则应当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根据前文的研究成果,习惯上的赠与行为、主观无价值的给付以及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可分别通过《民法典》第657 条赠与之适用范围的解释(将数额较小或者依善良风俗不宜返还的送礼行为归入赠与)、第985 条不当得利之得利要件的主观化解释(主观无价值不构成“得利”)以及第159条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反向推定规则的解释(恶意阻碍构成“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来达到排除返还的效果。
其次,鉴于特定场合下的不法原因给付和强迫交易与《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明知的非债清偿”在理论内涵上的差异,以及目前此两者在我国缺乏其他据以解释或类推的规范基础,为了确保在裁判适用上的明确和统一,同时参考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在《民法典》第985 条规定的三项情形之外将上述两种事由补充为不当得利的除外条款。
1.不法原因给付的两种规制方案。方案一:“给付人基于不法目的的给付若得以返还将违背公序良俗的,不得主张返还。”根据这一方案,基于不法目的的给付在诉讼中原则上仍然可主张返还;如果得利人欲排除返还,必须证明返还违背公序良俗。该方案为《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所采纳。〔65〕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七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07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6:103 条。方案二:“给付人基于不法目的的给付不得主张返还,但是根据给付双方的利益衡量需要返还以维持公平的除外。”根据该方案,如果给付人基于不法目的,原则上在诉讼中不得主张返还;给付人欲主张返还,必须证明基于给付双方的利益衡量需要返还以维持公平,也即不返还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目前德国、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之不法原因给付的实践操作情况基本可归入这一方案。〔66〕德国的情况已如上述。《意大利民法典》第2035 条基本为审判实践所遵循,准予返还之例外情况例如“出于友谊而借贷资助非法赌博案”(Cass. 20 June 1960, no. 1627),同上注,第1110 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7-6:103 条之注释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0 条第4 款之规定也基本为审判实践所遵循,个别例外例如“因受诈骗而行贿香港廉署案”(2007 年台上字第2362 号判决),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5 页。
上述两种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证明责任的负担,方案一将该负担归于得利人,方案二则将其归于给付人。〔67〕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证明责任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不仅包含诉讼法上围绕事实和证据的证明责任,还包括针对法律适用问题的法律论证义务。此处有关返还与否与公序良俗(或者公平)之关系的论证即属于后者。对不法原因给付的治理实乃公法与私法共同致力之领域,凡不法原因给付危害公共利益的,依公法适用收缴或者没收,〔68〕例如,《刑法》第64 条规定,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 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此外,根据以上两条规定,犯罪或者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追缴,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否则一律上缴国库。在我国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也充斥着有关没收、收缴等处罚措施的规定。对此无讨论私法上返还之必要,诸如毒品或军火交易、行贿犯罪的资金、销售犯罪器材等在我国均属于这一范畴。只有达不到公法上收缴或者没收之适用标准时,方须探讨私法调整的方式。而对于具有纯粹民事违法性质的给付(不法目的存在于给付人),私法上无论如何调整均难谓公允:积极干预(即强制得利人返还)实为纵容给付人的不法行为;消极干预(即排除给付人的返还请求)则会姑息不当得利甚至纵容得利人的不法行为。在此,法律选择的标准应当转向效率,在上述两种方案的效果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成本较低的方案胜出。就此而言,后者之消极干预方案省去了返还的经济耗费和可能的强制执行,实现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较低,应当成为私法干预的基础模式,除非给付人能够证明积极干预(即强制返还)的社会效果明显优于消极干预(即排除返还),比如前文述及之高利贷、打黑工以及违法承包工程。因此,方案二更为可取。
2.强迫交易规则建议拟定如下:“行为人明知对方反对仍为给付而对方有权拒绝却没有拒收的机会或者条件且该给付的性质导致其无法适用或者类推适用原物返还的,不得请求对方就给付的价值予以补偿。”
五、结语
由于“明知的非债清偿”在含义和适用范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功能上的局限性,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将其作为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事由在司法适用上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困难;同时,鉴于国内外的法制实践,该项规定也不符合当代的发展趋势。为此,当前必须在法教义学和司法解释层面妥善解决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3 项及其相关理论规则的适用问题。从长远来看,对该项规定之合理性的质疑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