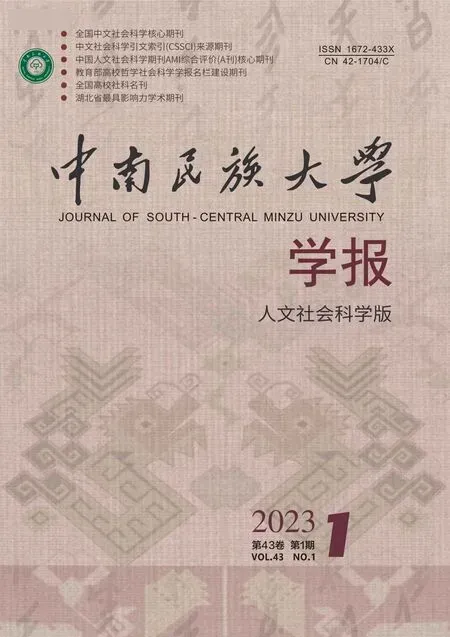写作的限度
——评吴仕民的长篇历史小说《佛印禅师》
2023-03-10叶立文孙秋月
叶立文 孙秋月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作家的主体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现代性思潮,都将表现人的主体性视为文艺创作的第一要义。尽管如此,作家对自我主体意志的极度弘扬,对非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度压制,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于是,反对启蒙神话、消泯主体性价值的文艺思潮随之兴起。具体到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领域,这一文艺理论问题更显突出:一方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对作家自我主体性的不断张扬,另一方面是九十年代以后世俗化文学语境对作家主体性价值的持续矮化。总之,围绕作家主体性问题的话语博弈,业已影响了当下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坛已有一些作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困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禀有人文精神的前提下为写作设限。吴仕民的《佛印禅师》以历史人物为原型,讲述了佛印一生云游逐道,为信仰九死而不悔的人生故事。作品在小说艺术上注重写作的限度,具有明确的形式意识。
一、写作限度
何谓写作的限度?单从字面意思来看,“限度”即为限制的程度。当在写作范畴内讨论限度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对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矛盾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因为所有写作层面的形式试验,几乎都是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而存在。作者意图不难理解,它反映的是作家对自我主体性的表达。为了在作品中宣示自我,作家会借助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在各种叙述策略中去表达自我意识,惟有如此,方能凸显作家的主体性价值。与之相比,文本意图却更显复杂,它独立于作者意图之外,往往是作家无法完全掌控的。小说情节的叙事逻辑和语言的话语权力,以及深存于文本结构的形式力量,皆有可能制造出种种不同于作者意图的文本意图。两者有时会和谐统一,有时则相互对抗。换言之,在创作过程中,文本意图不仅会经常偏离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还会与作者意图之间构成一种艺术张力。因此,一个深知小说文体内在规律的作家,定会洞察到写作其实就是一门遵守纪律的艺术——无论作家具有怎样的艺术想象力,都不应天马行空的“我手写我口”,而是以谨守写作限度的方式去展开叙述,否则就会让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沦为作家主体意志的“传声筒”。就此而言,优秀的作家虽然会忠于自己的表达意图,但在创作实践中,出于对情节本身、常识逻辑和语法规则等因素的尊重,他会作出适当的让步,即不以作者意图去遮蔽文本意图,并尽可能地远离叙事霸权,此即为写作的限度。
如果以此来观照《佛印禅师》这部作品,当可见出作者吴仕民在小说艺术上遵守写作限度的纪律意识。作者尊重人物成长和情节发展自身的逻辑,不仅能够平衡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的矛盾关系,而且也保证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为阐明这一问题,兹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知识叙写等方面展开讨论。
二、叙事结构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佛印禅师》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体量巨大,因此选择何种叙事结构来展开故事叙述就很能考验作者的功力。历史小说是一种具有相当写作难度的艺术形式,因为它直接关涉到复杂深广的历史知识。在写作历史小说时,作者既要贯彻自己的历史观,同时又要注意庞杂的历史知识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很多历史小说作者往往具有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等先验的历史观念,为了表现这样的历史观,作者会在小说中大篇幅地使用全知视角写作,明显具有为历史作传的史诗意识,笔触阔大处,动辄论及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继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的艺术效果。在这种创作理念的影响下,历史小说的结构也常为网状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纵横交错、经纬交织,看上去有气吞山河之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往往也十分突出。比如历史观念的生硬植入问题:有时候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会肆意篡改小说中人物的生命逻辑和故事的情节逻辑,这显然是对作者意图盲目推崇的结果,而叙事的霸权也在所难免。因此,这类历史小说不管看起来多么玄奥堂皇,都难免有故弄玄虚的弊端,毕竟若以先验的历史观为表现对象,小说中的人物就会成为网状叙事中的诠释工具,其结果只能证明作者文体意识的匮乏。
相比之下,《佛印禅师》并没有选择网状叙事结构这一历史小说的“形式惯例”,而是采用了一种成长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它以主人公佛印禅师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为主线,在保证为主人公立传的前提下,谨慎而节制地叙写了历史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似乎无意于用人物命运来表现某种先验的历史观,他只在意如何讲述主人公的生命故事。所以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之中,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佛印为了自我信仰九死而不悔的逐道之旅。佛印为了信仰不惜抛弃各种世俗欲念,勤于修习,广结善缘,也不断与遭遇的人性之恶展开搏斗,终成一代高僧大德。可以说,佛印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正因这种知行合一,佛印在其逐道的过程中,外在的肉身磨难和内在的坚定信念就具备了特殊的价值。小说的成长故事由是具备了内外两个层面,外在的是云游逐道之路,内在的则是精神升华之旅。“成长”这个看似单一的叙事线条便呈现出内外双重性,主人公外在经历影响内在发展,内在发展又推动外在经历的变化,外在和内在两条线索交相缠绕,虚实相生,从而立体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这种线性叙事结构的立体化呈现,不只表现在内外成长的双重性上,还表现在小说局部对整体线性结构律令的偏离上。小说并没有按照一条时空秩序井然、因果关系严密的理想的直线来发展,在文本内部恰恰有许多蜿蜒、游移乃至回环的部分。首先,扰乱时空秩序的叙写在小说中并不少见。比如,佛印在禅定之时总会凭借意念遨游,时时感觉不到自己肉身的存在,乃至“忘却了自己身处何处,忘却了日月晨昏,忘却了春夏秋冬”[1]66。时空在此时仅随佛印的意念游动,便成为一种纯意念性的展示,呈现出不完全遵从原秩序的复杂样貌。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偈语,同样具有扰乱时空秩序的效果。偈语本身是一种具有预言性质的语言,但它语言的象征性又决定了这种预言的指向是不明确的,这就使得偈语会不断延宕到最终谜底打开之时,让时空形成一种回环勾连的效果。比如,小说中最突出的便是日用禅师在佛印初次外出游历时送他的一则偈语——“四九可就,六七则成”[1]36。其后佛印经历诸多世事,前后三次揣摩偈语所指皆未解其本意,直到临终前方才明白,这则偈语实指自己一生会四任方丈、九坐道场、六十七岁圆寂。佛印由此顿悟“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轮回,今出轮回。未得解脱,今得解脱。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未得真笑,今得真笑”[1]337。他的圆寂也就不再是线性时空的终点,而具有了一种生命回环成圆的艺术效果。除了时空秩序上的变化,小说中也多有对线性结构上严谨的因果性的偏离。线性成长小说往往意味着要把人物生命中的诸多单列事件建立一定的因果联系,让其成为一个因果相承、环环相扣的故事。但在《佛印禅师》中有许多充满偶然性乃至戏剧性的松散事件,强调了命运、机缘、巧合等因素,如小说中佛印的多次脱险均有巧合和机缘的助力:当他遇到蟒蛇攻击无力搏斗时,想起佛家王令望读经避虎的典故,仿其坐地默念《金刚经》,蟒蛇不知是由于他身边树枝有尖刺还是真有佛家所谓灵性,未攻击他便离去;当他被恶人囚禁于密室之中,也是在打坐练习《金刚经》时无意触动了机关,打开逃生的地道。小说中类似这样的情节还有很多,事件之间联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世俗性与宗教性相互掺杂,严整的因果规律在这些情节中被很大程度地弱化了。那么缘何会有这些“不合规矩”的偏离书写呢?表面上看,这是受到佛家修行之法、言说方式、人物际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是作者不囿于结构律令,对特定文本的文本意图抱有相当敬意的表现。
由是观之,选择线性叙事结构来叙写《佛印禅师》,是作者克制先验历史观影响、专注人物自身成长历程的体现,其内在是对小说文本意图的尊重。这也使得作者以内外两条线索虚实相生地书写人物成长,突破线性叙事的结构律令,在局部包容偏离于时空秩序和因果规律的部分,从而立体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三、知识叙写
与小说叙事结构紧密关联的,还有叙事过程中的知识叙写和情节发展的关系问题。历史小说的题材决定了它或多或少会“掉书袋”,但怎么个“掉”法却很有讲究,因为“掉”不好就会成为无用的知识炫技。例如,盲目地追求宏大叙事往往会造成知识叙写的失控,炫技式的知识叙写可能会导致小说部分内容显得突兀、庞杂,因为一些看似深刻或者冷门的历史背景知识,一旦被毫无节制地铺排开来,就会遮蔽小说的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这种无限制的知识叙写对小说艺术的损害是无需赘述的。《佛印禅师》同样也要处理知识叙写的限度问题。小说写的是佛印禅师的人生故事,所以必然会涉及大量的佛学知识,但与熟谙佛学知识的作者不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佛学高深玄妙,别说佛理形而上的内容过于复杂难解,就连基本的佛教名寺、佛学典籍等知识,很多读者也并不知晓。于是,这就对作者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怎样从浩瀚的佛学知识中提炼出合适的内容,并将其自然而然地嵌入小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整体来看,由于《佛印禅师》采用了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因此对佛学知识的叙写和对情节发展的陈述就显得很有分寸,作者是紧贴着人物成长过程去展开佛学知识叙写的。如前文所述,佛印禅师的成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是人生经历,如出家修行、与各路得道高僧的交集等。为表现他的这种游历,作者会借机讲述一些寺庙建筑、教史演化、佛学典故等历史知识,这些知识都属于佛教史。在佛教史的书写上,作者不是漫无边际地展开,而是聚焦于佛印这个中心人物,贴近人物本身的阅历,如小说中对相国寺、金山寺等佛教名寺的介绍,是有意以主人公佛印的空间位移为坐标,行止何处便有背景知识和盘托出,这种文化地理的叙写方式,一直让人物处在佛学的宗教氛围里成长,佛教史内容也就融入到了人物成长的情节发展主线之中。对于佛学典故的介绍同样也由主人公当下的经历引出,而且作者只剪裁突出与人物和情节有互文作用的部分。例如,作者写佛印在宝积寺被僧人了元忌惮时,引出禅宗五祖传灯六祖的典故。这与佛印当下的处境是互文的,而且这种书写并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典故介绍,只是突出强调传灯时衣钵争夺的艰险,这实际也为后文主人公的遇险埋下了对应的伏笔,将佛学典故融入到人物境遇书写的主线里。
除了这种主线上的设计,为了更贴近情节发展,小说中叙事视角的选择也颇有章法。知识叙写和情节发展无疑有着先在的矛盾,往往会造成故事发展的中断或者搁置,即发生叙事上的停顿,这明显会对小说叙事的流畅性产生不小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好,即使与主线情节相关联,也很容易造成佛教史知识部分的赘余之感。为解决这一矛盾,《佛印禅师》在展开佛教史知识叙写时,往往并不都采用全知视角的直接铺叙,而是有意转用佛印的限知叙事视角,借助他的眼睛进行局部的聚焦,并通过展现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使得叙写的“景语”中都蕴含和浸透着人物的“情语”,叙事上也就不会有明显的中断之感。例如,小说并没有在佛印入开先寺之时就介绍藏经阁,而是后置到佛印入寺修行近三年,善暹禅师与佛印论禅时察觉到他的自满狂妄,便带其进入藏经阁时才进行介绍。佛印与师父同行,且不知师父此为何意,故心中惴惴不安,又因第一次进入藏经阁,自有好奇探究之心。于是,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叙事由全知视角切换到佛印的限知视角,借由佛印的眼睛,读者观得藏经阁一层诸多佛像,也知晓了最珍贵的紫檀佛像的传说。拾级而上,佛印步入藏经阁二层,观得满层陈列的浩如烟海的佛学典籍,便不难明白师父带自己来藏经阁的训诫之意。而紫檀佛像的观瞻又被后置三年,善暹禅师再与佛印论禅后,引他近处观瞻此佛像,读者也到此处才同佛印一起知晓紫檀佛像的全部知识。借助于使用此类限知视角,佛教史知识被巧妙地嵌入整体叙事之中,尽管知识叙写在小说中铺陈开来,但因人物内在情绪是连续不断的,所以不但不会游离于外,反而成为人物成长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在关乎人物外在经历的佛教史之外,为表现佛印禅师内在修为的提升,文中还有大量关于佛教义理的阐发,宗教学和宗教史两类知识也随处可见。作者往往采用言辩论理的设问对答模式,将佛教义理设计为贴近人物自身的对话,人物身份与内在修为不同,所问所答皆是不同。比如说,佛印与佛门中人言辩之时,总围绕修身求佛的主线,所探讨之佛理较玄妙高深;普通俗世之人则多从木鱼等可见之物发问,更兼有求佛多求外物的习气,佛印回答时也多用浅显例子类比,将佛教义理蕴含其中;神宗皇帝却是从国之治理处发问,佛印答帝王之问时,也重在阐释国法、家法与佛法之关系,庄重谨言;而与朋友,尤其是与苏轼言辩之时,则贯穿有三教合流的主线,说禅更兼论诗,潇洒肆意,颇有友人之趣。在这种贴合人物的对话设计中,作者借由对话人之口,深入浅出地讲述一些佛学义理,这些其实也是佛印自我内在启发成长的一部分。随着佛印内在修为的提升,对诸如三教合流等主题的认知愈发深入,这也就紧扣了人物成长的主线。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义理不同于一般的背景知识,它自身就有很多难以言尽的意义依附,言说方式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隐喻色彩,它激发出的联想内容往往会溢出作者本来的创作意图。在《佛印禅师》中,作者对这类知识的文本特性予以了相当的尊重,对佛教义理的论说往往点到为止,只择与人物直接相关处论说,并不意图穷尽阐释,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知识的多义性和开放性。
概而言之,《佛印禅师》中的知识叙写是有限度的写作,知识叙写是为人物成长、情节发展而服务的,不是脱离了情节主线的知识炫技,而是作品整体叙述进程中的有机部分,如此便不会有游离之感。说到底,这种知识叙写的限度正是克制作者意图、凸显文本意图的结果。
四、名物传统
如前文所述,《佛印禅师》中作者采用了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知识叙写时也有意识地克制作者意图的表达,不以作者意图遮蔽文本意图,因而小说的思想性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人学传统,二是名物学传统,两者又融会其中。
文学就是人学,这个观念由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倡导,经五四新文学运动引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便是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这样的文学潮流,主张小说的思想主旨在于写人,刻画人物的形象,讲述人物的生命故事及其反抗异化的觉醒过程。小说不管借助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表现手法,都是以不同形式来捍卫人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佛印禅师》蕴含的人学思想很明确。虽然作品中包含很多佛学知识,但落脚点始终是佛印的人生故事:他从幼冲到暮年、从家庭到寺院、从修行到得道,几乎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在昭示着这个人物的人性光辉。这种借助宗教描写来表达人学思想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里其实并不少见,比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涉及基督教知识,阿来的《云中记》涉及苯教知识,但小说的落脚点都还是在人身上。以此观照《佛印禅师》这部作品,不难发现,正如常伴佛印身旁那个母亲刺字的青布包袱所象征的,作者首先是将佛印视为一个人,其次才是超乎凡人之上的得道高僧,借佛性写人心,也便不难忖度其中暗含的教化之意。
更有意味的是,小说还有一个名物学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小说起初是凡夫俗子道听途说来的街谈巷语、八卦秘闻,是难登庙堂的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1]。这意味着小说在中国一开始并不是写人,而是名物,写各种各样的事物,为之命名,辨析义理,甚至是格物求道等。因此,名物学传统决定了中国传统小说有种笔记体的叙述倾向,这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小说定义的“更为广大的文体空间”[2]。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笔记小说,人与物的关系长久以来是平等和松散的,直到晚清以后,随着文学现代性标准的建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但启蒙文学的“狂飙突进”,却有拔高人的主体性,继而堕入启蒙神话的危险。
具体到历史题材小说中,也不难发现将人的主体性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写作取向。比如很多历史小说每遇山水名胜,多是点到为止,只将其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场景作简要介绍,并不重其形,更不必说赋其神。这与其说与作者的写作笔力有关,还不如说作者根本没有在此方面施展笔力的意图,除了刻画核心位置上的人事,作者自觉遗忘了其他方面。在这点上,《佛印禅师》除了表现人学传统,还呈现出一定的回归名物学传统的倾向,小说中对自然山川、寺庙厅堂等地理空间的叙写,对灵兽、名器等各种物的细致表现,都有名物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作者对物的描写并不是泛化的,而是在选取书写对象及角度时都明显内含着一种对“奇”的趣味追求。例如,文中多有写及蟒蛇、金钱豹、乌鸦等动物,它们都不是人类驯养的宠物亦或工具,而是各有灵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一只与佛印颇有缘分的白猿。这只白猿不只外形不同寻常,毛色奇异,而且似通人性,与佛印初次相遇便警示其路途危险,后又到寺院送野果于佛印,帮他治愈风寒之症。多年后,佛印游历四方回到真如寺担任住持之位,白猿携幼猿前来致意,并常伴佛印身旁。到佛印渐入老境含笑归天,它七日不食,一动不动蹲在化身窑旁,如石雕一般悲怆地凝视火堆,而后“昂起头,拼尽所有的力气,向上向前纵身一跃,宛如一条白虹,横过众僧面前。最后,那道白虹落在了化身窑中,依偎在了佛印法体之旁。转瞬间,白猿那白雪一样的身躯,融入了灼天映地的红色火焰之中,它要伴随佛印禅师,去往那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1]339。这是很明显的“奇”事,这只白猿恍若佛印老友,有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灵性。不只是动物,小说中的自然山川、花草树木、佛堂庙宇等书写,作者也总挖掘渲染其“奇”之所在,即使是看似寻常的诸如茶具等器物,也在作者笔下展现出独特的奇趣。
这种对“奇”的趣味追求,一方面使这些名物描写部分自然生趣,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赓续了笔记小说对于物进行审美观照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对看似是插入成分的名物描写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使它们超越了原有的具体所指,而成为有意味的意象群,在奇趣中生出禅趣,从而能够在名物描写之间组织出一个禅意涌流的大千世界,为小说营造出一种整体的具有禅趣的意境。再加之小说名物文字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意趣之美,如此便和小说的人物叙事形散神聚,水乳交融,名物学传统与人学传统融会于小说的整体禅境之中,这也是和佛教题材相契合的。
综上所言,不论是线性的叙事结构,贴合人物成长、情节发展的知识叙写,还是人学传统之外向名物学传统回归的倾向,都体现出《佛印禅师》是一部在小说艺术上具有相当形式自觉的作品。这种形式自觉,在作者的前作《铁网铜钩》和《旧林故渊》中都有所展现,而《佛印禅师》则将对文本意图的尊重推向了更加成熟的境地。作者不以自身意图去遮蔽文本意图,聆听“小说的智慧”[3],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凭借着“写作的限度”,反思了人的主体性神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