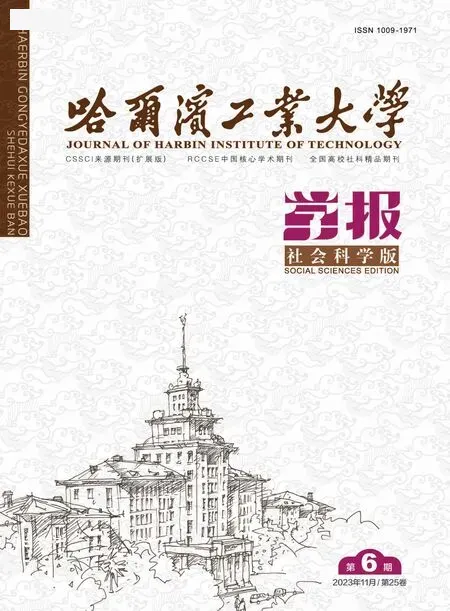民国监察官群体与监察权的现代转型
2023-03-09云静达孙文恺
云静达,孙文恺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23)
引 言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怎样的监察权? 对这一问题的准确回答,必须直面传统中国厚重的监察权运行史及其近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监察权向现代转型跨出的第一步,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官群体及运行机制、成为考察中国传统监察权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监察权是政治权力研究中的独特场域。 我国的监察权力实践根植于中国话语下的历史性创造。 它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发挥着彰善瘅恶、肃贪治腐的重要作用,也经受着现代性与法治化的诸多质疑。 有关监察权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研究多从权力属性的内在面向展开,如有学者从权力特征角度认为,“监察权具有独立性强、监察对象广泛、强制手段多样的特征,因而要构建‘设权与控权同步’的监察权监督制约体制”[1]。 也有学者从权力运行角度认为,“规范监察强制措施和保障被调查人权利是监察权健康运行的关键”[2]。 还有学者从权力创新的视角来审视监察权,认为“监察权的现代化应当保持监察权运行的平衡性和连贯性”[3]。
此外,考察监察权运行的外在视域——监察官群体及监察权确立的理念和运行机制,是全面了解监察权的独特窗口。 监察官群体作为监察权的人格化表现是权力实现的外在具象,监察官作为国家监察权行使的主体,其职业素养是观察监察权力效能的切入点和参考系数[4];监察官员“纠察不法”的能力是监察权威性的重要保障;监察官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个人形象也是监察权力价值塑造和文化机理的主要载体[5]。 因此,以民国监察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一时期监察权的现代转型具有现实价值。 那么,民国监察官如何在其制度层面体现独立性、专业性、保障性等法治的基本精神,在历史语境下呈现出怎样的现代化转型特征? 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官群体为对象,深度挖掘民国时期的监察史料,考察该群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理念设计、制度架构及其现代转型特征,以期对我国当代监察权运行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些镜鉴。
一、国民政府监察官制度的现代性理念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是国民政府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石,监察院长于右任则将这些理念逐步付诸制度实践。 1906 年《民报》创刊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先生把五权分立及独立监察权作为“将来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6]88,并在借鉴西方议会政体的组织形式和我国传统御史制度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为国人勾勒出现代中国监察权力运行的框架。①据常泽民先生在《中国现代监察制度史》一书中考证,“监察权一词系中山先生所首创” 。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民权主义时,首次使用了“监察权”的概念。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在监察政治实践中进一步细化为权能分治、专业监察、独立监察等现代性理念。
(一)权能配置的分权理念
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代表,二者最终体现于权能分治的制度设计中。 三民主义为五权宪法理论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指引,民权主义思想又构成了监察思想的底层逻辑。
首先,民权主义是监察权创设的法统来源。“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 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6]173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具体表现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大民权”。 选举权是人民选举官吏和被选举的权力;罢免权是指民众有权撤换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吏[7]。 其中,人民享有的罢免权是南京国民政府监察权力创设的理论渊源,所谓“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 监察官员的设立、监察法规的出台以及监察组织体系的构建,其要义在于通过法律程序引导人民在民主共和的轨道上行使罢免权。
其次,权能分治理念是监察权运行的指导原则。 权能分治根植于民权思想,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分立”——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民大会,而治理权能则分为立法、执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别由五院执掌。 “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 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8]由此,现代意义上的监察权正式出现在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中。
当然,监察权的运行也会受到必要限制。 为了进一步强化权能分治的思想,让治权为代表的监察权受制于国家最高权力,防止监察权独大,孙中山将监察权能体系进行了拆分:监察院仅保留弹劾权作为其核心监察权能,将惩戒之权分给了国民大会和不同的惩戒机关。 这一思想对国民政府监察权能的配置产生了关键影响。
(二)权力运行的职业化理念
权能分治理念的进一步延伸是如何确保握有治权的政府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以实现“良善之全能政府”。 因此,必须依靠掌握专门知识的官吏,让“有能的专门家”来管理国家。 官吏服务于人民,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部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做汽车夫……不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9]。 这些贯穿着平等特征的人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监察官群体的功能塑造。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官选拔所要求的专业性、高素质等标准来源于此。
专业监察思想的根源在于孙中山先生对清廷腐败政局的反思。 “卖官鬻爵,政以贿成”,“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若何,而问其权势之有无”[10]9。 清廷政治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国人最喜欢做官,不问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所学非所用”[11]。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不论是西学东渐思潮对人民思想的影响,还是初级工业化带来的专业分工,传统官僚所掌握的治理经验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管理日益专业化的需要。 加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征,国民革命队伍中裹挟了大量的封建势力,一些旧官僚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客,孙中山甚至评价他们是“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真无耻于人类者”[12]。 “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经”[6]524。 为净化革命队伍,孙中山要求考试院选拔人才时应当“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是为至要”[10]259。 承担惩贪肃吏重任的专门机关任职人员,亦应从中产生。
在此基础上,于右任真正将职业化的理念付诸实践,并提出拓宽监察专业领域的思路。 “除对于普通监察事项仍依平时及非常时期监察法规积极查察外,关于全会决议的特种政府工作,要以各工作方案实施程序为对象,随时随地用种种方法严密监察。 涉及专门技术方面者,更要适应需要,增聘人才切实做去。”同时要求“遇有特殊监察事项还要借助院外技术专家临时参加工作。”[13]82在他的努力下,专业监察的理念逐步上升为监察官制的指导思想,并吸纳了大量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和具有法学背景的高级人才加入到监察官员的群体中。
(三)权力设计的独立性理念
“五权制度最有趣味的创设在监察权的独立”[14]。 依托法制实现监察独立的现代性思想与孙中山有着重要渊源。 独立监察理论既是孙中山研究外国民主政治后的思想创见,也是对我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制度反思。 他认为西方议会监察模式下,监察权力因无法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趋于弱势,容易陷于议会专政,监察效能难以有效发挥。 传统中国的监察官员“虽能主持风险,然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15]331。 古代监察官员虽有独立之精神,但没有独立的制度。孙中山特别阐释了监察独立的重要性——“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这是不恰当的。”[15]320监察官员失去了独立性就必然会蜕变为权力的附属品,对其他机关的监督也只能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意义。
真正将独立监察理念制度化的是监察院长于右任。 在就职宣言中,于右任谈到“要使监察院为国爪牙,为民喉舌,为三民主义的前卫”[16]。 以此为宗旨,他倾心于监察院的建章立制,因而被誉为“民国监察之父”[17]。 于右任不仅强调独立监察的思想,更谈到了独立监察的审慎用权。 “弹劾权应由监察委员单独行使,包括院长亦只能依法将案件移送惩戒机关处置。”[18]“监察权的行使,由调查入手,须搜索证据,认清事实,方可适用各种监察法规,行使纠弹建议之权。”[13]82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以《监察法》《监察院组织法》为核心的委员制监察体系得以确立,以《监察委员保障法》为核心的监察官职业保障体系得以完善,现代监察官员的职业塑造和身份认同开启了现代转型。 1931 年2 月16 日,经监察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刘三、朱庆澜等23 人为监察委员。 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民国监察官制正式建立,监察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形象终于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二、国民政府监察官群体的制度架构
制度理念、人员结构和职权配置等内容是考察职业制度架构的重要尺度。 在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以近代政治理念规制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现代化过程中“内生性”与“外发性”交织的路径特征[19]。 独特的监察官制承载着这一时期监察权力的变迁与沿革。
(一)职业群体的民主因子
民国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渗透了近代中国已广为知识阶层接受的民主观念。 其身份塑造与制度建构融合了意见代表性、性别平等、区域平衡等诸多元素,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近代监察官群体的民主趋向。
首先,监察官员的籍贯分布体现了监察体制对于意见代表性和区域平衡等民主价值的关照。区别于民国时期特殊的人治文化和任职地域化的特色,监察院希望通过地域的广泛性来限制民国官场中任职地域化的不正之风。 在整个训政时期,监察使署和监察区的建立,国家监察权从中央部门向地方拓展。 1948 年“行宪”之后,监察委员的产生方式从任命制改为议会选举制,民主特征进一步彰显。 《中华民国宪法》第91 条明确规定:“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与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任期6 年,得连选连任。”选举制是推动监察委员具备广泛代表性的宪法性基础,使监察人员分布能够覆盖到所有的省、直辖市,甚至边疆民族地区。 例如,监察委员陈庆华籍贯为台湾台中;陶百川的籍贯为浙江绍兴;任秉钧的籍贯则是内蒙古土默特旗[20]。
其次,年龄结构也是国民政府监察官制度考虑的民主要素之一。 在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彰显国家监察的权威,监察委员必须具备威望、资历、专业等诸多特质,否则根本无力撬动官场顽疾。 因此,民国监察官群体整体的年龄结构呈现“老中青搭配”的特点。 “老人”诸如院长于右任(同盟会会员)、副院长丁惟汾(同盟会会员)、监察委员高鲁(同盟会会员)等均为国民党早期革命成员,这些直言敢谏的元老成为监察院中不可或缺的柱石。 “中青年”构成监察委员的主体。据考证,1931 年到1949 年间,监察委员年龄在41岁到50 岁的群体的平均占比为36%,30 岁到40岁之间的平均占比为15%[21]。 甚至38 岁的监察委员杨亮功,就已经参与审查张作相弹劾案、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等大案要案的调查工作[22]。 这种“老中青搭配”的年龄组合能够较好地契合监察职能的要求,在惩贪肃吏的监察工作中各尽所长,促进了监察效能的发挥。
再次,女性进入监察官群体体现了政治制度的民主面向。 随着民国时期女性权益尤其是政治权利获得相应的制度保障,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中出现了许多妇女代表,如黄觉、郭昌寿、丁淑蓉等。①详见《监察院监察委员通讯录》(1948 年)。女性参政不仅是妇女运动的产物,更是制度探索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标识。 在1948 年监察委员通讯录中记载的150 位监察官员中,共有女性监察官员25 位,占总数的六分之一,与男性监察委员的人数比值为1:5[20]。 对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样的性别结构足见其权力机制向现代化转型已经迈出了较大步伐。
(二)官员铨选的专业素养
受西学东渐背景和国民党革命经历的影响,国民政府的监察官员具有学历背景高且学科背景丰富的特点。 对此,监察委员陶百川曾言:“事实上出任是职者,多为硕学通儒,或功在党国,或政绩卓著,或社会名流,故人选并不浮滥。”[23]120民国监察官群体的这一特征,则有赖于监察官员选拔标准的革新。
首先,在重视学历学识的基础上,尤其关注海外留学经历。 受革命经历的影响,监察官群体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不乏少数。 以1931 年到1949 年之间监察委员的受教育背景为例,在统计的950 名监察委员中,大学以下学历仅有14 人,国内大学学历有422 人,留学者364 人,前清举人9 人,以上人员占总人数的85%,监察委员燕树棠、邓春膏、杨亮功、吴南轩、邹鲁、李旭寰、田炯锦等人均获得了博士学位[24]。 其中,田炯锦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后任监察院秘书长的杨亮功毕业于纽约大学。 留学经历与西式教育的影响下监察委员更容易满足监察院的功能设定,对于民主与法治的政治运作有着更为直接的体会,对于权力监督有着异于主流官场文化的理解。
其次,监察官员的人才选拔在多元学科的基础上尤为重视法学背景者。 学科背景对监察委员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习惯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因素都是监察工作开展的必备条件。 为保证履职效能,监察院设置了秘书室、参事室等作为监察的辅助部门,但监察委员依然需要独立完成调查、行文撰写等工作。 因此,监察委员还须具备较好的文笔素养,如杨天骥出生书香名门,诗词书法无一不精;监察委员王斧曾兼任《华暹日报》主笔。 抗战开始后,监察范围不断拓展,涉及行政、军事、教育、田政等多个领域,监察权能进一步丰富。 监察工作吸纳了诸多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监察委员。例如,监察委员吴忠信毕业于南京江南将弁学堂;监察委员李嗣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等。 监察权力行使所兼具的执法特质,需要监察委员具备较好的法律素养,这是民国时期监察权力运行的重要特征。 例如,监察委员王子壮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监察委员王宪章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 这些职业标准特征是近代以前的监察制度中所不具备的。
(三)日渐强化的监察权能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期间面临着挽救民族危亡与重塑国家权力体制两大主要任务,但监察职权在议会监察的组织框架下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强化、细化。
权能配置是监察效能的基础。 军政时期的监察职权虽然停留在书面上,但为后来监察院的成立提供了制度蓝本。 1926 年10 月公布的《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明确的监察职权包括“弹劾和审计在内的惩戒官吏、审判行政诉讼、考察各种行政事项。”①详见《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第1 条,载于《民国日报》1926 年10 月18 日第4 版。1927 年11 月修正公布的《监察院组织法》取消了原来惩戒和审判行政诉讼两项权力,②详见《修正国府监察院组织法》第3 条,载于《民国日报》1927 年11 月6 日第5 版。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弹惩分离”的监察权能分配模式,这样的权能架构奠定了日后监察院的权能基础。 训政时期(1928—1947),监察委员主要依靠《监察院组织法》《审计部组织法》《弹劾法》《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等法律来行使监察权,初期监察委员只有弹劾权、审计权、调查权这三项权能。 抗战爆发后,为提升监察效率又增设了纠举权和建议权,并通过《监察院分层负责办事细则》明确了内部人员的职责划分。 宪政时期(1947—1949),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监察法》之规定,监察院又增设了纠正权和同意权。此后,监察委员的属性逐步转变为分担监察职能的议会议员,监察院也从行政监察模式向议会监察模式转变。
人员配置是监察能力的直接体现。 虽然,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呈现出复杂的斗争样态,但监察委员的人数基本在稳步上升。 在法定人数方面,1928 年10 月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43 条中做出了监察委员人数为19 ~29 人;③1931 年监察院成立时,实际是参考1928 年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所规定的人数对监察委员进行选拔,故首批监察委员人数为23 人。1931年6 月15 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将人数调整为29~49 人[25]。 同年12 月修正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 对人数略有调整,改为30 ~50人[26]。 抗战胜利后,1947 年监察委员人数增至54~74 人[27]。 当然,实际工作中的监察委员人数也有区别。 “1931 年首批任命的23 名监察委员,实际就任者仅有18 人,后又有所任命,但到院服务者先后仅有21 人。”[23]120“包括被免、辞职或去世监察委员在内,1931、1932 年,监察委员分别为24 和27 人;从1933—1946 年,监察委员人数基本保持在46 ~54 人。”[28]1947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将监察委员的产生方式改为了选举制,包括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和地方行署的监察委员在内,共有239 人(含病亡)[29]。 从较长的历史区间来看,国民政府监察官群体的总人数呈增长态势。
三、民国监察权现代转型的特点与启示
“现代的监察权必须符合权力法定、功能优化、边界清晰、运行独立等特征,这些都是近代以前的监察权所不具备的。”[30]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官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监察权现代转型的独特轨迹: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法统不再是传统的天命而是宪法,监察权不是依附于皇权的耳目,而是国家治权的独立单元。 民国监察官群体的现代转型过程,体现了这一时期政治民主化探索的独特价值,并对当下监察官群体的身份塑造具有现实意义。
(一)民国监察权的现代制度转型
首先,从听旨奉诏到权力法定。 与传统监察权君为臣纲的法统来源不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政治设计迎合了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逐步向“法为臣纲”过渡。 首先,相较于传统监察权运行的听旨俸诏,现代监察权需要宪法授权以提供正当性,需要法律规定的程序和价值作为实践指引——通过将监察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责任等要素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监察权力才具备了独立运行的轨道。 其次,民国监察官群体的出现,不再是以御史内臣的亲疏关系为依托,而是以立法形式确立政治身份。 通过宪法性文件《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宪法》明确监察委员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义务;通过出台《监察委员保障法》提供履职保障和免责屏障;通过《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监察院调查规则》《规定呈送纠举建议案之程式令》等单行法律为权力运行提供程序规范。 与传统零散的监察规定不同,此时监察法规的体系化特征十分明显。 这种立法先行、程序先立、体例齐备的思路是现代政治运作的重要特征。 最后,这些法律又为监察官员独立履职建立了法制屏障,排除了法律层面的不当干涉。相较于古代听旨俸诏和风闻言事的监察传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权能融入了更多现代法治元素,监察官员在宪法的框架内享有较为充分的履职自主性,调查、纠举、弹劾等都依靠既定程序法来行使。 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得监察权力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处于法律上的优势位置,有助于监察效能的发挥。 当然,过分的独立也会导致监察滥用的风险。 因此,相关的监察法规又对监察官员作出了必要的职业限制,诸如不得兼职、不得为人写推荐信牟利等,①《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 年8 月)第45 条:“监察委员不得兼任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机关的职务”;监察院在1932 年1 月22 日的院务会议上议决通过“监察院人员概不得为人作介绍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还作出了专门的监察官惩戒程序,在立法框架内让监察者的追责同样能够于法有据。 这些举措弥补了数千年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治文化缺失,在保证独立监察的基础上,消弭了监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张力,为中国现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法治的基因。
其次,从皇权依附到独立监察。 监察权具有惩戒和激励的双重属性。 对于监察官员而言,其权力的开放与限制程度影响着监察效能的发挥,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的责任划定。 传统人治模式下,监察权的行使裹挟了皇帝与大臣之间如私人情感、政治利益等要素。 纠弹官员不法容易招致同僚记恨,驳斥皇帝违失更容易遭遇不测,监察程序的推进需要处处请旨,监察官员的谨慎并不在于对公权力的敬畏,而是对皇帝个人好恶的揣测。传统监察制度本质上是服务于皇权的人治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往往是混同的,天下是皇帝个人的私产,监察官员是皇帝的“耳目之寄”,监察权的正当性源自皇帝个人的授意,监察程序的推进依赖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即便是民初政坛,“吏治久疏,公德未彰,品流驳杂”已成为常态[31],保障监察官员履职尽责,光靠法律赋予其较高的政治身份是不够的,还需要明确的监察官责任制度。 具体而言,责任制度包括履职定责、尽职免责、失责惩戒三个方面。 履职定责是责任制度的前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法律将监察责任明确到个人身上,赋予了监察委员独立开展监察活动的职权地位,从调查、审查到最终弹劾均由监察委员个人负责,甚至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无权插手。 尽职免责是强调在制度层面让监察官员即便“激浊扬清”,也能“出淤泥而不染”。 在履职保障方面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度。 一方面,为鼓励监察委员纠举官员的不法之事,《监察委员保障法》(1929)第5 条对监察委员的失职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定,除非属于“受人指使而提出证据不足的弹劾案(捏造事实)”“接受公务员的馈遣供应(收受贿赂)”“有应受弹劾的事实,经人民举发而故意不予弹劾”这三种情形,其他职务过失都不能以失职论处。另一方面,由于监察权力的行使具有复杂性,因此监察院还建立了必要的容错机制。 根据《监察委员保障法》(1929)第6 条规定,如果监察委员存在证据不足而弹劾失实,监察委员只要证明其未受指使,最终只会受到监察院长的儆告处分。 经审查移送惩戒后发现官吏不应受处分,原弹劾人也不负失职之责[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法律方式将监察过程中的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加以区分,在保障监察官员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将权力运行的主要环节纳入法治的轨道,是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特点。
最后,从德行显著到专业兼顾。 监察官是监察权力的外在具象和制度载体。 规范监察权力的运行,需要在监察程序法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监察官法,从权力的内在和外在两个面向对监察权加以规制。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这种权力思想限于法统来源、评价标准、权力体系等原因,很难适应民国政治体制的要求。 在反思中国御史言官制度和西方议会监察制度的弊病后,孙中山尝试将传统制度经验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寻求新的突破口,南京国民政府在五权宪法的基础上创设了现代特色的监察官制。 一是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远高于一般文官。 传统政治实践中,唐朝以“性刚直敢、不顾犯难、有雅才”作为监察官的选拔标准[33]211-212,明朝则以“德行显著、学识优长且老成练达”为选任的关键[33]371。 传统选拔标准强调道德个性。 民国监察官制中,则以硕学通儒、功在党国,政绩卓著为选拔要件,关注品格素质的同时,强调政治经验和专业背景。 当然,现代监察权力的运行也是国家法治实践的过程之一,相较于传统文官体制中熟读四书五经的清流言官,现代监察官员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政治素养,这些条件强化了民国监察权的法治属性。 二是民国文官制度推行的高薪养廉政策为监察委员带来了优厚的生活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传统监察官制推崇“位卑权重”的理念,汉朝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六百石;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七品[34]。 在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中,“厚其养廉,永其俸禄”是确保文官“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的重要保障[15]10。 实践中,民国监察委员的薪资与官阶相挂钩,训政时期的监察委员属于简任官职,①根据常泽明先生在《中国现代监察制度史》一书中考证,训政时期的监察委员虽然属于简任官员,但其任用资格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地位仅次于最高的特任官职。 薪资方面,简任官的月俸为每月430 ~680 元不等[35],而同期《官俸表》中所显示的公务员平均薪俸仅为280元。 从权力功能的视角来审视,高薪制度也为纠举不法提供了基础条件,相比于古代御史谏官位低权重的特点,国民政府在监察官制中通过高薪养廉的现代管理理念吸纳了许多不同专业的人才,为这一时期政治权力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思路。
(二)民国监察权现代转型的借鉴意义
独立、专业、保障等现代法治理念成为监察官职业发展的价值要素。 完备的监察法律体系是监察权力独立行使的重要前提。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1931 年出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明确了监察官员的基本权力和职业保障等内容。 随后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监察委员保障法》《监察院组织法》《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等法律来保障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 从监察逻辑来看,监督者应当独立于被监督者,监察效力才能真正发挥。 而欲以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需要完备的监察立法对权力运行进行规范。 毕竟,监察权的独立性价值必然催生其封闭性,不论是监察权力的实现还是权力的规制,很容易导致权力治理中的“灯下黑”问题,监察法律体系的完备是避免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法治是赋予公权力正当性的最直接来源。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以《宪法》的形式赋予了监察官员监督公权力的法律地位,《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细则》初步建立了监察权力的运行机制,而《监察官法》则对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考核等内容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可以说,我国监察法治建设正在从“法制初备”逐步向“法权完备”阶段迈进。 接下来,我国监察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围绕监察官的权责配置,解决好调查程序优化、监察职权规范、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等问题,以程序化的立法价值为引导,为监察权的有效运行提供有序轨道,扎好监察权运行的“法治笼子”。
以道德与法律为约束的监察官职业体系。 在传统政治中,道德品性始终是监察官员铨选的重要考量。 近代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国家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延伸,法律成为约束公权力的重要手段。 此时,强调专业背景和法律素养的官员铨选制度为监察权力的现代化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委员吴忠信具有的军事专业背景,监察委员李嗣璁为物理学专业毕业,监察委员王子壮、王宪章、高一涵都具有深厚的法学教育基础,这些都体现了专业性和法治化为监察权力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 抽象而言,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的他律对于权力运行同等重要,二者结合才能有效遏制权力的恣意性。首先,通过职业道德入法,将政治素养和品性优渥作为监察官群体的首要标准,以实现监察官群体的整体道德自律。 此外,将监察职业所秉持的道德操守转化为公职人员的行动自觉,是监督者“先律己而后律他”的价值彰显。 其次,通过高质量的人事管理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监察官体系。监察官员作为监察权的人格化表现,个人素质对于监察权力的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规范监察权力的运行,需要在监察程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察官法,将法治和治人相结合,从权力的本体和外在加以规制。 再次,监察官制度不仅仅包括选拔机制,还应当有一整套详细的管理制度,具体包括招录、培训、调配、任免、晋升、福利、政治、宣传等事务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机制。 这些制度的完善对于监察官群体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价值,也是监察官区别于一般公职人员的专业性体现。
宽严相济的监察官责任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曾进行的制度尝试在中国监察法制史上是独具意义的。 不论是《监察委员保障法》中对监察委员失责情形的列举式规定,还是监察院会议中对监察委员的言论免责特许,抑或是对监察官员独立设置的惩戒程序等内容,均体现着民国时期对监察权力保障的基本面向。 同时,禁止监察委员兼职、写推荐信牟利等规定则体现了民国监察权的严格侧面。 这些规定首次将监察履职过程中的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加以区分,在保障监察官员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将监察权的运行纳入法制的轨道。 虽然,这些制度设计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仍然具有鲜活的当代价值。现代官僚的身份是“作为制度的人”和“作为现实的人”的二元合一。 合理区分监察权力运行中的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让监察权的运行始终保持在法律的轨道上,对于监察体制建设尤为重要。况且,健全的监察责任制度始终是保障现代监察权力运行的关键。 监察权是“治官之权”,让“治官之官”正确行使权力的前提是对权力主体的权责予以明确,因为监察权具有惩戒和激励的双重属性。 对于权力人格化的监察官员,既不能囿之于严,打击了监察官员的惩贪肃纪的热情,也不能失之于宽,放任监察权力滥用而侵蚀行政权力。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的责任划定。 光靠法律赋予其较高的政治身份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履职的失责惩戒机制和纠错容错机制,既能规范监察职能的行使,还能免去监察的后顾之忧。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委员作为整合国家监察权能的重要载体,其出现不仅意味着现代监察官群体的正式形成,更意味着传统监察制度的现代化之路开启了以五权宪法理论为代表的实践探索。 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路来看,民国时期面临的权力制约难题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困境独具时代特色。 在以近代西方政治模式挽救民族危亡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作用下,催生了传统监察权力从听旨俸诏到权力法定,从皇权依附到独立监察,从德行显著到专业兼顾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我国监察权力的优化与完善,可以借鉴这段转型过程中的合理因素,将独立、保障、专业等价值融入监察立法中,将权力法定、独立运行、边界清晰等理念内化于到监察实践中,让监察权保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如此,监察权才能发挥其惩治与激励的双重功能,在现代国家政治中彰显法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