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天文计量思想探析
2023-03-09关增建
徐 倩 关增建
(1.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2.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天文计量属于计量的一种,是时间和空间等计量内容在天文学领域的概称。中国的天文计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明末传教士东来,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天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方天文学,西方天文计量也由此进入中国,促成了中国天文计量的转型。徐光启(1562—1633)在这次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徐光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已有很多的研究,但从计量史角度来看,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有待挖掘。
一、计时定向本质问题的提出
(一) 中国古代的两种计时系统
学界已有研究认为,中国古代计时器有多种形式,包括日晷、漏刻、机械计时器、轮漏和木漏等,构造和设计原理都可自成体系。(1)参见陈美东、华同旭主编:《中国计时仪器通史(古代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1—546页。这些装置按照工作原理,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天然均匀周期运动为参照,笔者称其为自然计时系统;第二类则是以人为制造均匀运动为参照的人工计时系统。
在古代社会,一般情况下是两套计时系统并用的,这就产生了基准的选择问题。传统采取的是以天体尤其是太阳的周日视运动为基准,人工计时系统须以其为准进行校验。例如漏刻计时,其时间起点的选择、水流速率的调节,都需要参考日行进行校准,“古之为漏者,必有表”,漏之度要“考以日中之影”,为的是“与天相应”,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人工计时系统是对天文测日计时的补充。(2)参见陈美东、华同旭主编:《中国计时仪器通史(古代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但这种计时主次排序在宋代遇到了问题。北宋沈括的调漏技术十分精湛,在他之前,“下漏家”们的“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他们认为“水性如此”才使漏刻不精,于是便在漏箭的长短分划、水流速率、壶漏级数等方面深钻。沈括也在持续探究漏刻和日行不匹配的问题,他尝试调理漏刻,但“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于是“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通过十余年的研究,他发现“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故不及百刻”(3)详见冯锦荣导读,冯锦荣、林学忠、陈志明译注:《梦溪笔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这与黄赤相交造成的日行赤经变化正好相反。沈括由此指出了日行和天运(恒星天)速度不一致的问题,他认为漏刻的计时精度很高,出现漏刻“未合天度”的情况只能是太阳周日视运动不均匀造成的。古历法由汉至唐积累了许多日行盈缩的研究和创见,历算家们已经发现黄赤相交使日黄道运动的赤经分量变化不均的问题。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将日行不均与漏刻计时联系起来。(4)参见郭盛炽:《沈括发现的漏壶迟疾和太阳周年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0年第2期,第202—210页。而沈括通过比对漏刻与天文计时,发现漏刻计时的均匀性超越了日行,如此就不能以日行作为计时基准。沈括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因此遭到时人的怀疑。沈括曾感叹道:“余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5)冯锦荣导读,冯锦荣、林学忠、陈志明译注:《梦溪笔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无论如何,沈括的发现昭示着计时有三种参照:漏刻、日行和天运,究竟哪一个才是计时的最高标准?沈括没有明确回答。
沈括之后,漏刻和其他人工计时器具(如水运浑象)越来越朝着大型化、观赏化方向发展,不利于计时精度的提高。元明漏刻的制作和管理技术严重下滑,很难达到沈括的调漏精度。明朝还人为控制时间的运行制度,如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声称要遵照祖制,漏刻的昼夜时间管理便依然沿用南京制度。(6)参见吴守贤、全和钧主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北京观象台的仪器安置方向也完全复刻南京,并没有根据计时仪器的测量原理及时间流逝的客观特性进行调整。在这种认识水平的驱使下,计时基准问题很难被明确提出。且明朝历法直接将元《授时历》更名《大统历》行用,省却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实践,因此没有精确计时的迫切需求。元明两代,无论从人工计时精度、测时意识还是实践需求诸方面都激活不了关于计时本质的思考,沈括发现的计时基准问题因而被掩蔽了。而不时有学人对漏刻、圭表和晷仪进行探索比较的目的是调节漏刻“与天相合”,以符合人们对于时间的原初认知习惯,而非深究哪一种运动形式最能反映客观时间的流逝。总之,明末以前,计时基准问题无论在理念还是实践层面皆被悬置。
(二) 徐光启的创新:计时之本,准于天行
明末传教士东来触发了士人关于时间本质特征的探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认为时间就是对变化的量度。(7)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转引自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杨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45—46页。传教士邓玉函因循亚氏理念,基于运动变化标定时间并对其本质特征给予界定:
时者何物?凡诸有形之物必有变革,变革多端中有迁运一端。因其迁运先后,从而测量剖分之,则为时也。问:草木鸟兽人事,皆有变革迁运,亦可用以为时,何必二曜(日月)?曰:凡立术有三法:一须公共,一须分明,一须永久。惟二曜则然,他无有足比者故也。(8)邓玉函:《测天约说》,石云里、褚龙飞校注:《崇祯历书合校》,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0页。
邓玉函关于时间与有序运动的认知联系是深刻的,但他以日月运动作为其他运动“无有足比”计时参照的论断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便日月运动满足他提出的“公共”(一定范围内的同时性)、“分明”(易测)和“永久”(持续性)三个重要计时考量,但关于时间基准的两项要素均匀性和周期性才是至关重要的。(9)参见马利科夫:《计量技术概论》,国家计量局编译处等译,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3年,第167页。这也是古代中西方时间认知发展脉络中突出的方向性区别:中国更重视均匀性,而西方则更看重周期性。但日月因“偏心圆”中心差和地平观测视差等因素影响,在均匀性和周期性上都存在不足。因而二者并不是入选计时基准的最佳对象。
实践层面,崇祯改历之前,人工计时一度占领上风。彼时测时是先以圭表测影确定正午校准漏刻,再以漏刻所守之时作为天文观测用时。(10)详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25页。明末传教士带来了精度相对较高的天文观测仪器,使得观测技术有所进步,这就需要更加准确的时间计量。而计时基准若选择不当就会导致测算结果产生误差。徐光启等明末士大夫上疏改历的一个重要伴随命题就是:旧法已经不合当下天象运行,要验证历法疏密就必须保证计时准确。而计时不准问题在明末历测中已十分突出,“考验历法全在交食,览奏台官用器不同,测时互异”。(1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5页。《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法在对1629年6月21日的日食推算中均失准,西法虽然较为接近现代天文回推的结果,但其对日食持续时间的验算仍有将近15分钟的误差。这是明末北京观象台的计时器具漏刻没有进行时间校准所致。(12)参见Sperello di Serego Alighieri, Elisabetta Corsi, “The Eclipse of 21 June 1629 in Beij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Journal of Astronomi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vol.23, no.2 (2020), pp.327-334.徐光启意识到了计时方式准确性的问题,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明确表达了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先确定计时基准,再以基准校正其他计时系统。
那么哪种计时系统可以作为基准呢?人工计时的漏刻是否可行?徐光启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漏刻存在诸多缺点。其一,漏刻形制多且计时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壶漏等器规制甚多,今所用者水漏也。然水有新旧滑涩,则迟速异;漏管有时而塞,有时而磷,则缓急异”;(13)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其二,漏刻计时不能独立确定计时起点或校准点,必须依赖于自然计时系统;(14)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其三,漏刻“调品皆繇人力,迁就可凭人意”(15)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14页。,在时间管理上人为因素介入过多,容易产生偶然误差。也就是说,漏刻在“公共”和“永久”两个计时客观条件上都存在短板。
徐光启意识到,若选择各地可以同步观测到的周期自然运动作为参照标准,则可以大范围内实现计时结果的可复现性,“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16)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8页。。这是说自然计时系统能在大范围内测时,满足了计时基准应当具有的公共性和永久性特征,其计时结果更客观,“按晷定时,无可迁就,无容隐匿”,(17)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7页。人为介入因素较人工守时少很多,可作为计时基准使用,“惟表、惟仪、惟晷,悉本天行,私智谬巧无容其间,故可为候时造历之准式也”。(18)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页。显然,漏刻只能辅助自然计时系统,徐光启据此明确提出,“壶漏者特以济晨昏阴雨晷仪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时之本。所谓本者,必准于天行”。(19)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
他进一步指出不光漏刻,另一种人工计时装置即利玛窦进呈内廷的自鸣钟也同样不可:
定时之术,相传有壶漏,为古法;近有轮钟,为简法。然而调品皆繇人力,迁就可凭人意,故不如求端于日星,昼则用日,夜则任用一星,皆以仪器测取经纬度数推算得之,是为本法。(20)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14页。
沈括认为日行不均,人工计时更精确。但他受浑天说的宇宙图景所限,没能探究出漏刻与日行存在差异的另一项因素。沈括关于计时问题的疑问,在明末中西交流中得到了回应。徐光启超越了沈括的认知,不仅将基准重新放回到自然计时系统上,更是创造性地将基准从太阳视运动转变为恒星视运动,从而避开了对计时中日行不均因素的考量,这是徐光启洞察时间本质后在计时理论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古人长久以来关于计时问题的探求因徐光启“计时之本,准于天行”的基准思想得到升华。徐光启后学如熊明遇、李天经等人完全赞同以“天行”作为计时之本的理念。清代学者在撰著《明史》时也对徐光启的计时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21)详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35页。这也体现了徐光启在指导崇祯改历过程中多番强调的兼顾理算、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致知思想。
(三) 天行:作为计时基准的恒星定时
“天行”作为徐光启提出的计时之本,具体指的是恒星的周日视运动。徐光启定其为基准的原因也不难发现,人们从本能上即能觉知时间流逝的速度是恒定不变的,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最均匀连续的自然现象来作为时间运动的体现。恒星依附于“宗动天”,只有赤道“左旋”的“恒定”运动,其物理实质是地球自转的表现。地球以固定不变的角速度绕自身轴线均匀旋转,所以恒星的周日视运动比日行更均匀稳定。传教士罗雅谷就强调:“测星求时为公法,最为定准。”(22)罗雅谷:《测夜时法》,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第1页 b—2页a,转引自李亮:《日本抄本〈崇祯历书·测夜时法〉探赜》,《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9年第2期,第171—184页。对此,徐光启也曾多次提及,如“其(月食)时刻本以测星为正法”,(23)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1页。“其月食目所易见,止时刻难定,除壶漏外再用星晷测量,及用恒星推算时刻。先定某星高几度分为初亏,某星高几度分为食甚,至期用仪器测验,以定真正时刻”。(24)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3页。可以说,恒星视运动是明末乃至其后二百年内所能找到的最适宜的计时基准。
崇祯二年(1629)九月,徐光启请旨制造天文仪器,包括平面日晷、星晷、自鸣钟和望远镜,(25)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342页。但经费紧张,未能全部制造完毕。崇祯七年(1634),接任督历之职的李天经再次上书进言:“辅臣光启言定时之法……不如求端于日星,以天合天,乃为本法,特请制日晷、星晷、望远镜三器。”(2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册,第361页。徐光启使用望远镜来辅助定时,是他将恒星定时作为计时基准的一个旁证。使用望远镜可依次确定两颗上中天的恒星,根据星图、星表得到二者的赤经差,从而推算出时间差。
为了促进时人对恒星测时基准的接纳,徐光启针对崇祯四年(1631)六月钦天监所测各处“月食方隅晷刻,互有异同”现象,借机组织天文官生分组测时,一组使用壶漏,另一组“在台用星晷测紫微垣二星,用象限仪测织女大星经纬度数,以推变时刻”,测时结果显示出自然计时系统在准确度、精度和稳定性上比人工计时系统优越许多。徐光启据此自豪地指出,“臣之前疏所云‘定时之本,必准于天行,昼测日,夜测星’者,此也”。(27)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9页。
徐光启将测星定时作为计时基准并加以实施,体现了其计时理论的深化,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7世纪欧洲传入的凸凹结合的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放大倍率约为30倍,恒星视亮度增加(可见星增多)且望筒内安置有可定点的十字叉丝,便于夜晚测量恒星赤经以推时,大大提高了天文计时的精度。传统圭表、晷仪计时在读数上存在较大误差,浑仪环圈套迭,观测读数易被遮挡。尽管郭守敬简化仪器创设简仪,观测精度有所提升,但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仪器操作更加简便,计时精度相对较高,可以“随地异测,随时异用”,(28)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4页。使得天文计时技术得到了质的提升。这些,都为徐光启学说的实施提供了支持。
测星定时的实现是将恒星时间转换为惯常使用的太阳时间。“任测一星距子午圈前后度分,又以本星经行与太阳经行相加减,得太阳距子午圈度分,因以变为真时刻。”(2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38页。但恒星在白天无法观测,且“我国位于中纬度地区,许多恒星在一天中会有很长时间处于地平线下,选用这样的恒星会给时间测定带来很大的‘盲区’”。(30)王玉民:《明清月晷星晷结构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271—292页。因此,徐光启采用“昼测日,夜测星”来满足天文测时需求,“据法当制造如式日晷,以定昼时;造星晷,以定夜时”。(31)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5页。徐光启按计时原理为计时仪器划分校准等级,运用“准表、准仪、准针”中的一种仪器,“以造日星二晷,又因二晷以较定壶漏”,(32)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页。以此达到计时的精确和统一。
1612年,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传入了可测时刻的星晷,又名“时晷”。星晷由两个叠加的圆盘组成,盘面刻有天体坐标系统和节气时刻分划线,可随季节调整两盘相对位置。徐光启指出,使用重盘星晷可以帮助降低恒星测时的系统误差,因为明末时北极星已去极三度多,“《周官》旧法不复可用。故用重盘星晷……依近极二星用时指垂权,测知天正时刻”。(33)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页。1630年徐光启就用星晷测候月食时刻,观测前按当地日躔数据校准星盘位置,将星晷直表上左右两点分别对准北极附近的两颗恒星“勾陈一”(小熊座α)与“帝星”(小熊座β),星盘坠线即可指示出时间。由于极移,星晷测时从帝星转为天枢(纽星,鹿豹座32H)后,徐光启又将其定为勾陈大星(小熊座α)。(34)参见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
(四) 徐光启对定向的认识
漏刻计时需与天文计时对准校正,因而要选择校正基点时刻。中国传统历法计时起点是子正,但夜晚不适合漏刻校正,于是徐光启根据太阳运行特点选择午正校准漏刻,视定向为定时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指出,“定漏之初,必于午正初刻,此刻一误,无所不误,虽调品如法,终无益也”。(35)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午正对应的空间方位是日上南中天,要确定这个时刻,必须先确定南北子午线。古人通常利用指南针这种物理方法帮助测天仪器确定方向,明朝依循此法。如徐光启言:“设立表臬及用合式罗经,于本台日晷简仪立运仪正方案上,较定本地子午真线,以为定时根本。”(36)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5页。这也是徐光启总结“定时五事”(壶漏、指南针、表臬、仪和晷)(37)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会将指南针纳入其中之故,表现出他对于时空测量相依的一种认识。事实上,传教士如罗雅谷、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记述天文观测之法时,也都坚持这一认识,对定时与测向之法的介绍是交织在一起的。
交食测算往往是历法争议的重点,对预报结果的检验是平息争议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明朝测验交食,往往需要在多地(如北京齐化门、河北山海关和山东登州的观象台)协同测验,互相印证,因而各处仪器的方向校定就至关重要。但徐光启等明末学人已经认识到指南针形制杂乱且受地磁偏角影响,使用其测定方向、校定壶漏必然不准,“指南针……所得子午非真子午……若今术人所用短针、双针、磁石同居之针,杂乱无法,所差度分或多或少,无定数也”。(38)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徐光启后学熊明遇因之说:“壶漏之水因人工罗经之针,因物情率不能与天地之位分确合,则莫若昼用日晷与表臬,夜用星晷,是为因天而人物不与焉。”(39)熊明遇:《格致草》,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六》,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95页。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方向的物理本质及对测量思想的理解。人类对于方向的觉知和分划最早来源于地球自转,地球自转轴固定,于是人们产生了方向感,视感上表现为“宗动天”的恒定左旋。指南针因磁偏角而存在无法纠正的系统误差,还要经人工调整,故而测向直接选择天文方法,于物理原理上更准确也可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正因为如此,徐光启更偏向于使用天文方法测向,他详细论述了如何利用郭守敬所造的立运仪来校定方向,“于午前累测日高度、分至于长极而消,则因最高之度即得最短之景,此午正时南北真线也”,(40)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页。但立运仪测影时影端模糊,读数不准,不能得到精确的方向。加之,明朝观象台原有仪器的安置方向大多不准,“其正方案偏东二度,日晷先天半刻”(4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6页。。基于此,徐光启提出使用多种类型的测向仪器互相参验以校正方向,“依前仪器表臬南针三法,参互考合,务得子午卯酉真线”。(42)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页。
徐光启的测向理念比之前人有诸多创新。他指出测时与定向的高度相关性,并论述了指南针定向的不可靠,因此需要通过天文方法才能准确测向。在考量现实物质条件后,他提出了折中方案:使用多种不同测向原理的仪器相互参校、综合比较,避免单一测向方法的不足。但这种复合仪器综合测向的方法也存在问题,它缺少对各自误差量级的考量,因而不能确定综合测向后,误差是被消解还是叠加得更多。在缺乏标准数值验证的条件下难以定量判断复合测向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徐光启指出了正确定向的重要性,并重视天文测向方法的应用,这种认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二、西方计量概念的引介与阐释
(一) 经纬度
中国古代一般使用入宿度和去极度来标示天体位置,通过测量星宿和交食来确定地面区域分野。随着地圆学说和西方制图学的东传,更便利的球面坐标经纬度标示法也一并传入东土。徐光启认为经纬度概念的出现对测量工作大有裨益。他基于地圆学说,将经纬度概念应用到了星图测绘和天文测量实践中。在其督修的《崇祯历书》中使用天球经纬度绘制星图,如《见界总星图》和《赤道两总星图》;使用地球经纬度进行测算,使球面经纬度形成一种贯穿全书的基本计量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天文测算中的许多争议,如交食误差和昼夜长短计算问题,“交食之法,既无差误,及至临期实候其加时,又或少有后先,此则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经度也”,(43)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8页。“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地轮经纬,以定昼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无多寡先后之数”。(44)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页。徐光启对经纬度的发展脉络及意义有着相当准确的叙述,他指出中国古历大多只注重天经度的测算,《回回历法》中才开始讨论天纬度,唐代僧一行全国大地晷影测验之后始知地有纬度,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华才传入地球经度概念。于是,他根据天文原理和经纬度的现行测量方式总结出经纬度的测量特点:“上天下地各有经度纬度,测天则经度易,纬度难;测地则经度难,纬度易。”(45)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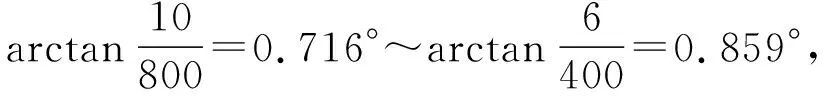
古代测天体纬度须先定北极点和子午线方向,再测极距,或测子午圈上两天体的高度差,换算出极距差,由已知天体的纬度换算出另一天体纬度。徐光启已经指出北极点的漂移会影响子午线方向的精确测定,且蒙气差也会导致观测的纬度比实际值高,致使测天纬度更加困难。不过,《崇祯历书》中借助几何球面三角学介绍了测量天体纬度的新方法:先测定赤道经度,在冬、夏两至测天体上中天时的地平高度角和距极高度角,通过球面三角学换算成赤道角,再用所测经度和高度角换算得到天体纬度。从操作难度和观测时程来说,测天纬度比测天经度难得多,因而古代的“治历名家大都于列宿诸星,有经度,无纬度”。(50)徐光启:《治历缘起》,徐光启编纂, 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第1614页。
西方地球经纬度概念的传入极具意义。徐光启指出,西法所推天文数据与《大统历》有明显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测算没有使用地球经纬度,“数万里外,地度经纬,亦各参差,牵彼就此,自多乖迕”,(5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4页。因此,他强调进行历法测算时应考虑地球经纬度的影响,并准确测定各地经纬度。测地纬度可以通过冬至、夏至测太阳高度角或北极出地度得到。而测地经度则相对困难,因为测地球经度需要测两地的东西弧线距离,或通过即时通信技术测两地天象变化的时间差,二者在明末的测量条件下均难施行。因而徐光启推荐使用西方月食法来测地球经度,即在各地同时测量月食的亏复时刻,通过各地的观测时间差换算得到地球经度差,并以北京作为零度经线换算出经度值。(52)详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0页。但这需要能准确清晰地观测月食全过程,对天气和仪器的要求很高,而明末钦天监使用的望远镜数量并不多,各地观测月食仍只能使用肉眼,测量结果比较粗疏。明末建基于地平观的月食理论,粗略的观测方法和粗疏的仪器精度,短缺的财力、人力,都不足以支撑各地精确的月食法测经度活动的开展。因此,徐光启只能根据《广舆图》并使用几何比例方法,约略推算出明朝十五个重要省直的地理经度值。
(二) 里差与时差
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奉命设局改历,他延请传教士入历局参与编撰历书,绘制图表,全面吸收西方天文学知识。《明史》特别指出,崇祯四年(1631)“十月辛丑朔日食,(徐光启)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5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5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册,第6494页。徐光启从西学的角度阐述时差与里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后世对天文大地计量的理论认知。
1. 时差关键问题的辨析
时差是历法中因月亮视差引起的对日食视食甚时刻与定朔时刻的经验修正值,唐《宣明历》将视差引起的时间差改正定名为时差。(54)参见陈久金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明代天文学中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时差符号判据是:日食时差和太阳距午时角有关。朱载堉(1536—1611)的说法是:“日中仰视则高,日暮平视则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见早,食于中后见迟。是故有时差。”(5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25页。徐光启基于其丰富的西方天文历算知识背景,提出将太阳赤道运动影响的距“时”改为黄道运动影响的距“度”,并说明日食只有发生在黄道九十度中限(黄平象限)才没有时差。“日食有时差,旧法用距午为限,中前宜减,中后宜加,以定加时早晚”,(56)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8页。“时差旧法以为论时……本局以为论度。则黄道九十度限是也。时与度,有时而合,有时而离”。(57)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85页。也就是说,时差应当是以太阳的黄经和时角为自变量的二元函数,而此前的时差算法则只考虑时角,完全忽视了黄经变化对时差的影响,因而是一种有缺陷的算法。(58)参见曲安京、唐泉:《中国古代的日食时差算法》,《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5—30页。
但传统历学民间代表魏文魁不赞同徐光启的说法,他驳击道:“日食法谓在正午则无时差,是也……所谓时差者,言旦夕也,不言距度也。”(59)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82页。也许这种“以黄道九十度为时差中限”(60)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6页。代替午正为时差符号界点的认知,让习惯于日食时差基于赤道计算的时人难于理解并接受,徐光启便从时差原理上给出了解释:“时差一法,但知中无加减,而不知中分黄赤……时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黄道限东西各九十度之中也。”(6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32—533页。意思是时差计算本就应以黄道正中而非赤道正中(对应午正时刻)立算,“独在黄道中限,乃无变差;虽食午正,而在中限左右,则亦有之,故曰东西时差,不以午正为限,以黄道九十度之正中为限也……无变为有,人多不觉,然古史所载亦有食而失推者,职此之故”。(62)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88页。徐光启对日食时差“中限”关键因素的提取、辨析及对黄道因素的考量,促进了本土日食测算的精确化和几何化发展。
2. 里差问题的提出和重新定义
崇祯改历过程中,西法的全盘引入招致了传统历法学者的批判。墨守旧法的魏文魁就率先向采用西法的徐光启发难。二人的往来论辩中有不小的篇幅涉及了对里差相关问题的争论。比如,二者关于郭守敬《授时历》回推的日食数据是否符合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429)的日食记录意见相左。徐光启认为郭算与记载不符,是因为“南宋都于金陵,郭历造于燕中,相去三千里。北极出地差八度,日食分数,宜有异同矣”,(63)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79—1780页。即推食二地分别在南京和北京,若用里差方法换算,二者便可相符。徐光启就此提出里差问题,里差是“计里而定”的异地天象差异。徐光启按纬度和经度将里差分为南北里差和东西里差,尤其注重对于东西里差内涵的阐释,他所论述的东西里差有别于传统里差定义,是其基于传教士传入的地圆学说、经纬度概念重新阐释的,即由地球经度差导致的地方时之差的意涵,“特缘地有经度,东西易地则先后时刻亦随处不一”,(64)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1页。“只因东西相去数万里,交食时刻早晚相去约二十七刻,历家谓之里差”。(65)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页。
事实上,里差算法并非徐光启新创,元朝耶律楚材(1190—1244)在撒马尔罕编撰《西征庚午元历》时,就特别创制了“里差”算法来修正相隔遥远两地间的天象时刻差异。但耶律里差是为了消除西域月食时刻与中原历法推算结果的差异而创造的修正算法,其内核架构仍然是基于传统宇宙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地平观念,并非如徐光启的里差诠释那般依托于地圆观念。耶律里差在根本上与地平观念相矛盾的事实,历经三百余年也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挖掘探究,这在逻辑上是难以理解的,但若把它放在传统的中历解释语境下思考,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中国传统历法中已然具有十分详备的月食解释理论,此说中的“月入暗虚,天下尽同”,“景之蔽月,无早晚高卑之异,四时九服之殊”(6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26页。等现象也为国人所熟知。因而明人认为耶律创制的“隔几万里之远仅逾一时”(6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5,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3页a。的里差是依附于传统月食理论下的一种修正算法,里差现象与传统月食理论没有实质矛盾,更遑论探究二者相悖的根源。例如明嘉靖陈霆就认为里差并非实际现象,“乃占步之一法”。(68)陈霆:《两山墨谈》卷12,明嘉靖十八年李檗刻本,第6页a。但明人在观测实践中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天象异地时差,但他们只归咎于各地计时上的偶然误差,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在月食计算中人为地忽略各地月食时刻分数的不同,只取整数,过于遥远的两地,则使用耶律里差算法进行修正。而其他如北极出地度、昼夜时长等历算参数“俱以京师为准。参以岳台,以见随处里差之数”。(6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22页。总而言之,古人关于里差的认识由于缺乏地球观念是知其果而不知其因的,无法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70)参见关增建:《地球观念的传入及其对中国计量发展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第52—57页。
利玛窦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中蕴含的地圆说在明末士人中广泛流播,部分儒士通过透析地圆学说与儒学知识的相似性,将地圆作为传统知识内容的增补而接受。(71)参见王静:《“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改历选择与圆融应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第93—99页。为了促进时人对地圆结构下里差内涵的理解,徐光启寓西于中,将地方时之差的含义注入到传统里差概念中,以便里差概念能顺利地与地圆说相适应。他赓续传统依地理位置分里差为南北和东西,将“千里互差一时”改为“南北里差……论北极出地若干里而高下差一度”和“东西里差,论七政出入亦若干里而迟速差一度”。(72)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86页。徐光启并未给出明确数值,虽然利玛窦已据西方宇宙数据及意大利与明朝的尺度,换算出天球一度对应二百五十里地长,并给出东西经度差30°两地差一时辰的结论,但徐光启为了更加审慎稳妥地推进西学,他认为应当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实测来检验理论和数值,以取信时人。但彼时明政府疲于应付战祸,已无力组织人力物力验证此说,徐光启便没有贸然使用,只是在定义中用度数差代替传统定义中的时间差来表示南北里差,用日行赤道一度换算出的时间计算东西里差,给后人留下了探讨和实证检验地圆和地方时之差内涵的余地。
徐光启吸收了西方地理经度差导致的地方时之差后,还巧妙地总结了日食中的里差规则,“日食随地不同,则用地纬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经度算其加时早晏”。(7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531页。这样的总结既兼容中西又逐渐将东西里差过渡到时差上,深刻地体现了徐光启“会通”中西的思想。魏文魁对此还颇有疑义,但徐光启通过各地日食观测实例一一批驳了魏的质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罗雅谷等传教士已在《崇祯历书》中使用西方“东西时差”的说法,来表述地方时之差的实质意义,(74)详见罗雅谷:《日躔历指》,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1页。但鉴于时差概念背后所蕴藏的地球观念比较颠覆传统,时人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徐光启便沿用中国传统“里差”概念以顺应本土的接受习惯。因此他称“变差法”为“历中玄指”,并对本土接受的难度大发感慨:“此理精微,盖必千百年积候,千万里互证,方能推究。若骤语之,虽聪明绝世,未易悬晓其然不然也。”(75)徐光启:《学历小辩》,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6页。
关于里差的测验方法,徐光启也给出了建议,他认为应当使用精密仪器在各地观测月食时刻,比对校正后确定经度方向上的里差值,并作为后续天文测算使用的标准数据:
今所以必推分数者,盖臣旧年九月原疏内称里差一术,东西时刻随在各异,必以地之经度为本,非从月食时测验数次不能遽定其数,故依法细推分数,正欲得其差殊,以为后来根本。(76)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0页。
徐光启关于里差测算的设想在清初得到了执行。康熙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活动,经实测开列出了各省市北极高和东西偏度,并测绘了全国地图,地球观念和经纬度概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受和应用。得益于徐光启在西方天文地理理论基础上对里差的重新定义,国人对地圆学说下的里差认识逐渐清晰,促进了后世天文大地测量活动向更加精确化的方向发展。
结 语
徐光启提出了关于计时基准、测向方法、经纬度、时差和里差等天文计量相关内容的重要认识。他注重计时背后所蕴含的根本问题,开启并深化了明清学人对天文计时标准和内涵的认知。时间精确校准的前提是方向的准确测定,徐光启以此为切入点从原理上探究计时和定向问题,将时间和空间测量统一了起来。由于物理测向天然不准,天文测向因仪器和环境条件而不精,徐光启进而提出综合各种类型仪器测向的方案,其出发点是符合计量误差理论的,但囿于物质基础未能深入探究各类误差的数量级。可见,徐光启的测向方案更多是基于定性方面的考量,未能超脱时代知识基础的局限。
明末西学东传,地圆学说和经纬度概念得以进入中国。徐光启借改历之机延请传教士供职历局译撰西学,他十分清楚新的计量观念、术语和表征体系对于本土探究自然哲学知识的巨大助力,因而不遗余力地引介和应用经纬度等概念和测算方法。在明晰中西方天文大地图景、计量名词和测量方式的各自演变脉络及特征后,徐光启得出了天地经纬度测量难易程度互换的准确论断。这体现了他兼顾计量理论和实践条件的双重观照与全局意识。在洞悉了中西天文大地观念和天文历法误差测算的本质差异后,徐光启进一步阐明了日食时差和里差的原理及二者对天文测算精确度的重要影响,并基于西方地圆学说和地方时之差现象,对传统里差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以期实现里差内涵的中西融合,这也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会通”理念。概而言之,徐光启对计时定向问题的深刻阐释,对西方天文地理概念的积极引介,使得明末中国计量理论得以深化的同时,又注重和西方计量接轨,为我国计量的近代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